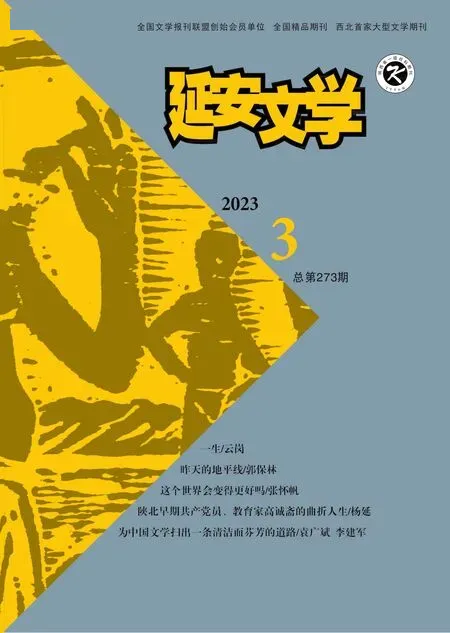过 年
2023-02-20徐海楼
徐海楼
一
东北过大年是从腊月三十早上开始的。各家各户就像事先沟通好了一样,吃过早饭,第一件事就是用白面打浆糊,然后贴春联。
贴春联这个活儿需要速度快,没有经验的人万万不可尝试。一旦第一次粘贴不成功,就会将对联冻变形,贴出来皱皱巴巴,这在人们的意识里是不吉利的。所以,这时候无论看见什么人,都不要精神溜号、不要多说话,礼节上用于应付的大多就三个字:过年好!回答也简单:过年好!男人贴春联,女人则准备饭菜,力争让过年的菜丰盛点,吉利点。
每逢佳节倍思亲!李永老汉老早就想去看看大儿子跃进,但一直没能成行。不是二儿子跃标没空,就是老姑娘跃清事儿多,顾不上陪爸妈去。你说又不是当乡长县长,咋还就那么忙呢?
天还没透亮,李老汉和老伴就早早起来了。双双八十好几的人了,觉轻,躺不住。李老汉去外面院里把昨夜今晨下的雪打扫干净。瑞雪兆丰年,对农民来说,是个好兆头。看到这白雪,就想起大跃进,勾起了他的伤心事。老伴在炕上把被褥拿过来,撤下旧被罩,哗啦一抖,装起来,依规矩到了初三或初六放水的日子再洗。剩下的被瓤子换上新被罩,抻直,用手摩挲平,摞起来,溜下炕,脚趿拉着鞋,点着灶坑,收拾下屋子,㧟碗白面,刷锅打浆糊,过年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今天年三十,一会儿跃标和跃清全家都过来,贴对联,缓冻秋梨、炒瓜籽、花生,准备各种各样的菜,煎、炒、熘、炸,一通忙乎,做一大桌子可口的菜,跟李老汉和李老太太一起过大年。跃标住在村西边,跃清在村北。李老汉和老伴与他们分开住,一家一个院落。李老汉家在村东老房子里住,平时过来过去。跃标和跃清不止一次要把爸妈接自己家去,又不是管不起,怕叫人说不孝顺,戳脊梁骨。可李老汉老两口不干,自己住着方便,怕住到一起,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整得一天扭头别棒多没意思,再说也吃不到一块去,老人愿吃稀粥烂饭,而年轻人愿吃硬点的饭,有嚼头,味香。去那干啥,还是自己单过舒坦。况且,这里有跃进的魂。
李老汉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又一遍,再巡视两圈,连个小棍树叶也不放过,孙子重孙一大帮,别把娃儿们绊倒。回屋把压岁钱用红纸一个个包好,放枕头下,好给孙子重孙子。没想到,一眨眼自己就当太爷了,真是岁月催人老呀,让这帮娃娃一茬一茬就把人撵老了。刚才扫雪的时候,肚子又一阵一阵地疼,拄木掀站一会过劲儿了。歇缓了一下,好些了,继续忙。一头雪白的头发,一会儿东屋,一会儿西屋,一会儿上房,一会儿仓房。门吱扭扭、呱嗒嗒响个不停,人也忙了不停。这套院子,是他和老伴亲自盖的,每处旮旯都流下老两口的汗水,所以特别亲切。
那时候他们年轻,有大把力气,干啥活都不愁。一栋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二十多天就盖成,随心所愿东西两开门,西头准备留给跃进结婚做新房,东头自己和老伴住。家家如此,水没来先筑坝,省得到时候抓瞎。
这座房子里,五八年“大跃进”生了大儿子,李老汉一高兴,给大儿子取名跃进;六零年“低标准”挨饿生了二儿子,取名跃标;六五年“四清”生的老姑娘,取名跃清。接着,像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似的,老伴不知作了什么病,立马打住,再也没怀过。
其实,仨孩子,也挺好的,儿女都有,又不缺项。老伴就一个一个拉扯。喂奶,换尿布,做衣服。开始孩子扶窗台走,后来硬实了,能撒开手,就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转悠,再后来小院装不下,就去大门外,老伴像老抱子一样盯着、护着,生怕一眼照顾不到,有个闪失。晚上被子里也不老实,一会儿你踢他一脚,一会儿他掏你一拳。老伴天天愁,这个的鞋破了,得做,那个的裤子开线了,该缝。那年头没钱,上学没书本钱了,东挪西借,说好话,赔笑脸。一窜儿,最小的老姑娘也奔六了,孙子重孙子都有了。想想,这日子真不经过呀。
不知不觉间,转悠到西屋,看到跃进走时穿军装的相片,挂在墙上玻璃相框子里,就愣了,要过年了,又想他了。寻思,过完年,说啥也要去看看他了,不能老依着跃标和跃清了,得自己做主。说忙,二儿子办了个大型养鸡场,雇了三十几号人,往里进饲料,往外批发鸡蛋;老姑娘开服装加工厂,规模不大也不小,一年四季都没闲的时候。
这把身子骨,就像墙上的挂钟,发条没劲了,随时都有停摆的可能。今年冬里似乎就不比往年强,腰酸腿疼,手脚一阵阵发麻,毕竟老了。七十三、八十四是坎儿,过年就八十四了,坎儿很难跨过去,李老汉忌讳这事,好几回跟老伴提起,老伴讥讽:“怕死了咋?”这个老东西!用话臭屁人,死有那么可怕吗?怕啥死?彭祖活了八百岁也难逃一死,只是心愿未了……
二
跃标领媳妇先推门进来,大包小包一大堆,又是酒又是肉,还有一条三十多斤的大鲤鱼,在袋里直扑棱儿。李老汉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鲤鱼,以前看过的都二、三斤跑长趟。跃标和媳妇放下东西,转身又去外面,从车的后背箱里抬下一大箱鸡蛋,李老汉见了就说:“上次拿的还没吃完,怎么又整来一大箱,真吃不下了,上顿吃下顿吃,就连放屁都一股鸡屎味。”
听了李老汉的话,跃标和媳妇哈哈大笑,儿媳妇擦擦笑出的眼泪说:“看俺爸说的,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老伴在一旁拿眼剜了一眼李老汉,说:“别听他胡咧咧,他不吃我吃!”
李老汉经老伴一呛,也知道说错话了,伤了儿子儿媳的一片孝心,戳在一边,不再言语。少顷,李老汉又问:“鸿君呢?”
跃标回答:“在鸡场呢,跟他说了,随后领媳妇和孩子过来。”
鸿君是李老汉的孙子,大学毕业后在县土地局上班,看自己的爸爸经营一个大养鸡场忙不过来,索性辞掉工作,领媳妇和儿子回到村里,和爸妈一起养鸡。年收入百万的养鸡场,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几年时间,变成一个年收入千万的现代化养鸡场。跃标一看鸿君有管理的天赋,就把养鸡场上上下下全交给他打理。
跃标从兜里摸出三千元,交给李老汉。李老汉不要,说我不缺钱,你留着吧。跃标说:“不缺也拿着,过年了,儿子孝敬您的不是?”
李老汉就接了,卷到一起,放进装钱的扁匣里,插上盖子。
不一会儿,孙子鸿君领着媳妇和儿子也来了。鸿君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都褪掉毛开完膛了的,白白净净的。
李老太太见着重孙子,伸手就揽在怀里,左一口,右一口,亲不够。
胖墩墩的重孙子小嘴说道:“祖太过年好!”
“哎!”老太太应声而笑,再来一口。
一句“过年好!”,把老太太乐得神魂颠倒,泪水涌出来,见又一辈人,格外亲近。
这时,老姑娘跃清和家人也呼呼啦啦进来。跃清女婿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李老汉和老伴见他长大,仁义且心地善良,就把跃清嫁给他,给盖了房,结婚的一切费用,李老汉全包。
老姑娘挑上好的面料,给爸妈一人做一套新衣服。女婿又把二十年茅台陈酿和法国葡萄酒拿出来,放在柜子上。
李老太太冲老姑娘说:“以前做的,你爸我的还没穿坏,都在柜里放着,老高一摞了。”
跃清笑着说:“那是平时穿的,这不过年了吗,得穿新的!”
李老汉接过话茬儿说:“这要是和过去比呀,天天过年,上顿鱼下顿肉,都吃腻了。”
李老汉的屋里,一下装下这些人,没几回,孙子、孙女、孙子媳妇、重孙子们,呼呼啦啦,屋里院里热闹极了,你呼我叫,爷爷长,奶奶短,弄得李老汉老两口感觉像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似的,一直抿嘴笑个不停。
三
老太太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花生、葵花籽、苹果、糖,一样一样叫吃。噢,差点忘了,扭身进里屋,又端出些用杏和沙果做的果脯,自己加工晒的,又酸又甜。老太太抽空偷偷去地里挖一筐地瓜,一个一个洗净,坐在门槛上转圈削皮,晾干。不偷去,怕儿孙们看到不让。把地瓜切成段,晒干,多次翻动,成为地瓜干,再用地瓜干打磨成地瓜面,掺到白面里包饺子,特别劲道。
老太太娘家是山里刘家村的,离这十几里。十五岁嫁过来的。爹娘早就没了,哥哥和姐姐也都走了。几个侄子在,每年过了初五,到初六叉伙过来,进门东西一放,呼啦啦跪下,扑噔扑噔磕头,姑长姑短叫着。喝一顿酒,每人塞下三百二百,晃晃悠悠走了。平时,偶尔也来,这个的孩子结婚了,那个的闺女生孩子了,跃标开车拉爸妈去,把李老汉和老太太放在上坐正位,接受敬酒。李老汉和老伴不善喝酒,不真喝,抿一抿了事,有时也喝茶,做比成样,就是那么个意思。
娘家的村子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新农村建设,房子、院落、大门及铁杖子都一样。前年,李老太太去老侄子家时,走到村部停下,找找那棵歪脖子松树,就知道侄家。对那棵树印象深,看了大半辈子,小孩子都爱往上爬,自己小时候也天天往上爬,坐到树杈上唱山歌。
李老太太当时地主成分,学校哪有她的座,只收贫下中农家的子女,导致她一生目不识丁。一个成分可把人坑死了,二十多岁也没人敢娶。恰巧,李老汉家里穷,二十多岁也没娶上媳妇。经人撮合,两人便走到一起,谁也别嫌谁了,凑合将就过日子。
娶她也简单。生产队吃大食堂,中午吃饭之前,队长讲几句话,宣布二人正式结为夫妻,坐下闷头吃橡子面窝头,饭毕,李老汉把她领回家。路上,李老汉在前头走,李老太太低头害羞跟在后面,心里滋味,五味杂陈。想起来,还怨恨他连手都不敢拉一下,也怨自己,凭什么就像小狗一样跟来,都是命。如今,再想想,一肚子怨气早已不复存在,老夫老妻这么多年,子孙一大帮,围前围后,谁有这等褔气?
四
有孙子鸿君,贴对联他全包了,屋里屋外跑,过道门、房门、大门、仓房门、鸡架门和猪圈门都贴。最可笑的,空猪圈里,一头猪没有,也得贴上肥猪满圈,图个吉利喀儿。从里到外,红红彤彤。红灯笼用竹竿挑着,挂在了院门口上,一边一个,扯进电线,咔嚓,灯泡瓦亮,红彤彤的灯笼鲜亮起来,年,真像个年样了。
鸿君忙乎个不停,身后像尾巴一样跟着一帮小崽子,呜嗷喊叫,把年的气氛抬高。
跃标媳妇和跃清还有鸿君媳妇三人,在厨房张罗晚饭和年夜饭,先安排菜谱,接着按照菜谱准备食材。有的不吃姜,有的不吃葱花,有的不吃韭菜,得各个照顾到。摘菜的手忙个不停,切橔的菜刀飞舞,拌馅的筷子盆里转,擀皮的擀面杖在面板上前后滚动。手忙着,嘴也不闲。这家刚买了小汽车,那家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张家的闺女跟女婿去了美国纽约,李家的儿子去南方打工一年挣十来万。
孙子、孙女、孙子媳妇们的手机一直在响,这个嘀嘀响两下,那个嘎嘎叫三声,全是拜年的微信,偶尔也有拨打电话的,全是“过年好”的话语。看看,嗒嗒摁按键,赶紧回复。李老汉看儿孙们个个举着手机,感慨这个时代的事,就像过去讲的神话一般。
厨房里做菜的三个人,忙得热火朝天,煎、炒、熘、炸,一盘子,一盘子菜陆续出锅。糖醋鲤鱼、芹菜炒肉粉、牛肉拌黄瓜、猪头焖子、萝卜豆腐丸子、老醋海蜇、拔丝苹果、香菜豆腐干、烀猪爪、红烧鲤鱼,还有小生菜小萝卜,都是鸡鱼肉蛋,吃点鲜菜调调口。菜是精心设计,各有寓意、名堂的,猪爪代表抓钱,鲤鱼代表鲤鱼跃龙门,拔丝苹果代表平平安安,萝卜代表查缺补漏,生菜代表生财。你说这人,把每道菜名都往吉利词上贴,粘不上边用谐音。最后一道萝卜钱饨腊肉,这是祖上从关里带过来一道名菜,每逢年节,必不可少的。这道菜谁做出来,跃标都吃不好,直摇头,没有老妈做的味道。吓得仨人谁也不敢做,怕跃标矫情,只得请老太君披掛上阵。
老太太从厨房出来,见老头子没事人一样看几个最小的孩子玩“羊了羊”的卡片,就问:“你事办利索了吗?”
李老汉疑惑地问:“什么事?”
李老太太剜了老头子一眼:“小脑萎缩成个傻子,上午不给,还得下午给吗?”
一句话,提醒了李老汉:“看我,光瞧几个孩子了,你不说,还真忘了!”说着话,伸手从枕头底下掏出来一沓厚厚的红包,“来,给你们发压岁钱喽!”
几个孩子一听有压岁钱,欢呼雀跃:“好呀!”“好啊!”拍着小手,跳起脚。
发压岁钱是传统习俗,压岁钱是年味咏叹调里一个奇妙的音节,是上下代或隔辈之间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手段和途径,也是一种凝合剂,能使家庭和睦生活美满皆大欢喜,这也许是压岁钱能延续至今永远传承下去的缘故。
李老汉先从跃标和跃清的孙子孙女发,一人一个红包,里面包了五百元钱。跃标两孙子接过压岁钱,说道:“谢谢祖太!”
李老汉高兴地应声:“唉!两淘小子!”
接着,轮到跃清的孙子和孙女们,两孩子比鸿君家的小,接红包却不含糊,接过揣进小兜里,里一半外一半,嘴里却没忘谢:“谢谢祖太!”
发完这一拔红包,下一拔该是鸿君这一辈。有鸿君和媳妇,还有跃清两儿子和媳妇,听李老汉唤领压岁钱,乐颠颠跑来。李老汉先跟他们说明:“你们都是大人了,红包自然而然比那几个小孩崽多些,但也不多,都别嫌少。”
“不嫌少!不嫌少!”鸿君媳妇率先开腔,其他人也都附和:“不嫌少!”
李老汉说:“这我心里就有底了。”说着,才把压岁钱一个一个发出去。
其实,老人给小辈的钱叫“压祟钱”,而晚辈给老人的钱才叫“压岁钱”,意思期盼老人长寿,但现在一般都叫压岁钱。
李老汉发完两代人的压岁钱,又叫二儿子:“跃标,你过来。”
跃标在外面说:“爸,啥事?你说!”媳妇看他没事却没动弹,就说:“爸叫你有事,麻溜过去得了,磨蹭啥?”跃标瞪了她一眼,不情愿过去了。
李老汉从兜里掏出三千块钱,往跃标兜里塞:“你妈把我说了,儿子给钱你就要。你的钱拿回去,我不要。”
跃标侧着身子拒绝,抢过钱,一边往李老汉兜里揣,一边说:“看您,收了的钱,哪有退回的道理?给您的哩,爸,过年了,儿子孝敬你的!”
李老汉执拗地说:“我不缺钱,你妈我俩都有工资,八十多岁国家发的还多呢!都花不完。”稍停顿一下,又说:“不但不要,我还得给你发压岁钱哩!”
跃标兴高彩烈地说:“爸,你是咱们家的大家长,给的压岁钱我要!”伸手接了李老汉递过的红包。跃标媳妇、跃清和跃清女婿也都纷纷领了压岁钱,喜笑颜开。最后,李老汉手中还剩一个,揣在上衣兜里,把一家人看得直愣神。
鸿君走过来从兜里掏出来五千,说:“爷爷,我爸的三千你不要,孙子这五千你可不能拒绝,必须收下。”
李老汉笑着对孙子说:“谁的我也不要!你们家大业大,花钱的地方多着哪,再说了,米面鸡鱼肉蛋都是你们拿来的,衣服和鞋都是你老姑包干,你奶我俩还要那么多钱干啥?没地方去花。”
鸿君哪容分说,把大大的红包,强行塞进爷爷兜里。
五
平常,李老汉屋里显得特别宽敞,就他和老伴,空荡荡的,肃静,连个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今天,四代人聚在一起,略觉挤巴,你碰他胳膊肘,他踢我脚后跟,走路都得加小心。
把客厅收拾收拾,放两张大桌子,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人喝白酒、啤酒、色酒,各取所需,愿喝啥就喝啥,随便,小孩子都一色喝饮料。
开饭之前,李老汉没忘先拿张靠边站放到院里,摆上香炉,插上香,又放上四样菜,杯子倒上酒。李老汉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一作揖,然后跪下磕头,祈求四方神灵保佑儿孙们家家平安。跃标一家也过来,跃清一家也过来,轮番磕头。李老汉又前头领着到上房,在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上,点上香,斟酒,洒酒,跪下磕头、作揖,祈求保佑子孙,平平安安。跃标、跃清一家家的,又跟着跪下,按程序一步一步走,这是每年必做的功课。
磕完头,李老汉问,你大哥那烧上香了没?老大在西屋,上房是祖宗。跃标说,上了。
“一会儿,小的们就过去给他磕头,过年了。”李老汉对跃标说。
“嗯!那是一定的!”跃标应声间,看到爸爸眼里浸着泪。
跃进的大相片在西屋里摆着,照片前放着香炉,香炉前放着饺子放着菜。一个酒杯,一双筷子,孤孤单单。小辈们从上房过来,纷纷跪下,磕头,作揖。
跃标对着大哥的相片说:“大哥,过年了,你一个人在那面多吃点好的,多喝两杯酒,解解冬天的寒冷……”哽咽在喉,再也说不下半句。
跃进是从部队参加援藏医疗队,一天夜里,牧民老乡得了急病,他骑马连夜去诊治,途中,发生雪崩,连人带马埋在雪山底下。这是部队和武裝部领导来家时,李老汉和家人才知道的,当时眼前一黑,晃了几晃,差点晕过去,幸亏跃标搀扶,才没倒下。
李老汉三个孩子中,数跃进长得好,高个儿,大眼睛,一笑两酒窝,说话文质彬彬。高中毕业后,本来村里推荐他到县联社上班,可他自己非要当兵。报完名,体检过了,部队接兵领导来一看,一眼就相中了,换上军装,走了。走的时候,抱着爸妈的头说:“爸妈,您们把我养大了,我却要离开您们,不能孝敬您们,原谅我吧!”
嘿嘿!李老汉给跃进整整军装说:“好孩子,家有跃标和跃清哩,放心走吧!”话虽这么说,跃进才走出院门,老两口不忍再看了,倏然转过身,胳膊左一下,右一下,抹起眼睛了。
李老汉听武装部人来家送功勋奖状的领导口中得知,说跃进被雪崩埋在雪山下,老两口哭了半年,眼泪都哭干了。
李老汉对跃标和跃清提出过了年,去看看跃进的要求。要去看看,说不去看看,可能这辈子就再见不到他了。跃标和跃清答应了,成。过了年,暖和暖和就去,咱从坐高铁去,快。
菜已端上桌,摆好。跃标对儿子说:“买鞭炮了吗?”
鸿君笑着说:“买了!在车里呢!”
跃标问:“多少响的?”
鸿君说:“一万响的。”
跃标就说:“要开饭了,赶紧放去。”
“好嘞!”鸿君一溜小跑,出去,身后跟了一帮小孩。放鞭炮,是孩子大人最爱看的,过年比谁家的鞭炮响数多,时间长。商店一万响是最多的了,假如有两万响,鸿君绝不买一万的。鞭炮劈劈啪啪响个不停,火药味充刺空气中,年的气息升高。
响声尽了,一家人围着饭桌坐下来,拿起筷子,倒酒,夹菜,吃年饭。吃罢后,跃标媳妇、跃清和鸿君媳妇还要去准备年夜饭。
李老汉夹了几筷子,肚子那里又一咬一咬地疼了,但忍着,没说出来。说出来,大过年的,怕叫一家人担心,弄得谁也过不好年。放下筷子,推说去茅房,走出屋。进茅房,哗,就吐了,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手扶着墙,站住了。咬咬牙,挺了挺,过劲了。使劲摁了摁,不太要紧了。跃清喊:“爸。”孙子外孙也喊。“唉,你们吃吧,别等我。我一会儿就吃。”噢!小辈们都放心了,说说笑笑,边吃边喝。
李老汉寻思,秋天的时候,只是觉得肚子比起以前来,稍稍有那么点不舒服,以为没事。劝自己,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头疼脑热肚子痛。可今天的疼法,针扎似的,跟往常不一样?摸摸部位,也怀疑不出是哪,是癌症?应该就是晚期了吧?离死也就不远了。
死,李老汉不怕,谁都要死的,世上哪有长生不死之人,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这岁数,比起那些四、五十岁就走了的,也算可以了。怕的是,也许就等不到暖和了,等不到和跃标跃清一起去看跃进了。
李老汉心里“呯”的一下,不会吧?他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知不觉进了西屋,站在了跃进的照片前。看了又看,眼睛不由潮湿了,伸手过去摸摸照片上的跃进,从兜中掏出一个红包,喃喃自语说:“过年了,跃标和跃清他们都领了压岁钱,你也有份,收好了。”顿了一顿,又说:“跃进呀,我的好儿子!过完年,开春了,爸去看你!你老妹偷着和你妈说,跃标担心爸高原缺氧,引起高原反应,走不上去。无论如何,拼了老命,也得试一试!”
不知什么时候,一家人都站在李老汉身后,李老汉猛一抬头,看见外面已是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