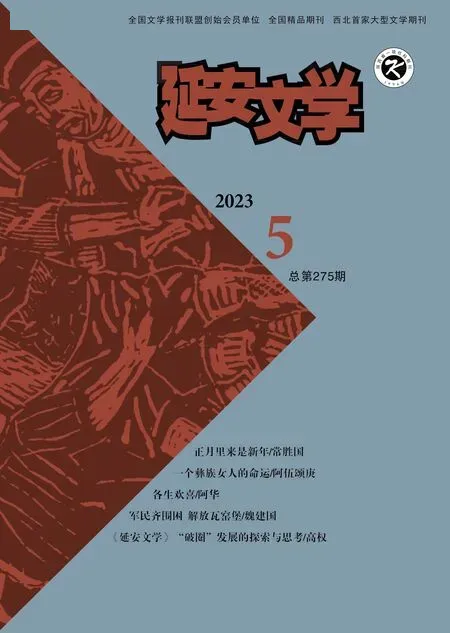一个彝族女人的命运
2023-02-19阿伍颂庚
阿伍颂庚
1
喝风,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贬义性质。当你第一次站在垭口,似乎听见鹰的叫声,或是细微的振翅声。别看身上是大红的大襟衣,其实你还是个懵懂少女,爱仰头看天,看蓝蓝的天。殊不知,你纯真的眸,已然成为那蓝天的眼。站在垭口,便见了鹰,是山鹰。是你的听觉出了问题,实际上鹰并没有叫,它静止在半空中,就像对过往无声的回放。你开始焦虑,跟数天前一样,整晚睡不着觉,夜间盗汗,午后梦魇。唯一安慰的是,像梦境一样充满黑暗与悲凄,可终将在苍苔露冷的清晨里醒来。虚妄的梦,焦虑的梦,死亡的梦,都抵不过在人间清醒一场,苦难只是那藏在皮囊以里的部分。
此刻,我记不清是第几次站在垭口,耳聪目明,却根本不可能听得到鹰的声音。如果这座山上的树不要那么让风肆意妄为,浅灰色石头和黄褐色的土质也懂得隐忍,包括土面上的草及垭口背阴处的阴生植物像少年时的我那样拥有茂盛的头发其实,我知道在思想深挖的背后是绝望。绝望和梦魇是孪生姐妹,一个喜欢在午间穿雪白的裙子招摇过市,一个爱在漆黑的夜晚与幽灵为伍。你没读过书,甚至没有名字?你当然不会深挖,你试着用善意来化解绝望,所以没有沾染一丝尘埃。可是,那喝风的鹰,叫唤的鹰,分明时时出现在你梦中的垭口上。你跟我提起过,所以也出现在我脑海的垭口上。你跟我讲鹰。它有强大的力量,“乃苏”中救人类于危难的神话故事,让我对鹰开始有了敬畏。你说,最初的人由雪变来,雪变人时,赤身裸体,鹰飞来用翅膀盖在雪人身上,雪人长大后成了彝人祖先。垭口已经够高,可我依然微微仰起脸来,因为我相信如果鹰出现,一定会是那个角度。所有的鹰留下的是同一个面孔,所有的人在鹰的眼里也会是同一张脸吗?我拥有一个神秘的童年,如果不是你神秘的故事滋养,我就注定不会是我,而会变成另外一个我也不认识的自己。我不是鹰,所有的脸在我面前都有不一样的温度。我充满诚意地站在垭口上,不是喜欢这吹落我头发的该死的风,而是想跟那天你第一次见到的鹰对眼,我想,我们彼此会在对方身上看到那时的你,是穿着大红大襟衣的你。
你不但没有名字,你还说不清楚时间。对一切过往的事物,你都习惯性称之为很久以前。那时候,在我脑海中的很久以前,最远就停留在你第一次站在垭口那天。我以为,神话故事里的鹰,就是那天你看到的鹰,它静止在半空,喝着风,叫着。后来你说,你的母亲年轻时也在垭口上见过鹰,也喜欢仰起脸来看蓝天。一道耀眼的白光,把女孩的天真和烂漫全吓没了。一个打扮奇特的男人坐在垭口上方的石头上,手里亮出令人胆寒的白光,那是一把钢刀。你的母亲想把已经来到跟前的男人推下垭口,尽管他会尸骨无存,起码不会再害人。是喜欢仰脸的天真烂漫救了她自己,才有后来的你。垭口上方还有好几个男人。你的母亲将褡裢里的黄豆全给了他们,包括心上人送的一块吊坠。你顿了顿,失落地说,在年轻时关于心上人的破碎的梦面前,吊坠算得上什么?当然,那活下来的心如死灰的烂命,又有什么用?信物和生命,失去什么或得到什么,那年代对一个女人来说,真的差别不大。
一切活着的意义,在于那只鹰。即便鹰出现过无数次,我们都不在场,究竟是谁负了谁,就像一场雨错过一阵风,没有道理可讲,纯属偶然,也可说是意外。我们知道,鹰总是要停在垭口上空的,它要活就得拼命喝风,风是翅膀带飞的胃囊。鹰是同一只鹰。对一个女人来讲,所有的人生也会惊人地相似,她们就像鹰的出现,只是前赴后继体验同一个人的生命。重复,又好像不太准确。总之,鹰出现的时候,山风一定会来,带来少女的纯净,风和日丽,世界干净得没有人烟。(那时候,我终于明白吹落我头发的并非谷底吹来的风,至于是些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比如说像梦,我根本无从知晓)
对话:关于一场世界干净得没有人烟的对话跟我毫无关系,也没有人知道这场对话的发生。垭口所在的大山,因为自始至终没有醒来过,所以就像死了一样。这场对话就发生在这里。它旁边就是高耸的阿则问山,战争年代充当过瞭望塔的山巅,此刻没有一丝风留恋,连一片云也不曾多停留一会。那些在当时所谓特别重要的事物,此刻显得微不足道。
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喜鹊?
鹰,天选之子!
可绣在枕套上的偏偏是鸳鸯,关鹰什么事?
喜鹊和鸳鸯,只是图一时兴起,鹰才是最终归宿。
……
这样的对话有些奇怪,关键还冗长。你没听见,即便听见也跟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现实生活中,你知道鹰和喜鹊、鸳鸯的区别,但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根本不屑一看。你是对的。你很清楚,人活着就是一场接力,无休无止的接力。尤其是身为女人,她们别无选择。你坦然面对现实,世间所有的磨难在你面前,就像一粒泥丸。你不说,但我知道在你眼里,还有什么苦难在生死抉择面前,比翻越横亘在两个世界的一道垭口还难以让人决断呢?
鹰从一开始就停在垭口上空,静静地待着,仿佛那才是它本来的生命状态,而飞走是它打破了歇息,开始去为某个任务而行动。我想到你跟我讲的神话,毕摩用鹰爪作法器主持祭祀,是因为鹰拥有神力,可作为毕摩沟通神灵的中介,可以增强自己驱邪请神的本领。那么,鹰从垭口飞离,我知道一定是从金沙江峡谷上空挤过,并且我知道,方向是昆明、昭通的方向。它始终肩负着彝人亡魂认祖归宗的重任。
2
大襟衣是方领的,前襟齐腹部,外罩围腰,后襟至小腿。长裤是宽大的,如果将鹰喝掉的风倒灌,你同样也可以悬浮在天际。腰围上圆下方,银质的链子在上面清脆地响着,那可是鹰喝进去的风声呢。在大红的底子上,衣领、大襟、袖口、袖中部、裤脚和围腰,都镶着花。那是象征图腾的马缨花,大红色的朵。你是纳苏,你们很高兴人家叫你们罗婺颇,所以你的衣领比别的女孩更精致好看,上面还绣着凤凰。你的衣服外面披着揉搓过的雪白的绵羊皮,除了遮风、保暖,还可供席地坐。你戴着的是绣花帽,前似虎头,后像凤尾,正前又是一朵红艳的马缨花,两侧则是花卉。其实你最珍视的是脚上的绣花鞋,有虎牙和鞋鼻,尽管跋山涉水,马蹄替你挡了许多风尘,可惜山高路远,垭口拒绝了马儿驮着它自身以外的物件翻越,哪怕她是个美丽的新娘。
同行的迎亲人是他的同辈兄弟和表兄弟,他们爱起哄,总爱拿你跟没见过的那个人打趣。你想,有这样有意思的堂兄弟表兄弟的人,肯定差不到哪里去。为了表示对父母和姐妹的留恋,你哭了三次。你的女伴们陪着你,围成一圈,边哭边唱。尽管事先排练过哭嫁,可调子对不对,你不确定。总之,你学会了女人的口是心非,隐隐地以植物为喻,怨父母,咒媒人,诉说自己不愿嫁,不愿去山高路远的地方过日子。你的头上盖着盖头,你不知道是他堂兄弟表兄弟中的哪一个,把你抱着放在背上,你感觉他们在往外走,你拼命抓住身边的一切,在你抓住门框前,你抓落了看热闹的人的杯子,在铺着青松毛的土地板上发出闷响,但没碎掉,这让你心安。你哭闹,可那些满脸被锅灰抹黑的汉子,把你轻松抱上了一匹红鬃马。当你蹬掉一只绣花虎牙鞋,听到身后抱着你骑马的人一声警告,你就怕摔下马来。出村的小路上,一股红尘淹没了送亲队伍,你的那些最不想离开的女伴们,从那天开始跟你分道扬镳。
还是垭口。在你母亲的少女时代,这里还属于那氏土司管辖的地盘。那安和卿,慕莲土司府末代女土司,一纸令下,守住了垭口和金沙江边的渡口。渡口通向四川会理方向,只有垭口是一座山通向另一座山。民国时期,红军长征经过此地,砸碎那安和卿土司大厅横匾,打开土司仓库,把粮食、衣物分给农民,还在土司府大门前的照壁上写下:打富济贫,杀官安民。红军继续北上。底层农民意识觉醒了,数百人冲入土司大院,将所有地契抄出来,在照壁前一把火烧光。这种纳苏汉子揭竿而起的反土司斗争,一场接一场,有些村的农民还饮鸡血酒,喊着“不杀土司不罢休”的口号,分两路直取多志力和新衙门。群雄并起之时,正是土匪盗贼猖獗之日。垭口,即便行人肯留下买路钱,给不给活路还得人家说了算哪。想想,你母亲那天是虎口逃生。真险!
3
你落在一个叫咱啦的村子。
我说:他肚里有些墨水,他那时在一个电站工作,尽管是合同工,毕竟也拿着“工资”,很了不起。他的枕边总是堆着一些《聊斋》之类的书,是从电站带回或是从别处借来的,它打开我的方式是从一串书名开始的。“今古抱哥!”阿哥起码认出了两个潦草字。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学会看语文课本,在这些期刊上读了许多传奇故事,包括那本引人入胜的鬼故事,我基本上能看懂比人还美的鬼,以及比鬼还恶的人。那时候,我还是个对文化不知足的小学生。我说:奶奶,我要抓背。奶奶,我要听古经。奶奶,我要一面抓背一面讲古经。其实你讲的古经实在不算高明,可我爱听,哪怕重复着讲,我仍爱听。贫瘠的大山,恶劣的自然环境,把人逼得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你的命我隐约见了,而我的命正破茧成蝶,传奇、神话、古经、鬼怪……都是不断生长的翅膀,有一天我想,我一定要飞越群山。大山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压得人接受现实,要么给人飞越的欲望。他看不上阿爸。吃饭的时候是他要发火打砸的重要时间节点。孩子没能吃顿饱饭,一天闹哪样闹嘛!我知道你说这话时毫无底气,他这么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还拿着“工资”,村里谁人不羡慕?可你呢,连替他生个一儿半女也不能够。你这一生做过最有底气的一件事,就是回到垭口那边跟亲哥讲:把你家大姑娘给我们吧,阿强那小子还不错……你阿哥知道你难做,也许出于对你下半生养老的考虑,默默地点了点头。氛围怪怪的,饭,并不香。阿爸开始往后山跑,带着砍刀和粑粑,清晨出去晚上回来。那些木头特别粗壮,拖回来时光溜溜的,横在院坝里的月光下,白森森的剥光了皮。
饭桌上的筷子原来可以跳得那样高。瓷碗也可以剧烈震动而不破碎。
他的眼睛鼓鼓的,这种青蛙眼曾经跟你说话时我也见过。他认为没有他的功劳,阿爸不可能找到阿妈,也不可能让阿爸读到高中毕业。阿爸则认为,如果当初他舍得拿一部分从电站赚来的钱打点,工作也许不会落空。最后阿爸说:没见比我还小的谁谁,只是初中毕业照样端铁饭碗!这种争吵不会有结果,随时,随地。你巴巴地看着,因为不懂男人之间的事,什么推荐上学,什么地主成分,通通都不懂。阿爸的肩上冒起高高的骨节,每到晚上就趴在床上,让阿妈用热毛巾敷。可阿爸多么满足啊,他看着满院子的木头笑了,因为在木头家族中栋梁之材还有个别名,叫做柱子。
建造新房势在必行。
他在电站工作,很少回来。你除了负担繁重的农活,还要背负膝下无儿无女的骂名。可你从不向我透露,哪怕半点这方面的怨言。你在给我讲古经。
古经:古时候,一户穷人家里有两兄妹,能卖的都卖了,仓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一天,阿爸阿妈决定把他们带去山上扔掉。阿爸说:在这儿等着,只要听到砍柴声就不要动。阿妈说:等砍柴声没了,你们才能走。直到天黑时,两个孩子等来的却是山风里挂在树梢的半片葫芦……
古经:古时候,有个贼专爱夜里偷盗。一次,三更半夜带着镰刀、麻绳出门,准备到人家地里偷麦。他来到一棵大树下,便遇到一只鬼怪。聪明的贼吓得半死,却强装镇定说:咱们是同类。鬼怪亮出又长又弯的獠牙,贼就把镰刀当獠牙;鬼怪剖腹扯出细长的肠子,贼就把麻绳拉长。鬼怪想细究,可天蒙蒙亮,只好放过他。从此,聪明的贼再也不敢偷盗,做回了良民。
古经:古时候,阿爸阿妈外出把兄弟俩留在家中。夜里有敲门声,哥哥想阻止,但弟弟已经把门打开。是一个老太婆。弟弟从她嘴里知道阿爸阿妈暂时回不来,但阿哥从老太婆身上发现了他们的信物,凶多吉少,但他假装不知道。老太婆递来零食,说:去洗澡,来跟我睡。弟弟高兴地去了,哥哥不但不洗,还把弟弟的水弄脏,这让老太婆非常生气。夜里,干净的弟弟跟老太婆睡,因为家里只有一张床,哥哥睡在大锅里。那晚上,老太婆递东西给他说:吃,吃蚕豆。接过来一看,是弟弟的指头。哥哥不敢出声,哭了一宿,为了活命第二天当没事发生。第二天晚上,老太婆亲自替他洗澡,要他一块睡。他故意尿床,老太婆非常生气,搬到大锅里睡,并让他赶紧去洗干净。哥哥早已在大锅底下架好了柴禾,出其不意地盖好锅盖,点燃。大锅里一夜翻江倒海,哥哥整晚死死按在上面。第二天早上,老太婆在大锅里化成了一摊水。然而,妖怪并没有死绝,哥哥所过之处,长满了恶毒的火麻草,因穷没鞋穿的他拼命跑,为躲避追击,不得已爬上一株高大的刺滕。他在刺滕上蹲了三天三夜,正巧有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见孩子可怜就跟羊说:让你的蹄在这里踩踏,让你的背在这里打滚。羊死伤大半,可恶毒的火麻草也失去了魔力,渐渐消失在刺滕下。牧羊人将背上的羊毛毡扔在树下,他就踩着出来。然而,因为羊毛毡通了个洞,他的脚趾有一个被残余的火麻草烧掉,从此,这种刺滕奇迹般地长出了圆圆的小果子,并得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蔷薇果。在咱啦山上,满坡满箐的蔷薇果,便是他掉下的脚趾。
4
一个家,分成了两户。
他回来,电站工作彻底放弃,原因不明。吵架,不可调和的矛盾。你已老,我还幼,咱们都插不进去。他要分家。阿妈说他是想把两个包袱甩开,我和阿哥。阿爸却赞同,私下跟阿妈说:只是可怜了他们奶奶。在那个阳光热烈的午后,在族人里威望较高的毕摩见证下,宣布分家协议正式生效。除了一点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带了很少的东西走。你那天在偷偷抹眼泪,是在场的人中唯一一个不争气的。你从来就没什么话语权,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你,我更喜欢神话故事里无所不能的你。我很清楚,你不同意,可没人要你同意。
阿爸一手建造的新房子规模不小,却四面漏风,里面还空空荡荡。火把节后,山里天气多变,我们躲在刚好站得下四口人的废弃烤烟房里做饭。顶上细雨飘飘,滴水从容不迫地滴下来,潮湿的墙角,在四通八达的耗子洞里,总有幽幽发亮的几双眼在偷窥,我归类于地底的鬼眼。有时候我想,它们不敢贸然出来,并不是因为怕我,而是忌惮于灌满每一寸空间的浓烟。
你那些翻来覆去讲的古经,对我早已失去了诱惑。我看见你找猪草,割牛草,背垫圈的干松毛,上山砍烧柴,洗衣做饭,洗碗扫地,喂猪喂鸡,几乎所有的农活全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只负责上山放牛。我很少见到你笑,你趴在土掌房上翻晒苞谷粒和葵花籽的身影,显得落落寡欢。多年前,你坐在院子里就着太阳剪破布,糊着魔芋粉贴在门板上的悠闲样儿,怎么就一去不返了呢?
我很少搭理你,偶尔去一趟猪圈也会匆匆离开。因为我知道,只有你会在意。而你总是抓住我不放,今天抓一把葵花籽,明天揣一把蚕豆。你越这样,我越想逃离。那天,我又看见你在院子里的土掌房上,你让我上来找你,我当没听见,继续把猪食倒进猪槽子,故意将铁桶使劲磕碰了几下,甩甩手大步流星离去。我没回头,可我知道你追了出来,可你哪追得上我?你那么矮。是的,咱俩的恩怨是分家那天结下的。
闹归闹,你死那天,我一个人把嘴巴歪了歪,哭了。读五年级的小男子汉,居然哭了。那是个多么美好的雨季,还是个周末,我一个人赶着牛群到山上去。傍晚回来,还意外创收了一朵开盘的牛肝菌。把牛入圈时我愣住了,门闩拿在手上,那么多人围在盖着白布的你身旁,除了阿妈和几个妇女的哭泣声外,所有人都神情凝重。一向没什么灾病的你去了,很突然,很意外。他们都说,这跟你不幸的一生休戚相关,苦难使岁月的轮廓更加真实具体。诚然,大地从未因一个平凡的女人死去而感到过悲哀和战栗。然而,在安节巫峰上,一生渴望飞越群山的纳苏少年,将永远与垭口上的鹰一同纪念你的善良和美丽。
很多年后,他也离开人世,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叫他爷爷,可他却不是阿爸阿妈的阿爸。你离开后,我看见自由的他。他的自由不但以你的死为代价,我还看见那条捡来的黑狗,它被拴在柱子上,长期的饥饿使它后腿支棱不起来,垫在土坑里的破棉衣变成了一坨坨狗屎。他的自由,给了酒精,还给了几笔风流债。已经十年了,村里有个酒鬼也随他而去,有人从那酒鬼女人的口中听到,酒鬼生前亲眼看到,那天你撞破了他的风流债,所以被他扼住咽喉……大家都知道的是,那天你跟他去地里撒农家肥,你死去时双手全是牛圈里挖出来的粪。有人亲自帮你洗净。
我考大学找工作,现在成了家,有了两个男孩儿。二儿子正牙牙学语,已经学会了喊那两个字——奶奶。大儿子上了幼儿园,已经知道爸爸的妈妈叫奶奶。我想起垭口所在的那座大山——安节巫。当年,你第一次站在垭口,用单纯的眼眸看着鹰,可惜那个画面他没看到。按习俗,他没有在迎亲队伍里面。多年以后,我阿妈也因你出现在安节巫峰上的垭口。她同样微微仰起脸,看那一动不动的鹰。你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安节巫已然没有人烟,就像旁边那座阿则问山上废弃的瞭望塔,放牛的人都懒得去。也许还有鹰,会停在半空喝风,可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你来的那个地方,现在算不得山高水长,公路绕过所有的山,汽车小半天就可轻松抵达。就像那时候的那安和卿在你阿妈眼里出现过,现在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也没有在你负重的一生中出现过。索性,阿妈依然记得安节巫,记得垭口上静止的鹰,她跟我讲起的时候还会兴高采烈,因为翻山过去就是外公外婆的家,即使他们都已长眠地下。
5
我站在安节巫垭口,看见山的尽头还是山。崇山峻岭,莽莽苍苍,这是我童年世界的全部。穷尽一切,终其一生,我的梦想全在这只鹰身上。这是渗进血液里的血统,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在我生命里不习惯没有山的远方,并且须得是大山。城市显然不是。我没有丝毫贬损城市的意思,只是没必要矫揉造作和虚伪。城市很好,可并不适合一只鹰。如此而已。
汽车到不了安节巫,我已十多年没上过安节巫峰。
那只鹰,它依然还爱喝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