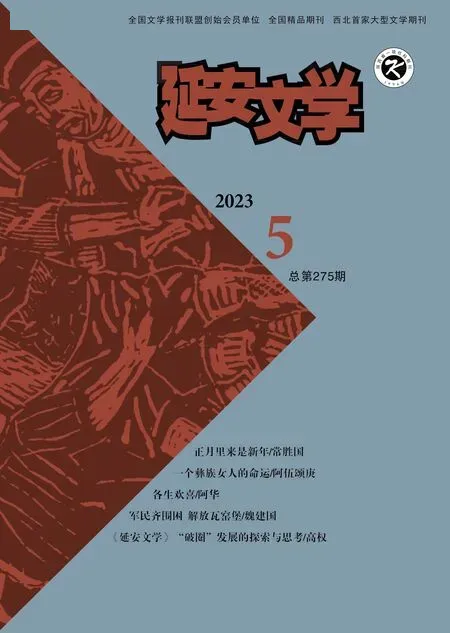雪落河川
2023-02-19范怀智
范怀智
羊铃铛
羊栏连着一眼破窑,窑里堆满柴禾,红红的大太阳还没在崖畔上冒出来,羊就在圈栏里叫呢。明显得很嘛,羊在叫元丰起床,羊们“饿呀饿呀”地叫着,还把犄角往栏门上撞,无非等他来开门,等他往水槽里放满清水,它们咕噜噜喝一顿,好美滋滋地去啃青。
满河川的青绿,说去啃青,反倒是哪里有青可啃?青绿的是麦苗,自上了九月,齐茬的麦苗疯天疯地地长过一阵,真把河川里的绿油全给渗了出来。迎了风摇个浅浅的绿浪,这么一个丰盛又甜美的模样,怕要把羊们能香馋死,可元丰咋能把羊赶进麦田里去?就是老福清也不会让羊们去香馋一回。
羊们只好齐排排地上到坡面去,啃一口草黄,吃几捧子干雪,仰起头在叮当响的羊铃声中,眼巴巴地瞅看无边的青绿。绿油油的青香随风抚上坡面,虽则冷嗖嗖的,羊们还要忍禁不住地打几个喷嚏,细格溜溜的涎水滴入干草,干草下的冷雪陷出个小小的坑臼。
羊摇响羊铃,风也摇响着羊铃。头羊的脖颈上拴颗拳头大的铜铃铛,铜铃铛的响声嗡儿嗡儿的,不只如土一样厚重,还如河川和远山那样苍古。老母羊的脖颈拴颗铁铃,被老羊的体温捂亮了铁釉,不论走到哪里,哪都有哐哒哐哒的铁铃在动,铃声沙哑而朴拙。此外,新生的小羊羔子的脖项,拴系着指蛋大的铜串铃,像风干的野菊开放在雪地。
入了冬了。羊们只好散涣在坡地,披一身增厚了的皮毛,极不情愿地揪扯干草时,心里必定惦念青绿,隔会儿它们要抬起头来,向河川里瞅瞭。吃吧吃吧,别老吃着碗里的,瞅个锅里的,大冬天能往嘴里揪口吃食就不错得很了!再说呢,捂过一场雪,草儿从深秋开始冬藏,历经过酵变,有了甘醇的酒味。把头埋下去,揪扯进满肚子的草黄,就几口干雪,瞑闭住眼瞳,慢悠悠地反刍,真似醉酒了一般,整个身子骨要荡漾起来,要陷进比甘醇的草香还深的梦境。再一个,若元丰懒睡进午后,别说往河川的麦田去撒个欢,恐怕连揪口干草的愿望,都成了幻想。一带明汪汪的小湋河水,弯弯绕绕的,不知从哪来又弯绕到哪去?
归 宿
没有啥梦,梦个啥呢,终究还不是个梦!啥也没有想,想啥呢,到头来还不是空想!每每入睡前元丰都这样告诉自己。每到心念纷呈,明知是个空想,仍要一个劲地想时,元丰这会就该说句狠话了:“谁爱想谁想去,反正我不想!”因此他空空静静,跟个空寂的绵羊一样。吃饭、睡觉、拦羊、看书,夜黑了给羊们撒了几搂草料,就着灯光坐到桌前来,写点不写会睡不着的文字。
要说人世有执着,元丰在读书写字这事上有些执拗。读书写字为啥?不为啥!只顾懵头懵脑地写,只让比长城还长的夜,给消磨到一个适宜的长度。
夜里睡得晚了些,元丰起来时,红崭崭的大日头晒到了紧固羊栏的木桩上,喜鹊在院场北侧的青槐树上叫,青槐树下是村上给修盖的保障房。为防止这老院场出意外,帮扶单位出面给盖了两间平房,彩钢瓦苫顶,水电接通。
过了夏,接近多雨的秋日,帮扶单位拉来旧的桌椅和板床,为确保他安稳度过雨季,帮扶人和村干部们还把老窑间的被褥一齐搬进了小平房,说莫轻心,莫大意,防患要紧。
“老窑塌方村里有过,再说你住的老窑年代久了,谁敢保证不落个土块,万一窑顶的塌土落到炕头上呢!”
干部和村人走了,他当晚住进了小平房。朝南的大窗户分外敞亮,坐桌前,拐子放到桌侧,铺展书本,灭掉新房的灯,他看到了窗户外头的繁星,看到弯弯的月亮和朝新房张望的羊眼睛。嘶嘶儿的蝉鸣,还有锦鸡在槐树后头的柏林里叫呢!青槐树后头三五亩大的柏林子,是院场主人栽就的,听说主人跟子女们去了北京,往后这院场成了鳏寡老人的居所。
元丰记得,村人所说的柏树院的增福老汉殁了,院里长满了杂草,常有野狗潜进窑门。增福老汉是从别处招赘到了小湋河川,老伴过世,他住进柏树院,直至故去。记得麦收前安葬了他,到了秋雨日他住过的老窑坍塌了,老窑陷进土中。另一眼连襟子的老窑也受了连累,塌了窑檐,半扇子窑壁颓圮,徒余东北角上堆放柴禾的那眼窑垴矗在土崖下,窑顶倒垂着长了枣树。
元丰清除过堆积经年的杂物,这堆了柴禾的窑垴还算攒劲。请了匠人,盘就灶台火炕,总归有了个栖身的场所,有了不再拖累家人的归宿。
母亲特意往紫蓝镇街去缝了被褥。灶眼生起红火,元丰住进柏树院的头天夜里,春寒料峭,尚未镶就玻璃的格子窗外,映着明净的星斗。此夜没月亮,独有弯折如小湋河的北斗星凝驻在晴空,瘦瘦的星斗明灭着。没有睡意,偎窗而卧,静默的北斗星看着他,他静默地瞅着它出神。弟弟结了婚,父亲离开了村落,去了村北的坟园,那里没了狗吠鸡鸣,徒有蟋蟀跟狐子们的踪迹。
思忖过许久,满夜没有瞌睡,他终究在母亲的饮泣中做定决断,他必须把残破的自己从家的躯体上剔除出去。他像别人脸上的一块赘肉,还像别人脚上多余的骈指,更像老羊头顶的犄角,显得沉重又无措。
不得不认命时,他相信前世肯定欠了文债,没有向白纸讲讲故事、说说话的日子,他有种慌急的烦躁和隐忧,他忽然觉得自己是这河川里废弃的人。文字给他信心,给他遇见美好的理由。每天写下如野草般自然生长的文字,元丰便在富足的恬静中安睡。弯月西垂,隐进浅浅的云朵和水雾。
睁亮眼睛时,一如小米粥样的阳光铺满窗棂。喜鹊跳跃在枝梢。出于习惯,他照例要看看入睡前在炕沿下摆放齐整的鞋子。鞋子似曾自己动过,跟入睡前的齐整模样稍有偏移,不知今天会遭逢啥样的人。
头 羊
太阳升上来,白霜还未杀下去,露珠未沁上麦苗。元丰去拦羊。
捅旺炉火,侍弄一顿早饭,往随身的暖壶灌满水,拣拾两块馍馍,一并装进背包。背包装着笔和书。
敞开圈门,尽是手腕粗细的刺槐木镶就的栅门。最先摇响串铃的几只小羔子急慌慌地蹦出,它们欢欣雀跃地跳起蹦子。随后被体温釉亮的铁铃摇响的老母羊,肉身打个松活的突鲁,稳沉沉地踱出圈门,守在门侧,等候那只领头的小公羊。小公羊脖项下的铜铃发出嗡噌的响动,它真像电视里的关二爷那样微瞑着眼瞳,仰高脖项,擎住它尖尖的犄角,从圈窑深处踱出。它真像个尊贵的羊王,径直走出圈栏,众羊簇拥它下了院场。
那么多的小羊羔,元丰只挑中了这只。它的体格比别的小羔子大一些,自落草的那一刻,母羊舔舐它身上的胎腻时,仅凭母羊的舔舐之力,它柔弱的四肢就能颤微微地站立。待到母羊尚未舔出它湿漉漉的皮毛时,它则跌撞地闻嗅母羊的气息,找寻母羊的乳头,并将双唇紧叼在母羊的大奶穗上。有多少小羔子全凭母羊的恩赐,直到鼓堆堆的奶穗触碰到眼前,且不知伸嘴去叨住乳头呢!
背好背包,拄稳拐子的元丰跟随在众羊后头。听着头羊嗡沉的铃铛声,浩荡的碎蹄子踏踩着水泥路赶往村北。与其说元丰驱遣众羊,不如说众羊引领他赶往村北的大坡面子。坡面子斜斜地挂在塬顶跟河川间,这一回那只精壮的小公羊,成了羊群里真正的头羊。
小公羊出生半年后,老头羊真老了。那阵子老头羊身上粘满了尿泥跟粪蛋子,可依然不失头羊的慈威。到秋叶落尽,它努力着爬过最后一波羔,开始怕冷。正逢小雪节令里的小雪落过,老头羊隐进了窑垴,它的身骨里淤了寒气。太阳升上来,羊们拥搡地挤出栅栏,守在院场一哇声地唤叫它时,它静默着闭实了双眼反刍。它肯定感知到了肉身的沉重,它是那么小心谨慎着,生怕摇响脖项的铃铛,搅扰得众羊心生迷茫。
夜静了,它睁开汪汪的泪眼看月亮,残缺、圆满、又残缺圆满的月亮。满月的夜晚,老头羊在柏树院的一生终归圆满,它卧在吃剩的干草上,下颏枕了前膝,双目瞌闭,面孔上凝固住恒久的微笑。它的使命完结,元丰葬它于院北的柏林,吃着小湋河川的草出生,又终被小湋河川的草埋没。到翌年盛夏,老头羊的坟堆上长满茂盛的青草。
倔强的小公羊已满两岁,它宽阔的体格像银白色的小山在坡面上蹦跶。抵近深秋,闹腾在骨子里的情欲促使它去爬羔了,它蹿跃而起的身子那么矫健,分明是老头羊重生。
到月亮圆满的静寂中,元丰用纸笔回望老头羊的一生。他说,它终于要成了接替老头羊的头羊了,虽则它爬羔的姿态还那么莽撞,可它毕竟是上天给柏树院,给群羊们的恩赐。
灯影铺散出窗外,铺展到羊栏那处。房门开启,一只光溜溜的木拐敲进影子交叠的院场,笃笃的拐子敲进了羊栏。一瞬串铃子的悸动,默然许久的铁铃铛一瞬晃摇。母羊或站或卧着反刍,或一门心思一如禅修般冥想,或如石雕般仰望明月。夜晚的群羊,是一副气静神闲的样子。在等待吗?大约受到了冥冥中的某种启示,小公羊会不会知道此夜它将受命?
小公羊真如一尊石雕站在羊栏一角的木桩前。挽根红绸带的铜铃铛拴系上它的脖颈——就是老头羊传递下来的铜铃,嗡沉的铜铃铛在皎洁的月影里,摇出了比弯垂的谷穗子还饱满的声响。就它尚未健硕的身骨子而言,新头羊稍显稚嫩。羊本来是个通灵的畜类,它能通晓和顾贴主人的心思,虽则它年轻,要说亲和力,它比老头羊要略胜一筹。当成年的母羊亲近它,想获取它的温存和宠幸时,它跟绅士一样谦和自尊。总的说来,新头羊除过爬羔显得有些将就外,其它各方面都是那般贵气与雍容,此外它的脖颈又添缀了五彩丝绳的铜铃铛,它当然要那般地出类拔萃了。
铜铃响动处,极少见到小公羊走往众羊前头,它以一副优雅又丰实的体格行进在众羊当中,铜铃响响停停,众羊停停走走。头羊引领了它们,在铜铃铛的引领中它们等待元丰。每隔一阵,羊们会把他遗落在身后。
富强和老福清
通村的水泥路不宽不窄。羊们停伫蹄步时,弯绕的水泥路面真像卧了白云。白云缓缓裂开,它们给前方摁喇叭的摩托车让路。富强回了村。
富强在县城买了房子,媳妇、儿子、老人搬去了县城,隔几天他要去趟县城,第二天一早得赶回小湋河的村委会。前些年他在新疆贩轮胎,母亲病了,他回河川流转了三百多亩田地,重拾起了耕种。
富强没想过要去吃力不讨好的村委会,偏偏村人推举他。一是有资金,二是有魄力,三是正当他的好年纪,也好做留守村民的产业带头人。生怕与羊群冲撞,他双脚拖拉在地,摩托车驶过羊群的缝隙,停在元丰近前。
“嗨!”富强叫声元丰,告诉他,“近两天牛国清要来找你,说要你编本书。晌午不要拦羊去了,在院里等他!”
他俩是发小,元丰的低保和二级残疾证都是富强给申办的。
元丰问他:“我托你买的麸皮,买下了没?”
显然迟到了,大抵村委会有接待跟检查。富强轰轰油门,朝上河里去。村委会在上河,在邻村,在河川前往紫蓝镇的坡根处。
富强像撩抛来一个苹果一样给他撩回话来:“没,没顾上。”
元丰还想问问牛国清是谁,在喧闹的摩托声中那话落空。
细碎的羊蹄踏踩过村道和田坎,它们上了坡地。像阔别已久的老友,它们与另一群绵羊嬉闹到一处,一同争食,有时还会怄气似地犄撞,那是老福清饲喂的羊群。元丰远远看见老福清在老杏树下煨一堆草火,他蹲蹴在红旺了的日头下,听装满了名角的戏匣子——儿子特意买给他的。看到元丰的羊群忽而涌进坡面,老福清高声叫喊元丰。老福清脸庞消瘦,鼻梁上架了副圆坨子的眼镜,茶色的镜片儿弹射起阳光。
“噢,拦羊呀!”
彼此打过招呼,名角的清唱在坡地上播散得像阳光一样明澈。老福清爱吃柴火煨熟的洋芋。一大早肯定没吃早饭,往他陈旧的军用水壶灌满水,往背篼里放进水壶、洋芋、镰刀,再有一盘结实的麻绳。水壶和背篼总要伴着他,这些个成了老福清的标配。
儿子五岁时老伴过世了,儿子二十出头去了北京,竟在北京成了家立了业。年老的福清这下真成了鳏夫。除了耕种,羊成了他的伴偶。到现今,他并非再是那个恪尽职守的拦羊人,他修了彩钢瓦羊棚,羊棚下码摞起成垛的干草,干草垛旁装一台打草机。有了打草设备,他不用每天去拦羊。直到喝足了罐罐茶后,觉得该去拦羊了,他才会拦羊去。
坡面子
洋芋烧熟了,绵绵的洋芋味飘散进坡面。散进槐树林的羊们朝老杏树方向张望,它们瞭看老福清吃洋芋的样子。他戴个圆眼镜,身侧是漆皮斑驳的水壶。他吃几口烫嘴的洋芋,要抿一小口水。
风掠过,袭来一绺清寒。元丰走近那块青光光的大石头,石头的一侧罩满了野刺玫,石头另一侧有个浅浅坑凹。每次上到坡地,他背依大石,面向挪进南天的太阳摊开书本,大冬天他在脚前煨起火,一抹青烟抚漫上晴空。坡地上散涣的铃铛摇响,懂事的头羊不时咩叫,它有意地告知主人,它们未走远。煨住火,并在火堆近旁支楞起两块馍馍,他掏出手机,点开村主任的微信,他得问问:“你说的那人是谁?”
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仍有那么多书要读。他是农民,读书仅是爱好。有了这门子爱好,他每天得写点随意的文字,觉着哪篇文字给了自己欢娱和欣喜,或被哪个感同身受的人物命运所击中,他则要把这样的文字呈送出去,以唤起更多的同感和欢欣。他有一辆三轮摩托车,一则为了购物方便,二则为了去投稿。
赶上阴雨或雪花封门的日子,元丰给羊们添足草料,会心地坐到桌前,他把手稿敲进电脑。网购了打印机,待到晴好的日子,他去县城寄稿,或去紫蓝镇街购物时,顺便将成稿快递出去,他不等待有个回音。有个回音甚好,没个回音,那时他也已忘记。
抵近午后,富强没回应。村委会忙乱得像蜂箱里的蜜蜂一样,真像天底下的所有事情全集中到了村上。反正河川里没了多少人家。守住村落的除了耄耋老人,便是跟元丰一样的特殊群体和他们无力送往县城就读的孩子。
元丰在他长到不会有结尾的《小湋河》中写道:“既然村庄剩下了这么样的两波村民,不知富强他们还要忙什么忙!有时看到富强他们那么忙乱,仍要禁不住地想,其实他们那么忙乱也是对的,正是有这些老人、残疾人和出不了河川的孩子,他们忙乱着来操心留守人家的事情也是对的呢!”
老福清不常来坡地,偶尔来坡地,会下到元丰近前。他会手抚膝头圪蹴在大石头上,跟元丰有一搭没一搭地拉会话,有时好似并非拦羊,只为见见元丰。每次圪蹴到坡面上的大石头,他免不了慨叹:“你说说,你说说,这坡面子上咋就能有这么一大块的青石头?你说是人拉上来的吧,人咋会有这么大的气力!你说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我看就是!你说天上咋能掉下个这么大的石头,还青光光的映着天光,不偏不倚咋就掉到这么个地方?”元丰怀疑过这块光洁的石头,最好别是陨石——不是陨石,它将永远留在坡地。
手抚膝头,瘦癯的老福清圪蹴在大石头中央,他远远瞭看河川,瞭看河川两侧的台原。他的身影映在被时日打磨成明镜样的石面上。比房子还巨大的青石上坐着元丰,他坐干草上,坐在向阳那侧,脚前煨一摊红火,火堆近前支楞起的两个馍馍烤黄了,太阳稍稍西斜。铃铛寂灭,细细的串铃声如细小的星星。吃饱了肚子的羊们,静守在坡地,它们听风穿过阳光的声响,若轻微的吸气声。
元丰没有收到富强的回信,他听见站回坡面高处的老福清唤羊了,他触到了太阳偏斜后的第一股子冷风。他的羊群朝它们的头羊聚拢,头羊朝老福清身后的老杏树走近。这一天他没从老杏子树那旁走下,没圪蹴上青石头。身上布满黑斑的群羊聚拢。乱格纷纷的羊铃声,倒别有些韵致。
元丰再次回望,老福清的羊群已上了坡顶,要从坡面子的另一面下往院场。元丰喝过暖壶里的水,他不急着赶羊回栏。羊们的肚子到底还是个无底洞,不是说这一顿吃饱了,不会再找下一顿。为了晚晌能少添一回草料,他得等羊们啃过午后的第二波干草,才让它们回去。少了老福清黑脊背的羊群,坡面陷入寂静,稍稍响动的铃铛,若那形单影只的麻雀飞掠。
元丰扶住石头,拄稳拐子站起。他得捡拾些枯枝,塞进大石下的空隙,以备来日之需。太阳西斜了。
冬 夜
吃毕晚饭,收到富强的信息。羊们守定圈舍反刍,元丰坐定桌前书写他的小湋河川。亮汪汪的灯光漫上院场,炉火温煦。
富强告知:“牛国清是文化馆的副馆长。”
元丰问他:“羊等着吃料呢,麸皮啥会子能买上嘛?”
富强回应:“一点点的麸皮都没了吗?”
元丰说:“半个月里够吃!”
“那你急个啥?”
“怕下了雪,买下了拉不回来。”
“保准饿不住羊。”
富强说过,中秋节前种油菜,买下三千斤麸皮来安苗。今年雨水涝得很,地里的蝼蛄不是很多。接连两场雨,小苗苗们稳住了根系,倒把一千斤没了归落的麸皮稳稳地剩在了手里。
富强每年要种上百亩油菜,先是为了避开麦收时节的用工荒,再者他跟紫蓝镇的老油坊签订了每年五万斤的收购协议。
冬雨萧瑟,没能回往县城的富强晚上到了柏树院。他瞅看瞅看元丰的羊栏,瞅看瞅看小平房,看看灶屋的水龙头。富强轻轻一拧,清亮的水淌进水瓮。
富强问他:“好着哩?”
他说:“好着哩!”
富强斜歪着身子躺到元丰的床上。元丰坐桌前。
富强说:“每天都写呀写的,哪有那么多字要写?”
元丰说:“就是自己跟自己说个话,自己给自己讲个故事听!哪能像个你,老婆娃娃热炕头,不是娃娃家闹,就是媳妇子闹,人在闹腾里才活得滋润,才能活出个心劲来!”
富强说:“书读得多了还是好,嘴巧。”
元丰问他:“吃过饭了?”
富强吃过了,一个人守住个院落,冷清清的,忽而想起个元丰,就到下河来转转。他说:“噢!想在村委会后面的空地上建个土梁油坊。元丰,到时候你来搞个管理,卖个油,你觉得咋样?”
果真是富强的关爱,元丰也不会贸然答应。元丰说:“我拄根拐子,尽给你添累,既是村委会建的油坊,就归村委会的干部来管理,这么着才相宜。”
富强说:“村上的事,我能干到个几时,干成眼目前这番样子,都觉着泼烦得很,不如咱自家种上百十亩地自在舒心。”
铺落光影的窗户外头,凄零着冬雨。雨轻薄又细密,光影的铺展处像起了雨雾,河川里沁起了潮哄哄土腥腥的味道。这是冬旱的味道,也是冬藏时节。
他俩随心所欲地聊着小湋河的未来和往昔,聊着曾经相伴又悄悄故去的那些人。这几天,总有母羊夜静时产下小羊羔。天明时,给羊舍去添干草,必然看见颤微微的小羔子偎在母羊的身侧。它们要急不可耐地去跪乳,去娴熟地噙拽母羊的乳头。看到小羔子跪乳的场景,元丰会痴痴地看过许久。他惊诧于生命中那些莫可名状的消息:草怎么会拿尖尖的头拱破地皮,探出绒黄的小脑壳子,又迫切地吸吮甘泽雨露?小羊们怎会在断掉脐带、被母羊舔净胎腻时,就在无知的彷徨间去探寻母羊的乳头?不知啥原因,这年的产羔季提前了近两月,会不会是年轻的头羊跟那几只公羊乱了爬羔的节律?趁了夜静,他要到羊栏里给悄然出生的小羔子拢起一摊火来。
大约富强忘记了筹建油坊的提议。时日过得缓又过得急,元丰未再提及。
芳 兰
文化馆的副馆长,一个拦羊的农人,两者间有着天高地远的差别,一如城镇与乡村,不光距离遥远,生活的境态和意趣也差得远哩。过了好些日子,没等到牛国清的身影,却在傍晚等来了老福清的侄女芳兰。
芳兰拖拽了女儿芝萱,跟在老福清身后。老福清愈来愈清瘦,沉甸甸的眼镜压塌了鼻梁,压扁了鼻孔。他左手拎根羊腿,右手拎捆粉条。元丰正在羊栏中挑撒干草。老福清问一声:“忙着呢?”那端直的问候,像根竹竿戳了元丰的后背。猛乍乍的,元丰吓一惊。元丰拧头望,看到芝萱、芳兰,看到圆眼镜。
窑垴接地气,愈入深冬愈发温腾腾地和暖。生起大火炉子的窑垴像春天,把书桌和坐椅偎近炉火,彤红的炉火在歌唱,一如精灵的笔舞蹈在雪野般的白纸上,轻缈的羊铃声恍若月光。每年小雪节气,满河川会扯起呼啸风,疯癫的风在蹿腾。秃树枝的呜咽晃动,河水皱起的鳞状的冰纹,是风经行的印痕。小雪刚过,飘雪宰羊的旧俗推到了日程。
青壮的村人进了城,村落里少了宰羊的匠人。唯有年少时稳固在身心里的习俗,随着岁月的递增发酵得日久弥深。村里的留守人每到旧俗的既定期,定要躬身践行。
河川少了宰匠,紫蓝镇添了家屠宰厂。见不得羊倒进血途,卖羊的前夜和当日,尊崇旧习的老人在庙宇、老树、碾石前点亮香火明烛,暗祷羊们超生。
“奈何做了刀途的羊。生处即来处,放却会饥饿会苦痛皮囊。飘飘荡荡,飞飞扬扬,落入那安稳的故乡,无刀无血亦无伤。”
无助地祈愿完结,老福清卖掉了羊。把反复清点过的羊们送往了镇街,顺从习俗,他买了整只的羊肉回往院场。
每年定有这样的日子,守望羊棚的众羊默念不归回的同类。前往坡地,或守了棚舍,大约受到某种启示的羊们,在静静的立卧间,关闭掉自己的喉咙和肠胃,不叫不吃,它们向天地禁食三日。
拎一捆粉条,拎一根羊腿,老福清有求而来。坐进窑垴,拥旺炉火,口无遮拦的老福清说明来意。
“冬冷了,咱拦了一整年羊,还不给咱盛条羊腿。没有别的啥,你看我的侄女来了,小孙子也来了嘛,就是叫你给芝宣呢说说作业,补补课,你看是咋样子报答你,是叫芳兰替你做饭喂羊呢,还是叫她给你洗衣做饭,这些个都难不住她。本来的嘛,你不是给娃娃家说个作业,你也有个时间做饭洗衣嘛!”
已近中午,独自久居的元丰矜持内敛,他撑个拐子给老福清和芳兰沏茶。芳兰一伸手接替了他。
老福清接过茶水,他坐到炉火跟前,叉开手掌,安闲地烤火。窑里暖暖的,他只管袖住手瞑闭住眼睛,让暖笼上身,滋润地渗进骨铆。他烤火的样子,憨态可掬又质朴可亲。好奇的芝萱偎偎蹭蹭翻动元丰的书本,芳兰轻声喝斥她。芳兰坐进桌侧的那把椅子,她拽住好动的闺女,生怕芝萱乱了书籍。
“娃娃有作业,天天有作业,天天都有不会做的作业。娃娃哭哩嘛,芳兰呢她又不会,满河川捋了几遍,还是想下个你。除了你,旁的那个谁,都没你攒劲,都没你称心!”
老福清的话老要直端端地,可他说得中肯又中听。
“元丰,就是叔给你说下的这么个话,娃娃家的事不打扰你,还能打扰个谁?你怕误工夫,叔呢拿羊给你抵,给你赔。就是我的大羊棚,你看上了哪只牵哪只,你要多少赶多少。若怕耽误你拦羊,这个话咱也好说得很嘛,大不了叫芳兰去给你拦。说到底,咱都为了个娃娃嘛!你看咋样?”
还能咋样,老福清的话已说到了这份上!
芳兰离婚了,带了女儿净身出户。芳兰回了河川,住进了哥哥家的院场。哥哥家的两口子在邻县的医院上班,前几年在宝鸡买了房,为了照看孩子,芳兰的双亲去了宝鸡。哥嫂周末才赶往那个人口百万的市区。知道芳兰不得不回到河川,周日哥哥带了父亲驱车赶回,把窑门的钥匙放到芳兰手上。
元丰早听说芳兰在西安有了房子。忽而面对她回来,面对坐到近前的她,不免有些惊异,好端端的日子,别人全狠了劲地往城里赶,她咋带了闺女回了河川?
不用芳兰给他拦羊,不用她来洗衣做饭。毕竟羊栏外堆了干草,尽是羊们爱揪扯的麦秸。每年夏收毕,拦羊的人家约请了打草机,把麦秸打成瓷实的草锭,齐整地码摞进圈舍,元丰自不例外。他们以此来减弱拦羊出坡的劳顿,亦会因此腾出个劳力来,去下河湾的农业园区务个工。
“河川无闲草,村里无闲人。为个吃穿,人人忙累,一家人有一家人的艰难,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困窘。芳兰又不是没拦过羊,她打小满河川疯跑,你有个啥难处,叫芳兰给你有个照应!”
老福清的话语分外耿直。对住火焰熊腾的炉火,他翻转身背和手心,等待元丰应答。
“不用芳兰去拦羊,不用她来帮衬。我一个拄拐子的人,又不去熬活务工,日子没那么紧!只是大冷天的,娃娃总得芳兰来接送!”
狐子声
月亮钻进凤凰状的大云。羊腿留下来,粉条留下来。老福清抬手稳稳茶灰色的眼镜,傍晚渐近,一只火狐子呕叫几声。从上河向下河,狐子奔驰过墨绿的田地,像一袭火红的风贴地而去。冷冷的夜宿满了河川,老福清袖住双手下了院场,他的身板子端正硬朗。芳兰跟他身后,芝萱挣脱了拽揪,蹦跳地跑在前头。坚实的水泥路上落下浅朦朦的身影,大凤凰云朵化作了狮子状的云团,月亮恰好从狮状云团的嘴巴钻出,酷似狮子刚咬去月亮的一半。
第二天黑云垂落,老杏树的枝梢伸进了云层。拢过一堆火,烘烤过馍馍,暖壶里的水尚未喝尽,慢吞吞的羊群朝头羊汇集。毋须等待羊来揪食第二波干草。元丰有想头羊有应,会意的铜铃铛响起。坡顶旋下骤风,拧扭的风撩抛起枯枝杂草,旋卷上升,斜斜地升腾进黑云。捂灭灰烬,元丰下了坡地。
侍弄过羊群,提早吃过晚饭,捅旺炉火,洗漱过手脸,元丰坐桌前。天气预报有雪,雪将落未落,隐隐的狐子声飘摇而过。每临大雪节气,河川必有轻幽的狐子声。元丰听到这个轻如一粒光点的声音,不知那个通天彻地的灵类启示着什么样的讯息。芳兰跟芝萱哼唱着小视频中正火的那首歌曲,芳兰的鞋跟干脆地敲在水泥路面。天已擦黑,母女默契地合唱着上了院场。
芳兰为她的到来做过细心筹备。她给他端来了晚饭,清洗了他的锅台,他坐桌前瞅看芝萱的作业。推谢不过她的诚挚,她替他清理窑垴间的杂物。
芝萱午后五点回到村庄,校车会到院场下准时停靠。如果没有积雪干扰,芳兰会站在下院场等待高歌的校车缓缓驶近。听闻校车喇叭里的儿歌,元丰朝窗外观望,喇叭高亢,河川顿然有了喧活的生机。晚上六点到八点成了芝萱学习的时段。冬夜八点已黑静,芳兰不好回还。打开手电,一根端直的光柱伸到很远。
芳兰说:“用不着你做晚饭!”
元丰说:“劳烦了你!”
拐子敲上院土,他送芝萱和芳兰。风追撵风,此夜两股子暴躁的风在下河湾相遇,桀骜地厮咬、揪斗。手电光柱间肆虐起飞尘落叶,还有风召唤风往下河麇集。雪迟迟未落。
牵拽着芝萱,芳兰走去时说:“天冷,河面结了冰。”
手电的光柱探往了远处,光柱所到处夜若洞窟。芳兰说:“干吗要去拦羊,院场上堆了那么多干草!”
风打起呼哨。看那扫动的光柱上了下河的院畔。
坚硬的风逡巡乱撞,把倔强的羊们拢进羊窑。元丰进了羊栏,往羊窑撒过几搂干草,用几根木棍封挡住羊窑的出口。冷风蛮横,今夜注定有雪。
在风里,就在风里,又听见缈缈的狐叫,一如远山的一粒蓝光,更像飘缈轻移的磷火,是一滴细小到荧蓝的光斑。坐桌前煨住皮实的炭火,他瞑住眼睛,捕捉那粒遥远处的狐叫。他听到了,那粒狐叫就陷在他的耳孔中。没有瞌睡,明日不准备去拦羊,他在他的小湋河川里走到了天明。
天明时云破日出,四野凝霜,曾一夜嘶吼的风,竟绵软得像跪乳的小羔子,在河川懵头懵脑地乱撞。松活松活僵硬的腰身,他照例往羊舍添过干草,往结了冷冰的水槽内倾满清水,洗罢脸放齐整炕沿下的棉鞋,倒进火炕惬意地安睡。
太阳西斜,蜜状的阳光乳漫上窗窑,他从生涩的困倦中醒转,是羊们“饿呀饿呀”的呼叫摇醒了他。翻转身子,拨拉开窗帘,蜜黄色的阳光涌入,粉白的窑壁上敷上了融暖。羊们叫得那般殷切。他趴伏到窗台,看见包着红头巾的芳兰蹬着梯子,高举着大杈耙,挑扔下干草锭子。元丰静静地看她,看她下了木梯挣断捆草锭的绳子。草锭拔散了,抡高大叉耙,干练的芳兰挑起干草撒过羊栏。
阳光明澈
坐起身,习惯性地看一眼炕沿下的鞋子,确有一只鞋子有了偏移。说不定,柏树院该来个谁?窑门开启,干净的阳光灌进窑根,院场的平房那处停放一辆崭新的电三轮,三轮车上高高堆起几大袋子麸皮。
芳兰说:“早上送芝萱坐校车,富强则刚好回村上。他叫我给你带话呢,说面粉厂拉了两吨麸皮放到了村委会,他给你预定了五百斤,叫你抽空拉回去!吃过晌午饭,闲着呢,我专程去了村委会,怕是去迟了叫旁人抢没了。”
元丰拽出小平房下皮管子,他往栅门旁的大铁桶中蓄水。
元丰说:“不会,有富强呢!”
芳兰说:“咋的不会,我去时上河的李明劳正守住五袋麸皮叫富强给你打电话呢!富强说元丰说好了,他拦羊回来骑车来取。李明劳说,五十多头猪呢,吃过今晚晌明天要断顿呢!李明劳说,你给元丰说他拉两袋,我拉三袋子两厢顾贴着,你说能有啥问题。李明劳呢,他猪场上的猪哪要断顿了?他呢,是瞅着村委会拉回的麸皮一斤便宜一毛钱呢,他就想来捡下这么个便宜。幸亏富强没给你电话,要是富强给你打个电话,你怕是要把五袋子麸皮都得让给了他。你说李明劳他早干啥去了!”
元丰笑笑,斜往正西的太阳暖暖的,羊舍里满是羊们的气息。羊们真渴了、真饿了,攒挤成堆自顾自地揪草饮水。芳兰进了羊舍,她捉起铁锨攒扫散落的羊粪蛋子。羊们咩叫,铃铛盏盏,听到有人的说话声,院场上了人。他俩自我介绍说,是文化馆的牛国清和韩启鹏。牛国清说,韩启鹏是办公室主任。坐进窑垴,牛国清说明来意,芳兰沏了茶水。
牛国清说:“听说你在《人民文学》和《中国作家》上发表了文章。”
元丰说:“几年前的事了!”
牛国清说:“咋不早说呢嘛!听说你是高中毕业,去西安的建筑工地干活时落下了残疾,往后一直在河川读书、写作。”
元丰说:“是在西安鸡市拐的工地上去搞建筑,卷扬机钢绳断了,砸断架杆,摔下来了嘛,摔断了腰胯。你说在高三复读了两年都没考中,除过搞个建筑,没啥出路嘛!过了三年能拄个拐子下炕了,二十五岁了,得有个营生。务个农,拦个羊,闲了嘛,就看看书,写写字,也没啥,就是跟打麻将一样的爱好嘛!”
牛国清说:“文化馆要出一套非遗丛书,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再一个呢,我们这边有几个馆员写的散文跟论文,你帮忙给修改修改,能不能顺便给推荐一下。是这样子,我们馆里明年要招一个创作方面的文化干事,你在大刊发表过文章,馆里研究过,不论你的年纪和成绩都挺合适。”
元丰说:“我就是农民,拦羊和务农是我的主业。我说过了嘛,读书写字就是个爱好。爱好嘛,无非是寻个乐子的事情,旁的也没啥!”
彤红的太阳坠下去,枕上河西原畔。他送走牛国清,小湋河的上空拉扯了一带软软的水雾。起过圈,往小平房的檐台卸下麸皮,芳兰回了下河。芝萱要回来了,听到校车在歌唱。乳状的水雾淹没河川,一群黑牛样的夜影降临。
落了雪
大雪后的太阳晴得老高,鹰鹞盘桓,几抹跟小羔子样跳蹦子的风。启动多日未用的三轮,三轮的驾驶座旁系拴住拐杖,元丰集中年底的光阴去投稿。只是要把文字的欢欣放飞,他没期冀文字的回报,这只是个闲暇时自说自听的喜好。因这喜好,他能触到隐秘的生灵在文字的时空里哭笑。
盼望有雪。迟迟的雪落进午后,落进夜黑。灯光沁出窑窗铺展进雪野,那只喜鹊在羊棚间跳跃。听不懂它叫喳喳的言语,兴许是去觅食的那只还未回还,兴许是白雪的洁净促生了它埋得很深的情愫。羊们避入羊窑安卧一处,嗫嗫地磨动牙齿反刍着。雪在积厚,灯光映照处雪在旋卷。
有了芳兰和芝萱的光顾,柏树院有了柔和的煦暖,明净的玻璃上有了“蝠鹿闹梅”的窗红。窑门开启,打根手电,拖拽住衣帽臃肿的芝萱,芳兰下了院场,拐子敲进雪地。
元丰问她:“为啥要回来?”
芳兰说:“不为啥,不回河川还能回哪去?”
“会不会走?”
“富强说油坊那边缺人手,问我要不要去。”
雪在手电的光柱中蹿飞,密集而炽烈。他听得出芳兰的话外之意,哪里会有个为啥,回来就是回来,事实如此没有为啥。看似无意,看似乱纷纷地飘摇,其实每片肆意乱舞的雪花,都会落进它该落的那处,不偏不倚。光柱消隐雪中,雪隐进黑。
偶或一声铃铛响。每个夜晚,会有不眠的白羊静静地倾听河川。它们静若流水,它们瞑目佯睡。这个夜晚,雪比羊白。是夜添进夜黑色的黑炭,捅旺炉火,在白纸般的雪地,顶一身雪白的光影,元丰要在小湋河川的白雪中,静默寂寥地走下去。
他用夜黑色的水墨在白雪般的纸上写道:民国三十三年,祖父白彦龙引领他们的团丁在潜回河川的路上,纵马围堵了两只狐子,雪霁月圆,一狐逃遁,一狐毙殒。适逢大雪节令。此后经年,每至大雪时节,河川夜静,总有狐子呕呕泣鸣……
你梦到了你该梦见的那个梦。梦一直在那里等你。
雪从深深的天幕落下。凡是落入河川的雪,都是该落进河川的雪。
每瓣雪花只落在那处,没落往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