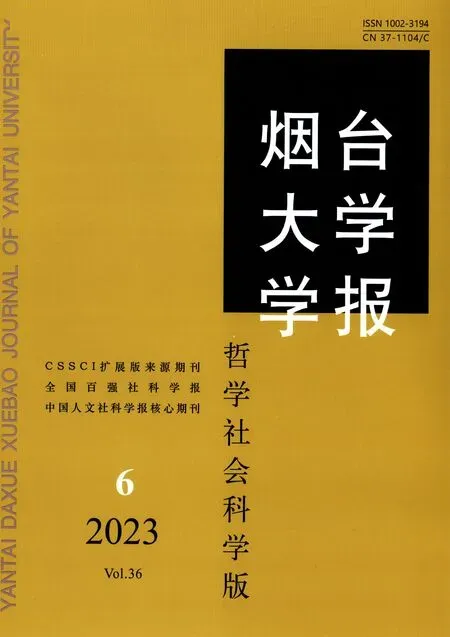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货币本质及其权力批判
2023-02-18谢亚洲
谢亚洲,刘 婷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不断催生新的产业革命,借助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数字化迅速覆盖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方位改写了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固有形态。数字技术和经济活动的密切融合,催生出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构建新一代货币体系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发展机遇。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本质上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一种以数字形式体现的货币形态,是数字经济顺畅运行的关键架构,是一种复杂多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发展的最新形态,涉及数字技术、货币金融和主权信用等多重维度,已然成为各国的研发重点和学界的讨论热点。目前学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范畴(1)杜金富、张初晴:《数字货币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3年第1期。、性质特征(2)李秀辉:《货币性质评判的四重维度——兼论数字货币的性质》,《求索》2023年第3期。、发展趋势(3)孙馨月、陈艳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货币发展路径研究》,《经济问题》2023第6期。和经济效应(4)赵恒、连飞、周延:《法定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影响及福利效应研究——中共二十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学理阐释》,《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1期。等领域,鲜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对数字货币的本质进行深刻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为工具,以价值形式化运动和货币符号化趋势为线索,通过对价值“表现形式”的分析,对货币权力“抽象统治”的演绎,对数字货币“崇高对象”(5)在《照亮世界的马克思》一书中,齐泽克主张将《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The Sublime Object of Ldeology)中的“object”译为“对象”,因为它隐含着动态的关系,是欲望着的一个东西。拉康对崇高对象的定义出现于《精神分析的伦理》一书,是指“被抬到(不可能的——实在界的)原质层面的对象”。齐泽克进一步强调,崇高对象是无法过于接近的对象,如果过于接近它就会丧失它的崇高特性,沦为庸常的鄙俗对象(vulgar object)。它只存身于间隙(interspace),处于中间状态(in an intermediate state)。本文认为数字货币就是这样一种既不可磨损又无法撕破、坚不可摧又难以企及、由资本创建并维持的“崇高对象”。的祛魅,来探究货币形态蜕变的内驱动力和数字货币的本质特征,从而充分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当代的丰富内涵和强大生命力。
一、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与货币权力的形成机制
马克思高度强调了价值形式的重要性:“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6)⑦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8、51页。在《资本论》前三章的论述中,他将研究对象规定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层面,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为分析起点,从单个商品的抽象分析再到商品交换的具体分析,科学揭示了商品、货币、价值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有力打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化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的幻象。建构这样一套概念体系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进一步追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7)⑥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8、51页。商品价值最终又是如何以货币这种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面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价值的形式化运动时采用了一种辩证的进展方式,逐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图景。
马克思首先论证了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价值实体是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他将单个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细胞”单位,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为“解剖”切口,层层拆解笼罩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商品“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特性变得更加清晰。一方面,“可感觉”是指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赋予商品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商品依靠这种自然属性成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另一方面,“超感觉”是指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体现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不同的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互交换。这不是基于使用价值这种异质性的物质内容,而是基于隐藏在商品各色外表之下的同质性规定,即“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9)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8、51页。这即是说,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互为前提的共轭关系,商品异质性的使用价值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必然,而商品同质性的价值使得交换成为可能。一切商品共有的属性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商品在交换中获得的可通约性使得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了同样的可通约性。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社会劳动,在质上是一般人类劳动,在量上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马克思对价值概念做了科学抽象,不仅将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视为价值在质上的实体内容,而且进一步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视为价值在量上的衡量标准。这超越了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的简单表达,马克思为劳动时间加上“社会必要”这一限定,窥见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张力,再次强调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价值是一个客观且高度抽象的范畴,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价值无法被单独把握,必须借助某种物质表现形式,才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如实呈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单个个体必须借助于商品交换来满足生活需要,马克思进而聚焦于对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分析。“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10)②③⑤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0、79、90、62页。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虽然抽象劳动规定了人类劳动的质的同一性,为商品交换进行量上比较提供了可能,但是价值实体的“无差别性”不能通过单个商品的特性内在地体现出来,一个商品的价值必须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比较中外在地表现出来。商品要实现其使用价值就要通过交换,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中;而参与交换的商品必须被视作物化的人类劳动,才能进行相互比较。“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11)①③⑤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0、79、90、62页。商品交换使得价值对象性能够开显自身。单个商品无法经由自身表现为价值,作为“有用物”的商品必须获得“社会公认的形式”,“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12)①②⑤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0、79、90、62页。至此,通过普遍交换的中介作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生产者被交换行为强制拉入资本主义建构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生产丧失自己的私有性质并成为社会过程”,(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8页。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4)①②③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0、79、90、62页。
拨开缭绕在商品交换中的种种迷雾,马克思进一步解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商品价值那“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特征是借由货币形式而展露的。当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用价值与价值那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就“产生了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表现为这种一定的商品,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5页。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物性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货币的出现打破了商品交换共时性和同域性限制,各个商品之间直接的、复杂的交换关系进一步表现为全体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最终,“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16)①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90、79、90、62页。原本抽象且难以捉摸的价值经由交换机制最终以货币这种物的形式展现于世界。货币本质上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一方面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被社会承认的化身,通过交换转移了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它把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掩盖了价值与劳动的真实关系。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考察和分析,确证了货币用物的形式对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之间社会关系的遮蔽,折射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转移癔症”:“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2页。马克思已然察觉到货币具有一种外在于生产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性力量,这种力量强制所有人参与到商品世界的普遍交换之中,支配着社会成员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行为,从而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为表现形式的异化状态。
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逻辑上必然发展出的外在形式,其理论研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占据关键地位。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涵括了对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逻辑与历史等哲学论题的思考,也是《资本论》中从商品范畴过渡到货币范畴的关键节点,强调了交换关系之下被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马克思以价值形式的演变来勾画商品世界如何从异质的自然形式实现同一的等价形式,并一直阐述到世界本身存在的所有物都可以通过货币形式将之同一化的可能性,其实他意欲表明的正是价值形式使人无意识地屈从于资本主义构建的一切皆可通约的逻辑框架。人们深谙商品和货币拜物教之道,其理性活动始终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之内的理性,始终绕不开资本的逻辑。作为商品交换的普遍中介,货币代表了“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19)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215页。拥有“万能之物”的强大权力。这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理解数字货币的出场逻辑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视角:价值从产品的商品形式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正如齐泽克所言:“商品和资本的世界不仅是有限的经验领域,而且是先验性的社会—超验(socio-transcendental a prior)领域,是派生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之整体性(total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的母体。”(20)⑤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90页。正因如此,为了维持并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仍然需要在数字空间中嵌入价值形式逻辑,以此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
二、货币的符号化趋势与货币权力的
普遍化发展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细致剖析,意欲追问资本的本质,洞察资本主义通过何种方式将所有人裹挟进充斥资本逻辑的商品世界。他强调:“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21)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215页。物质生产过程是商品价值“自在”(in itself)生成的环节,商品流通过程才是商品价值变成“自为”(for itself)存在的关键一环。“正是因为‘自在’与‘自为’之间存在着分裂,资本主义才需要形式上的民主与平等。”(22)③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90页。马克思高度重视并刻意凸显交换关系,实则是为货币权力的社会性出场埋下伏笔。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中,货币展现出普遍的可直接交换性,可以和整个商品世界的任何东西相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构建了一种抽象统治的经济秩序,从而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和社会权力。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货币不单是一个可以代表价值的符号工具,而且是“表象和真实的复合体:独立个体对象化了的社会联系”。(23)Hans-Georg Backhaus,Dialektik der Wertform,Freiburg: ca ira Verlag,1997,s.56.作为价值完成形式的货币是如何实现权力统治的?货币形式在弥合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裂隙的同时,又将矛盾引向何处?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对货币形式的分析,而是通过透视货币关系的固有矛盾,展开对资本逻辑更加深入的剖析。
从马克思对货币的最初定义来看,货币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同商品的自然形式相脱离而成为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似乎先验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性”通过“物的依赖性”建立起了普遍的互相依赖关系,这种互相依赖主要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有时仿佛就是商品世界里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全都必须臣服于它,顺从它的命令,在它的权力祭坛前膜拜”。(24)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货币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独立形式存在,根源于货币是处于“一般等价形式”位置上的一般等价物。“价值是关系性的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它的对象性后果才能以可感知的方式来掌握它”,(25)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商品交换产生的物质性关联构造起来的。这即是说,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应该带来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必然带来一种能够表现出这种社会性特征的价值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一般等价物至少具有三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其一,一般等价物以其自然形式成为了整个商品世界的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货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26)⑤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5-106、127、152页。它与其他商品处于同一水平,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货币来表达。“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8页。货币成为了价值本身的社会表达。其二,一般等价物将丰富多样的私人劳动变成了同一性的价值化、货币化的劳动。其他一切商品都以换成货币、实现惊险的跳跃为目的,以此表明“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28)③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5-106、127、152页。其三,一般等价物“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29)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519、518页。这意味着货币能够被个人所占有和让渡,资本积累由追求庞大的“商品堆积”转向追求巨大的货币储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得以成为可能。货币既是动力因又是目的因,如同高悬于世人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象征着崇高的社会权力,同时也昭示着资本主义的拜物陷阱。
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表现形式,存在自身价值与表现的价值相背离的可能性。在商品流通领域,这种背离具体表现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之间的彼此抵牾。马克思强调,“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30)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519、518页。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货币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方式是基于等价交换原则,即货币商品的价值量与其他商品所含的价值量必须相等,这意味着物质属性是货币的内在规定。而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货币只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联结,用以确保相互交织的商品形态变化过程能够顺利实现、永不停息。“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31)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5-106、127、152页。货币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质言之,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对货币的品质和数量存在差异性要求。价值尺度职能要求货币要有一定的品质保证,能够准确代表其他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必须本身具有相应的价值,必须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流通手段职能则要求货币要足够便捷灵活,必须脱离笨重的实体形式而转向符号化。货币一方面通过符号化获得加快流通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因为名义价值脱离自身实际价值而失去了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依据。横亘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之间不可化约的矛盾,隐含了货币形式不断升级以弥合自身裂隙的端倪。诚如大卫·哈维所言,货币是资本主义“驱动的产物”,“这种驱动要求使货币臻于完善,使它作为交换的‘润滑剂’变得没有摩擦、没有成本,又可以即刻调整,同时还要维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32)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第398页。货币历经实物商品、金属货币、铸币、纸币、各类信用货币等形式不断演进,最终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货币既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又是权力与信用的符号象征。货币形式的发展对于构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信用货币从实体形式限制中解放出来,庞大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极大提高了流通的速度和效率,这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言尤为重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是金融体系的关键基础,以此为开端,资本主义的统治力量威慑着身处交换关系网络之中的所有个体,货币的权力触角也迅速延伸至世界市场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为缓解货币内在矛盾而创造的多种货币形式固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仍无法根除其本身固有的矛盾,信用货币的流通反而使矛盾得以“扩大、普遍化、发展”。“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9-70页。随着信用制度的持续发展,货币符号化趋势更加模糊了货币与价值的真实关系,削弱了货币与社会劳动的现实联系。藏匿于金融体系背后的精英集团“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34)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00、670页。他们操盘大部分社会资本,沉醉于逐利的乐趣,全然不顾社会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危险,疯狂制造资本泡沫。信用创造和金融膨胀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控境地,进一步带来各主权国家之间国际贸易失衡、货币霸权、信用竞争、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构筑了强大抽象权力的神坛,燃起人们心中对社会地位、权力威望的欲望之火。同时,信用货币的符号象征意义也反映了对国家主权信用的依赖和对权力体系的服从,迫使人们陷入贫富悬殊、阶级矛盾与冲突激化的混沌沼泽。
如果说价值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映不同的社会关系,那么货币作为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就是充分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表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晶。建立在货币基础之上的金融体系依赖于“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35)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00、670页。货币——作为资本主义创造的,继商品之后的新物神——不仅暴力地将世界之物、社会之人都置于资本预设的交换网络中,而且主导着万物的存在意义。货币金融体系化身为主宰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和上帝”,将芸芸众生吸纳进资本主义经济治理秩序之中。货币权力借助种种吊诡的经济手段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和掌控。从这个角度而言,货币的符号化趋势推动货币形式化约为“纯粹的形式”,实则是想要为货币权力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统摄消除形式障碍。挣脱了物质属性束缚的数字货币是“符号的符号”“象征的象征”,是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妄图使“抽象成为统治”的极致体现。
三、数字货 质与货币权力的无限扩展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伴随着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勾连而拉开序幕。回顾金融资本主义繁盛时期,金融的驱动和滋润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强烈地彼此裹挟,货币职能的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升格为“特里芬难题”,即主权国家无法在扩大货币储量以满足经济全球化需求的同时保持币值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美元迫于黄金储备不足以偿还国际债务的压力,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先声,新帝国主义摒弃黄金对于货币价值的锚定作用,助推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主权货币霸权。在金本位失灵崩溃和金融资本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疯狂增长的双重刺激下,新帝国主义建构起以占据霸权地位的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当货币的可兑换性在事实和观念上都不复存在时,货币形态进一步丰富并“以符号和一些表现形式来代表货币,最后还以计算机化账户里的数字代表货币”。(36)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第19页。在金融风波中诞生的比特币,就是资本寄希望于借助数字技术,在脆弱的中心化货币体系之外构造去中心化加密货币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当代货币已经不再囿于物质表现形式,数字货币成为新一代“纯形式货币”的发展方向,这为重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结构的升级催生出关于价值形式和货币理论的一系列新问题,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阐释力发起挑战。
从数字货币的概念定义可以初步管窥数字货币的双重特征,即它是数据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结合。严格来说,数字货币是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技术的虚拟货币,可以分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和各国积极研发的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37)④ 钟伟、魏伟、陈骁等:《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6-57、115-119页。从“数字”维度理解,数字货币的出现毋宁是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的必然现象。新一代信息技术点燃了数字货币的创造火焰,并持续为之贡献颠覆性的技术理念。无论是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架构的比特币,还是以DNA(Data Analytics, Network Effect and Interwoven Activities)商业模式为基础的科技巨头创建的加密数字货币,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数字货币是依托数字技术架构而形成的一种当代货币的极限形式。从“货币”的维度理解,当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已然演化为价值符号象征体系。数字货币完成了从物理有形到电子无形的形态跃升,看似发行数量可以不受实际价值制约,货币流通可以超越国家界限,数字货币完美贴合马克思对世界货币“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6页。的描述。数字货币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商品价值的“纯形式货币”,是价值符号象征体系衍生的疯狂之作。数字货币的双重特征意味着搭建双重信用机制的可能:一方面,数字货币自身具有数据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基于时间戳的链式区块结构、分布式节点的共识机制和灵活可编程的智能合约等关键技术特性,(39)② 钟伟、魏伟、陈骁等:《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6-57、115-119页。技术信用有望重构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另一方面,数字货币作为价值的数字化表达,要获得普遍认可就必须得到公共部门信用保证,因此,数字货币的推行和普及依旧离不开国家主权信用作为基础。
从数字货币的发展进程来看,数字货币脱胎于货币职能的裂隙空间,通过货币职能的裂变分化,逐步发展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用货币(special purpose money)(40)专用货币是具有专门用途、职能受限的货币,区别于具有通行用途、行使全部货币职能的通用货币。。根据马克思对货币职能的理解,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是货币的五大职能。这是分析考察一种商品能否作为货币使用的基本考量,也是数字货币属性争论的核心维度。数字货币研发浪潮缘起于支付方式的变革,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41)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和解释,参见莫开伟、邱泉、李凤文:《数字货币——数字时代的金融生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是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独立化的产物,标志着数字货币进入了初级阶段。电子货币实质上是借助电子设备将实物货币进行了数据化,故作为反映货币数值变化的记账工具,只具有支付手段职能而无法直接充当流通中的一般等价物。电子支付的普及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推动着数字货币走向私人数字货币无序发展阶段。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并不是由合法货币机构发行的,其价值源自市场对私人数字货币的信心,(42)李建军、朱烨辰:《数字货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0期。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投机性资产。由于脱离社会经济关系基础,私人数字货币存在币值不稳定、供给受限、难以监管等结构性经济问题,(43)钟伟、魏伟、陈骁等:《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第152页。无法在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获得合法地位。从货币职能角度看,不具备法偿性的私人数字货币只能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执行货币的部分职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的无序发展严重阻碍现有货币体系的良性运转,迫于“正本清源”的需要,数字货币正在经历从私人数字货币向央行数字货币的转变。央行数字货币是具有法定地位、国家主权背书、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数字化的技术形态,其本质是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能够执行货币的全部职能。(44)李晶:《数字货币与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综合来看,数字货币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货币发展的时代体现。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以货币职能的裂变和分化为原初动力、以货币职能的复归和统一为现实诉求的辩证历程。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价值形式的数字表达,是与数字技术和信用体系绑定在一起的虚拟价值符号。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对数字货币展开思考。
第一,数字货币是价值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极限表达,反映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按马克思的理解,“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不过是商品本身的结晶了的形式变换,而这种形式变换又不过是商品所有者借以完成其物质变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化表现”。(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3页。马克思对价值形式问题的追问,对货币形式变化的分析,直接导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探究。价值的本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商品的社会关系,货币形式的关键在于对特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表达,货币本质上蕴含了发展为符号和“纯形式”的内在可能。因此,从价值形式分析角度来说,“货币物不是物,而是它所替代的关系场境”。(46)张一兵:《价值关系异化:作为商品中劳动交换关系物性结晶的货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再研究》,《东南学术》2023年第1期。数字货币作为当代货币形式的衍化升级,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数字世界开创了新型交换网络,这里没有现实性物理的商品交换和流通,取而代之的是虚拟性数据的信息传输和价值传递。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可感的交换关系发展为冰冷的、抽象的数据关系。这同时意味着,数字货币可以轻易打通地域界限和空间阻隔,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数字资本语境下货币的内涵变得模糊,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夹带资本逻辑的数字活动,其中潜藏着国家间政治角力和利益争夺。例如,基于货币篮子方案的Libra宣称,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47)Libra 协会:《了解Libra(白皮书)》,华盛顿:Libra 协会,2019年。这看似削弱了全球霸权货币的溢出效应。但是,从货币篮子的构成来看,美元占一半比重且刻意回避人民币,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借助脸书(Facebook)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全球化的用户群体继续推行货币霸权政策,以此挑战和威胁其他国家主权货币。因此,霸权国家金融体系主导下的数字货币仍然属于金融资本范畴,是金融资本在新的技术变革下的扩张工具。数字货币的背后是隐而不显的政治博弈,其数字外壳下暗藏着新帝国主义企图肆意剥削世界市场的野心。
第二,数字货币并未脱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而是以数字符码形式掩盖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通过规避社会矛盾的对抗冲突,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以“和平”渗透的方式逐步实现货币权力的抽象统治。之所以把数字货币视作一种不可磨损又无法撕破、坚不可摧又难以企及的“崇高对象”,是因为它占据着“欲望的不可能——实在界的对象”(impossible-real object of desire)的位置,(48)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275页。即一般等价形式当中的一般等价物的位置。价值实体与其表现形式正是在这里达成短暂的“综合”。然而,当数字符码占据了一般等价物的位置后,数字货币的形式化本质再次割裂了价值与货币的脆弱联结,“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49)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2、91页。数字货币必须不断回溯性地设定自身的前提,从而确证自身的形式在场。维护数字货币与价值的关系有两种可行路径:一是控制货币流通量以保证币值的稳定,比特币就是通过算法技术预先设定了总量,因而被称作“数字黄金”;二是设定货币价值锚以确保货币品质,从现有货币体系的金字塔等级结构来看,高级货币形式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已有的货币形式,而是呈层级间动态互补的关系。一切货币形式的基础归根到底均源自于劳动价值。数字货币似乎与实际价值脱钩,却又必然与传统货币形式牢牢绑定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在价值被简单化约为纯粹形式的数字空间中,资本借由种种非生产性活动榨取财富,形成了对实体经济的抽血效应。数字货币是社会权力抽象统治的极致体现,它以“无形之形”支配着生产者的生产、支配着劳动者的劳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50)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2、91页。这正是异化形式的当代呈现。数字空间的繁荣假象背后是现实世界劳动者持续遭受的“他者剥削”,数字货币的狂热积累背后是虚拟世界劳动者不断加深的“自我剥削”。“一切物化都是遗忘”,(51)Theodor W.Adorno,Max Horkheimer,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ischer,Frankfurt a.M,2000,p.286.一切形式化都是对本质的蒙蔽。数字货币以纯净、平等、崇高的形式遮盖了资本肮脏、残酷、血淋淋的剥削劣行。
第三,数字货币搭建了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统治秩序连接的桥梁,是把旧世界的统治力量带进新世界的“特洛伊木马”,使货币权力更加广泛地无限扩张。货币“归属于社会构建与组织的范畴”,(52)约翰·史密森:《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修订版)》,柳永明、王蕾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它构筑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世界上任何绚丽多彩的存在物都可以透过货币棱镜变成价格标签,情感、知识、技能也能够被出卖以换得货币。人们没有意识到货币如何将日常生活形塑成商品世界,但是却时刻在感受金钱的力量,时刻在期待财富的增长。货币作为一种形式结构,捍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根基。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数字货币就是数字空间的关键基础设施:数字货币将货币的抽象统治权力延伸至数字空间,搭建起数字资本世界的形式结构,以维持资本在数字空间的统治地位。从产生时间来看,数字资本的积累先于数字货币的诞生,可以将数字货币视为资本自身孵化的货币形式。质言之,数字货币建立在数字资本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为数字资本搭建了一个基层社会结构。在这个基层结构中,万物都可以表现为被赋予价值的数字符号,从而在数字空间中重演货币拜物教的历史。因此,传统货币体系的进化与数字货币形态的创新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险恶手段。数字货币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呈现的独特形式,本身就具有荒诞的拜物教性质,在人们的头脑中建造起“崇高对象”,将所有人围困在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使其始终无法逃离资本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未来数字货币从发行到应用必将是一个丰富的产业生态,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层次地对人的控制。正如当今互联网金融所体现的那样,资本借助于数字支付平台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们的投资偏好和消费水平。数字时代看似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它的统治秩序之中。恰如德勒兹所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通过监控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53)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9页。
尽管数字技术的进步可以推动货币形式的革新,但是社会权力关系和统治秩序仍然建基于资本逻辑之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依旧适用。货币形式的符号化夷平了人作为主体存在的丰富个性,使之成为缺乏内在世界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货币权力的普遍化推动了资本逻辑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经济现象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因素,各国积极研发数字货币的表象背后是主权国家、区域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较量。数字货币本质上反映的是数字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关系的深化。因此,要打破新帝国主义霸权制造的技术壁垒,有效建立新型世界货币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不被各种形式所蒙蔽,把握货币与价值的真实关系,在全球经济中积累壮大社会主义因素。
四、结 语
资本寄希望于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来消解固有矛盾和时空局限,为世界范围内的秩序创新、货币形式更迭和体系重建等创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数字货币为人类描绘了未来数字资本生产和流通的基本轮廓和雄心,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批判论域。因此,首先要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工具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完成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本身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批判,完成对旧有概念话语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从而理论地再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的辩证运动。立足于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货币只是一种价值表达形式、一种社会关系反映形式、一种资本主义借以彰显自身权力的形式。
价值通过形式化运动,不停地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寻找新的宿主。货币形式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性,即本来应该代表价值(社会劳动关系)的货币,却在符号化的过程中逐渐掏空自身的物质基础(与劳动相脱钩),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危机。现有数字货币所倡导的“去中心化”构想,力图解除资本限制,转移金融风险,为资本增殖提供最优条件。然而,资本主义危机总是藏匿在矛盾间隙之中,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临时性和暂时性的,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宿命的某种延宕。每一次对具体问题的短暂解决,都承载着对全球性矛盾升级的承认,承载着对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僵局的承认。货币所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形成、普遍发展和无限扩展都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恶无限”,一个高度商品化和货币化的世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充斥象征意义的单一、空洞、虚无的符号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既顺应了历史发展和时代需求,又体现了创造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世界秩序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