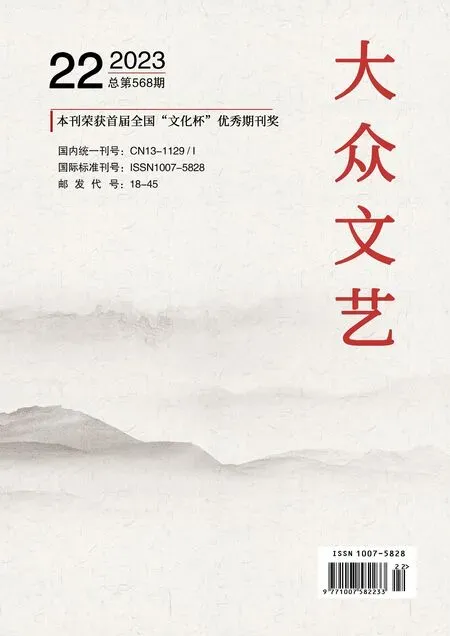论《宠儿》中塞丝从独体到共同体的身份转变*
2023-02-16王金美袁庆锋
王金美 袁庆锋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托尼·莫里森是非裔美国女作家,于20世纪60年代末登上文坛,其代表作《宠儿》等,“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宠儿》取材真实的历史,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讲述了女黑奴塞丝在携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因不愿看到孩子再次沦为奴隶,毅然杀死幼女,而十八年后奴隶制早已废除,被她杀死的女婴还魂归来的故事。小说聚焦美国奴隶制晚期和南方重建时期的历史问题,迫使读者再度反思种族主义造成的文化记忆与身份的伤痛和割裂。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也会遭遇危机,而美国种族主义正是通过精神上的侮辱对少数族裔及个体进行摧残、贬低,破坏其精神生态,使其扭曲或异化,最终陷入文化和身份危机。本文以《宠儿》中塞丝为研究对象,基于精神生态的纬度关注其精神世界,探讨种族主义精神侮辱带给少数族裔的文化创伤与精神分裂。
一、物化:白人对黑人群体的精神侮辱
白人中心主义的排他性注定奴隶主绞杀黑人族群利益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对黑人文化及其价值观进行审判、贬低和否定,并通过白人凝视维系其权力运作。萨特认为凝视表明“我是一个为他的存在,我在他人凝视中发现自己,我即是他人,是为他人而存在的。”[2]奴隶主通过权力“凝视”把被看者置于被动位置,对其进行监视与审判,以控制黑人族群。黑人族群长期在“看”的监视下,内化了白人价值观,自主地鞭笞、监控自己,如塞丝所说,“(白人)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想不起来”①[3],所以黑人社区得到奴隶主前来追捕的消息却不告知塞丝,最终导致塞丝弑婴惨案的发生。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形式,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物关系,通过商品化衡量劳动和人导向的结果是以商品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最终导致人的物性,能力成为可以占有和出卖的“物”,人的权利和价值被忽视被剥夺[4]。
“学校老师”在追捕黑奴时算的一笔账可以浅窥物化的特质:他把塞丝和她的孩子们用只来计量,用公母论其性别,把孩子称作崽子,并用塞丝的“价格”与2个幼年“崽子”相论,甚至思考塞丝的生育能力所“下的崽子”可能带来的利润。黑奴被奴隶主视作家畜、个人财产和商品,被贴上价格标签,他们的价值从一个人主观能动的价值变为机械单一的商品价值。黑人的价值被限制在这样的框架下变得狭隘、低廉,被剥夺人的价值,黑奴也最终丧失对自己生而为人的基本价值追求的权利意识,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卢卡奇指出,物化把人的劳动变成商品中对象化的抽象劳动,被商品化的劳动便理所应当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进行,将生产过程合理化。黑人作为商品而言,一切苦难被视作理所应当,这是种族主义的“原罪论”[4]。
当保罗D问一个黑鬼到底该受多少罪时,斯坦普说该受多少受多少,能受多少受多少。前者把受苦作为必然前提,后者则认为黑人应该毫无怨言接受种族命运,苦难潜移默化成了黑人的命,具有种族合理性。如塞丝背上的那棵“苦樱桃树”,明明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却和塞丝融为一体,仿佛与生俱来。黑人族群在白人物化下对自我价值和命运产生怀疑与悲观,甚至把不幸当作种族命运,无知无觉中接受白人对黑人族群劣等化的文化灌输,变得麻木,内耗,忘记抗争。
二、独体:精神创伤与人格分裂
种族主义精神侮辱导致黑人族群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人格分裂,使黑人个体、家庭共同体和族群共同体分崩离析,精神创伤往往伴随黑人一生,沿着代际横向蔓延。“创伤”的核心内涵是人们对自然灾害、种族灭绝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它对受创者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巨大影响,导致遗忘、恐怖、麻木、抑郁等情绪,使受创者无法构建正常的个人和集体文化认同[5]。种族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寄居于被奴役黑人心中,无从和解,变成一座不断酝酿悲伤的坟冢深埋内心,而逃避痛苦过往,选择不去面对苦痛的经历,只会被动陷入身份迷失,每个人变成一个被围困的、没有出口和入口封闭的孤岛式的“独体”。
1.行尸走肉的独体
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认为,爱的客体的缺失和外在世界的诡秘变异会产生内并心理创伤,[6]在自我的心理空间形成了一个秘密坟冢,用以隔离和埋葬所失去的爱的客体,使自我处于一种对创伤麻木或无意识的状态,内化并拒绝思考,因此被剥夺了直面自我、社会和历史的力量。
《宠儿》中黑奴被白人视为财产物品,被彻底剥夺了权利和价值。塞丝意识到黑奴身份导致她无法保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格也在奴隶主的蹂躏中遭到摧毁,她从学校老师的非人待遇中逃脱以便与这种奴隶制永远地决裂,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生为黑奴的命运,无奈但决绝地选择将孩子杀死。应激式的弑婴使塞丝连为人的精神都彻底丧失,“眼白消失了,她的眼睛有如她皮肤一般黑,她像个瞎子。”②[3]塞丝的愧疚和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鬼魂般悄然折磨着她,这种心理创伤一直被她埋在心里不敢面对。“至于其余的一切,她尽量不去记忆,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③[3]她鸵鸟式地把遭遇的苦难和失去的亲人深埋心中,而被埋藏的创伤在她心里成了内心创伤沉默的坟冢。内并心理创伤使塞丝拒绝思考和回忆过去,拒绝与痛苦的过往重逢,拒绝直面自身。塞丝所经受的是广大黑人经历的缩影,黑人族群的内并心理创伤对过往历史、世界、自我的逃避导致了黑人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2.名存实亡的家庭共同体
代际间幽灵是“无意识的产物。它以尚待确定的方式从父母的无意识转入孩子的无意识……在主体自己的心理空间中,它像腹语者、像陌生人那样活动。”[7]代际间幽灵把上一代内心埋藏的创伤在无意识间传递给下一代,如幽灵般如影随形。塞丝的观念对塞丝的儿女皆产生了巨大影响。塞丝在意识到奴隶制对黑人的摧残后选择杀死幼女以示反抗,而弑婴的记忆使她极度抗拒回归社区和面对白人,由此创造出以124号为基础的对外封闭的名存实亡的家庭共同体。而她的儿女,在此情境下被动地、潜移默化地接受塞丝的观念,承受塞丝传递下来的创伤,对外界与白人产生敌意与畏惧。124号的压抑氛围正是塞丝内心沉默坟冢的体现,她对于宠儿挥之不去的愧疚就像124号的鬼魂,藏匿于黑暗处,日夜不停地折磨着塞丝和她的家人,导致家庭纽带的断裂,没有温暖的关怀,而是塞丝和丈夫黑尔、塞丝和情人保罗D、塞丝和小女儿丹芙之间的疏离与漠视,以及儿子们由于无法忍受压抑家庭气氛而出走远离。塞丝的家庭共同体名存实亡,家庭成员缺乏自我认同、独立性,也没有任何的沟通与共情,而变得形同虚设。
3.乡邻/精神共同体的消亡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基于现实的有机的一种结合关系,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8]。塞丝弑婴引起周围黑人群体的不满与排斥,他们无法理解,更不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白人种族主义带来的群体悲剧与苦痛,在孤立塞丝一家的同时,也形成自我孤立,黑人共同体分崩离析,也反过来巩固了白人的宰制地位,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文化隔阂、对立与冲突,即便存在着友善开明反对种族主义的白人如纳尔森、鲍德温。丹芙作为代际间幽灵的承受者,她也与社区和白人有着巨大的隔阂和恐惧:“在外面,有的是罪孽深重的地方,当你走近时那一切恶事还会重演……时间在那里停滞,像她妈妈讲的那样,不幸同样也在那里等着她。”④[3]她站在124号与外界的通道时,所感到的源于未知与混乱的恐惧和警惕一次次阻挠着124号与外界的连接。
黑人家庭与社区本应是黑人的精神家园,但种族主义宰制下缺乏自主权的黑人难以建立起紧密的纽带。黑人族群在同病相怜的同时没能主动打破白人价值观的禁锢,反而内化白人价值观,接受“被劣等化”的命运并互相伤害、孤立。
三、从独体走向共同体身份的辩证统一
除了反映黑人的惨痛历史,莫里森在《宠儿》中更加关注黑人族群如何走出创伤,如何构建一个美好、健全的黑人族群的未来。落脚于现在的叙事、宠儿的消失和塞丝与黑人社区关系的缓和、丹芙走出黑人社区做出融合于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都体现出莫里森对此问题的思考。
1.正视创伤本质
对于承受创伤的个人和共同体来说,如果不理解过去,就难以走出迷惘和徘徊,只有正视了过去才能面对现在和未来[9]。种族主义精神侮辱导致黑人群体无法承受的心理、文化、历史创伤,使其难以建立自己的文化历史与身份认同。小说中塞丝多次拒绝前往“林间空地”,对于她来说,那里就是她埋葬痛苦回忆的地方。因为曾经所受过的苦难,致使她不敢再度面对,也不愿再接触外界,因为她害怕再次为之付出代价。由于无法正视创伤,她便一直无法了解自己恐惧的根源,以至于被囚禁在过去,内疚、自责而无法做出改变、迈向未来。
而宠儿的再度出现,让黑人社区都回忆起了曾经的苦难。如果不回望过去,就不能明确自己为何走到这里,怎么走到这里。只有对过去的清晰认识,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自我身份认同。当黑人社区都回到124号前时,他们再度记起了在这片土地的共同经历,进而变得更加团结,帮助塞丝和每一个黑人抛弃独体的自闭,同时打开彼此之间共同体的大门。正视历史现实使塞丝和其他黑人最终走出种族主义的阴影,找到自我,重新构建自我身份,并最终实现个体身份与共同体身份的辩证统一。
2.打破独体禁锢,构建共同体身份
“凝视不但要求黑人成为被看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是要求黑人放弃对自己的主权。”⑤[9]凝视使得黑人内化白人的审判,成为被监视被操控被鞭策的客体和他者。接受凝视的黑人为了迎合白人而行动,像黑人社区在学校老师赶来时的默不作声,便是一种对白人迫害的潜在认同,丧失了维护族群权利的意识,从而导致白人对黑人更加牢固的操控。对于这种强加给黑人族群的价值限制、“框架”,黑人族群需要主动跳出这种价值评判,认识真正的自我,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当丹芙主动叩开琼斯女士的家门,主动看向外部世界时,就找回了部分的主动权。用“看”来建立对自己的正确认知和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才能使人们拨开心中来自种族主义的迷雾,以更坚定平等正确的眼光审视来自外界的恶意,使得这些曾经可怕的审判露出其虚无本质,才能使得黑人面对种族主义精神侮辱的价值贬低和低人化时坚定不动摇。
此外,一个人的身份离不开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殷企平在阐述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时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深度共同体”[10]。这种共同体的连接不是仅凭血缘或地缘所联系,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共鸣和生活的共同体验而形成的深度共同体[11]。当社区成员来到124号时,”她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坐在台阶上的丹芙,而是她们自己。”⑥[3]宠儿的存在揭开了社区成员记忆深处的创伤,使得黑人族群与塞丝再度联结、共情。情感的连接使得塞丝能够与社区成员共同面对宠儿,给予塞丝勇气正视过去伤痛,重新认识自我价值,并寻求出路。在塞丝与社区再度联接时宠儿的悄然消失,象征着住在124号和塞丝心里的鬼魂,塞丝内心沉默的、创伤的坟冢里埋葬的愧疚与伤痛正在为塞丝所接纳所正视,并且化解。共同体的构建帮助黑人愈合过去的伤痛,勇敢面对过往并且与之抗衡。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互相扶持互相关爱帮助黑人个体找回自我身份,形成自己的、种族的文化传统与联结。比起用一个人的力量去与奴隶制度所带来的创伤抗衡,在共同体的支撑下找回自我身份的认识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增强个人价值观和自信,更有利于对抗历史的、现世的以及未来的、原形毕露的抑或隐匿的精神侮辱。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宠儿》作为一部黑人遭受精神侮辱的记录史,深刻地揭示了白人精神侮辱的本质、手段及其对黑人群体造成的种种困境。白人奴隶主通过凝视与物化击溃黑人的价值观与自我认同,白人的审判渗透进黑人族群的观念使其自我监禁,白人的迫害留下的创伤使黑人族群一代一代麻木逃避,始终阻碍着黑人共同体的构建。正因如此,莫里森借助塞丝从独体到共同体身份的转变,指出受歧视、排斥的少数族群应该积极勇敢面对种族主义精神侮辱与创伤,主动找回自主权。通过族群共同体的构建,时刻以共同的遭遇为警醒团结起来,建立起族群自身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树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积极谋取族群发展,以给予白人长久以来的价值审判以反击。但少数族裔共同体不是拒斥、远离主流社会孤立封闭自己,而是打破血统论肤色论,以情感共鸣的精神共同体为核心导向。虽然,少数族裔对于个体和族群主权的重新构建与发展的道路依旧曲折多阻,但莫里森对共同体(“最重要的属性是文化实践,意在改造世界”)的倡导与文学实践,为其指明了前进方向[12]。
注释
①②③④⑥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第291页,第139页,第6页,第244页,第299页.
⑤陈后亮.“被注视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和种族身份建构[J].外国文学评论,201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