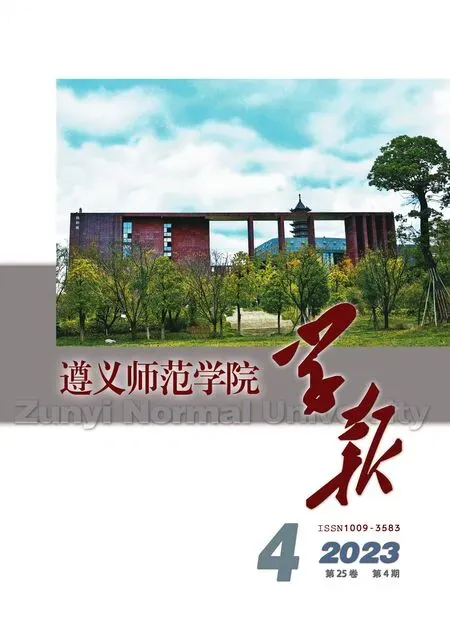论《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运作与权力反抗
2023-02-12胡梦蝶
胡梦蝶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江苏 南京 211200)
《使女的故事》(下称《使女》)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出版于20 世纪80 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美国(彼时更名为基列共和国),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育资源稀缺,人口数量下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使女,被分配给社会统治者——大主教们繁衍子嗣,沦为生育工具。小说基本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使女奥芙弗雷德的口述,描绘了阴森恐怖、压抑晦暗的基列极权统治,以及包括使女在内的所有基列民众饱受极权摧残的悲惨群像。
权力,一直是《使女》的主流研究方向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于我而言,政治涉及一切”[1]。关于基列权力的运作机制,既有研究多采用福柯理论,从规训权力视角剖析女性“驯服的身体”[2],从话语[3]、空间[4]、身体[5]等方面讨论微观权力的操控。可见,学界多借助福柯的经典权力理论,忽略了当代左翼思想家对福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虽有学者[6]从生命政治视角讨论同名美剧中的现代生命政治危机,但也仅是作为一个论证环节,有关《使女》中的生命权力、生命叙事和生命政治学等问题还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关于权力反抗策略,学者们多从语言和话语视角分析,探讨权力和语言的关系[7],认为女主人公通过叙述的方式反抗权力压迫,语言成为反对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8]。本文认为,话语只是反抗策略的冰山一角,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还采用解构为策略进行权力反抗,但既有研究对解构的讨论不多。基于此,本文围绕“极权政治”这一核心概念,综合运用福柯、阿甘本等西马思想家的权力理论,探讨以生命权力为驱策的极权运作机制,以及以解构主义为主要途径的极权反抗策略,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极权统治下弱势群体的关注,为人类走出极权统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一、生命权力驱策的权力运作机制
诚然,针对使女的权力改造主要表现为“红色感化中心”嬷嬷们的权力规训。根据福柯的经典权力理论,掌权的嬷嬷采用规训权力通过训练、监视、考核等手段,将使女,尤其是使女的身体禁锢在封闭空间进行有目的的改造,重塑成一种符合权力者意愿的特殊主体。例如,电动牛刺棒是她们权力的外化,呼应了弗洛伊德“阳物崇拜”,映射了男权的菲勒斯中心。然而,基列政权对所有民众的权力改造更多体现在生命权力的运作上。权力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理论体系的支点,生命权力是他三大权力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生命权力将群体的人口纳入到权力作用的范围内,旨在管理作为群体的人口生命、保证生命安全,提高生命价值。生命政治学自福柯以降,后经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奈格里和哈特等西方左翼思想家进一步阐释和发展,成为当今西方思想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之一。结合《使女》文本,作用于基列民众群体的极权政治运作机制,具体表现为生命权力驱策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术,如例外状态常态化、个体群体化、人口管理、性的操控、种族排斥等。
起初,一批美国极端右翼分子通过制造“例外状态”发动政变,开启了极权统治的基列时代。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是意大利当代学者吉奥乔·阿甘本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指一种非常态,“又称紧急状态,指的是当国家秩序、法律面临存亡威胁时,统治者、主权者宣布弃置法律,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种状态的情境。例外状态下,整个国家、社会进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日常生活秩序、规范都被完全悬置,公民的权利、安全、自由也均无从谈起,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主权权力的规定执行”[9]。小说中这样描述基列的政变:“一切发生在那场大劫难之后,他们(右翼分子)枪杀了总统,用机枪扫平了整个国会,军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被冻结时这一切便发生了。”[10]P201。民众一开始对新闻上的各种暴乱感到震惊,觉得难以置信,但由于政变者欺骗性的安民宣传,“他们说这是暂时的。街头上甚至见不到丝毫暴乱迹象”,他们于是错以为这些报道不过是距离自己生活甚远的偶发事件,对此麻木不仁,“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一如既往,视而不见,未能及时察觉危难逐步逼近。夺取政权后,极端分子实施“例外状态常态化”,将本是“例外状态”的极权秩序变成永久存在。民众此时方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极权统治下,无论这种例外状态多荒谬,多反智反常识,被统治者除了无条件接受,别无他途。正如丽迪亚嬷嬷告诫使女那样:“所谓正常,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使女)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如果规训权力着眼于个体,那么生命权力则着眼整个人类、整个种族等宏观层面。福柯指出,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术并不在乎每一个个体,而只在乎社会的整体的人口,包括出生率与死亡率、健康状态、人均寿命和人口分布等等。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维护社会总体的量和总体的人口质量,这就是生命权力的国家治理术。基列建国后,统治者迅速将个体的人改造成群体化的人口,并采用生命权力管理人口。他们先通过服饰的区别实现个体群体化,例如,夫人穿象征圣洁的蓝袍,使女穿象征性和生育的红裙,马大则身着象征家务劳动的暗绿服,如此便将人口沉降为生物性的存在,变成生命权力的征用对象。尤其是对那些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来说,她们不仅被取消了通过知识和个人能力实现经济独立的权利,而且也失去了人身和婚恋自由。女性不再是人格化存在,没有社会属性,只有生物学的属性,即成为生产人口的机器。基列服饰政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个人“成为可以被忽视的、被抹杀的,服务于集体利益的工具”,使个人的权利被“合理的、正当地被剥夺”[11]。也就是说,保卫社会可以牺牲个体,保卫群体的生命可以无视个体生命。福柯这一“生命政治”学说后经阿甘本继承并发展,并由后者提出“神圣人”(Homo sacer)的概念。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中会产生“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同时又在司法秩序之内,皆是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的“神圣人”。基列国为解决人口急剧下降的问题,宣布二次婚姻和非婚同居皆为非法,收罗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区隔为使女,分配给身居要职的大主教们繁衍子嗣,美其名曰“授精仪式”。身着红衣的使女,一方面,她们因为特殊的服务性质,高冷而神秘,神圣不可侵犯,人人对她们“表示敬意是理所应当的”[10]P23。另一方面,她们居无定所,游走于各家大主教之间,孤无所依,她们是生命权力作用的对象,是极权政治行使国家治理术、个体让位于群体的牺牲品,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生育自由,成为一种特殊存在,一个“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10]P136。她们可以轻易被杀死,但因具有生育价值又不能被祭祀,沦为“神圣人”。另外,除了使女群体,基列统治者还通过取消个体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利,从而优化整体人口结构。那些年迈无法生育或者不愿生育、屡教不改、顽固不化的“坏女人”更加悲惨,她们会被毫不留情地发配至集中营,遭受核污染,自生自灭,或被送至“荡妇俱乐部”,成为高层人士泄欲和炫耀特权的工具,暗无天日地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此外,当权者还通过性的操控来实现极权治理。福柯发现,由于性处于身体(规训权力的对象)和人口(生命权力的对象)的十字路口,所以性的管理至关重要。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通过权力和权力机制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刺激性话语的生产”[12],“只要有性欲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关系”[13]P53。福柯主张不应该仅仅被拒斥、否定和压抑性,而要对性加以利用,使它显示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性的积极性、生产性出发,把性当成是管理的对象,属于公共的权力。小说中,基列当权者积极发挥性的生产性作用。第一,他们摒弃性的自然属性——欲,只关注性的功能——繁衍,严惩一切与生殖无关的性行为,“不仅包括熟练的性活动,而且还有感官抚摸、一切邪恶的目光、一切淫猥的话语,一切淫念”[13]P14,如眼神交流、触摸、手淫等,堕胎更是明令禁止并追溯清算。第二,性本是最隐秘的文化禁忌,基列却取消性的私密性,将性纳入到公共权力中,从而管理生命,提高人口出生率。授精仪式现场,夫人、马大、司机等全家成员“必须在场……所有人都必须耐着性子挨到一切结束”,见证大主教和使女的授精仪式。女主人公坦白说,众目睽睽下的整个性行为的过程“毫无丝毫刺激之处。它与热恋、情爱、浪漫以及所有那些过去常令我们感官兴奋不已的概念毫无关联。情欲是根本谈不上的”[10]P107,连主教自己都表示“太冷冰冰没有人情味”[10]P108。奥芙沃伦产日,不仅嬷嬷和使女们齐聚一堂,连所有大主教夫人都亲临现场,演一场极具荒诞色彩的代孕闹剧。极权政治之下,性之隐私性消失,性成了集会的动机,全然暴露在生命权力运作之下。第三,基列把“性”当成社会奖惩措施,只有位高权重的上层官员才有资格婚配,拥有出身显赫的夫人且能享受使女的生育服务,中层男性,如天使军士兵等,直到他们战功卓绝,得蒙升职,才有望包办到经济太太,而司机等身份卑微的男性则无权婚配。这种反人性的制度反而激发了中下层男性对基列事业的献身意愿,不知不觉成为生命权力改造的对象。
基列统治者的生命权力行使,还包括使用极端手段确保本国人口的健康和安全。由于人口下降,不育人口数量和新生畸儿数量偏高,繁育成为基列国一项重要工作,负责繁衍的使女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成为整个国家管理的关键。因此基列当权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保证人口供给和生命健康:第一,为保证使女的人身安全,使女的活动严格受限,外出必须两两同行,街头巷尾到处布满士兵的“保护”(监视)。第二,为保证使女的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正常,国家要求使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脱离,以保证充足的休息。她们的饮食由马大专门负责,不注重味道可口,只保证“都是营养极好的食物”[10]P73,禁绝咖啡、茶、烟酒等有害物质的摄入,从而“成为一个有用的容器”[10]P73。使女还要定期接受医生的身体检查。这样,掌握着知识(Savoir)的医生也拥有了一定的权力(Pouvoir),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使女的生死,无形中也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治理的参与者。第三,将生命权力与种族主义相联系,生命权力致力于群体管理,决定了它必须成为种族主义的同谋。因为本族生存,就意味着对本族生存构成威胁的异族死亡,本族要生存发展,就要取消异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小说中,基列统治者先将人口进行差异性划分,区分为“应当活的人”,如有生育能力且愿意生育的使女、掌握知识的医生、服从性强的马大、司机等,和“应当死的人”,如无生育能力和屡教不改的“无用之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之后生命权力进一步诠释了这种割裂,当权者把“无用之人”投放进集中营,任其自生自灭,由此取消异族生存发展的权利,保证本族的生命安全和安居乐业。
二、双重权力反抗策略
《使女》勾勒了一个权力笼罩的恐怖世界,那里阴森晦暗、压抑绝望、令人窒息。那么,生活在权力压迫下,饱受极权摧残的基列民众是如何应对这种生存困境的呢?大体上说,小说中的权力反抗策略分为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口述历史和群体层面的二元对立解构。
个人层面上,学界普遍认为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使女把叙述作为反抗的手段。《使女》继承了现代主义意识流的手法,打破了线性叙事,充满了大量时空交错的内心独白,符合福柯“话语即权力”的主张:使女只能使用例行的套话打招呼,无法自由地进行有意义的交谈,象征着她们失去了权力,成为权力的对象。阿特伍德自己也将《使女》归类为“目击者文学”。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同时认为,话语只是女主人公反抗极权的手段之一,她的叙述,本质上是一种解构策略。
小说末章“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基列政权的形成原因和基列时代的社会样态等内容侃侃而谈,乐此不疲地考证大主教的真实身份,却无意着力探寻对挖掘基列历史贡献最大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一句“不甚了了”便草草打发。而且,学者在发言中屡开黄腔侮辱女性。读者遗憾地发现,几十年后基列极权虽然覆灭了,但女性的地位似乎从未发生明显变化,女性依然是社会中边缘化的存在。因此,女主人公的口述,本质是她作为历史的社会边缘化的“他者”,用言语(Speech)叙事解构历史学家的书写叙事(Writing)、用飘忽不定的记忆,含混的暧昧,甚至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小写历史,对抗逻辑清晰的大写历史的终极方式。无独有偶,书中多次采用解构策略来消解基列统治的权威,例如小说中经常出现“自由游戏”(Freeplay)来调侃掌权者的用词,如“枣油菜”“五月天”和“救救我”,莫伊拉用“基列的炸弹”替换掉大主教冠冕堂皇主持词里的“基列的乳香”等。再如莫伊拉换装成嬷嬷,通过置换身份成功避开眼目逃离了感化中心,从而解构了嬷嬷的权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有服饰的不同,权力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创造”的,是被赋予的。可见,解构才是挑战父权制、消解宏大叙事、反抗基列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不仅是使女,极权统治下的其他女性群体以及中下层男性群体也深感焦虑和痛苦。下文是从性别角度具体阐述小说中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及权力解构。
首先,前基列时代,以母亲和莫伊拉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痛恨鄙视男性,认为他们都是“沙文猪……远不如女人能干”[10]P139,“除了十秒钟制造婴儿半成品的那一点点价值外,男人什么用也没有。男人不过是女人用来制造别的女人的法子罢了”[10]P139。而基列建国后实行男权统治,女性完全沦为男权作用的对象。尽管如此,红色感化中心的使女们利用过去男权“凝视”女性的产物——女洗手间的洞来实现指尖触碰,达成女性之间的交流。在授精仪式中,拥有至上权力的大主教成为“被看”的对象,尴尬不自在:“作为一个男人,被一群女人注视,那感觉一定怪异无比,让她们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10]P99。荡妇俱乐部里,在使女眼中,平日威风赫赫的大主教“脱去了制服,他显得更瘦小、更苍老,像一个风干的东西”[10]P295。女性借助“凝视”将权力主体男性客体化,两性的二元对立慢慢消解。另外,女主人公通过和大主教交往进一步解构了两性对立。她在与大主教的“拼字游戏”中用语言模糊了森严的阶级和性别的等级制度,他们在办公室秘密幽会和“荡妇俱乐部”的经历构成了两人间的投名状,女主人公觉得自己“对他拥有了某种权力”[10]P244,可以对高高在上的大主教“有所要求”,通过性“操纵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10]P166。也就是说,她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主教“拥有了某种权力”,实现了底层女性对上层男性的权力抵制。
其次,基列将女性服饰划分的同时,也将男性划分为若干等级,中阶男性实行婚姻“配给制”,下阶男性则无权婚配。中下阶男性同女性一样,都是权力压制的对象。上阶大主教们的普遍不孕与“渔王传说”形成互文。韦斯顿女士在《从祭仪到神话》中提及过渔王传说:古代部落首领渔王失去了性能力,因而他的部落土壤贫瘠,五谷不结,牲畜不育。弗雷泽在《金枝》中也提到该传说并得出结论:部落繁荣昌盛有赖于首领的生命力,只要首领强壮而有生殖力,其部落就能欣欣向荣,反之则如同一方荒原,荒芜凋敝、寸草不生。著名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长诗《荒原》中也曾借用这一神话讽喻战后民不聊生的欧洲世界。基列国给无嗣的大主教分配使女,本是为了优生优育,保证统治阶级血统纯正,但小说暗示,相当一部分使女成功受孕,是借助低阶男性的基因,并非源于大主教血脉。在生育能力上,中下阶男性挑战了上阶大主教的权威,颠覆了上阶的权力,解构了基列的极权统治。
此外,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女性内部的紧张关系:第一,主教夫人对女主人公的到来十分厌恶,入门时即立下马威,起居室里立规矩,之后又因嫉恨使女各种刁难,双方交往中尽是焦虑和威胁,但在借腹生子一事上,尽管出于不同利益,但她们达成了共识:“至少在这一时刻,亲如密友”[10]P239。使女和夫人的矛盾得以缓和。第二,使女和马大一开始也互相反感,马大嫉妒使女能够远离繁重无聊的家务,使女则羡慕马大忙忙碌碌、有事可做。之后,在疑似自杀事件上,女主人公和卡拉达成保密约定,使女和马大之间建立了默契,找到了“联系我们两人之间的纽带”[10]P174。第三,使女之间最初也是互相监督,相互防备的,对方都是装腔作势的假正经,但是女主人公的搭档主动交心,透露“五月天”组织的秘密打破了她们之间的猜忌,使女之间“终于跨过了那道看不见的界限,走到了一起”[10]P194。第四,女主人公前任使女留下的那行拉丁文书写着她们共同的命运,前任的存在让她不再“以为自己在这里是孤身一人”[10]P335,给了她勇气和力量。第五,奥芙沃伦分娩现场,所有使女“将对方当作自己的身体,努力去感同身受”,以至于产生“腹部有了轻微的疼痛,双乳鼓胀”[10]P142的体感,使女们“灵肉相同……不再是孤军奋战”[10]P144、145,似乎“建立了一个女性文化”[10]P146,一个女性共同体。最终使女和马大之间,使女和夫人之间,以及使女内部都缓解了敌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二元对立的消解,走向了女性的“大同社会”。
本文围绕“极权政治”这一核心概念,论述《使女》中权力运作与权力反抗问题。基列极权通过一系列国家治理术开展生命权力驱策下的权力运作,具体表现为例外状态常态化、个体群体化、人口管理、性的操控、种族排斥等。同时,被权力征用的基列民众也从个体和群体双重层面开展权力反抗:个人层面,使女用边缘化“他者”口头叙事颠覆了历史的宏大书写叙事;群体层面,两性群体之间、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内部二元对立的消解,解构了基列极权政治。小说开放性结局为人类走出极权世界的二元对立,走向大同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2019 年,80 岁的阿特伍德出版了《使女》的续篇《证言》,再次问鼎当年布克奖。这本续作中,阿特伍德采用多声部叙事,通过基列国三代女性之视角,揭露了基列共和国末期的腐败和灭亡过程。其中,有关基列国末期的极权运作、丽迪亚嬷嬷形象的变化、续作与原作细节的呼应和背离等等,可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未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