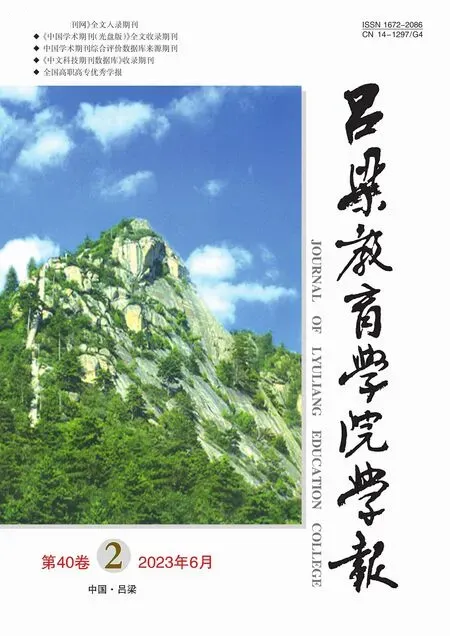身体空间的书写
——以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为例
2023-02-12孙俊瑶
孙俊瑶,张 涛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异化之始——身体内部空间的分裂与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的肉体和精神双重伤害,于是卡尔维诺将战争影响下千疮百孔的身体与精神彻底分裂,裂变成多个看似违背常理,却又真实反映现代人现状的空间。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一方面身体与空间的结合成为其新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裂变状态是为表现现代社会冲击之下人异化的状态,这恰好也是卡夫卡与卡尔维诺都擅长的。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从身体内部空间的分裂来书写的。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1]145-146,即身体与所处环境共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混乱的战争背景下,全球的伦理环境都遭受到了摧残,人人都卷入到战争的世界中,梅达尔多子爵形象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指路的断手”“满地的死尸”“吃人肉死掉的鸟的羽毛”等,随处可见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战营里艰苦的戎马生活,战士们流露的厌倦情绪。梅达尔多子爵却无比地轻盈,丝毫不曾对战争的残酷有所畏惧,或者说,他是带着童真般美好的幻想来到战场,而残酷的现实终会使幻想破灭。战争中的梅达尔多子爵受伤裂变成两个不同的身体空间,一半在医院中得到救治。战地医院恰似烈焰地狱,其中死尸与伤者的戾气和残酷性远比战场还要惊悚,医生对于士兵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威,这个“半身人”从医院中侥幸归来,成了恶的化身;而另一半被两个宗教信徒的怜悯之心治愈,在众多基督教国家的熏陶下成为善的化身,就像“潘多拉盒子”的底部一样,保存着善良和怜悯之心。但他具有理想色彩,虽然能在言语和行为上治愈他人,行动却不切实际,根本无力打破混乱的伦理现实与裂变的空间状态。他与恶的一半所形成的空间都不为人们所处的原有空间所容纳。
战争使得梅达尔多子爵的身体分裂为善恶两半,尽管他们都爱上了帕梅拉,但对爱情的看法依旧呈现出不同态度。恶的一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他试图将自己身上的恶灌输给帕梅拉,企图以囚禁的方式逼迫她接受自己的恶,沦为自己的玩物。而“善”的一半对于帕梅拉的爱情也是强制的,爱情就是应该行善。面对帕梅拉的身体诱惑,像极了苦修禁欲的清教徒,他忽视帕梅拉对自己的爱,把自己的人生信条灌输在帕梅拉身上,希望帕梅拉用身体去拯救“恶”子爵,这种强加他人的爱情思想也是病态的。分裂的梅达尔多并不为证明善恶究竟孰为对错,而是表明裂变后的身体比起完整迂腐的身体,才真正具有了人性,成为有思想感情的人。战争使得“完整人”分裂为“半身人”,他们与之前完整的身体相比较,他们的对世界的体验和感觉被放大,他们摆脱了最初作为完整人的无感,可以用“半身人”的观念去理解和体验世界的不完美,也对自己留下的身体的一半感到弥足珍贵。二者皆从对世界的无感转而表现对世界的关注,从而联想自身存在的意义。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那时“正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2]93卡尔维诺在压抑的冷战气氛下模仿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对立,将人物身体空间也分裂成善恶两部分。然而他想探讨的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展现现代人身上逐渐蚀入骨髓的异化状态,卡尔维诺试图借助融合来缓解异化趋势,融合的身体不再是最初被驯服的状态,而成为精神与肉体、伦理善恶在身体内部空间博弈后达成平衡的结果。卡尔维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战争背景下长期压抑的环境导致人的身体空间的分裂,恰恰体现作者对于身体空间分裂导致异化人的初期发现,他希望借助简单的二元分裂和融合,呈现现代社会存在的异化现状,引起对现代人的初步关注。
异化延伸——身体外部空间的压抑与排斥
相比较战争与权力对人身体内部空间的作用,《树上的男爵》中则体现了权力在家庭、社会中的运行下身体外部空间的分裂,它以轻松愉悦的笔调形成树上与树下两个并行的空间。树下的世界代表权力对身体行为的压抑和个性的丧失,而树上则是绝对的自由。为反抗树下世界,柯希莫企图建立树上王国。但西班牙贵族们最终在国王的号召下还是回到地面。“你要后退吗?不,是抵抗。”[2]163柯希莫为了自由和个性爬上树,怎会听从像父亲一样迂腐的西班牙贵族重回过去泯灭自我的生活呢?
在爱情的态度上,柯希莫也呈现了进步的爱情观。柯希莫渴望爱情,但他不愿意在爱情中失去自我。两段失败的恋爱经历都在试图表达,无论是婚姻的捆绑还是自我个性的丧失,与爱情之中现代身体的需求都相悖。柯希莫拒绝了一见钟情的乌苏拉,在他看来,“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2]163他选择留在树上,坚持自由的生活。薇莪拉的归来,让他内心对爱情与自由之间再次痛苦地博弈。薇莪拉认为的完美爱情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并放弃自我,她将爱情塑造成身体和心灵的囚牢,要当爱情中的统帅者,而这与柯希莫的“理性地保持自我”相悖逆。柯希莫视树下薇莪拉的两个追求者为没有理性的“爬虫”,始终保持着“我和我的想法是统一的”[2]213观点,二人在爱情观上对身心不同的要求,也注定他们会再次分道扬镳。无论是来自树下家庭的威压,还是爱情中自我的渡让,柯希莫始终坚持自我,与树下“隐形”权力运作的社会保持距离。他像一个游荡者般观察着整个世界的运作,热爱着自己孤独而又自由的人生。
《树上的男爵》借助启蒙时代的话语,将身体的个性与自由提上了新的高度。柯希莫不愿放弃自己的个性,不想受权力世界的约束,这层与树下世界的隔膜也注定了孤独的命运。“他像上帝一样观察着人们的生活,热爱地上的一切。他一直在利用树上的空间为自己创造一种专属于自我的生活形式,为自己找到了在他人与自我之间游走的恰当的平衡点。”[3]树上的柯希莫是“自然人”的代表,自由地无拘无束,却无法断绝与地上的联系,就像他的墓志铭一样:“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2]262-263柯希莫一直试图在这两个空间中寻求最佳生存状态,他既不想丧失自我,也不想回归权力世界的压抑,他在平衡中不断地寻求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避免权力社会对自我的泯灭和异化,但最终寻求无果,只能孤独一生。法国画家莫罗曾经画过一幅《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画中斯芬克斯是权力与欲望的共同体。上半身的斯芬克斯容貌美丽,诱惑的胸脯依偎在俄狄浦斯怀中,下半身却用兽性的爪子对准俄狄浦斯的身体,暗示人们在权力与欲望面前很难坚持自我。柯希莫生命的每一刻都顽固地追求自由,追求自我个性,为自己和他人坚持世俗社会所不允许的特立独行。他在欲望与权力掺杂的世俗社会,能够坚持自我、独立个性是格外难得的,它对于身体的理解相较于前一部作品更具有启蒙意义。相较于前一部展现现代人走向异化的初步状态而言,此作品则更深入探讨异化会逐渐吞噬人的自由和个性。面对现代性不可逆转的趋势,作者尝试借助启蒙时代的话语,希望人们无论面对权力还是欲望,可以坚持自我,重构主体性的话语,建立一个以理性为维度的全新的生存空间,莫让身体再度回到压抑和沉寂的生存状态。
异化完全——“非人”身体空间的虚无与幻灭
现代性不可逆转的趋势已将人们的主体性湮灭,只留下如机器般没有灵魂的“非人”。《不存在的骑士》呈现的便是异化的完全状态——精神与肉体的分裂。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世界中,身体一直处在被规训的状态下,士兵的身体规训来自统治者最高权力的运作,然而“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相反,它在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内运作。”[4]30从最高的统治阶层流向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身上,无形之中形成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在这种规训下,身体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并幻化成一些驯服的意象和符号,成为镶嵌在这套权力机制中的一个个齿轮。”[5]身体规训的过程也被涂尔干、莫斯、布迪厄等人重视,他们认为:“这一反复的实践逐渐内化进身体中并养成习性,但是这个习惯不仅仅是身体性的,它也以认知的形式出现。”[6]21没有肉体的精神依旧延续,恰恰体现权力对人思想的控制,而卡尔维诺笔下的阿季卢尔福正是这类人的象征。只靠意志力存在的骑士阿季卢尔夫是个军人,既是纪律的忠实拥护者,也是完美的爱情对象。看似符合一切士兵标准,实则却有着巨大的缺陷——没有肉体,这恰恰体现了卡尔维诺笔下权力控制士兵身体的一套规则的极大讽刺。“肉体是驯服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他们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7]154所有的士兵都为统治者权力中心服务,他们所接受的军事化教育都成为了精神烙印深深地刻在阿季卢尔夫的世界中,使他成为规训下最完美的士兵。同样在战争背景下还存在着只有肉体没有精神的古尔杜鲁,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他的行为,但从未有人对其存在产生质疑。他与阿季卢尔夫产生鲜明的对比,形成两个并立的身体空间。一个是被权力规训和控制的身体空间,另一个则是未接受控制,自由的“自然体”。卡尔维诺塑造这两个空间,抛出了有关异化的重要问题:混乱的战争背景之下,究竟做一个被规训异化的机器,还是一个未经规训的自由人,该如何去寻求人存在的状态和意义?
第三部小说《不存在的骑士》相较于前两部对现代性于身体的作用有了更深层的思考。二战结束后的意大利致力于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高强度的垄断与机械化将所有个体卷入生产之中,每个人都像运行在机器上不可分割的零件,被捆绑束缚在机制体系中,成为失去人格、自我的“单向度的人”。阿季卢尔福时常感叹这种生活以及自身的幻灭感,他说:“如果我打瞌睡,哪怕只是一瞬间,我就会神智消散,失去我自己。因此,我必须清醒地度过白天和黑夜里的每一分每一秒。”[8]18由此可见,作者用一副空盔甲,展现中世纪对骑士身份与战争荣誉的嘲讽,阿季卢尔福在荒谬的世界边缘不断地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实则是在掩盖自我意志已经逐渐消失的命运,更表现出他的空虚和异化。荒诞战争背景下的不存在的骑士,恰恰体现现代社会各行各业中所代表的一类人的隐喻,他们已经像卡夫卡笔下异化的甲虫一样,没有思想和个性,习惯了现代社会带给他的压迫和束缚感,成为空洞无感的“机器”和“工具”。不存在的骑士所拥有的“习惯的状态”,象征着现代社会的荒诞与虚无。阿季卢尔福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的“非人”,其完整健全的人格系统不复存在,也无法把握自我命运,只能埋没在现代社会空虚荒诞的世界中,随波逐流且无力改变。
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中围绕身体与空间创作了三组不同的小说,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身体都逐渐与所处的空间发生裂变,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逐渐异化的表征。卡尔维诺试图揭示其异化根源,寻求扭转异化趋势的方法论,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相比较第一部作品身体空间的分裂尚且带来了摆脱异化的希望,《不存在的骑士》却已经展现笔者对于整个社会的绝望和无力之感。从人性异化的思考,辗转于启蒙对身体个性自由的深思,最后拓展到对整个社会异化现状的思考,《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全部围绕身体空间的裂变,来反思伴随社会发展而逐渐深入的现代性困境。在这三部作品中,可以梳理出异化逐渐深入的痕迹,而之后卡尔维诺的创作也使得身体与空间的对接更加娴熟。
结语
从古希腊身体的二元对立,到梅洛·庞蒂身体空间的提出,以及卡尔维诺身体空间在作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卡尔维诺作品中频繁呈现的身体空间裂变状态以及发展脉络。卡尔维诺试图凭借身体空间的裂变书写进行批判和反思现代社会对人身体的束缚和压抑,并将身体置于二元对立的空间中进行对比,表现不同空间的对立和博弈的过程,并试图让二者逐渐适应融合,达到平衡,这种开放多元的身体空间书写恰恰体现时代发展下身体逐渐启蒙的历程。卡尔维诺针对身体抛出深奥的哲理思想,探求身体空间裂变后带来的现代意义,他不仅完成了空间的构建,也实现了身体与空间的融合,对空间极具思辨性的探索也使得他的空间书写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