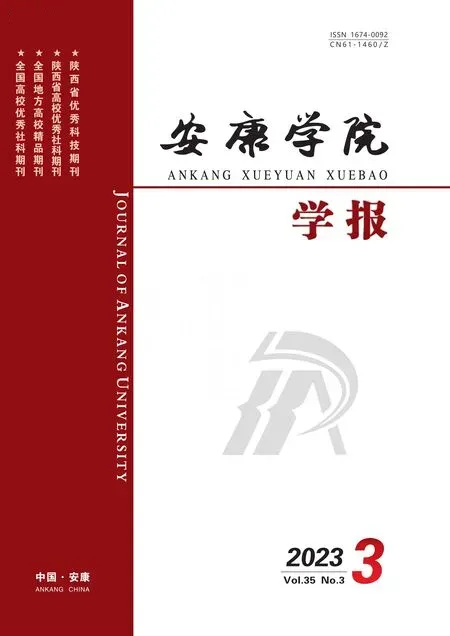清初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选评
——以张伯行为中心
2023-02-08赵豫陇
赵豫陇,高 凡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从明中期开始,关于“唐宋八大家”的选本渐多,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唐顺之《文编》等。清代文人编选大量相关选本,直接以“八大家”命名的有吕留良《晚村八家古文选本》、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刘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等。储欣等人的选本体例较大,独有张氏选本较精简,方便流通,评语多从理学角度出发。从张氏选本可看出清初文化导向,展示理学与文学间的矛盾。从理学角度来看,张氏《唐宋八大家文钞》标志着清代“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1]分化的开始,有着典型性意义。但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本书对古文的评述并不成功。
一、张氏选本的体例与选编思想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选本同名,体例较为接近,明显受到茅坤影响,但篇幅仅是茅本的八分之一,张本仅有19卷,而茅本多达164卷。在选择作家作品的比例上有较大差异,张氏选择苏洵文仅有1卷2篇,苏轼文1卷26篇,苏辙文2卷27篇,曾巩文7卷128篇,王安石文2卷17篇。茅坤选择韩愈、欧阳修、苏轼的篇目较多,曾巩文章反而最少。从选择篇目上可看出张伯行对曾巩大为赞赏,大力排斥苏洵。从整体来看,茅坤对八大家文的选择内容较分散,态度较公允,对诸家数量把握较平均。张伯行选择三苏文的数量大不如前人,在评语中多有批评。
张氏选苏洵文只有《上仁宗皇帝书》《苏氏族谱亭记》,苏轼文有《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伊尹论》《晁错论》《范文正公文集序》《六一居士集序》《李君藏书房记》《喜雨亭记》《潮州韩文公庙碑》《日喻》《书六一居士传后》等27 篇,苏辙文有《再论分别邪正札子》《上枢密韩太尉书》《上刘长安书》《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臣事策六》《黄州快哉亭记》《管幼安画赞》等27篇。如果将《赤壁赋》看成前后两篇,那么苏轼和苏辙二人的文章数量是一致的,这很有可能是张伯行有意为之,三苏文共有56篇,占全书316篇的六分之一。曾巩文却多达7卷128篇,超过三分之一。张伯行对王安石采取贬斥态度,仅选其文17 篇。张氏甚至责难道:“王介甫以学术坏天下,其文本不足传。然介甫自是文章之雄,特其见处有偏,而又以其坚僻自用之意行之,故流祸至此;而其文之精妙,终不可没也。”[2]5
张伯行突出苏轼、苏辙与欧阳修的继承关系,因为二人都有《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苏轼《六一居士集序》《书六一居士传后》与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记载了与欧阳修的交往。张伯行强调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核心的文人团体,故多次选择和欧阳修相关度较高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氏削弱了三苏的独立性,把三苏归附在欧阳修的影响力之中。张伯行评《六一居士传》:“欧公晚年寓意之文。东坡集多得此解。”[2]153张伯行极为注重道统的连续性。他提出:“至欧阳公出,文章遂为天下宗匠,学者翕然师尊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事。此其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2]3张伯行以朱熹为圭臬:
朱子曰:“六一文一唱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又称其“平淡中却自然美丽,有不可及处”。读公之文者,当以是说味之。[2]3
仅以欧苏相比,张伯行明显崇欧抑苏。张伯行把三苏归在欧阳修的影响之内,既推崇欧阳修“通经学古”的道统性,也暗中削弱苏氏父子的独立性。如果张氏以朱熹之意贬斥三苏是外在的、直接的,那么用欧阳修为准绳牵制三苏是内在的、间接的,这是张氏选本中欧苏勾连的成因。深究张伯行的编书思想,要从张氏学术入手。《清史稿》载:
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览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杂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3]9939
张氏的理学著述有《道学源流》《道统录》《伊洛渊源录续录》《原本近思录集解》《续近思录》《性理正宗》《正谊堂文集》等。张伯行在《困学录》中谈及学习方法:
学者实心做为己工夫,须是先读《五经》、《四书》,后读《近思录》、《小学》,则趋向既正,再读薛文清《读书录》、胡敬斋《居业录》,然后知朱子得孔、孟之真传,当恪守而不失。再读罗正庵《困知记》、陈清澜《学蔀通辨》,然后知阳明非圣贤之正学,断不可惑于其说。从此观诸儒语录,则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黑白,可以无歧趋之惑矣。[4]557
张氏主张沿袭儒家的传统路径,从四书五经到程朱著作,有着强烈的明道尊古意识。张氏把学术和正心联系起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主张,在张氏的教育体系中成为关键,学习的目的在于为己、正心。张氏门人张霖朱评述其重道观念:“吾师敬庵张先生以明道觉世为己任,直接紫阳朱子之传,学者当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寻求于文词章句之间,此非霖一人之私见也。然文以载道,道非文不传,舍是以求先生则又不可。”[5]312此评述仍是朱熹的主张范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6]清初文学观念的重道色彩非常浓厚,挤压了文学的独立性,文章为传道服务。张氏表现出保守内敛的心态:“为学如吃饭,无论家常饭食,须是吃在腹里,方才会饱。若不实在吃了,只向口头去讲,虽说甚么精馔,说甚么美味,非不倾耳可听,终是济不得饥。”[4]558以吃饭喻学强调自我满足。
张伯行对苏轼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选择数量不够,评点较为刻板,赞美点评集中于文风,对作文思想处处提防。张氏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文章分类不够细致,基本上按照策论文在前、记叙抒情类文章在后的方式排列。张伯行对曾巩文选择较为细致,体例编辑较整齐,主要有“书”“序”“记”“启”“状”等类型,三苏文的编辑较驳杂,不成体系。就整部选本来看,张氏着重推崇曾巩,直接贬损王安石,暗中贬低三苏的“心术”“权术”,部分肯定三苏的文采。“三苏古文”在张氏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处于劣势地位。
二、理学视角下的“三苏古文”评点
张伯行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进士,以推行程朱理学为己任。“然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5]263“惟敬庵专宗程、朱,笃信谨守。”[4]553张氏对三苏的态度在《三苏文引》中直接体现出来: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此言极得苏氏之病。[5]3
张伯行认为三苏文章效仿纵横家,并非来自儒家,对三苏文十分挑剔。张伯行对三苏文被广泛关注做出阐释,他认为:“盖正大之旨难入,而巧辨之词易好也。且以其便于举业,而爱习苏氏者,尤胜于韩、柳、欧、曾”[2]3。三苏文风更华丽平易,甚至大超其他五家。《宛陵先生年谱序》:“宋嘉祐二年,诏修取士法,务求平淡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贡举,而先生为试官,于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横渠张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间,不惟文章复乎古作,而道学之传,上承孔孟。”[7]苏氏兄弟平易的文风本是科举的产物,“不惟文章复乎古作,而道学之传”证明了苏文的内在价值,所以能被广泛接受。但纵横家的本意在于说服,文字有着鲜明的目的性,论说道理时有着强烈的策略性,甚至诡辩性。张伯行对三苏文章受到纵横家影响的风格极为不满,他以朱熹为论据否定其价值:“朱子自谓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自家意思都不正当,以此知人不可读此等文字”[2]3。朱熹对苏洵文章的批评是站在理学立场上的,从古文角度来看,朱熹的评价未必公允,甚至其中隐含有理学与蜀学之争。张伯行以卫道为第一目的,忽视了古文的重要特征——说理。古文的说理特征早在唐代就有人指出:“文以理为本,而辞、质在所尚。元宾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质,故理胜其辞。”[8]唐人沿用孔子的“文质说”,肯定了以“文”为代表的词藻和以“质”为代表的思想可以共存,二者各有所长。不论“文”与“质”如何消长,在古文创作中都要以“说理”为第一线索,三苏发扬了古文的说理功能,张伯行有意贬低三苏的态度让选本的价值大打折扣。
古文有载道作用。“骈文属于言志的系统,与之相对,古文是由载道观念所支配。骈文与艺术接近,古文则与载道文学、儒教体系密切而且专致于此。”[9]11可以说苏轼把古文推向了最高峰。“如果说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话,那么宋代则是文人的觉醒,文人的自我意识变得非常强烈,他们的价值标准不再是立功、立德,而是立文,借立文以实现自己不朽于青史的自我价值。”[10]328张伯行对文学自身的变化规律把握不够,有意忽视古文强烈干预现实的因素。
就具体篇目而言,张伯行选择苏洵的《上仁宗皇帝书》《苏氏族谱亭记》,这两篇文章都不长,缺乏代表性。张氏评《上仁宗皇帝书》:“召试不赴,盖得难进之义。所上书辞旨多未纯,故不录。盖苏氏议论足以动人,熟其文,便不知不觉深入权术作用去也。”[2]174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辞藻修饰,苏洵做不到儒家所谓纯正的文学观念,更何况张伯行心存芥蒂,对“权术”大为排斥。张氏评《苏氏族谱亭记》:“文字峭刻,而道理醇正,余于老苏集中,独取斯文。”[2]175苏洵作此文为团结亲族,以礼仪和等级规范乡里亲族,这类文章在众多族谱类著作中较常见,不算有特色。儒家道德规范中“修身”“齐家”是最基本的主张,张伯行对此文评价甚高不过是“瘸子里拔将军”罢了。与张氏看法相反,其他选评家看出苏洵“道理醇正”背后的辛辣讽刺。茅坤指出:“此是老泉借谱亭讽里人并族子处。”[11]328沈德潜则认为此文不够精致:“族谱亭记篇,面目太粗。”[11]328沈德潜和张伯行评论的差距要从二人的学术背景考量。沈是诗人,对诗歌散文的赏析多从形式、词采方面评价,而张是理学家,把眼光局限在思想层面。苏洵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直指里巷小人的弊端,毫不隐晦,正是“面目太粗”的原因。
张伯行对苏轼论、书、序、记、赋等文的选择较平均,选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抒情散文有《喜雨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其余都为说理记事等实用类散文。其他选评家注意到《留侯论》变化纵横的优点,王遵岩说:“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2]181;茅坤说:“然子瞻胸中见解,亦本黄老中来”[2]181。翻陈出新是苏轼的优势,苏轼长于做翻案文章,对事实重新解读,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但这在张伯行眼中成了“权术”的操纵:
论子房生平以能忍为高,却从老人授书、桥下取履一节说入,乃是无中生有之法。其大旨则本于老子柔胜刚、弱胜强意思,非圣贤正经道理。但古来英雄才略之士,多用此术以制人。学者若喜此等议论,其渐有流于顽钝无耻而不自知者。故韩信之受辱胯下,师德之唾面自干,要其心术皆不可问也。[2]182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基本上以儒家为主,对佛、道等思想都有所吸取。”[12]20《留侯论》充分说明了忍辱求生、以退为进的道理。张伯行主张儒家正道,警惕心术不正者和权术的使用。这种警惕早被康熙提出:“宋、明季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13]2222与之相通的是张氏评注《贾谊论》再次强调心术和权术的危害性:“则是权诈作用,并将上面所引孔孟皇皇救世之心,都错看入此途去也。此最坏人心术处。读者勿徒爱其文,而忘其理之不正也。”[2]184张伯行对于苏辙也毫不放过,评《上刘长安书》:“文气峭劲,笔锋犀利;但以拙养巧,以讷养辩,又入权术法门矣。读者不可不知”[2]227。张氏评价苏辙文风还算公允,但对文章思想却暗含贬斥,即“以拙养巧,以讷养辩”,儒家一贯反对“巧言令色”,“巧”和“辩”都是动机不纯,归于“权术”。对于孟子的浩然之气,苏氏父子与张氏有不同的理解。张伯行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道:“苏家兄弟论文,每好说个气字。不知圣贤养气工夫,全在集义。而此所谓旷览山川,交游豪俊,特以激发其志气耳,与孟子浩然之气全无交涉也。”[2]222张伯行对于三苏文处处警惕批评,绵里藏针。
张伯行重视作文的实用性,但仅限于阐释儒家学说,排斥文学的审美功用。张氏评《张君墨宝堂记》:“学书费纸,学医费人,世之学无用诗文,以费精神、费岁月者多矣。吾愿其亟返而自省焉。”[2]203张氏认为作无用诗文毫无意义,无法欣赏生活情趣。对于苏轼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张氏评价极为简短。张氏评价《喜雨亭记》仅一句,对苏轼溢于言表的喜悦毫不在意,张氏忽视古文中的抒情性。苏轼理解的“道”是形而上的客观规律,而张伯行的理解是形而下的、局限在儒家主张中。如《日喻》中运用惟妙惟肖的比喻,说明具体实践的重要性,对生活中一般规律的总结正是古文的说理作用。但张伯行对此文仅敷衍点评一句:“两喻俱有理趣,思之令人警目。”[2]216
三、复古——文统与道统的矛盾
三苏古文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宋代文化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是打着复古进行的”[10]31,苏轼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目的,他赞誉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14]603,故苏文亦用文统干预道统。最为重要的是:苏轼以文章为工具弥合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张氏的复古和“唐宋八大家”在政治和文学中提倡的复古完全是两回事。张氏的复古有着强烈的理学烙印,以清廷的文章实用要求为出发点,反对“尚奇”“炫耀”,这注定张氏的主张较为保守。其文《圣人可学而可至论》写道:“稍知学者,率皆求之高远,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探异,日从事于不可究极之域,以炫耀示人。”[4]564苏轼弥合的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在张伯行这里再次浮现出来,使此选本彻底走向“重道轻文”。
张伯行处于清初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时刻,康熙重视理学并提拔了一批理学大臣,“作为封建帝王尊崇的程朱理学,无非是其统治术中所需要的工具,他们并不喜欢那些抽象谈论性理的空言”[15]14,张氏心领神会。他评欧阳修《乞补馆职札子》:“用人之道,不当重材能而轻儒学,可谓深识治体之论。”[2]123后人对张氏的评述也注意到了儒学复古与恢复秩序的内在线索,即从孔孟直达韩柳。乾隆时人高斌作《正谊堂文集序》:
昌黎之文跨越百代,同时如子厚、习之辈出,其所作磊磊明明,莫不互相雄长。然泰山北斗之仰必归昌黎,则以尊信孔孟。若《原道》及《答孟尚书》诸篇,提阐圣绪,力辟异端,实关乎世道人心,而非华而不根者比也。方今圣圣相继,正道昌明,海寓承学者类知宗仰濂、洛、关、闽,以溯邹鲁之渊源。然高明之士不屑平近,希心顿悟,默浸淫于新会姚江之说者多有之矣,于此有墨守程朱心之身之以助流圣化、昭示来兹者。吉光片羽为有识所珍传,应不在昌黎下。大宗伯张清恪公自幼即志于圣学……[16]123
高斌极力提升韩愈的地位,在于塑造一个典型的复古人物,在序言后半部分高斌才显露出真面目:以韩愈为张伯行做铺垫。后世称张伯行为“敬庵学案”,张氏在一定程度上同韩愈一样,起到了复古理论再度归附的作用。
张伯行重视严谨的人品,但苏轼为人旷达,“苏轼在政治活动中文人习气浓厚,往往意气用事”[10]223。苏轼的独立精神是宋代文统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宋人以文统促进道统的发展,苏轼的文章确实推动了北宋古文运动,苏轼以海纳百川般的学术功底消解了“文统”与“道统”间的矛盾。《宋史·苏轼传》:“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17]10801苏轼的学术根基和心理认同是以庄子、贾谊为代表的文人系统。“蜀学确实有杂学之嫌,而其虽杂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文人之学。”[10]230张伯行不具备苏轼兼备儒释道的学术素养,处处以程朱理学为教条,纵横文风在张氏眼中成了阻碍,在整个选本中对古文的抒情性几乎没有什么评点。“从文学散文的角度而言,抒情是散文的一项重要职能,情感是散文的血液,没有血液,散文就难以血肉丰满,难以感人。”[10]63情感是古文的灵魂,张氏的做法抽取了古文的灵魂。张伯行对苏轼的具体观点亦有驳斥,如《陆宣公文集序》中直接反驳苏轼对陆贽的评价,认为“然则苏氏之论公者,公固未必许为知己也”[5]261。张伯行认为写文章当遵守君臣等级,重在实用。“读贾生之文,雄伟可喜,犹杂以策士纵横之余习。而公之文周详委曲,恻怛恳挚,洞悉情事而惬适人心,故草诏之下,能使将士读之流涕奋发,而猜忌如德宗犹能听纳以收其益,盖感人以诚而不在于辩。”[5]261贾谊、苏轼都以好辩出名,张氏推崇陆贽文章中的真诚、实用的方面,排斥纵横论说的文法。
宋代苏文多被批评,“言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此所以不能自重,坐讥讪得罪于先朝也”[18]9444。宋代文士团体对政治的影响甚大,没有哪一个朝代可以相比。苏氏父子经历了北宋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目睹了文学的作用,甚至参与其中。余英时总结了“熙宁变法”中以学术著作推动政治变革的意义:
由此可见“文”在熙宁变法中所占据的枢纽性地位。若用刘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文”是一条历史主线,把“体”和“用”绾合在一起了。[19]308
清初从统治者到当朝学士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安抚民生上,不希望再生变乱,自然对三苏文有所警惕。张伯行对文学的政治功用有所察觉,这是他对三苏和王安石警惕的最大成因。
方苞认识到八大家的学术与文风不同:“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大家言之,韩及曾、王并笃于经学,……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文字之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闻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韩、欧、苏、曾之文,气象各肖其为人。”[20]164—165张伯行推崇“醇正”的学术观点,显然不能区分不同的文风。
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齿奇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3]9940
与三苏相比,曾巩对文章学的意识更加清晰,在《王平甫文集序》中说道:“自周衰,先王之遗文既丧,汉兴,文学犹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尽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及其衰而遂泯泯灭矣。宋受命百有余年,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21]462。曾巩先后用“遗文”“文学”“文章”三个概念,表现出文学自身的流变。北宋学者开始注意到文章的影响力。程颐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2]187虽然程颐是站在理学家的角度批判文学对理学的侵染,但从侧面反映出文章学在北宋的形成。文学在较短的时间段内会产生兴衰更替,但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会有持续性的变化,曾巩为宋代文章学的发展找到了合理且有力的依据。在曾巩眼中,宋文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化成果,但清代理学家看到的是曾巩对过往历史的回溯,更注重统续性,即“道”本身存在连续,宋文是对道统的继承。这是张伯行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大力选编曾巩文的重要因素,这种价值取向在张伯行的《立言部总序》中表露无遗。
程子曰:“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夫六经四书德盛之言也,继此而先儒遗书犹庶几焉!所谓文盛言传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门设教,分为四科,群弟子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后世源远而流益分,豪杰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于世者,其趋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观世变矣。……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后伟,其意精神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经而显,足以周当世之务,此韩柳欧曾苏王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者,夫岂偶然也哉!虽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圣贤非有意于文也,本道而发为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见道,故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在读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选是集不特以资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学者诚能沿流以溯源,究观古圣贤之所以立言者,则六经四子而下程朱之书具在,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16]182—183
立言本为儒家主张,张伯行认为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价值在于表现出时代风气变化,有记录功用。张氏把八大家归纳入孔门四科的历史传统中,打压了文章的独立性,以道统为重。张伯行对文人之文明确反对,提出编辑古文选本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举业,而是在于穷理格物,以唐宋而上溯孔孟才是其编选文集的目的,唐宋八大家所形成的文统在张氏眼中不如孔孟至程朱的道统。
张伯行反对苏轼文章中的比喻联想,如在《书六一居士后》点评道:“人之所以异于物者,以其能别是非,而不为物累也。若以有知觉之人,与无知觉之物等而视之,谓能不累于物,则天下无是理也。欧公自号六一,聊以寄兴,未必有此意。而东坡以老庄之旨,从而为之辞。此朱子所以讥其不根而害道也。存此而论之,以概其余”[2]217。文学本身具有虚构性,苏轼常借题发挥。张伯行没有把握好文统与道统间的平衡,完全倾向于道统,导致选本中过分强调朱子学说中的性理之学,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发展特色。从张伯行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其作为“道学先生”迂腐的一面,不能深刻领会文章的美感,处处强调道德教化,大大降低了此书的文学性。此书限于篇幅,对诸家的选文总体较少,难以使读者深入了解八大家的思想。
四、结语
“事实上,康熙期间唐宋八大家文在流行,……并且初期的考证学派、古文作家、时文作家之流并非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中,在巨大的时代思潮之中他们也都具有相近的风气。”[9]160清初八大家文章的流行有着深厚的历史成因,交织着诸多因素,比如学术走向更为细致的考证,科举的需求,以及古文创作自身的演变等。张伯行重道轻文,没有处理好道统和文统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三苏古文的文学价值,如文章的审美价值:
“文”被看重,最根本的就是“文”的审美特性被看重。与宋人重“文”思想相呼应,其文学思想中也出现了崇“美”的倾向。[23]301
苏轼古文的成就不是孤立的,放在整个宋代文化中看,苏轼的价值在于兼收众长,与其他各种文体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能吸取其他文体的长处,亦能打破其他文体的限制,这是苏轼“破体”的成就。“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24]323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创作出的文章风格与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人文风大为不同。“宋文与唐文相比,要平静得多,较多条理性,较多分析性,较富于细微的观察,穷根究理的倾向也较多见。”[9]15“宋的古文与唐的古文的最重大的差别,在于表现手段方面理论性的彻底。”[9]78张伯行推崇欧阳修、曾巩文章的儒家道学成分,从侧面肯定了宋文中穷理的特性,但因为三苏文采成就较高,掩盖了道统线索,导致张氏对三苏大有偏见。更何况张氏的理学有漏洞之处,康熙申饬云:“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朕博览载籍,即道书、佛经无不记识,讲即讲,作即作。若以朕为天纵使然,此即是逢迎朕者也。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13]2228。张氏的主张不过是迎合康熙罢了,未必对学术有切实理解,张伯行对康熙的要求不过是做做样子,他对文学的理解未必深入准确。苏轼古文成功标志着宋代文章学的全面胜利,与唐文化的结晶诗歌相对,宋代文化的结晶为宋文。佐藤一郎道:
有“唐之诗,宋之文”这样的说法,“宋之文”已被认为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代表时代的一种文学体裁。[9]15
“是以其立足儒学,通达庄禅的人生态度,萧散简远的美学追求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树立了典范意义。”[10]241苏轼的人格价值是张伯行不能触及的。
当然不能否认张伯行编选此书有独特的目的和成就,此书主要服务于科举,作为学者和官员的行为指南。如曾巩《救灾议》被张伯行大为肯定:“读子固此议,下为百姓计,上为公家计,大要存破去常而速为之赈救。深思远虑,无微不彻,真经济有用之文,学者所当留心者也。”[2]419张伯行着重强调文章经世济民的作用是出于廉吏爱民,“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3]9937,张伯行并非意识到了古文干预现实的功用,但他的点评符合为官主张。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有着推动“唐宋八大家”继续经典化的作用,使人一窥唐宋八大家文章,以选本的“点”反映出清初理学文化这个“面”,标志着“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的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