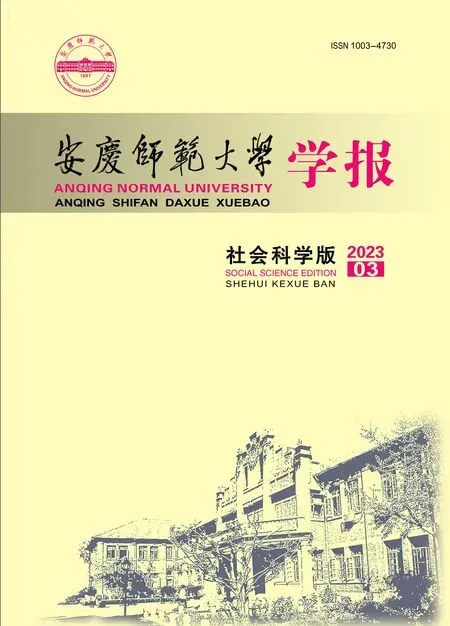纪录片《奇妙之城》的空间建构与意义呈现
2023-02-07王恒乾
王恒乾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城市是地理与物质的客观存在,亦是特定空间下社会关系与人文精神的集合。2021 年,由著名纪录片导演萧寒执导、优酷出品的城市人文纪录片《奇妙之城》运用艺术化的镜头语言与情感化的叙事技巧成功构筑起贵州、重庆、厦门、西安、克拉玛依、青岛六座城市的“自然之奇、人文之妙”。自1月5日开播以来,全网视频播放量超10亿,豆瓣评分8.8 分,微博的话题总阅读量超过74 亿,成为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纪录片之一[1]。20 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把空间由自然领域引向了社会、政治、精神和哲学等一系列领域。纪录片《奇妙之城》作为地域影像表述与形象传播的载体,通过对城市空间下社会关系与人文精神的挖掘,实现城市文本在情感层面的意象传递,完成了媒介空间下的文化表征与意义再生产。
一、本体视角下城市物象的立体表达
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重基本层次。物理空间作为空间理论的基础维度,强调人们直观可感的物质性与客观性。《奇妙之城》将城市物理空间下的景观风貌通过客观的视听符号与主观的具身走访呈现在观众面前,为城市物象的表述提供直观、立体的叙事文本。
(一)视听符号建构城市的物理空间
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地,其内部的自然风貌、地标建筑、人文景观构成了城市地表空间下独有的物质形态。纪录片《奇妙之城》以诗意化的镜头、高清摄像技术与流畅的剪辑,综合运用延迟摄影、航拍、滤镜等影视语言,构筑起六座城市斑斓多姿的光影魅力。
从视觉角度看,形态各异的建筑分布与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既完成了城市空间下的地域表征,也渗透着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人文发展的内在逻辑。六座城市各具特征的视觉符号在慢镜头与特写镜头交织中充溢着真实、温馨的色彩。云贵高原民族村落群滋养着贵阳的少数民族的热情;山城重庆错综复杂的自然地貌建构出当地8D交通;海滨厦门恬适的生活渗透出的浪漫浓厚的艺术气息;凝结历史风雨斑驳不堪的城墙下孕育着西安厚重的历史;夕阳下大漠孤烟勾勒出克拉玛依的戈壁风情;浓烈的啤酒文化洋溢着青岛的乐观洒脱。从听觉角度看,小商贩热情的叫卖声、菜场熙攘的生活声与公园游人的欢笑声等同期声相互交织,让每座城市弥散出浓郁的亲切感和生活气息。城市居民间地道的方言对白不仅散发出质朴的地域特色,更勾连起离乡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城市本体层面独有的视听符号透过影视语言的编码,在光影艺术的渲染下既具备了绚丽、震撼的奇观美,也饱含着质朴、温馨的平凡美,更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体现出城市是人类的美好家园。
(二)具身体验认知城市的人文空间
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美国哲学家爱德华·苏贾指出:“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是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2]换言之,城市作为一种地理与物质客观存在的空间,并非单纯地指涉几何学与物理意义上的位移,其中更蕴含着城市空间下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人文精神。纪录片《奇妙之城》打破了传统城市题材纪录片单向宣传、说教式的表述方式,引入体验性、交互性与娱乐性等叙事元素,巧妙地将纪实性叙事与体验性叙事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内容表述的趣味性与人文意蕴的丰富性,实现了城市影像从符号平面化描摹到具身立体化沉浸的演变。
《奇妙之城》在叙事层面以第一人称为主,叙事主体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参与其中的“体验者”。观众在体验者的带领下与不同城市的灵魂相遇,获得心灵的震撼与情绪的感染。自此,城市不再是单调、空洞的“壳式”空间,而是丰富多元的人文故事的集合,满足了观众对不同城市空间的想象。一方面,被凝视的身体景观解构着城市的人文肌理,承担着探寻城市生活、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内部视角;另一方面,与城市零距离的具身呈现增强了观众对城市的感性层面的认知。片中周深、肖战、白宇与王晓晨以回乡者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卸下了偶像的包袱,露出最本真、自然的一面,热情地把自己家乡的美食、美景与淳朴的民风习俗介绍给银幕外的观众,流露出一种家乡代言人的韵味。吴磊与许魏洲父子以新奇的目光探寻着厦门与克拉玛依的新奇世界,具备了探索式的叙事视角。不同城市空间下的风景建筑(视觉)、民歌方言(听觉)、美食小吃(味觉+嗅觉)与体验互动(触觉)下,多重感官“联觉”下拼贴出的全景式沉浸体验与在场感,传递给观众感性层面更深层的认知效果的同时,激起观众对城市人文空间的向往与想象。此外,探洞、冲浪、赶海一系列城市地域环境下特有的年轻人运动,弥合了年轻观众的观影趣味,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和互动感。这种“认知城市”“体验城市”“刻画城市”的方式,让城市形象不再浮于表面符号和景观的堆砌,拓宽了城市人文体系的建构方式。
二、光影叙事下城市意象的情感观照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问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历史性、社会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当代人文性的内在理论视角[3]。《奇妙之城》以影像艺术的语言解构城市表征下的意指,在对城市物象进行记录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内部的人与事,将叙事锚点从城市表层的物象空间升华至精神内核的讲述,走向城市内部意象空间的开掘。
(一)以人物性格透视城市精神气质
城市的精神气质不只存在于宏大的社会话语体系中,更存在于每一个生活与斯的生命个体。人是城市空间下的主体,人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城市作为人生活、成长的土壤,城市的人文气质和精神内核也因生活于此的人而彰显。正如学者杨东平所说:“不同城市人的个性、文化心理、行为特征、精神风貌、教养和趣味等,体现了城市文化的丰富性和不同的品位。”[4]城市承载着不同社会关系下人的性格,人的气质风貌亦是城市精神的表现,“人”与“城”在相互纠葛中获得独特的精神旨趣。
《奇妙之城》并没有将叙事悬浮于高空,而是选择将视角落地、聚焦于城中平凡的普通人,将城市的精神气质与弥漫着城市温度的人物性格缝合,通过城中人的形象实现城市独特个性与气质的传达。纪录片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对叙事主体映射与再现的过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淡化了传统社会时期民族化、地域化的性格特征与生活习惯,但在外表趋近的现代城市空间下的人们亦有截然不同的精神旨趣与生活态度。《奇妙之城》以犀利的目光捕捉着社会发展下的城市个性,城市不同的生命个体用滚烫的生活诠释着城市的精神与气质。自由舒适的贵阳诞生了钟情田园生活的一焱和生性乐观的贝姨;新潮火辣的重庆孕育了坚持梦想的相声演员圆圆和外表凶猛内心柔情的“猩猩”;多元包容的厦门不仅有只做本港海鲜美食的杰哥,还有平均年龄60 岁笑对人生的雷厝乐队;具有厚重历史的长安成长了对传统戏曲痴情的小武和用现代脱口秀逗笑西安人的啸雷;苍凉的戈壁拥有昔日的猎人今天的野生动物保护者赵兰生与时尚潮流的石油乐手塔依;热情的青岛成就了精神富足的文艺酷大爷赵宗伦与坚持合唱梦想的“XUAN了合唱团”。在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渲染下,不同城市的生命个体体现出的性格表征形塑了城市充满想象的精神思维空间,城市的内在气质在鲜明的人物性格的透视下获得了全新的升华。
(二)以镜中影像关照民间众生百态
影视艺术通过视听语言的生产将观众带入光影艺术所建构的“镜域”空间中。对于观众来说,对影视形象的凝视既是对他者身体的关注,亦是将自身与镜中人进行联系、对比与反观的过程。纪录片《奇妙之城》中没有悠久厚重的历史、英雄伟人式的人物,也没有刻意的美化包装,有的只是社会图景下的日常琐事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正是这份本真、质朴的平民化表达形成当前社会现实的全景式勾连,与观众产生内心情感的共振。
《奇妙之城》运用交叉板块式的叙事结构,一方面将城市与平凡个体的命运相链接,通过一批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形象,述说着城市化浪潮下都市年轻一代的艰辛与顽强的向上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选择城市空间下最具烟火气息的生活故事,还原城市发展浪潮下蕴藏着的人间温情和想象的余味。镜头下城市现实空间下的普通大众,他们有着各自家庭里的琐碎;有着对人生态度的追求与看法;也有着生活中的困惑与艰难……这些鲜活的人物影像是当下无数都市人群的缩影,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同样也是荧幕外观众所面对的。重庆篇中,四川女孩圆圆放弃家人规划好的人生,选择了自己追逐的演绎梦想,只身来到重庆打拼。现代都市里坚持梦想的年轻人苦涩与甜美并行,追梦路上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能深切体会。再如,克拉玛依的赵兰生从年轻时的猎人成为今天的野生动物保护者。一生刚硬,内心柔情,像野兽守护家园一样守护着戈壁,守护人与自然共同的家园。爱家爱国热爱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是现代人共有的生命哲理。这些有着个性特征与共性情感的影像个体,面对和你我一样琐碎的生活,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化、情感化的话题成功点燃观众的情感共鸣。
不同的观者从中看见自身的影子连接着关于他者的想象,勾起关于自我生活与生命的想象,彰显了城市影像精神维度的意义。镜头下城市里的故事不仅是当下无数年轻人奋斗的故事,更是当下城市飞速发展下芸芸众生自己的故事。纪录片《奇妙之城》及时关注社会转型中人们精神空间的变革,于城市空间的社会化浪潮中发现值得深思的问题,形成了对现实生存空间的反映与观照。现实中的生活与影像里的故事得到了缝合,城市素颜下的人情冷暖勾连着社会图景下众生的百态,传达的现代性诉求和痛楚直戳观众内心深处。
(三)以怀旧情怀勾连社会集体记忆
城市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过程中承载着记忆的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是城市在时间层面的过去式。人们在记忆生产实践中将非共时性的生物记忆碎片重组,让城市保持了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借此完成城市身份的指认。城市记忆不仅包含城市历时时空下政治、经济、人文等显性层面的发展和积淀,更浓缩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生活环境隐性的心理感知和认知评价。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定范围群体建立在记忆和反思基础上的重构[5]。纪录片是城市发展的影像记录,被誉为城市空间下的家庭相册,对唤醒内部居民的集体记忆有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将人类集聚在特定的空间下,人类成为城市空间的建构者,城市亦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保管者。就城市纪录片的内向维度而言,城市纪录片能够帮助人们认知和理解城市的精神意识,强化地域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根基,唤醒集体的文化记忆。《奇妙之城》运用了“以现实时空勾连历史的独特方式”[6],关注城市发展中的现在与流逝的历史之间的连接。在呈现当下进行时态现实的基础上,力证过去与现在并不是漂浮和割裂的,而是历史在当下时空的延续。重庆的肖战在军哥书屋与几位爱收集老物件人聊天,看到旧时的火盆、轨道、门牌时,不由的回忆起儿时邻居们摆龙门阵、喝茶聊天、生火烤红苕、放学后防空洞乘凉等生活细节。对传统艺术有着执着与不舍的西安青年小武,以马号、火彩阐述西安这片土地独有的历史空间形态和文化品格,如果说秦腔是陕西人的魂,那像小武一样对传统文化无法割舍的一代人就是这个城市灵魂痴心的守护者。
《奇妙之城》从传统纪录片制造的城市奇观符号到深描精神气质的深度价值转向,体现了影像艺术应有的人文温度和价值意义,传达着城市内部集体记忆的永恒追问。城市里一批爱好收藏的人珍藏着城市过去的时光记忆,通过城市空间下城市记忆的开掘,进而使地理空间的身份归属转化为对城市记忆空间的回溯,成功唤醒“城里人”的情感共鸣、集体乡愁和保护传统文化意识,在城市文化价值建构的同时做到了城市内部凝聚力的凝练。
三、媒介生产下城市形象的意义呈现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空间既是被生产的,同时还具有生产性。媒介传播格局下,城市纪录片通过镜头符号与话语文本将城市空间下的具体物象与精神意象进行链接,推动城市形象在媒介视域的意义生产。
(一)“1+N”融合延展城市形象的传播策略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成为传播链条终端接受和始端创作群体,传统媒介向场景化、社交化和个性化风格趋近。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形象被不断包装、重塑,生成了融合化的传播场域。据《2019年中国网络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称:纪录片的受众群不断扩张且年轻化趋势明显,中国纪录片正进入“网生时代”[7]。具言之,当下纪录片的发展呈现出产业格局上的“融媒化”,内容形态上的“网感化”,受众分布上的“年轻化”与传播生态上的“网络化”相结合的特质。由此观之,新时代纪录片的创作、生产与播出跨形态、跨行业、跨平台合作成为潮流。
作为一部面向现代大众的城市人文纪录片,《奇妙之城》及时抓住传播生态的变革,以年轻化的表达探索数字媒介时代纪录片创作的新边界,以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革新纪录片表达的新范式。通过系列“1+N”的创作方式熔铸纪实本体与现代艺术表达间的联系,凿通与年轻观众间的话语壁垒。首先,以“纪实+明星”为叙事主体,在人物选择上让流量艺人参与到纪录片叙事中。导演萧寒曾表示,就是希望明星艺人能够把粉丝带到纪录片里,以“饭圈”带动纪录片在年轻群体间的传播。以重庆篇为例,肖战在节目中光顾的重庆小面馆与藏在老街巷的军哥书屋一炮而红,成为了年轻人竞相光顾的打卡圣地。其次,以“纪实+综艺”为叙事手法,该片之所以能引爆市场,离不开叙事手段的创新。《奇妙之城》成功突破了传统城市纪录片叙事层面的桎梏,将纪实与综艺元素相融合。一方面,综艺娱乐元素的引入,让纪录片契合了大众口味的同时在叙事方面获得了更新颖、时尚的表述方式;另一方面,综艺化表达裹挟下流露的浓厚乡味,抚慰着每一颗在外漂泊游子之心,传递出每座城市独有的力量和人文关怀。最后,以“纪实+融媒”为传播生态,《奇妙之城》借助网络平台的传播优势,在上映前期便在微博宣传,播出期间频频制造相关热度话题,引发网友的持续关注。纪录片相关话题#①有关#号使用,参见了《〈了不起的长城〉:深耕文化沃土 讲述中国故事》一文中的用法。文中涉及微博话题时使用了“#”符号。原文见《〈了不起的长处〉:深耕文化沃土 讲述中国故事》《电视研究》2021年第4期,第64‐66页。肖战说自己长了一张大众脸##肖战重庆风景拼接照#阅读量均突破3亿,而长期话题#肖战奇妙之城#和#肖战加盟奇妙之城#的话题阅读量已超过10 亿。一系列网络话题带动了《奇妙之城》在年轻观众群中的话题热度,在纪录片传播方面赢得了巨大空间。由此观之,《奇妙之城》革新了传统纪录片的表达方式,融合了新媒体传播手段,在塑造与传播城市形象方面实现了“1+1>2”的意义显现。
(二)激活流动图景下的社会意义
纪录片对于形塑客观形象、传播社会价值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意义空间并非一种可视化的符号体系,它内嵌于故事文本中,是隐匿于故事背后的一种意义系统。”[8]由此观之,城市纪录片在通过城市空间下真实故事的讲述,实现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城市形象的意义生产。现代社会关系中,城市内部资源不断地生产与重构,城市间人才、思想、价值在物质与精神的空间中流动、碰撞、整合,构成了当下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有学者认为:“每个地方都是由陌生的‘他者’变成家园和生活记忆的,这个过程使人们关于空间的集体记忆,上升至地域性的认同。”[9]城市纪录片《奇妙之城》诊释了当下城市空间人文精神价值缺失的现实症候,还原了城市图景下温馨的一面,抚平和纠正城市化过程给人们带来的焦虑和偏见。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物质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与心理的变迁现实,《奇妙之城》纾解着流动社会下大众的内心郁结,激活了大众对不同城市空间下的文化认同。
纪录片以独特的表达方式重构着观众对城市下大众情感的认同场域。导演萧寒将《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工匠精神带到了《奇妙之城》,深度挖掘了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城市记忆传承与文化价值输出的双重意义。片中所建构的对城市的美好人文精神的向往成为一种情感召唤,通过个体情感达成受众对城市空间以及纪录片文本的文化认同,呼吁人们热爱城市、热爱自然、热爱自己的家园。在奏响集体记忆的同时,更彰显了媒体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对城市精神文明的抚慰。《奇妙之城》对城市价值空间的生产,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地方文化内核的基础之上的,进而形成并持续推动新时代城市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发展。就城市纪录片的外向维度价值而言,《奇妙之城》通过挖掘中国城市文化蕴含的个性价值,既彰显出我国地域文化的民族特色,又能表达价值共识,凸显了城市文化传播的脉络底蕴。《奇妙之城》以现实的城中故事构筑城市的真实性格与烟火气息,通过城中鲜活的人与平淡生活中的琐屑,创造出一座座温馨、鲜活而又让人倍感亲切的城市形象,实现媒介视域下城市价值空间的凸显与意义空间呈现的双重循环。
《奇妙之城》对于城市精神与人文情感层面的信息传递是一次成功的、深入的探索。纪录片《奇妙之城》以多元的表达形式、独特的空间叙事方式与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深度挖掘了不同城市的文化气质与精神风采,阐释了城市空间下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哲思,抚慰了流动社会下离乡游子的思乡情怀与发展焦虑,成为新时代城市空间利用影像讲述城市人文精神、城市价值的典型范本。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现实图景下,我们期待更多最质朴的人与最鲜活的城中故事,点亮观众心中对城市家园的憧憬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