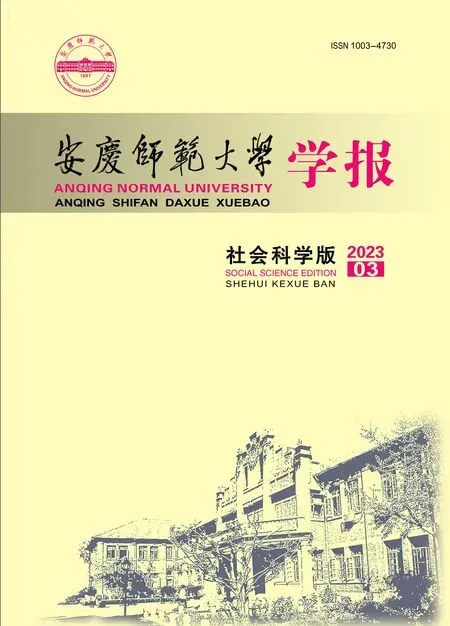西学东渐背景下晚清桐城派的经世思想
——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中心
2023-02-07董根明
董根明,李 娟
(1.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 246011;2.池州学院地理与规划学院,安徽池州 247000)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西学东渐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明清之际,中国涌入大量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术著作,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也在国内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到民国初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突破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地理环境、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使得西学大规模在中国传播,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其恪守程朱义理,常被理解为一个保守的派别。在西学东渐和列强入侵的背景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晚清桐城派的治学取向逐渐由“义理”转向“致用”,积极主动宣传、引进西学,以期救亡图存。其中,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和无锡薛福成作为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为学界公认的曾国藩四大弟子。曾门四弟子既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使者,同时也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的代表。在国门大开、西学涌入之际,他们破除“华夷有别”观念,放低姿态、适时而变,秉持经世致用理念,学习西方。综观学界有关桐城学人与西学东渐的研究成果,更多关注于个案研究,以时代群像为主体的研究鲜有涉及。本文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世思想。
一、晚清桐城派经世思想源流
(一)经世思想的萌发及兴起
曾门四弟子的经世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源流可追溯至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1]15,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学者痛斥空疏流弊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经世实学。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提到,古时以“天下为主”而现今以“天下为客”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倡导民主。作为同时代进步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君子为学应“明道救世”,增加学问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密度,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经世思潮始兴起。
及至康、雍、乾三朝特别是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文网严密,推行文化专制。如此文化高压政策,禁锢国民思想,学者们埋头故纸,专注考据,而成“乾嘉考据学派”,考据学由此兴盛,经世之学湮没。嘉道时期,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对内吏治败坏,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奢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既包括武器落后,也包括军队训练懈怠,“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危害社会”[2],军纪荡然;民间起义四起,如白莲教起义、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造成了清政府武力及财政削弱、社会矛盾激化,国势衰落。对外鸦片大量流入,荼毒国民;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西方列强势力频频东侵,社会秩序混乱。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王朝统治,道光帝任命一些年富力强和敢于向他直言进谏的官吏,条陈时弊,整顿吏治。在他的支持下,修改盐法、改革漕运、整顿吏治等措施并举,稍有成效。乾嘉时期没落的经世实学及至道光时期再度兴起。由此可见,经世之学的兴起与道光帝的支持不无关系。
经世之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贺长龄支持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文编凡120卷,下分吏政、礼政、户政、刑政、兵政、工政、学术、治体八纲,其后还有续编4 部,共16 部经世文编,目的在于“以资实用”,匡时救弊,以挽救统治危机。魏源批驳空谈义理,对文人墨客舞文弄墨更是不以为然,独崇尚今文经学,讲求通经致用,《皇朝经世文编》集中体现了他治学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促成了经世文编现象,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也使经世思潮得以复兴和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对传统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亦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晚清桐城派经世思想的发展
自十七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于是,资产阶级开始向外开拓更广阔的殖民地,以获得新的市场及原料。英国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和掠夺原料,向中国源源不断输入鸦片,致使民生凋敝。此时“康乾盛世”的余温犹存,而英国已将炮舰瞄准了中国大门。一声炮响,国门大开,西方文明涌入,扰乱社会秩序,清王朝危机四伏。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有良知的文人志士“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1]114,桐城派学人受经世思潮影响,其治学取向由“义理”转向“致用”。方东树指出“要之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3]344,文章如若不能反映时势,指斥社会弊病,无论文辞何其华丽,皆为“无用之言”。“教以专治时文,俟得科名,然后更求实学”[4]43“教化云者,非空文而无实具之谓也”[4]51,管同以文阐明教师教授学生也应以“实学”为主。梅曾亮亦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5],认为文章应反映时人时事,提倡文人治学应与现实相联系,适应时代的需求。“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是姚莹提出的为文原则。“四者明贯谓之通儒”[6]120,其作为桐城派学人著书立说的标准之一,反映出姚莹治学倾向于现实。同时,姚莹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注意到西方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深感忧愤,因此他开始关注夷情,了解夷情,撰成《识小录》。《识小录》主要记叙了西北陆路,对于西南海外之事,尚未不详。为了解“外番异域之事”,姚莹编著《康輶纪行》一书,记叙了他奉使乍雅途中的风俗人情、山川地貌和语言制度等,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也多有研究,成为一部研究西南陆疆史地与域外地理的专著。“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6]280,他希望中国有志之士能一雪所耻,折射出经世致用思潮的光影。
时值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际,鸦片泛滥,吸食鸦片者更甚,上至士大夫阶层,下至普通民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今俗有嗜鸦片烟者,兴起不二三十年而蔓延,天下皆遍。是其为民生之害。吾子固默识于胸久矣”[3]221,作为桐城派学人的方东树较早认识到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他在《劝诫食鸦片文》中列举了吸食鸦片的四大害,食烟者“手足痿弱”“一切人理尽废”,为一大害;食烟者“形状可憎如鬼”,为二大害;吸食鸦片耗费资财,“致父母之养不顾,妻啼儿号不恤”,为三大害;“官旷厥职,士荒其学,工废其业,商贾耗其赀,兵役堕其职事,奴仆懈于使令”,为四大害[3]225‐226。他将鸦片视为民生首害,“食者其源,贩者其流也……其源不塞,而徒止其流,虽多方以遏之,亦多塗以决之”[3]222,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源”“流”之间的关系,欲从这两方面根除鸦片之害。首先从源头上严禁官民吸食鸦片,“今诚下一令曰,凡食鸦片者,官褫职,永不叙复;幕宾立辞去,仍申令大小官中不得复相延聘;士子食者终其身不许应文武试;兵役奴仆食者立绌退,仍申令永不得复应顾役。凡民食者抵罪……乃著令曰,凡食烟者,一切嘉会吉礼宾祭之地不得与,其亲故悉绝,其属不许相往还”[3]223,若士大夫、士子、兵役和民众等不同阶层吸食鸦片,均采取惩治措施以抵罪。其次从“流”的角度,“谓宜弛其禁,益令内地种熬,以分夷人之利,以餍食之者之欲”[3]224,关于鸦片贸易建议采取弛禁政策,并鼓励本国种植鸦片,防止白银外流。管同作《禁用洋货议》论到,“今中国之与西洋固邻居也,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4]23,希冀抵制外来品,保护本国手工业,发展经济,其为文不仅仅是空疏的“义理”之辞,经世致用色彩极为鲜明。
(三)曾国藩承继经世思想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学源源不断涌入中国,有志之士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保守,力图改变现状,引进西学。冯桂芬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7]57,遂兴起以曾国藩为领导、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盟主”,“力矫桐城懦缓之失”[8],其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筹办洋务。在《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中提出首先要网罗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9],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和容闳,皆精通西学。其次是创办军事工业,广集人才于安庆建立内军械所,制造机器,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随后,又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规模宏大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再者是选派留学生,“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10]。他不仅认识到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应选拔学生出国留学,培养新式人才,以收远大之效。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桐城派始终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其所尊之道在两百余年中无大变化,其用以经世之‘用’则代有不同,至洋务运动时期果敢地以西为用,为中国带来不少新鲜空气。”[11]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弟子,受其影响,承袭他的经世思想,在西学东渐和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们将“中体西用”思想应用到实际,以期救亡图存。
二、晚清桐城派的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享有“桐城古文中兴大将”的盛名,位高权重,爱惜人才。其幕府之中人才济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和无锡薛福成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名声渐起,并称“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和吴汝纶曾执掌莲池书院,门生故吏遍布各地,多承袭桐城文法。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有游历、考察访问国外的经历,对西方的政教体制、风俗习惯有所认识。在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没有顽固死守桐城“道统”,而是主张因时适变,强调经世致用。
(一)“采西学,制洋器”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门户洞开,源源不断涌入西方的科技、思想。面临“千古未有之奇变”,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坚定了有志之士学习西方的决心,曾门四弟子开始寻求救国方略,酌用西法,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
黎庶昌认为西洋富强的原因在于轮船火车,中国欲图自强,“火轮车公司之建当为今日首务”[12]684,“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绝少者,独火轮车一事耳”[12]220。无独有偶,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从用途不同叙述了轮船的重要性,“用为商船,则贸易独盛;用为兵船,则水师尤精。然则握富强之枢者,岂非以轮船为第一要图乎”[13]56?“藏富于商民,则整理船政,其急务矣”[14]74‐75。“首务”“急务”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兴办轮船的重视。张裕钊也钦羡西洋轮船,“自泰西人创兴轮舟,驰骤大瀛海之上,上天下地,日星所烛,霜露所濡,穷幽极遐,靡不洞辟”[15]212‐213。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富家之基在于器数技艺。在《上张制军》一文中吴汝纶指出,当今中国自救之策当以开采矿产为第一要义,“专学洋人炼冶之法”,开矿设局,“制器练兵,绰有余地;转弱为强,易如反掌”[16]7,不再是传统的从外洋直接采购机器,而是进步性地提出本国自制机器。张裕钊提议向西方学习,破除因循守旧的落后观念,认为“泰西人故擅巧思,执坚刃……日新无穷……又以其舟车之力……徬徉四达,竞相师放,精能俶诡,甚盛益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尝有也”[15]34。为此,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黎庶昌在《西洋杂志》里记述了他在出使西洋时的所见所闻,对西洋制炮厂、钢铁厂、玻璃厂等更是详细记载,惊叹之余也表达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憧憬,且认为西方的强大源于其发达的科学技术。
除此之外,薛福成提出开垦荒地、兴办屯政、去除捐例、严肃吏治、筹建海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时局[14]1‐26。一方面,他建议筹设专款购买西洋机器,遴选工匠学习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另一方面,选派聪颖子弟留学西洋,“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14]20。他提议培养西式人才学习西方制器之学,期望中国可以自主制造洋器,以提高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达到自强的目的。
(二)“商握四民之纲”,大力振兴商务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一股倡导发展工商业的思潮,以抵抗外资侵略。薛福成尤其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列国虽欲与之颉颃争衡,而终不及其心计之工规模之远也。……自有地球以来,商务之盛,未有如英今日者也”[13]147‐149,英国国力富强、“蒸蒸日上”,招致其他国家仿效,缘于英国重视商务。同时他也简洁有力地说明了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正是“以工商诸务之振兴”,而中国日渐贫弱,就在于商务不振兴。他批判了传统的“商为末”思想,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新思想,揭示了“商”虽位于传统四民阶层最末端,却仍促进其他阶层的发展。这一观点对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促进商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皆是“崇本抑末”,如今欲振兴商务,桐城派学人薛福成在《商政》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商务之兴,厥要有三:一曰贩运之利。一曰艺植之利。一曰制造之利。”[14]72‐74具体而言,为扩大商务则有八条建议:“一、曰设专官。一、曰兴公司。一、曰励新法。一、曰杜伪品。一、曰趋时尚。一、曰设赛会。一、曰改税则。一、曰导商路。”[14]135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提到,要使中国商务真正振兴,必须要摒弃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商务活动中存在的三大弊端,“一、在抢揽生意。一、在搀杂诈伪。一、在电报灵速”[14]129‐130。薛福成在《振百工说》中提到,“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14]164‐165,中国欲发愤自强,则须以发展商业为首务,振兴百工。另外,黎庶昌鼓励发展私人工业企业,让他们自负盈亏,大胆经营;“必仰赖朝廷权力,明示扶持,庶免公司倒折之虞,即杜外人觊觎之渐,商务当日有起色”[12]222,建议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助私人工业企业以振兴商务。吴汝纶提到私人企业若无政府支持,“欲兴丝业,似宜仿照外国考察蚕子之法,以清其源,仍与西商合立公司”[16]159,不因循守旧,延聘西商为经理,讲求工艺,发展商业。如此,既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来源,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又可“稍分洋商之利”,藏富于民。
关于振兴商务,他们透过现象、探明源流,提出八条建议、革除三大弊端、明示扶持私企及创新合作方式,可谓是鞭辟入里。
(三)“学校不兴,人才不出”
自列强入侵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开始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教育革新即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张裕钊和吴汝纶即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但在民族危亡、西学涌入的情形下,他们仍主张学习西学、革新教育制度,崇尚经世致用。为此,他们躬亲实践,勉力而为。
抨击科举制度。张裕钊和吴汝纶都曾执掌保定莲池书院,虽都是科举出仕,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15]279‐280张裕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了科举制度现今已弊端丛生,危害社会,“仁义道德”已至“腐熟”。吴汝纶进一步指出,“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16]365。身处世变之亟,他们针砭时弊,理性地对待科举制度,力图革新教育。
注重培养人才。“贤才者,国之元气也,人无元气则亡,国无元气则灭”[12]32,黎庶昌将人才与国家兴衰昌敝紧密结合。张裕钊重视贤才,“夫穷天下古今尊主庇民,批患折难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15]219“今天下师儒学子……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水流濕,火就燥,志气所动,人蹶而兴,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15]280,他重视人才,并且期望通过“一人”之才来影响“一邑”乃至“天下”之才,以达到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制船购炮,尚属第二义”[16]32,相较于购买西洋船炮,吴汝纶认为培养人才才是当务之急,若人才不兴、政令不改、习俗不变,则“殆未有可以转危为安者也”[16]114。为培养人才,他提议兴办学校,明确指出“学校不兴,人才不出”[16]365‐366“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16]365,以期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来培养新式人才,认为传统学堂难以造就“真才”。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聘请英国、日本教师授课,教授日语和英语,开办东西文学堂,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薛福成在游历欧洲时,为英国、德国的水军、陆军所震撼,反观本国兵备,积弱不振。“泰西各国,选将练兵,皆出学校。武备一院,选聪颖子弟读书十数年,再令入伍习练”[13]72,他倡导学习西方培养军事人才办法,遴选读书久、阅历深的精良士兵,改变中国兵备落后的现状。
主张学习西学。相较于张裕钊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吴汝纶更加重视学习“西学”,“科举改制,国家注意西学……天下书院尽改为学堂,民间社学、义塾,一律讲习西学……今天下已汲汲谋新,岂可默守故见”[16]196“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16]249“非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不可”[16]314,可见学习西学已然成为当今首务。薛福成在日记中写到,“盖凡为官为士为兵为工为商,皆当周知舆地,惟其童而习之”[13]86,无人不洞悉形势,谙练世务,重视舆地学。他认为须学习“天文、地舆、器数之学”,对“重学、化学、汽学、光学”等格致之学亦不可忽视[13]6。张裕钊在《策莲池书院诸生》中提到,“自泰西人入中国,其所绘舆图详尽精确,无毫发差失……有心者其必以舆图为当务之急矣”[15]240,他观察到西方重视地理且精于绘图,而传统知识分子则一如既往围绕四书五经治学。为此,他希冀以舆地学为突破口来改变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达到革新教育制度的目的。讲求西学,最主要的是延聘西师,如若“西师难请”,则延请日本人为师,“其功效正复相同”,因“近来西国学术,日本皆已精通,且能别出新意”[16]196。聘请西师教授课程,以“西文、西语、算数、天文为主”[16]127,目的是“从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能尽读西书,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西国深处”[16]129,了解外国形势。另外,他还注意培养专门人才,“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16]437,注重人才的多样性。
创办新式学堂。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使得吴汝纶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大失所望。他意识到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已不再适应急遽变化的社会,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历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为此,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学制。这一考察经历记录汇编成《东游丛录》。在书中,记录了他考察日本幼稚园、小学、中学及大学堂等多所学校,包括商业学堂、实业学校、高等女学堂、师范学堂等,培养专门人才,教育体制较为完善。从日本归来,吴汝纶在《与桐城绅士》一文中,阐明自己意欲兴办桐城学堂的计划。他撰写《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开办学堂呈稿》《开办学堂章程十七条》等,详述学制、开设课程及办学理念等,为筹立桐城学堂做了充分准备。桐城学堂的创办,是吴汝纶教育理念得以贯彻的实践经历。
(四)注重外交,洞察西方政治
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薛福成提倡同外国打交道,剖析自我,了解夷情,而后才能平天下。1876 年,黎庶昌出使西欧各国。在深入考察各国情况之后,他认为西欧国家以国力强弱来进行外交,故提议“窃谓今日时势,似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结纳,以为外交”[12]610,与他国结交,提升本国的外交能力。1881 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出使期间,他通过文学和酒文化与日本交往,深化了中日两国的交流,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文化。在游历美国和日本归国后,他观察到“西洋视公使甚尊”,即使是蕞尔小国日本对待外国公使的访问,也是“待四方宾客之至”,而中国则不然,于是他在《敬陈管见折》中提议道“公使宜优赐召见”,学习外国对待使节的礼仪[12]221。
薛福成亦有游历域外的经历,通过观察西方国家的政教风俗,他认识到只有仿行西法,实行君民共主,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日记里,他详细描述了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并着重突出君主之国的弊端。“合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13]190“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13]134,观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黎庶昌编撰的《西洋杂志》里,记叙了自己游历各国的所见所闻,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西洋民政之国……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12]585。他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要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洞察与思考。
三、晚清桐城派经世思想特点
在西学东渐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国内民族矛盾突出,加之受曾国藩筹办洋务的影响,曾门四弟子的经世思想更多关注社会民生,他们从诸多方面寻求救国救民方略,力图改变清朝落后贫弱现状。从其经世思想的具体主张看,无疑是积极、进步的,可将其放置于当时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下,又难免有些局限性。
(一)突破“夷夏之防”,践行“中体西用”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续至今。“夷夏之辨”从殷周时期强调地域和血缘族类之分,发展到后人理解的带有强烈价值判断意味,从而由开放走向了封闭[17]。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不同程度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长处,而几乎很少主动学习外来文化,进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特征。在此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撬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明源源不断地涌入。即使如此,鸦片战争之后,仍有众多封建士大夫视别国为“蛮夷外邦”,视本国为“天朝上国”,坚持“华夷之别”。
以曾国藩为首的开明士人从蔑视西方文化到兴办洋务,开始突破传统夷夏观,承认“夷狄”确实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夷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7]49。曾国藩等人以实际行动表明对待西方态度的转变,从蔑视西方文化到兴办洋务,已突破传统夷夏观,不再“遮掩”。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认为西人已经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这种无法逆转的时局,如果中国善于把握机遇、适时而变,则“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18]。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背景下,曾门四弟子认识到不能再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念,而应采取适时而变的方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主张中国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创办新式企业和学校,筹建海防,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突破“夷夏之防”,破除“驾驭四夷”的观念,脱离“天朝上国”的陈旧偏见。
(二)修正传统义利观,强调工商立国论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历来是奉行“重义轻利”观念,即重道德而轻物质。乾嘉时期士大夫尤尚空谈而不务实,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义利观已不适应急遽变化的时代。
西学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冲击,固然引起顽固士大夫强烈不满,他们用传统义利观、本末观攻讦“以夷变夏”的思潮。魏源较早对传统义利观提出质疑,认为传统义利观空谈礼义不讲求富强之道,导致国用不足、吏治败坏、百姓生活困苦等,因而必须摒弃“无用之王道”[19],修正传统义利观以适应社会现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衰退,国弱民贫,急需发展经济,图强御侮,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筹办洋务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义利观的一种修正。
中国自古以来秉持“农本商末”的思想,重视小农经济的生产发展,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是忽视甚至抑制商业发展。吴汝纶在《原富序》中指出“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忲习于重农抑商之旧说”[20]196。他指摘讳言利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旧说,“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破除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重农抑商,则财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财之所以通也。农者,生财之一途也。闭财之多途,而使出于一,所谓隘也”[20]196,因此力求富强须选择“生财之多途”,发展商业。传统义利观的消极影响即表现为“重农轻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洋务维新时期,薛福成、黎庶昌大力提倡振兴商务,强调工商立国,批驳顽固派“重本抑末”思想。薛福成在日记中写到:“中国圣贤之训,以言利为戒,此固颠扑不破之道……然此皆指聚敛之徒,专其利于一身一家者言之也。《大学》平天下一章,半言财用。《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可见利之溥者,圣人正不讳言利。……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14]130他批驳讳言利的义利观,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发展商品经济,变以农业立国为以工商立国。为此,他们通过实践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修筑铁路、开办工厂、制造轮船等,希冀“稍分洋商之利”。凡此种种,冲击了中国传统义利观和本末观,也促使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化。
(三)固守学术底色,维护清廷统治
对于西方文明,顽固派采取抵制态度,而作为洋务维新时期的开明士人则采取开放态度,突破“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界定“体”“用”,“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21]。他们把学习西学作为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手段,希望借助西方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新式学堂所设课程中,吴汝纶虽然力主西学,同时他也唯恐西学兴而中学绝,“西学既行,又力患吾国文学废绝……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世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16]381。因此他坚持桐城学术,认为“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16]235,故中西学并行,且“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16]381,如此才不致中国传统学术消亡。作为桐城学人,虽顺应时势,但也不忘桐城派学术底色。
然曾门四弟子的经世主张囿于“中体西用”论。他们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了实现对外“强兵”,以图御侮,实质上仍是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们提议开办工厂,发展商品经济,以工商立国的思想实属曾门四弟子的一大进步。可这只是少数开明士大夫才具有,传统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依然坚持以农业为本的思想,没有达到“农商皆本”的思想境地。即使如此,稍有发展的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小农经济,但依然没有撼动封建经济的根基。曾门四弟子废科举、立新学的主张,在当时适应了社会发展需求,培养了众多新式人才,在客观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可他们的经世主张并没有触及上层建筑的变革,只仅仅停留在对西方议会制、君民共主制的赞赏和向往,难以触动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命脉。
四、结 语
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形下,西学不断涌入,对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固然是一种冲击。曾门四弟子虽为接受传统教育的桐城学人,但在封建体制下的他们并没有固步自封、踯躅不前,而是因时适变、顺应潮流,不断地学习西方的优势以弥补本国的不足。他们从最初购买西洋器物、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逐步过渡到革新教育制度、培养新式人才,自主制造新式机器。这种学习方式的转变在当世抑或今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众多类似于曾门四弟子一样的人物,在国势衰微之际,努力寻求救国救民方略,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可作为传统士人群体,曾门四弟子的经世思想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们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根本,学习西学只是作为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且曾门四弟子的众多经世主张停留在思想层面,只有极少数付诸实践。应当看到,曾门四弟子处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和西学对中学造成冲击的背景下,纵然其经世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受其认识的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