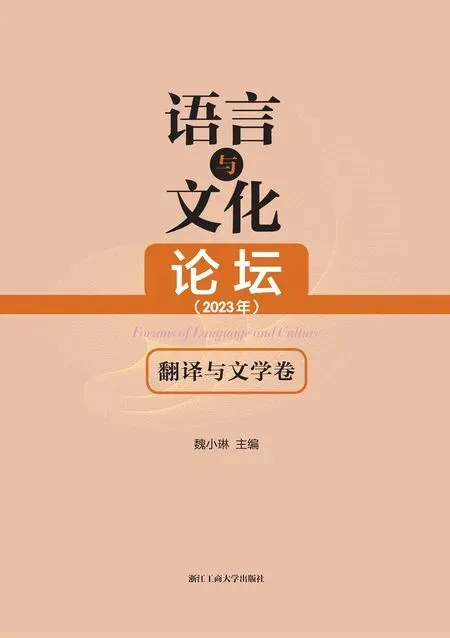论迈克尔·坎宁安《夜幕降临》中的审美生存心态①
2023-02-06李敏敏
李敏敏
1. 引言
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是美国当代作家,他对于自己的每部作品都精雕细琢、力求突破,不断尝试新的写作领域和叙述方式。这使得他的小说广受赞誉,也让他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多项殊荣,被《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夜幕降临》(ByNightfall)发表于2011年,故事以美和艺术为中心展开,又聚集了身体、欲望、爱等诸多叙事元素。其中的身体意象受到傅婵妮(2017)的特别关注,她结合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身体图式理论分析身体所蕴含的意义,指出主人公通过主客身体的暂时性统一实现了对美的追求。在这部小说中,坎宁安继续展现了他在叙述艺术和心理描写上的深厚功力,梅克尔(Mäkelä,2017)因此从小说中的叙述权威和叙述声音入手,分析了生活和艺术之间最终的不平衡关系。卡斯特拉诺(Castellano,2022)则抓住艺术这一主题,通过对当代艺术体系的分析,探讨了小说中文学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承认艺术体系的价值和规范在社会领域对自我定义和自我实现过程的影响。
坎宁安在小说正文前引用了里尔克(Rilke)的诗句“美,不过是恐怖的开始”,这不仅直接道出了小说的主题,也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美的本质。美和艺术贯穿小说始终,坎宁安描绘了主人公将之融入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实践活动,这种生活美学正体现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存心态”(habitus)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审美生存心态”是指用一种审美的视角和艺术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努力创造能够带来审美体验的可能性,从而使日常生活富有审美愉悦感,它既是一种生活理念,也是一种生活实践。坎宁安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种非功利的艺术审美的生存方式,探讨了现实生活与艺术理想的关系。如前所述,从美和艺术这一主题出发,学者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但对主人公审美生存心态的形成及其外化的行动和思想缺少具体的阐释,故留下了一些思考的空间。坎宁安(Cunningham,2004)xvii曾写道:“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奥森巴赫(Aschenbach)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他想要的比生活愿意提供的更多,他的失败和他的英雄主义紧密相连,这两者不能轻易分开。”坎宁安的主人公皮特则更具生活气息,他的生活失败与他的唯美主义密切相关。奥森巴赫以死亡成就了他的欲望,而皮特在美的陷阱中步步沉沦,凸显了人的欲望终将落空的悲剧性命运。皮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美国当代中产阶级中年人的精神危机和生活困境,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面临的生存难题,透过他可以审视当下生活中关于美丽和欲望、艺术和现实的选择和得失。
2. 身体与审美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而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又是重中之重。它不仅仅为个体维持生命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人通向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媒介。《夜幕降临》中有很多关于身体的描写,它们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都包含着美的意义。
舒斯特曼(Shusterman)(2002)在其著作《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PragmatistAesthetics:LivingBeauty,RethinkingArt)中为身体美学下了定义:“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的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由此可见,身体美学研究的是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美感以及人们借助身体所进行的审美实践。小说中的身体承载着不同形式的美,皮特通过身体媒介感知到了世界中美的存在。
2.1 美的载体:身体
身体问题的渊源与发展涉及意识哲学和身体哲学这2种哲学的对立,其在各自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意识美学是早期现代美学,它高扬精神性而排斥身体性,认为审美只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活动,跟欲望和身体无关。后期现代美学转向了身体美学,身体得到了重视。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等身体美学的倡导者倾向于把身体和人的活动、体验、情感、意志等方面联系起来。在前人身体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梅洛-庞蒂形成了自己的身体美学思想,使身体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64)所提出的“身体”概念以人的知觉为前提,身体被看作知觉的主体,而对于审美活动,身体又是一个“两层的存在”:“一层是众事物中的一个事物,另一层是看见和触摸事物者。”因此,身体内蕴着一种可逆性,这使得身体既是可见、可触的主体,同时又是被见、被触的客体,审美活动正是在身体与其他身体、事物的可逆性交流中进行的。小说里讲到了2种身体,艺术品中的身体和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身体。皮特作为身体主体,通过上述两种作为客体的身体来感知世界中的美,获得情感上的审美快感,并在观看和感受身体的过程中发现生命的本质,实现主客身体的统一。
作为艺术经纪人,皮特时时刻刻都在和各种艺术品打交道,而他最钟情的是那些表现身体的艺术作品,如雕塑、画像等。法国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Rodin)创作的《青铜时代》,没有巨人的体魄,也没有完美的身型,可这种被创造出来的身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个体的生命力和活力,并将之保存了下来。深谙艺术之道的皮特通过这件艺术品和当时还是无名小辈的罗丹实现了跨时空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达成了统一,皮特仿佛成了那个半男人半男孩的雕塑,实现了他对美之永恒的追求。
2.2 艺术与现实
和艺术品中的身体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衰老、死亡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体现在人身上的朝气、青春、美貌等美好特质都会慢慢消失。皮特把自己对美的诉求投注在妻弟“错错”这一客体身上,将之与其身体联系起来,看到了生活的本质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皮特觉得哥哥马修在某些方面近乎完美,但他在生命应该绽放光彩的时候走向了死亡。当年的瑞贝卡是湖边女神,勾起了皮特无限的遐想和欲望,但现在是一个没有一丝性感的中年妇女。在皮特的记忆深处,年轻的马修和瑞贝卡像但丁和贝娅特丽丝那般纯洁而永恒,他们魅力四射又完美无暇的身体呈现出“一种万事万物无法言说的完美,这种完美不仅存在于现在,也将存在于未来”(坎宁安,2013)115—116。在种这完美中,时间仿佛凝固了,主体身体和客体身体也在这种凝固中融合在了一起。皮特通过马修和瑞贝卡的身体感受到了世界中永恒的美,产生了敬畏之情,可是死亡带走了马修,时间吞噬了瑞贝卡,美成了不可感知的东西。或许马修和瑞贝卡的变化还不足以让皮特直观深切地感受到美的消失,但“错错”的出现让美在2个身体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错错”的身体像青铜雕塑,充满青春活力,而妻子瑞贝卡的体态在平淡的生活中逐渐失去了美感,这就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衰老。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主体既是审美的主体,又是饱含情感的感性观照的客体。作为身体主体的皮特在看这些客体身体时,不仅获得了美的享受,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对美的特质难以延续感到遗憾和无奈。
在小说中,“错错”的身体对皮特而言还有某种特殊意义,他在凝视“错错”身体的过程中,不只将其看作自然美的载体,或者年轻版的瑞贝卡,更是投射了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感受。因为审美主体是建立在知觉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身体主体拥有审美的知觉力,而凭借这种审美知觉,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可以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知识、经验等等倾注在审美对象中,使审美对象不再是原来的客体对象,即知觉的能动性使“错错”的身体呈现出了只属于主体皮特的美的形象,独一无二。审美知觉只着眼于客体身体的感性形象上,不在乎其本质如何,因此,作为客体的“错错”能被按照皮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加工或完善,成为更理想的审美对象,在加工处理的过程中,主体身体和客体身体的联系不断加强,二者在可逆性的交流中实现了主客统一,“错错”成了皮特心中那个内在的自我。
在皮特生活的世界里,无论是艺术品中的身体,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身体,它们都具有审美特性,而皮特也在视看这些身体的过程中获得了美的体验。但是,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永恒与短暂的差异。对人类群体来说,美是自然的、永恒的,它在人与人之间以代际的方式传递,从不间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普通个体所拥有的美貌、青春、生命力等这些可见或不可见的美的特质会逐渐消失,那些曾经在我们生命里绽放美丽的时刻和瞬间也会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皮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具象化在错错这一鲜活的肉体上,这就注定了他理想的破灭。
3. 性向与审美
在迈克尔·坎宁安的作品中,性少数群体是他描写的主要对象,《夜幕降临》中的主人公皮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准确地说,他经历了由异性恋者变为同性恋者这一过程。皮特在与错错的不断交往中逐渐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种挑战传统和伦理的做法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审美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实践。
3.1 爱欲与审美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异性恋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性少数群体之间的爱情被视为反常的、病态的,受到社会的谴责、法律的约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当下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同性恋/双性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种性取向没有像传统的异性恋一样为人们普遍接受,但人们看待这类人群的眼里多了几分宽容和理解。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被‘正当’论述说成‘异常’的地方,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也是审美创造的理想境遇,是最值得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和鉴赏的地方。”(高宣扬,2015)这种生存理念和生活实践可以被看作福柯(Foucault)所说的“游戏”,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反叛和创新。通过这种反叛和创新,皮特可以抚慰自己不安分的灵魂,“他希望能在自己身上发生一些离奇、轰动、丑闻性的大事。他可以——他必须——给自己一个惊喜”(坎宁安,2013)216。福柯认为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永远不甘寂寞、时刻都在尝试超越现实生活,以求得更刺激的审美愉悦感。福柯一生都在进行着反叛和创新的双重游戏,并在这种无止境的“永恒游戏活动”中达到了新的生命境界。同样,皮特在生活平淡、精神空虚时,也选择了非常规的方式,获得了更刺激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历。
小说中,“错错”的美以身体为依托呈现出来。如前文所讲到的,皮特在心里对“错错”的身体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投入了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使之更加完美,而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皮特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取向。因此,就像舒斯特曼(2011)所说“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讨论皮特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问题还要回到身体上来。皮特对“错错”身体的每一次观看、他与“错错”的身体接触以及二人之间产生的爱情,都是以身体审美为基础的。坎宁安多次描写了“错错”的身体,从某些方面看,他长得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里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给人一种宗教狂热的感觉,但又有那种年轻人特有的悲伤,带有性感的色彩。当“错错”成了皮特最喜欢的一件艺术品,或者说是一种行为艺术时,已经暗示出同性爱情可以转化为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二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具有了愉悦性、审美性。
坎宁安的多部小说都没有将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放到性爱活动上,而是以唯美的笔调将这种深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心理娓娓道来。《时时刻刻》(TheHours)是简单的同性之吻、相互理解的陪伴;《末世之家》(AHomeattheEndoftheWorld)是内心带有伤痛的3个人试图在一种另类的关系中建立和谐的家庭;《夜幕降临》则是将对美的渴望表现为在精神上占有美,没有颓废和色情的含义。皮特强调“他是美的仆人,但他不是美本身,那是‘错错’的角色”(坎宁安,2013)205,可见皮特对美怀着崇高的敬意,甚至是敬畏。皮特深知,倘若自己和“错错”进行了肉体上的结合,那么美就失掉了神圣性,这种美于他而言就黯然失色了,而他也在夫妻生活中感受到:性没有意义。因此,皮特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纯粹的美,精神上对“错错”的爱慕和占有比性欲更有价值,他在这种精神满足中使自己成为独立自由的审美生命体。
3.2 “希腊”的隐喻
皮特将自己和“错错”之间的爱情看作是纯精神的恋爱,追求心灵沟通而排斥肉体,他曾经幻想过这样的画面:在希腊的小屋里,他和“错错”像一对父子在一起看书。希腊人对美有着无限的神往,而这种对美的欣赏不仅仅局限于异性之爱,也包括同性之间的情愫。他们的民俗、体育以及艺术都与同性恋有着某种联系。体育场里男子健美的身体,雕塑和陶艺展现出来的同性恋倾向,这些都说明了希腊人对同性之美的赞叹。柏拉图(Plato)(2003)在《会饮篇》(Symposium)中借助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之口道出了爱情的几种类型:男与男、女与女、男与女。开初的时候,人是球形的,有4条胳膊和4条腿,头颅上有2张脸,他们除了有男女这2种性别外,还有男女混合在一起的阴阳人,这些人神通广大、蛮横无理,因此,宙斯将他们劈成两半以削弱人类。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体验到了爱的滋味,经常相互思念,妄图再聚合在一起以求完整。于是,被劈开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同性恋,而被劈开的阴阳人就成了异性恋。这就是阿里斯托芬所说的爱情,其本质是追求自我的完整和整合,在于个体性的自我关怀。皮特意识到自己对美的渴望并用认同性取向的方式将之满足,就是自我关怀的一种表现,他在对身体的观看与欣赏中寻求着“错错”的特殊性,也实现了自身的完整性。“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他们把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席勒,1985)席勒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完美融合为一体的希腊的自然,而沟通这种物质与形式的桥梁便是审美,它能唤醒人身上的游戏冲动——自由。与“错错”的交往中,皮特面临着内心的挣扎,而希腊的自然可以帮他解决内心情感和理智之间的矛盾。
对美的追求,是皮特一切活动和行为的精神动力。皮特难以接受现实生活的平淡与精神的空虚,新鲜刺激的审美体验似乎是他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虽然皮特的性取向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但对他而言却是获得审美享受的可能途径。通过这种方式,皮特拥有了美,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感,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审美生存方式。
4. 生存与审美
“生存心态”是布尔迪厄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关键概念,“Habitus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既是静态的内化心理、精神和情感结构,又是行动中实际发生外化作用的精神力量”(高宣扬,2008)。生存心态是人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同时又外化在客观的行动表现中。结合这一理论来理解审美生存心态,就是将审美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布尔迪厄以人在所处环境中的地位及其所相应形成的心理态势来解释人的实际活动,认为人的生存心态是在其与所处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对皮特来说,这个环境就是他所在的曼哈顿艺术圈、他所成长和生活的家庭,这些都深深影响着皮特,让他坚定心中对美的理想信念,并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它。
4.1 生活艺术化的理想
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纳入研究范围。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这样艺术只是模仿的模仿,艺术美就没有现实美来得真实。亚理斯多德(Aristotle)(2005)也主张模仿说,但他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情”,所以艺术比现实更真实,也比现实更美。然而到了王尔德这里,艺术和生活倒置了过来,他在《谎言的衰朽》(TheDecayofLying)里提出美学的新原理: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无论是生活模仿艺术,还是艺术模仿生活,二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坎宁安的笔下,凭着对美和艺术的满腔热爱和敏锐的感知力,皮特坚持在生活中追求美的事物,力求实现生活的艺术化,却最终明白生活是艺术的来源,也是艺术的对立面。
简单来说,审美生存心态就是使生活艺术化。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佩特(Pater),他在《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佩特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万物皆流,永远变化”为理论的出发点,强调个体现世价值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解读了艺术的本质所在,把艺术活动和个体的生命价值联系起来,把艺术看作实现人生意义与感悟生活真谛的理想途径。小说中的皮特执着于美和艺术,努力尝试用美和艺术来把自己的生活填满,积极地对生活进行美化、艺术化,是因为他在夜幕降临时感受到了存在的虚无和人生的短暂,这种生活于他而言像是一个铁笼,而理想中的美和艺术可以带他脱离这种生活的常规、秩序,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的:“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Gerth,1946)皮特曾经借助展现艺术美的作品,借助自然美的承载物摆脱中规中矩的世俗生活,他在瑞贝卡充满浪漫气息的家里、在罗丹的青铜雕塑上、在周围人的身上都获得过短暂的审美享受。倘若将生活艺术化,把生活当作一件特殊的艺术品,用一切艺术和美的元素来装点和改造生活,或许就可以使生活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个体的生命、体验都是有限的,由生活中一个又一个转瞬即逝的片刻构成。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尽一切努力去充实每一个瞬间,实现个体存在的价值,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佩特(1988)所说的艺术:“因为你从事艺术的活动时,艺术向你坦率地表示,它所给你的,就是给予你的片刻时间以最高的质量,而且仅仅是为了过好这些片刻时间而已。”皮特正是明白了艺术的这一功用,才坚持将艺术的气息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关注美的存在。通过生活艺术化,在生活的世界里融入美和艺术的气息,体验其中的无限意味和情趣,从而达到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的人生境界,这是唯美主义者理想的生存状态,追求完美的皮特必然会将此付诸实践。
4.2 生活艺术化的困境
人总是希望把美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然而,生活中的事物并不都是具有美感的,当生活的琐碎不堪甚至丑陋地展现在唯美主义者面前时,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容忍妥协。小说中皮特的客户卡罗尔在室内装饰、花园艺术、服装搭配方面对生活进行美化和艺术化的实践,但终究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悲伤,皮特也面临同样的生活困境。生活是一个线性不可逆的进程,它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强调当下的每时每刻。艺术可以永存,艺术品的伟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本身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而保存下来。
美,是皮特生活破碎的源头,“错错”的出走令皮特夫妻俩发现自己对彼此感到了可怕的厌倦,让爱受到了怀疑。在生活中,人们因爱联结在一起,成为夫妻、密友、手足等,并用爱来维护和巩固这些关系。然而,人们以为自己倾注了很多的爱,有时却会成为他人眼里的负担,甚至成为彼此疏离的原因。皮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和女儿,结果却是将她们越推越远,他在曼哈顿过着惬意的生活,却对生活感到不满。不仅仅是他,瑞贝卡和她的2个姐姐,卡罗尔、贝蒂,她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无论如何都会走向衰老和死亡,在生活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烦恼。但又有谁会在乎这些生活优渥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危机呢?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哲学,或积极,或随性,或压抑。他们年轻过、疯狂过,曾以为自己不是普通人,但最终敌不过岁月,走向平淡琐碎的生活。
王尔德说,人的生活中有2个悲剧,一个是我们得不到所想的,另一个是得到所想的。皮特极度地渴望美,却在夜幕降临时预感到某种形式的美将要陨落,为此倍感遗憾和无奈,“错错”的出现虽给了他满足欲望的机会,但在获得短暂的审美体验后,其生活陷入了更深的泥潭。这就是皮特生活的双重悲剧,也是大多数人生活中面临的关于得失和欲望的难题。
5. 结语
《夜幕降临》的创作带有托马斯·曼的影子,但坎宁安又不像曼那样庄重和严厉,而是更倾向于伍尔夫、乔伊斯等人的写作风格,聚焦于人物的日常生活,语言更富音乐性和诗意。坎宁安在《威尼斯之死》的导言中写道:“20世纪欧美文学中的大多数英雄都在奋斗,不是反对婚姻约束、出身卑微和政治制度,而是反对损失本身。” (Cunningham,2004)xvi—xvii布鲁姆、达洛维、亨伯特、盖茨比和奥森巴赫等这些角色虽各不相同,但他们也有一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茫茫大地上的小人物,尽管世界已经给了他们生存所需的一切,但他们依旧热切渴望着某种东西。迈克尔笔下的主人公同样如此,他们的生活比大多数人更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得真正的胜利。皮特真诚地渴望美的理想,追寻美的事物,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美进行追问,最终发现了其价值的虚无性。如果说奥森巴赫的命运更为宏大高尚,也更令人感到欣慰,那么坎宁安则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使主人公更具普通人的特质。死亡使时间得以永恒,奥森巴赫在死亡中占有了永恒的美,而皮特向往的美则不断被生活瓦解和颠覆,展现其令人心碎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特对生活的渴望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欲望投射。坎宁安将美的难题摆在皮特面前,让他来平衡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也将这一难题抛给普通大众。20世纪西方社会突出地体现了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欧美文学大多展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问题依然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坎宁安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人物来了解这个时代” (Cunningham,2004)xvi,他也力图使自己的主人公成为可以展现时代特性的典型人物。他以美和艺术为小说叙述的主题,观照人的精神向度,探讨人类内心真正缺失的东西——一个可以让人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进而揭示了其悖论性:人可以借助精神理想来超越生命和死亡,但又会因过度的追问导致生活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