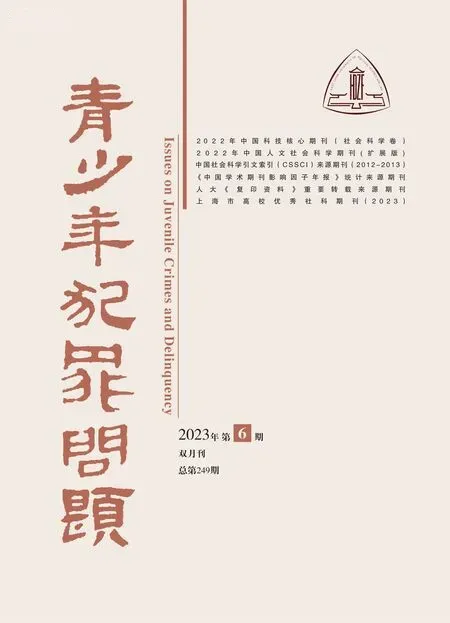事后抢劫的新解释
——基于《刑法》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的立场
2023-02-06黎森予
黎森予
《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条在理论上通常被称为“转化型抢劫”“准抢劫”或“事后抢劫”(下文均采用“事后抢劫”的表述)。由于刑法规定对事后抢劫适用抢劫罪的法定刑,而抢劫罪的法定刑较严厉,所以对本条适用范围的明确界定显得格外重要,以确保本条所涵盖的行为的不法、责任与其法定刑相匹配,同时避免产生处罚漏洞。在理解本条规定的各种要素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但既有观点均以事后抢劫属于法律拟制为前提,这可能难以完全解决本罪面临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初步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思路,旨在解决本罪内部以及本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处罚不均衡的问题,以实现处罚的协调与合理。
一、《刑法》第269条的规范性质
(一)法律拟制说的疑问
通说认为,《刑法》第269条属于法律拟制。(1)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500-501页;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7页;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页;陈兴良:《口授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3页。法律拟制是指在明确知晓事物事实上不相同的情况下,依然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同等对待。(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33页。就事后抢劫而言,这意味着《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情形本不符合第263条的规定,但依然要作为抢劫罪处理。不过,即便这样理解,也只是在形式上重新表述了现成的法律规定。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必须将不符合抢劫罪成立条件的情形拟制为抢劫,并适用如此严厉的法定刑,即法律拟制的根据何在。关于这个问题,理论上通常有两类说明。
第一种观点认为,拟制的理由在于其预防必要性较高。亦即,从犯罪学对犯罪现状的观察可以看出,盗窃犯在犯行终了以后或者在放弃盗窃的意思并离开现场之际,经常会实施暴力或威胁行为。因此,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观点,对这种情形需要相较于普通的暴力、威胁行为加重处罚。(3)大谷實『刑法各論[第5版]』(成文堂,2018年)162頁参照。另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或者说,事后抢劫的拟制规定是基于犯罪心理学上的考量,向已经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行为人传递“穷寇不可妄动”的信息。(4)参见林东茂:《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但是,这种观点存在颠倒刑罚中的责任与预防关系的缺陷。根据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行为人科处的刑罚不得超过责任的限度,而责任的程度又是对违法行为进行非难的程度,所以责任的程度和分量不可能超过不法的程度和分量。因此,只有与个别行为的不法相关的要素,才能增加刑罚的分量。(5)井田良「量刑事情の範囲とその帰責原理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一)」法學研究55巻10号(1982年)89頁参照。对于犯罪预防的考虑,不能超出反映既有责任的报应刑的范围。(6)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第2版〕』(有斐閣,2018年)14頁参照。所以,在不能说明事后抢劫的不法、责任较高的前提下,无法单纯从预防必要性高低、犯行发生的常见程度来说明将事后抢劫拟制为抢劫的根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之所以要拟制为抢劫罪,是因事后抢劫的不法和责任与普通抢劫是同质的。普通抢劫是先使用暴力、威胁行为,造成压制反抗的状态,然后取得财物;而事后抢劫是先取得财物,后使用暴力、威胁行为,并造成压制反抗的状态。本罪的取财行为与强制行为的顺序虽然与普通抢劫罪相反,但是仍存在时空的紧密连接关系,以致与普通抢劫罪的不法相同。(7)参见许泽天:《刑法分则(上):财产法益篇》,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46页;另参见黄惠婷:《准强盗罪之强盗本质》,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7年第99期。或者说,取财行为与强制行为发生的顺序,并不影响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8)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238頁参照。于是,在整体不法程度上,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等值。(9)参见张明楷:《侵犯人身罪与侵犯财产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8-269页。但是,如果认为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不符合抢劫罪的构造,那么将难以解释两者的不法、责任何以等质。
其一,事后抢劫的不法与普通抢劫并不同质。一般认为,抢劫罪是暴力、威胁等强制行为与盗窃行为的结合,但是,抢劫罪并不是两种行为的简单组合。在我国,单纯的殴打、威胁行为至多处15日拘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43条),而盗窃罪基本犯的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但是,抢劫罪的基本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远远超过上述两种行为的处罚之和。可见,抢劫罪的不法不是强制行为与盗窃行为相加,而必须超过孤立的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的总和;(10)参见[日]桥爪隆:《论事后抢劫罪》,王昭武译,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同样的结论,曽根威彦『刑法の重要問題〔各論〕』(成文堂,2006年)162頁参照。否则,就不能与其法定刑匹配。抢劫行为与孤立的强制行为、盗窃行为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实施强制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超过要素,强制行为被作为取财的手段,而强制行为对被害人生命、身体造成的危险性程度高低,必须结合上述主观超过要素进行判断。(11)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3版]』(有斐閣,2016年)98頁参照。亦即,植根于夺取财物的物欲的暴力、威胁行为,其性质更加执拗、凶恶,(12)参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232頁参照。针对被害人人身的危险性高于通常的殴打或威胁,正是这一点使得抢劫罪的法定刑高于一般的殴打、威胁行为与盗窃行为的处罚之和。
问题是,如果认为事后抢劫是法律拟制的特别规定,那么上述处罚根据将不复存在。一方面,既然在先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已经陷入既遂或者未遂的停止形态,那就意味着先前犯罪中财物的占有转移已成定局,事后抢劫中的暴力、威胁行为无法改变先前犯罪已经取得财物或者没有取得财物的结局,亦即后续的暴力、威胁行为不是作为取财的手段,并非植根于物欲,并不具有特别执拗、凶恶的性质,缺乏升高不法的主观超过要素。由此,所谓的事后抢劫实际上是孤立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和殴打、威胁行为(治安违法)的并合,缺乏拟制为抢劫罪的根据。简言之,要具备作为抢劫罪处罚的根据,单纯具有强制行为是不够的,更关键的特质在于强制行为必须充当取财的手段。(13)参见佐伯仁志「事後強盗罪に関する覚書」『川端博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下)』(成文堂,2014年)189頁参照。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事后抢劫中的暴力、威胁行为依然是取得某种财物的手段,(14)例如,认为事后抢劫的行为是取得“对财物更稳固的占有”,或者认为是取得“返还义务的免除”这一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依然具有针对某种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非法占有目的,因而对被害人的人身具有某种特殊的危险性,那么只能说明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就符合普通抢劫罪的构造,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拟制规定。
此外,难以认为单纯的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目的也具有提升暴力、威胁行为危险性的特质。这是因为,构成其他犯罪的行为人也完全可能为了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但刑法却没有加重处罚这样的行为。(15)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成文堂,2018年)232-233頁参照。例如,危险驾驶罪同样是当下案发率非常高的犯罪,但刑法并没有加重处罚危险驾驶后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16)即便在有些场合可以作为妨害公务罪与前行为并罚,所加重处罚的程度也远远轻于事后抢劫的法定刑。可见,从刑法的其他处罚规定来看,不能认为单纯的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目的就是提升暴力、威胁行为危险程度的根据。
其二,如果认为事后抢劫是拟制性规定,那么它的责任与普通抢劫不相当,甚至低于孤立的强制行为、盗窃行为。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后续的暴力或威胁行为是为了捍卫已经到手的赃物或者使自己摆脱处罚。犯罪人自己掩饰自己的赃物、自己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自己在犯罪后窝藏自己,这些掩饰赃物、毁灭证据、窝藏自身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正是因为上述动机的形成“并不是行为人自己在行为当下可以自己作控制,而是几近于人之天生的必然,所以有所谓‘人之常情’的说法”。(17)黄荣坚:《强盗罪概念的重构》,载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刑与思: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74页;另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6页以下。因此,如果认为事后抢劫不是为了取得新的财物,而单纯是为了捍卫已经取得的赃物或免于刑罚,那么事后抢劫中强制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将低于通常的暴力、威胁行为。这样一来,其处罚按理本应低于通常的暴力、威胁行为。但在现实的立法中,对事后抢劫的处罚不但没有基于上述因素减轻,反而远远重于暴力、威胁行为(治安违法)与盗窃等犯罪所对应处罚的并合。可见,原有的解释与立法现状并不相容。
其三,如果认为事后抢劫是特别的法律拟制,那么还将引发其他处罚范围上的矛盾。“法律拟制的内容并非‘理所当然’,只是立法者基于特别理由才将并不符合某种规定的情形(行为)赋予该规定的法律效果,因而对法律拟制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18)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1页。显然,敲诈勒索行为比诈骗行为更加凶恶、粗暴。如果认为诈骗后出于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其不法、责任尚且和普通抢劫同质;那么,敲诈勒索后出于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其不法、责任程度应当更高,更有必要拟制为抢劫罪。问题是,《刑法》第269条并没有将敲诈勒索明文列举为先前行为,如果认为本条属于法律拟制,而法律拟制的规定不能推而广之,则敲诈勒索后的“事后抢劫”行为不应拟制为抢劫罪,但这种处罚范围上的差异既不公平、也难以理解。(19)可能有的意见认为,当先前犯罪为敲诈勒索罪时,虽然不可能成立事后抢劫,但出于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然可能成立针对财产性利益的普通抢劫罪,抢劫的对象是“返还义务的免除”这一财产性利益,因此结论上不存在不协调之处。可是既然承认上述定罪逻辑,那么在先前犯罪是盗窃、抢夺、诈骗罪的场合,也完全可以认为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就成立针对财产性利益的普通抢劫罪。最终在结论上,便只能承认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而且,普通抢劫罪中的强制行为既包括暴力、威胁,也包括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法,但是《刑法》第269条并没有将“其他方法”规定为事后抢劫中的后行为。由于法律拟制的规定不得推而广之,因此如果认为本条属于法律拟制,便只能认为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压制反抗的方法不构成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问题是,“其他方法”针对被害人意思自由的压制程度以及针对被害人人身的危险性,完全可能超过威胁。例如,使用麻醉药物致被害人昏迷或手脚无力的,通常都被认为是暴力、威胁以外的其他方法;(20)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500页。但是,这种行为的危险性显然超过口头上威胁被害人的行为。既然认为出于特定目的实施口头威胁的不法、责任尚且与普通抢劫相当,那么对于更恶劣、更危险的“其他方法”,没有理由不将其拟制为抢劫罪。但现实的立法与上述推论不符。
简言之,如果认为事后抢劫行为本不符合普通抢劫的规定,而是特殊的法律拟制,那么将难以解释其不法、责任何以与普通抢劫相当。如果否认事后抢劫行为具有进一步取得财物的性质,那么其非难可能性甚至低于孤立的强制行为与盗窃行为的并合。此外,在法律拟制的前提下,存在某些不法、责任明显高于通常的事后抢劫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无法拟制为抢劫罪定罪处罚,法律拟制说无法解释这些处罚范围的差异。
(二)注意规定说的提倡
笔者认为,《刑法》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具体而言,即便没有设立本条,本条所描述的行为原本就符合《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普通抢劫罪。抢劫罪的对象除了有体物,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尤其是债务的免除。(2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1-1272页。因此,采取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压制被害人反抗,使被害人事实上不能行使债权,并使债务人一时地或终局性地免于履行债务的行为,原本就构成针对财产性利益的抢劫罪。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移了某个财物的占有,进而产生了返还原物的请求权以及相应的债务。以盗窃、诈骗、抢夺等方式剥夺被害人对财物享有的占有地位,固然是一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不法结果;可是,这一结果未必能完全评价进一步的针对返还原物请求权的侵害,后续行为具有超出先前行为的法益侵害结果的损害。以盗窃为例,盗窃既遂后,行为人可能出于某些原因主动归还原物,可能毁坏赃物使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事实上灭失,还可能通过敲诈、诈骗等方法事实上免除对赃物的返还义务。显然,在上述三种情形中,被害人的财产法益的受损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不可能认为最终取回原物的被害人的财产状况和赃物最终被毁坏的被害人是一样的。但是,上述差异无法直接反映到盗窃罪的结果中,因为就先前的盗窃罪而言,上述三种情形都属于盗窃既遂,在既遂结果上没有任何差别。可见,针对返还请求权的侵害,是超出盗窃、诈骗、抢夺等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外的新的法益侵害事实。要反映后续的法益受侵害情况,只能认为后续针对返还请求权的侵害行为可以构成新的犯罪。事后抢劫正是以“压制反抗”这一最凶恶的方式取得“免于返还赃物”这一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得以在盗窃、诈骗、抢夺等先前犯罪之外,单独成立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抢劫罪。在这个意义上,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就符合抢劫罪的构造。(22)类似的观点,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第7版〕』(弘文堂,2018年)198頁参照。仅在先前犯罪既遂的场合承认事后抢劫是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普通抢劫的观点,参见周啸天:《事后抢劫罪共犯认定新解——从形式化的理论对立到实质化的判断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3期;佐伯仁志「事後強盗罪の共犯」研修632号(2001年)6頁参照。易言之,根据后一种观点,先前犯罪未遂的场合也可能成立事后抢劫,此时不再是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普通抢劫。
事实上,认为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就成立普通抢劫罪,不但是理论上的推论,而且是部分国家司法实践采取的立场。例如,前苏联刑法并没有类似于我国《刑法》第269条的规定,但其通说认为:“当犯罪人占有他人财产时,因为被害人不在或入睡等情形,而未施用暴力或未以施用暴力相威胁。但是犯罪人因受归来的或睡醒的被害人的阻拦而施用暴力或以施用暴力相威胁,犯罪人在被害人追捕时也可能进行抵抗。在这种场合下,犯罪人的行为也应该以强盗论罪。”(23)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等:《苏维埃刑法分则》,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76-277页。显然,其通说主张认定为抢劫罪的情形,包括了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盗窃后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捕的情形,但这一结论并不以专门的拟制性规定的存在为必要。加拿大刑法也是如此,即使没有特别规定,刑法理论也将上述情形当然地包括在抢劫罪当中。(24)参见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当然,除了在理论上说明将《刑法》第269条解释为注意规定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既然事后抢劫的行为原本就构成抢劫罪,刑法为何要将此种情形特别规定出来?如果不能说明做出注意规定的理由,即如果根本没有必要做出注意规定,那么所做的规定则更可能是法律拟制。(2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页。对此,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之所以要做出注意规定,是因为事后抢劫的对象的特殊性。“对于针对财物的犯罪而言,由于其客体是有形的、可视的财物,所以可以相对容易地认定其转移、取得的情况,与此相反,针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的客体是无形的利益,对其转移、取得情况的判断就不一定那么容易了。”(26)曽根威彦『刑法の重要問題〔各論〕』(成文堂,2006年)163頁。我国早前甚至有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完全不是抢劫的对象。(27)参见张国轩:《抢劫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事后抢劫的对象是无形的返还请求权,所以刑法需要以注意规定的形式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这一财产性利益的要保护性,不能以对象是无形的利益为由否认抢劫罪的成立,也不能认为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抢劫行为完全被先前犯罪吸收。
第二,事后抢劫的规定还带有罪数规定的性质。虽然在先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与在后的暴力、威胁行为在构成要件的层面成立两个不同的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并罚。虽然前后行为分别触犯两个不同罪名,而且前行为针对的对象是被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本身,后行为针对的对象是衍生而来的返还请求权,但是,财物和财物衍生的返还请求权实质上指向经济上的同一财产,对财物的侵害行为与对返还请求权的侵害行为之间具有原因—结果的紧密关联性,两者符合包括一罪的关系。(28)山口厚『刑法総論[第3版]』(有斐閣,2016年)403-404頁、町野朔『犯罪各論の現在』(有斐閣,1996年)146-147頁参照。亦即,当同一行为人同时构成在先的盗窃、诈骗、抢夺罪与在后的抢劫罪时,不应将两者并罚,而应只认定较重的抢劫罪,并将先前犯罪作为量刑情节处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正是为了提醒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不得将抢劫罪与先前犯罪并罚。
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争议
《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事后抢劫以“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前提。由于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因此应当按照针对财产性利益的普通抢劫罪的构造理解这一要素。由此,“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实质上是表明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的要素。
第一,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必符合盗窃、诈骗、抢夺罪的全部条件,不问数额、次数,但行为人必须在盗窃、诈骗、抢夺中实际取得财物。在日本,主流学说认为,作为事后抢劫前提的盗窃罪不限于盗窃既遂,还包括盗窃未遂的情形。因此,即便行为人在先前的盗窃中没有取得任何财物,但当场为摆脱抓捕或毁灭罪证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然得以成立事后抢劫。(29)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創文社,1974年)479頁、大谷實『刑法各論[第5版]』(成文堂,2018年)162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239頁、中森喜彦『刑法各論』(有斐閣,2015年)126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300頁、山口厚『刑法各論』(有斐閣,2010年)227-228頁参照。日本判例历来也坚持这一立场。(30)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24年(1949年)7月9日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3巻8号1188頁参照;大審院昭和7年(1932年)12月12日判決,大審院刑事判例集11巻1839頁参照。相反,在德国,要成立抢劫性盗窃,盗窃行为必须在暴力、威胁行为前已经达到既遂,即“行为人必须已经破除了他人对相应物品的占有并且建立起了新的占有关系。”(31)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在我国,早先有部分学说主张,成立事后抢劫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盗窃、诈骗、抢夺到了财物;(32)参见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但是,当前大多数学说和判例均认为,成立事后抢劫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罪达到既遂。在此前提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用语包括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未遂的情形,但是盗窃、诈骗、抢夺的目标财物必须满足“数额较大”的要求,或者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必须满足次数等方面要求,否则不符合未遂罪的成立条件,不能构成事后抢劫。(3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5-1276页。另参见赵拥军:《转化型抢劫罪的司法认定思路及要点》,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5期;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2-1043页;张国轩:《抢劫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6页;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5页。实践中,也有司法工作人员指出,只要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对象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就可能转化为抢劫罪;反之,如果行为人针对数额显著轻微之财物实施偷盗,由于先行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之后被人发现而使用暴力的,当然也就不能转化为抢劫罪。(34)参见聂昭伟:《小偷小摸行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载《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立事后抢劫只需要具备外观上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既不要求财物或行为满足数额、次数等方面的要求,也不需要达到既遂。这是因为,“普通抢劫罪的成立并没有数额限制,而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只是在暴力、威胁与取得财物的先后顺序上有差别,并无实质性不同,因此,在成立犯罪的条件上也不应该有差别。”(35)郑泽善:《转化型抢劫罪新探》,载《当代法学》2013第2期。另参见曾粤兴、贾凌:《抢劫罪、抢夺罪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司法实务中,多数的做法采取了后一种观点,亦即成立事后抢劫并不要求先前犯罪达到既遂,而且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满足数额较大、行为次数等要求。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主要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一般不考察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否既遂。”例如,被告人见被害人家无人便翻墙进入院内,意图实施盗窃;进入院内后,被告人发现自己的行为已被村民发现,便又从院内翻墙出去。随后,村民对被告人实施追击,被告人在被追至一池塘边时为能顺利逃脱,便从携带的电脑包内掏出西瓜刀,对追击的村民实施威胁。尽管被告人在盗窃中没有取得任何财物,但法院依然认定其成立抢劫罪,且属于犯罪未遂。(36)参见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2014)鸠刑一初字第00091号刑事判决书。此外,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审理意见》)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盗窃、诈骗、抢夺接近‘数额较大’标准的;(2)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诈骗、抢夺后在户外或交通工具外实施上述行为的;(3)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结果的;(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的;(5)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据此,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即便先前行为并不符合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但只要具备《审理意见》规定的其他条件,就可以作为事后抢劫处理。例如,被告人在某超市将一件黑色男式长裤(价值人民币47.5元)穿在身上欲盗走,后在超市一楼收银台处被被害人发现并将其拦截。被告人在听说被害人已经报警的情况下,趁被害人不备逃跑,抓捕过程中被告人用嘴将被害人的左手手腕咬伤。经鉴定,该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从数额、次数、地点等方面看,行为人先前的盗窃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要求(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但法院依然认定成立事后抢劫。(37)参见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初字第00034号刑事判决书。
诚然,《刑法》第269条表述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一用语既可以包括既遂行为,也可以包括未遂行为。但是,对于在盗窃、诈骗、抢夺中没有取得任何财物的行为人,将后续暴力、威胁行为认定为事后抢劫,这一结论明显不合理。首先,各个实行行为的内容必须包含法益侵害的危险。(38)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77頁、西原春夫『犯罪実行行為論』(成文堂,1998年)16頁参照。可是,如果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没有取得任何财物,那么后来的暴力或威胁行为将完全不具有侵害财产的性质,其法益侵害性不可能与普通抢劫同质,不能作为抢劫的实行行为。其次,事实上,如果在先前行为中没有取得任何财物,为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做出的暴力、威胁行为就仅仅具有妨害司法活动以及妨害公民行使扭送权的效果。(39)正面承认这一点的,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239頁参照。而对于已经犯罪的行为人,实施一般的暴力、威胁行为逃避对自己的追诉,是缺乏期待可能性的举动,(40)参见曾淑瑜:《准强盗罪之共同正犯及既未遂》,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3年第51期;黄荣坚:《强盗罪概念的重构》,载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刑与思: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73-275页。在妨害公务罪的场合的讨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4页。本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可是如果将其认定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则不但作为犯罪处理,而且作为特别重的抢劫罪论处,这与期待可能性的一般原理不相容。最后,即便认为为了特殊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所以不得不将盗窃、诈骗、抢夺未遂后的暴力、威胁行为作为抢劫罪处理,那么,这也依然无法解释为何不同样地将敲诈勒索未遂、职务侵占未遂后的暴力、威胁行为作为事后抢劫予以规制。
基于上述原因,“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包括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未遂犯,但不应包括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没有取得任何财物的情形。对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未遂犯,行为人必须至少取得一些财物,才能按事后抢劫处罚。(41)同样的结论,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第7版〕』(弘文堂,2018年)192頁、林幹人『刑法各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216頁参照。类似的倾向,松宮孝明『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成文堂,2018年)232-233頁参照。在此基础上,不必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满足数额较大、多次、入户等条件。这是因为,就返还请求权的产生而言,任何盗窃、诈骗、抢夺都会导致行为人负有向被害人返还原物的义务;是否产生返还请求权,与财物的数额大小、行为次数多少以及是否入户等因素没有必然关系。因此,只要行为人在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多少取得了一些财物,就有可能针对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成立抢劫罪。当然,对于不满足数额、行为次数、入户等条件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字面上似乎不能评价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些行为看似不符合《刑法》第269条的适用条件。但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或者删除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4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第二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页。由于《刑法》第269条是第263条的注意规定,而作为基本规定的第263条没有对普通抢劫罪规定数额、行为次数之类的要求,因此在事后抢劫也不需要满足这些要求。基于此,“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被理解为泛指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而不限于成立犯罪的情形。或者说,本条之所以仅仅提示性列举了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情形,而没有全面地列举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因为只有在先前行为构成犯罪的场合,才需要提醒司法工作人员仅能认定为抢劫罪一罪、不得数罪并罚。在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场合,不可能数罪并罚,所以没有提示的必要。
第二,不限于普通的盗窃、诈骗、抢夺,针对特殊对象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也可能满足事后抢劫的前提。此外,实施盗窃、诈骗、抢夺以外的侵犯财产行为后强制免除自身返还义务的,也可能成立事后抢劫。我国刑法既规定了普通的盗窃、诈骗等罪,又规定了盗伐林木、合同诈骗等特殊的盗窃、诈骗行为。对此,一部分观点认为,事后抢劫的先前行为限于刑法分则第五章中的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包括其他以盗窃、诈骗、抢夺方法实施的犯罪,“这是遵循立法原意、恪守罪刑法定之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43)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另参见李希慧:《抢劫罪的对象、标准及转化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8期;沈志民、高晓春:《论我国刑法中的非典型抢劫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便盗窃、诈骗行为同时满足盗伐林木、合同诈骗等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妨碍其成为事后抢劫的先前行为,后者也属“犯盗窃、诈骗、抢夺罪”。(4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7-1278页;黎宏:《刑法学各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300页;肖中华:《论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由于特殊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也可能产生返还请求权,所以也满足事后抢劫的前提,即先前行为并不限于普通的盗窃、诈骗等罪。从结论的均衡性来看,特殊的盗窃、诈骗行为的不法重于普通的盗窃、诈骗等罪,既然更轻微的后者无疑得以成立事后抢劫,那么更恶劣的前者也应满足事后抢劫的前提条件。
此外,由于《刑法》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所以得以成立事后抢劫的先前行为不限于盗窃、诈骗、抢夺三类,而应包括一切可能产生返还请求权的侵犯财产的行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不是对三种犯罪的封闭式列举,而是仅仅提示了事后抢劫的常见情形。依据《刑法》第263条进行判断,一切可能产生返还请求权的侵犯财产的行为都满足事后抢劫的前提。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职务侵占后,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手段免除自己返还义务的,也完全符合事后抢劫的条件。此时,应当按抢劫罪一罪论处,不再与敲诈勒索、职务侵占等罪并罚。实务中,部分判例对职务侵占后使用暴力窝藏赃物的行为否认事后抢劫的成立,而是认定为普通抢劫并与职务侵占罪并罚。(45)参见甘肃省环县人民法院(2015)环刑初字第249号刑事判决书。这种结论在形式上符合《刑法》第269条的文义,但实质上并不妥当。一方面,判决认为由于前行为不属于盗窃、诈骗或抢夺,因此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的规定,进而适用第263条认定为抢劫罪;又因为第263条没有包括一罪的规定,所以可以与职务侵占罪并罚。于是,便形成了不公平的局面:如果前行为是更粗暴的盗窃、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仅构成事后抢劫一罪;但如果前行为是更温和的侵占行为,为窝藏赃物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反而导致抢劫罪与(职务)侵占罪并罚。另一方面,判决认为职务侵占行为不属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范围,进而不适用《刑法》第269条,但又依然适用第263条,这实际上表明前一判断对于抢劫罪的成立而言是多余的。亦即,在结论上,无论前行为是否属于“盗窃、诈骗、抢夺”范围之内,都可能构成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抢劫罪。可见,应当将《刑法》第269条理解为第263条的注意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一表述就仅仅是对部分事后抢劫情形的特别提示,而不是封闭性的列举。
三、“当场”的判断标准
大多数学说认为,事后抢劫中的“当场”是指后续的暴力、威胁行为与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的接近性,两行为在时间上的间隔长短和空间上的距离大小是判断当场性的基本因素。(46)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301頁、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弘文堂,2018年)192頁、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252頁、大塚裕史『刑法各論の思考方法』(早稲田経営出版,2010年)174頁参照。另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1页;黎宏:《刑法学各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0页。
一方面,如果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做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场所附近,而且两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那么几乎可以无障碍地认定其具备当场性。《指导意见》规定:“‘当场’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由此可见,以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中心形成的一片在时间、空间上比较接近的区域,都属于“当场”。例如,被告人到位于综合市场的某废品收购站,看见被害人停放在门口的一辆摩托车(价值1200元)的电门锁插着钥匙没有上锁,遂走上去拧开该车的电门,但无法启动,被告人即推着该车走,走到综合市场前一小巷时被赶来的被害人抓住,被告人反抗并在扯打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威胁被害人。虽然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场所并非盗窃的场所本身,但由于两者在时间、空间上比较接近,所以依然得以认定当场性。(47)参见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14)汕海法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书。
另一方面,如果从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的场所开始对行为人进行连续不断的追捕,行为人在被追捕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多数观点也认同此时满足当场性的要求,此时连续不断的整个追捕过程被视为盗窃、诈骗、抢夺“现场的延伸”。(48)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黎宏:《刑法学各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0页;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8页。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301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239-240頁、大谷實『刑法各論[第5版]』(成文堂,2018年)163頁参照。
例如,被告人先携带作案工具到L花园实施盗窃,被该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并报警,被告人使用自制钥匙将L花园楼下停放的一辆摩托车的电门锁扭开,并驾驶该摩托车通过该小区北门时,被守在该处的民警拦停;被告人马上弃车逃跑到Y小区,民警一直在后面追赶并进入该小区围捕,被告人试图翻墙逃跑时,一只脚被民警抓住,为抗拒抓捕,拿出随身携带的胡椒喷雾向民警喷射,随后被多名民警制服并抓获。对此,被告人辩称其实施盗窃被发现后离开了现场,在Y小区与搜捕人员发生冲突并反抗的行为不具备法条规定的“当场性”。法院认为,“当场”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抓捕的整个过程与现场;公安民警从在L花园北门口查获盗窃摩托车的被告人后开始实施追捕,并随被告人进入Y小区,被告人在Y小区躲避期间,民警的搜捕行为一直没有停止,并在重新部署抓捕方案后在Y小区将其抓获。因此,被告人系在公安机关持续进行的抓捕行动中被抓获的,具备构成事后抢劫的“当场性”。(49)参见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刑终558号刑事裁定书。
诚然,如果将《刑法》第269条理解为第263条的注意规定,并认为事后抢劫在本质上是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抢劫的一种特殊情形,那么确实难以解释为何刑法规定当场性这一要件。(50)十河太朗「事後強盗罪の本質」同志社法學62巻6号(2011年)461頁参照。单从免除自身返还义务的角度出发,即便被害人一年后再偶然碰见盗窃、诈骗、抢夺其财物的人,返还请求权也一直存续,此时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免除自己返还义务的,也应构成事后抢劫,但这似乎不符合“当场性”的要求。结局上,“当场”就成了一个游离于返还请求权以外的要素。(51)嶋矢貴之「事後強盗罪における窃盗の機会継続性」ジュリスト1247号(2003年)167頁参照。可是,对于这个矛盾,有必要首先检讨的问题是:《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当场”是否只能解释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与暴力、威胁行为在时间、空间上的接近性?刑法将事后抢劫的处罚范围限制于前后行为具备当场性的场合,根据何在?
实际上,大多数学说要求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比较接近,是为了保证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在外观上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直觉上的相似性并没有刑法规范上的意义,通说实际上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前后行为在时空上的接近性为何有决定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如果认为事后抢劫是法律拟制,那么它与普通抢劫根本不可能“相似”,(52)参见[日]桥爪隆:《论事后抢劫罪》,王昭武译,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5期。因为事后抢劫完全颠倒了强制行为与取财行为的顺序,强制行为也不再是作为强取财物的手段而存在的。近来,一种更有力的观点认为,“当场”做出的暴力、威胁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有特殊的危险性。亦即,当场性代表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紧迫对立状态的存在,“在这种尚未平稳化的、紧迫的对立状态之下,行为人出于法所规定的目的,实施暴行或者威胁行为,奠定了与抢劫罪近似的罪责基础”,并且“一旦这种对立状态平稳化,就不能认为属于‘盗窃的机会继续中’了”。(53)[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7页、第209页。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弘文堂,2018年)192-193頁参照。上述冲突状况会给行为人提供强烈的逃离现场的动机,并给被害人强烈的抓捕行为人的动机,进而两者的冲突会为被害人的人身带来危险性,因此需要加重处罚行为人“当场”做出的暴力、威胁行为。(54)嶋矢貴之「事後強盗罪における窃盗の機会継続性」ジュリスト1247号(2003年)167頁参照。究其本质,之所以行为人与被害人形成对立状况,不是因为在时间、空间上接近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而是被害人在现场提出了当即返还原物的诉求而行为人不服从,两者的对立与距离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远近没有必然关系。即便是被害人在被盗窃或诈骗一年后再偶然撞见携带赃物的行为人,只要两人互相认出且被害人当场要求返还赃物,那么两者间紧迫的对立状况便又立刻形成,这与被害人在盗窃或诈骗的现场要求行为人返还的情形,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亦即,从“紧迫的对立状况”视角出发,无法得出事后抢劫必须限于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比较接近的情形这一结论。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人是否被追捕、追捕过程是否连续,这些因素与紧迫的对立状况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恰恰相反,行为人在被追捕的过程中消耗了体力,完全可能认为此时对被害人的危险性小于一年后又偶遇的情形,所以没有重罚的必要。
基于以上讨论,不应当从时空的接近性、追捕过程的连续性等方面理解《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当场”。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的间距,对刑法而言没有独立的意义。相反,本文认为,“当场”是指被害人一方可能当即取回财物的现场,(55)类似的表述,近藤和哉「事後強盗罪の根拠と解釈」神奈川ロージャーナル5号(2012年)33-37頁参照。只要存在被害人一方在现场即时夺回赃物的可能性,就有成立事后抢劫的余地。
固然,返还义务的免除属于抢劫罪中的取得财产性利益。但是,并不是任何拒不履行返还赃物义务的行为都转移了返还请求权这一财产性利益。抢劫罪是转移占有的犯罪,成立抢劫罪要求财物由被害人占有转移给行为人(或特定第三人)占有,对于无形的财产性利益也是如此。因此,只有当行为人“现实地取得了具体的财产性利益”,才能认为存在类似于有体财物的占有转移那样的财产性利益的转移,而不仅是抽象的、间接的、附条件的取得利益的机会。(56)大塚裕史『刑法各論の思考方法』(早稲田経営出版,2010年)160-162頁参照。
在事后抢劫的场合,能否认定行为人通过强制手段现实地、具体地取得了“返还义务的免除”这一财产性利益,正取决于其实施暴力、威胁行为时,是否处于可能当即被夺回赃物的现场。如果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被害人(及被害人一方的人)本有可能当即夺回财物,且行为人面临着来自被害人一方的迫切的归还财物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从紧迫的现场中脱身,便构成事实上对自身返还义务的免除。(57)中森喜彦『刑法各論』(有斐閣,2015年)124頁、内田文昭『刑法各論』(青林書院,1996年)273頁参照。此时,对返还义务的免除是现实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间接的。或者说,在行为人携带赃物并面临被害人的归还要求的情形中,行为人本应立即将手中的赃物归还,如果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脱身的话,便至少取得了“暂时迟延履行债务”这一财产性利益。(58)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298頁参照。反之,如果根本不存在当场返还赃物的可能性,例如赃物被藏匿于他处或者早已被毁坏,那么即便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从被害人要求归还的现场中脱身,也难以认为存在具体的财产性利益的转移。这是因为即便行为人停留在现场,也不存在当即返还财物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场合中被害人并不存在具体的、现实的夺回财物的手段,而仅仅具有抽象的、间接的、附条件的取回财物的机会,如进一步向行为人施加压力或要求警察拘留行为人,迫使其交出藏于别处的财物。但是归根到底,这时的被害人事实上难以使行为人必然地、现实地交出财物,只能委诸行为人进一步的决定以及客观事态的发展,在财物已经毁坏的场合,甚至连返还的可能性也不具有。因此,如果当场不存在即刻夺回/返还财物的可能性,那么被害人事实上就无法享有具体的、现实的返还请求权,只有某种抽象的请求行为人返还的机会;与此相应,行为人摆脱被害人的请求、离开现场的做法,也不属于现实地、具体地转移财产性利益或者现实地、具体地免除自己的返还义务,因为被害人在这种场合根本不享有这种利益。
据此,完全可能重塑对于当场性的判断标准。一方面,当场性成立与否不取决于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间距。即便在盗窃既遂一年后,行为人手持赃物(例如被害人的手机)在逛街时偶然与被害人相遇并被被害人认出,被害人要求返还而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从而离开现场的,仍有成立事后抢劫的余地。(59)在我国,曾有学说指出:“事隔若干时日,在其它地方为窝赃、拒捕、毁证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也应适用第一百五十三条(即现行《刑法》第269条——引者注)……这里所说的‘当场’并不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劫罪的现场,也不受犯上述之罪的时间、地点的限制,而是指‘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见王礼仁:《如何理解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的“当场”——兼与朱庆林同志商榷》,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此时,由于被害人完全有可能当即将行为人手中的赃物夺回,行为人强制离开现场的做法,事实上免除了自己现实的、具体的返还义务,而不仅仅是削弱了被害人取回原物的机会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赃物已经彻底毁坏、已经交回被害人或者被丢弃,那么便不再具备当场性,被害人在这种场合不再具有具体的、现实的返还请求权。例如,被告人在鞋业商贸城档口趁档主不注意,盗得内有人民币7500元的挂包1个,后在逃跑过程中被档主的丈夫发现并夺回挂包,其丈夫因被告人手持弹簧刀相威胁而放弃将被告人抓获,后被告人被鞋城的保安人员制服。(60)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刑初字第2347号刑事判决书。由于实施威胁行为时,盗窃所得的赃物已经被夺回,因此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刻不再是被害人一方可能当即夺回财物的现场,不再具备当场性的条件。又如,被告人尾随被害人,趁其不备用镊子将口袋内的一部手机夹出盗走,随后被害人发现手机被盗,追上并用双手扭住被告人的衣服和手臂,要求归还。被告人见无法逃脱便将手机归还给被害人,但被害人为了防止被告人逃脱,始终抓住其衣领,被告人为了逃脱便假称自己患有艾滋病并咬了被害人一口,被害人因害怕而松手。(61)参见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7刑终271号刑事判决书。从被告人归还赃物时起,被害人便不再具有返还请求权,不可能再次从行为人身上夺回赃物,因此归还赃物后不再属于“被害人可能当即夺回赃物的现场”,此后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不具有当场性。不仅是被害人主动夺回财物的场合,行为人自行丢弃赃物的,也不再满足当场性的要求。(62)我国唐朝时的法律即采取了这一立场:“窃盗发觉,弃财逃走,财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类,事有因缘者,非强盗。”“疏议曰:……窃盗取人财,财主知觉,遂弃财逃走,财主逐之,因相拒捍。如此之类,是事有因缘,并非强盗,自从斗殴及拒捍追捕之法。”见(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岳纯之点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事实上,对于已经返还赃物或原地丢弃赃物的行为人而言,单纯为了免受刑罚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并不具有侵犯财产的危险,反而属于期待可能性减小的行为,不可能具备与普通抢劫罪相当的不法和责任。以“拟制”“政策”之类的理由将这种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实质上并不公平。
四、事后抢劫的既遂与未遂
关于事后抢劫的既遂与未遂的判断标准,当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理论上的多数说认为,事后抢劫的既遂与否完全取决于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罪既遂与否,如果先前行为既遂则事后抢劫既遂,反之则未遂。(6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8页。団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創文社,1974年)479頁、大谷實『刑法各論[第5版]』(成文堂,2018年)163頁、山口厚『刑法各論』(有斐閣,2010年)229頁、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300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成文堂,2015年)323頁参照。少数说则认为,本罪的既遂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最终取得财物的占有,即便在盗窃、诈骗、抢夺既遂后又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但最终赃物还是被被害人当即夺回的话,事后抢劫仅止于未遂。(64)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第7版〕』(弘文堂,2018年)195頁、曽根威彦『刑法の重要問題〔各論〕』(成文堂,2006年)180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16年)239頁参照。
我国司法实践似乎采取了上述少数说,即便先前行为既遂,但是在赃物被被害人夺回的场合,对抢劫罪认定了未遂。例如,被告人趁无人之际潜入被害人住处,将被害人的钱包(价值人民币54元)偷走,被告人出门准备逃走时,被赶回来的被害人发现,被告人在逃跑至路口之时,被在后面追赶的被害人拦住,被告人在抗拒抓捕的过程中将被害人的左上臂咬伤、右手背抓伤,后被赶到的警察抓获。法院认定被告人已构成抢劫罪,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成立抢劫未遂。(65)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2)金刑初字第877号刑事判决书。又如,被告人驾驶电动三轮车将被害人的15斤铝合金(未能核价)偷走,过程中被住宅内的被害人发现,被告人见状遂驾车离开,被害人用手拉住车上的物品,被害人继续驾车行驶,被告人被拖着跑了约60米远,后治安员加入追赶并大声责令被告人停车,被害人松手并倒地,被告人边将车上的铝合金扔在地上边驾车离开现场。对此,由于被告人未能最终取得赃物,法院对抢劫罪认定为未遂。(66)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6刑终804号刑事判决书。本案有认定为中止的余地。
此外,由于通说认为先前行为没有取得任何财物的场合也属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也可能构成事后抢劫,因此在这种场合,判例也认定为事后抢劫的未遂。(67)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刑初1260号刑事判决书。如前文所述,对于先前行为没有取得任何财物的场合,本文认为根本不具有作为事后抢劫论处的余地,加重处罚这种行为在实质上并不公平,所以当然也不存在既遂或未遂的问题。至于先前行为取得财物的场合,多数说的观点并不合理,不能认为只要先前行为既遂,事后抢劫就一定既遂。
第一,如果认为事后抢劫的既遂与否完全取决于先前行为,那么就颠倒了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的关系。(68)参见娄永涛:《事后抢劫罪的未遂研究——兼及对“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的修正》,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实行行为是因果关系的起点,(69)参见〔日〕桥爪隆:《论实行行为的意义》,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2期。实行行为在时间顺序上必须出现在既遂结果之前,否则实行行为就不可能成为引发既遂结果的原因,毕竟原因不可能出现在结果之后。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必然包括暴力、威胁行为,如果既遂与否是由先前行为的既遂与否所决定的,就会导致事后抢劫的既遂标志出现在暴力、威胁这一实行行为之前,这完全颠倒了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第二,多数说的结论并不均衡。在行为人盗窃既遂后,又产生了抢劫的故意,于是暴力压制被害人反抗,但由于警察赶到、尚未取得财物就被迫逃离现场的,一般认为属于盗窃既遂与普通抢劫未遂的想象竞合。(70)西田典之=桥爪隆『刑法各論』(第7版)(弘文堂,2018年)195頁参照;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5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300頁似乎认为是包括一罪的关系。之所以不能并罚,是因为在先前的取财行为是抢劫的情况下,后续的抢劫未遂行为必然被吸收并成立抢劫既遂一罪;如果在先前是盗窃的场合将盗窃与抢劫并罚,最终的处罚就会重于先前是抢劫的场合。这显然不公平。之所以不能认定为事后抢劫,是因为另行抢劫的故意(以及进一步取财的非法占有目的)不能评价为窝藏赃物等目的。可是,如果行为人盗窃既遂后又为窝藏赃物使用暴力,那么根据多数说的结论,无论最终是否被立刻抓获,都必须认定为事后抢劫的既遂。两相比较,前者的法益侵害性重于后者,前者的可谴责性也重于后者,但多数说的结论却是后者构成既遂但前者构成未遂,这显然不公平。与之相比,少数说的结论具有合理性,但其理由存在疑问。这是因为,少数说依然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解释为目的,作为主观超过要素,成立本罪既遂自然不以目的的实现为必要。所以,少数说的结论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作为主观超过要素的性质之间存在矛盾。(71)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251頁参照。
本文认为,由于事后抢劫属于注意规定,本质上是针对返还请求权的普通抢劫罪,因此既遂与否的标准当然在于行为人是否成功地免除了当场返还的义务。相应地,《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应解释为构成要件结果,而非目的,它们是返还义务被事实上免除的征表。
首先,虽然第269条使用了“为……”这一表述,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代表主观目的。诚然,日常生活中的“为……”的表述通常是指主观想法;但是,仅就日常生活的平义解释法条与用语,不可能揭示法条与用语的真实含义,而不过是一种“机械法学”。(72)参见[美]劳伦斯·索伦:《法理词汇》,王凌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事实上,刑法所使用的“为……”这一表述,完全可能解释为客观上的结果。例如,《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便是指避险行为现实产生了使上述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这一效果,如此才符合紧急避险的相当性的要求。相反,如果认为只要在主观上具有避险意思就满足这一要素,那么假想避险也构成紧急避险,这显然不可思议。同理,第20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也是指防卫行为客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效果,而不包括假想防卫。由此,《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客观上达到“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结果。
其次,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解释为目的,存在明显不协调之处。一方面,既然“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只是主观超过要素,那么这一要素就不需要在客观上存在,只要行为人有这样的意思就够了。这样一来,如果行为人误以为对方打算夺回赃物或者实施抓捕,进而抢先对对方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但对方实际上是不相关的路人,那么依然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主观目的,从而成立事后抢劫。(73)得出这一结论的,参见张明楷:《侵犯人身罪与侵犯财产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74页;中森喜彦『刑法各論』(有斐閣,2015年)126頁参照。前者后来改变了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3-1284页。可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通说均要求被压制反抗的被害人是财物的占有人或者是对财物有保护意思的人,而不包括与财物毫无关系的第三人。(74)中森喜彦『刑法各論』(有斐閣,2015年)121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成文堂,2015年)307頁、山口厚『刑法各論』(有斐閣,2010年)219頁参照。如果认为事后抢劫中的暴力、威胁可以针对与先前行为以及财物毫无关系的第三人实施,就使得其丧失与普通抢劫的同质性。此外,不可否认的是,与普通抢劫相比,事后抢劫存在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特点,其成立标准本应比普通抢劫更高,(75)参见甘添贵:《刑法体系各论》(第二卷),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8页。但如果认为暴力、威胁的对象包括毫无关系的第三人,其成立范围就会比普通抢劫更宽泛。
另一方面,在本罪属于法律拟制的前提下,如果认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属于目的,则意味着基于其他目的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人不能构成事后抢劫。例如,行为人趁独居老人入睡时入户盗窃,却仅得一千多元,心生不满怪罪于老人,持木椅殴打老人并命其下跪道歉;由于行为人使用暴力并非出于上述三种目的,所以只能构成盗窃罪及伤害罪(如果达到轻伤标准的话)。可是,与事后抢劫的情形相比,“窃贼对所得心生不满,怪罪于老人,以致于施暴于被害人,命被害人下跪道歉,事属鲜少,在一般观念中也是更难理解的鲜耻或恶性更大之事……相对的,窃盗后的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等行为的产生是属人之常情,但是其强制行为却招来准强盗罪的特别重刑。如此轻重失衡问题所在,不难窥知。”(76)黄荣坚:《强盗罪概念的重构》,载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刑与思: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71-272页。打击报复、伤人泄愤的动机分明比通常的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更恶劣、更值得谴责,将事后抢劫的目的限于后者而将前者排除在外,并不合理。
再次,“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都可以实质地解释为行为人免除了自身的返还义务,因而相对于针对返还请求权的事后抢劫而言,属于构成要件结果。其一,“窝藏赃物”在平义上就可理解为对本可立即返还的赃物拒不返还,而且令被害人一方无法立即夺回,因而属于具体地免除自身返还义务。此时,行为人的人身是否被逮捕则并不关键,即便行为人不能现实逃脱抓捕,但是通过现场转移赃物使被害人不能取回的,依然因构成“窝藏赃物”而成立既遂。反之,如果赃物被当场夺回,“窝藏赃物”这一结果便不满足。其二,“抗拒抓捕”可以理解为免除对于无形财产的返还义务。众所周知,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的行为既可能针对有体的财物,也可能针对无体物或财产性利益,例如通过诈骗取得他人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余额。一方面,对于无形财产,似乎难以肯定“窝藏”的成立,因为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余额等财产性利益原本就不存在任何形体,谈不上被藏匿于任何处所。另一方面,对于存款债权、微信/支付宝余额等无形财产,被害人要当即取回赃款,则必须控制行为人的人身使其将上述财产处分给自己。亦即,对于无形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要确保行为人会处分、归还财产给被害人,则必须要控制行为人的人身。反之,如果行为人摆脱被害人的控制和抓捕,则是否要将赃款等财物处分给被害人,就成了可以自由决定的事,被害人强行要求其返还赃款的请求权在事实上落空了。(77)即便行为人逃脱控制和抓捕,但是被害人在观念上还存在通过报案、民事诉讼等方法取回赃款的可能性。不过,到底能否通过这些渠道取回赃款,终究是不确定的事;即使最终能够取回,也必须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与当场强令被控制的行为人将财产处分、归还给自己,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能因为被害人多少保有通过法律程序取回赃款的可能性,否认具体的返还请求权的现实丧失。因此,客观上“抗拒抓捕”的实现就征表了行为人对无形财产的返还义务事实上被免除。但是,对于有体物而言,行为人使用暴力,不能窝藏赃物但成功摆脱抓捕的,由于未能现实免除返还义务,因此应当认定为抢劫未遂,单纯摆脱抓捕这一结果并不具有令财产犯罪达到既遂的效果。其三,“毁灭罪证”也可以理解为令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事实上无法当场行使。被害人要当即夺回赃物或者强令行为人将赃款处分给自己,必须清楚证明先前侵犯财产的事实存在,以及准确识别出需要归还的赃物或赃款。在这个前提下,行为人毁灭证据的做法会使得被害人无法证明自己享有返还请求权或者不知对哪部分财物行使返还请求权,进而无法实际行使权利。例如,行为人盗窃既遂后对被害人使用暴力取得其手机,删除记录自己盗窃过程的录像,那么即便行为人当场被抓捕,被害人也难以立即证明盗窃事实的存在,进而难以要求行为人立即将所得赃物返还给自己,事实上无法行使返还请求权。在这种场合,即便行为人既不能转移赃物的处所、又不能成功逃脱抓捕,但仍使得被害人无法行使立即取回原物的权利,因此依然构成抢劫既遂。
最后,由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属于客观要素,所以只要行为人使被害人无法立即夺回财物,那么“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就已经实现,犯罪陷入既遂。反之,如果被害人将赃物当即夺回,或者成功抓捕行为人,相关证据又未遭毁灭,确定得以没有障碍地令行为人将财产性利益处分给自己,那么行为人就没能免除自身返还义务,事后抢劫止于未遂。相反,不能认为只要先前行为既遂,事后抢劫就当然既遂。此外,事后抢劫真正的主观要素是抢劫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大体上只要行为人具有相当长时间内不返还先前取得的财物的意思,就能认定针对返还请求权的非法占有目的。在此基础上,行为人还有报复、泄愤、进一步取得其他财物等动机的,也不必然阻却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