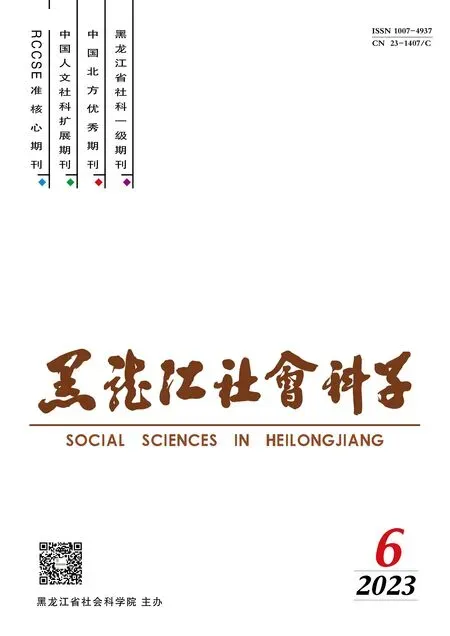宋代三苏家族崛起的地域因素与文化自信
2023-02-05马强
马 强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以及对其文化的生命力及永久价值持有的坚定信心。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问题,传递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有明确的阐释:“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还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所在:“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如果说前面所引的这些表述是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理论提炼,那么他在2022年6月10日视察四川眉山三苏祠时所发表的重要谈话,则可看作他对中华文化精英人物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的具体阐释。习近平在三苏祠说: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这是自北宋眉山三苏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家族诞生九百多年来,中国国家领袖对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做出的最高评价。习近平的讲话言简意赅,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褒扬了三苏所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包含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需要广大文史工作者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思考、阐释。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而地域文化就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宋代三苏家族的出现与成功并非偶然,既与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影响有必然关系,同时也与伴随三苏成长的本土地域文化--巴蜀文化的培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文化的自信毫无疑问包括地域文化的自信,巴蜀文化温良、敦厚、达观、刚强、自信的品格对三苏家族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从巴蜀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三苏家族在宋代的崛起、三苏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认同及其意义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巴蜀文化与眉州三苏家族的走向成功
巴蜀文化是中国十大地域文化之一,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板块。巴文化与蜀文化自古血脉相连,巴文化的特征是浪漫自信、勇健刚强,蜀文化则表现出更多的旷逸放达与重文崇雅。历史上的巴人曾经参与过商周之际改朝换代的“牧野之战”,而且表现得相当英勇而浪漫。《华阳国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以想象,来自大巴山南北粗犷、悍勇的巴人,在东征殷商的滚滚洪流中载歌载舞、生龙活虎,把血与火的战争当作了一场声势浩大、注定会大获丰收的狩猎活动。在这场决定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巴人表现得那样的青春、那样的乐观,难道不也是这个山地民族的文化自信吗?巴族作为一个部族虽然战国以后泯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巴域民众却在此后的岁月中常常活跃在中华历史舞台上,楚汉战争、三国战争、宋蒙(元)战争直至现代的抗日战争,巴域民众都以勇敢慷慨的姿态参与其中,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话剧。《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道出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互补性。
蜀地山川秀丽、自然条件优越,史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卷28《地理志》)。蜀地纳入华夏文化体系较早,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相张仪、大将军司马错伐蜀,一举灭掉蜀国,接着司马错又攻灭了蜀地东北的苴国与东南的巴国,将四川盆地纳入秦国的版图。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群出土的秦国木牍表明,早在秦武王时期,秦即已在今四川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并按照《为田律》进行土地管理[1]。汉文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大力兴办地方官学、推行儒学教育,蜀地文化迅速走向繁荣,班固即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卷89《循吏传》)秦汉以后,虽然巴蜀地区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及“僚人入蜀”,经济文化有所退缩,但尚文崇雅之风未绝。到了唐代,蜀地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至武则天时期已经成为唐朝重要的经济区与财赋来源之地,如陈子昂所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陈子昂:《陈拾遗集》卷8《上蜀中军事》)到唐代中后期,蜀锦、蜀绣、造纸、刻书、药市、花市等闻名全国,杜甫客寓蜀地时即感叹成都“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篁”(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6《成都府》)。在晚唐人心目中,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社会经济已经与东部江淮繁华之地扬州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扈仲荣等:《成都文类》卷23《唐成都记序》)晚唐王仙芝、黄巢之乱爆发,中原战乱频繁、社会激烈动荡,国都长安也沦为血雨腥风之地,因蜀地相对平静稳定,大量中原、关中衣冠士人遂举家举族流亡西迁入蜀,其中不乏名门望族,为经济发达的蜀地带来了文化兴盛勃发的大好机遇。宋代蜀地文化能够得以异军突起,与晚唐大量士人迁入有密切关系。
三苏家族文脉绵长,其先祖源于河北赵郡苏氏,而与蜀地发生联系则始自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苏洵在《苏氏族谱》中写道:
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尧(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1《族谱》)。
苏味道曾两次入蜀为官,一次任集州(今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刺史,一次任眉州刺史,后卒于赴任益州长史途中,归葬眉州。苏味道死后,其二子苏份在眉州定居下来,苏氏遂开始在眉州繁衍开来。但有唐一代眉州苏氏少有作为、声名不显,真正成为文化星宿升起于灿烂星空是在北宋三苏之时。地域乡邦文化是任何杰出文化人物生成的“原型空间”,也即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家族的成长发育都离不开地域文化传统的涵泳。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教育,推崇且耕且读、诗书传世,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多以诗书经史传家名世的家族,然而就影响当时之社会及后世之深远而言,历史上的文化家族恐无出于宋代眉山三苏家族其右。“唐宋八大家”而苏氏父子居其三,试问历史上哪个家族有此荣耀?然而宋代三苏家族的崛起并非偶然,是与巴蜀地区特别是眉山一带的文化传统、乡风民俗的熏陶有着密切关系的。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深情回忆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吕祖谦:《宋文鉴》卷82)眉州这一文化现象并非仅见于苏轼的叙述,与苏轼同时代的吕陶说得更加到位:“眉阳士人之盛甲于两蜀,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理励风俗、训子孙,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故其后裔晚生,循率风范,求为君子,以至承家从仕,誉望有立者众。”(吕陶:《净德集》卷23《朝请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志铭》)眉州士人重视经史诗书的治家风气由来已久,在三苏家族崛起之前,眉州就有藏书丰富、科举成功而居显官者。据记载,眉州人孙抃六世祖长孺“喜藏书,为楼而置其上,蜀人号为‘书楼孙家’”,孙抃则于天圣六年(1028)登进士第甲科,“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后官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曾巩:《隆平集》卷8《参知政事》)。晚年的苏洵也十分看重乡风民俗对家族的教化作用,而续修族谱就是彰显先贤、训导族人的重要举措,故其撰《苏氏族谱》,并刻石筑亭,公之于家族乡人:
匹夫而化乡人者,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乡有庠,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呜呼!彼独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积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岁时蜡社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
苏洵特地将族谱刻石于祖茔之旁,以使每年上坟扫墓者不忘先祖遗风,使“吾乡邻风俗之美”(苏洵:《嘉祐集》卷14《苏氏族谱亭记》)传之久远。这一崇文习儒的文化风气有很大的经世进取催化作用,从而使得包括眉州在内的西蜀地区在宋代人才辈出,南宋邛州蒲江人魏了翁对此不无自豪地说:“吾州之俗,检履醇固,而被服文雅。盖自汉以来,代有显人。”(魏了翁:《鹤山集》卷40《大邑县学振文堂记》)而眉州则堪称西蜀学术风气浓厚之典型,赢得了“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的美誉(祝穆:《方舆胜览》卷53《眉州》:“学者独盛。张刚《通义儒荣图序》:‘后世以蜀学比齐、鲁……政和御笔:“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由此可见,西蜀淳美的乡风民俗、崇儒重教的价值取向、“贵经术而重氏族”的文化传统是使得三苏家族脱颖而出、走向全国文化巅峰的精神源泉。
蜀地文化塑造了三苏文化心理的基调,其中对苏轼影响尤为明显。苏轼曾多次谈及家乡眉州地域风俗与学术传统对自己的影响,在《谢范舍人书》中他对当时蜀中文化风气有如是评论: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涂。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东坡全集》卷75)。
蜀地地理位置偏远,但山川雄奇、物产富庶,自战国中期入华夏版图以至西汉,文化学术逐渐异军突起,经过文、景之时蜀守文翁等人大力倡导文化教育,蜀地一跃成为西部文化昌盛之地。《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蜀地自此人才辈出,盛极一时。然而魏晋之后,巴蜀社会动荡不安,僚蛮入蜀,文化倒退、经济凋零。入宋以后,经过官方大力倡导,推广科举制度,得以移风易俗、文教再兴,苏氏家族也由此名显于世。苏轼《谢范舍人书》可谓对蜀地文教昌盛之风气作了生动回顾。眉州地域文化风俗既对青年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苏氏家族得以走出四川、走向全国的重要文化原因。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对于家乡眉州的学术文风进行过叙述与总结: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
由此可见,苏轼时代的眉州“通经学古”之风盛行,文化教育发达,在蜀地别树一帜。宋代眉州文化家族辈出,特别是三苏家族的出现与成功,与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大有关联。
二、三苏深重的巴蜀文化情结及其文化自信
巴蜀地区自秦汉进入华夏文明圈以后,逐渐成为诗书礼义之邦、文化昌盛之地,英才辈出,屡载史册。汉代蜀地诞生过司马相如、扬雄等文赋大家,魏晋时期的陈寿、常璩,唐代的李白、陈子昂也皆以文史诗豪之才名传天下。唐宋之际,众多中原优秀文士及世家大族涌入巴蜀,蜀地文化得以繁荣,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巴蜀都得到了深厚的积淀。我们说宋代三苏作为中华杰出人物最能代表巴蜀文化的自信,是因为苏轼等人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巴蜀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价值意义。宋代蜀地文化昌盛、人才辈出,除了眉山三苏父子外,北宋华阳范镇、阆中三陈、梓州苏易简,南宋眉州丹棱李焘、嘉州井研李心传、邛州蒲江魏了翁、井研牟子才等都是精英人物,以卓越事迹入载《宋史·列传》。宋代以降,四川文脉不绝如缕,明代新都杨慎、巴县蹇义、荣昌喻茂坚,清代遂宁张鹏翮及张问陶、眉州丹棱彭端淑、罗江李调元等皆闻名朝野,或以忠于社稷、秉公执法,或以博学多才著称。
三苏家族是在巴蜀文化涵泳中长成的参天大树,苏洵父子对巴蜀故土的情感无疑是浓重而一往情深的。如果说安土重迁是在中国深厚的农耕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那么浓重的家园意识则是古代士大夫共有的文化情怀。蜀地作为苏轼的桑梓之地,巴蜀文化符号与其生命历程可谓伴随始终。尽管苏轼发出过诸如“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词·定风波》)、“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东坡全集》卷28《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之类的感喟,有学者遂由此认为苏轼已经习惯于四海为家,乡土文化观念相对淡漠[2],但笔者对此则不能苟同。实际上这些诗词是其在不同人生际遇及特殊环境下的感叹,也是对自己大半生流贬经历的自讽与幽默达观的表现,并不能因此说其乡土意识淡漠。苏轼出生于“介岷峨之间”“江山秀气聚西眉”(祝穆:《方舆胜览》卷53《眉州》)的眉山,一生对巴山蜀水的热爱与眷恋始终如一。而除了人之常有的故土之恋外,巴蜀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浓郁的地理风情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学创作灵感。嘉祐六年(1061),年轻的苏轼兄弟随父亲苏洵离开故乡眉州,走水路,取道戎、泸、渝、涪、万、夔、巫至楚,循长江水路出川赴京师。一路上他们为沿途雄奇的自然风光所深深陶醉,父子三人吟诗不辍,互相唱和,后汇编为《南行集》。苏轼在《南行集前叙》中说:
山川之有云雨,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东坡全集》卷34)。
《南行集》中有苏轼诗作78首,第一次走出家乡的苏轼在诗中尽情抒发了对蜀地地理风情、人文景观的惊叹与喜爱,像《初发嘉州》《过宜宾见夷中乱山》《夜泊牛口》《江上看山》《留题仙都观》《八阵碛》《诸葛盐井》《白帝庙》《入峡》《巫山》《神女庙》等诗篇便尽写峡江之雄奇与殊异。
陕西凤翔府是年轻的苏轼释褐入仕的第一站,研读苏轼仕宦凤、岐时期的诗作,不难发现其对关中西部的地理景观有强烈的排斥感。苏轼习惯了蜀地的青山绿水,对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原感到强烈不适。在通判凤翔府期间,尽管有时会被厚重的周秦文化所吸引,但每当看见尘土飞扬的赭黄土地与荒山秃岭,他就会不断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东坡全集》卷1《东湖》);“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与鸦鹊,浩浩同一声。”(苏轼:《东坡全集》卷1《真兴寺阁》)在秦岭的深山峡谷中,也会引发诗人的故乡之思:“门前商贾负椒荈,山后咫尺连巴蜀。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苏轼:《东坡全集》卷1《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南山连大散,归路走吾州。欲往安能遂,将还为少留。”苏轼青年时即有归隐思想,当与对初仕地赭山黄土的自然环境感到强烈不适大有关系。
人的故土之恋往往基于融入心灵深处的童年、少年景观记忆。蜀地江河纵横,水量丰沛、水质优良,其中岷江流经眉山、嘉州,清澈如画,早在唐代即有“蜀江水碧蜀山青”(《长恨歌》)的美誉。苏轼诗词中的“蜀江”有时说的是长江,但更多的则是指眉州的母亲河岷江:“蜀江久不见沧浪,江上枯槎远可将。去国尚能三犊载,汲泉何爱一夫忙。崎岖好事人应笑,冷淡为欢意自长。遥想纳凉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苏轼:《东坡全集》卷2《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仕宦凤翔时期,苏轼诗作如“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苏轼:《东坡全集》卷29《题宝鸡县斯飞阁》)等频频表达出思乡归隐的想法并非偶然,地理环境的殊异感乃是重要原因。而在苏轼的词作中,乡关之思同样表现强烈。在黄州,苏轼作词总难挥去蜀地山水的影子:“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南乡子·春情》)。尽管蜀地远离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汴京,但苏轼一生从未放弃自己“蜀人”的身份认同,始终以西蜀人自居,如在荆州时他说“轼西州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苏轼:《东坡全集》卷75《上王兵部书》);即使在其仕途最顺达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苏轼:《东坡全集》卷72《上刘侍读书》)。在风景如画的人文胜地润州,观览雄阔的长江时,他也会油然想起长江上游的家乡:“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羇愁畏晩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苏轼:《东坡全集》卷3《游金山寺》);甚至日常的山中游览也每每引发其归乡之愿:“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携琴已寻壑,载酒复经丘。”(苏轼:《东坡全集》卷32《集归去来诗十首》)元丰七年,苏轼借为故里州官之请作《眉州远景楼记》,再次深情地写道:“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晩也。”可见作为蜀士的苏轼,终其一生故乡情怀始终伴随,怀蜀乡愁成为苏轼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型”情结。
比较而言,苏洵的诗作较少,主要以史论、政论散文而名世。有学者指出:巴蜀地区具有地域的封闭性与文化的开放性之特征。由于蜀地四周高山险江环绕、入蜀出蜀皆难,所以巴蜀文化比之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对轻微,六朝江南浮艳绮丽的文风对蜀地文风影响亦甚小。到了宋代仍然如此,因而以苏洵为代表的巴蜀散文作家之作品具有独特的自由奔放的风格[3]。北宋名臣张方平在为苏洵写的墓志中曾经回忆说: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部,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蛇其无间断也。因谓苏君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张方平:《乐全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42)。
欧阳修读了苏洵投献的文章后也由衷赞赏,并推荐给仁宗皇帝:
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说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辨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0《荐布衣苏洵状》)。
苏洵的政论、史论、策对,往往开篇即给人以滔滔不绝、汪洋恣肆之感,具有很强的说理性,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苏辙的政论、史论、策论则杂糅了佛道、纵横之学,如《上皇帝书》《三国论》可谓论说环环相扣、谋篇气势恢宏,寓哲理于叙史说今之中,说服力、穿透力极强。他们父子不同于传统儒者,也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在宋代学术中保持了独立品格与巴蜀特色。可以说,三苏的秉性与诗文风格与巴蜀文化的自由奔放、少受束缚的特征有直接关系。苏轼等人创立的蜀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可谓别树一帜,经历两宋之际的风雨激荡,到南宋前期受到朝野一致推崇,从而影响深远,体现了巴蜀文化独立精神与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结 语
“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的重要讲话包含两个层面的论断:一是三苏祠作为宋代三苏家族的住宅遗址受到历代官民的保护延续至今,代表了中华优秀家族文化的绵长文脉;二是三苏家族卓越古今,所谓“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其影响早在宋代即已逸出国界,在现代更是具有世界性影响,成为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例证。三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巴蜀文化的培育与涵养无疑是重要的因素,是巴蜀文化赋予了三苏达观、自由、潇洒的个性禀赋,使他们成为宋代文化的优秀代表;而反过来说,三苏的作品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巴蜀文化内容,为巴蜀文化史册增添了无以复加的荣耀,也代表了有史以来蜀人所创造的最高文化成就。三苏的英名及其文化遗产必将继续惠泽后世,成为中华民族文脉永传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