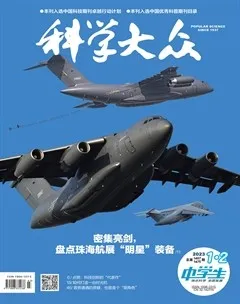用画笔连接科学与艺术
2023-02-03卞毓麟


“没有一幅画真能够发生效力的,要是不向无穷张一张眼,不向无限开些窗子。”读着罗方扬先生《诗意星空——画布上的天文学》中那些出色的作品,不禁再次想起前辈诗人卞之琳留下的这一警句。
无穷、无限,让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宇宙——天文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天文学是科学,油画是艺术。科学与艺术同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们共有的基本特质,就是具有高度的创造性。面对无穷的宇宙,《诗意星空》为读者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的窗子。
罗方扬是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还是一位热心的中小学天文科普辅导员。多年以前,他就是一名酷爱绘画、喜好文学的天文爱好者。他曾说过,起初致力星空美术,本是想通过绘画普及天文知识。《诗意星空》则已超越这一初衷,而达于美妙的升华。
《诗意星空》画册中,美术、中国诗词歌赋和天文元素三位一体。其题材大致有三:一是纯天文类的,如各种星云、星团、掠日彗星、中国空间站、南极望远镜等,算得上“硬核”;二是天文和诗词歌赋结合类的,如《寄声月姊》《观沧海》《黄河之水天上来》《静影沉璧》《滕王阁序》《春江花月夜》等,描绘传世名篇中涉及天文现象的特定情景;三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瑰宝——二十四节气,组成画册中的“二十四节气”部分。
综而观之,《诗意星空》是一本用油画材料通过中国画意境表现的画册,既具油画光影效果之魂,又得国画唯美意境之魄。罗方扬曾有言:“油画传入中国已将近200年,国人若一味唯西方传统技法或风格马首是瞻,则永难在画作质量上超越西方。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绘画风格,因此我采取国画意境加上天文、优秀诗词元素来画出自己的风格。”
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正是罗方扬艰辛探索、终获成功的原动力。科学和艺术浑然天成地融合在其画作中,李政道先生特地为此函允,同意《诗意星空》使用他本人在2011年为科普刊物《中国国家天文》的题词:“科学与艺术的重逢”。
《诗意星空》所载作品,原件尺幅有不小的跨度。尺寸最大的《寄声月姊》(380厘米x150厘米),曾获2017年无国界天文学家组织举办的全世界星空美术大赛一等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该奖项。
“寄声月姊”一词源出南宋张孝祥《水调歌头·金山观月》:“江山自雄丽,风露与高寒。寄声月姊,借我玉鉴此中看……”张孝祥是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廷试第一。曾上疏言岳飞之冤,触犯秦桧而下狱。其诗词多慷慨之气,有苏轼之风。鉴于《寄声月姊》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处谨从绘画和天文两个角度做一浅析。
就绘画角度而言,《寄声月姊》是带有国画风格的油画。国画为表现山石纹理和阴阳面,常在勾出轮廓后,再用淡干墨侧笔而擦,使之富有立体感,这就是所谓的皴法。皴法有多种,运用频繁者如有披麻皴、雨点皴、斧劈皴等。其中,披麻皴用笔线条较软,宛如披散开来的麻绳,适于画因多雨而草木俊秀的南方山石。《寄声月姊》全用披麻皴法,以表现南方山水秀丽,蕴张孝祥在镇江附近观赏江景之意。
再以天文角度视之。《寄声月姊》中一弯呈反“C”形的蛾眉月,是农历初四前后的月相,出现在日落不久的西方天空。画中最明亮处是天上众多的旋涡星系。星系乃是成百上千亿颗恒星组成的巨大集团,旋涡星系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星系,各有多寡不一的若干旋臂从中心部分往外伸展,故从正面观之呈旋涡状,并因此而得名。若侧视之,则大致呈梭状。我们身处的银河系就是一个旋涡星系。而仙女座星系是一个比银河系更大的旋涡星系,它们虽然相距200多万光年,但在星系世界中却属近邻。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这两个巨大的星系正在彼此逐渐靠近。据推测,数十亿年之后,它们将会合并成一个新的星系。《寄声月姊》所绘星系的旋臂互相缠连,似乎暗示了这一点。
科学和艺术的融合是个宏大的话题。
就科学而言,古人囿于技术手段和认识水平,无法看到太空中的星云和星系,也看不到大洋深处的缤纷多彩,更无法洞察微观世界的细胞乃至基本粒子。尽管这些科学客体和自然现象始终存在,古人却无法感知,当然也无从描绘。
就艺术而言,不管是亘古的宇宙、现代的航天还是海底世界、微观粒子,它們都很美,作为绘画题材,展示空间极其广阔。特别是表现力极为丰富的油画,不仅可以画人物、花鸟、山水风景,也完全可以画出科学的真与美。科学类题材,应该成为油画创作的新方向。
(本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
(责任编辑:郝雅文)
相关链接
罗方扬所著《诗意星空——画布上的天文学》荣获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银奖。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为该书再版作序,从绘画和天文视角对作者在科学和艺术融合方面的探索进行了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