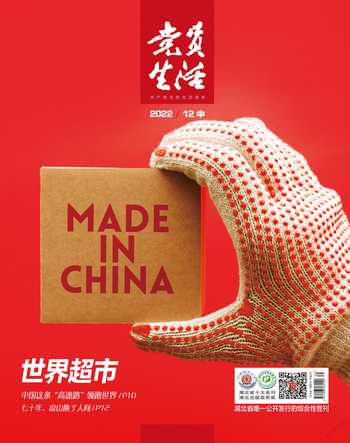辛亥革命究竟花了多少钱
2023-01-31齐风
齐风

孙中山领导的现代革命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每次密谋起义,都要先筹足款项,用以购买、运输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有人统计,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时17年,先后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所筹得的款项总额为112. 3余万港元。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革命债券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他一生也在为筹款而奋斗。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第8条之后,孙中山还加上了一句广告词,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有利可图多了,能够获得10倍的收益,机不可失。孙中山共从中筹到港币1.3万元。
1905年12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元,实收250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仅售出了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00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5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8万港元。总计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万港元。
华侨支撑的革命
买革命债券的多是海外华侨,义捐也多是海外华侨。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
很多华侨为了革命可以说是倾家荡产。1895年,为支持广州起义,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贱卖其牛犊,捐助4612美元。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虽然说华侨是为了革命而捐款,但他们没有投资的意思。1908年,孙中山劝说吉隆坡大侨商陆佑捐款,并许诺:如果陆能捐助革命,军政府“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的钱所占比例高达79%。其实当时国内的大商人都很有钱,据统计,武汉商会仅在1911年10月13日一次就向义军捐款500万两,重庆商会为四川境内的革命军筹饷有录可查的有40多万两,不过却没给孙中山多少资助。
金钱引起内讧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就曾因经费问题跟孙中山撕破脸皮,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前,接受日本政府送的5000日元和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1万日元,只留下2000日元给《民报》,其他的都带走用于他处,招致了章太炎等人不满。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因为黄兴等人顾全大局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1907年秋天,陶成章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没答应,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击孙中山。
面对内讧,孙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实地为革命捐款而破产的事实,痛心而又感慨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二人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据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
借助外人
为了革命的资本和武器,孙中山还曾與友邦承诺一些不甚具革命性的条款。1903年前后,孙中山抵达越南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指孙中山)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孙中山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全权。布思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以保证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17个月之内筹足350万元,分四期付给孙博士。”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文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执政期间,为了革命事业筹集经费而将苛捐杂税摊派到普通民众之上,曾引起群众的不满。
不妨这样说,债务曲线构成了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路线图。美国学者韦慕庭说:“在追求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然而,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理解孙中山”是一个还要继续进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