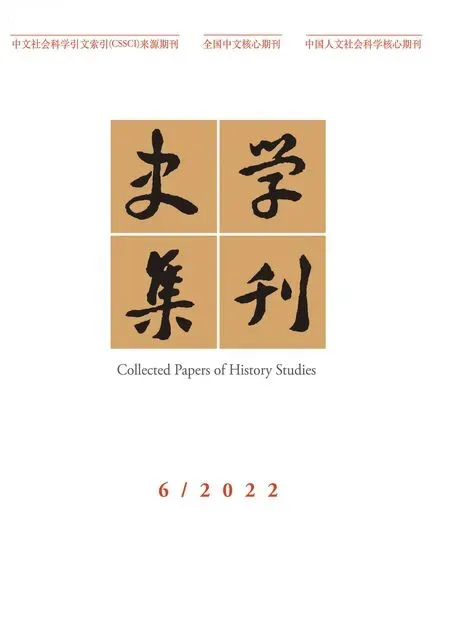19世纪初期的留德学生与美国文化独立的先声
2023-01-26高岳
高 岳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19世纪初期的美国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宪法为蓝本的共和制国家,但当时的美国工业化进程尚处起步阶段,而且由于缺乏历史传统,文化建设尤其薄弱,在世界舞台上仍然默默无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有识之士即认识到知识的传播对共和国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倡导公众教育的推广,吸收和借鉴欧洲的文化和思想。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即承袭英国的建制、文化和习俗。建国初期,美国人的热情集中于对国家建制的讨论,热衷于写宣传小册子,却疏于文化的建构。尽管有康涅狄格州的作家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但其主题却与美国本土的环境、生活和文化相去甚远,在风格上也具有浓厚的英国小说的特征。美国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曾在《纽约外史》中描绘了最早定居于纽约的荷兰移民,作家詹姆斯·F.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1821年开创了完全属于美国的题材,但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他熟悉的纽约州的韦斯切斯特地区。(1)[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许季鸿等译:《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40页。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美国的史学作品也具有浓厚的区域特征,大多是城镇、州或地区的编年史。本杰明·特朗布尔(Benjamin Trumbull)的《美国通史》(2)Benjamin Trumbull,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rom the Discovery in 1492,to 1792,or,Sketches of the Divine Agency,in their Settlement,Growth,and Protection,and especially in the late Memorable Revolution,Boston: Farrand,Mallory,1810.和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3)David Ramsay,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 volumes,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789.打破了地方史学和保守观念的限制,开始尝试把美利坚看作一个完整的国家来书写其历史。但是,二者都没有通过追溯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历程来探讨美利坚的民族特性。
进入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追寻民族特性,进而建立民族文化成为很多知识精英的共识。尤其在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发展民族文化以对抗英帝国殖民者的呼声更加强烈和急迫。19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德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对美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美国也正是在选择性和创造性地借鉴与吸收德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创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到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则成为德国文化输入美国的重要媒介,他们对德国文化有选择地吸收,率先发出了美国文化独立的呼声。
对第一代德国留学生的研究可见于19世纪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之关联性的著作中,教育家查尔斯·特温(Charles F.Thwing)在《美国和德国大学:百年历史》一书中介绍了在19世纪的百年间美国青年到德国接受教育的状况、移居美国的德裔学者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以及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教学方法的借鉴,其中第一章大致展示了第一代美国留学生在德国的学习生涯。(4)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学者卡尔·迪尔(Carl Diehl)在其著作中以两章篇幅大致介绍了19世纪早期到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的总体状况,包括他们对德国大学的适应过程,以及对德国文化的了解和评价,作者认为第一代留德学生并未认识到德国学术的真谛。(5)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学者奥里·W.朗(Orie William Long)关注19世纪早期到德国留学的六位美国学者,简要介绍了其生平、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和对知识传播与推动学术发展的贡献,也涉及这几位美国学者对德国文化的感受。(6)Orie William Long,Literary Pioneers: Early American Explorers of European Cul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上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美国留学生在德国大学的学习状况,以及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体制变化的影响,但留德学生如何在回到美国后引介德国文化,从而塑造美国文化并推动了美国的文化独立,仍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转移史(transfer history)的视角(7)转移史考察基于文化媒介关联起来的两个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国家、区域、市镇、机构等)的相互关系。文化媒介指书商、出版商、大学、留学生等对技术、思想、观念等的传播和转移起到重要影响的因素。转移史亦关注某一民族文化内部的现象在传播到不同的文化之后引发的相似或不同的结果。转移史是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尝试,是跨国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对转移史的讨论,详见Heinz-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Comparative History: Methods,Aims,Problems,” ed.by Deborah Cohen,Maura O’Connor,Comparison and History: Europ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4,pp.31-37.来考察美国以留德学生为媒介,在建立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和吸收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以及如何与本土环境和现实相结合来塑造美利坚民族文化的特性。
一、美国青年留学哥廷根的缘由及其对德国大学的评价
19世纪,很多美国青年学人选择德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在当时的欧洲,随着法国大革命转向拿破仑专制,法国走向帝国的趋势开始与美国的共和主义观念格格不入。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人眼中,法国人被视为“不信教者”,其松懈的道德感也倍受美国人憎恶。有些美国人认为,法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会使人道德堕落。美国青年在法国仅能领会到智识生活的意义和艺术鉴赏的品位,而这些被美国人视为皮毛之物,真正的学识还是要凭借德国大学严格不懈的训练来获得。当时英国的大学也很有吸引力,然而英国的科学研究却在大学之外繁荣发展。一些兼备才智和财富的个人进行独立研究,远离社会和政治生活,且不关心国家事务,对推动英国的高等教育收效甚微。英国大学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教学方式并不适合美国学生,因为后者把大学教育作为未来职业的铺垫。而且直到1871年之前,进入牛津、剑桥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签署安立甘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8)三十九条信纲是新教安立甘宗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清教徒认为英国国教会对天主教的改革并不彻底,希望净化英国教会,因此遭到英国当局的迫害。为了进一步改革新教,清教徒在17世纪移居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传统深厚,因此美国学生无法接受签署三十九条信纲。这个要求也是阻碍美国学生进入英国大学的原因之一。(9)Charles F.Thwing,The American and German University: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p.76.基于上述原因,在19世纪里,大部分美国学生选择德国作为海外留学目的地。
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学生不断奔赴德国留学。据粗略统计,1815—1914年大约有9000~10 000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进行专业化的学习。(10)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49.1810—1840年间在德国大学注册的55名美国学生,在哥廷根学习者为25名,人数远超在柏林、海德堡及其他地方的学习者。(11)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p.55.哥廷根大学是当时德国大学的翘楚,其地位可与柏林大学匹敌。哥廷根大学建于乔治二世时期,主要由汉诺威王朝枢密院大臣闵希豪生(Baron Münchausen)一手操办,其本人也是启蒙精神的拥护者。另一位发起人是语言学领域杰出的学者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他拥有经世致用的智慧,是管理哥廷根大学的灵魂人物,其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子。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浪潮中,哥廷根大学不断得到发展,经过19世纪初期的改革之后,其学术声誉进一步提升,尤其在语言学、文献学和哲学等领域,在欧洲居于引领地位。哥廷根大学的语言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诠释文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发展为批判式思维方法,并应用到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德国语言学家艾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和历史学家希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萨尔费尔德(Friedrich Jakob Christoph Saalfeld)继续将这种治学传统发扬光大。
美国的知识精英与哥廷根大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66年,是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哥廷根参加皇家科学协会的会议,由此美国学者首次与哥廷根大学建立联系。从1795年到1812年,汉堡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埃贝林(Christoph Daniel Ebeling)与在波士顿北部萨勒姆镇的威廉·本特利(William Bentley)一直保持通信联络,(12)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pp.14-15.这使得哥廷根大学在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得以被新英格兰的学者所闻知,推动了美国学生留学哥廷根。1815年8月,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和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一同从波士顿启程到达了位于德国汉弗莱的小城哥廷根。两年后,以出色的表现从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毕业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得到学校的资助,赴哥廷根留学。此三人成为赴哥廷根大学留学的首批美国学生。
这三位青年均在享誉欧洲的哥廷根大学语言学系学习,研读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文献,同时修习现代欧洲语言。初到哥廷根,蒂克纳即被其现代大学的自由风尚和丰富的图书资源所吸引,求知欲得到了极大满足,弥补了之前的知识短板。他认为,阅读是智识增长的基础。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拥有大约200 000册图书,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尤其丰富,学生可以自由借阅,这与哈佛学院的图书馆形成了鲜明对比。(13)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Boston: James R.Osgood and Company,1878,p.72.
在两年多的学习过程中,蒂克纳被哥廷根大学学者们严谨的学风和深厚的造诣所折服。1815年11月10日,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古希腊语老师舒尔策博士(Dr.Schultze):“每天我都被其讲授内容的多样性和准确性所震撼。他准备充分,探讨问题细致入微。在其令人羡慕的成就下,我每天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才是希腊语学者,如何才能造就希腊语学者。舒尔策只比我年长几岁,我无法想象,多少时间的投入,或者怎样不可企及的天赋才能令他对已经被遗忘的语言如此精通。”(14)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3.
蒂克纳对哥廷根大学老师们的教学热忱和精湛的教学艺术赞不绝口。在有关福音书的课程中,蒂克纳评论道,艾希霍恩对福音中的一些疑难内容阐释清晰,他审慎严谨的态度,雄辩的口才,在诠释福音书时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对真理深沉的热爱,对于学生极富感染力。(15)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9.1815年11月,蒂克纳开始重拾拉丁语学习。在美国时,蒂克纳认为拉丁语很难习得,现在却进步很快,在他看来,这得益于“舒尔策投身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擅长教学,具有牺牲精神,美国没有这样的学者”。(16)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p.79-81.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对其讲授的自然史极其精通和熟练,具有令人愉悦的幽默感,并与其讲授的重要内容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令人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由此,蒂克纳体会到美国大学和德国大学在教学方法上的重大差异。在哈佛学院时,老师讲授有限的知识,学生机械刻板地背诵。在哥廷根大学,他意识到靠记忆获取知识和被引导进行研究的区别。他在信中提到,教希腊语的学者不仅精通希腊语,而且懂得如何去教授希腊语。(17)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72.
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哈佛学院对班克罗夫特的期望,班氏最初立志要成为一名牧师或从事圣经和神学方面的研究,因此他在哥廷根大学苦读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古代叙利亚语、拉丁文等古代语言,以期将来能够从语言学的角度批判地研究神学。(18)M.A.DeWolfe Howe,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Bancroft,Vol.I,New York : C.Scribner’s Sons,1908,pp.49-54,79.哥廷根的学者们对于古文献的研究却使其兴趣发生了转变。班克罗夫特十分钦羡哥廷根大学的学者们对于古物研究和古文献整理的热情。“当你看到一位饱学之士如何鉴赏古物,甚至视其为挚友与其进行精神交流时,那是十分美妙的情境。他能够听到来自遥远过去的微弱声音,当德国学者将其严谨、准确的技艺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结合之后,历史中最隐秘的部分竟然呈现于眼前。当你看到每一份收集到的手稿,每一种著作,无论是沉闷或是有趣,无论是富有天才或是缺乏创见,经过悉心审阅之后,它们显现出其价值;当你发现无论多么渺小的硬币和徽章、艺术的残迹和大自然的废墟都承载着可供研究的题目,你内心的欣喜之情不免油然而生”。(19)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72.
班克罗夫特发现,德国的学者把学术研究作为终身热爱的事业,专注于此以求达于至臻。他们热衷于智识生活,虽然与世俗财富无缘,却投入其中并体味它的甘甜。海涅甚至用18年的时间去阐释荷马的一首诗,其影响深远,引发了德国学者对神话学的讨论,由此也为他赢得了学术声誉。(20)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855,pp.152-153,158.
三位美国青年在哥廷根大学的留学生涯,不仅使他们开拓了视野,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训练,而且也令其亲身体验到德国大学的自由氛围,表现为选修课制度对于学生个性的尊重和潜能的发掘,以及教师们的教学热忱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尤其令三位美国青年印象深刻的是,优秀的专业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投入使学生把专业研究作为一项事业。上述所见所闻,使这三人在回到美国后,期望以德国大学的体制和文化振兴的模式为参照系,推动美国传统学院的变革,培养知识精英,引领知识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独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学者对于德国文化并不是照搬全收,而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有选择地借鉴吸收。
二、美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实践
埃弗里特、蒂克纳和班克罗夫特先后获得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皆受聘于哈佛学院担任教职。在哈佛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体验到美国大学与德国大学的显著差距。哥廷根大学已经具有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专业设置分明,学生按照自己的选择接受专业训练,聘请具有研究专长和丰富成果的学者担任教职,虽然由政府出资建立和维系大学的运营,但大学的管理权却掌握在教授之手。
19世纪初期的哈佛学院则仍然停留在传统式的学院教学的窠臼中。学生入学后并不划分专业,而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修读拉丁语、希腊语、逻辑学、语法、修辞,数学、几何、自然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动物学和天文学,以上是必修的基础课,高年级学生则主要学习情感和道德哲学。通常由一位资深牧师担任教师,讲课内容完全随教师的心意,但目的是使学生铭记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道德目标。(21)George P.Schmidt,The Liberal Arts College,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pp.45-47;R.Freeman Butts,The College Charts: Its Course,New York,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1939,pp.116-155;转引自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p.25.由于当时的教师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同时抱守相对陈腐的教学理念,通常的授课模式是老师讲授有限的知识和内容,学生机械地接受和背诵。对于陈旧的教学内容,教师缺乏适度的热情,学生也只是为了达到考试要求而被动吸收。
1819年,埃弗里特继续其在1815年毕业后即被哈佛学院授予的希腊文学教职,蒂克纳则被授予法语和西班牙语、经典文学(Belles Lettres)教职。蒂克纳认为,哈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仅相当于德国高中的标准。因此,他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埃弗里特亦是哈佛大学改革的倡议者和践行者,他向学校倡导应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所学科目,对学生进行不同领域的专门训练,强调划分专业的必要性。
传统的教学方法尤其需要革新。蒂克纳强调教学过程中严谨的精神和详尽的阐释是十分重要的。“相比于是否缩短假期时间,或者增加上课时间,认真教学的原则尤其重要,不应被忽视”。(22)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2.他认为教师的治学精神和思维方式应随着讲授的内容传达给学生,使其能够真正领悟掌握知识的方法。美国的大学投入资金多于欧陆大学,却没有一名好的希腊语学者,没有人在毕业后精通拉丁语,学院教育也没有为学生开启去从事某个领域专门研究的大门。很少有教师能够传授给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鼓励其勤勉的精神,通过适当的奖惩来推动其学业进步。“如果采取了以上措施,那么(大学)则实现了其职责,对公众大有裨益”。(23)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3.
1821年时,有人意识到哈佛学风不严谨,年轻人耽于享乐。蒂克纳对于学生的选拔和管理提出动议:入学考试和学年考试应更加严格,不合格的学生将不能毕业,学科设置应更准确,授课应更严谨,纠正学生中存在的堕落风气,以此来赢得公众的信任。(24)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59.在蒂克纳的建议下,哈佛学院开始实行选修课制度。改革措施在蒂克纳所在的现代语言系取得了进展。学生根据专长选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大部分学生能够选择他们乐于从事的专业。针对学生在入学时知识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蒂克纳提出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程度来分班,这样有利于学生学习进步,体现公平原则。(25)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p.366-367.现代语言系的管理也不同于其他系,由教授进行直接管理。
蒂克纳提出的认真教学的改革主张在哈佛并未被广泛接受,除了埃弗里特践行了其倡议,其他教师皆表示反对,分歧源于对于大学的功能和培养目标的不同认识。19世纪初期的哈佛学院,仍然沿袭了殖民地时期仿效英国大学创建的传统学院模式,很多教职由牧师来担任,期望通过基督教的训诫使学习者承担公民责任,实现公共利益,课程设置不面向任何一种职业培养,具有比较强烈的宗教色彩。而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们秉持着学术自由的精神,奉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这种以“研究为信仰”的观念在当时的美国大学看来却如异端邪说。
哈佛学院的很多教师并未接受过现代的专业训练,教学理念也比较陈旧。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埃弗里特和蒂克纳,接受了相对专业的学术训练,已经具备将专业研究作为职业选择的意识,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现代式认知开始扭转新英格兰学子们对于文学的传统看法。对于19世纪初期的清教徒来说,阅读文学作品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清教倡导遵循教义宣讲的美德,渗透到清教徒的生活中则表现为勤奋工作、节俭克己、减少休闲娱乐。因此,文学只是一种不被看重的休闲方式。蒂克纳则怀着极大的热情,认真又翔实地讲授法国和西班牙文学史,引导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有些学生开始意识到文学并非仅仅为了消遣,而是一项可以投入的终身事业,甚至为之放弃有利可图的工作。(26)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24.
虽然蒂克纳的改革动议和举措在哈佛学院一时没能广泛展开,但其有关现代大学的观念获得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蒂克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高等教育应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传统的习俗和体制已经不适宜加速发展的时代,时代呼唤秉承自由精神的大学,如果仍然止步不前,则会被时代所抛弃。”这篇文章被全国各地的多家报纸转载,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一些在宗教观念上与蒂克纳有分歧的教派,也对其有关大学的观念表示赞同。(27)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364.
在德国学成归国后,班克罗夫特和约瑟夫·G.考格斯威尔(Joseph G.Cogswell)(28)考格斯威尔是班克罗夫特的学长,180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也曾在欧洲留学。决定以德国大学预科学校(gymnasium)为范本,在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的圆山(Round Hill)建立一所大学预备校。圆山学校在一段时期内运行得比较成功,甚至从佐治亚州到缅因州的很多父母也慕名送自己的男孩子到这所学校就读。(29)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New York: Alfred A.Knopf,1944,p.73.班氏认为,教育对民主制度至关重要,其目标是为公民带来履行职责的道义和勇气。教育能够培养国家需要的领袖,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30)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p.77.
这三位美国青年受到德国大学教育的熏陶,回到美国后致力于推动哈佛学院向现代大学的变革,把追求知识和真理融入职业目标中,使大学生涯成为学术研究和职业培养的结合体,并使在本土接受教育的美国学者习得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机构,在班克罗夫特看来,知识分子有责任投身于公众事业,激发思想,塑造大众的道德观,培养社区自由和自治精神。(31)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111.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构建的引领者,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为美国的文化独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对德意志文化的吸收与对美国文化独立的倡导
蒂克纳、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在德国接受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训练,打开了知识的眼界,他们认识到,对于文学等学科的专门研究不仅可以作为通向未来职业的途径,亦可成为终身投入的学术事业。哥廷根大学被其视为知识的殿堂,迎合了他们最初的期望。提升自我虽然是三位青年学人的初衷,但在个人价值实现的背后还有美国文化独立这个更宏大目标的支撑。这既是受到他们在德国所见所闻的启迪,亦与其在哥廷根大学受到的教育相关,同时植根于美国的社会现实。
19世纪初,德意志在法国的占领下沉沦,普鲁士率先觉醒,为社会底层赋予更多的自由。政府建立学校,尤其是在柏林、哥廷根等地建立大学,带动了知识和自由精神在德国的传播,振作了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学者形成了独立的阶层,德国北部出现了学术共同体,最初仅存在于萨克森、普鲁士、汉诺威等地,随着拥有新教观念和哲学思想的自由主义大学的发展,其影响不断扩大。蒂克纳在给其家乡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普鲁士政府创办大学,解放精神,通过知识的传播开启民智。(32)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100.班克罗夫特也曾撰写文章介绍德国的文学、语言学、天文学、动物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状况。他以每门学问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核心,在概览其生平中展现其学术旨趣,从其人生中具有影响力和戏剧性的事件入手去言说典型人物的人生选择,尤其赞赏其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引领公众精神世界的提升,带动道德的净化。(33)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03-205.
三位青年在德国亲身体验到德国学者如何开启大众的知识视野,引领社会品位的提升,从而振兴了德意志的文化,以及对知识的信仰和文化的传播如何突破了地区的限制。蒂克纳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当某个普通德国人讲到其自身的归属,他会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黑森人,这种排他的、强烈的爱国情感不输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当问及一位学者,他会把自己与整个德意志联系起来,在受到新教观念和哲学观念影响的地方尤为如此。当提及驱逐一个汉诺威人或普鲁士人,使其被迫放弃‘国籍’,一个普通德意志人会非常恐惧。但对于德意志学者来说,从柏林到哈雷(Halle),都会有宾至如归之感”。(34)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Ninth edition,p.101.
19世纪初期的德意志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普通德意志人具有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却缺乏德意志人的身份认同。德意志学者在知识传播和学术追求中体现的自由精神使其超越了地区或者公国的桎梏,形成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德意志精神,从而引领了德意志在精神上的统一。三位美国青年亲身体会到文化发展给德意志带来的变化,他们意识到无论是古代经典,还是近现代的文学,都有助于公众文化的提升和道德感的净化,这对于美国这个新生共和国的维系是十分重要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区域差异仍然十分显著,缺乏凝聚力,因缺少历史传统带来的民族身份的迷茫是年轻的美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应该建构美国自身的民族属性,而民族文化的建立则是一条必经之路。
埃弗里特认为应当借鉴德国对古典文本的研究来塑造美国的民族文学。他在1817年时不无忧虑地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约翰·桑顿·柯克兰(John Thornton Kirkland):“难道我们不需要科学吗?不需要文学吗?……不需要以文化为这个民族奠定基调,为这个国家建立公共品味,并使我们的子孙引以为傲吗?难道我们只追求没有文化的腓尼基人式的商业繁荣……难道我们会以新英格兰咸牛肉闻名欧洲而自豪吗?”(35)Everett to Kirkland,19 April,1817,MHSE,in 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 1770-1870,p.175,Note 60.
在《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班克罗夫特谈到了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研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美国人应该在古典的自由原则中发现乐趣和教益,这也是为这个民族带来兴盛和荣耀的途径。”班氏认为,美国人应该以古代经典为武器,来对抗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及其文学和品味。“经典研究应被视为通向民族文化独立的路径”。经典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抗美国人自身过于偏好实用性的解药,以此来建构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在当前时期,我们的民族特性正在快速发展中,可适时引入新的元素,我们要鼓励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这样能够唤醒公众对艺术的珍爱之情,社会风尚亦会随之变得文雅。”班氏进一步论证古典研究的必要性:“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不应为探究问题设限,人类每个阶段的状态都值得了解。古典文学研究是最好的研究。”(36)George Bancroft,“The Utility of Classical Learn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9(July 1824),p.125.
班克罗夫特还提出了具体的举措,比如,美国应资助大学的发展,建立图书馆,为具有才干的青年提供奖学金,提升教育水平,引导大众对文学的热爱和良好的品味,只有建立起本土文学,才能维持共和精神的纯洁和力量。美国的文学应建立在经典研究的基础上,因为古代共和国为现代共和国提供了丰富的遗产,可供借鉴。班氏很有气势地预言:“在古希腊的碑铭之前,美国的文学天才将会点亮自己的火炬。”(37)Russel B.Nye,George Bancroft: Brahmin Rebel,p.78.班氏的想法与杰斐逊不谋而合,后者也正希望通过建立弗吉尼亚大学,发展古典语言学,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建立。
德国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严谨和热忱影响了埃弗里特、蒂克纳和班克罗夫特,使他们意识到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究对维系自由精神的必要性,以及对于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只有推动文化的传播,拓展公众的知识视野,培养公众的文化品位,才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创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应该承担引领者的重要职责。
班克罗夫特在其文章中赞扬德国学者致力于研究学问,虽然与社会疏离,却在智识世界中探究知识,通过自身对真理的探寻带动大众精神的提升。班氏肯定德国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影响,认为其作品激励了民族精神,并赞赏著名作家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作品中的道德论调,认为二者都是复兴德国文化的重要引领者。(38)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58,150.班氏进一步提出美国的民族文化应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为己所用。“我们并未诞生民族文学,但已经曙光微现,美国文学的发展应借鉴根植于自由的政治制度,去除偏见和狭隘,去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精华”。(39)George Bancroft,“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23-124.蒂克纳也有感于文学研究对于精神世界提升的价值,提出“我迫切地希望从精神世界的需求出发进行文学研究,而不是把文学研究视为单调沉闷的工作,这种追求应该被移植到美国,在自由的氛围中,文学研究会即刻得到滋养”。(40)O.W.Long,Thomas Jefferson and George Ticknor: A Chapter in American Scholarship,Williamstown: The McClelland Press,1933,p.19.
埃弗里特、蒂克纳和班克罗夫特不仅发出了建立民族文化的呼吁,而且付诸行动,他们希望引介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作品,带动美国公众对文学的兴趣,提升公众的阅读水准和文化素养。19世纪初期,新英格兰出现的一些文学期刊即诞生于这样的氛围中,创办于1815年的《北美评论》是引介欧洲尤其是德国文学和哲学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埃弗里特于1819—1825年间担任《北美评论》的编辑。班克罗夫特、蒂克纳和埃弗里特在内的新英格兰知识精英翻译德国的诗歌、戏剧、小说和哲学作品,此类作品大量发表在《北美评论》上。同时,对德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也会撰写文章,评论德国的文学和哲学,发表自己的观点。莱辛、席勒、歌德、费希特等德国学者的作品及其思想是《北美评论》探讨的重要主题。(41)William Cushing,Index to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s.L-XCCV,Cambridge: 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1878.
18世纪末期,只有英国舶来的文化产品才被美国视为优秀作品,美国人对于本土文学作品通常投以怀疑的目光,出版机构也不鼓励本地人写作。直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版商才愿意冒险出版本土作品并付给作者版税。到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逐渐形成了有文学品位的阅读群体,对专业性比较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知识的需求不断提升。当受过一定教育的阅读群体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后,他们对欧洲大陆文化的好奇心不断增强。如此,欧洲中世纪以及现代的历史和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以满足大众的需求。(42)Carl Diehl,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p.114.不断扩大的文学消费市场不仅带动了吸收德国文化的土壤产生,也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发展,研究欧洲文学的专业人士增加,品位不断提升的文化市场与人文学科的专业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上述留德美国学生认识到在德国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民族的传统紧密相连。蒂克纳在给友人的信中阐释了德国文学的特性:“德国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直接源于其自身土壤,与其民族特性紧密相连,外国人则不太容易理解。”(43)Edited by G.S.Hillard,etc.,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Vol.1,p.119.班克罗夫特在其文章中讲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收集和整理中世纪时期流传于德意志民间的歌谣,通过语言学的考证,发现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44)George Bancroft,“Writings of Herder,”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20(Jan.1825),p.138.他们意识到民族文化源于其历史和传统,而正是由于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每个民族的文化亦具有自身的特质。美国却是一个没有古代历史可以承接的现代国家,如果要建设自身的民族文化,需要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构建美利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认同。19世纪早期,以德国文化为同盟来对抗英国的影响是美国知识精英一种潜在的渴望。(45)Kurt Mueller-Vollmer,“German-American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Jacksonian Era: Six Unpublished Letters by Francis Lieber and John Pickering to Wilhelm von Humboldt,” Teaching German,Vol.31,No.1(Spring 1998),p.2.
德国的历史哲学到19世纪已经趋于成熟,发展出自成体系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德国学者对于民族精神的追寻带动了整理古籍、史料的热情,推动了对德国历史的研究。在德国历史观念的熏陶中,波士顿的精英们开始探讨历史研究的价值,最终确定历史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美国历史是十分值得书写的主题。(46)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2,No.1(Jan.-Mar.1971),pp.138-139.赫尔德的历史观念对美国历史的撰写具有很大的影响。赫尔德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每一种完美性都是民族的、世俗的”,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种族遗传和心理特质,由此各个民族具有独特的内在精神,这种个体性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民族之间存在基本的价值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呼吁德意志传承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47)M.D.Learned,“Herder and America,”German American Annals,September,1904,pp.531-570.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使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认识到,美利坚作为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精神,珍视共同的历史传统,而这种传统则需要在历史中追溯。班克罗夫特敏锐地发现,美利坚民族的特性需要在其历史中界定,在其后来享誉大西洋两岸的《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史》中,班克罗夫特通过对殖民地历程、独立战争和立宪过程的宏大叙事,揭示了美利坚民族的源起、特性和使命等重要主题,在其著作中向读者展示了如下观念:条顿的自由精神是美利坚追求自由的特性之源头。(48)高岳:《浪漫主义史学与19世纪中期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构建》,《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1页。
班氏一方面从欧洲来追溯美利坚民族特性——自由精神的源头,但他同时也注意到,美利坚的民族性格植根于北美大陆的土壤,从自由精神中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在北美的环境中孕育出的结果。因此,他在对美国历史的书写中融合了赫尔德的人道观念,并把这种观念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联系起来。赫尔德作为早期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提出了“人道理想”的观念。“人道理想”向人们指出,所有人都存在着一种萌芽式的共同人性、高贵和尊严。(49)[美]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人道理想”也同样适用于具有个性特点的民族。在1825年,班氏曾发表文章评论赫尔德对于人道(humanity)的界定:“人道是人类天性中最优秀的禀赋:美好的情感、慷慨的天性、秉承高尚的原则……这是赫尔德最热爱的主题,他相信人类会越来越符合人道的原则。”(50)George Bancroft,“Writings of Herder,”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20(Jan.1825),p.444.班氏把这种对人道的热情融入美国历史的撰写中。班氏相信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变革和前进的重要力量。美国革命的爆发是人民大众的意愿,反映着时代的精神。(51)George Bancroft,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The Author’s Last Revision,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1890,IV,pp.160,185; 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55, pp.415-417.他坚信美国自身的经历符合道德判断的标准,并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而这是一个不会停顿和不可逆转的过程,美国由此会成为文明世界的典范。在讲到民主制度时,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性被凸显出来。班氏正是在对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呼应中,挖掘了美利坚精神的独特性。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快速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对民主实验的乐观愿景,人们对美利坚民族文化的自信也随之而起。学者帕尔弗里(John G.Palfrey)指出,美国历史是值得研究的主题,他甚至认为新英格兰的古迹与古希腊、罗马的遗迹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52)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2,No.1(Jan.-Mar.1971),p.136.
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席卷欧洲并传播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德国的美国青年正是把上述思潮引入国内的重要媒介之一。德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因此,虽然德美两国的学者同样受到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感召来建设民族文化,但发展路径和引发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从转移史视角可做如下分析。
19世纪初期,德、美知识阶层面临着相似的形势:德意志人分散在几百个邦国中,以所在的邦国来确认自身的身份,崇尚地方主义的传统仍在延续;(53)[英]以赛亚·柏林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美国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并未产生一种统一的文化来整合这个新国家。与此同时,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发掘一致的精神来凝聚人心,振兴民族文化成为时代的召唤。德、美均凭借文化民族主义打破了地方主义,德意志构建了跨越地区的文化认同;美国则突破了新英格兰的狭隘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欧洲乃至世界。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传统的发掘和探寻过去的重要动力来自巩固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德、美两国均如此。德意志知识界要发展民族文化,就要抗拒柏林宫廷的崇法力量,正是在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威压和霍亨索伦王室专权的抵制中,推动了自由精神的生长。美国社会则在西进运动和社会改革相融合的过程中,孕育了对普通人的潜力持有乐观信念的时代精神。此时的美国人正在为新国家的建设而踌躇满志,展现的是乐观向上的氛围,而且共和民主制度正是其与欧洲具有鲜明差异的特质。所以,美国学者把德意志的哲学观念与其民主特性结合起来,塑造自身的民族性格。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知识精英借鉴德国的高雅文化并将其与美式的民主政治相结合。
美国学者对德意志文学作品中的观念并不完全认同,而且有选择地借鉴。虽然歌德的文学禀赋得到留德学生的肯定,但歌德被评价为“不忠诚于情感和上帝”,“忽视道德感”。正如班克罗夫特在一篇评论中所言:“因为歌德不仅描述温柔的情感和真正的人性,还常常涉及由想象引发的哀伤和文雅衍生的罪恶。在美国,歌德的作品被视为对人性危险的诽谤而被搁置一旁……歌德代表了没落的贵族阶层,缺乏民族情感,他在道德上是不及伏尔泰的。”(54)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95-200.相反,席勒则是被美国学者高度肯定的作家,不仅因为其作品中展示了文学天才,而且具有道德感,并体现了爱国情感。19世纪初期,清教伦理在美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教导信徒要保持对上帝的虔诚,为了获得拯救而勤奋工作,节俭克己,为社区和教会做出贡献。清教徒无法接受德国文学的感伤主义和人性的复杂之美,因为这是违背清教伦理的,因而是不道德的。多愁善感和对人性消极面的剖析并不符合当时美国人的口味。对于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人来讲,沉浸于个人的内心于社会发展毫无用处。
在19世纪上半叶,宗教自由之风席卷了新英格兰,唯一神教逐渐摆脱了加尔文主义教条的影响,倡导不局限于教义忠诚,信任个体的理性和判断。尽管如此,一些德国学者对《圣经》的批判和在宗教上彻底的怀疑主义态度,仍然无法被美国社会接受。美国学者把康德看作无神论者,摧毁了宗教的本质。(55)Richard Arthur Firda,“Germ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15-1860,”p.140.德国学者艾希霍恩以怀疑主义精神对《圣经》进行解释,令班氏觉得他缺乏严肃的宗教观和道德情感。(56)Orie William Long,Literary Pioneers: Early American Explorers of European Culture,pp.120-121.“直到19世纪末,德国的神学观才逐渐被美国人所接受,其批判主义不再被视为对美国宗教的威胁”。(57)Jurgen Herbst,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pp.7-8.
班克罗夫特在对德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中,热情地赞颂赫尔德,不仅仅是由于其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贡献,而且因为赫尔德的作品“提高了国家的声誉,改善了整个国家的品位。很少有人像赫尔德一样多才多艺且具有道德感”。(58)George Bancroft,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iscellanies,pp.167-168.赫尔德提出,每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具有独特性,却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它是强调价值平等和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的民族观提出的假设是:促进人类精神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之间存在基本的价值平等。美国知识界正在探寻文化独立之路,赫尔德提出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平等的历史哲学为其构建美利坚特性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使美国学者意识到,民族特性的源头要到历史中去追溯。在对美国历史的书写中,班克罗夫特挖掘了美利坚民族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的源头,并结合人道的观念,凸显了美国民主试验的进步性,从而塑造了美利坚的民族特性。在第一代留德学生看来,美利坚的民族特性在于美洲大陆独特环境孕育出来的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进而衍生出美国超越欧洲的决心,美国的“优越性”也由此而生。
结 语
蒂克纳、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对于德国大学学术自由风气的引入、对哈佛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给当时美国陈旧和僵化的学院体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看重大学对于精英的培养,从而引领公众提升精神世界,熏陶公众善于思考、热忱于公共事务的品质,进而培养社区自由和自治的精神。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研究,则可以借鉴古代共和国得失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有利于美国的成长。19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英格兰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于实用主义倾向过强的美国社会,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经典作品的传播正是陶冶情操,安抚心灵的良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希望在文化上脱离英国的殖民,思想独立即是民族的当务之急”。因为,“一个民族不仅由领土、军事力量、政治或者经济来界定,而且由民族独一无二的属性来界定……并通过其文化和文学作品来展示”。(59)Michael T.Bernath,Confederate Minds: 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in the Civil War South,Civil War America series,ed.by Gary W.Gallagher,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0,pp.27,31.以蒂克纳、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第一代留德学生,受到德意志民族复兴经历的启发,结合美国社会的现实,希望通过对德国文学、哲学等作品和理论的引介与传播,提升美国人的文化素养,净化社会良性发展所需的公共道德,构建自身的民族文化,从而推动新生的共和国不断向前发展。他们借鉴了德国有关民族文化的理论,在对美国建国历程的追溯中发掘出美利坚特性,进而发出了美国文化独立的先声。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上述留德美国学生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并付诸实践,但其影响力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历史传统的年轻国家,文化独立的最终实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蒂克纳、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的倡导启发了新一代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为民族文化的独立铺垫了道路。1837年,爱默生在波士顿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的演讲中,指出了美国学者应具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孕育于北美的环境中,是欧洲学者所不具备的。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羹来获得营养”。(60)[美]爱默生著,孙宜学译:《美国的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此演说被很多知识精英认为是美国“思想的独立宣言”。爱默生在青年时期即受到蒂克纳、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的启迪。19世纪中期,以美国社会为主题,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梭罗的散文、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小说、惠特曼的诗歌等“灯塔的光芒”亦给人们以信心:文学并没有迷失在民主的黑夜中。(61)[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许季鸿等译:《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39页。上述文学作品正是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彰显,推动了美国精神的塑造,助推了美国的文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