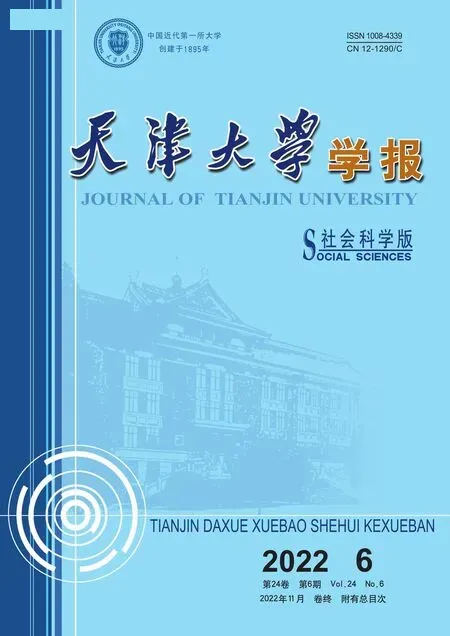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版本流变与选择
2023-01-25韩诚
韩 诚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天津 300387)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樊骏曾提出文学史料工作不是“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而是“在整个文学研究事业中占有不容忽略、无法替代的位置”,其难点和重点在于“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1]。随着近40年来的文学研究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础的文学史料内容不断丰富,特别是与现代文学相关的期刊、图书电子数据库的建成,为文学史料的检索、利用提供了便利。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到作家、编辑、出版社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版本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多数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初版本和最终修订本,而对其间的过程版本研究不足,尤其缺少展现作品版本流变的汇校本,使版本研究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短板,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一、 版本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多样性
中国现代文学虽发展时间较短,但其版本的复杂性并不亚于古代文学,有些作品一经发表不再修改,但也有不少作品包含了初刊本、初版本、最终修订本和多个过程版本。严家炎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对比,认为古代文学作品是在传抄刻印过程中出现异文,而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变化主要来自作家的修改[2]。现代印刷业的发展,使传抄刻印的疏漏减少,但不少作家则勤于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不同版本间产生了大量的异文内容。对于内容的变化,有些作家会在版本说明、前言或后记中提及,但也有不少修改缺少必要的注释和说明,需要研究者进行版本比较才能发现。
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式与古代文学作品不同,作品在正式结集出版前通常会先在报刊上刊登,形成最初的刊本,即初刊本,这是最能体现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据统计,自1872年《申报》创办我国第一种文学期刊《瀛寰琐纪》起至1949年,我国出版文学期刊4 194种,其中纯文学类期刊2 772种,综合类文学期刊1 422种[3]。文学期刊的快速发展,为作家发表作品提供了便利,长篇文学作品更是多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如巴金的《家》最初发表在《时报》,曹禺的《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老舍的《骆驼祥子》发表在《宇宙风》,郭沫若的《女神》中多数作品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通过报刊发表文章不仅为作家提供了稿酬,也使文学作品的讨论空间更为开放,增加了作家与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互动的可能性。作为文学作品的原始形态,部分初刊本的文本较为粗糙,主要是因为报刊发表注重时效性,容易产生情节不连贯、引用不准确、内容表述不当等问题,需要作家在此后再版时进行修订。此外,受到文学批评家、读者的意见影响,以及作家自身思想的转变,不少作家会进行多次修改,甚至主动调整写作风格,如巴金提出作家应有修改作品的权利,强调“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4]。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均有多次修改作品的现象,《女神》《家》《骆驼祥子》《雷雨》等经典之作更是经过多次修改,最终修订本往往与初刊本、初版本的内容差异较大,甚至会出现一段内容被反复删除又恢复的现象。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初刊本、初版本、过程本到最终修订本的过程中,多数的修改是作者的主动行为,包括修订文字的疏漏、替换新的规范用语、迎合时代的主题,形成了时间历程上的动态修改过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年发表在《宇宙风》半月刊后,先后在人间书屋、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开明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期间经历了多次修改。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增加《后记》,强调“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但这里所谓“枝冗的叙述”却并非简单的词语调整,而是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初版本中祥子堕落等内容大量删改,重点突出祥子性格好的一面,凸显祥子“穷苦人民”的形象。老舍将这些修改可以概括为“明白了一点革命的道理”的变化,体现了作家对政治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5],这也是多数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修改旧作的主要原因。
考察文学作品版本时,在作家授权、正规出版的图书之外,盗版书籍也值得关注。如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郭沫若等知名作家的作品遭到大量盗版,既有正规出版机构违反出版约定的额外加印,也有未得到作家许可的书商或个人的盗版印刷。从文学价值的角度考虑,盗版的图书通常编辑、印刷质量较差,保存的价值不大,但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看,盗版图书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郭沫若的《黑猫》最初刊登在《现代小说》月刊1929年第3卷第1期、第2期,10个月后被上海仙岛书店以《黑猫与塔》的书名盗版,比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的单行本还要早一年,此后又被以《黑猫与羔羊》《桌子跳舞》《我的结婚》等书名多次盗版。与正规出版相比,盗版书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出版商对热门作品的追逐,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如在萧斌如、邵华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中,第五部分专门罗列了郭沫若的“翻版本”(即盗版书),包括39种著作的55个版本,11种译作的11个版本[6]。尽管多数盗版书籍内容庞杂、质量较差,但也有少数图书的编辑质量较高,具体的盗版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此类图书的研究为作品版本流变、作家与书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 版本错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复杂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对文学评论提出了新要求,朱金顺在《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中认为版本学是“新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部分人因为不懂版本,难以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7]。研究者因为选择版本不同,很容易出现文学评论的失语现象,争论者依据不同的版本各自提出观点,形成了错位对话的现象。如《围城》在出版后不久,方典、张羽、巴人等评论者针对初刊本、初版本中的情欲描写,批评其为“香粉铺”“春宫画”“争风吃醋的小场面”,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评价多为赞扬与肯定,并将此前负面评论视为“哗众取宠,赚人噱头”[8]。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既有研究者观念的差异,更多的则是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对相关内容的删减,影响了评论者的判断。文学作品版本的差异对研究观点的影响,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基础工作的不足,需要借鉴版本学方法做好图书版本谱系的梳理。
在评价具体的事件或人物时,作者在不同版本之间的描述可能存在差异。如郭沫若在《黑猫》初刊本中细致描写了“称心与不称心之间推动”的微妙心态,既期待妻子是“理想中的爱人”,又担心“媒妁的结婚”可能会失败,婚后因为强烈不满将其称为“一场痛苦,一场耻辱,一场悔恨”。编入《沫若文集》时,作者对复杂的心理变化和不满情绪进行了大量删减,描述变得更为平淡和理性[9]。与之类似的还有丰子恺对老师李叔同的评价。如果仅看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中的《怀李叔同先生》,很容易得出李叔同的爱国教师形象,新版本中删除了该文章原题《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的李叔同在青年时期的“有不可一世之概”和在教学中“严肃而新鲜”的特点,以及赞扬弘一法师的“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等评价。丰子恺对李叔同评价的变化,与其在1952年发表《检查我的思想》中的观点一致,是对以往“佛教的影响”的反思,因此不再多提“护生戒杀”“人世无常”等内容,进而反思了原有的旧人道主义观点[10]。
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之间,受到作者修改影响,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也会发生变化。如郭沫若《女神》中《凤凰涅槃》是修改较多的一部作品。有研究者认为《凤凰涅槃》的情绪节奏是“从《序曲》的沉郁,经《凤歌》的愤懑,到《凰歌》的凄婉,再到《凤凰更生歌》的激昂,形成了‘弱—强—弱—特强’的节奏起伏,从而把对旧世界的诅咒、对新生的渴望和新生后的欢快,逐层次尽情渲染”[11]。对比《凤凰涅槃》的前后版本发现,体现“特强”节奏最后一节“凤凰更生歌”中的“凤凰和鸣”部分,是郭沫若修改最多的章节,从1921年版最初的15小节诗句到1928年版删减至5小节诗句,保留了“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悠久”等积极向上、充满乐观情绪的主题词,而将“我们恍惚呀”“我们神秘呀”两小节删除,让全诗更符合持续变强的节奏。这一细节修改让《凤凰涅槃》不再是最初版本中的个人情绪的自然宣泄,去掉了“神秘”“恍惚”的结尾使内容变得更为光明,体现出“新生后的欢情逐层次地渲染”,忽略了初版本中的“神秘”和“恍惚”,作者最初创作时的复杂的个人感受,变为积极乐观、持续高涨的情绪。对“凤凰和鸣”部分的修改,直接影响到《凤凰涅槃》全诗风格,反映了郭沫若修改时的心态调整。因此,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时,同样需要将不同的版本的内容进行对比,并结合作者的经历和所处环境,进而探讨作品风格转变的原因。
三、 版本定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性
瑞士文艺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er)在《语言的艺术作品》中提出文学版本选择问题,认为最重要的版本是作品的初版本和最终修订本,初版本是作品的最初形态,“随同着这个版本这部作品开始它自己的生涯和它的影响”,而最终修订本是“作者曾经亲自处理的”“代表他最后决定的意志”的版本,是“精校本的基础”。但同时也强调了手稿和过程版本的重要性,“一切手稿和印行的版本的差异”都是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资料[12]。
沃尔夫冈·凯塞尔对初版本和最终修订本的重视,反映了学者对作品版本的选择倾向。其中初版本最被重视,如《中国新文学大系》通常收录作品的初刊本或初版本,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表示,“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13]。正是初稿的缺少修饰和质朴,最能反映出作品的原貌,体现作者最初的所思所想,不受后期修改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说作品初稿并非仅指初版本,也包括作品的初刊本。一般情况下,初版本是对初刊本的第一次整理修订,作者会在文字、情节等方面进行完善,比初刊本更适合作为研究底本,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极为复杂,两者孰优孰劣需要进一步考证。如《郭沫若全集》收录《黑猫》时,以1931年上海现代书局的初版本对比最终修订本,补充了大量异文内容,体现了编辑对初版本的重视。但详细梳理《黑猫》初刊本、初版本、过程版本和最终修订本时发现,所有过程版本都是以初刊本为底本,跳过了时间相对靠后的初版本,导致初版本缺少前后传承关系,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初刊本反而更符合作品初稿的概念,适合作为版本流变研究的底本。
受到作者、编辑、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作品编纂过程中,无论是原汁原味的初版本,或几经修改的最终修订本,都有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作品版本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需要依据编纂情况而定。如《郭沫若全集》延续了《沫若文集》的编选标准,强调“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14]。以最终修订本为底本符合作者及其家属的意愿,但却被部分研究者诟病,认为无法体现作品原貌,遮蔽了作者创作之初的观念。另一些作品以初版本为选录标准,如《老舍文集》称“根据初版本校勘”,弥补了修订本的不足,但同时也对编纂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骆驼祥子》虽根据初版本恢复了多数内容,但个别涉及性描写的内容却没有恢复,也没有加以注释说明,反而增加了版本的复杂性[15]。《丰子恺文集》文学卷在编纂中强调“尽可能保留这些集子的原貌”,但受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修改的影响,在底本选择中却出现了混乱的情况,有些文章以初版本为底本,另一些文章以修改本为底本,部分文章甚至出现两个版本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版本的新内容。还有些作品集强调作者的审定权利,如《曹禺全集》在采用初版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在出版说明最后强调“经曹禺先生亲自审定”。将“亲自审定”作为编辑标准成为作家全集编纂的不成文规定,却容易与“采用最初版本”产生矛盾。正如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16]尽管多数作家不会彻底否定早期作品,但其晚年的态度却容易影响到版本选择。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初刊本或初版本,还是作家修改后的过程版本和最终修订本,都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选择哪一版本作为底本,针对哪些版本进行校勘,需要结合具体的版本情况进行分析。
对于版本众多的作品,研究者通常需要选择一个版本作为“善本”,但“善本”的选择却是一个复杂问题。初刊本和初版本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原汁原味,但容易出现文字粗糙、编辑质量差等问题,如郭沫若的《黑猫》初刊本不仅文字有待润色,还存在一些过于夸张的描述内容。过程本的情况较为复杂,可能存在更换题目、删改不完整、节选内容、增删注释等问题。最终修订本的编辑质量较好,但可能存在过度删改的问题,如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尽管与旧作同名,但在筛选文章、内容修改上受政治环境影响较大,有可能偏离作者的真实修改意图,成为具有时代特色但内容存在缺憾的版本。对于一些经典作品,更是存在版本众多的现象,如巴金的《家》前后修改了9次,改写了主角觉慧对祖父的态度以及与鸣凤的恋爱过程,使人物形象、故事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修订本与初刊本内容差异非常大。曹禺多次修改《雷雨》产生了9个版本,其中对涉及鲁大海的情节和形象反复调整,体现了不断合理化悲剧主线与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之间的张力和矛盾[17]。因此,很难简单地判定哪一版本是最合适的作品“善本”,需要结合具体的版本脉络进行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作品版本研究,需要将不同版本进行整合,形成作品的汇校本。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众多,但正式出版的汇校本极少,目前仅有桑逢康汇校的《女神》,陈永志校释的《女神》,黄淳浩汇校的《文艺论集》,王锦厚汇校的《棠棣之花》,龚明德汇校的《死水微澜》,胥智芬汇校的《围城》,金宏宇、曹青山汇校的《边城》、张桂兴汇校的《骆驼祥子》、孟文博汇校的《文艺论集续集》、张立华汇校评注的《四十自述》,仅涉及郭沫若、李劼人、钱钟书、沈从文、老舍、胡适等作家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本数量较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围城》汇校本官司影响最大,并引发了学者对“汇校”概念的争论。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未经钱钟书同意出版了《围城》汇校本,引发了官司并因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被判败诉,未获许可的《围城》汇校本被认为是扰乱正常的出版秩序[18]。这场官司引发了对汇校概念的讨论,钱钟书认为该汇校本是变相盗版,作者的修改没有必要标明出来,杨绛也表示《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才有版本研究的价值[19]。但也有学者从研究的角度对汇校本表示支持,如朱金顺提出能否汇校的关键不在于创作年代,而是“有没有大量的异文”,是否具备足够的汇校资料[20],金宏宇则认为汇校本实现了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15]178。多数文学史料研究者认为,汇校本是进行版本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受到版权、出版社、作家等因素影响,特别是《围城》汇校本官司的案例效应,多数研究者还是绕开了汇校本的方式,转而采取“校读记”等形式开展研究,如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译文集〉校读记》,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蔡震的《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此外,还有从目录学角度汇总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版本著作,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卷”,《鲁迅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著译书目》等资料性质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中文期刊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瀚文民国书库等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期刊、图书数据库陆续建成,提供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初刊本、初版本和过程版本内容。与传统的老旧报刊相比,数字化史料更容易获得,并且具有内容丰富、查询便捷、方便复制的优势,为学者进行版本研究提供了便利。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汇校本、校读记等版本工具,但丰富的数字化史料弥补了这一缺憾。只是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内容完整性、版本描述、目录索引、内容检索等方面不够完善,存在不少的版本信息错误。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与版本研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为版本研究提供丰富内容的同时,也需要专业的版本研究进行规范,使杂乱无序的原始资料变为规范有序、内容精准的数字化信息。
四、 结 语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版本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是文学史料研究的初步工作,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短板。尽管已有部分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数据库建设不完善、汇校本编纂不足、版本研究专著较少等问题,导致部分研究者不熟悉文学作品的版本流变,特别是对初版本、最终修订本之间的过程版本缺乏了解,影响到文学史料研究、文学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推动文学作品版本研究需要开展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应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初刊本、初版本、过程版本、最终修订本等版本形态进行收集汇总,梳理经典文学作品的版本谱系,进而推动汇校本、注释本、校读记和版本研究相关著作的出版,提升作品版本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和影响力,促进文学史料研究达到严谨科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