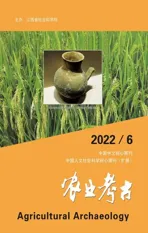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稻作蕴含的土地伦理*
2023-01-23赖毅
赖 毅
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西双版纳地区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干湿分明,适宜多种动植物的生长,拥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的优越条件。傣族主要居住于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地势相对较低,河流密布,气候也较周边山地炎热。充分利用环境气候和动植物资源,傣族传统以稻作为主要生计来源。在稻作生产与土地生命的互动中,傣族形成了以泥土为根本的环境认识,其稻作生产蕴含的土地生命协同、土地多样性利用和土地生命力养护的伦理规范,维护了稻作生产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土地生命协同的稻作
土壤由成土母质在一定水、热和生物条件作用下形成,除气候条件外,动植物和人都是土壤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环境动植物与土地、土地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傣族将动植物和人视为大地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其稻作生产也成为与多元土地生命协同的生产。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以下简称《巴塔》)作为傣族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傣族先民把握和控制自然的集体意识。《巴塔》描述,从烟雾和气浪中生出的太空神“英叭”先用身体污垢和水神鱼浮于水面的污垢创造了大地,又用头部污垢创造了管理地上万物的神灵和人类祖先神,由此,自然世界成为具有人体形式的生命存在。虽然创造大地的污垢具有可捏、可揉、可搓的无机性,但由污垢形成的自然却具有生命的特征。这不仅因为大地具有生长的特性,还因为大地有生命体的营养需要。为维护神灵和大地的生命存在,“英叭”大神不仅创造了为神灵享用的花果园,还通过神灵培育了营养土地的植物。正如《巴塔》中所言:“所种的植物多达九万亿,有坚硬的栗树,有粗壮的芒果树,有标直的椿树,有皮厚的木棉树,有垂叶的波沙莱,有成蓬的竹子,也有低矮的花树……”种植这些植物为的是“以它们的叶根,以它们的花果,养活大地生命”[1](P196-197)。为使土地具有活力,神灵还创造了各种动物,史诗中修补大地女神说:“我是女神,我是母亲,我来做动物,做够九亿种,使大地变活。”[1](P191)大地女神用水中泥土创造了各种陆地动物和水界动物。为区别人与神、人与动物作为土地生命的不同,又用来自天上的神树果泥创造了第二代人①。由此,神、动物和人作为不同形式的土地存在,分享着大地植物的营养。正是在平衡人类发展与不同土地生命的矛盾中,稻作生产得以产生。这是因为“人类形成后,人没有吃的,树皮吃光了,草叶吃光了,红土被掏空,人天天挨饿”,解决自然植物对土地生命支持的不足,“神可怜人类,对人发善心,撒下了谷种”[1](P253)。从此稻谷与自然植物共同为土地生命服务。
通过将神、动物和人视为不同形式的土地存在,将自然植物和稻谷共同作为土地生命的营养,傣族对土地生命的养护就转化为对自然植被和稻作生产的维护。
与各种自然植物的存在相同,傣族不仅将稻谷视为神灵的恩赐,也将稻作生产的发展归于神灵的作用。《巴塔》中描述神不仅帮助谷种成活,还划分了年月日和季节时辰,帮助人类发展稻作生产。由于神灵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傣族各村寨和各勐都有供祖先和自然神灵居住的竜山,如西双版纳俗语所说:“家长死后当家神,寨子首领死后当寨神,勐的首领死后当勐神。”傣族竜山中有埋葬祖先和村民的坟地,竜山也被称为坟山。由于祖先神与各种自然神灵为竜山的所有者,竜山中的植被除祭祀活动外,禁作他用。因竜山少则300—500亩,多达上千亩,傣族对竜山植物的保护使得大量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因为各种神灵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竜山外的各种大树也常作为神灵的象征得到保护。此外,傣族还要种植黑心树、樟树、毛竹、茶树、木棉等经济林木,这些林木与竜山森林一起为人和野生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与多样性树木对土地生命的养护相同,傣族稻作生产也具有多样性。根据《云南稻种资源目录》调查,云南南部地区栽培稻品种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而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布朗族的人口比重与稻种的丰富度之间均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2]。据1962年初步普查,景洪县6个区共有水、旱稻品种178个,除去同种异名的34个以外,全县已知名的水、旱稻品种144个,其中增产大、运用广的有61个[3](P54)。据1980—1982年西双版纳州大规模农作物品种资源普查,全州仅稻谷品种就有1600多个,其中水稻800多个[4](P106)。多样性谷种的存在,不仅为傣族利用不同类型土地发展稻作生产创造了条件,也为应对自然灾害和抑制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保障。
虽然稻谷是神给予人的恩赐,但作为养活土地生命的营养,稻作生产也为其他土地生命所分享。《巴塔》描述,最先获得谷种的是鸟雀和老鼠,人是因为吃了雀屎和鼠屎里的谷种后才开始捡雀屎和鼠屎来栽种。由于人与动物分享稻种,为了争夺谷种,人与动物曾经发生过矛盾,但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让雀吃饱谷、让鼠吃饱谷,以吃饱为数,鼠雀屙的屎,归人类所有”。这一表述既是傣族稻作发展的历史,也是傣族对其他土地生命系统土地权益的认知。协议的达成表明:为维护土地生命的存在,稻作生产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土地生命。“所以自古以来,有人就有鼠,有谷就有雀争吃”[1](P262-263)成为傣族稻作生产的常态。这种稻作生产与土地生命的协作关系虽然具有想象力,但这种关系只有在与此有关的生存体验得到强化时,才能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
虽然稻作生产主要为人类生存服务,但通过不同土地生命在稻作生产中的作用,傣族将人、自然圣境和各种动物整合到稻作生产体系中,为土地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感受到头对身体的支配作用,与神灵用身体污垢和头部污垢创造自然相同,傣族村寨不仅有为祖先神和自然神居住的“寨头”,还有供人居住和各种生产活动利用的“寨身”。通常“寨头”位于村寨地势较高的竜山或竜林,寨身主要由村舍和稻田所组成。将不同的土地生命连为一体,傣族建寨不仅要立寨门,还要在村寨周围种植树木,并以此确定村寨的边界。此外,傣族地区有“建寨要先立寨心,建勐要先立勐心”之说,因为在傣族看来,立了寨心、勐心,村寨和勐才有了作为生命体的灵魂。傣族祭寨心时要举行拴线仪式,仪式由头人主持,要求全体村民参加,届时全村成员共同修葺寨门,从寨门沿村寨四周围以草绳象征寨墙,作为村寨界线[5](P223)②。由于祭寨心仪式参与者限定为村寨成员,通过仪式活动的排他性不仅加强了村寨成员的集体认同,也维护着作为村寨成员共享的稻作生产小生境。
稻作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需要有水源的保证,虽然傣族靠河而居,但由于大部分村寨建在丘陵地带,且河流低于土地耕作面,稻作生产所需的水大多只能依靠山林水源引水灌溉。由于寨头竜林对水源的涵养,稻作生产有了水源的保障。据高立士先生调查,景洪坝传统灌溉系统由13条水沟渠组成,其中有5条较大沟渠的河水均源于勐神林“竜南”神山,这5条大沟灌溉了景洪坝区45000亩水稻田的60%。如将引用“竜南”神山的河流沟渠所灌溉的其他坝子面积相加,灌溉面积占全州水稻总面积的22%[6](P187)。由于水对于稻作生产的重要性,作为自然圣境的竜山或竜林成为傣族稻作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
傣族传统稻作以糯稻为主,而糯稻也是极易感病的稻种,保证稻作生产的顺利进行,除作为神灵象征的竜林外,作为土地生命存在的各种动物也为稻作生产创造了条件。由于竜林和各种树木对动物的养育,傣族稻作生产减少了病虫草危害。如傣族农谚所说:“吃了鼠肝稻田杂草多,吃了鸟肝田畴荒芜地瘠薄。”[7](P80)老鼠虽然会吃食谷粒,但也会食用草籽,由此可以减少稻作生产杂草的危害,而鸟类可以带来各种植物籽种,并以各种危害稻作生产的害虫为食,因此,鸟类的生存不仅有助于稻种改良,还可以减少水稻虫害。傣族传统稻田中除有鸟和鼠外,还有鱼、泥鳅、田螺、虾等动物,这些动物不仅在稻作生产中获得了生存空间,还帮助稻作生产疏松了土壤,培肥了地力,成为稻作生产不可或缺的助手[8]。
二、土地多样性利用的稻作
由于稻作生产与多元土地生命的协同,傣族稻作不仅要保障稻作生产所需的土地,还要维护其他生命存在的土地权益。通过为不同土地生命分配土地权益,平衡人与人的土地权利,调控多样性稻种的土地利用,傣族稻作生产形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巴塔》中说,维护大地生命的存在,大神“英叭”在地的四方用污垢造出了四门,又造出一对狮子、一只大象和一头牛来守卫四门,他在“西门放雌狮,南门放雄狮,北门放大象,东门放黄牛,守卫罗宗补(大地),这样天才平安,这样地才无事”。用“一只动物啊,表示一个洲,四只代表四大洲。这是英叭神,巧为天地安排,把不同方向和地域分开”[1](P42-43)。根据四种动物不同的喻意,傣族结合村寨地形地势进行功能布局。这一布局方式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景龙村村寨中还可见一斑[9]。由于西双版纳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状况,利用这一地势与稻作生产的关系,与雌狮的威武和繁殖功能相配,村寨选择西边为祖先神灵居住地,也即坟山或竜山。南方由于地势低,便于水流和人流汇聚,为傣族水源汇聚地,这一方面因土地为太空神和水神鱼污垢所造,借助雌狮与雄狮相配具有的生命孕育意象,这一区域为水生动物和野物所有,也是村际之间交易的市场所在。另一方面,由于洪水、野物和外来人员带来的危险,故需用强大的雄狮来守卫。与象作为佛教神灵地位相对应,也与象在傣族传统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相关联,北边为傣族佛寺所在和经济林木生产地,也有部分稻田,这一地域为稻作之外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场地。与牛在农作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相关,东边为稻田所在。位于四方之中的是寨心,也即人的居所。由于傣族村寨地势地形不同,各村寨功能布局有所差异,但多样化的土地利用却是傣族村寨布局的基本宗旨。
为维护不同动物象征的土地利用,避免单一化土地利用扩张,傣族还有其土地权益调控策略。《巴塔》描述,在傣族稻作生产之初,不仅人与鸟鼠争抢稻谷,人与人也争抢稻谷,人们互相打斗,谷子被吓跑,不仅人死了很多,而且水浪滔天、日月昏暗、大地摇晃。为了人和自然的稳定,先祖帕雅桑木底先是均分了稻谷,实行了对偶婚,又学动物建盖了房屋,教会人们种稻。但人们仍为争夺稻谷而斗殴,直到帕雅桑木底均分了田地,划分了村寨后,纷争才得以解决。进入阶级社会后,虽然傣族不同等级社会成员有着土地权利的不同,但基于公有土地的平均分配仍是傣族社会平衡生产者土地权利的重要措施。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傣族寨公田所占面积仍然较大,据木芹对西双版纳25个勐的统计,由家庭公有和村社公有的土地占77%,其中为村社成员共同所有的土地占58%,加上开荒后归村寨使用的公田,傣族村寨公有土地的面积处于增长状态[10](P258-259)。这些公田为平衡傣族社会成员的生存利益提供了保障。
由于傣族传统社会领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傣族村社成员使用土地的条件即是向领主交纳贡赋(无偿代耕领主土地和实物地租),并承担修路、架桥、兴修水利等公役。贡赋和公役以村寨为单位,由村寨成员集体承担。为均衡负担,傣族有“金纳把尾”一说,即吃田就出(一整份)负担,土地成为接受负担的前提条件。傣族村寨通过公共土地分配来均衡土地负担,即使是那些不以土地为生的外来户也要强制接受份地,而不接受份地的村民则会受到排斥[11](P42)。离开村社的普通农户,除退回所种土地外,还要留下较大数量的谷子作为接受这份“份地”代出的“出户钱”费用[10](P259)。对于村寨成员而言,每个家庭都有其土地,只要有劳动力,能承担“甘曼”(村舍公共事物)和“甘勐”(地方公共事物)的村社成员就可分得土地。为了平衡土地负担,每当有村寨成员退出,村寨都要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土地,以均衡寨公田的利用。由于每年都有新立户或通婚关系的外迁户、迁入户,或因疾病死亡丧失劳力户,因此,每年泼水节后,春耕前,各寨都要召集各户户主参加村民大会,分配一次稻田。由于土地肥力不同导致土地产出的不同,每隔30—40年,村寨还会对土地进行一次重新分配[12](P73)。这样的土地调控模式虽然不利于生产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取土地规模效益,但却有助于平衡稻作生产者的收益,减少因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矛盾,也节制了土地的无序开发和过量占用。
在以土地均衡保障村寨成员土地利益的同时,傣族稻作生产还为其他物种的土地利益进行分配。由于竜林对水源的涵养,傣族地区水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较大,但在一部分不能为水灌溉的田地中,傣族仍要种植旱稻、玉米、豆类、烟草和其他杂粮。尽管如此,傣族村寨还留有许多荒地,任由杂草生长。为此,傣族做出了稻作生产选择。傣族以籼型晚熟糯稻种植为主,一方面,这类稻种植株较高,有利于压制田间杂草生长。另一方面,因季风气候影响,西双版纳干湿季节明显,如栽早稻,栽时因雨季未到而缺水,收时又正逢雨季;如栽中稻,中稻将完全在雨季中成长,抽穗和收获正逢多雨期间,水稻易感病害;而栽晚稻,抽穗和收获时已过多雨季节,收割时稻谷稍经晾晒,便可堆置田间[13](P5)。这种水稻生产选择不仅保证了稻作生产对环境和土地的利用,也为其他作物和野物提供了生存空间。
三、土地生命力养护的稻作
土地生命力表现为土地支持植物生长的土壤肥力。为保障稻作生产对多元土地生命的养育,傣族有其土壤肥力维护措施。西双版纳土壤以红壤为主,红壤由于土质较粘重,土壤透气性不足,有机质含量低,属于低产土壤。为获得稻作产量,傣族一方面要以环境动植物补充土壤有机质。另一方面,还要减少土地有机质的消耗。为此,傣族传统稻作形成了一套环境资源利用技术。
添加客土,特别是水流中的泥沙,有助于改善土壤黏性,增强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加快土壤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分解,从而增加土壤肥力。在傣族看来,泥沙具有驱除鬼邪的作用,而各种疾病和灾害的发生在傣族看来都是因为鬼邪的危害,为使稻作生产免于病虫危害,傣族有用沙驱邪的习俗。泼水节作为稻作生产的开始,节前一天要举行堆沙塔仪式,届时,青年男女要到河边采集没有被踩过的细沙,和着白胶泥到寺院中堆三五座一米左右高的宝塔,在塔尖插上缠有彩纸的树枝和供品一起赕佛。摆放好供品后,全寨男女老少围坐在沙塔周围,听大佛讲经,预祝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14](P247)。念经结束后,这些沙被作为吉祥的象征和有效的驱邪物带回撒入田中。水稻栽秧后,为防止病虫害,在关门节期间,也有佛寺和个人组织的驱鬼活动,人们不仅要在竹楼里撒沙,表示把家中魔鬼驱出家门,还要到田地中撒沙,以将各类邪魔从家中、田地和村寨中驱除。在每年祭寨心仪式中,也有撒沙活动,这些仪式活动中对沙的利用,不仅有助于河渠的疏通,也改良了土壤。
如傣族农谚所说:“树美需有叶,地肥需有水。”[15](P232)水不仅是水稻生产的保障,也是傣族土壤培肥的重要措施。西双版纳雨季时间较长,多达240多天,受雨水的冲刷,水中带有大量的山林泥沙和腐殖质,这些泥沙和腐殖质随水进入到土壤中,不仅可以改善红土的黏性,还能增加土壤肥力,为而水稻生产对山林水资源的引用而开发的沟渠又进一步为土壤改良提供了条件。傣族虽然不直接使用人畜粪肥田,但男女大小便喜在水中溺之,凡沟渠河流,便是便溺场所。虽然夜晚牛马猪在竹楼下过夜有粪便的堆集,但每日家畜出栏时,傣族会将粪便清除,以便住于上层的人不致被秽气熏蒸。这些粪便在水的冲洗下进入到沟渠,随之进入的还有日常生活烧粪、烧柴留下的灰分。这些废弃物随着水流进入到稻田中,成为稻田有机质的组成,这也是傣族将土地视为污垢创造的重要原因。
由于红壤有机质含量低,且缺乏钾元素,种植绿肥和增施有机肥或草木灰(植物茎叶燃烧后剩下的灰分,钾含量较高)是增加土壤肥力的有效措施。傣族地区雨热条件较好,生物和土壤之间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交换快,利用这一特点,傣族传统稻作生产不仅是粮食生产,更是绿肥生产。傣族传统水稻品种多选择高秆品种还在于稻谷收获后,有大量的生物质可用于增加土壤有机质。此外,傣族传统稻作生产不进行中耕除草,与水稻生长相伴随的还有各种杂草的生长,这些杂草也与水稻稻秆一起成为来年营养土地的肥料。傣族传统有用象或牛踩田的耕作方式,其目的还在于将稻秆和野草踩入田中为土地提供肥力。随着犁耕的普及,傣族传统稻作发展了“堆田”技术。撒谷和栽秧前傣族要先堆田,用火烧去地面上的稻秆后,为使残留的稻秆及其残根快速转化为土壤有机质,傣族要先犁田,然后放水淹田,将稻秆及杂草淹没,15天左右将水放干后起垄,即扒泥将稻秆及杂草覆盖,以便稻草腐熟,10—20天后再将垄扒平放水淹田,这样淹水、扒田、放水、起垄重复两次至三次后即可将稻秆及杂草熟化,通过这样干湿相间的做法,即可将稻秆和杂草转化为营养稻田的绿肥。为此,傣族传统稻田耕作一般是犁1道,耙2—3道,为补充秧田肥力,撒种后还要再覆盖草木灰。尽管如此,傣族一年只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任由野草生长,同时,在这些休耕地中放牧猪、牛。这些野草与牲畜糞肥也一起成为土地有机质的补充。
在养护土地的同时,傣族还要对土壤肥力进行合理的利用。为此,傣族将不同排灌条件和肥力的土壤进行划分,划分的标准通常为稻田的产量。傣族史籍《帕萨坦》记载,傣历181年(公元819年)茫乃统治者地方官组织民众开挖水沟,并将开出的田地分为产量为一百挑、一千挑、一万挑3种规格的稻田,如数清点交给傣泐王[16](P124)。根据排灌条件和肥力的不同,移栽秧苗的大田通常分为三等。一等田为排灌条件好,便于管理,适宜水稻生长的田,这类田是靠近村寨的水田,也是猪牛鸡能进去的水田。二等田为排灌条件不足或肥力略有不足的田,也是牛喜欢在旁边睡觉的田。三等田为排灌条件差和肥力较少的田,通常为雷响田或沼泽地。通常傣族根据稻谷品种水分和肥力需求选择不同等级的稻田种植,为避免水稻病虫的危害,稻作生产每年还要换种或换田。同一块田第二年要种植不同的品种,同一品种第二年连种则要换田。换田多根据稻谷生产情况进行土地调配,在一等田、二等田中长势不好的稻谷,来年会种于三等田中,而三等田中收成不好的稻谷来年会种于一等田中[18](P25)。这样一来,不仅不同肥力的土地得到平衡利用,也使不同稻种获得适宜的生长条件。
傣族民谚有“水稻田头好,旱稻地脚肥”[15](P231)之说,田头为水源入口之地,留存有随水带来的腐殖质和养分,因此是稻田肥力较好的地方,而地脚由于地势低,有利于水分和肥力的留存,成为旱地作物生产较好的选择。水稻生产中,秧苗需肥量最多,竜林水源流经的寨脚田水肥充足,可以为秧苗提供充足的肥力。因此,傣族秧田多选择寨脚田,这些稻田也成为村寨所有稻田的“田头”所在。为不同的稻种提供适宜的土地,傣族还会在同一稻田的不同位置种植不同的水稻品种。除村寨稻田有“田头”外,每块稻田也有“田头”。傣族将谷魂的存在作为水稻生产的保障,“田头”具有了谷魂的象征,犁田、栽秧、收割,皆从此处开始。大面积栽秧前,傣族要先在“田头”栽上从秧田中选择的粗壮秧苗或需肥较多的秧苗象征谷魂。收割后,田头收割的谷子又作为谷魂送到谷仓里供奉,在送谷魂途中,主人一路吆喝呼唤,为谷魂引路[18](P60)。傣族民间有“好谷压田”之说,紫糯因营养价值高,可作滋养品,也可药用,在民间也有以紫糯为稻谷祖先的传说,傣族传统稻作生产通常会在“田头”种植紫糯。
通过土地肥力养护和多样性稻种土地利用调控,傣族稻田在贫瘠的红壤下每亩仍可获得200—300斤的单产,加之西双版纳地区地广人稀,传统稻作生产仍可获得较高的人均产量。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西双版纳曼竜枫做出典型调查后有这样的表述:“每个劳动力可负担耕种面积八亩,生产谷物二千斤,扣除生产费用和生产成本一千斤,剩余一千斤。”[13](P145)这样的人均稻谷产量保障了傣族基本生活所需,辅之以其他森林环境资源的利用,也使傣族改善了农业生产动力不足的状况。
四、结语
自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以来,将人类视为大地生命共同体的一员,尊重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帮助大地从技术化了的现代人的控制下求得生存,成为人类对大地共同体的义务。在大地生命共同体中,个体并不拥有独立于生态关系的价值,生命体的价值由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来决定。傣族稻作生产即是一种具有生态功能的生产,其生产体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维护了土地生命共同体的共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都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要义下,傣族稻作土地伦理为现代农业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启示。
社会生活利益与生物多样性环境利益的统一,是傣族稻作土地伦理的特点,实现现代农业生态化转型不仅需要生产者应用生态农业技术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还需要生产者具有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活利益。傣族土地伦理有其形成的社会环境,但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发挥稻作土地伦理对农业生产的规范作用,不仅需要傣族地区生态农业技术体系的重构,还需要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策略的有力支撑。
注释:
①《巴塔》中描述,第一代人由神灵用身体污垢创造出的两个贡曼神演变而来。这两个贡曼神在蛇的诱惑下,吃了神果园中的芒果而成为了最早的人。此后,这两个贡曼神又用泥土创造了第一代人。第一代人灭绝后,第二代人的创造虽然与第一代人的创造有所不同,但由于第一代人的形成是果实与泥土的结合,第二代人用果泥来创造,保持了与第一代人的联系。
②傣族传统观念认为人体有三十二魂,譬如头有头魂,手有手魂,脚有脚魂,拴线可以防止灵魂丢失或使不同的灵魂相结合,拴线活动常在叫魂或结婚仪式中使用。在身体图式的村寨结构中,祭寨心使用的拴线仪式也有将多种有利于村寨的灵魂相结合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