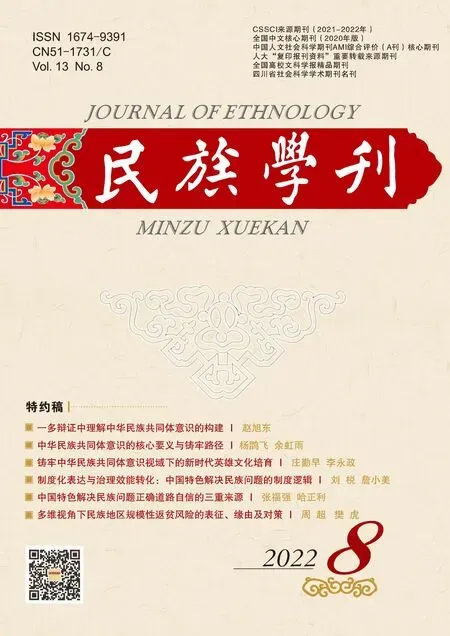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2023-01-23苏利海
苏利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引发了学界对多民族文学的深入探讨。如马梅萍《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1]、刘大先《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2]等探讨如何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铸牢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与发展又有了新的认知,只是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现当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言,尚有不足,因为倘若不知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只停留于当下的讨论,一些深层次问题就难以被触及,讨论难以推进和深化。本文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传统多民族文学的关系,思考如下问题:面对数量众多、创作情况更加复杂的传统多民族文学该如何界定?以何种方法来探讨?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如何落实到传统多民族研究中?如何将中华文化的一体性与传统民族文学的多元性相结合,进而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如何通过讲好民族故事向全世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新时代迫切需要新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来呼应现实问题,传统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亦已到了需要推进、革新的阶段。本文认为传统的民族文学研究需要突破汉族文学史“缩小版”的研究格局,更新方法,重新定位,新时代下更需要一种“大文学史观”。在此,本文以“一个中心三层视野”的研究框架对此问题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仅供学界参考。
一、为何倡导“大文学史观”?
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文学主要包括两大块:民间口头文学与文人作品。前者主要以史料性、民族性、口头性彰显,如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史诗,极具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有力填补了汉族古典文学作品在叙事性、传奇性、神话性、谱系性等方面的不足。文人作品则主要是汉朝以后,由于大一统格局的成熟,诸多少数民族慢慢融入汉文化圈,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者的创作大多以汉语诗文为主,创作量巨大,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例如《回族典藏丛书》涉及回族文学创作的多达140多种,《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中收录清代蒙古族诗文创作者近百位,其中五十四位有完整的别集存世。其他如满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创作量亦巨大,以《古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为例,据主编徐希平介绍,西南如白族、纳西族、彝族、回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九个少数民族均有汉语诗文集留存,涉及百种文集。可见在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上,少数民族作家占有足够重的分量。但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文人的汉语诗文写作大多类似于汉族士大夫写作的风格、手法,故对其作家、作品的民族属性一直存有争议,如对清代一个回族诗人的研究论文,质疑者往往发问:这明明是汉族文人的写作风格,何来少数民族成分?这样的诗人还需要打着少数民族的旗号吗?众多学者虽未公开质疑,但显然认同这种发难,体现在各类《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对少数民族作家论述颇少,与其总量、价值极不相称;即使收入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仅在身世简介中添补一句民族属性,但在分析作品价值时又毫不顾及其背后的民族特色,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价值也因此被一直深埋在文学史的表层下。
确实,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的民族特色并不明显。但其中一个问题往往被学界忽略:为何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一定也是少数的?为何只有描写当地民族独特的宗教和民俗才是少数民族作家?这里,我们犯的一个逻辑错误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定是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应地,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才是少数民族作品。这种将作家族裔与作品简单挂钩的看法,既是一种偏见,也实实在在地为民族文学的研究带来巨大戕害。一个杰出的作家在创作时,一面固然在自觉、不自觉地追逐、彰显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但另一面也在不断超越自己单一民族特性,将自己对个体、自然、人生的思考提升至宇宙、人类的共性当中,在这过程中,汲取其他民族的营养成分是必然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是必然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发展中的,求同与求异、共性与个性原本是辩证存在的。因此,一定要在少数民族作家身上找到一种亘古长存的少数民族特色,显然是一些批评家以固态、静止的思维来看待少数民族文化,这种思维在对传统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上戕害颇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秦汉以来即追求大一统格局,语言、文化均定于一尊,不少少数民族作家通过举荐、科考等途径进入中华文化圈时,已相当熟悉汉族文化的语言、文字,所做诗词,必然烙上中华文化共同的底色,故此,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身上一定要寻求到单一的民族特色,显然无视和忽略了中华各民族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学史上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既要重视其民族身份的独特性,又要重视其文化上的大同性,在同与异之间寻找一个动态平衡点,方能对其有客观、全面的研究。
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中华文化一体性辩证地诠释出来?如何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如何说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情境必然更新学理、方法,亟需新的文学史观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倡导“大文学史观”的必然性由此产生。
对“大文学史观”,现代学界已有一定的探索,较早如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已然建构一种融“精神层面”“文化层面”“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为一体的“大文学观”,尤其强调文学史要注重“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与“边地民族多缘活力”的相互作用[3]1-21。此“大文学观”偏向于“大文化”的文学观,但已然关注到多民族文学的一体性。最近杨洋在《大文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4]提出大文学史的视野、方法,不过主要针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且只是提出若干思路、方法,并未有全面细致论证。
本文“大文学史观”借鉴前人成果,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的时代背景而生发。该文学史观的内涵为“一个中心、三层视野”:一个中心,即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理念,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把握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多”与“一”的辩证性,通过“多中之一”来处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一体性;通过“一中之多”来处理多民族文学中的个体性、多元性。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实践即体现在“三层视野”上,三层视野即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这三层视野互为补充,共建一体,共同维护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
二、民族性:共同体视野下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
民族性,是指各少数民族以本民族语言书写、传唱的作品,它是各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之根、之魂,是原初,是本源,弥足珍贵,非常值得珍惜、继承。这方面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受到国家重视,通过在国内大规模系统地收集、整理、编写,绝大多数有口头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作品已及时得到保护。最近几年,学界又汲取西方人类学、口头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了一系列以口头文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项目,同时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将前期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保护、研究工作做了更扎实、细致的完善。可以说,当下对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收集、整理在体量上已初具规模,后期的研究、理论升华,尤其是在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性上,仍然有广阔的前景。这些民族文学杰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如藏族、蒙古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维吾尔族的《阿勒普·艾尔·通阿》《优素福——阿合麦提》、彝族《勒俄特衣》《梅葛》《天地祖先歌》、纳西族《创世纪》、佤族《西岗里》、景颇族《凯诺和凯刚》……这些民族叙事史诗篇幅巨硕,情节曲折,语言丰富,如作于11世纪的回鹘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长达一万三千余行的长诗,以及创于13世纪的蒙古长诗《蒙古秘史》。……这其中侗族就有《金汉烈美》等几十部叙事诗,布依族有二十多部,壮族有上千部叙事诗[5]14。可见,中国多民族文学体量之大,创作之丰,堪称世界奇迹,它也是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宝贵财富。对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学进行系统梳理无疑是必要和亟需的。
这些丰富的作家和作品是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学,犹如五十六颗星,但这些恒星不是静止不动的,相互之间也不存有着天然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复原多民族的原貌,既是尊重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要完美绘出每一颗星的形态,更要绘出五十六颗星背后组成的星空图,绘制出这些恒星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探讨其背后体现的中华多民族文化、文学的互动性、一体性。中国的各民族平等包括文化上的平等,大文学史观更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呈现各民族文学原貌的基础上。
三、中华性:共同体视野下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体格局
多民族固然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基石,但这种“多”不是分散、独立、单独的,而是在中华文化圈内和而不同,融为一体,互为补充、融入,这种特性就是大中华性。大中华性,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下,专注于各少数民族后期融入中华文化圈后,受汉族儒家、宗教等影响,作品中所彰显的中华文化一体性,体现了各少数民族积极汲取异质文化,进而推进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特征。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在固有文化基础上循环往复,那只能是文化的退化。一个民族的发展必然是在不断融入、汲取其他民族的新质,方能蓬勃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显然不能要求各少数民族固守本民族文化底色,毫无变迁更新;同理,我们也不应以必须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成就,甚至以此判断是不是属于少数民族。这只看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异,忽略了他们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互融、互通的一体性。这个问题在不少《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相关专著中体现明显,例如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对明代著名文学家李贽的阐释,标题虽是《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李贽一生多有著述,对儒、道、佛都有论述,但很少有关于伊斯兰教的言论”[6]146,唯一能证明其伊斯兰教属性的,只是遗嘱中的安葬方式,那么其大量的诗文作品与回族文化有何关联?且文章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描述与现行各类“中国文学史”的论述相似,围绕“童心”“求真”关键词展开。这种现象在国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等相关著作中体现比较明显,除了标题是少数民族外,其内容基本是仿照“中国文学史”而来,也可以说扣着少数民族的帽子,内核却是汉族文学的话语。这难免被读者质疑,整个文学史如何彰显“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个难题颇难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只关注到民族间的异质性,却忘记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同质性,倘若不能辩证梳理同与异的关系,只注重一端,而忽略另一端,必然导致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尴尬。可以说,中国传统各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特色不彰显,正是中华文化一体性的特质,在此,我们不必仰承西方固有的文化理论、民族理论来圈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如何提炼、升华这种“少数”之中实存的“中华民族共性”,是国内学者必须扎实、细致去研究的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呼吁在“中国文学史”中加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分量,但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是简单地入史与否,更重要的是如何入史?入史后的价值如何彰显?如何变旧史为新史?新的文学史又能否呈现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大格局、大风范?其实,对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心应是在质上如何彰显其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在“中国文学史”篇幅上多增加几个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如果价值得不到彰显,少数民族作品添入量再多,也只是锦上添花,成为点缀。
同样,只关注同,而忽略异,也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研究的偏差,这个现象在当下颇为普遍,如现代通行的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中,虽然在生平简介中标示了一些作家的民族身份,但在陈述中往往未能顾及其民族特色。这显然只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共性,而忽略了其间的差异性。此类失误颇多,如以清代文学史为例,清代满族文学成就卓越,但文学史教材中对其描述大多沿袭既往的文学审美标准,丝毫不关注其民族特色。例如对纳兰性德词的研究,千篇一律是爱情、边塞题材两大划分,词学价值仍是“言真情、写真景”此类常用的诗学术语。以此界定,纳兰的满族属性自然是可以忽略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纳兰的边塞词为例,《中国文学史》教材上认为其词“以自然之眼写自然之景”“真实感人”,这些判定自然不错,但这是怎样的真景?怎样的真情?如何产生的?为何词体近千年的发展,无人达到此境界?所谓的“自然”该如何理解?……诸多问题学界未有深究。倘若深挖下去,以上问题的答案均需回归到纳兰的满族文化背景中去探讨,方能有一清晰答案。我们先看其几首边塞词的代表作,如《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如梦令》: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菩萨蛮》:
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这些边塞词均写得壮气淋漓,写景如画,写情感人,融阳刚与柔情于一体。孤立地看纳兰词,确实只能以传统诗学术语中的真实自然来概括,但倘若我们的考察视野放长远一些,将纳兰纳入满族文化去考察,则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这种自然真实的审美观与满族特有的渔猎文化属性有着巨大的关联。我们发现清代满族诸多诗人、词人的写作大多烙有此痕迹,以康熙诗词来说,其对南北山水的描写同样自然雄阔,以真见长,如《塞上宴诸藩》:
万里车书皆属国,一时剑珮列通侯。
天高大漠围青嶂,日午微风动彩斿。
《登澄海楼观海》: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
波涛滚滚乾坤大,星宿煌煌日月光。
……
这些边塞诗气势豪迈,阳刚之气逼人,且语言自然清新。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满族女词人顾太清身上,如其《廿七登清风阁后西北最高峰顶》:
步上最高峰,巉岩小径通。阴崖飞异鸟,绝壁走憨童。山豁东南阔,花光西北丰。等登临渺下界,目断四天空。
《廿九雨中晓发云冈》:
云起万山失,天开大水横。东风晴未稳,一路听鸠鸣。
《清风阁看雪是日大雪节》:
人道西山积雪好,我住西山积雪中。试问城中高卧者,几人得见此天工?
……
这些诗境界雄健大方,气象高远。以上三位诗人的身份、阶层、性别、时代均有差异,但在作品中均有雄健高深的气象,这一诗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只能回归、聚焦于他们所属的满族文化。满族在长期游牧、渔猎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一种亲近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化基因,并一直流淌在每一个满族成员的血液中,进而在其成员作品中形成一种共性书写。但对这一重要的民族特色,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均未尝涉及,单一的汉族文学史视野仍然固步自封,至今难以撼动。最不可思议的是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相关著作中,在论及纳兰性德、顾太清的作品时,其语言、思路、方法依旧沿袭《中国文学史》教材,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模式化书写方式。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往往以“知人论世”的理念,将作家作品以时代为限,分别按照王朝的初期、盛世、没落来划定作家、作品的特色,并不顾及在时代背景下个体间的差异,尤其是民族间的差异。前面所举的满族词人作品在文学史上即被分别描述为反映着清代政治的黑暗、压迫等诸多泛语,忽略了这些不同时间段的作家所隐含的共性——民族文化,致使对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缘由、价值等考察只能依赖单一的时代背景来确定,很多深层次问题未能被及时捕捉和梳理。
当然,我们在关注满族文人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也不能忘记满族入关后,积极融入汉族文化,他们在保持满族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同样带着汉族文化的烙印,民族融合给他们的创作带来质的飞跃。如纳兰创作的大量抒发缠绵凄婉的爱情之词,这其间的因素则非满族文化所固有的,而更多是受到汉族文学与文化的影响。纳兰一生痴迷《花间》《南唐》词,这些词中经典经他反复阅读、模仿,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最终玉成了他在清词中的经典地位,如《如梦令》: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
《采桑子》: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粱。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瓣香。
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
大量缠绵旖旎的爱情词,无疑是受唐代花间、南唐李煜、宋代晏几道、秦观等人的影响。除纳兰性德外,其他满族诗人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深度接受,他们在爱情、亲情、友情的诸多描写上无不受儒家文化影响,这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如康熙的《示诸皇子》:“勤俭守家法,为仁勉四箴。读书须立体,学问便从心。”这里,康熙俨然以汉族士大夫的口吻在教育子女,语气温和亲切,严厉之中不乏温情。在治国理念上,康熙亦处处师法儒家,在其诗文中有大量体现:
《古北口》: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山海关》: 历数归皇极,纲维秉化权。漫劳严锁钥,空自结山川。在德诚非易,临风更慨然。
《春雪》: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君。
《景山春望》:云霄千尺倚丹丘,辇下山河一望收。凤翥中天连紫阙,龙蟠北极壮皇州。……却向闾阎看蔀屋,崇高还廑庙堂忧。
在这些诗歌中,康熙处处彰显着一个儒家文化要求下的君主必备的美德:重教化、重勤民、重农业、忧社稷……,这些儒家文化因素的融入无疑为康熙诗歌抹上了一笔厚实的思想底蕴。
又如顾太清诗词之所以有此惊人的高度,与她勤于学习诸多汉族作家作品有关,在其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和黄山谷”“和姜白石”“和柳永”“和周邦彦”“和吴文英”“和张玉田”“和李清照”……足可见她对汉族诗词文化的热爱与勤奋学习。在此基础上,她才能镕铸百家,自成一体,形成了哀婉深挚、真切自然的特色, 如《早春怨·春夜》:
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栖鸦。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 红楼不闭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临江仙· 清明前一日种海棠》:
万点猩红将吐萼,嫣然迥出凡尘。移来古寺种朱门。明朝寒食了,又是一年春。细干柔条才数尺,千寻起自微因。绿云蔽日树轮囷。成阴结子后,记取种花人。
这些词轻柔细腻,彰显了满族女性的内在柔曲之美,这种性格的彰显与表达,与顾太清巧妙学习、汲取汉文化诗词中的营养有着巨大的关联。
总之,在清代满族作家的作品中,儒家文化的融入颇为醒目,体现在满族文人作品中对日常居室、治家、交友、饮食、书画、宗教上的大量描写,无一不在彰显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可以看出,倘若不言及纳兰等满族文人的民族身份,很难对其诗词的自然真实有确切把握;同样,不言及他们创作中的汉族诗词文化元素,则难以说清楚其作品背后的深度与成就。满族文学如此,蒙古族、回族等明清以来诸多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均有此特点,但对这些卓越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目前学界还未达到将个性与共性辩证统一的深度。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民族文学史的专著达100多种,对各民族文学间关系的融合,学界也有广泛探讨,但深度还需拓展。如何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到中华文化共同圈内来研究,进而在质上提升“中国文学史”的质量,让“中国文学史”真正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这是个巨大工程,也是个极有价值,也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四、世界性:共同体视野下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人类关怀
如果说民族的、中华的视野,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审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那么世界性则是向外的。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如何反观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属性?如何提炼出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进而讲好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这层视野,对内是高扬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则是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软实力,彰显着中国文化对全球文化的贡献。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不是考古似的挖掘、复原,而是一种价值的溯源,尤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彰显它的价值,在世界上树立中华文化这一坐标,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我们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反观自身的独特性、差异性,走向世界舞台,说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现代学界亦已关注这个问题,如学者汪荣在《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7]、李鸿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8]等文已充分关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引入世界文学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与改造”的问题,但学界尚未关注到我们在引入世界,学习西方的同时,如何放出自身的光芒,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自身的故事,而不仅是被动地学习世界。对此,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不能固步自封,局限于中华文化圈内,还要走出国门,步入世界,通过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基督文化、贵族文化对比,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固有价值。例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着神性文化、基督文化的宗教属性,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诸如摹仿、合式、寓教于乐、崇高、悲剧、三一律等诗学理论。不只是西方,邻邦日本亦是我们可资比较的世界视野之一,日本文学在贵族、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侘寂、物哀、幽玄的特质。与西方的、日本的民族文学相比,中华文化则在汉、蒙、藏、回、满、苗等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下,形成了崇拜天地祖宗,崇尚天人合一,提出了诸如赋比兴、温柔敦厚、神品、模仿、比拟、自解、风骨、自然、平淡、韵味、妙然等诸多独特的美学概念,彰显中华民族文学崇尚自然,强化世俗,追求伦理的经典特质。与西方、日本的文学相比,中国传统诗学的宗教性、贵族性并不彰显,而独显出虔诚地崇拜天、地、人的文学特色,伦理道德性突显。这里,我们注意到西方古典文学在强烈的宗教意识下,形成的对宇宙、神有了敬仰、畏惧之心,对世俗生活的厌;日本文学则在神道、禅宗文化影响下形成独特的哀、玄、寂的贵族文化。与这些民族文化相比,中华民族文学则有着家国一体、天人合一、哀己及人的审美特色,追求的是自然、平和、神气畅然的气象。这些无疑是在彰显中华文化个性,也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性思维下可与全人类分享的文化资源。中华各民族文学在文化融合中形成了敬天法祖、重人伦亲情、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性,这些特性已然超越民族界限,上升为人类文明的贡献。故此,在谈及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时,视野需上升至人类文明共同体,这不是在比较优劣,而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对比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彰显民族特色。
总之,“大文学史观”强调的是在中华多民族一体视野下,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体性、多元性、世界性的新属性。其中民族的、中华的视野侧重于复原中国多民族的真实场景,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问题;世界的视野回答的则是“什么是中国民族文学”问题,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弘扬中华民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新价值,这层视野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的升华。如果说民族、文化的视野提供的是一幅真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图景,那么世界的视野则是彰显中华民族的大国气魄、民族自信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和担当感。
五、结语与展望
当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通过三重视野来反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会跳出单一、狭隘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对此认知有着更为通融、长远的判定。对传统多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既关注民族属性,又要关注中华属性,更要关注其人类属性,这个理论即来自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推广。在共性中掌握其特殊性,在个性中体悟其共性。对传统多民族作家,既看重其民族身份背景,又不能执于单一民族性;在传统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下,民族融合已是主流,民族的个性并非突显,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如满、蒙、回等深度接受汉文化,其创作的作品已然与诸多汉族文人创作的作品并无突显的差异,在此刻意强调其民族身份,确实有些牵强。这里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必执于单一民族身份,非要寻出其民族特色、价值;但也不能脱离多民族特色,脱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事实,而要透过多民族“共同”这一底色,讲好中国少数民族“大文学史”。
总之,当下诸多的“中国文学史”简单地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因“少数”而忽略于文学史之外,这种忽略不仅体现在量上,即对大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忽略;同时也体现在质上,对一些经典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民族性深挖不足,这些弊端的产生正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一特质的忽视。对此问题,早已有不少专家进行呼吁,如《文学遗产》期刊社2015年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中华文学”问题,刘跃进先生特意撰文《中华多民族文学经典理应进入中文系课堂》[9],强调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应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视。
本文倡导一种“大文学史观”亦是对此类学者观点的呼应,强调“中国文学史”中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书写,不仅在数量、篇幅上的重视;更是在质上,理性、辩证、全面梳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这其中少一些个性的关注,多一些文化共生的领悟;少一些单一视角,多一些关系研究;少一些空话,多一些实证研究,这无疑会让我们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上少走一些弯路,更多精品成果不断呈现,进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
当下,我国已有55个少数民族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10]。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色既不同于美国熔炉式的多元文化,也不同于欧洲民族认同“离心的”式民族文化,“因为它缺乏一个核心或一个独特的根源”[11]512。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特色的把握、梳理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以“想象”的方法来定义中国多民族文学特质,而要回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实况,从文献入手,深度拓展,通过对大量文本的梳理、溯源来澄清当下对此问题的诸多争论。所以,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能否入史?如何入史?怎样定位?前景何在等诸多难题的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和史实,需要我们打破以往的一些狭隘界定和视野,代替以打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来关注和研究,这对文学史家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所见者大,所言者必深,本文所言,亦是抛砖引玉,期望学界能对此有更深入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