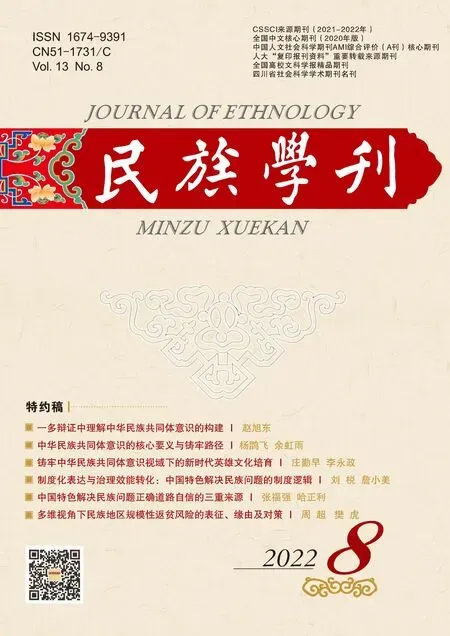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自信的三重来源
2023-01-23张福强哈正利
张福强 哈正利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不断探索出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该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历程、意义等方面①,主要探讨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对为什么问题关注较少,即较少分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什么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重要功能。通过理论分析,廓清认识。一方面,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阐释体系,有利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更好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说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分析其蕴含的内在和外在必然性,从而更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道路选择的必然性
道路选择是决定道路是否成功有效的关键第一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在面对特殊问题、在特殊背景下完成的道路选择,这种选择是内因和外因共同推动的结果,具有理论与时代的必然性。它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有密切关联。同时,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迫切要求一个先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彻底实现民族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一)理论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视角
中华民族的演变是多元汇聚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早期多元文明在相互碰撞中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一体性发展的基础。自此开始,一体和多元的关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演变。历代封建王朝都必须考虑用制度安排对多元和一体关系进行协调,从而保证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然而,传统民族事务治理思想更多从天下观中演变而来,它以“己”为中心,对待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此种治理方略是在新的世界体系尚未形成,国际秩序处于传统体系中发展形成的,缺乏比较政治视角,有其自身缺陷。囿于传统王朝本身权力结构的限制,这种缺陷是本质的,无法在传统王朝体系中彻底得到解决,需要在现代国家体制中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调节。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体系崩溃,但多元和一体作为历史遗产被继承下来,成为转型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资源,同时多元和一体的矛盾也制约着现代中国的转型。各种政治势力不得不面对多元和一体这样的矛盾统一体。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促进一体性的发展,同时兼顾多元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家们普遍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在不断探索中,用超越性的视角来协调多元和一体之间的矛盾,有效弥合了传统王朝中民族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境。
这一超越性视角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问题被置于人的全面的、自由的视域下考察,群体差异可以在个体发展中得到解决。民族差异是后天的、建构的、动态的,非本质性的。“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1]人类发展最为核心的主线并非是民族之间的争斗,而是阶级斗争,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相比而言,只有从属意义[2]。“人对人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灭亡。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民族问题需要依赖其他方式来实现最终的、彻底的解决。它只有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中逐步得到解决,只有当阶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民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结合中国实际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用民族解放、全人类解放、阶级平等等超越性的话语来突破中华民族多元和一体的内在紧张感,用超越群体差异的方式重新淬炼出了另外一套新的话语方式。这一套思维视角不仅超越了传统王朝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缺陷,同时对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用一种全人类的视角和世界主义的眼光,整体性地思考民族产生及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既不是历史上的强制同化,也非任凭各民族自在、自由发展。从产生效果看,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身份、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性地解决了多元和一体之间产生的张力导致的国家建构困境,有效促进了新中国的国家整合和中华民族整合。“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性或叫作共性。这个共同性或者共性,就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作为中华各民族大家庭,是共性、个性、差别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共性和各民族个性生动地结合起来的统一体。”[4]
(二)现实必然性: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迫切要求
近代中国是一个脱嵌和再嵌的过程,这场大脱嵌革命始于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在延续。个人、家庭,到民族、阶层,再到国家、文明都被卷入到这个过程中去[5]。近代史上的各种危机都可放置在此背景中考察,再嵌过程并不是由个体、民族或者国家的自在发展就可完全实现。在残酷的现代国际竞争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力量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型。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上台,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一再嵌化的伟大进程。
近代部分边疆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活动,本质上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产生的不适应引发的阵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中央政府无力对边疆实现有效治理,传统王朝松散、间接的统治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治理模式。“东南海防报警来”“西南边疆起衅端”“西北边疆狼烟有起”,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因而,要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仅从民族本身出发开出来的药方,治标但不治本,只有抽离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关系历史性转变。具体而言,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转型时代的中国涌现出的民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目标,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分裂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来瓦解中国的图谋全部失败,肃清了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外部根源,民族问题更多体现为民族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改革、民主改革等手段,铲除了阶级压迫的根源,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实现了全面平等,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厘清基本逻辑,在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安全稳定。
二、道路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道路自信首先来源于道路选择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同时,从百年党史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具有政策的连续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这种特殊的历程为我们树立坚定的道路自信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主线的连续性
(1)革命时期以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为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的解放始终居于核心位置。中共二大、三大宣言中提出要实现人民解放。红军长征时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实现弱小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和独立是核心表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条件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解放和独立话语更多集中在中华民族层面,小民族的民族自决得到摒弃。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谈到:“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各时期面临的问题和局势各不相同,但追求人民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主线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2)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时期以人民的平等和团结为核心。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成员要实现一律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大团结成为党在过渡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谁不承认和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7]《共同纲领》中第五十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宪法对民族平等、各民族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等做了专门规定。1957年召开的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民族权利等问题都做了系统说明,主要内容聚焦如何落实民族平等、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友爱等主题。
(3)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的富裕和繁荣为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发展成为中心任务,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所变化,民族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1981年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8]其后历届领导集体对民族政策的主线均做过论述,但促进各族人民的发展和繁荣一直是核心主题。
(4)十八大以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问题也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亦在不断发展,民族政策由发展和繁荣等主线逐步转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体体现在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中。从“十二个必须”的内容看,民族发展被放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行系统考察,民族发展不仅指经济发展,更强调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调统一,在各方面协调发展中最终实现各民族、各民族中的个体成员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政治平等方面,涉及民族平等的原则性、总体性纲领的坚持,也包括用民族区域自治、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等刚性的制度约束来对民族平等进行有效保障,同时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的核心力量。在经济繁荣方面,依然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进步方面,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精神发展方面,凸显了各民族共享的精神文化符号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还特别注重通过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来看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此外,“十二个坚持”还特别凸显了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国家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关系,只有在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安全的保障基础之上,个体的自由、安全发展才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
(二)牢记使命:以国家复兴为核心的理想信念的连续性
(1)以革命建国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开展,改良主义、立宪主义、技术救国等各种国家建构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得以成功。民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多元和一体的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主要任务要服务于党的革命建国的主要目标。如何通过民族政策来凝聚人心,积累更多的革命力量是考察民族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党在初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通过宣传民族解放来号召边疆地区人民反抗压迫,压迫是超越民族的,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反抗实现革命建国是主要目的。“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蒙古族农民以反抗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淹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工农兵大联盟,要能联合内蒙古农民的斗争。”[9]抗战时期,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日成为中心任务,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政策所涵盖的人群不仅包括少数民族的被统治阶层,而且包括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是在于团结各民族于一体,共同对付日寇。”“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10]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党的中华民族观进一步成熟,通过民族政策来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革命事业成为中心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主要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任务。刘少奇把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放置在当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上看。“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6]136从政策实践看,民族识别构建起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民族秩序,在此秩序基础上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论,既保证了新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如统一的制度、宪法、政府设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合理解决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传统的保护,实现了统一与自治的统一、区域与民族的统一,有效推动了新中国政权的稳固发展。民族地区的“三大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数年努力,各少数民族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为国家建构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得以在一致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快速推进。
(2)以发展富国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的重心开始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民族政策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类型,制度的价值导向开始以发展为核心,通过制度引导调整生产关系,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在民族工作中,民族地区被赋予更多发展的意义,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大家都要做国家四化的促进派,做加速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派,而不要做中间派,更不允许做反对派。现在民族工作战线内外,有一些同志认为,少数民族的四化与民族事务单位关系不大,或者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11]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始终贯穿着发展的主线,对民族工作部门的工作重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要发挥的经济优势等做了明确规定。
(3)以治理强国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号角。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依托和实践基础,着力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主要体现在治理的系统性方面。系统治理要求把民族问题放置在整体的角度来分析,处理民族问题要求用系统思维,强调在各种关系纠葛中看待民族问题,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来处理民族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看待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国内与国外的结合重新定位民族工作在国家能力提升中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等,本质上都是运用关系思维来重新审视民族问题。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既包含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国际环境对民族问题的产生也有密切联系。源头治理就是追根溯源,厘清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发展阶段。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中,特别强调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观念,同时把民族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在具体方式上,既通过消除经济发展差距来解决民族问题,又通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来促进共同性的增长,兼顾了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国家与国外、精神与物质等根源。
三、道路实践的有效性
衡量一套制度体系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要考察其产生的制度绩效如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自信的确立,除道路选择的必然性、道路发展的连续性之外,道路实践的有效性或者制度绩效优势也是中国道路的“底气所在”。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适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为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政治绩效
(1)个体权利的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实现没有很好的社会基础,尤其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个体的婚姻自主权、发展权、选举权、教育权等,甚至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三大领主占据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占有农奴的人身,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政治压迫。“农奴如果触犯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农奴‘向王公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击之;不受主人约束者拘捕之;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13]
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西藏民主改革61年来,妇女在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西藏自治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至63.68/10万和8.9%,而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孕产妇死亡率高达5000/10万,婴儿死亡率为430%。经济层面,随着西藏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藏族人民的健康权和发展权均得到有力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7岁。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100万增加到现在的300.2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4万人,占90.48%。[14]
(2)群体权益的维护。群体权益的维护必须要依托公共权力的使用,群体必须要参与到国家权力体系的分配中,才能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国家权力结构中首次纳入了少数民族,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结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少数民族干部比例等,少数民族有表达本民族诉求的合法路径。再如,民族识别工作为各民族权利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重大意义应该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思想序列,新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变的全局性、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经过几个阶段的努力,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得到廓清,少数民族第一次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合法地位和身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中国的民族关系自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国家安全的维护。民族政策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关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发展,与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国家运用制度和政策体系来协调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解决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分离主义风险,通过民族政策体系和民族工作实践来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从而维持国家的完整性,应对国外反动势力对国家的颠覆。可以说,民族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反分裂意义。具体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地处理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之间的张力,通过新的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转形式来维持国家稳定的同时兼顾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的武器,其意义首先在于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有力维护了中国特色的单一制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维护了国家统一。”[15]
以新疆为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取得巨大成就。政治方面,新疆各族人民有效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提高,基层群众自治依法推进;经济层面,平等享有经济发展权,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持续提升基本生活水准;文化方面,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全面保障受教育权。“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是确保新疆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16]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屡屡发表新疆人权的不实言论,在“新疆棉花”等方面诋毁污蔑党的民族政策,而上述几十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成就是对西方反华势力的最好回击。
(二)经济绩效
(1)从区域经济发展成就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的贸易存在物资交流不畅、欺诈贸易横行、价格体系不透明等问题,经过数年努力,民族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复苏,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产量和牲畜头数,一九五七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分别增长了62.9%和141%。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业总产值,由一九四九年的5.4亿元增长至一九五七年的29.5亿元;增长了4倍多。[17]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民族地区经济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极大飞跃。从1979年到1988年,民族自治地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为820.4亿元,比1950年到1978年28年中总投资580.52亿元还多239.88亿元。1988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092.33亿元,比1949年的36.6亿元增长19.5倍。从1981年至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10.0%,超过民族自治地方“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2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6.6%的发展幅度。[18]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计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计划的开展,民族地区迎来发展新机遇。2004年,民族八省区国内生产总值13710亿元,较2000年相比,年平均增长13.05%,这一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同期年均11.06%,民族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自2000年的9.11%上升到2004年的19.59%,且逐年递增[19]。十八大以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更加凸显内涵式发展特征。截至2019年,民族自治地方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达到84027亿元,占全国的8.48%。从增长看,2001年到2019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民族自治地方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0]
(2)从个体收入提高看。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6元增加到2009年的14070元,增长了46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增长了27倍多。民族八省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01年的3076.8万人下降到1452万人,部分少数民族已实现整体脱贫。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后,2009年边境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2000年相比增长117.5%。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效果。2012年至2018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从3121万人减少到60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8%下降到4%,脱贫攻坚取得重要突破。[2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民族地区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产业结构趋于科学合理,发展潜力得到激发,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生活的各项指数朝着良好态势发展,少数民族生活幸福感得到有效保障,完整体现了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体系的经济绩效。
(三)文化绩效
(1)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从建党之初,我党就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被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国务院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员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等十多种政策、条例、指示,保护和传承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尤其对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意义重大。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2009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今后发展的任务、重点、政策措施等。经过数年努力,从中央到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了文化馆、图书展、出版社、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电视台等文化机构。此外,还为牧区提供流动文化车、汽车博物馆、流动剧场等。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情况看,我国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3068人,其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为855人,占总数的27.87%。除了普米族和高山族两个少数民族没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外,其他民族均有,其中藏族非遗传承人数量居于首位,为182人,其次是蒙古族93人、苗族64人、维吾尔族53人、土家族46人、回族45人、满族38人、彝族37人、侗族31人;再次是瑶族22人、哈萨克族18人,壮族和傣族都为17人,布依族和土族都为14人,朝鲜族11人,柯尔克孜族、白族和黎族都为10人等。[22]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不论在整体的制度设计、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文化的传承保护的实际效果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部分,随着时代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也在不断传承创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表现,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科学性、实践性的有力证明。
(2)推动中华文化延续创新演变。民族文化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建设,推动整体层面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体而言,民族文化政策在促进文化共同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政策体系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同时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创造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各种文化在交融中发展创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最终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资源和内部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市场化的冲击,如何使带有鲜明区域特征的民族文化走向全国,在动态的演变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民族文化积极适应时代的必然命题。以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例,单一民族的文化展示多体现特殊性,而将多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放置在同样的统一的、具有联系性的体系之下,进行结构性的编排,来体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异彩纷呈的历程,更能引发观众对中华文化的新认识,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要定期举办大型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从1980年开始我国成功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001年、2006年及2012年分别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及第四届。2016年第五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其中将彝族、仡佬族、怒族、土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6首不同风格的敬酒歌融为一体;白族的八角鼓、满族的太平鼓、瑶族及朝鲜族的长鼓集合成了《幸福鼓·中国梦》最受观众欢迎。观众不仅感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加了解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之后蕴含的巨大艺术价值和潜力,兼具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整场晚会以一体中的多元为主线,展现了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反响。
总之,民族政策的文化绩效考察,一方面要基于民族政策在保护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如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各民族在民族政策的引导下,促进各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如何。在百年党史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由于时代任务不同,民族政策所产生的文化绩效也应具体结合时代问题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更重要的是赋予各民族平等的地位,各民族文化的保护成为工作重点;改革开放后,要研究民族政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什么作用。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要衡量其在促进各民族碰撞交融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考察民族政策在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如何。
四、结语
道路选择的理论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解决的是道路的起点问题;道路发展的连续性主要关注的是道路的发展过程;道路实践的有效性讨论的是结果问题。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论述,可充分说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性、正确性,它对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史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的改进,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中,完善政策和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的新要求,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是在充分肯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基础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尤其关于“四对关系”的论述,把民族事务治理放置在国家治理的系统层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进行考察,是对道路实践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升级。
注释:
①主要有张淑娟的《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李春琳的《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光辉历程》,《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杨顺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深刻内涵》,《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王德强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内涵与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