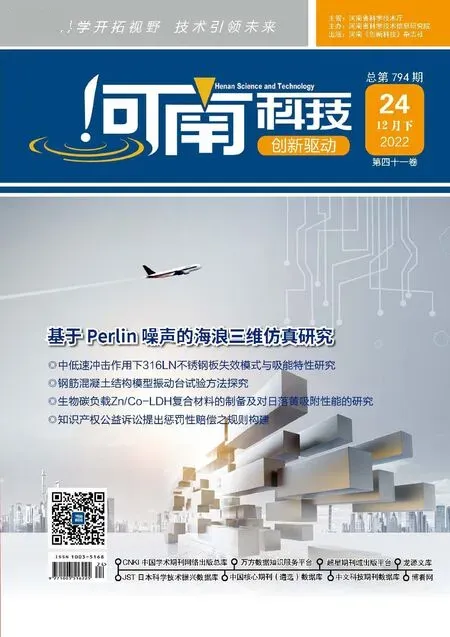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之规则构建
2023-01-21陈淑清
陈淑清
(开平市人民检察院,广东 开平 529300)
1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现状
1.1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实践现状
2001年的“乌苏里船歌”案,为保护公共领域的民间艺术作品做出了成功尝试;2005年,五位教授质疑以飞利浦为首的3C联盟在华收取高额许可费的合理性,请求宣告相关专利无效。
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来新领域的不断拓展,2019年,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检察院对邓某等5人及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1]提起公诉,同时建议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对某公司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主张涉案金额三倍的惩罚性赔偿。202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状告中国知网擅自收录其100多篇论文,获赔70多万元,著作权保护与知识资源的提供、公众的合理使用权与垄断等问题再次导入舆论。
1.2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理论现状
有学者认为,受保护的知识产品最终进入公共领域,让公众自由利用,专有领域和公共领域是存在于知识产权法中的两大领域。有学者认为,假冒注册商标不仅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亦有学者认为,对公有领域资源主张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垄断的行为。
笔者认为,当知识产品进入公共领域后,即变成社会公众自由使用的资源,对公有领域内的资源主张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的行为,是变相将公有权转化成私有权,将其重新纳入知识产权专有保护的领域,这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打破了专有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平衡。
2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2.1 弥补禁令、损害赔偿的不足
禁令是指命令侵权者停止实施违法或不当行为,能够制止不当行为继续造成损害或预防不当行为的产生,如停止侵害。知识产品可复制、传播快的特点导致侵权行为极易发生,禁令只能制止侵权者继续实施侵害知识产品的行为,对已造成的损害却无能为力。
损害赔偿是指加害人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被侵害人请求加害人承担财产上或特定情况下的非财产损失[2]。其目的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而一般不具有惩罚性。损害赔偿有利于恢复受害人因侵害行为而减少的财产,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使受害人回到“倘若损害事件没有发生时应处的状态”[3]。赵德馨教授状告中国知网擅自收录论文案引发的相关热议显示,博士论文作者可一次性获得面值400元的检索阅读卡和100元稿酬(硕士论文为300元阅读卡和60元稿酬),但文章每次被下载,平台就会收取15元/本至20元/本的费用,论文作者却完全不知情,这表面上是“强制授权”的霸王条款,实际上却是对智力成果的垄断。对侵权者主张损害赔偿可以恢复受损者因侵害行为而减少的财产,因其不具有惩罚性,无法对侵权者产生威慑作用,而惩罚性赔偿则可以弥补禁令和损害赔偿的不足。惩罚性的赔偿,指判定的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原告人的补偿,而且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4]。因此,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确有必要。
2.2 英美法系国家提供的域外借鉴
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规定有反托拉斯行为的,处于不超过最高数额的罚款;《克莱顿法》也规定以托拉斯形式共谋的,处以三倍的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原告提出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件并不罕见。在2001年美国犹他州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承担1.45亿美元的巨额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性赔偿,联邦上诉法院的判断条件是“被告的品行是否显示出对其他社会公众的健康或安全的冷漠和鲁莽无视”或“重复实施了这种侵害行动”[5]。虽然美国通过巨额惩罚性赔偿惩治恶意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但数额“非常过分”,违反正当程序条款时,法院会对惩罚性赔偿的合宪性加强审查。
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设立之初适用于大部分侵权案件,到20世纪60年代,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受到了限制。英国1988年的《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规定,侵犯版权或外观设计的纠纷中,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人侵权的恶意程度,以及被告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并基于案件公正的要求,判决附加性损害赔偿金。为了防止自由裁量过度,英国规定法院在裁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考虑欧洲人权公约的准则、存在不特定多数的原告、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恶意程度以及获益等因素。
2.3 与现有法律体系相适应
《商标法(2013修正)》第六十三条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倍数幅度为一倍以上三倍以下。《商标法(2019修正)》第六十三条将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据该规定,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故意和情节严重的客观后果。著作权法、专利法领域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如《著作权法(2020年修订)》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故意侵犯著作权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专利法(2020年修订)》第七十一条也规定了故意侵犯专利权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202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情节认定、赔偿数额以及倍数。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有些学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八条没有明确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也有学者认为,侵害知识产权损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如江苏消协对邓某城、厦门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起消费者权益民事公益诉讼,主张涉案金额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笔者认为,虽然《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为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案件,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民事侵权案件,侵权者的行为符合《民法典》《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起诉主体就可依据相关法条主张权利。
3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规则构建
3.1 厘清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202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对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做出大致归类。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中的公共领域可以界定为可以不受知识产权人控制、限制且可以自由地接触和利用的部分[6]。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中保护“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的法律精神,笔者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做以下分类。第一类,侵犯知识产权又损害其他公益领域的,如邓某等5人及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民事公益诉讼案,邓某等5人及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在刑事上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因损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都属于消费者保护安全领域。第二类,侵害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公有领域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但公有领域一般涉及公共利益,因此,侵害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案件理应属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如利用保护期限届满或被宣告无效的知识产品重新申请专有权保护涉嫌垄断的行为。第三类,控制、限制公众特定使用的行为,如中国知网擅自收录论文、收费下载阅读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教授的著作权,还损害了公众读者的合理使用权。第四类,损害包含公共利益的知识产品,如非法编撰或丑化历史名人、英雄的作品,非法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等作品。
3.2 规范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3.2.1 双重构成要件说。该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同时符合“恶意(或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个要件。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上,“恶意(或故意)侵权”是主观构成要件,“情节严重”是客观构成要件。因“情节严重”关注行为方式和后果的严重性,通常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7]。而侵权地域广、长时间侵权、多次侵权、影响力大、损害后果严重等均属于“情节严重”的表现情形[8]。
3.2.2 单一构成要件说。该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仅需满足“恶意(或故意)侵权”的主观构成要件。但为了防止惩罚过重,行为人主观上应为故意不能为过失,过失侵权施以惩罚性赔偿容易“罚不当责”。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应以故意侵权为适用条件,“情节严重”应理解为判断数额多少的条件,依赖于法官的内心确认和自由裁量[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主观构成要件和客观构成要件相互影响,互为表现形式,为了防止惩罚性赔偿被滥用,应同时考量“恶意(或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种因素。因此,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应采用双重构成要件说。
3.3 明确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
在前文论述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前提下,又同时符合“恶意(或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个构成要件,即可适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
3.3.1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按“实际损失”“所获利益”“许可使用费倍数”的顺序予以适用。第一顺位“实际损失”是指因侵权行为的存在,权利人实际获得的利润与假定没有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10],这符合民事侵权赔偿的填平原则[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对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何为被侵权受到的损失进行细化解释。与知识产权私益诉讼不同的是,知识产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受损的公共利益,由于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无法确定受害者的总数,“实际损失”难以量化。第二顺位“所获利益”是实施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但侵权商品数量、利润等证据难以举证。因此,《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均有被告不提供侵权相关材料,法院可以原告的主张和证据判定赔偿数额的规定。第三顺位“许可使用费倍数”主要根据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许可使用费标准予以确定,单一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可以为“许可使用费”提供直接证明,而包含多种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合同,如北京同仁堂有限公司诉黄卫东商标侵权纠纷案,许可使用合同中包含9个商标、30种药品,对于该案的1个商标、1种药品不具有参照性。
3.3.2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最新修订的《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均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是知识产权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将其用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否合理?在广州市检察院提起的四起生产、销售假盐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广州市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提出十倍惩罚性赔偿并获判决支持。美国的惩罚性赔偿金遵循“比例原则”,以避免过度赔偿。亦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可以参考侵权人的侵权动机与目的、是否重复侵权、恶意的程度、侵权后果等因素,程度越严重倍数越高[12]。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按照“实际损失”“所获利益”“许可使用费倍数”的顺位予以确定,虽然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幅度较大,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任意作出裁定。当“实际损失”“所获利益”“许可使用费倍数”逐一无法确定时,法院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幅度内确认。
3.4 优化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后续处理
有些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为了维护众多消费者损失的权益而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应赔付给消费者,其不同于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直接上缴国库。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陈东强、李明明认为,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处置方式主要有上缴国库、设立基金和法院托管,其中第三种符合诉讼效率也便于主张。
本研究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划分为四类,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都涉及不特定的消费者或群众,第四类涉及公共文化遗产,前三类是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或群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属于有形侵害;第四类侵害的是人类传承的精神财富,属于无形侵害。对于前三类案件类型,可征集受害者,根据人数、受害程度计算比例赔偿,剩余的上交国库,作为保护消费者公益基金。对于第四类案件类型,主要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日后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等公共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维权经费。目前,较多专家支持设立基金的形式,基金由专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判决生效后,惩罚性赔偿金先提存冻结,再根据受损主张进行发放。综上所述,笔者更认同设立消费者保护基金的方式,但保护基金的管理机构、管理流程、受害消费者的征集、公示等应有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