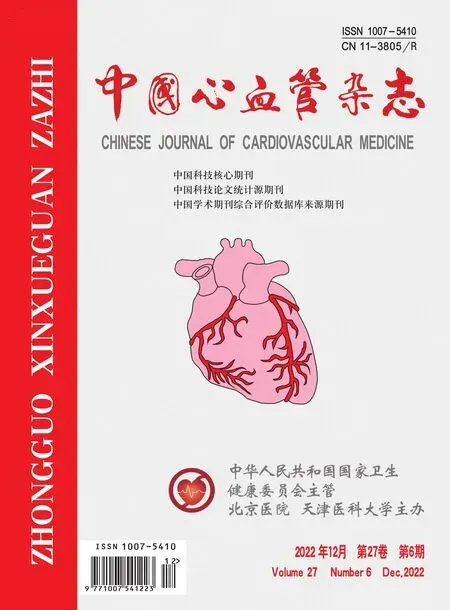经皮左心耳封堵术后器械相关血栓的诊断治疗研究进展
2023-01-21罗乾友莫丽莉杨钦宇潘竟王章兰李伟曾安宁
罗乾友 莫丽莉 杨钦宇 潘竟 王章兰 李伟 曾安宁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成人心律失常,如不治疗,发生脑血管和全身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将增加4~5倍[1]。AF在不同年龄段的患病率不同,随年龄增长,患病率逐年增加[2]。AF的主要危害是在左心耳处易形成血栓,并易脱落导致心原性脑卒中或系统性血栓栓塞。大量文献资料表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NVAF)患者的血栓90%以上来源于左心耳[3-4]。目前,对于NVAF患者(CHA2DS2-VASc评分≥2分)采取药物抗凝是防止卒中发生的主要治疗策略,但由于有出血风险增加、患者依从性差、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及经济问题,大多数患者不能长期坚持抗凝。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实践和研发设备逐步完善,经皮左心耳封堵术(percutaneous closure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PCLAA)已成为NVAF患者的一种安全有效的非药物治疗选择[5],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在多个注册研究中得到充分证实[6-7],并被多个国际指南推荐用于预防AF卒中的治疗[1, 8-9]。然而近年来,随着对PCLAA不断深入研究,其术后并发症(如心包积液、心脏压塞、封堵器脱落和封堵器残余漏等)越来越受关注,特别是PCLAA术后器械相关血栓(device-related thrombus,DRT)的发生已成为临床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之一,DRT的发生会导致PCLAA术后的卒中风险增加3倍以上[10]。有关PCLAA术后DRT的诊断治疗尚存较大争议,还未形成统一的临床诊疗指南,故本文拟针对DRT的发病率、形成机制和诊疗进展作一综述。
1 DRT的定义和患病率
DRT是指医学影像检查所发现的附着在植入人体内的医学器械上的血栓,不包括围术期器械血栓事件及器械内部的血栓。本文特指左心耳封堵器植入术后在其表面形成的血栓以及因其植入而引起其他部位的血栓。
DRT是PCLAA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文献报道其患病率为2.8%~17.6%[11-13]。在国外较大样本试验研究中,PROTECT-AF研究中DRT的患病率为4.2%,EWOLUTION研究(n=835)2年的随访结果显示DRT的患病率为4.1%[14]。在国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观察研究也报道了术后早期(60 d)总体DRT的患病率为3.6%[15]。2018年,1篇纳入了10 154例PCLAA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DRT的患病率为3.8%[16]。2019年,Asmarats等[17]的研究显示DRT的患病率为3.3%(n=1 197)。2021年,Simard等[13]汇总分析了37个中心的711例行PCLAA的AF患者的术后随访资料,显示DRT的患病率为2.8%。简而言之,现有资料显示DRT在大样本试验中的患病率是比较低的,只是在小样本(n<50)的试验研究中比较高,Plicht等[12]曾报道DRT的发病率高达17.6%。DRT患病率的研究报道高低不一,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大多数试验研究的样本量较小;(2)超声医生的技术水平;(3)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DRT影像学诊断共识或指南;(4)患者术后是否规律服用抗凝药物;(5)随访经食道超声(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的频率、完整性和解释。
目前,相关文献报道DRT的平均患病率为3.4%[16],这看上去确实是比较小的一个概率(P<0.05),但有研究报道DRT的形成可能会导致卒中风险增加3倍以上[10],这使得心脏介入医生和器械研发人员不得不去关注DRT的发生,并且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预防或减少DRT的发生。最新研究显示,使用新一代的Watchman FLX封堵器的DRT患病率为1.75%[18],这提示随着设备技术不断改良,PCLAA会让更多的AF患者得到更好的临床获益。
2 DRT的形成机制
关于DRT的形成机制还没有明确统一的定论,封堵器械植入后器械表面的内皮化进程及凝血系统反应性激活是目前DRT形成机制中比较具有可信度的研究结论。
一些学者使用动物实验观察不同左心耳封堵器表面的内皮化进程。Schwart等[19]使用Watchman封堵器植入犬模型的左心耳3 d后,封堵器心房面即开始出现纤维样蛋白膜的附着;45 d后,心内膜完全覆盖封堵器所有暴露的表面,并与左心房表面相连续;90 d后,新生的内皮组织和纤维结缔组织膜完全覆盖封堵器表面。Bass等[20]在犬模型中使用ACP封堵器进行封堵,封堵器在植入后90 d即被新生组织内膜覆盖。与上述实验结果相似,国产LAmbre封堵器植入犬模型的左心耳1个月后表面形成内膜组织,3个月后则完全内膜化[21]。Tang等[22]研发的LACbes封堵器在犬模型中实验结果显示,植入后4个月内封堵器左心房盘面达到内皮化。因为犬类左心耳的解剖结构与人类大致相似,故以上4种不同封堵器实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左心耳封堵器在人体的内皮化过程。综合动物实验结果,不同类型封堵器装置在植入后90 d可达内皮化,这与临床上推荐的PCLAA术后进行抗栓治疗的空窗期相吻合。但需要阐明的是,以上数据均是统计平均值,且存在患者个体差异,同时受封堵器植入后形态大小、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封堵器的内皮化所需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别。因此,PCLAA术后的患者需要根据临床实际制定个体化方案来预防DRT的发生。
DRT形成的另一机制可能与凝血系统反应性激活相关。目前,左心耳封堵器主要材料是由镍钛合金和聚酯纤维覆膜组成[23],对于AF患者,封堵器无疑是异物,在其植入左心耳后内皮化过程中会伴随着体内凝血系统反应性激活。Rodés-Cabau等[24]检测了43例患者PCLAA术后的凝血功能变化,结果显示PCLAA与凝血系统的显著激活有关,凝血活化的标志物凝血酶原片段1+2和凝血酶原Ⅲ水平在术后7 d达到峰值,并在第30天部分恢复到基线水平,而在PCLAA术后180 d,仍能检测到凝血激活的标记物有轻微的增加。这提示了PCLAA术后患者存在着凝血系统短暂性激活,需要采取药物抗凝措施来预防DRT的发生。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也只关注了血液指标、未设计试验对照组,对于器械植入术后能否用相关凝血物质的检测来预测DRT的形成,未来还需更多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数据来支持这一结论。
3 DRT的诊断
目前临床上DRT的诊断是通过影像学来实现的,临床常用的影像学随访方式有TEE和心脏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两种。在临床实践中通常把TEE作为PCLAA术后首选的影像学随访方式,只有当TEE不可用或存在禁忌证时才考虑CT作为随访备选方案[25-26]。不过,对于PCLAA术后何时进行影像学评估尚无共识,Glikson等[4]建议术后6~12周使用TEE或CT对有无DRT进行评估,而最新影像学随访研究数据显示大多数(64%)DRT在PCLAA术后180 d确诊,并随着随访频率增加DRT的确诊率也在增加[13]。这提示影像随访医师在PCLAA术后6个月内应对患者进行多次随访。
TEE随访诊断DRT的标准,现临床上主要参照PROTECT-AF研究[27]提出的在TEE下DRT的表现特征:(1)器械左心房面存在高密度回声;(2)成像伪影不能解释;(3)与正常愈合或器械影像表现不一致;(4)在TEE的多个平面可见;(5)与器械相连接。除此以外,在随访期间要特别注意区分组织的“生理”生长和血栓的“病理”形成,器械上的生理组织覆盖层仅由薄薄的组织层组成,任何增厚或突出的部位应视为病理发现[28]。根据相关文献报道,血栓形成的首选部位通常是装置周围的小间隙、壁龛或未覆盖的肺叶、具有低血流量和突出的装置结构[16, 29],如螺钉[30]。这提示超声医生在随访期间应着重关注这些地方,以便及早诊断DRT和尽早开启或加强抗凝治疗。
对于一些无法耐受、有禁忌证或拒绝TEE检查的患者,CT也可作为PCLAA术后影像学随访的备选方案。DRT在CT中表现特征为封堵器心房面出现造影剂的充盈缺损征象。2019年,Korsholm等[31]回顾了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医院进行左心耳闭塞的301例患者的CT影像表现。以TEE为参考标准,将封堵器心房面的CT影像表现按衰减度增厚(hypoattenuated thickening,HAT)分为低等级HAT和高等级HAT,并定义了DRT的CT影像学标准:(1)封堵器心房面出现层状的HAT且厚度大于3 mm;(2)封堵器心房面带有蒂或不规则;当CT影像表现低等级HAT时,可能提示封堵器表面正在进行良性、平稳的内皮化过程[32]。同时得到CT在检测DRT方面似乎与TEE一样好的结论。然而,Cochet等[26]分析了117例PCLAA术后患者的CT影像,结果发现有19例(16%)可能存在DRT,随后TEE检测确认了其中5例,另外14例由于封堵器表面回声厚度<1 mm被认为是封堵器表面的内皮化组织。这与Korsholm等[31]得出的结论不大相符。因此,CT和TEE对DRT检出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以及两者之间的优劣性仍需更多临床数据和专门设计的“头对头”研究进行比对。另外,由于对比剂肾病的发生风险较高,对于有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不建议采用CT随访。
4 DRT的治疗
由于DRT的存在与卒中风险的增加有关,在确诊后应立即开展治疗。目前,DRT发生后的抗栓治疗还没有统一的方案,对于术后采用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应换用或加用抗凝药物治疗。关于DRT药物治疗的数据有限,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和口服抗凝剂(oral anticoagulants,OAC)。Lempereur等[16]对30项关于DRT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并对治疗策略进行了总结,其中45.5%的患者采用LMWH平均治疗2周,36.4%的患者采用口服华法林平均治疗3个月。随访TEE显示,采用LMWH治疗的患者DRT获得100%溶解,采用华法林治疗的患者89.5%的DRT溶解。此外,对于肾功能不全不适合应用LMWH的患者可选择静脉注射肝素以达到溶解DRT的目的。尽管缺乏临床数据支持,一些个案和小样本研究报道显示新型口服抗凝药(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NOAC)阿哌沙班(小剂量)和达比加群可有效治疗DRT[33-36],但数据有限,尚不能支持循证医学的检验,需后期更多相关研究数据论证。Saw等[37]总结了目前DRT的治疗策略,建议首先推荐华法林治疗8~12周,维持INR在2.0~3.0;对于已经在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建议维持INR在2.5~3.5;也可推荐最大耐受剂量的NOAC治疗8~12周,优先选择阿哌沙班、利伐沙班,避免使用达比加群;在检测到DRT后必须进行密切的TEE随访:建议在初始治疗2周后进行LMHW治疗的随访TEE,否则在开始使用其他抗凝药物治疗8~12个月后进行随访TEE。在确认血栓消退后,需要继续随访,因为血栓形成可在确认血栓消退后14个月内再次出现[17, 37]。如果抗凝治疗仍然无效,或DRT存在时出现复发性栓塞,或血栓非常大,则应考虑手术清除血栓[38]。
5 小结
综上所述,经皮PCLAA术后DRT的平均总体发病率较低,但DRT一旦形成会使行PCLAA的患者缺血卒中风险增加3倍以上,而在老年患者风险会更大,因此术后患者应积极进行TEE或CT随访,这有助于DRT的尽早发现和治疗。对于随访发现DRT的患者应当立即重启或延长抗凝治疗。目前对于DRT的形成机制中凝血系统反应性激活的实验数据比较少,需更多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数据来支持这一结论。CT在PCLAA术后随访中的应用正逐步展开,相信随着经验不断积累,CT在检测诊断DRT时会与TEE一样适用。未来,可以重点研究DRT的形成机制,从源头上解决PCLAA术后患者DRT的形成,提高PCLAA的临床获益。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