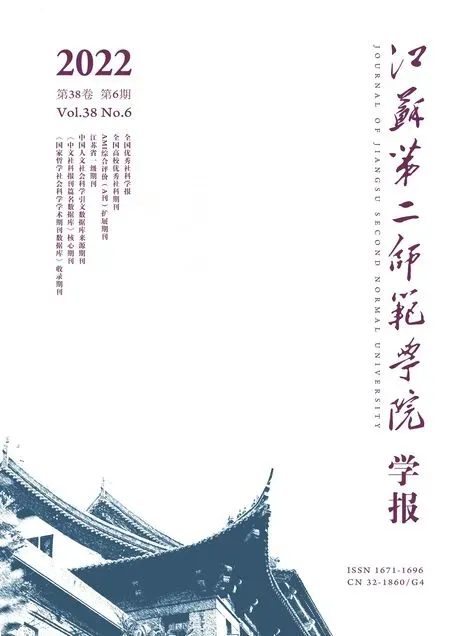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二七”纪念媒体传播研究
——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例
2023-01-20卢鹏俞祖华
卢 鹏 俞 祖 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烟台 264025)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为保障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以及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了实现“争民主,争人权”的目标,高擎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七”大罢工,由此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在此危机形势下,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通过刊发领导人讲话、发表文章和社论以及报道纪念大会盛况等方式,对“二七”运动进行了纪念活动。著名专家陈金龙先生指出,“纪念既是一种文化,寓文化于活动之中,又兼具传承文化、生成文化、传播文化的功能”[1]。总体上,学界对于“二七”纪念与“二七”精神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前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于“二七”纪念的著述,而对新时代下“二七”精神的传承以及现代中国革命与“二七”这一政治符号的联系方面,特别是对全面抗战时期“二七”纪念媒体传播的研究则显薄弱,值得做深入研究(1)目前学界主要代表性成果有:李良明,黄飞《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大革命失败前的“二七”纪念》,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刘莉《政治符合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刊于《民国研究》,2017年第1期。。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央机关报对“二七”纪念的宣传报道
全面抗战时期,为更进一步强化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新闻宣传工作,《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作为当时党的机关报,充分发挥其媒体传播作用,在“二七”纪念日前后,对于“二七”纪念的宣传报道,主要是通过发表党内重要领导人的纪念文章、刊发社论以及报道“二七”纪念大会盛况等。
1.刊登党内重要领导人的文章
每当到重大革命活动纪念日或是每逢重要节日之时,在党报党刊等媒体公开刊登党内重要领导人的文章是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刊登了张浩同志的“二七”专论“‘二七’与抗战”,该文总结了“二七”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在抗战中吸取经验教训[2]。1941年2月6日,《新中华报》刊登了林伯渠同志的“纪念二七,坚决保卫边区”,指出“今天纪念伟大‘二七’纪念节日的时候,必须把保卫抗战全国策源地的边区的任务,当作空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严重的政治任务看待”“真执行保卫边区的各种工作”“团结抗战才是全中国人民所应该走的大路”[3]。1941年2月9日,《新中华报》刊发了邓发同志纪念“二七”的文章“发挥‘二七’精神反对反共投降亲日派”,文章指出“今年我们纪念‘二七’,更要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彻底性、坚持性、组织性,全国工人要更加团结起来,团结一切抗日人士、反对反共内战,反对进攻新四军,反对进攻边区,全国友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致并肩对日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贯彻‘二七’的革命精神,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4]。1943年2月7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刊登了邓发的文章“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指出继承“二七”光荣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困难与接近胜利的关头,必须团结一致,熬过难关,发扬“二七”英勇斗争精神、争取最后胜利,特别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的工人阶级,更应热烈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来纪念“二七”,让每个工人起来学习赵占魁,来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5]。1943年2月7日,《新中华报》第二版刊登了立人同志的纪念文章“为生产而战为学习而战”,向工人同志们阐述了当年纪念“二七”的意义:一方面要加紧生产,达到丰衣足食,强壮我们的身体;另一方面还必须要加紧学习,武装我们的头脑,为提高技术、文化、政治认识,消减落后意识而斗争[6]。1944年2月7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和第二版连载崔田夫的“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介绍并分析了赵占魁运动开展的经过与近况、赵占魁运动使边区公营工厂发生了什么变化、赵占魁运动的经验总结以及今后应如何坚持与提高赵占魁运动[7]。
2.刊登社论
在1938年至1945年间,《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每年“二七”前后会刊登社论来纪念“二七”,从而宣传党在当前局势下的政治路线及方针政策。
1938年2月10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刊发社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刊登了边区总工会的三条纪念宣言:“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中国工人的组织统一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争”“拥护苏联的工会与第二国际工联联合反法西斯反战协定”[8]。1942年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刊登的社论《“二七”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经验教训》,鼓舞中国工人阶级继承“二七”斗争的精神,接受和学习“二七”的宝贵教训,继续和发挥“二七”为自由为人权而战的奋斗精神,为全民族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自由而奋斗,锻炼无数忠实于国家民族、忠实于阶级的战士和党的骨干,组织中国工人阶级一致起来,反对侵略中国的法西斯强盗日本帝国主义[9]。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刊登的社论《为独立与民主而战,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指出在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解放区内,职工们已获得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完全摆脱了从外部敌人及内部反动派所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但是中国职工除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之外,在其他地区依然是没有民主和自由的,争取抗战胜利与实行人民民主是不可分的,并且也指出了成立各解放区职工联合组织——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10]。
3.报道“二七”纪念大会盛况
全面抗战时期,在各级党组织、政府,工人团体的组织下,各地解放区都采用多种方法和形式来开展“二七”纪念活动。《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通过对各地解放区“二七”纪念活动的及时报道,使得各地“二七”纪念活动的盛况得以广泛传播,扩大了各地解放区“二七”纪念活动的影响力。
1940年2月28日,《新中华报》刊发了陈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工人阶级需要组织,华北战区工人已经建立了工会,他们要联合起来组织战区工人联合会”来“加强华北抗战力量”,并且还“可以增加沦陷区及全国工人的力量”[11]。《新中华报》还刊登了吴玉章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今年纪念“二七”的主要意义,一方面“纪念工人牺牲的烈士”,另一方面“使党员同非党员懂得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前途远大”[12];在第五、六版刊登了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讲话说明了“二七”惨案的历史,论证了“二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与中国职工运动上之意义,指出了纪念“二七”与开展职工运动的联系[13]。同日,还刊发了朱宝庭在“二七”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每个同志都要作职工运动”“好好利用罢工这个武器”“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将来要像苏联一样,求得最后解放”[14]。1942年2月9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于2月7日下午五时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边区工人“二七”纪念大会盛况,延安附近十余工厂工人千余名参加了纪念大会,纪念大会还邀请了朱德总司令、职工运动的领袖邓发、朱宝庭等同志,大会开幕后朱总司令号召边区工人,学习苏联工人热爱祖国的精神,老工人领袖朱宝庭同志讲述边区工人已获得了民主自由。大会通过了致全国工人、各民主国家工人以及南洋华侨工人的通电,随后公演《它的城》《辕门斩子》《贩马计》等戏剧节目[15]。1943年2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7日下午六时延安附近各工厂二千余名工人在边参会大礼堂参加“二七”纪念大会的盛况,有首长及工人领袖的演讲,有总工会高主任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讲话,晚间有由大众俱乐部主持、中央印刷厂演出的评剧[16]。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报道了2月7日边区被服厂全体工人举行的“二七”纪念会,高长久同志总结并宣布了三点开会的意义,在为“二七”死难烈士静默三分钟及唱国际歌后刘少奇同志发表讲话,随后邓发同志围绕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中心意义发表讲话,赵占魁同志也做了报告。在纪念大会上还报告了相关时事,并举行生产节约动员大会,该厂厂长号召全厂工人以今年生产节约七百石粮食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二七”[17]。《解放日报》还报道了中央印刷厂全体职工在7日晚集会纪念“二七”,祝厂长致辞中,强调大家不要自满,今年要以更大的努力迎接新的任务,响应工会的号召,开展更广泛深入的赵占魁运动,向劳动英雄看齐,各人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随后工人们进行了游行,最后该厂工人同志表演自己排演的评剧《牧虎关》《武家坡》《打渔杀家》及《恶虎村》[17]。
二、中央机关报对“二七”精神的弘扬传播
重大革命事件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纪念价值”,因为它有着被后来的人去“继承”以及“弘扬”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能够反映事件本身的“精神内涵”,并且凸显出它的“当代价值”[1]。在日寇大举侵略、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中央机关报宣传报道“二七”纪念,期望借助“二七”纪念,构建并宣传“二七”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广大民众振奋精神、弘扬“二七”精神完成神圣抗战的使命。在抗战的语境下,《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将“二七”纪念的基调定位为:着眼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宣传“二七”斗争的反帝爱国精神;着眼于发展民主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宣传“二七”斗争的反封建民主精神;着眼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二七”斗争的团结精神。
1.宣传“二七”斗争的反帝爱国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是全面抗战时期最大的敌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二七”斗争体现了工人反帝爱国精神,因此中央机关报期望借助报道“二七”纪念,着眼于中日民族矛盾,宣传反帝爱国精神。中央机关报指出,“二七”工人始终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宁死不屈,高举起“反帝”的“旗帜”,“以雄壮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进行了全国的伟大斗争”[13]。他们心怀满腔爱国主义热血,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达到了中共领导的首次工人运动浪潮的顶峰,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吴玉章在纪念“二七”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吴佩孚等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所以,工人阶级最初的斗争就是“反帝国主义”的,“二七”工人不单单遭受了封建军阀的压迫屠杀,而且也“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屠杀”,忍受着“国外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12]。因此,“二七”运动完全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帝”的“先锋”[13],显示了工人阶级“第一次自觉地、广泛地参加到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生长了一个新兴的革命的伟大的力量”[2],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核心群体。
全面抗战时期中央机关报借助报道“二七”纪念,广泛宣传“二七”反帝爱国精神,号召全国工人及民众继承“二七”反帝爱国精神,始终坚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为将深处危难的中华民族解救出来,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应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央机关报报道了“二七”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延安附近数千名工人齐集八路军大礼堂,工人们一致喊出:“纪念‘二七’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精神,打倒法西斯蒂保卫民主自由”[15]。“二七”后,工人不断锻炼自己,磨炼自身力量,在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领导作用,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下,“中国工人阶级是担负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18]。在日寇大举侵华的背景下,宣传“二七”反帝爱国精神,正是为动员工人以及民众去“专心一致地来贯彻长期的抗日军事计划”,以期“达成抗战建国工作之完成”[19]。当汪伪汉奸在香港创办的南华、天演、自由三报鼓吹其所谓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之时,在香港反对汪逆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官僚政客,而是《南华》《天演》和《自由》三报的印刷工人,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汪逆汉奸的卖国理论和行动”,随后“进行了罢工”[13]。显然,中国的工人继承了“‘二七’优良的传统”以及“奋斗的精神”,并始终站在反帝的前面。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二七”纪念号召全体工人及民众继承“二七”反帝爱国精神,向三报工人学习,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反对分裂倒退,“严斥‘倒蒋反共’的邪说”“揭破挑拨离间的阴谋”[20],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
2.宣传“二七”斗争的反封建争民主精神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汉奸集团、国民党亲日派及托派为首的“反蒋反共”、投降卖国活动日益猖獗,他们恰恰就代表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广大工人在“二七”运动中同封建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英勇战斗的精种堪称“中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模范”[12]。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二七”纪念,宣传“二七”斗争的反封建争民主精神,着眼于发展民主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
“二七”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做流血斗争的纪念日”[12],京汉路工人为争取创建总工会的权利发动罢工后,封建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采用了最残酷的手段”,他们“用断肢切臂杀头的办法对付被捕工人及我们的英勇战士”[13],致使“被压迫阶级先进战士”[13]林祥谦、施洋等同志英勇牺牲。中央机关报指出“二七”时,“工人阶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对于“阴谋压迫”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优秀代表与领袖”[13]。林祥谦就是在“二七”大罢工时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共初期“为数甚少的工人党员”,是“中共党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烈士”,是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标志性人物”[21]。林祥谦临死时“头可断,工不可开”的壮语,体现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21],也表现出了“舍生忘死的伟大的牺牲精神”“堪称万代楷模”[22]。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职工们由于“国民党政府固执一党执政”,贯彻其“法西斯军令政令”,并且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与全国进步人士所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一党专政”的建议不闻不问,“毫无诚意”,不但“障碍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扬”“损害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而且“延缓了日本法西斯死亡的时间”,从而“影响整个反法西斯胜利的来临”以及“拖长人民痛苦过程和牺牲的加重”[10]。因此,为抵制亲日投降派的卖国行为,中央机关报借助“二七”纪念,号召民众学习“‘头可断工不可复’的伟大义勇行为,至死不屈的英雄气概”[9],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
“二七”工人为获得自身解放、实现民主自由,“在第一次走上了政治舞台时遭受到极残酷的摧残”“遭遇着很恶劣的环境”,但是,他们的斗争仍然是“英勇坚决”的[13]。在抗战时期亲日派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降卖国之时,中央机关报通过“二七”纪念“公开告诉一切亲日派反共阴谋家”,“二七”时“吴佩孚萧耀南曾杀了林祥谦、施洋”,但是,“在工人阶级中”、在中国共产党里则“产生了数十万个新的林祥谦、施洋”,抗战时期“亲日派反共阴谋家消灭了新四军江南部队近万战士”,同样会“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千百万新四军的新战士”,中央机关报纪念“二七”,号召民众“继承‘二七’战士精神奋斗到底”[13]。为消灭一切“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反对一切“倒行逆施的压制与捕杀抗日人民与共产党的罪行”,中央机关报借助“二七”纪念,期望国民政府“废止一党专政”“改组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开放民众运动”“坚持抗战到底”[13]。中央机关报借助“二七”纪念动员国民斥责“不顾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之徒”的恶行,号召国民将“这些败类”予以“应得的制裁”[22]。中央机关报呼吁用牺牲自我的魄力来打倒亲日派等封建残余势力,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3.宣传“二七”斗争的团结精神
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中央机关报通过纪念“二七”,着眼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二七”斗争的团结精神。“二七”体现了中国工人“千里同轨、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23]。“二七”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能量,正是来自各地的工人组成了稳定的联合阵线,将自身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行。“二七”“启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性”[9]。
全面抗战时期,工人及民众“必须团结统一”,才能“形成自己的力量”,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形成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强大能量”[2]。工人不仅要“组织自己”“团结自己”,形成“牢不可破的统一力量”“找到自己的出路”,而且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来“争取民族解放彻底的胜利”[24]。中央机关报通过“二七”纪念发出了反对“进攻新四军”、反对“进攻边区”和反对“反共内战”的呼吁,号召全国的抗日“友军”应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并肩对日作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13]。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利益才有保障”“背叛民族利益的敌人才能肃清”“侵略中国民族的敌人才能打倒”,最后“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才能胜利地完成”[13]。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借助报道“二七”纪念果断戳穿汪伪政府等汉奸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阴谋,对于他们“破坏团结”行为进行了批评打击,号召国民应拥有强大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始终“抗战到底”,战胜“悲观失望”的负面心情,抵制“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22]。日寇及亲日派懂得“工人阶级是最坚决的反日队伍”,他们的力量是“不可无视”的,所以在各地用一切手段“破坏工人的团结”“分裂工人的统一”“拆散工人的力量”[24]。全国总工会被国民党解散后,工人“无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二七”纪念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各解放区的职工会”应该“首先联合起来”,成立“各解放区职工联合组织——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10]。在工人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日寇及汪精卫集团正加快瓦解全民族共同抗战、反动派接二连三地制造军事冲突的局势下,中央机关报号召工人及民众要“团结得血肉不可分离似的如像一个人一样”,去抵抗“日寇的进攻”,对亲日派实行的“分裂破坏政策”进行抵制,“为统一全中国工人阶级而奋斗”[24],号召全国工人在“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抗日救国和共同创造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的共同目标”及“民主集中和公开合法的方式”之下,从“行动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职工组织”[8]。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二七”纪念呼吁将“二七”团结精神传承下来,将工人运动的共同阵营及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进行强化。此外,中央机关报还报道了“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人们“得到了解放”“享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建立了工会的组织”“争取到生活的改善”“发扬了他们的抗日力量”[24]。
工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统一起来”,才能“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以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毛泽东主席强调,抗战想要获得胜利,必须使“工、农、兵、学、商”步调一致,大力“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25]。因此,中央机关报通过报道“二七”纪念呼吁民众要始终团结在一起,把离散的力量和涣散的意志汇聚起来,如果将所有“精神上的桎梏”摆脱,“振衰起敝”“团结一致”“抵抗外寇”,中华民族就能“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22]。中央机关报还号召民众“拥护国共合作”的方针,对恶意制造摩擦及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捣乱前线后方”及对国内“统一团结”进行阻挠的“阴谋家”实施“必要的制裁”[22]。
三、中央机关报宣传报道“二七”纪念的当代启示
1.坚持纪念日的宣传报道,使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纪念日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显性文化现象,是人类维护、传承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大创造,成为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方式和媒介。”[1]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始终注重利用党报党刊进行节日纪念、革命日纪念,刊登纪念文章,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构建纪念话语,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建构革命记忆。利用革命纪念日,可以沟通历史与现实,构建不同时期的不同纪念话语,宣传当时党的政治理念、实现党的政治诉求。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我们要“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6]。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7]247,红色血脉不能断,红色基因不能变。但是,红色基因不能主动遗传,只能“通过教育来传承”,所以,要想将红色基因继承好,必须“加强和创新红色教育”,坚持纪念日的宣传报道,使红色记忆永不褪色[28]。纪念活动“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和缅怀,强化了历史记忆”[29]。新时代媒体通过对重大革命事件进行纪念,来揭示“纪念对象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1],利用纪念日开展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活动,既强化了历史记忆,也传达出符合核心价值观的某种理念的价值所在,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充分发挥党媒的传播功能,使红色精神广泛流传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了党媒的作用,给予了“二七”纪念及时充足的报道,使得关于“二七”纪念的社论、纪念文章以及纪念盛况在工人团体及根据地军民中广泛传播,使工人及群众更深刻地了解了“二七”精神,对党强化工人团体以及边区军民的精神教育和团结工人及民众力量、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体现出了党媒强大的号召力。
在今天,新时代党媒应继承《新中华报》及《解放日报》的传统,充分发挥党媒的作用,强化对于人民的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红色精神,使红色精神广泛传播。
3.不断创新传媒的形式内容,使“精神谱系”与时俱进
党在纪念“二七”时所采取的各种纪念形式和方法,为我们今天开展重大革命纪念日和节日的纪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其中党在开展纪念活动时遵循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纪念“二七”时,始终将“二七”与抗战相结合,借助“二七”纪念,来为抗战服务。纪念活动的开展,要始终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其根本出发点,以现实为最终落脚点,这也是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开展“二七”纪念过程中始终坚定的方向。也只有把“二七”纪念与现实诉求联系起来,才可以将纪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意义充分体现出来。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概念,我们要借鉴全面抗战时期中央机关报宣传报道“二七”纪念的经验,不断创新宣传的形式内容,使“精神谱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