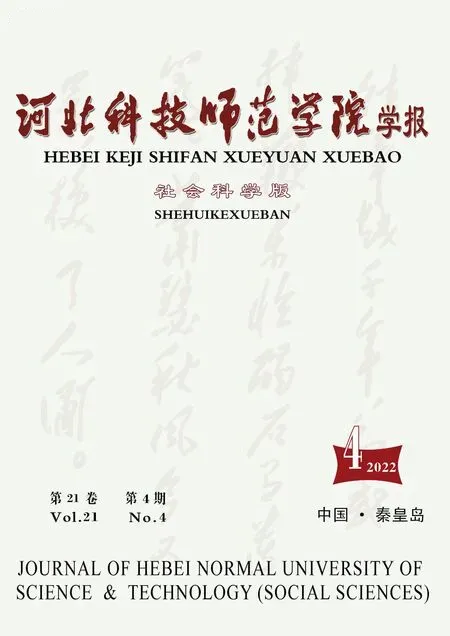“吃”的隐喻、逻辑与阶级性
——中国现代文学中饮食书写的历史演变
2023-01-20郭剑敏
郭剑敏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谈及中国现代文学中“吃”,可先从鲁迅谈起。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他在作品中虽描写饮食不多,但每每谈及却颇能呈现出浓浓的绍兴当地特色。如在《社戏》中写到了看戏归来偷罗汉豆吃的情节;《孔乙己》中的茴香豆;《在酒楼上》的“我”在名为“一石居”的酒楼上点了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还点评到:“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1]《幸福的家庭》里写到一道菜为“龙虎斗”,因着江浙人不吃蛇和猫,便将食材假设为蛙和鳝鱼。可以看到,鲁迅作品中谈及饮食,不论是食材还是口味亦或是烹饪法,都具有着十分鲜明的浙东当地菜系的色彩。不过在鲁迅作品中的饮食描写最具深度与鲁迅个人思想色彩的是以“吃”作比,即将“吃”作为一种颇具隐喻性和象征性内涵的行为,以此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反思与批判。如《狂人日记》中鲁迅便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国传统礼教传承的历史也便是“吃人”的历史。在小说《药》中,鲁迅着重写了茶馆老板华老栓为给儿子治病而去买人血馒头,而这个“人血馒头”显然充满了象征意蕴,揭示了早期民主革命运动中,革命与民众的隔膜。在杂文名篇《灯下漫笔》中,鲁迅更是以“人肉的筵宴”作比,批判所谓的中国文明。可以说,鲁迅在其行文中以“吃”作比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子进行批判,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启蒙时代的思想特质,饮食的日常性恰恰揭示出了封建思想毒害的广泛与深入,由此才使得国民性的改造与精神病痛的疗救显得如此的迫切与需要。在现代作家中,以吃作比写得十分精彩的还有张爱玲和钱钟书,张爱玲以吃来比拟世情百态,而钱钟书则以吃来讽喻现代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
在文学作品中深入而全面地展现一个城市的饮食文化特色的作家首推老舍。老舍在作品中对饮食的描写细致入微、绘声绘色,把老北京的饮食文化特色呈现得淋漓尽致,这其中又饱含着老舍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对老北京市井风情的深深留恋。老舍小说的京味儿特色,也深深地体现在他作品中对北京饮食文化的生动而传神的呈现,在这方面小说《四世同堂》最为突出。小说写的是北平沦陷后的历史情景,但作品中不断写到沦陷前北平的市民生活和市井生活情景,从而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追忆往昔生活情景时,饮食是老舍着重描写的对象。如老舍用在小说中用杏来串起有着老北京夏天的记忆,“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象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重,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绵纸遮护着下了市,好象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2]老舍在这里用一个杏来串起一整个老北京夏天的记忆,色彩丰富,有色有声,深深的市井气息,无限的故土情怀。老舍笔下的老北京饮食已成为呈现旧是北京民情风俗的重要方面,也成为沉淀着这座特殊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所在。老舍出身北京市井,在这饮食叙述中,有着老舍对童年、对家乡、对亲朋邻里的深情。
在现代作家中,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深入而全面的书写的是梁实秋,其代表作是《雅舍谈吃》。梁实秋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与翻译家,是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其小品文,堪称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举凡琴棋书画、衣食住行尽收笔端,温婉平和的叙述中,把一种典雅而精细的生活情趣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适闲、淡泊宁静的人生姿态。散文集《雅舍谈吃》集中收录了梁实秋谈美食的近百篇文章,《烧鸭》《锅烧鸡》《爆双脆》《乌鱼钱》《满汉细点》《佛跳墙》《西施舌》等等,写的舌尖上的味道,呈现出的是数千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同时也把作家浓浓的故乡情意及家国情怀书写了出来。现代文坛上另一位小品文大家周作人也曾有多篇文章专述饮食,《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窝窝头的历史》《吃茶》等等都是其论及饮食的名篇,也有着与梁实秋文章一样的文化意蕴与人生情趣。
从饮食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后要谈及的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因喜吃喜聚而形成的一个著名的文人圈,这便是“二流堂”文人群落。“二流堂”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形成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文人群落。这是一个由性情相投的文艺界人士在交往过程中聚合而成的朋友圈,主要成员有:唐瑜、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盛家伦、冯亦代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人群落在不断地扩大,成员主要来自美术、音乐、戏剧、书法、电影、文学等领域。可以说,这是一个由文艺、新闻、演艺界人士组成的一个朋友圈,大家彼此因意气相投聚合到了一起,在这个文人圈子里散发出一种自由主义文人散淡自在的气息。
“二流堂”文人的一个特点便是喜聚、喜吃。“二流堂”文人在一起时常聚餐,无拘无束,洒脱不羁,而且重义轻利。当年在重庆时,他们便是有苦一起吃,有钱一起花,不分彼此。这种交往风格在他们后来的岁月中也继承了下来,成为一种传统。夏衍当年在重庆时便与“二流堂”文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每去北京必去“二流堂”文人所聚居的栖凤楼,据说有一次为了和好友自在聚会,路上还故意甩掉了自己的警卫人员。进入新时期,饱经风霜的“二流堂”文人们又聚到了一起,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以聚餐的形式召集。“二流堂”文人们因才气而聚,因义气而聚,也因性情相投而聚,聚会既是一种交往的方式,同时也是情义的表现,尤其是共同历经坎坷,这种聚集更具有一种见证历史、见证情义的意味,这在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有些十分独特的意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情投义合者走到了一起,“二流堂”的交往成员也有了更广泛的联系,正如李辉在《亦奇亦悲二流堂》一书中所写:“‘二流堂’就不再仅仅是原有的那批人的圈子,而是在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物以类聚’。从王世襄、杨宪益、范用、黄永玉,到稍微年轻一些的姜德明、邵燕祥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人士,也都不时出现在‘二流堂’的聚会上。维系他们的当然依旧是绵绵不绝的文化情怀。”[3]
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吃”的描写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一方面吃香喝辣成为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化描绘;另一方面,忆苦思甜成为正面人物的一种革命性的表现。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不论是小说、电影、戏剧等,饮食具有了阶级性。好吃、贪吃、吃好的等等思想和行为被视为是落后的、反动的、丑陋的、罪恶的。赵树里小说《“锻炼锻炼”》中讽刺一个贪吃的落后农村妇女,给她起的绰号叫“吃不饱”;当年有关地主刘文采的故事叙述中,他在吃的方面的讲究和奢靡,成为表现他反动性的重要证据;而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土匪首领坐山雕于除夕时大摆百鸡宴,众土匪齐聚一堂,成为整部作品叙事的高潮,当然最终被杨子荣带领解放军一网打尽。
可以说,在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吃”具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与内涵,对饮食的喜好具有了划分阶级阵线的意义。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推杯换盏、大鱼大肉常常成为描绘反面人物生活的典型场景,而吃糠咽菜、忍饥挨饿则成为描绘革命战士与革命群众日常生活景象的常态。这其中暗含着一条成规,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能战胜肉身的欲望,能彻底地抵制美食、美色的诱惑,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相反,则会有着经不起诱惑而导致背叛革命的危险。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粗菜淡饭、省吃俭用成为一种革命的、高尚的品质和境界。如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中写梁生宝进城买种子时,着重写了他为了给大家节约开支,舍不得进城里的小饭馆吃饭,一路上全靠自己带的干粮充饥。“吃苦”的革命性的形成来自于红色革命叙事的打造,在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叙述中,“吃的苦”“吃的粗而简” 不仅是笔下革命者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也是一种革命品质的体现。在有关长征故事的叙述中,吃野菜、剥树皮,煮皮带成为十分典型的细节和场景,由此,“吃苦”成为一种革命传统,成为一种高尚的品质,相反,贪吃、好吃等沉溺于肉身欲望的行为被看作是一种品行不端或思想反动的表现,而只有超越肉身欲望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忆苦思甜也便成为这一时期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革命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对省吃俭用的提倡,一方面来自于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缘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物质供应匮乏的事实。为何爱吃、讲究吃成为了革命的对立面,这其中包含着意志品行的考验,意味着沉溺肉身欲望有着导致意志不坚定的危险,反之则会成为革命意志坚定的有力保障。所以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吃得苦”成为革命者的重要品行。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饮食书写终于褪去了阶级的色彩,回归其本色,谈吃、谈美食又成为了作家可以正面书写的题材与内容。具有展现新时期农民新变化和新面貌标志性意义的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正是从“吃”入笔,通过叙述农民陈奂生进城卖油食的经历,写出了进入新时期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面貌上的变化与特征。而陆文夫的《美食家》堪称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书写饮食文化的经典之作。小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80年代的时间背景下,讲述资本家出身的朱自冶的“吃”的故事,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年代里,贯穿着的是主人公朱自冶对美食的始终不变的执着,美食沉淀着苏州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美食也承载着一种往昔岁月里上层社会生活的某种蕴味。朱自冶以对美食的沉醉,游离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外,也终在进入新时期以后的社会变革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美食情怀的天地。小说一方面是有关饮食文化历史的呈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从那种政治化的写作中摆脱了出来,在一种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写作中而传递出新的审美走向。汪曾祺也写有谈饮食的散文《五味》《故乡的食物》《家常酒菜》《萝卜》《豆腐》等,其中体现出的不仅是作家对于饮食的特殊记忆,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进入新时期之后,曾经承受政治风云的一代作家走出阴霾后的那种轻松愉悦的心境。
三
民以食为天,也许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食物短缺,饥饿成为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的一种深刻的记忆。长时期的物质匮乏、生活用品和日常食物的限量供应,都使得关于吃成为一个头等大事,也许正因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吃了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碰面时的问候语。也正因此,有关饥饿的叙述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写作命题。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直面描写粮食短缺年代情形的代表性作品有高晓声的《“漏斗户”主》、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这些作品聚焦于底层小人物于饥荒年代里的艰难生存的本相。这种关于饥饿、饥荒的叙述,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汇聚而成所谓的苦难叙事,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即《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张贤亮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围绕以邢老汉讨老婆成家过日子为线索,串连起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底层农民艰难生活的历史。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是讲述了大半辈子没有讨到老婆的邢老汉,却在饥荒年代意外地因收留一个逃荒要饭的外乡女子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搭伙过日子的人。这种女子在饥荒年代通过委身他人而度过灾年的情景在其他作家的笔下也多有述及。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发表于1986年第9期的《中国》,小说开篇即写村里的老光棍杨天宽在饥荒年代里用二百斤谷子换来个脖子上长着瘿袋的女人当了自己的老婆。瘿袋女人长得很丑,却在杨天宽面前逐渐变得十分强势,这强势主要来自于女人的两大本领,一是能生娃,二是能弄来吃的,这在饥荒连连的乡村社会里,几乎就是天大的事了,而瘿袋女人却有本事把这两样都做得无话可说,也因此而在杨天宽面前变得霸道。女人因能弄来糊口的粮食而变得强势,却也最终因弄丢了购粮的粮本而自觉颜面尽失,最终吃有毒的杏仁儿而自杀身亡,咽气前那一句“狗日的粮食”也成了女人命如草芥的卑微人生的一种诠释。小说《绿化树》里的章永璘在饥荒的年代里,练就了一身觅食、讨食的本领,读书人的所有智慧都转化为如何能够获取多一口的食物,一个窝头,一勺野菜汤,不饿死成为人生最大的追求。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以孙光明为视角,书写出了一个底层家庭在饥荒年代里,因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亲情关系的极度恶化与极度冷漠。而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为养家而不断地卖血求生的故事的叙述,呈现出了50~70年代底层家庭辛酸的生活史。
在20世纪80年代众多讲述饥荒的作品中,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有着特殊的意义。小说最初发表于 1980 年第1期的《收获》,后于1981年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小说讲述1960年春李家寨的四百九十多口人陷入了饥荒,李家寨的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冒着风险,在昔日战友、现今为县粮店主任的帮助下,从粮库里“借”出了五万斤的粮食,村民得救,自己却被作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而被捕。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作品中较早的一篇直接对当代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行书写的作品。作品开篇从1960年春的饥荒开始写起的,“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1960年春天。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4]5而这时的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杨文秀则热衷于搞浮夸风,热衷于“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4]6。当村民开始因粮食短缺而闹饥荒时,有关上级却弄出所谓的“化学食品”来邀功请赏,以期糊弄百姓。上级动员缺粮的公社、大队搞代食品,杨文秀很快组织人搞出了所谓的新的食物品种,有称为“一口酥”的玉米皮淀粉虚糕、“扯不断”红薯秧淀粉粉条、“将军盔”麦秸淀粉窝头等等,但其实这些号称用玉米皮、红薯秧、麦秸做出的“化学食物”,其实纯粹是弄虚作假的产物。瞒干、乱干、高指标,加重了饥荒,作品对这样的一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表现,也正因如此,该作成为新时期初期反思文学中的一部力作。
1980年第2期的《新观察》发表了汪曾祺的一篇题为《黄油烙饼》的小说。小说主要是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展开叙事,讲的是萧胜的爸爸妈妈都是科研人员,在口外沽源县的一个马玲薯研究站工作,因条件所限,在萧胜三岁那年,爸爸只好把他送回到家乡农村与奶奶一起生活。萧胜七岁时,奶奶于饥荒中去世,但她到死也没舍得去吃萧胜爸爸早些时候带给她的那瓶牛奶炼的黄油。奶奶去世后,萧胜被接到了爸爸妈妈工作的马玲薯研究所一起生活。小说中令人触动的是作家讲述那种艰辛生活时的淡然,虽然命运很是不公,但这对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没有抱怨,不论是面对亲人的去世,还是自身处境的不公,还是基层社会中的不平等,他们都淡然处之,不抱怨,认认真真地生活,认认真真地工作,只有在儿子不解乡下三级干部开会时所吃的黄油烙饼是何物时,正咽着红高梁饼子的妈妈下狠心取出那瓶奶奶一直没舍得动过的黄油,给萧胜做了一张黄油烙饼。“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5]79这是汪曾祺复出后发表的较早的一篇小说,书写的正是有关过往岁月里的饥荒经历留给人的一种记忆。不久之后,汪曾祺又在1981年第5期的《收获》上发表了小说《七里茶坊》,这篇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与汪曾祺划为右派后的劳动改造经历有关。小说中的七里茶坊因在张家口东南七里地而得名。小说讲“我”在一家农业科研所下放劳动,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拿着介绍信、带着三个人去张家口的公厕掏大粪。那是1960年,天寒地冻,白天掏粪,晚上回到车马大店睡大炕。“掏公共厕所,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这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实实的,得用冰镩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装在单套车上,运到七里茶坊,堆积在街外的空场上。”[5]167住在车马大店,一早一晚都是店掌柜来给做手推莜面窝窝,莜面是自己带来的,做熟了蘸着自己带来的麦麸子做的大酱吃。吃得是粗饭,“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〇年!”[5]168劳动的脏和累,吃的粗,住得简陋,但作者恰恰是要写出这种天寒地冻的时节,在这车马大店所感受的温暖和香甜。不管是一起劳作的同事,劳动中互不计较,互有照顾。车马大店的掌柜,一早一晚生火做饭,即使碰上的同住一个在炕的赶牲口的坝上人。人与人之间,无戒备,无妨犯,坦诚相待,即使一碗水,一袋烟,一块咸菜,见得真情真义,汪曾祺把社会底层的真性情写了出来。汪曾祺的作品述及了六十年代初岁月的艰辛,但他却把这种艰辛讲述得很淡然而宁静,他更多呈现的是艰难岁月里所显示出的那种人间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