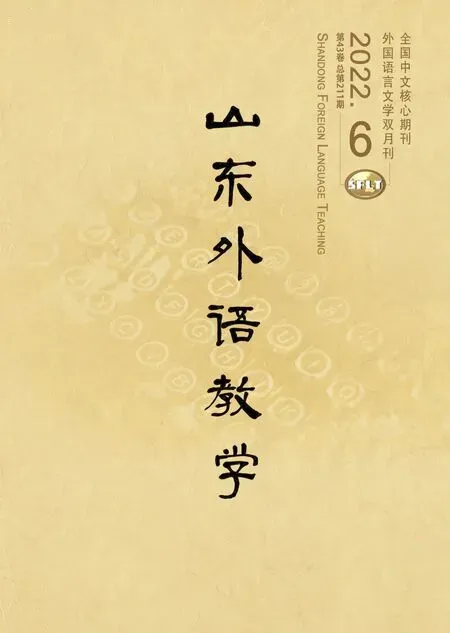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历史、现状与启示
2023-01-16蓝红军熊瑾如
蓝红军 熊瑾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1.引言
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相较于文学的悠久历史而言,儿童文学从一般文学中分化出来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儿童的独立性及其需求的独特性未得到承认和满足,儿童文学一直处于被成人文学遮蔽的状态。同样,相较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而言,儿童文学翻译及其研究也姗姗来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翻译就已兴起,17世纪时,文学翻译就成了英法等国翻译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但直到19世纪,儿童文学翻译还较为稀疏零落。英语世界里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转折点是1823年德国《格林童话》的英译和1846年丹麦《安徒生童话》的英译,这使得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翻译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Hunt & Ray, 1996:515)。20世纪下半叶,针对儿童文学翻译的专门研究逐渐兴起。及至现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已由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新视点,发展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Lathey, 2011:212)。当前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态势。“相较国外研究的规模与进展,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深度与广度有限”(李文娜、朱健平,2021:47)。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进行描述,以此观照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希望为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儿童文学翻译”的概念与“儿童文学”的概念密切相关。作为文学术语,“儿童文学”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清楚,它可以是“儿童的文学”(Children’s literature),也可以是“为儿童所创作的文学”(Literature for children)。有的学者认为,儿童文学意义宽泛,指“儿童所阅读的任何文本”(Gubar, 2011:209; Hunt, 2021:42),包括“为儿童改编的文本和儿童与成人均可阅读的文本”(Lathey, 2011:198),也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创作中将儿童读者群体区别于成人读者来看待的产物,应视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或为儿童所阅读的文学”(Oittinen, 2000:61),还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实践,如写作、出版、批评等,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儿童时期的读者视为典型读者的读者意识(Beauvais, 2015:8)。另外还有学者从外部视角出发,认为儿童文学不在于文本形式,而在于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行为和行动者,他们将儿童文学界定为“各种社会权威机构认为适合儿童的文本”(O’Sullivan, 2005:12)。总体而言,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均支持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直接读者,针对儿童特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本文将“儿童文学翻译”界定为“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文学翻译(活动和产品)”,并以此为标准,收集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献。
2.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translated children’s books”“translating picture books”“translated children’s stories”等为关键词,检索Web of Science、JSTOR、SAGE、Taylor & Francis、Springer以及ProQuest等英文数据库,并借助谷歌学术的文献引文进行检索补充。同时,根据文章摘要内容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符的文献,经人工筛选后得到的文献数量如图一所示。检索截止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

图1 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文数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文数量稳步上升,且发文量的增长率呈现阶段性特征,即研究数量大致以十年为周期增长一倍。因此,下文将以十年作为时间间隔,考察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发展特点。
3.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发展(1980—2009年)
3.1 20世纪80年代: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视角的研究为主
二战的结束给世界带来了精神和文化交流的巨大需求。儿童文学具有影响、教育儿童和塑造儿童精神世界的功能,因而“被视为增进国际理解和民族和平的一个方式”(Carus, 1980: 173)。文学界、翻译界和出版界都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投诸了更多的关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随着学界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学文化功能的认识加深,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凸显出其学术吸引力。
这一时期正是翻译研究寻求自身独立学科身份的时期,翻译学还处于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的荫护之下,没有形成自足自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因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与该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传统一脉相承,发端于对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儿童文学的比较探讨,多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如何通过翻译实现儿童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性问题。此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成果是Carus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Children’s Literature”。文中Carus以二战后经典童书的国际传播为例,指出儿童文学的启蒙作用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翻译研究的经典问题置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语境中加以初步考察。与此同时,“多元系统论”以系统、动态的多元文化观开始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Even-Zohar(1979)提出这一理论仅两年后,Shavit(1981)便应用该理论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开启了有明确理论框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一改过去以再现主观审美感受为主的方式,在文学翻译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Shavit(1981)认为,儿童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可通过儿童文学翻译行为中体现的翻译规范来判断,若儿童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那么儿童文学译者在顾及社会对翻译文本是否具有合适的认知和儿童自身的理解水平的同时,仍拥有较高自由度。此外,Shavit(1981)也提出了翻译文本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开创了儿童文学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的先河。
在第一个十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围绕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学和文化功能展开,如助力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功能和帮助儿童了解异域文化并习得语言的教育功能等。在这一时段,接受理论逐渐成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人们认识到翻译只有满足了受众对作品或文本的期待,翻译的文学和文化功能才能实现。受此影响,一些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学者们开始展开对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接受度的研究。如Oittinen(1989)采取文本研究的形式,通过译为芬兰语的一个对话体儿童文学翻译个案,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预期读者反应并适当创造,从而赋予文本新生命。Puurtinen(1989)则采用实证检验的方式,以芬兰语的儿童文学译本为例,验证了语言模型中句法结构和可读性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按照译入语的自然风格处理译文不仅符合翻译规范和读者期待,还有助于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译文风格的可接受性。
3.2 20世纪90年代:以描写译学范式为特色
20世纪90年代,描写翻译研究兴起,极大地推动着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发展。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开始沿描写译学路线前进,一方面放眼宏观,展开理论探讨,关注翻译规范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另一方面着眼微观,进行实践总结,重视儿童文学翻译中文本特征的描写和分析。
翻译规范作为描写译学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讨论。具体而言,在认可翻译规范存在共相的基础上,主要展开对翻译规范存在的殊相的比较与分析,并得到三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源语和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环境和社会语境不同,致使译入语原创文本与翻译文本存在不同规范,可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考察译本遵循翻译规范的程度(Puurtinen, 1997)。第二,为符合译本产生时代的语言规范,翻译规范会因时而变,加强或减轻对译本某些方面的要求,通过儿童文学的重译本可见一斑(Du-Nour, 1995)。第三,既存翻译规范可能由于翻译教学和翻译学习等行为而得到强化(Ben-Ari, 1992)。与此相关,Even-Zohar(1992)也探讨了希伯来语中的儿童文学翻译政策,包括文学政策和文字政策。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儿童文学翻译奖项开展了研究(Bell, 1999)。
描写翻译研究对方法论的科学性十分重视,强调文本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译文为出发点,对比原文和译文之间特征的异同,这是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同时,文学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特征是翻译中所应尽力传达的要素,如何保留原文的文本特征是儿童文学翻译的难点和挑战。因此,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话题也于此有集中的体现。在文本类型方面,此时的研究探讨了英译挪威语中神话的翻译(Rudvin, 1994)、英译法语图画书的翻译(Gagnon, 1990)等。在文本元素方面,此时的研究探讨了儿童文学文本中语言效果的翻译,如韵律效果的翻译(Metcalf, 1995)和幽默效果的翻译(O’Sullivan & Bell, 1998)、某些意象的翻译(Tanski, 1994)和图文关系的翻译(Al-Mahadin, 1999)以及功能主义指导下文本标题的翻译(Nord, 1995)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研究者首次将儿童文学经典的“双重读者”(即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问题纳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野,并藉此深化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多元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儿童文学译本对成人读者的吸引力能够提升儿童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O’Sullivan, 1993)。
3.3 2000—2009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逐渐丰富
进入新世纪,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深化,译学界对翻译跨域属性的认识深化,进一步推动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学基本确立了独立的学科身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作为分支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受到认可。表现为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革新、研究成果显著等方面。研究对象方面,边缘性作品的翻译、非主流语言间的翻译作为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内部问题得到关注,市场化条件下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关的外部因素(如教育、政策、出版等)得到考察(Lathey, 2015)。
研究视野的扩展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特征。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译本所受的意识形态制约在这一阶段得到广泛关注。继Puurtinen于1998年探讨了不同语种儿童文学系统中的意识形态规范后,López检视了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市场和作者对作品进行的审查、改写和删节(López, 2000),并于此后又撰文讨论了具体国别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审查机制(López, 2005)。
方法论的多元化也是此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随着语料库方法在上世纪90年代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研究,一批翻译学者也开始探求这一方法如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也从个案性的翻译规范描写、文本特征对比,发展出了语料库驱动或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此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Puurtinen,她应用语料库方法针对特定语言结构对译文可读性的影响以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翻译语言体现出的共性和特性做出了深入研究(Puurtinen, 1998;Puurtinen, 2003)。这一时期,语言学、文学叙事学、叙事语料库、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均有使用,多学科视角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他研究方法的突破还包括融合翻译过程和叙事学中信息传递模型,生成新的研究框架,用以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O’Sullivan, 2003)以及语言学角度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House, 2004)等。
4.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2010—2021年)
进入21世纪后,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展加速,尤其是最近10年里,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加。本文认为,从2010年到2021年的12年是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最为成熟的阶段,因而将此阶段单列出来作为现状描述。以下将采取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关系论视角(蓝红军,2020)对上述研究文献进行分类分析,梳理出当前研究的聚焦点。
4.1 文本与文本的关系研究
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指翻译中的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多种译文文本之间、翻译文本与原语原创文本/译入语原创文本之间的关系。在针对儿童文学翻译中文本与文本关系开展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文本对比方法,讨论译文与原文的对应情况(忠实情况),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与原文对应,什么因素限制了这种对应性忠实的达成等问题,也表现为对儿童文学译本偏离原文的程度和儿童文学译本中的改写现象的关注。一般而言,在严肃成人文学翻译中,为了保持文本的完整性,不会大量删改原文。然而,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儿童文学,不属于经典文本,因此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删改现象较为常见,由成人文学作品改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如此。Lefebvre出版于2013年的论文集汇编了不同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中“改写”这一现象的研究,涉及改写的目的、用途、题材、时代、元素、语言等方面存在的不同,以及译者自身对改写这一方式所持观点和改写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和困难。Akbari(2012)、Ghoreishi & Aminzadeh(2016)基于卡特福德的“转换”理论对儿童文学译本的改写进行了研究,从文本的各个层面探究了不同层次的转换对译文可读性的影响。另外,基于文本对比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多元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也产生了诸多创新性成果。

4.2 人与文本的关系研究
翻译中的人指具有人格的翻译主体和客体,人与文本的关系具体为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等(蓝红军,2020:11)。在针对儿童文学翻译中人与文本的关系开展的研究中,译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是研究焦点。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译本的首要读者都是儿童,因此考虑到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儿童观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及翻译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讨论了其他影响译本接受情况的因素。其一是儿童文学译本是否业已经典化。未经经典化的首译本不会对新译本的接受带来消极影响,如此读者对新译本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新译本接受程度仍然较高,反之则不然(Fornalczyk & Tonin, 2015)。其二是译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若译入语社会具有或已铺垫好能够兼容源语作品的文化艺术环境,译本的接受程度会更高(Pichugina & Poplavskaya, 2016)。其三是译本是否符合译入语儿童文学系统的需要。译入语儿童文学系统可通过源语文本融合于译本中的多元文化,达成文学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此外,儿童文学译本的多重读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翻译不仅是面向儿童的翻译实践,也是面向市场的出版活动。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的出版政策和出版商的决策都会影响儿童文学译本在目的语国家市场的接受情况。民族志研究、横向对比与历史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提供了对出版机构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所扮演角色和当前儿童文学翻译市场的主导作品等的深入分析(Biernacka-Licznar & Paprocka, 2016;Egeland, 2020;Nicewicz-Staszowska, 2020)。
4.3 人与人的关系研究
翻译中人与人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神、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的关系(蓝红军,2020:11)。在针对儿童文学翻译中人与人的关系所开展的研究中,翻译规范研究在其研究基础上获得了长足发展。较之二十年前,当下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对翻译规范的讨论更注重共时性,即探讨当前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多重规范问题。具体而言,当前研究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语言规范、文化规范、社会规范、教育规范、出版规范等各类规范,描述了规范间产生的冲突和规范与儿童读者兴趣之间的不一致之处。据此,翻译研究可以在修正已有解释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模型,以更好地描述这些互相冲突的规范(Lathey, 2010)。在译者惯习等社会学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的背景下,对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的研究逐渐转变为社会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将译者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其中的其他主体均纳入考量。此外,由于世界多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回归到翻译与民族身份研究。此类研究多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分析巴西、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多语种译本展现出的民族性(Kruger, 2011;Romala, 2021)。
综上,近12年来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展更为丰富和多元,方法论创新意识更强。日益细化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始终紧紧围绕原作民族身份的体现和译作的接受及影响因素展开,在尝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时勾勒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应然”形象,而在解释由实践引发的种种现象时又厘清了其“实然”形象(李文娜、朱健平,2021:45)。
5.对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知,国外学者从不同研究侧面,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所涉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刻且系统的研究。相较而言,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整体上偏重于儿童文学翻译语境下的翻译基本问题研究,如宏观层面的儿童文学翻译忠实性研究和微观层面的儿童文学译文语言特点等。在国外翻译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已开始借鉴国外以多元系统论为代表的研究理论和以语料库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从而加深了对国内儿童文学翻译面貌的认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相关研究无疑可以启发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为之提供创新性研究思路和研究进路,从而丰富和深化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理价值和实际效用,提升国内研究水准,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提供译介途径优化(董海雅,2017:95)等方法论启迪。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未来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5.1 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体系构建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可根据儿童文学题材分为少年小说、儿童诗歌、儿童戏剧等,又可根据翻译研究对象分为译者研究、译本研究、接受研究等。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易造成研究碎片化。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这一译学分支的良性发展,有必要以体系化的思维统观该领域主题各异的研究。此外,当前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失衡问题,如经典理论过于泛化的使用致使理论创新性不足。多元系统论、翻译规范论和翻译操纵论因其较强的解释力而被奉为经典,此类理论视角下的个案研究已较为充分,而其他理论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未出现显著成果。因此,构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体系作为指引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工程,其确立不仅能够化解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存在已久的研究失衡问题,还能够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标准和依据。鉴于此,可尝试从多模态话语分析、形象学、文体学、叙事学、伦理学等角度展开跨学科研究,从而修正原有解释模型或开拓新理论。问题之二在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标准获得的学界反馈不足。一般而言,翻译研究中的译本描述、翻译批评和读者反应研究等均可直接或间接地助推实践标准的完善。然而,现有研究无法有效描述译本间的差异,翻译批评标准讨论不够充分,且未能涉及重译的市场和读者反应。后续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可从儿童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性出发,建立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总之,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体系的构建能够帮助研究摆脱理论贫困,发现更多的研究问题,得出更丰富的评价维度。
5.2 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证研究方法
自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端于描写译学以来,基于儿童文学译本的描写性研究已成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主导。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便存在这一弊病,即个案研究分析对象重复性强而差异化不明显,证实性研究充斥而实证性研究较为有限。由于研究多见于文本分析方面,缺少实证检验支撑,因而量化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尚处于可行性探讨层面,缺乏应用此类方法对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和儿童文学译作的系统分析。具体表现之一是翻译策略影响因素研究的众声喧哗和自说自话现象。当前国内研究经验主义特征明显而实证研究不足,致使翻译策略研究局限于基于研究者语言优势的双语研究的经验分析,缺乏更广范围的比较研究,导致关于翻译策略影响因素分析较为片面且相互间存在较大分歧。近来虽有将语料库方法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案例(韩洋,2019),但整体上客观性数据收集方法的运用仍然贫乏。因此,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必要效法国外研究(如Kruger,2013等),或是采用包括语料库研究和眼动跟踪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对当前翻译研究问题的主观性结论进行检验。或是从理论性研究转为实践性研究,超越对儿童文学翻译本质的探讨,细化对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多重因素和面对的多层次读者接受状况的研究。
5.3 着眼于中国儿童文学海外译介研究
近十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其关注重心从欧洲儿童文学间的互译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儿童文学的翻译,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译介。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与成长离不开译入的外国儿童文学,而日臻成熟的中国儿童文学也需通过翻译达致与他国儿童文学的沟通。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海外译介研究可以帮助发现被遮蔽的中国儿童文学,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化,实现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具体而言,在经典儿童文学文本外,还应关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重新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机制。总而言之,译介研究可以补充并扩展当前的翻译研究,将包括译者个人选择和出版商的决定过程等影响儿童文学出版的研究均纳入考察。
6.结语
本文从儿童文学翻译工作的定义出发,回顾了近40年(1980—2021)来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特点,包括研究脉络梳理和研究现状分析。其中前30年研究依据的学术史意义,以每十年一个单位梳理国外儿童文学翻译以往的研究热点与热点演进等情况。对于近十年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检索结果,从翻译主体间关系论的角度展开分析,归纳出当前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的三方面阶段性特征。最后,本文借鉴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对已基本立足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出了三方面启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