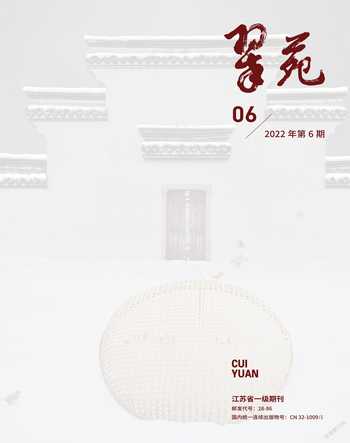“港漂作家”的记忆音像带
2023-01-11邵栋贺与诤
邵栋 贺与诤
2022年8月22日,常州新世纪商城半山书局邀请邵栋做新书推介,借此机会,我有幸专访到邵栋老师,做进一步创作谈活动。
邵栋,1989年生,江苏常州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写作文学硕士课程主任。历获“文学与人”全球华语文学原创大赛小说首奖、台湾林语堂文学首奖、第四十二届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已出版学术专著《纸上银幕:民初的影戏小说》。《空气吉他》是邵栋的首部小说集。共收录9篇小说,每个故事都围绕一件日常物品或一个随处可见的场所发生开来。聚焦庸常日子和微妙人心,一半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另一半是青少年时期人人有过的经历。早熟的少女从喜爱的小说中窥探未来;平凡的青年在防疫糖丸里咂摸过去的错误和快乐;困窘的打工者因一台旧冰箱,体会到一丝欢欣;丢失的钻石戒指见证了感情的变迁和遗憾……
邵栋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翠苑》杂志的支持下采访到您。在今年,您新出版了小说集《空气吉他》,我想就这本小说为基点,和您谈谈小说创作。
1. 无论是在讲座中,还是在小说里,感觉您始终有一份思绪是在和“真实性”博弈,请问这一思考的由来是源自理念层面,还是生活的某种确证?
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虚实难辨的现实,或者说二手经验,它既不是虚假的,但同时又与切身体验不同,某種意义上我们又离不开这种经验,而这恰恰可能是现代生活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人:被恋爱综艺甜到,为偶像的吻戏萌发醋意,沉溺于言情故事,为与自己无关的集体感到骄傲或愤怒。午夜时分,无数人躺在床上刷着相同的手机软件,了解遥远的从未听说过的明星男女的八卦新闻。日常经验是无趣的,所以我们需要二手的,他人的奇遇。我想,这可能是现代的困境,也是现代的妙处,我的小说大多数取材都来自这样的二手经验:比如《钻石山》当中骨灰钻戒的知识,就来自于坐小巴经过西九龙时看到的一个广告牌;《泊凫》故事的起源是,一个港大的师姐,抱怨总是收不到邮局的信;《鹦鹉》的写作灵感,则源于江歌案的猜想……某种意义上,二手经验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认知,连做菜都可以看youtube和小红书,与此同时,而我们也在制造大量的二手经验,甚至是误导性的二手经验予他人。譬如,明明吃了一家米其林餐厅很不值,但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夸赞就餐体验甚佳;明明生活一团糟,还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网络和虚拟生活为我们创造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我们制造了更多撒谎伪装的可能。这同样也是我写作的一个核心兴趣点。
2. 许多人说您的写作有张爱玲的身影,这或许在我看来,除去细腻的笔触之外,更多的是您在文字间向我们展示的跳跃的机敏,那种灵动感是对自我少年时代的回望,也是对于曾经记忆的褒奖。请问可以和我们谈谈您的“枕边书”或是学术史吗?
我本身并不十分喜欢张爱玲,但却十分佩服她的一篇叫作《封锁》的小说。小说描绘了封锁阶段一辆电车上,陌生男女来得快又去得快的爱情。作者对于虚拟关系的描绘,对于都市人面具下的真情,谎言中的默契有着非常动人的描述。因此可以说,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就预言了我们当代生活中的荒谬,以及荒谬中的爱情生活。孤独的人在城市中对于虚拟生活的依赖,构成了生活本身。而这也是我想在小说中书写二手经验的重要原因和相当重要的起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尤其是《佩德罗巴拉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另外,郑克鲁编写的《新派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算是我的写作启蒙读物。最近的话,把四大名著和金庸的小说重看了一遍,觉得挺受启发的,怎么把小说写的好看比写的深刻要有意思多了。
3.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一段璀璨而炙热的时期,在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于家庭与时代震动的影响或许会更为深刻,您的小说中也有一些篇目触及了这一母题,请问您如何看待时间与空间的破碎感和切割性的?
我小时候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末期的产物,供销社,粮店和饭票,这些我小学时还经历过见过,但少年成长时期就是加入WTO,整个消费文化都改变了,许多地方原本都有自己城市的山寨可乐、山寨雪碧,很快这些作坊式的经济体就被舶来品打垮。过往的社区结构也变了,小时候住平房,和周遭小朋友的互动方式,自然与如今楼房的结构非常不同。实际上,我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经历过改造,搬迁和拆除,使得我常常怀疑一些记忆是否真实,自己所在的地方究竟原来是什么地方,这是我感到最割裂的地方。
4.虽然我们现在不再愿意武断地去用代际来规约作家,但是在相似的地域或所处的时代,仍然不免给年龄相当的作家群体带来某些共性,这些共性也是无法避而不谈的。在历史上常州是一座轻工业城市,想请问您对于您的童年与少年阶段“工业文化记忆”是如何看待的?
最深的记忆就是,对工业有概念的时候,认识的工厂里的亲戚都下岗了。只能在“谁谁谁原来是毛纺厂的”“谁谁谁和我曾经是一个车间的”这样的说话了解过去的情况,而那些废弃的厂房就在社区周边,现在想起来,很像一篇韩国小说,金爱烂的《水中的歌利亚》,好像一些曾经无比巨大的宏伟之物,静穆地被淹没。
5.“双城书写”构成了您《空气吉他》中的重要内核,对于江南和香港的双重视角,当下也有许多作家在各自的方向上爬梳着。请问您可以从城市体验的陌生化与文化共性这两个方面谈谈您对于“双城书写”的看法吗?
有次在九龙坐的士与司机闲聊,司机问我来香港多久了家在哪儿,我都一一作答。他又问:“你现在在香港工作,那多久回去一次呢?”我说:“过年的时候回去。”他便转过头来和我说:“我懂了,就是和内地的那种农民工差不多对吧?”我说:“是是是,师傅你总结的太好了。”这段对话似乎提醒了我,作为现代都市成员中那种不可摆脱的异乡人身份,永远生活在别处,工作性质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这一本质。
在香港和江南故乡之间,常让人犹疑自己的身份,也曾叩问,是不是不够香港,却始终记得一位学院前辈和我说,香港不止是个本土的城市,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呀。既不在此,又不在彼,可以有多重身份,又可以什么都不是,这可能是香港教会我的武功心法。所以也许可能双城不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兼顾。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并没有从双城的角度上思考写作问题,但是小时候所有的香港记忆,金庸的武侠电视剧,武打电影,搞笑片,录像带里面的香港确实在最近十年的生活中慢慢变成某种现实,是我理解华人文化共性的一种角度。
6.城市中的漂泊感与悬浮感构成了现在许多青年人的生活关键词,您如何看待这种空虚、浮荡之感,或者说在您看来青年人城市生活贯穿性的精神实体是什么?作为一位80后作家,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城市生存经验带给您怎样的体会吗?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讲过一个理论,叫作惊颤经验(chockerfahrung),他通过研究波德莱尔的诗歌,捕捉到巴黎都市生活中琳琅满目的要素给我们心灵的震荡,而这在农村小镇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中尤其明显。所以我小说里会写到,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外乡到香港,年轻人还是会渴望熟人社会结构当中的亲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产生联系。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青年的动力和资源没有达到一定地步,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融入更广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我也很着力地去描绘这样的状态,希望在小说中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共通的身份焦虑和疏离心态。同时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共通的困境,如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现代人永远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这也是永远值得书写的境况。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些是一些蓝领阶层或者更底层边缘的人,大部分来源于我的现实观察和情感体验。我中学时暑假曾在一个很高级的饭店打工,见过包厢里的海鲜盛宴,也见过后厨员工餐的简陋,试过下班后汽车坐过站的疲惫。我也曾经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住过,里面电线排布杂乱无章,24小时都会有人醒来。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住民的手机还是蛮不错的。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很快买到一套房子,但他们很需要让人知道自己赚到了钱,而表征就是能买一个好手机,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样的所思所想让我动容,所以我很想去观察他们,并且希望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尝试体验他们的生活。再加上我父亲是记者,一直都有观察底层生活,也是受到家庭影响。
7.虽然在《空气吉他》的后記开头您说自己在音乐方面是一位“门外汉”,但实际上您却用“空气吉他”弹奏出了虚构与生活中蕴蓄着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记忆、地域见闻等等,在您看来,文学与音乐之间具备怎样的联系,或者说两者在节奏上有什么共性?
文学和音乐一样,充满了变化和选择,或者说在写作的时候和音乐一样,可以有很多元的自由,而且两者在创作上基本不需要花钱,也没有太多门槛。但我本人其实连五线谱都不熟悉,由此也可以说两种艺术都有一定的表达限制,需要一定程度上熟悉规则。但大体上,个人觉得心中之事最为关键,无论以音乐还是文学,都是一种外化的形式。
8.在阅读您的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十分注重对于感觉的描述,这也使得您的文字充满了丰盈的细节感,当然也不乏游戏性的俏皮。有许多人说您的写作与张爱玲具有某种链接或共性,您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语言问题的呢?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以五四前后的文学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时段。所以看了很多民国时期相关材料,尤其是通俗小说之后,我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语言训练,可能和普通的语文训练略有不同,这也是常常为编辑所诟病的。实际上,现代中文的语法相当欧化,和过往的白话殊异其趣。港台的中文和内地的中文表达略有不同,其实是因为来自于不同的传统,因而会有我的语言和张爱玲相近的理解,本质上是因为我和当下一些内地作家语言相远的缘故。
此外,我认为喜剧特别难写,所以日常只能写点没有那么欢喜的内容,但多多少少希望有多一点不同的笔调,也希望自己的小说更多一点幽默。
作者简介:
贺与诤,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现当代文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写作发生学、江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