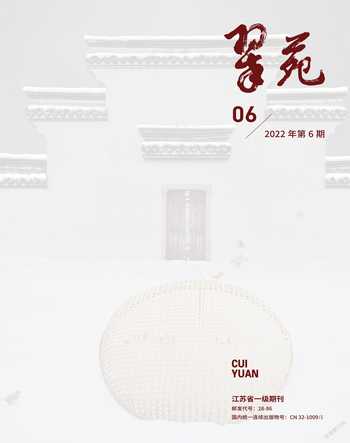麻雀的家园
2023-01-11朱群英
小时候,最常见的鸟就是麻雀了。椭圆的小身子,尖尖的嘴巴,灰色的羽毛,头上还长着一撮烟色的翎毛,好像顶着一块方头巾。它的背上还有几块深褐色的斑点。有的麻雀脖子上有着一些绿色或深蓝色的绒毛,十分醒目。骨碌着两只透亮灵活圆圆的小眼睛,一双肉色的小爪子,一副挺机敏伶俐的样子。但是人们并不喜爱它。
麻雀成群结队,飞到哪里,哪里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玩耍吵闹个不休。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飞着,有的在树叶间往返飞着,像是在玩捉迷藏似的;有的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似的,一个劲地往前飞;还有的像运动员似的,翻了一个大跟头,猛地落在地面上。它们不仅飞的动作优雅,走起路来那乖巧的样子像只欢畅的小精灵。当它在树枝上歇脚的时候那由三根棕色的毛组成的尾巴总是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着,那一双小眼睛还不时地东张西望,不知道它在寻找着什么,甚是可爱。如果村里哪家种了高粱,肯定会在绣穗并结籽的高粱地里竖一根旗杆,上面系一块红布,风一吹就呼呼啦啦地飘,以此吓跑偷食的麻雀。幼时的我常常揣摩猜测:麻雀一定是惧怕红色,要不为什么红布一飘,它们就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呢?
穗子弯腰的谷地里,主人常会扎上个草人,把两根木棍钉成十字形,外面缚上稻草,上罩一顶破斗笠,一手執一蒲扇、一手牵一红布条即可。一阵风过,破蒲扇“扑踏、扑踏”的,红布条也一飘一摇的。刚开始,麻雀们从上空掠过,硬是不敢着落。也许那独脚草人老是木讷的表情、单一的动作,让聪敏的麻雀们看出了瑕疵和破绽,用不了几日,麻雀们又会毫不顾忌地成群飞到谷地里照吃不误。甚或大饱口福大快朵颐之后,还会有几只胆大地跳到稻草人身上驻足歇息呢。田野中,麻雀们那活泼天真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枝头末梢上跳跃,忽儿成群地飞过天空,留下喋喋不休、不绝如缕的美妙歌声。麻雀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欢快的小鸟。其实,这些小家伙的叫声,一点都不好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是唠家常的大妈,中间夹杂着抱怨、夹杂着嗔怒,但却从来没有愤怒没有哀伤,倒是有着最细小的幸福。麻雀不是为唱歌而生,天生不具有好嗓子,不可能成为名满天下的歌手,但这并不妨碍麻雀的歌唱。麻雀的唱词短促,音色平淡,节奏琐碎。麻雀唱不了所谓的大歌,自然不会去参加选秀,不会为了名利为了考学而练破嗓子,这倒跟麻雀的卑微身份名副其实。
让我们仔细欣赏麻雀它那诙谐的装扮吧!它头上戴着一顶土灰色的帽子,圆溜溜的小眼睛总是纳闷好奇地瞅着四方;那有光泽的小肚皮上覆盖着一层软软的灰白色的绒毛。还有它那迷彩服般的羽毛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麻雀,就像一个十分机灵十分聪明的淘气小男孩,非常惹人喜欢。每天早晨,我总能看见一群小麻雀在不远处的老柳树上叽叽喳喳地海阔天空侃侃而谈,或者在树枝上忽左忽右蹦来蹦去地锻炼身体。或者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若有情况,一群麻雀就忽地一下惶恐地飞起,在天空中回旋,等了好久,断定并没有什么风险时,才谨小慎微地回到柳树上,又开始忙碌喧哗起来了。赶上麦收季节,麻雀们会结队成群地飞到麦地里觅食。恰在此时,肯定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掷块石子,于是它们只好“哄”的一声远走高飞了。白天对于这样的袭击,麻雀都司空见惯置若罔闻了,因为那时麻雀在人们的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况且那年月粮食匮乏。很多人厌烦冬天,他们龟缩瑟抖在室内,很多鸟也不喜爱寒冬,它们选择长途翱翔去遥迢的南方。但是麻雀,专心致志屏气凝神地守着家园。在我看来,麻雀是喜欢冬天的,虽然食物有些贫乏,但缺少了众多的竞争者,麻雀反而活得更加津润,这或许正是麻雀的高妙之处。冬天下雪时,麻雀也并不衰颓,它们像灰色的石子一样溅落到皑皑的雪地上,接着用尖嘴刨开积雪,仍然可以找到果腹充饥的食物。麻雀视力极好,可以看得见很细微的草籽,麻雀不挑食,只要能吃的,不管味道美不美,都不假思索地吃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麻雀当中出不了响当当的美食家,但也绝不会有活不下去的顾虑。
麻雀落到地上,左瞅瞅,右瞄瞄,大抵在寻觅食品吧!我哩哩啦啦地撒在地上一些米。开始,它们东瞧瞧、西望望,看见四周没人,就吃上几口,如若有一丁点的动静就赶紧飞起来,这样来回往复几十次,方才把米吃完。这时野地里最吵闹的莫过于那些机敏矫捷的小麻雀了。叽叽喳喳,在稀稀疏疏的枝头琢磨着心事,成百上千只会倏地从树上飘然而下,洋洋洒洒如无数片落叶。在杂草间蹦蹦跳跳乱啄一阵,见得人来,又呼啦啦一齐飞去。春天的时候,人们开始耕耘,麻雀就跟在铧犁的后面,一跳一跳地搜索去年藏在土里的渺小种子和虫卵,它们沙哑急切的叫声让人感到久别的盎然春意。暮秋粮食归仓,夕阳镀金的柳树上,一群麻雀仿佛在开大会,你一语我一言,有时候是大家争辩,斗嘴,面红耳热,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你踱至树下轻轻扬一扬胳膊,团团簇簇的麻雀腾空而起,似一朵仓促飘起的黑云彩,你的目光会尾随很久,最后你的目光也会落在另一棵老树上。麻雀一旦被逮住,伙伴们便跟踪着守望着,伺机劫持救援。更有另一手伎俩,落难的麻雀佯装死亡,乘人不在意时一下逃掉了。麻雀是衬托在人类生活过程中的活标点:落在某一个墙头上时,是句号;落在冬季枯枝上时,是逗号;求偶的一对儿追逐翻飞累了落在上下枝时,就是分号;好几只一起落在电线上时,是省略号。
那时老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池塘,塘边有一处竹园,园里的竹子棵棵竹叶儿绿、竹杆儿青。塘里虽没有荷花飘香,却丛生着葱翠的蒲草和水葫芦。白天那是我的天下:我可以信步去找我家的小鸡仔和老母鸡;也可以进去寻树下零星的蝉蜕,或折几枝蒲草绣出的蒲棒……但是每当夕阳西下,竹林就成了鸟的王国。麻雀们也会从四面八方飞临竹园栖息,大呼小叫,又唱又跳,每次总吵到很晚。夏日的我坐在门口一边纳凉一边听鸟叫、蝉鸣和蛙声。偶尔闲不住地投块石子进去,竹园里登时鼓乐齐停。但是仅仅一会儿,它们又继续跃跃欲试地开始叙说各自一天的故事。
后来,大家的日子富足了,房屋也讲究宽阔起来。渐渐地那处竹园被毫不在乎地划作了宅基地,而后人们就在各自的宅基地上盖起了自家既宽绰又敞亮的大房子。从此竹林消失了,麻雀也迁移了。
再后来,就是忙着上学、忙着长大、忙着成家、忙着过日子……自然就遗忘了那小生灵。直到有一天,我抱着孩子立在大廈的某一窗口,孩子指着远处问我:“那是什么?”我才豁然发觉现在还没有被高楼吞噬的老房顶上,蹦着几只小麻雀,可却仅仅只有可怜的几只。钢筋混凝土把我和它们隔成了两个世界,我已听不到它们开心的叫声。从那偶尔扑棱的翅膀中,隐约窥见它们对自己悲剧的不屈和最后的挣扎;它们焦灼惊悸地凝视着机器的巨臂和空中无数生疏的窗口,无依无靠的身影不再跳跃成幼时美妙的童话。我豁然顿悟:麻雀也该有个家。它们不喜欢这狭窄的空间,它们属于自由,属于广袤的天空和田园。造物主在创造生灵的时候,一定是注意搭配和均衡的。羽毛美的鸟一般就配上了比较差的嗓音,而好听的嗓音就配给了羽毛不好看的鸟。麻雀的毛色和嗓音都不好,是造物主不小心亏欠它们了。麻雀满不在乎,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一天到晚乐得没心没肺傻里傻气。
天气冷了,树叶泛黄飘荡,有霜冻在午夜悄然降临。直到这时,人们才抬起头来,看到村庄四周的树枝上只剩下麻雀、喜鹊,还有乌鸦。有多少只鸟儿都飞走了,仅有麻雀留下来,伴随着我们度过寒冬,让我们的目光有点着落,让我们的心思有点起伏。在冬天,听着窗外麻雀的鸣叫,蓦然感到酷寒中难得的沉着和融洽。在冬天,看着麻雀跌跌宕宕,心中居然升起一股久违的激动。在冬天,我也愿做一只麻雀,恪守家园,唱着最寻常的幸福,那么,你呢?
可是,现在的城市和比邻城市的农村,已没有它们永久的家园:川流不息的交通,高楼大厦的林立,人来车往的喧嚷和机器不分昼夜地轰鸣,还有日趋稀少的绿地和树林……今年夏末,我在大都市待过一段时间。站在十六楼的阳台里,看见大都市的日新月异,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墙体大理石细腻光滑,反射着光芒。我没有看见一只燕子,也没有看见一只麻雀。城市已经谢绝这些生灵,五彩斑斓的夜空已经断然缺失它们的翅膀,鼓噪的人声和汽车喇叭的刺耳已吞噬了它们细小的叫声。风轻云淡的清晨,我看见一些拎着鸟笼子遛鸟的人,他们悠悠地迈着方步,恬静坦然地走过。可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尘世笼子里的一只鸟呢,他们的叫声又愉悦了谁?是谁像他们遛鸟似的也在遛着他们?
作者简介:
朱群英,生于1969年8月,中国作协会员,丰县作协主席。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中国年度散文》《新华文摘》《中华活页文选》等版本。著有《林则徐的声音》《俊彩星驰》《乡雨》《蓝天下的风景》《月籁音丝》《炊烟的记忆》《净土》《大沙河笔记》。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