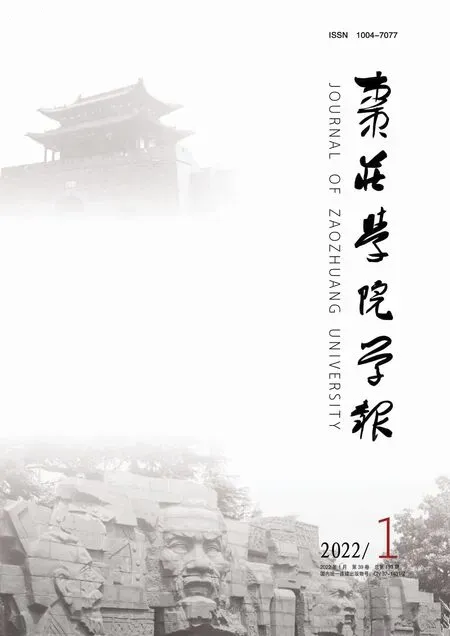《天香》:爱在流动中实现的个体建构与深层觉知
2023-01-11孙凡迪
孙凡迪
(1.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气象局,北京 100081)
一直都觉得爱从来不是一种谦卑的情感,爱就应该是高尚的、美好的、伟大的,可是读完了路文彬先生的《天香 》,我对待爱和被爱有了全新的理解。在关于爱的这些所有华丽高大的词汇底下,藏着爱最真实开启的姿态,它首先是谦卑的,善意的、低垂又自然地走进你的生命。强者往往主动选择爱,而弱者会等待被爱。那些因为所谓的尊严和怕伤害而不敢去谈爱的人,内心大多是一个孤岛,他们宁愿以拒绝爱的姿态,让自己看上去是无坚不摧的。但其实是占有的底层思维禁锢了生命本身。而真正的强大和成熟,往往是敢于直面和迎接伤害,敢于承认存在,并用自身的爱和善意去建立一种全新的连接和流动,会使得自体的爱与善以更强的内生性去探寻与觉知,蓬勃生长,永不消亡。
一、爱的形式:存在与占有
爱,是高于和大于爱情的一种人类本能体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沙瓦、齐谷、齐峰、贵子、庄可天和习句,他们每个人和因爱而构建的交错关系,都有爱的成分的流动。高尚的爱,是既无私又自主的爱,在爱别人的过程中,不丢失自己,又不会因为欲望,而把爱一个人视为全部的占有;而低劣的爱,就是以爱对方为理由,处处体现自己对所爱的占有、控制,并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对方意愿之上,通过各种话术,使对方被动接受自己的逻辑与立场,还要心怀感恩,这种变态索取的爱。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尊重并在承认彼此存在的状态中,能感受到更好的自己。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认为生命是过程而非物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存在就意味着变化与不断成为的迭代过程。在小说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齐谷对齐峰最终的理解。每个人在最初遇到爱的时候,一定是先于自我的感受,被对方身上的特质所吸引,之后随着二人相处并了解后,自体意识开始增强,并希望用自我的价值体系来评判对方的行为。这也是为何齐谷在齐峰选择一次次攀登珠峰,身受重伤还不放弃的时候,自己对这份童年就爱恋已久的强烈感情开始质疑的原因。她觉得齐峰是自私的,是不值得爱的。但是到最后看着齐峰是用生命在和山峰相处并靠近,而并不是她之前所理解的征服的时候,她对齐峰的爱,产生了指数级的升华。她觉得自己之前对爱狭隘的理解,局限了对齐峰对梦想追求的认知,也影响了她对齐峰的爱的纯粹。如果她自己不是以占有这份爱为前提去看待彼此的选择,就不会对齐峰产生失望和误解。所以最后齐谷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延续齐峰和自然的对话与交融,这是齐谷自体意识跃升的体现,也修复并升华了之前相对狭隘的价值体系,在珠峰的脚下,在爱的流动中看到了更好的自己。
在人性中,占有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它最早的体现就是吸收,也就是婴儿对母体营养的吸收和索取。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中就提到:
“大多数物品无法以实体的方式被吸收,即使可以这样做,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复存在。但还存在象征性和魔法形式的吸收。权威、体制、理念以及形象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内化吸收:我占有它们,就好像永远把它们保存在五脏六腑中。”[1](P31)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存在各种“习得性占有”。对知识的占有、对记忆的占有,对谈话的占有,对阅读的占有力和对权力的占有。一切占有的前提都是丢失了“爱与自由”这个本质的命题。一旦占有,对象必定僵死,而因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的霸权和僵化,所以主体也不能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实质,这种占有的意识,会降低主体的自主能动和创造力。比如我们如果对过去记忆是以占有为前提,那么一切就是机械性的,没有唤醒,没有连接,没有重塑。童年的阁楼就是房屋的一角,我仅仅占有这份回忆,就按压住了回忆中所有元素和现实、情感流动与关联的可能,它可能就是一种逃避童年某种情绪的单一场所。但是在存在模式的记忆中,一切都是非线性的,也不是纯粹逻辑性的,而是鲜活与流动的。阁楼可能既小又大,既远又近,既阴冷也温暖,全看我们盘活了哪种情绪和记忆产生共鸣。这种记忆本身,包含了主体积极思考和勇于构建的过程,很类似弗洛伊德提出的“自由联想”。
爱的占有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比实体的占有更复杂,会有更多的变体。看似沙瓦对齐谷的爱,是以逃避开始的,不存在想去占有,但实际上在他内心,就因为占有是最终目的,他才会在觉得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最开始选择了逃避与沉默。这是对“爱的占有”而不得的一种自我保护下的应激反应。他给自己表面的理由是因为庄可天提前表达了对齐谷的爱,所以自己不想破坏友情,又不想去奢望这份悬殊极大的恋情,所以一开始就退出了。但是从存在与占有的角度看,这份爱的退出,就承认了要占有的最终命题。到后来,沙瓦看到了庄可天对齐谷的爱的勇敢,看到了齐谷对齐峰的爱的执着,他也不断在更新自己对爱对自我的认知。当他开始真正踏上寻找齐谷的那一刻,他的爱,才从以占有为目的中扭转过来,开始以存在为前提,去感受他对齐谷的这份爱。他开着吉普车飞快地远离城市,驶入乡间,驶入荒漠,他寻找的方向就是依循内心对齐谷呼唤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一种爱在存在中的复活。不再一味地占有,就不怕失去,不怕失去,就更加有勇气和力量去感受存在中的爱,而这份流动的爱,也让沙瓦自己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勇气、光明和使命:
“一股蓄谋已久的巨大旋风正在毫不知情的沙瓦身后悄悄逼近,骤然升起,致使沙瓦手中的帽子犹如惊慌的鸟儿腾空而去。……沙瓦伸出手去,像是要抓回那顶帽子,又像是在同它挥手告别:飞吧,沙瓦希望它就这样永远地飞下去,直到齐谷有一天能看到它。她一定会知道,这是沙瓦在四处寻找她。”
小说结尾用帽子这个意向再次和开头呼应。只不过这里的帽子在人物内心挣扎变迁后,产生了全新的意义,不再是过去对生活的一种抵抗和逃避又或者是霸凌的象征,而是象征爱与存在,象征着探寻与勇气,象征着自我真正的觉醒和生命的重新建构。
《天香》在最后唤起了我们每一个读者内心的真实共鸣,并能更好地激发由内而外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自我觉知。我想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如路文彬先生在他的《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中提到:“情感的匮缺是此类文学史力求客观而不得不招致的一个显在缺憾,这种弊病使得文学史的阅读从来都是单向的窥探,而非阅读者同写作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共鸣。”[2](P215)
二、最初生命的建构:寻找意义
对爱的认知其实源于我们自身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理解和生命的建构。人的第一声啼哭发生在空间中,从这一刻一切的意义都与空间密不可分。意义需要人在一生中不同的空间中完成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家,作为婴儿出生成长的第一性空间,尤其对性格的养成起到决定性意义。少年时期的沙瓦,不缺钱只缺爱。在那个时代相对富有的家庭中,沙瓦得到的爱始终是空荡荡的,在房间里带着巨大的回响,让他很难感受到爱的实体。
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有非常系统又生动的分析。他提出一个意象“家宅”。家宅中可以同时体现空间的统一性和复杂性,在对家宅的所有回忆中,我们总是可以得出一个内心具体的本质,来证明那些受保护的内心空间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沙瓦恰恰缺的就是这个“内心具体的本质”。家对于他一直是模糊的,生疏的。因此他从一个每天给对自己围追堵截的人准备“分钱”的老好人,变成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勇少年,再到打架成瘾成兴被退学的社会混混,其实只占用了青春一段很短的时间。
沙瓦是一家糕点店老板的孩子,当其他小伙伴只能用每天积攒的几块钱想干点大事的时候,沙瓦早饭时随便向父母开个口,一百元大钞就放在桌子上了。这是少年时期的他闻到的最初也是最多的爱的味道。父母把爱的付出自以为是地等价为了金钱的给予。他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优秀的哥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摆脱不了父母时刻比对自己和哥哥的阴影,而钱的增量也徒增爱的稀薄。
青春期的少年各有各的问题,在自我意识开始萌生的年纪,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疑问。而大多数父母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对待这些曾经以为吃饱穿暖就没那么多为什么的孩子,或者父母的青春也是这样被忽视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有准备好接纳或者不想费心思去琢磨这样年纪的孩子。
《空间的诗学》中提到家宅最宝贵的益处是:“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能够让我们在安详中做梦。并非只有思想和经验才能证明人的价值。有些代表人内心深处的价值是属于梦想的。梦想甚至有一种自我增值的特权。它直接享受着它的存在。”[3](P5)所以在这样被疏离、被对比的环境下长大的沙瓦,根本无从体会家宅最重要的价值意义。他开始没有梦想,后来误入歧途觉得打架斗殴就是锄强扶弱、就是梦想,他在认识那一帮真的好朋友之前,对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一直是迷惘和缺失的。当父母一味用金钱填补这种亲密关系中的黑洞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加速了沙瓦内心对家宅的意义的坍缩,这里不是一个真正能让自己得以存在的空间。这里只是一个住所,是没有生气没有灵魂的住所而已。他需要的是一种让自己真正活过来、活起来的意义的空间。
意义,是灵魂的收割机。对意义的追寻往往会被世间的虚无草草盖棺。所以最需要被小心呵护,认真引领的这段青春期,大多数少年的命运就这样有意无意地被视而不见了。反正有没有这一段的迷茫,日子都是要过下去的。和所有青春期的我们一样,在紧追不舍的盛大迷茫中,沙瓦带着一颗半推半就的心,把自己往迷失里狠狠又踹了几脚。半只烟、几罐啤酒和躁动地打架斗殴中,刺激藏在孤独的身后不断添油加醋。沙瓦不是一个坏小孩,但是在他曾经那么努力都无法解释青春各种感触的时候,他开始转身主动攻击这个世界。他的善意,无法被这个世界理解,也无法让自己快乐并找到意义,但是他发现恶意,可以带来快感,恶意的流动可以让青春的意义不再那么重要。快感,是治疗青春阵痛的一剂猛药。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就从心理学的因素来解释过革命为何会突然停止,其实这也和青春期叛逆的我们那种极端的盲从与激进的认知一个道理,最终都会陷入巨大的麻木与虚无。他说:“快乐,就像痛苦一样,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而且如果所有的情感过于激烈,都会导致感觉麻木。”[4](P11)
不问目的的打架,让自己躁动的心,在可能是幻觉的光亮中得到一点点平静。随后,沙瓦被退学了。他知道之前的一切的确都是幻觉,而退学以后的他也不准备清醒过来,幻觉中的无意义和清醒中的有意义,没有谁更好或者更坏。度过青春的一百种方式,都有青春自恰的理由。当时的沙瓦觉得最昏暗无助的时候,义气比意义重要太多了。然而在一次次自我破碎又被七零八落地挽救回来之后,意义还是悄悄来到他身边了。沙瓦遇到了青春时代几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朋友:余大石、习句、庄可天还有齐谷。余大石在打架中突然的死亡,让沙瓦第一次感受到活着本身或许就是最大的意义。
三、成长中的自我探寻:爱而不得
在生者身上意义难寻的时候,死亡有时候是最好的唤醒意义的方式。不过死亡,只是让沙瓦明白了一点意义,习句和齐谷的出现,这种带着全新生命力的召唤,在一个摆脱家宅既定空间的新维度中,给他打开了新的价值空间,让他看到了希望,并可以寄存更多的希望。
习句是一个患有早衰病症的诗歌爱好者,他每遇到一个新朋友都会作诗相赠。年龄和面貌如此不相称的他,偏偏对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热情,好像今天如果用不完,明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一样。事实上他的这个病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别人用来挥霍的青春,对他而言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所以他用尽力气去写诗,去记录美好,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诗集可以出版,那么他就可以摆脱私生子的这顶帽子,找到真正的那个同样爱写诗的父亲。沙瓦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习句的这种执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可是当习句对诗歌的热爱和坚持,让一个早衰的生命绽放出那么耀眼的光芒时,沙瓦逐渐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这是生命和现实赤膊相见的时候,最震撼的光芒。在习句和沙瓦构建的这个友情的正向流动的空间中,他那被疾病即将压垮却靠意志力支撑起来的小小身躯,在诗歌的面前变得剽悍、矫健,洋溢着一种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欣然相迎的强韧精神力量。他虽然那么瘦弱、丑陋、虽然爱而不得(他想出版诗集,想寻找自己的父亲),但是在沙瓦眼中,这是比炽热的太阳、盛开的向日葵、聒噪的鸣蝉更为全情投入、更为无我、更为壮烈的一种美感。这是对生命本身和父爱的渴求,激发出的生命的一种无意识状态,然而这种无意识比青春期所有的有意识都更具魅力,因为它真挚、强大、不矫情、在生命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不会让人觉得悲壮,反而只会觉得壮大。
虽然沙瓦很舍不得这些朋友,但最后还是决定跟随父母飞去美国投奔哥哥。他羡慕像习句这种在无意义的废墟上,让诗歌照亮生命的有意义的举动,但是他依然在无滋无味的青春尾巴上,咂摸着那些迷失带来的成瘾的堕落。青春时代的友情是拉着你臂弯的那只手,而爱情才是让你清醒的一巴掌。
绿衣少女齐谷的出现,让沙瓦毅然决定留在这片生养自己的故土。这是在友情的空间给了他积极的自我探寻之后,又一次在爱情的维度促使自己的生命全新地打开一次。在这里他会遇到逐渐觉醒的自己。那是很平常的一天,但是他和庄可天一同被天桥上飘过的这位仙女迷住了。后来他们知道这个女孩叫做齐谷,就在南淮大学门口的旁边开了一个书店。沙瓦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个正规大学毕业,又如此优秀的经营着一家书店的女孩,但是他就是爱上了。而他同时悲催地发现自己迟了一步,庄可天也深爱上了这个出众的女孩。所以沙瓦对她的感情打算一直深深埋在心里。但这份不会开花结果的爱情,倒让沙瓦心里的春天真正赶来了。沙瓦觉得那是一种很奇妙的唤醒,他认为真正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它会以别的形式在生命中留下点什么,又开启些什么。
爱上齐谷以后的沙瓦,开始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曾经的自己认为意义是一种气势汹汹的东西,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一种存在,所以整个青春时代,他都在费劲心力地找寻这样的意义,但是最终是虚空,是徒劳。因为生活就是结结实实贴地皮的一种前行方式,命运总是在迷失的时候伴随着毫无意义的各种颠簸,但自己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命运很少会大开大合,就是一些平凡细碎到骨血里的磨人日常。直到有一天,你忽然遇到了生命中那个真正的“意义”,可以是一段爱情,可以是彻底失去的一段亲情或者友情,你会忽然明白,所有的追寻最终都要回到当下。从那些平时最看不上的不起眼的小事认真做起,摒弃那些好高骛远和眼高手低,你会发现在一些支离破碎中,慢慢体会到一种脚踏实地的幸福。那时候你的心会敞亮起来,不会再死磕在意义这个层面了,你会带光前行,意义便紧随其后。
其实第一次看到沙瓦这个名字,就莫名联想到很喜欢的《山月记》中有几句话:“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5](P15)遇到齐谷之前的沙瓦应该是在类似这样的状态中睡眼惺忪,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又怯懦羞耻。所以青春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害怕暴露自己才华不足之卑劣的恐惧和不肯刻苦用功的无耻之怠惰”中消磨没有了。直到爱的萌生,让他忽然顿悟,不肯虚度的每一秒当下,就是意义。于是他在离那个美梦最近的大学报了汽车技工修理学院,每天做着又脏又累的技术活,傍晚就会溜达到学校旁边的书店,从外面的灯火阑珊中急切地寻找店里那个点燃自己生命的身影。虽然从未走近,也没有机会再点破,但是沙瓦心里总是如沐春风般的。他和庄可天一起爱上了齐谷,但是谁也没有走进她的心里。因为齐谷,也是一个正在寻找爱和意义的人,她的心全部在另一个男孩子身上,他叫齐峰。是在齐谷很小失去家的时候,唯一让她有了家的感觉的帅气的大哥哥。但是这份复杂的爱,依然是不能言明的,因为齐峰始终把齐谷当做需要被照顾和呵护的妹妹,而自己的身边也早有了深爱并不离不弃之人。可能齐谷身上那种淡淡的忧郁和出尘脱俗的凄美,和自己的身世以及一生放不下也得不到的人有关。
一段多米诺骨牌的爱情,似乎永远是顺向的链条式反应,从不能转身相遇。在这样一个看似积极的友情和爱情营造的空间中,每个人都在“爱而不能”中,不断地去探寻,去了解别人,也更加深入地认知自己。这种探寻更加促使爱情中失意的三个人互相抱团取暖。沙瓦、庄可天还有齐谷,慢慢形成三人小团队,他们在尽可能小心地维系着这段外人不理解,自己似乎也解释不清的关系。但沙瓦明白,只要能时不时看到齐谷,他的生命就不会再次迷失,而庄可天是比沙瓦更勇敢的一种守护,他大方地表明爱意,并决心无论齐谷心里的人停留多久,都不会影响他对齐谷的爱。而齐谷心里清楚,齐峰对她而言,不仅是爱情一样的存在,更是一种生命的意义,一个前方永不熄灭的火种。齐峰心里的爱,似乎更是一种超越,那是和自然的比邻与相依,他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亲吻天空,向天地表达自己用生命酝酿出的敬意。齐谷曾经赌气又不解地和齐峰说:“一见到山,你就成了精灵。”齐峰的确是这样的人,他对登山的执着和酷爱,已经逐渐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他不理解为何一定要日新月异地去改变大家熟悉的城市,和这种多变带来的不适相比,登山的这种固有的敬畏反倒更能给自己一份安全感。
但齐谷还是不明白为何一次次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也要攀登珠峰。她甚至误认为这是人们在类似飙车中所谓体验的那种快感。但是齐峰认为这种极限绝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单纯的刺激和放纵:
“登山是对自然和自我心灵的亲近,它属于孤独者的事业。一个让你疏离自我,让你在无限的沉沦中收获自我毁灭的乐趣,而另一个却是让你面对自我,让你在不断的进取中体验生命丰富的意义。二者怎能相提并论呢?”
齐峰在一次次试图登顶的过程中,留下遗憾,最终在雪崩中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珠峰。但是这次齐峰一点都没有遗憾了,因为他把有限的生命用在了一次次追求完美中,虽然完美不曾到来,但是这种无限靠近的感觉,就是齐峰认为最重要的生命的意义。遗憾,让完美更加尊贵。而且生命虽然消失,但是对山的这份忠贞的爱恋,会让灵魂不死。
齐峰对山的爱而不能,齐谷对齐峰的爱而不能,沙瓦对齐谷的爱而不能……都不仅没能摧毁自体,反倒是让自体一点点蜕变强大,跃升到生命更高的层面。从惧怕平庸惧怕死亡,到可以直视并平和地接受一切。在遇到外部困难的时候,并不再一味地向外寻求解决之道,而是向内寻找。让自己的内心做好能够承受此种困难的准备。不是慌慌张张地临时应对,而是在很早之前似乎就拥有了这份坦然和坚定的幸福。不再寻找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整个世界上已经逐渐不需要有那么多需要破解之事了。一切都在顺应中流动并清晰起来。
四、自体的深层觉知:让爱流动
自我探寻之后,会进入一种自体深层的觉知。探寻后会使得物我之间的相对位置产生位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又事事处处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渴望,这是爱在每个人、每种关系的流动中带来的最高级的价值。被波浪卷走的人会淹死,而乘在波浪之上的人是能够超越它的。所以一切都不是停滞不变的,物我之间相对的位置至关重要。
要首先看到并且让自己不断超越这种有为转变,再次达到不坏不动的境地。但是世间又有几人能完全超越是非、超越善恶,物我两忘呢?大部分凡人都在试图超越或者超越的进行中,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这个尽头,不是终点,它是自我升华的新的起点。齐谷感受到这种超越于生命之上的震颤和博大是在最爱的齐峰死后。她意识到肉体的消亡,绝不会带来爱的泯灭,她对齐峰的爱,是可以感召天地的。她一个人只身来到珠峰下,在一声声声嘶力竭的呼喊中,她蓦然看到:
“浑身披挂着冰雪的齐峰从山峰上朝自己走来,而另一个携带着春风的新生的自己也正在向对方走去。他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这旷世的拥抱啊。冰雪融化了,春风止息了,剩下的唯有一座顶天立地的高峰,在用永生的巍峨与庄严印证着一种不朽的爱和坚持。”
凝固的爱,是小我之间的情欲,爱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更好更无私地滋养着自体和客体。抛开意识头脑层面的自我,和卸下面具包袱的你,赤裸又真诚地相对。此时的生命,让爱意在流动中,积攒出了无限的力量。在这份旷世的拥抱中的爱,已经超越了男女之情,也超越了救赎之意,这份爱,可以让人性中所有自私和阴暗的部分土崩瓦解,激发迸射出一个更好更强大的你。
而沙瓦对齐谷的爱,也在追逐中有了新的流动。不再是胆怯和羞涩的守望,而是主动地扬帆起航。曾经的沙瓦觉得一份藏起来的爱,是可以将它保值的最好的方式。他小心地维系着和齐谷之间这份情感的平衡,怕戳破会失去得更多。所以退守并默默看着齐谷,就成了自我感动的最好的爱她的方式。所以后来沙瓦也曾经一度放弃齐谷,和贵子开始了爱恋。但是他知道齐谷是他心底永远的女神,那一沓沓写了又不敢寄出的写给齐谷的情诗,是对沙瓦这个一度要腐坏的生命最真诚和及时的救赎。虽然齐谷什么也不知道。这份爱在沙瓦心里的流动中也在长成,从最初以占有为目的,害怕失去,逐渐由单向度变为多向度的循环往复,变成以存在为形式,就是不断去承认这种爱恋的改变,让其尽情流动,在变化的过程中大胆释放自己的爱慕和善意。不仅自己获得了自由,也让被爱的对象获得了永久的自由。这种爱是一种高尚的成全。
所以当齐谷彻底失联去寻找自己心中永恒的爱的时候,沙瓦终于也鼓起勇气打破了那个封闭的胆怯的自我,他想让自己对齐谷这份爱意也汹涌澎湃起来,他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庄可天为了齐谷进了监狱,但是自己总是在爱的外围兜兜转转,这份自以为是的守护,真的对齐谷有意义吗?这份静止的狭隘的爱意,本质上只是成全了自己的自尊心和羞耻心。所以最后沙瓦什么也不想再考虑了,何为意义呢?意义就是当下的我亟待要寻找到内心最爱的齐谷,要让她知道,爱不仅仅是占有,更是一种谦卑地进入关系和守护生命的态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沙瓦对自己的觉知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因为理解自己这份爱的存在,而更加感受到给爱自由,比让爱凝固更伟大。沙瓦从最初的被动胆怯,这种僵死的占有模式,进化到全新的“存在型生存模式”,也就是独立,自由和批判理性。这种积极主动也意味着:“自我更新、成长、流露、热爱、超越孤立自我的藩篱、对一切兴致盎然、热切期待并且不吝给与。”[1](P97)爱在流动中,让沙瓦感受到了那种灵与肉的暂且分离,真爱可以战胜一切,它以不求回应的姿态,已经赢得了万物。灵魂的交融和追求,会减少对肉体死亡的恐惧。这是爱最大的魅力。他飞奔在寻找的路上,只不过这次不是在寻找虚无的意义,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意义,因为它在与爱,一起飞行。
注释
[1][美]艾里希.弗洛姆著,程雪芳译.占有还是存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2]路文彬.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5][日]中岛敦著,徐建雄译.山月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