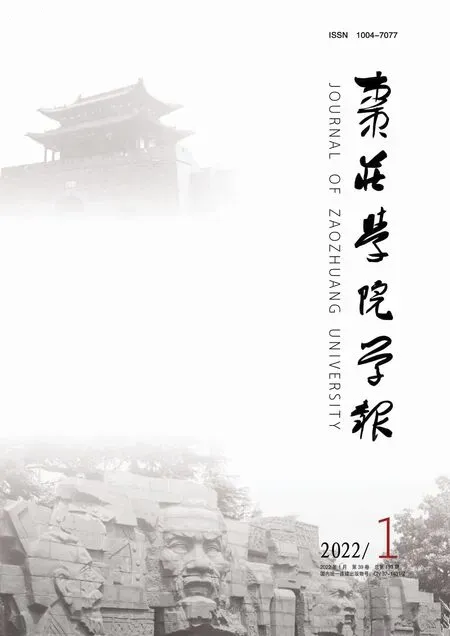《又见桃花开》:高原女性的精神成长及其困境
2023-01-11苏文韬
苏文韬
(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
云南女作家李云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桃花开》以女性敏锐的视角与独到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极为鲜活的当代云南高原女性形象。小说以女主人公“桃花”及她身边的女性们满怀深情地走进男人的世界,在受到男人的误解、背叛、抛弃之后,仍然痴心地在男女的情感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痛苦心灵历程,展示了女性对男权的理性审视和对男性话语权的拒绝。
《又见桃花开》成功塑造了多个彝族女性形象,与汉族女性相比,少数民族女性无疑是更刚烈、坚韧、顽强却又不失女性独有的柔美与母性的,当代文学史中无数个著名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无疑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张承志《黑骏马》中敢爱敢恨的蒙古族少女“索米亚”,电影《五朵金花》中倔强追求爱情的白族女性“金花”。《又见桃花开》中也刻画了一个因为家乡“老蛙寨”的贫穷而被迫当了妓女,不惜以“牺牲我一个,拯救我一家”的勇敢来承担下家庭一切苦难,并在“桃花”的帮助之下摆脱贫困,拯救自己与家庭的坚韧彝族女性“李秀彩”。彝族自古是“火神”“虎神”等多神崇拜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崇拜女性的民族,这一点从彝族神话“三女找太阳”的传说中便可见到,由此也造就了彝族女性坚韧、担当、勇敢、勤劳的特点。当代彝族女性及高原女性早已摆脱了落后、贫穷、愚昧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论及当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却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代社会的男性霸权给女性的精神成长带来的困境依然值得探讨,本文将对彝族女作家李云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桃花开》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叙述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究。
一、情感创痛与女性精神成长
《又见桃花开》之中的“桃花”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先不论这种爱情至上主义的正确与否,“桃花”绝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桃花”在被男人抛弃、被男人背叛的痛苦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却屡屡遭遇情感困境,于是她将男人看成了自己生命中无以逃脱的困境。作家无疑是极为敏锐的,她抓住了女性本身不论情感或是生理层面之于疼痛感的特有体验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剖析。“疼痛”无疑是这部小说中出现最多的语词,也是小说绕不开的一大主题。如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天地之大,每个人都拥着昨天的痛苦,迎接今天新的痛苦,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经受痛苦,最终以死亡结束痛苦,使痛苦得到终极化的最好诠释。”[1](P10)
“‘处在痛苦中的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那就是痛苦。’‘你就这么确定。’‘是的,我敢确定你和我有着共同的熟人。’‘痛苦吗?’‘是的’”[1](P11)。
“我的痛苦是我的爱人有了别的女人,成了一个病态狂,老化的痛苦是他的爱人抛弃了他。”[1](P16)
由引文可知,“老化”与“桃花”的相遇正是源于他们共同的痛苦,情感的创痛恰给他们创造了新的爱情的机缘。与此同时,正如“桃花”自己所言,人不经历痛苦是不可能会成长、成熟的,也正是在经历过不同的伤害之后,人的精神才能得以成长,“人因痛苦生成精神,精神使痛苦的人成为真之灵魂”[2](P122)。在此,作者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女性独特的比男性要强得多的痛感经验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描写,这一点无疑是成功的。女性不论是在情感上或是生理上对于疼痛的感知能力都要比男性要强得多,而这恰源自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经验。“在这种经验看来,所有的男性都是出自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血肉。所以,他们无法旁观男性们的痛苦。男性则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是源于他们背叛的天性,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属于的母体,及其所给予的精心哺育。他们的独立与自由显然是以背叛和遗忘为代价的。”[3](P3)因此,不难看出女性是比男性更具历史性的存在。女性出于她们自己本身的母性,因此,他们无法直视男人们的痛苦。与此相比,男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就要弱小得多,恰恰是女性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身处于痛苦之中的男人们。很多的时刻,与其说他们是男人,倒不如说他们是那还依旧没有长大的孩子,是女人给了他们一个如同母亲一样的温暖怀抱。
如果说“桃花”与“老化”的相遇更多的是因为彼此共同的痛苦的话,那么“桃花”与之前所深爱的“家仁”的相遇就是个彻底的悲剧。相较于“老化”极强的责任感与他本身社会阅历与经历造就的成熟,“家仁”显然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当“桃花”想要强行与“家仁”分手的时刻,他显露出了自己极为不成熟的一面,他甚至强奸了她。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那晚,我被家仁折腾着,一个烂醉如泥的女人是没有力量反抗一头野兽的,就这样,家仁在有了别的女人后强奸了我,是的,我们曾经的欢爱被他演绎成了肮脏的奸污,我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P39)
正是家仁的这次行为使得“桃花”彻底看清了他,放下了他而真正爱上了“老化”,决定跟他在一起。但是“桃花”又是极为不幸的,没有跟“老化”过上多久的好日子,做药品生意的“老化”却因为这次事件对“家仁”大打出手而进了监狱,最终只留得“桃花”一个人来面对着这散落一地的情感碎片,当她自己拾掇起这些碎片时,却茫然发现所有的一切痛苦还是得自己来承担,男人在她的世界里只不过是一个来了又去带给她无尽伤痛的符号而已。
受伤,几乎是小说中“桃花”的专有名词,作为一个女作家的“桃花”显然是敏感又多情的,俨然是当代“林黛玉”,她一直在男人们的世界里打转,而正是她的敏感给她带来了太多的苦痛。“桃花”能否在这些情伤里得以成长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她本身就将自己长期陷在与男人的战争里无法自拔,小说中这种明显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两性观念亦是十分可疑的。如小说中有着这样的描写:“男人成了女人的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男人即使每日里依香偎翠,夜夜笙歌,仍然可以一身光鲜,一脸坦然,不留任何痕迹,女人则不同。”[1](P229)小说中多次有着这样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观念,而这恰是女性无法在痛苦之中得以升华与成长的原因。要知道,这种性别对立的观念恰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压在女人们身上沉重的枷锁,在这种男权社会之中,不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没有谁会是真正胜利的一方,因为他们彼此互为困境。正如同小说中有着这样的追问,“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女人有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是女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的,更可悲的是,女人一辈子都无法改变这些困境,都必然需在这些困境中寻找出口。”[1](P175)在此,这种男尊女卑传统世俗观念的卑劣一面展现无遗。男权社会之中,不论男女,没有任何一方是真正自由的,女性在这种社会中只不过是更不自由的存在罢了。女性们所要反抗的绝非是某一个给她带来了情感创伤的男性,而应该是这种压在自己和这个社会之上沉重的枷锁。如果女人本身还沉沦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两性观念之中,那么不论经历多少伤痛,女性在精神上一定是无法得以真正的成长与成熟的。只有打破这种狭隘的观念,女性本身才能在痛苦之中得以成长,关于两性二元对立观念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笔者将在下文予以具体分析。在此,女人与男人不同,女人一生下来就有着很多困境。这种判断无疑是很正确的,恰如波伏娃所言说的那样。女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生下来就是被社会定义为第二性的:
“只要家庭和私有财产世袭依旧作为社会的基础,女人就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女人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只有从家庭逃脱。”[4](P46)
“女人永远是他者,因此男女并非彼此之间互为罪恶。”[4](P68)
“男人自相矛盾地希望迫使女人只有扮演双重角色:男人要让女人专属于她,又想女性与他无关,他理想中的女人既是女仆又是荡妇。”[4](P82)
“女人是逐渐形成的。从生理、心理或是经济因素,是整个文明社会决定了女人的他者属性。”[4](P116)
基于此,身处男权社会的女性其本身就是一种他者性的存在,她们大多都附属于男性。当代女性要想真正在精神上得以成长就必须要冲破男权社会所给予她们的沉重枷锁,女性的成长之路道阻且艰,关键还是在于女性们对于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的觉醒。痛苦,是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痛苦造就了真之灵魂,唯有选择理性而非沉沦于情感,才是女性摆脱自我困境的唯一选择。
二、爱情癔症与女性成长困境
小说中的“桃花”是一个彻底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爱情的癔症曾经一度折磨得她生不如死。在经历无数的心灵疼痛之后,“桃花”逐渐意识到只有逃离男人这个困境才能拯救自我。她开始拒绝男人,甚至拒绝男人的世界。她把自己的一切深埋在女性的“祈语”里,在对男人世界渐行渐远的迷惘中失去了爱的能力。然而“老化”的出现,上天又再一次将一种缠绕在女性左右的强大的不可抗拒的男性磁场、男人的阳刚与豁达、温柔与体贴或明或暗地呈送到她的面前,像一股股温热的琼浆玉液,一次次润泽着她干涸凄绝的心路,她又一次成为爱情的俘虏。她的内心中始终在呐喊着:“女人过不了男人这道坎。”她一次次冒着更大的情感伤害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进入爱情的魔法之园,她老是无法放过自己纠缠在两个男人中间无法自拔。热爱爱情是无可厚非的,爱情恰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但是沉迷于爱情之中的“桃花”却是一个彻底的爱情癔症患者,与其说她过不了男人的那道坎,还不如说她是过不了自己的那道坎。“桃花”将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女人是水做的,点点滴滴需要男人来珍惜。女人是脆弱的,时时处处需要男人来呵护。女人是美丽的,花蕊片片只有男人能品味。”[1](P41)
“女人的信仰是爱情,是拥有一个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在女人的心目中,爱情是高于一切的。”[1](P188)
在此“桃花”无疑是一个有着“恋爱脑”、爱情至上的女人,将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奉为自己信仰的“桃花”对爱情的彻底失望亦是必然的。爱情本身其实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有缘人对它的理解。人本就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如果在爱情或者情感之中彻底沉沦,那便等同于放弃了上帝赋予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故此,情感便会彻底成为一道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失去了理性的情感其本身的依赖性便会使人堕落,最终使人失去自由。患有爱情癔症或情感依赖症的“桃花”一次又一次在这多巴胺与催产素的折磨下就范,如果“桃花”结了婚进入了婚姻的状态,那她也会对婚姻彻底绝望的,婚姻是爱情坟墓的原因是因为人们错误地看待了爱情。不论是“家仁”还是“老化”对于“桃花”只有着赤裸裸的占有,然而“桃花”呢?她对于男人从一而终的道德要求不也只是对于这种占有付之于同样是占有的回应的吗?他们之间有着真正的以自由为前提的爱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爱情’作为名词只是对爱这一活动的抽象,与人是脱离的。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情成了偶像,人把自己的爱投射到这种偶像崇拜之中。他不再是感觉着的人,而是异化为一个偶像的崇拜者。”[5](P10)彻底沉沦于爱情中的两个人在这场占有的游戏之中、在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而逐渐异化,彼此占有着的双方之主体意识都是很难以真正存在的。“‘存在’(being)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其中之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拥有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5](P7)基于此,爱情需要在这种简单的相互占有的关系之中得以成长与升华为真正的爱,单纯的爱情在占有的同时必然是要求要有所回报的,这种简单的债务关系玷污了爱,而真正的爱是自由的,因此是不要求回报的。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一种爱之渴望,且因主体在施予爱时不具因施恩而想要得到回报的要求,爱本是便是最大的回报。”[6](P1)亦如弗洛姆所言:“‘爱’是强大者之于弱小者的给予,爱是在对方身上唤起有生命力的东西。”[7](P145)因此,爱情癔症患者“桃花”或与此相似的中国女性,要想在爱情之中得以成长就必须在这种爱情关系之中理性地坚守住自我的主体性,不在爱情之中沉沦。除了爱情,女性亦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追求,事业也好、家庭也罢这些追求并不是有了爱情就足够的,而也只有在自由之爱里女性才能真正得以成长与成熟。除此之外,在男权社会之中,占有性质的从一而终的爱情或婚姻本身也已经沦为了压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中国文学史上那一个个女性或从一而终或两小无猜的纯美爱情故事,不恰恰就是使得女性无法摆脱爱情困境的绝美骗局么?正如小说中所言,男性大可以三妻四妾,风流逍遥,而女性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在男人与男权社会一起合谋编织的巨大困境之中挣扎,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女性的不幸。怨天尤人做个怨妇与情种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重要的不是仇恨,而是爱,是和解而不是冲突。对于女性,真正的和解是要同那个饱经创痛的自己和解,唯有真正与自己和解才能真正拥有爱的能力。小说中的“桃花”是匮乏这一能力的,并不是任何人剥夺了她的能力,而是她的认知无形之中剥夺了她的能力。因此,唯有彻底消解爱情至上主义才能真正拥抱爱情,拥有爱之能力,这理应是当代女性精神成长的必修课程。
“李秀彩”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正是“李秀彩”悲苦的经历和命运彻底唤醒了“桃花”的女性主体意识。“李秀彩”的命运是极为悲苦的,小说中写道:
“牺牲我一个,富裕一家人,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让弟弟能够好好地读书,我就牺牲了自己吧,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让我耻辱地活到今天。”“想不到在这样一个想来很肮脏的灵魂深处,竟然还能隐藏着如此夺目的牺牲意识。”[1](P127)
“李秀彩孤独的身影在老蛙寨寂寥的夜空里沉寂,老蛙寨的人在李秀彩在家的日子里诅咒着李秀彩的堕落,声称这样的女人死后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李秀彩在老蛙寨只有黑夜。”[1](P130)
老蛙寨的李秀彩在赚到了钱之后并没有只想着自己与自己的家庭,当寨里的阿亮父亲生病急需钱救命的时候她毅然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你们不就嫌我的钱脏吗?这种紧要关头什么钱都是钱,都能救人的命,救人要紧。’李秀彩毅然将钱塞到了阿亮手里。”[1](P131)在到山区扶贫认识了“李秀彩”,了解了她因为全家的贫穷而不得不去做妓女,回到寨子里积极拯救寨子里村民的事情之后,“桃花”决定一定要帮助她,让她进城工作,从而真正改变了同为女人的“李秀彩”的命运。“桃花”也就此开始真正变得坚强了起来。小说这样写道:
“李秀彩是因为家乡的变化而找回了自救的勇气,我是因为李秀彩而看到了不堪的自己。在挽救李秀彩的同时,李秀彩也挽救了我,她让我感觉到,一个人必须自救然后才能获得重生。”[1](P134)
至此,在经历了两个男人对自己的伤害之后的“桃花”鼓足勇气准备逃离爱情的桎梏,开始了自己的自救之路。
四、性别二元对立与女性成长之困
回城之后的“桃花”帮助“李秀彩”以及寨子里的彝族姑娘找到了在彝族服装厂的工作,之后又帮助他们积极创业赚钱。同时,“桃花”为了拯救因自己而遭遇牢狱之灾的男人,她毅然选择抛弃自己的爱情,在她的心目之中正义是第一位的,此时的她必须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了实现拯救他人灵魂的崇高精神理想,她背离了心爱的男人,为自己的理想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在此期间,“桃花”对于“老化”不是没有过期盼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曾有过太多故事的女人,“老化”对于他们的感情是并不坚定的,“桃花”的背离同样引来了自己心爱的男人的背离。在经历了这个男人再一次选择离开自己的时候,她忽然顿悟,男人和女人是互为困境的,在情感的纠葛中根本没有谁胜谁负。她在拯救她人灵魂的同时自己坠入了人格尊严的强烈危机之中,她拯救着别人却让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此,她毅然决定脱离男人这个困境而获得身体和灵魂的自由和再生。恰如同当年鲁迅笔下的“涓生”那样毅然出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在彝人古镇桃花盛开的季节里为自己凄绝的过去唱响了嘹亮的挽歌。在此,作家笔下的“桃花”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早已伤痕累累的女性的灵魂对于男性社会的一个拒绝。这种拒绝体现出的正是女性对这男性霸权社会的彻底绝望、失落与茫然。正如同当年的“涓生”出走一样,红土高原的女性“桃花”的出走似乎并没有多少的新意,但是这已经快要过去近一百年的女性于文本之中的再次出走,除了显明的复调色彩外,其拷问的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社会在走过了近一百年的路后,男权的暗影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笼罩着。追问“桃花”出走后会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答案已然写在了文本中,她要么更堕落了,要么又开始重复之前的老路了。历史是那么可悲的相似,女性独立与成长之路是何其艰辛,如果不彻底清洗这腐朽与堕落的男权思想和两性二元对立观念,女性之成熟更是无从谈起。
“桃花”出走之后的路将是异常艰辛的,最为可悲的便是“桃花”作为女性本身自始至终都未能彻底认清性别二元对立观念的本性,她即便走出了这个男人的困境,但是很有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男人的困境之中去。“即是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敌对关系,那也不过就是一种虚假的关系,是知识贫乏所造成的对于真理关系的蒙蔽。”[3](P4)此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所消解的便是男女双方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不在恰恰证明了这种二元关系已然彻底背离了爱情之中自由的本质。当自由遭临遏抑之时便是真爱消逝之时,爱情的本质理应是自由的,失却了自由的所谓爱情关系已经异化为彻头彻尾的债务关系。建立在债务关系基础之上的所谓情感是没有未来与成长空间可言的,此种情感所招致的只能是彼此的消费与消耗,最终的结局便是一种彻底的悲观与虚无罢了。从小说之中不难发现此种消费、消耗最终消解彼此关系的影子,而这也正是男女两性二元对立观念的可悲可鄙之处。因此,女性要真正走向个体的觉醒、成长与成熟就必须得打破这横亘在两性之间的藩篱,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在理性之爱里得以成长。
《又见桃花开》是一部写在高原之上的女性赞歌,小说中的高原女性,特别是彝族女性所展现出的坚韧、勇敢与担当精神是红土高原所赋予她们的一抹独特的亮色。纵览整个当代女性文学史,高原女性及女性形象必将永存于读者们的心中。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正如同中国其他女性文学一样,云南当代女性文学仍然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伦理并不足够成熟,女性意识依然受到男权意识影响:
“中国小说,男性话语呈现出很复杂的‘女性镜像’:女性是柔弱的、服从者、听命者,是社会和家庭中被压迫的群体,这是对女性在家庭、社会和文化中的身份定位,以便男性在俯视和窥视中施与启蒙与拯救。”[8](P50)
而这种启蒙与拯救又往往是以从一而终的爱情幻象与美丽童话的方式不断出现的,中国的女权及其意识总是在崇古与突围之中苦苦针扎,女性本身究竟如何准确地确立起自己的性别定位与权利意识,不再只是简单地反抗男权而忽视了本应该得到重视的女权,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女人如何来做女人,如何来认识自己的性别,而不再只是在“女人能顶半边天”强烈的非理性呼声之中不断地与男性去争取平等的权利,甚至异化成为“女男人”而彻底背离了自己的女性本质,这是值得探讨与关注的一大问题。“女性向男性本质看齐的所谓平等,不是提升了自己,而是在时代标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自己、迷失自己。”[8](P147)
女性所应争取的是权利,而绝非带有暴力性质的权力。女性觉醒与自由之路道阻且艰,但是仍需不断前行,女性之觉醒与自由亦需男性之觉醒与自由。女人是女人们自己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