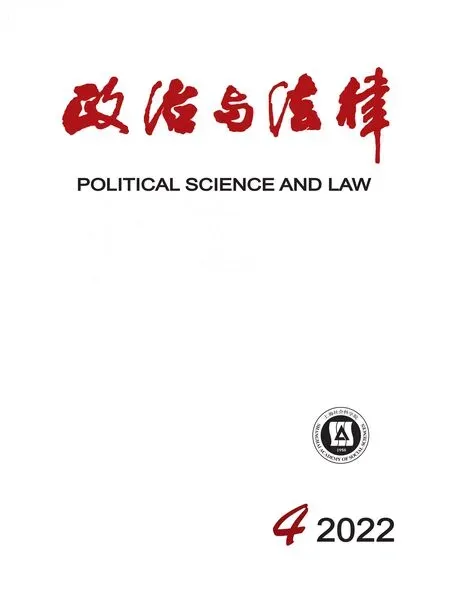不作为因果关系判断中的自由意志与规范假设
2023-01-09喻浩东
喻浩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在结果犯的构成要件认定中,因果关系的确立是构成要件结果得以归责的前提。在“归因—归责”的二分框架下,为归责提供事实性基础的因果关系之判断适用条件公式,即对于结果出现的条件,如果不能想象其不存在,否则结果就不会出现,那么该条件就是该结果出现的原因。〔1〕Vgl.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2006,§ 11 Rn.7.尽管这一表述通常指代作为犯中行为与结果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但对于不作为的因果关系认定来说应当同样适用,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一个完整的因果性解释来说,不仅需要积极的条件,而且需要消极的条件,而结果的发生恰恰以不存在阻碍结果发生的因素为必要前提。〔2〕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30 Rn.22.只不过由于不作为因果关系考察的是倘若履行了作为义务能否避免结果发生,因此其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和规范归责关联的判断也就合二为一了。然而条件公式根本不是扮演在个案中查明某一行为之因果关系的工具性角色,它毋宁试图在已知的因果关联的基础上,阐明因果关系概念的内涵。〔3〕Vgl.Frisch,Die Conditio-Formel:Anweisung zur Tatsachenfeststellung oder normative Aussage? Festschrift für Karl Heinz Gössel,2002,S.60.之所以能够斩钉截铁地声称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自然法则和交往法则,以至于在判断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时,根本不需要再去论证该自然法则或交往法则的存在。〔4〕Vgl.Frisch,Die Conditio-Formel:Anweisung zur Tatsachenfeststellung oder normative Aussage? Festschrift für Karl Heinz Gössel,2002,S.68.张明楷教授同样指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是以存在因果法则上的知识为前提的,而在判断者知悉相关因果法则的情况下,既能肯定条件关系,又能肯定合法则性条件关系。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5 页。但在损害结果的发生由多个自由意志的主体共同导致的场合,要认定先行为人怠于履行作为义务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条件公式就会遭遇失灵:由于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因果法则,也即,当其中一个主体履行义务时,其他主体是否也会履行义务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志,因而无法认定不作为与结果间的条件关系。
以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案件为例,可以明显发现条件公式的失灵:一方面,就算生产商发出召回命令,但零售商是否会按照该命令合乎义务地执行召回决定,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志的决定;另一方面,即便生产商和销售商向消费者发出了召回通告,但消费者是否会按要求退回缺陷产品,也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志的决定。如此也就难以认定生产商倘若履行召回义务就一定能够阻止消费者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寻求这一问题的教义学解决方案,本文将以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典型案件为切入,尝试运用规范论思维来构建不作为因果关系在自由意志介入下的判断标准。
一、自由意志介入与条件公式的困境
在“三鹿奶粉案”中,被告单位石家庄市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07 年12 月就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出现尿液中有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 年5 月20 日,该集团为查明原因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经排查确认,婴幼儿系列奶粉中“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 至6 倍,因而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但是该集团领导层并未就此开会决定停止生产、销售并召回该系列的问题奶粉。直至2008 年8 月1 日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测报告确证三聚氰胺的存在后,该集团领导人才组织召开了经营班子扩大会议,决定暂时封存仓库产品、停止产品出库且以返货形式换回市场上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5〕参见《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9 年第4 期。
三鹿集团实际上同时涉及两段怠于召回缺陷奶粉的事实:一段是从2008 年5 月20 日怀疑可能有三聚氰胺时起至8 月1 日明确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时止。在此期间,尽管三聚氰胺并未得到检测证明,但该集团领导层对此具有预见可能性、能够预见到婴幼儿若继续食用该奶粉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集团领导层成员涉嫌怠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过失不作为责任。另一段是从2008 年8 月1日明确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且该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开会做出决定时起,至2008 年9 月12 日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时止。在此期间,该集团领导层已经明知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实以及认识到继续食用该奶粉将会给婴幼儿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涉嫌怠于召回缺陷产品的故意不作为责任。
追究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以认定不作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为前提,然而按照传统的条件说,即便该集团领导层做出集体决策发布了召回命令,也未必能够成功阻止流通中的缺陷产品。因为这取决于零售商和消费者是否会执行或者配合召回措施。审理法院将判决重心完全置于生产者继续生产、销售的作为之上,因此也就未能考虑这一不作为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但在德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类似的问题多次得到了审理法院的关注,并引发了刑法学界的争论。案例1:皮革喷雾剂销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于没有在最初的肺水肿病症出现时引导召回行动而遭检方指控。辩护人提出,在那些使用者罹患肺水肿的个案中无法证明,如果董事会成员引导了召回行动,零售商就会执行召回的决定。〔6〕Vgl.BGHSt 37,127 f.案例2:被告人是一家运输企业的车间主任。他在检查重型卡车时发现存在刹车问题,但却怠于对后轮轴的制动鼓进行检测。于是,他只将刹车问题归咎于前轮刹车上有缺陷的调节器。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老板,并且表达了一个想法:在调节器得到修理之前,不能让该车上路行驶。可是随后老板仍然指示该车辆可以继续使用。此时,新的调节器已经到位了。后来,正是因为该车辆刹车的整体失灵,导致了一场车祸的发生,司机和另外两人不幸遇难。〔7〕Vgl.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8,S.1897.案例3:被告人曾是一家研究所的副所长,该研究所为杜塞尔多夫的多家医疗机构生产并供应血液制品。由于卫生预防措施不到位,致使五名病人被输入感染细菌的库存血,并导致了死亡。州法院判决并非直接参与该起事件的被告人构成过失杀人罪,理由是,她怠于向自己的上级以及主管当局报告存在库存血被不当处置的情况。审判庭认为,如果她真的报告了,就不会发生这起事故。〔8〕Vgl.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0,S.2754.
在案例1 中,联邦最高法院是这样论述因果关系的:“在本案中,因果性的问题呈现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在第一个层次要认定,召回行动是否本可以开展,在第二个层次则是判断,召回决定是否本可以到达夹在中间的零售商,以及第三个层次要判定,这些零售商是否就会重视召回决定,也即,确保不将会引起损害的皮革喷雾剂售卖给消费者,因而可以避免出现健康损害的结果。刑事审判庭对于处在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假定的)因果关联作出了无法律错误的说明......基于已经做出的认定,也可以肯定第一个层次的(假定的)因果关系”。〔9〕Vgl.BGHSt 37,107(127 f.).
对于前述辩护意见,联邦最高法院则驳斥道:“对召回行动和损害避免之间的假定因果关联的可证实性——通常来看——抱有怀疑的态度,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仅仅取决于这一待决案件中的真实的证据评价。”〔10〕Vgl.BGHSt 37,107(127 f.).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低估了上诉审法院的审查权限,它对于事实审法院做出的事实认定是有指摘权力的,且有义务去审查,事实审法院做出的事实认定是否与一般性经验法则或思维法则相符合。〔11〕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8.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秉持的“近乎确定可以避免结果”之判断标准,其本不应该赞同事实审法院的认定结论,因为唯一存在的经验法则恰恰是,很多零售商并不会执行召回决定。而且,一旦采用这一判断标准,那就只能得出否定因果关系成立的结论,因为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经验法则可以说明,当零售商或零售商群体接到召回决定之时,他们一定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除非零售商真的身处那样一个必须抉择的时刻,否则他也不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12〕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9.
案例2 和案例3 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案例2 中,尽管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被告人的义务违反性在于,他没有将可认识到的刹车系统的问题,即近乎损坏的后轮轴的刹车装置,全面地报告给公司老板。可是法院却质疑不作为因果关系的成立,认为被告人没有履行这一作为义务,并不意味着其不作为就与交通事故中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使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被告人全面地报告了车辆刹车系统的糟糕状况,那么就算是一个踌躇不决的老板也会被说服,且人们能期待他此时放弃单纯的图利思想。可是,老板在得到这一全面的提示后是否真的会改变主意,阻止车辆继续投入使用,却无法得到证明。〔13〕Vgl.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8,S.1899.显然,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还是没有采纳“显而易见的结果避免”这一思想。在案例3 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并不足够。其在判决中指出,按照判例一贯秉持的立场,即要求合义务的作为能够近乎确定地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那么在本案中就是存疑的,理由在于:其一,对于同样被判有罪的所长来说,即便他得到下级的汇报,也可能在考虑到财力拮据的情况下,不打算在血库的人力和物力方面投入更多。其二,对于主管当局来说,其很有可能与所长取得联系,并在其影响下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4〕Vgl.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0,S.2757.
可是,人们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暂且不论上述因果关系是否能成立,但可以肯定在介入第三人自由意志之行为的场合,条件公式所依赖的因果法则根本是不存在的,那就意味着,结果避免可能性大小的判断也是无稽之谈。并且,采纳“近乎确定可以避免”之标准在刑事政策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第三人介入的场合当中,没有理由可以让先行为人以他人同样可能违反义务为由为自己开脱罪责。〔15〕Vgl.Roxin,Problem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Festschriften für Hans-Achenbach,2011,S.428.显然,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为这种场合的不作为因果关系寻找更具说服力的判断标准。
二、两种风险升高理论的尝试与失败
为了克服“近乎确定可以避免”标准制造的困境,风险升高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早先被用于判断过失作为犯的义务违反关联性,主张在行为人即便遵守注意义务,损害结果仍有可能出现时,只要违反了注意规范的行为显著提升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危险,就可以肯定法不容许的风险之实现,因而可以将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16〕Vgl.Stratenwerth,Bemerkungen zum Prinzip der Risikoerhöhung,Festschrift für Gallas,1973,S.227 f.之后,该理论被转用到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判定中:只要行为人履行必要的作为义务可以实际降低结果发生的风险,就足以肯定因果关系的成立。其理由在于,保证人应当实施那些并不确定能够阻止结果发生但却具有救助法益之盖然性的行为。〔17〕Vgl.Lúis Greco,Kausalität-und Zurechnungsfragen bei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n,ZIS 8 -9/2011,S.676 ff.;Otto,Grundkurs Strafrecht,Allgemeine Strafrechtslehre,11.Aufl.,2004,§ 9 Rn.98 ff.;Stratenwerth/Kuhle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6.Aufl.,2011,§13 Rn.54 ff.
在缺陷产品不召回的案件中,若采纳这一理论,似乎就可以宣称,尽管零售商是否会在接到召回决定后予以执行并不确定,但如果生产商合义务地发布了召回决定,至少可以降低零售商继续售卖产品的概率,从而提升消费者法益受到保护的几率。不过,由于该理论在不作为犯中的适用一直未得到司法判例的认可,〔18〕Vgl.BGH,Strafverteidiger,1985,S.229;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0,S.2757;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1987,S.2940;BGHSt 37,106(127).因此必须对该理论支持者的立论基础进行重新审视。
(一)刑事政策进路的风险升高理论
适用风险升高理论的路径之一,便是主张其在刑事政策考量上相较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更具合理性。部分论者指出,在被害人陷入较大危险的场合,如果此时免除作为保证人的行为人的救助义务,那在刑事政策上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有意义的规范要求,要抓住每一个拯救法益的机会。〔19〕Vgl.Otto,Risikoerhöhungsprinzip statt Kausalitätsgrundsatz als Zurechnungskriterium bei Erfolgsdelikten,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80,S.417 ff.于是,诸如在父母怠于为生病的孩子呼叫医生的案件中,除非从一开始就肯定孩子不可能得到救治,否则,只要父母及时地呼叫医生本可以增加孩子被救治的几率,就应当认定其不作为与孩子的死亡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仅以此来肯定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在规范论基础上就是不牢靠的。有论者提示道,一种对刑事政策不正确的转述,即在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那里,并非100%有效的救助行为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其忽视了结果避免可能性恰恰指向了结果无价值而非行为无价值。一个要求抓住任何救助机会的命令规范,仅仅涉及了行为无价值的表述,是从事前视角来判断规范有效性的,但是,它没有说从事后来看,行为人是否要为结果不法承担责任。〔20〕Vgl.Lúis Greco,Kausalität-und Zurechnungsfragen bei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n,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Strafrechtsdogmatik,8-9/2011,S.676.
其实,风险升高理论所面临的首要批评,就是放弃了根本性的归责前提,将实害犯转化成了危险犯。〔21〕Vgl.Samson,Hypothetischer Kausalverlauf im Strafrecht,Frankfurt am Main:Metzner,1972,S.155.对此该理论的支持者回应道:一种观点认为,批评者没有意识到,客观构成要件的结果归责总是经由行为人所创设的危险才得以完成。实害犯与危险犯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实害犯中,不被容许的危险实现于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损害结果中,但对危险犯而言,则是危险实现于一个按照不同标准予以界定的危险结果之中。但在风险升高的合义务替代行为之场合,被禁止的风险却已经实现在了构成要件的损害结果中。并且,风险升高是否真实存在如同风险实现一样,是从事后来加以判断的。〔22〕Vgl.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2006,C.H.Beck,§ 11 Rn.93 f.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风险升高理论也承认在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应当存在必要的关联性,只是并不认为,必须在结果避免可能性达到100%的情况下才能肯定该必要的关联性。因为,合义务替代行为能否避免结果的发生,本身就是概率大小的问题,不可能得出绝对的答案。倘若在这时一概放弃归责,那么很多注意规范就几乎形同虚设。〔23〕参见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4 期。
然而,上述回应仍然存在可疑之处。一方面,在未能证立义务违反关联性的情况下,就宣称“不被容许的危险实现于构成要件结果之中”,等于彻底取消了归因与归责之间的界限,致使客观归责体系的存在本身失去了应有的意义。〔24〕参见徐成:《论风险升高理论的法理证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 年第4 期。至少在作为犯中,因果关系的成立仅仅意味着行为人的能量投入与结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基础关联,但要将结果作为行为人的作品归责于他,则必须论证该能量投入的违法性特征与结果之间存在规范性关联。〔25〕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3 Rn.30.另一方面,风险升高理论的确只建立起了义务违反与结果出现可能性之间的规范关联,表明行为提升了结果出现的风险,只能表明法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更高,却不代表法益必定遭受损害。因此该理论可能错误地将可能性与现实性混为一谈。〔26〕参见徐成:《论风险升高理论的法理证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 年第4 期。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在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判定中,风险升高理论的刑事政策取向却是值得赞同的,因为它避免的是在充满危险的生活领域中对行为人欠缺的谨慎所给予的不当豁免。〔27〕Vgl.Lúis Greco,Kausalität-und Zurechnungsfragen bei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n,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Strafrechtsdogmatik,8-9/2011,S.681.尽管该理论的反对者曾指出:结果归责中的风险升高理论,只有在以一般预防为导向的刑法体系中才能获得正当化,但是预防性的刑法体系自身将刑罚纯粹工具化、混淆作为刑罚根据的罪责与作为刑罚目的的一般预防以及无法提出一个可以稳定秩序信赖的明确标准的危险。而若在相应个案中采纳无罪的结论,却未必会动摇国民对法规范的忠诚,因为仅是个案中注意规范不具备实效,不代表注意规范普遍失去了效力。〔28〕参见蔡仙:《过失犯中风险升高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反思》,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4 期。可是,尤其是在第三人介入的不作为案件中,人们之所以无法接受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正是因为,倘若仅因无法确定第三人是否会履行自身的义务,就否定不作为因果关系成立的可能性,那么规范失去实效的就将不是一两个个案,而是几乎所有的个案。在此,不得不说许迺曼的论断颇具洞见——刑法是透过禁止规范的一般预防效力来防止侵害,所以只有当结果归责本身能够被放入一般预防的效力装置时,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29〕参见[德]许迺曼:《关于客观归责》,载许玉秀、陈志辉汇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551 页。
(二)概率提升进路的风险升高理论
适用风险升高理论的路径之二,是主张将义务违反关联性视为一个以盖然性方式存在的要素,认为规范背后的目的是结果避免,而不是降低结果发生的风险。〔30〕参见蔡仙:《过失犯中风险升高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反思》,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4 期。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证进路。
施特拉腾维特率先指出,当自然科学开始揭开有机生命体中高度复杂的调节和控制机制的那一刻,所谓拉普拉斯的世界精神就基本消失殆尽了。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的运动并不都是可以精确测量的,而是只能以盖然性的方式对之进行描述。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者,在他那里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基于此,他认为萨姆森批评风险升高理论“违反了罪疑惟轻原则”就是没道理的:因为在风险升高理论所涉及的那些案件中,就算采取了事后视角,解释了一切可以解释的情状,也无法对那些因果流程给出超越于盖然性的解释。〔31〕Vgl.Stratenwerth,Bemerkungen zum Prinzip der Risikoerhöhung,Festschrift für Gallas,1973,S.233.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犯罪侦查上事实描述的局限性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是不同于假定因果流程的不确定性的,只有后者才会促使我们在特定条件下将其解释为可能或者盖然的。〔32〕Vgl.Stratenwerth,Bemerkungen zum Prinzip der Risikoerhöhung,Festschrift für Gallas,1973,S.229.
普珀对这种立场表示了赞同。她认为在诸如微观物理学、微观生物学、疾病治疗以及人类决定等领域当中,并不能通过严格决定论的法则加以解释,因此要求用“近乎确定可以避免结果”的标准来判断结果归责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些非决定论的领域中,客观上无法确定的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了结果出现的最低充分条件中的一个必要要素,因为根本不存在依据一般因果法则界定最低充分条件的可能性。所以,去追问若行为人正确地实施行为,事实是否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毫无意义的。〔33〕Vgl.Puppe,Brauchen wir eine Risikoerhöhungstheorie? Festschrift füt Claus Roxin,2001,S.302 f.那么,在非决定论的领域,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适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盖然性法则进行归责,要么完全放弃归责。如果使用盖然性法则得出的归责结论都因为不充分而遭到否定的话,那么在非决定论的领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归责了。如果人们无法忍受这种结论,那么除了在此领域使用盖然性法则进行归责,别无他法。〔34〕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2.借着对联邦最高法院“肿瘤转移案”判决进行评述的机会,她详细地阐释了自己的这一立场,并阐述如何运用盖然性法则进行结果归责。该案案情是:被告人对一名罹患前列腺癌的病人实施了半睾丸切除术,以清除他身上的恶性肿瘤。由于在手术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残余癌细胞组织停留在手术区域内,而这些癌细胞组织会分散到身体中、并在其他位置形成肿瘤转移,因此在医学上进行放射治疗以杀死这些剩余组织绝对是有效的。可是医生却怠于进行这项治疗。该病人两年后死于肿瘤转移。医学专家证人解释道,根据统计学上的调查数据,90%的病人在接受同类手术之后又被放射治疗的,其生存期大于2 年,仅有10%的例外。〔35〕Vgl.BGH,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1988,S.184.在上述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90%的盖然性程度并未近乎确定,因此认定州法院对医生所作的有罪判决违反了罪疑惟轻原则。但有论者对此批评道:在医药科学领域,很多致病过程以及治愈过程都不再被视为完全由因果法则来决定。基于医疗过程的不确定性,要求提供该病人属于那95%放疗有效果的群体、而不属于那5%放疗无效果的群体的相关证据,是极其愚蠢的。〔36〕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0.罪疑惟轻原则在此处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只有当人们对多个可能的事实中究竟存在哪个事实抱有疑问,而客观上确定的是其中必然存在一个事实时,才能适用疑罪从无原则。但在非决定论的流程中,对于该流程到底是在此方向还是彼方向上是被决定的,则合乎情理地不存在疑问,因为确定的是,这两种决定论的假设都是错误的。〔37〕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1.
该论者继而指出,相较于决定论法则,盖然性法则从不认可指向结果的必然性推论,毋宁只认可一个结果之发生总体上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推论。对于结果归责来说,只要为归责奠定基础的行为人的行为成为完整的盖然性法则的组成部分,就足够了。〔38〕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4.所以,在前述案例中首先要确定,前列腺癌病人在接受睾丸切除术之后活不过两年的风险有多高,而不论他们是否被实施了放射治疗。接着,应将那些没有被实施放射治疗的病人从整体中挑选出来,这样存活期不超过两年的显著的风险提升就会呈现出来。这表明,怠于实施放射治疗无论如何构成了在本案中适用的完整的盖然性法则的组成部分。如此也就明确和肯定地证明了将病人死亡的结果归责于怠于实施放疗的不作为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而达到这一明确性和肯定性原则上是完全可能的。〔39〕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25.
介入自由意志决定的情形,也属于“不可查明的情形”或者“非决定论的领域”。那么在此处,本体论意义上的风险升高理论能否得以适用了呢?答案恐怕也是存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案件而言,大多只是零星地发生,因此并不存在诸如医学上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底气声称,根据总体上产品未召回的统计数据,生产商没有履行召回义务情形中未召回的比例明显偏高。而且,相比于医学领域的那些潜在的阻止病患康复的因素而言,经验层面所显示的零售商不执行召回决定的比例,更是成为适用风险升高理论的障碍。〔40〕Vgl.Roxin,Probleme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Festschrift für Hans Achenbach,2011,S.430.这主要是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风险升高理论,原则上适用于存在自然科学所承认的非决定性的场合,可是,此处存在的却是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基础的非决定性。〔41〕参见徐凌波:《义务违反竞合与结果可避免性》,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 年第2 期。难怪普珀自己也承认,倘若采用风险升高理论的话,那么结果归责就取决于零售商本会执行召回决定这一假设是否存在高度的盖然性。如果人们想象在零售商之间一种不良风气蔓延开来,即大家原则上都不执行召回决定,那么对召回行动负有义务的生产商事实上就可能因此免除责任。〔42〕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31.
综上所述,试图以风险升高理论来消解不作为因果关系中因自由意志介入导致的条件公式的困境,可能是失败的。一方面,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风险升高理论试图抓住每一个拯救法益的机会,在目的理性上固然可取,但终究无法摆脱正当性上遭到的质疑。另一方面,概率提升进路的风险升高理论,虽然可以用于解决诸如医疗等非决定论领域的归责问题,却无法适用于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非决定论领域的归责判断。
三、心理因果关系与规范论的归责路径
可以看到,在此类案件中,直接决定损害结果是否会发生的并不是先行为人怠于履行自身义务的不作为,而是介入的第三人(或被害人)在意志自由的支配下所作的内心决定,因此不难想到,先行为人是否要为损害结果承担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或许取决于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心理性的不作为因果关系,也即,由于先行为人怠于以作为的方式向第三人(或被害人)施加心理性的影响,从而因果性地导致后者实施了直接造成结果发生的行为。对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施加心理性影响的过程,能否认为存在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二是,倘若承认这种新的因果关系类型,那又该以何种标准认定其在具体个案中的成立,并得以将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呢?
(一)承认心理因果关系为新的因果类型
自由且有责任能力的个体,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规范性假设。〔43〕Vgl.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2006,§ 3 Rn.55.基于此,旧溯责禁止论认为,如果一个意志自由的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独立的因果序列,那么原有的因果流程就被中断了,因为自由和有意识地指向结果引起的条件才是结果出现的原因。据此,先行为人所施加的心理性影响就无法因果性地引起后行为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此也就无需对后行为人所导致的结果负责。〔44〕参见何庆仁:《溯责禁止理论的源流与发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 年第2 期。可是,不论是德国还是我国,都没有人会否认教唆犯和(心理性)帮助犯需要为正犯所造成的结果负责,而最为重要的负责前提便是教唆或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45〕我国司法判决明确表述了教唆犯与实行犯之间的心理因果关系。例如,“共犯中的教唆犯是指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人灌输犯罪思想,以便使他人实施犯罪,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参见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2019)辽0811 刑初117 号刑事判决书。又如,“郑某某已预见到李某某去被害人家可能会碰到人,且可能会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上的威胁,而仍然对其进行教唆,其唆使他人的行为与抢劫的实行行为及其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参见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4)沂刑二初字第83 号刑事判决书。显然,上述因果关系论意义上的溯责禁止早已过时。溯责禁止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仍可能在后行为人实施故意或过失行为时,否定前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责任,但排除归责的理由却不再是因果关系的中断,而是援引了信赖原则、规范保护目的、风险升高、社会相当性等规范性标准。〔46〕参见何庆仁:《溯责禁止理论的源流与发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 年第2 期。
问题是,这种心理性关联是否可被称作心理因果关系?不同学者对此持有歧见。一部分学者主张所谓非因果的心理性关联。科里亚特(Koriath)认为,用合法则性来描述心理性过程并不正确,因为沟通交流过程不可能由自然法则来决定。受到哈特和奥诺尔的启发,他主张对于人际交往的心理过程适用非因果性的归责原理。〔47〕Vgl.Koriath,Kausalität,Bedingungstheorie und psychische Kausalität,Verlag Otto Schwartz,1988,S.224.贝恩斯曼(Bernsmann)也指出,将目的、动机等要素看成是因果决定论范畴,不仅违背了刑法中的责任原则,也使得在澄清事实时仅赋予诉讼参与人以客体的角色。他倾向于认为,在人的意图与举止之间存在的那种逻辑关系,不是休谟意义上的原因与效果间的因果关系。〔48〕Vgl.Bernsmann,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Recht,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1982,S.536 ff.佩雷斯·芭芭拉(Perez-Barbera)则别出心裁地以“决定性”这一上位范畴统摄了因果性、统计性和目的论三种决定论类型。他认为,因果关系总是只能与物理意义上的“力”联系起来,这种“力”要能够单向地改变外在世界的形态;而目的、动机等目的论要素则无法以因果性方式加以解释,只能作为统计性决定论的下位类型。〔49〕Vgl.Perez-Barbera,Kausalität und Determiniertheit,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114(2002)Heft 3,S.600 ff.
另一部分学者认可心理因果关系,只是对该因果关系是否具备法则性有不同看法。恩吉施作为合法则性条件说的提倡者,认为在人的心理性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种法则性关联,即他所称的动机惯习的认知(Kenntnis der Motivationsgepflogenheiten)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特定类型的决定与行为方式之间前后接续的规律性。〔50〕Vgl.Engisch,Die Kausalität als Merkmal der strafrechtlichen Tatbestände,Mohr Verlag,1931,S.267.萨姆森(Samson)干脆说,这就是一种可查明的因果法则,因为当前后行为人间有交流时,后者或多或少会在前者的影响下产生对未来行为的想象。〔51〕Vgl.Samson,Hypothetischer Kausalverläufe im Strafrecht,Frankfurt am Main:Metzner,1972,S.184.希尔根多夫反对将这种因果关系解释为决定论的,因为这与德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意志自由相违背。他主张在心理因果关系的场合适用统计法则,例如,某人被特定的欺骗行为所欺骗的可能性大于50%。面对可能的异议,他认为原则上无须在给定的情况下确定待解释事件出现的概率大小,法律适用者只需要以其所具有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合法则关系的基础。〔52〕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90 页。
相反,罗克辛和普珀均否定了这种因果关系的法则性。罗克辛指出,在自然法则支配的关联性中,将法则运用于个案就能够对结果做出预测并将其解释为被特定事件所决定的。但在法学的因果关系检验中,并不牵涉到对某个决定进行预测或对其产生方式予以解释。足够的是,在事后查明行为人所施加的精神性影响促使正犯或被害人做出了侵害法益的行为。换言之,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建立在法则之上,但与被因果性决定的结果一样可以得到证明。〔53〕Vgl.Roxin,Probleme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Festschrift für Hans Achenbach,2011,S.416 f.普珀则强调了不同类型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她认为我们必须放弃统一的因果概念之幻想,应当在严格的因果法则和统计法则之外寻求另一种原因与效果间的关联。〔54〕Vgl.Puppe,in:Kindhäuser/Neumann/Paeffgen,Nomos Kommentar,StGB,3.Aufl.,2010,vor § 13 Rn.131.条件公式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其适用以行为完全受到一般法则决定为前提,但是无论是法官还是国家都无权将公民作为一个被决定的机器来看待。对于一个公民来说,他是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某个决定,还是在受到欺骗、恐吓或其他心理性强制的情况下做出了该决定,区别显然是很大的,因此,不能用一个假设的选择去替换一个实际做出的决定,否则就等于在剥夺公民的自由决定权。〔55〕Vgl.Puppe,Die psychische Kausalität und das Recht auf die eigene Entscheidung,Juristische Rundschau,2017,S.513.
上述观点在结论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要让法学上的因果关系概念从属于自然科学或者哲学。倘若放弃从属性,提倡刑法因果关系服务于刑法的目的和功能,那么在坚持人的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就应当承认心理因果关系是一种新的因果类型,只是要发展出区别于合法则条件说的另一种非法则因果关系的判断原理。
(二)作为的心理因果判断:优势信息下的行动理由提供
心理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之探讨,最先是从作为形态开始的,也就是行为人通过信息的传递对第三人或者被害人积极施加了心理性影响的情形。以诈骗罪的心理因果关系认定为例,德国司法判例当前沿用了条件公式,但其不当结论遭到学者的诟病,被认为不如回到先前的共同原因说。与之类似的是,我国司法实务着重正向考察条件关系,实质上也采取了共同原因说。〔56〕英美法中民事欺诈的责任认定也遵循这一学说,认为“欺诈只要构成受欺诈人行为的原因之一即可,而不要求其构成主要的或实质的引致……必要条件即‘要不是’检验并不适用。即便被告的欺诈人抗辩到“如果没有我的欺诈,原告也会订立合同”成立,也不影响原告撤销合同的主张”。参见许德风:《欺诈的民法规制》,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2 期。不过也有不少辩护意见提出,行为人要在信息上占据优势地位,不然就应以被害人并未受到心理性影响为由否定因果关系。
1.德国司法判例:共同原因说之提倡
预备文官案:一个预备文官请求一个商人给其提供2000 马克的贷款,而这个商人显然将他当成了法官。该预备文官虚假声称,他只是短时间内亟需这笔贷款,因为他正等待着不久将发放的矿井股份的红利,另外他有钱的父亲还会给他一笔钱。在针对该预备文官涉嫌诈骗罪所开启的刑事程序中,该商人解释道,他也是商事法院的法官,就算他知道该预备文官不是法官、而仅仅是一名预备文官,以及就算该预备文官没有在他面前撒下有关矿井股份和一个有钱的父亲的谎言,他也会贷款给他。〔57〕Vgl.BGHSt 13,13.
在“加拉维特案”中,〔58〕案情简括如下:治疗癌症的医生向病入膏肓的患者以过高的价格向患者兜售一种叫加拉维特的药物,这种药品虽在德国为药品法所禁止,但是在跨国药店里却能够以远低于被告的要价购买到。被告也借助电视节目欺骗这些病人,声称加拉维特在俄罗斯作为一种成功攻克各类癌症的良药已被检测证实。一个演员违背事实地讲述自己仅通过服用加拉维特就从前列腺癌中痊愈的故事。联邦最高法院曾以“一群无药可救的癌症病人,他们被迫去‘抓紧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无论如何也仍然会做出购买的决定”为由,〔59〕Vgl.BGH,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2010,S.88(89).否定了诈骗罪的心理因果关系。显然,联邦最高法院考察的并非真实的心理因果流程,而是在行为人实施合义务替代行为的前提下的被害人的假设决定。可是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由于我们并未掌握任何可以决定这种流程的因果法则,所以无法声称,倘若一个无药可救的癌症病人知道了有关加拉维特的真相,他又会做出何种决定。如果非要去纠结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估计就只剩下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做出有利于诈骗行为人的解释,即该病人就算知道真相也还是会购买药品。这样就等于,行为人为了获利,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骗无药可救或持怀疑态度的病人们,〔60〕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49.而不会遭受刑法的制裁。这难以让人接受。
相反,在“预备文官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考察假定的因果流程。其以如下的理由肯定了因果关系:“这并不取决于,该理由对于商人给被告提供一笔钱来说是否充分。事实上正如判决中所查明的或至少是所预示的那样,商人之所以给被告人钱,是因为他相信了被告所作的虚假陈述。只要这对于他借钱来说起到了共同决定的作用,那么即便存在另外一个动机,该动机不会被认识错误所动摇并且可以单独引起他做出同样的决定,前述缘由也并不会因此就丧失其法律意义。”〔61〕Vgl.BGHSt 13,13(14).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共同原因说,其考察的是被害人因信赖行为人的陈述而做出财产处分行为的真实因果流程,至于假定的因果流程,即被害人是否会出于另一动机做出这一财产处分的决定,则被认为对于该真实因果流程而言无关紧要。〔62〕Vgl.Nikolas Bosch,Die Hypothese rechtmäßigen Verhaltens bei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Festschrift für Ingeborg Puppe,2011,S.376.
2.我国司法实务:正向条件判断+信息优势说
苏荣飞诈骗案:被告人苏荣飞经与苏玉坤等合谋实施“购车退税”诈骗后,分别组织被告人苏淑清等人,在福建省厦门市三处地点,由被告人苏荣飞提供诈骗用的手机、电话卡、银行卡号及其非法获取的车辆有关信息、车主联系电话等,被告人钟丽琼等人利用被告人苏荣飞等转交的上述信息,冒充相关车管所工作人员致电被害人江某等人,谎称购车后可退税并提供所谓“国税局”的电话号码,再由被告人苏玉坤等人冒充国税局工作人员接听被害人回拨的电话,进行进一步欺骗,并诱骗被害人在自动取款机上操作所谓的退税款相关步骤,致使被害人等32 人银行存款计519151.08 元被骗。〔63〕参见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13)南刑二初字第0058 号刑事判决书。
杨云廷诈骗案:被告人杨云廷使用同学王某1 的身份证在浙江省永康市某路开了一家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被告人使用该身份证和银行卡,并提供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的代销证等,通过北京博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加盟了“87 彩店”,且自己给加盟店起了名字为“阳光竞彩店”。之后使用被告人提供的邀请码在“87 彩店”手机APP 注册成功的客户就属于其客户了。2018 年4 月,被害人石某通过微信联系到被告人,让其在“87 彩店”以代买体育彩票的方式投注球赛,石某共通过支付宝或银行卡转账给杨云廷1447773.75 元,被告人将收到的部分资金用于体育彩票实体店出票,其余部分在未经被害人石某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中的562411.29 元投注于英国的一个“188 金宝博”外围网站,非法获利20 万元。〔64〕参见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6 刑初94 号刑事判决书。
在前一个案例中,法院综合评判认为,“被害人桑某等十人陈述的诈骗电话号码在公安机关串号反查的电话号码中均有显示,能够对应相关的被告人,且上述被害人在即时报案笔录中均陈述是根据诈骗电话的提示操作,导致被骗。故认为,上述被害人的被骗与相对应的被告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认定”。〔65〕参见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13)南刑二初字第0058 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根据电话提示操作,导致被骗”是一种正向的条件关系判断,而且实质上也是采取了共同原因说,因为被骗人是否出于其他动机处分财产,在所不问。
在后一个案例中,辩护人却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诈骗罪提出了异议:“本案杨云廷系接受石某的委托代其购买彩票,在该代理行为中,购买彩票的金额、比赛场次、下注哪支球队均是由石某本人决定,而且下注时比赛国内的实时赔率作为公开信息石某本人也心知肚明。换言之,如果没有杨云廷的介入,由石某本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购买彩票,也会导致与今天毫无二致的结局”。〔66〕参见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6 刑初94 号刑事判决书。尽管法院在判决结论中是以被告人缺乏非法占有的故意否定了诈骗罪的成立,但辩护人所称“石某本人决定,公开信息心知肚明”无疑表明,被告人没有基于认知优势对被害人形成信息操纵,这自然是诈骗罪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关键理由。
3.判断标准提炼:信息优势下的行动理由提供
在作为心理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应当将德国和我国实务的观点结合起来,提炼表述为“信息优势下的行动理由之提供”。一方面,正如普珀所言,我们之所以做一件事情,要么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要么因为这样做是合目的的,这些行动理由对我们来说必须是明确的,而正是自由决定使得我们选择将什么作为行动的理由。每一个为他人做出决定提供了理由的人,当他人正是基于此种理由而做出决定时,也就和该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便他人做出这一决定还有别的理由,这一结论也成立。〔67〕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45.另一方面,信息优势的存在是必要前提。施蒂宾格(Stübinger)指出,信息归因的成立常常是以信息提供方存在认知优势为基础的,尤其是当信息接收方的决策依赖于提供方时。之所以有依赖关系,就是因为接收方对特定信息一无所知,因此他看不到该信息将造成的差异。当信息接收方同提供方存在相当的认知能力时,我们就很难认为后者的信息为前者的决定提供了理由。〔68〕Vgl.Stübinger,Zurechnungsprobleme beim Zusammenwirken mehrerer fahrlässiger Taten,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Strafrechtsdogmatik,7/2011,S.617.此时应当基于被害人的自我答责排除行为人的责任。
(二)不作为的心理因果判断:合义务行为假定+自我决定权剥夺
按照上述信息归因的思路,似乎可以认定前述案例2 中的心理因果关系。在该案中,车间负责人由于履职过失而向工厂主报告了错误的车辆刹车信息,形式上属于积极地施加了心理性影响的情形。而且,尽管该负责人自己并没有实际认知到该车辆刹车的真实情况,但他相对于工厂主来说,更有可能认知到导致事故发生的车辆后轮轴制动鼓的缺陷,因而具有信息优势。接下来则要去询问工厂主,他从车间负责人那里接收的错误信息是否在其决定中起到了作用。〔69〕这就是“行动理由提供说”的判断方法,不是要去问,如果行为人没有提供错误信息的话,第三人将会如何做出决定;而是要去考察实际发生的心理性流程,即去询问第三人或被害人,行为人所提供的错误信息是否在其决定中起到了作用。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2019,§ 2 Rn.46.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也是肯定的,因为工厂主之所以会做出准许继续使用的决定,通常就是基于车间负责人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
然而,由于归因总是为归责服务并且受到归责目的的制约,〔70〕参见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 年第6 期。因此值得质疑的是,上述归因的方法是否契合了归责的需求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果按照信息归因的判断方法,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车间负责人所提供的错误信息与工厂主所做的错误决定之间,那么其目的必然是要为车间负责人的过失作为犯归责提供事实基础。可是,单纯过失地引发他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并不能为过失作为犯的结果归责提供坚实的理由:刑法上的注意义务是维持公民遵守规范之能力的辅助规范,履行注意义务主要是为了避免给他人法益直接造成某种法律禁止的损害,而并不包括避免引发他人做出侵害他人法益的错误决定。在过失教唆和帮助均不可罚、且过失间接正犯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情况下,〔71〕德国学者阿茨特明确主张过失间接正犯的概念:在因行为人提供错误信息而过失引发他人违反义务的案件中,他认为基于限制正犯的概念,只可能让行为人承担过失间接正犯的刑事责任。过失间接正犯并不是像故意间接正犯那样,是由幕后者的行为支配或者幕后者相对于幕前者是完全答责的来奠定可罚性。但可类比的是,过失间接正犯的幕后者相对于直接行为人来说,单独或者在更高的程度上应当为结果负责。例如当幕前者基于对幕后者的信赖而不构成过失正犯时,那么幕后者就可能构成过失的间接正犯。两者之间始终应存在一个结果避免能力的落差。Vgl.Ast,Begehung und Unterlassung-Abgrenzung und Erfolgszurechnung,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2012,124(3),S.612(654).就无法将法益损害的结果归责于车间负责人的过失作为。正如法院判决所示,审查的重心应当置于车间负责人未能提供正确信息的不作为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前述的案例1 和案例3 来说,这种作为的心理因果判断标准就毫无用武之地了:当皮革喷雾剂的零售商或者卫生主管当局完全没有接收到来自生产商或血库副所长的任何信息时,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询问后者的方式来认定,该产品信息是否在后者的决策当中起到了作用。此处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可描述的真实的心理因果流程,而只是一个潜在的心理因果流程。那么,针对这种不作为的心理因果流程,应当采取何种标准判断其因果关系呢?以下分别论述第三人和被害人介入情形下的判断标准。
1.第三人介入的场合:合义务行为的假定
行为人能否通过履行作为义务来避免结果的发生,其不确定性正是在于第三人决定的不确定性。对此,雅各布斯曾指出,我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应该以它现有的样子为基础,但如果要对它未来的样态进行预测,那就只能从所有人符合规范的行为出发。据此,当不确定第三人将会在另一种情境中做出何种决定时,就应当假定他会做出合乎义务的决定。〔72〕Vgl.Jakobs,Strafrechtliche Haftung durch Mitwirkung an Abstimmungen,Festschrift für Miyazawa,1995,S.432.金德霍伊泽尔也就此分析到,要思考的是,我们究竟是在一个事实上的世界还是在一个规范性组织的世界当中审查结果避免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是在一个规范性组织的世界当中考虑这一问题,那么这一世界的样貌就是符合法律的规范性期待的。显然,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只能在以规范性组织的世界中使得责任的归属成为可能。当通过规范进行法益保护时,倘若基于一个替代性的规范违反而允许法益侵害,那就让人无法接受。〔73〕Vgl.Kindhäuser,Zurechnung bei alternativer Kausalität,Goltdammer’s Archiv für Strafrecht,2012,S.134.
德国司法实务首先在义务违反竞合的情形中明确适用了这种规范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审查方法。如政治局案:被告人曾经是民主德国政治局的成员。他们就任的时候,针对两德边境所制定的边境管理制度已经生效了。在他们任职的这段时间内,为了阻止所谓的越境行为,边境士兵执行了射杀命令,杀死了好几名避难人员。为此,政治局的成员们被判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74〕Vgl.BGHSt 48,77.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射杀难民的边境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真正要为难民之死负责的是作为命令发布者的政治局成员。他们被视为不作为的间接正犯,理由是作为保证人,他们负有义务随时废除这种边境管理制度,或者从宽对待越境之行为,以致边境地带不再发生死亡事件。对此,每一个政治局成员都有义务随时去为形成一个废除该项制度的决议而争取、呐喊和投票。可是没有一个成员做过这样的努力。〔75〕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30 Rn.1.对于每个成员的不作为与难民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过一种可能的论证理由:“对于不作为犯的‘准因果关系’的判断,只能依据规范性的标准。在这一关系当中,应当假定其他平行的保证人实施了合法之行为;因为法律是以他们遵守规则为出发点的”。〔76〕Vgl.BGHSt 48,77(95).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不允许援引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也即,尽管自己努力促成集体决策达成,但却在争议情形中因其他人的多数票无功而返”。〔77〕Vgl.BGHSt 48,77(94).
不过,这里之所以能够假定其他平行的保证人会实施遵守规范之行为,是因为并未发生其他保证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事实。倘若真的有平行的保证人实施了违反规范的行为,那就不能反事实地假定其仍会实施合乎规范的行为,以此来做出不利于行为人的认定。〔78〕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30 Rn.10.实际上这种强调与刑法中的信赖原则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信赖原则意指行为人对于行为时有权假设其他社会生活参与者会尽其规范上之义务,因此行为人在此一信赖基础上所为之行为并非不法。〔79〕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第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9 页。在这种意义上,对于他人实施合乎规范之行为的期待,会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制定自身行动计划的前提,只要对方没有实际实施违反规范的行为,该社会生活参与者就也应当以遵守规范为行动的基础。但是,如果他人违反规范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可以清楚地预见或者已经实际发生),同时行为人也有充分时间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发生法益侵害结果,那就不得以信赖对方仍会遵守规范为由,以免除自己的责任。〔80〕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第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0 页。对信赖原则所做的这一限制,无疑是表明,社会生活参与者在以规范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的同时,无法脱离现实世界的事实基础,因为规范必须要在现实世界中加以运作,符合规范之行为方式的设定必须要以现实中发生的情境为依据。因此有论者指出,当被信赖的对方违反了规范之时,他就不再认可将规范作为行动模板,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继续以此丧失认知性基础的对方行为来为自身行为提供规范性的定位,便是毫无意义的。〔81〕Vgl.Pizarro,Das erlaubte Vertrauen im Strafrech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7,S.267.
基于此,当被信赖之人破坏了信赖基础时,信赖他的人就必须独自承担解决交往冲突的任务。换言之,因对方的规范违反而产生了要求行为人弥补其违法行为的次级义务。〔82〕Vgl.Pizarro,Das erlaubte Vertrauen im Strafrecht,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7,S.267.既然如此,当能够被信赖之人尚未违反规范之时,行为人更是不能以对方假定的义务违反为由为自身违反义务的罪责开脱。在不清楚其他社会生活参与者将要实施何种行为时,行为人只能先自己实施合乎规范的行为,以为信赖原则的援引提供起码的事实基础——当他自己都没能履行好自己的义务时,就不能够期待由自己所创设的危险能够被他人所消除。尤其是在分工合作的义务共同体中,避免法益受到侵害的义务,常常必须由处于分工关系中的多人共同履行,任何一人的义务违反都可能导致阻止法益受损的努力付之东流,在此情形下就必须要求每一个负有法益保护义务之人都必须尽其所能,而在判断每一个保证人的义务违反关联性时,也只有做出如此合义务的设定,才不至于造成集体不负责任的荒谬结论。于是,普珀提倡在此种场合引入自然法则之外的法律法则作为归责之基础,也就是在做出因果解释时以其他参与者会遵守自身义务为规范性前提。〔83〕Vgl.Puppe,Brauchen wir eine Risikoerhöhungstheorie? 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2001,S.287.
按照这种合义务假定的判断方法,在前述的案例1 中,就应当假定在喷雾剂的生产商发布了召回决定的情况下,零售商们会合乎义务地不继续销售可能损害身体健康的喷雾剂给消费者,从而较为确定地阻止法益损害结果的发生。尽管如前所述,销售者基于纵向分工的机制,原则上仅对于自己支配范围的产品负有必要的贮存、包装、运输和咨询等义务,然而一旦其接到了生产商所发布的缺陷产品召回决定,就负有义务去阻止这些产品流入消费者的手中。正是这一保护者保证人地位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做出上述合义务的假定。所以尽管被告人为自己辩护道,召回决定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被遵照执行,但联邦最高法院仍然正确地驳回了这一辩护意见。它只是怠于为这一驳回提供如上理论根基而已。〔84〕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34.在案例3 中,初审法院已经提及联邦最高法院在案例1 中创设的原则,认为副所长不能以即便自己努力去促成上级机关的决定也可能失败为由而免责。当只有通过多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促成阻止损害所要求的措施时,那么每一个违反自身参与作用之义务,未对此做出贡献者,都与不作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85〕Vgl.BGH,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2000,S.2757.这一认定结论是基于规范性而非事实性的理由,因为没有实际发生的救助者的行为决定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具有其固然性,因此并不受制于罪疑惟轻原则。但是案例2 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当运输企业的老板知晓了卡车前轮的刹车系统存在问题时,就已经负有义务停止该车的继续使用了。因此我们似乎无法再假定,如果他知晓了刹车系统整体失灵的信息后会做何种反应。〔86〕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30 Rn.21.不过,由于刹车系统整体失灵的信息构成了另一个可能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基础,所以还是可以规范性地假设老板在获知这一信息后仍然会合乎义务地停止运输汽车的使用。
2.被害人介入的场合:自我决定权之剥夺
上述不作为因果关系的讨论并不完整。“皮革喷雾剂案”中仅仅涉及了缺陷产品召回案件的情形之一,即缺陷产品仍然处于销售者的控制范围。但在现实当中大量发生的却是,缺陷产品已经流入消费者的手中,脱离了销售者的可控范围。于是,因果关系认定的问题又多出一个层次:当销售者合乎义务地执行召回决定时,消费者是否就会停止使用缺陷产品,从而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这似乎同样取决于消费者在具体情境中的自由决定:他很可能没有关注到缺陷产品的召回通知,或者,他已经关注到了该通知但并不配合召回行动,又或者,他立即将缺陷产品退回了销售者那里。这里同样不存在任何经验法则以决定消费者究竟会做出哪种决定。但与销售者不同的是,消费者并无义务去配合送回有缺陷的产品,因为并不存在“理性对待自己的法益”这种法律诫命,所以此时就无法以假定消费者会合乎义务送回缺陷产品的方式去检验不作为因果关系。〔87〕Vgl.Nikolas Bosch,Die Hypothese rechtmäßigen Verhaltens bei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Festschrift für Ingeborg Puppe,2011,S.384 f.而且,即便我们认为消费者负有某种自我保护的义务,但根据自我答责的法理,有意识地实施自我危害原则上会阻却行为人的责任。这和生产商不能援引零售商可能的义务违反为自己开脱罪责并不相同。
此处的问题是,当一个行为不是妨碍了他人的义务履行,而是和被损害人自己的防范措施有所关联,且不执行这个防范措施则被损害人面临危险且该危险随后在结果中实现,该如何论证这一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88〕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38.对此,普珀提出在法律规则之外认可将智慧规则(Klugheitsregel)作为论证行为人行为和结果间合法则关联的基础——不去有意地实施自我危害,是一个智慧规则,人们通常会遵守这一自我保护义务。倘若被害人基于完全的自我决定违反了这一规则,造成了自身的法益损害,那么这一危险实现的因果流程就会超越先前由行为人的义务违反所开启的因果流程。〔89〕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39.但前提是,被害人必须拥有在自由意志前提下做出自我决定的可能性,因此他有权要求负有义务之人为其提供充足的信息以作为决定之基础。倘若该负有义务之人违法地怠于履行信息告知的义务,就剥夺了被害人基于自我决定违反智慧规则的可能性,〔90〕Vgl.Puppe,Die psychische Kausalität und das Recht auf die eigene Entscheidung,Juristische Rundschau,2017,S.518.那么他就无法援引被害人就算知晓完整信息也会做出损害自身法益的决定而为自己开脱罪责。
德语区刑事审判实践中曾多次涉及类似的问题。滑雪电影案中,被告人博格勒是轰动一时的滑雪电影的制片人。他预备和一群滑雪选手去一个受到雪崩威胁的高地山谷拍摄影片。但在出发那天,他得知这一区域将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雪崩,却并未将这一信息完整转述给这些演员们。于是,尽管演员们知晓了部分警告信息,他们仍然决定前往该危险区域,结果好几个人在雪崩中不幸遇难。瑞士联邦法院事后判处该制片人构成过失杀人罪。〔91〕Vgl.BGH 91 IV 117(124 f.).煤气接口案中,被告经营了多个建筑工队,其中有些也在压力作用下安装煤气接口。由于煤气网的经营仍然是供应富含一氧化碳的城市燃气,因此就存在一个规章制度,规定在进行这样的施工、特别是在竖井中施工时,必须戴上防毒面具,因为燃气重于空气,因而在竖井内部会聚集起来。可是被告违反既有规定、没有给他的建筑工队中的每个人都配备防毒面具,而仅仅是给所有人配备了唯一一个防毒面具。由于没有佩戴任何防毒面具,被害人在竖井中于压力作用下安装煤气接口时窒息而死。事故发生时,防毒面具被放在另一个地方,而这个防毒面具本应被取来使用。〔92〕Vgl.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RR,1996,S.229.
在前一个案例中,遇难的滑雪选手们事先并非对于雪崩的危险毫无所知。他们想要去往的高地山谷常年因雪崩危险而被封锁,在山谷的入口处就立有明确的警示标牌。但这些滑雪选手们对其视而不见,因此他们违反了自我保护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自我答责的自我危害。因为按照智慧规则,一个理性的滑雪选手不会去忽视滑雪缆车运营商的警示标识。〔93〕Vgl.Puppe,Die psychische Kausalität und das Recht auf die eigene Entscheidung,Juristische Rundschau,2017,S.518.那么,是否能够以这些选手有意识的自我危害来排除电影制片人的过失责任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则上说,以被害人自我答责排除行为人的不法,其前提在于不存在认知上的劣势,〔94〕Vgl.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2006,§ 11 Rn.113.否则当后者有义务消除前者认知上的劣势时,就无法辩称,即便前者获得了完整的危险信息也会做出相同的自我危害决定,因为他剥夺了前者做出这一自我决定的机会。因此,瑞士联邦法院的判决最后也简短地说道,除非制片人不仅告知了选手们他已经知晓的危险信息,而且也告知了他原本基于谨慎义务应当获取的信息,不然就不能援引后者事实上并未做出的自我危害之决定为自己开脱罪责。法院做出的事实认定也表明,电影团队早已决定谨小慎微地行事,想要尽可能避免陷入危险。所以制片人缺乏责任心,因而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承担共同责任。〔95〕Vgl.BGH 91 IV 117(125).
在后一个案例中,被害人同样违反了自我保护的义务,因为他本应当花时间去取回防毒面具。但是,该职责违反之所以发生,原因正在于防毒面具没有发放到被害人手中,而本该对此负责的是企业主。然而,审理此案的瑙姆堡州高等法院要求查明如下事实:“如果有防毒面具可供使用的话,那么被损害人是不是近乎确定会在工作前佩戴它”。〔96〕Vgl.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RR,1996,S.229(232).这一事实是无法查明的,因为装配工人会在另一种情形中(即有充足的防毒面具可供使用)做出何种决定,本身就是非决定论的。应当基于企业主违法剥夺了装配工人这一自我决定权而肯定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所以普珀认为,装配工人不会佩戴随手可得的防毒面具这种可能性,无须在认定行为人行为对于解释结果发生的必要性时加以考虑。最多可能会基于被害人自愿的自我危害考虑排除企业主的责任。但这里不能这样做,因为劳保法的意义恰恰在于,要给每一个建筑工队配备一个防毒面具,因而在节省时间和建筑工队成员的自我危害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冲突。〔97〕Vgl.Pupp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19,§ 2 Rn.42.
综上所述,在介入了被害人自由决定的场合中,我们并不是假定被害人会合乎义务采取避免自我危害的措施,而是基于智慧规则去反问行为人有无剥夺被害人自由地做出自我决定的机会,以此来检验行为人怠于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与被害人发生法益损害结果之间的不作为因果关系。
四、基本结论及拓展适用
至此,本文形成如下基本结论。第一,自由意志介入所导致的条件公式的困境,无法简单以风险升高理论加以解决。刑事政策进路的风险升高理论尽管有利于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但在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上终究无法摆脱来自罪疑惟轻原则的质疑。概率提升进路的风险升高理论,主要适用于存在自然科学所承认的非决定性场合的事实因果的判断,但却无法适用于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非决定论场合的事实因果的认定。第二,应当承认心理因果关系为一种新的非法则性的因果关系类型,将自由意志介入下的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纳入不作为的心理因果关系的思考范畴。作为的心理因果关系判断以信息优势下的行动理由提供作为规范标准,但其无法被适用于事实上并未对第三人(或被害人)施加心理性影响的不作为犯。对于不作为的心理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重新采用规范论的思维构建路径,区分为第三人介入和被害人介入两种情形:对于前者,应当假设负有义务的第三人会合乎规范地行事,在此基础上再来判断行为人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对于后者,应当考察行为人怠于提供正确信息(包括提供完整信息)的不作为是否剥夺了被害人基于自由意志做出自我救助决定的机会。
由此,在前述三鹿奶粉案中,为公司整体的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责任奠定基础的因果关系就得以证立。〔98〕对于三鹿集团召开会议集体决策不召回缺陷奶粉来说,除了要认定公司整体的不作为与消费者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之外,还要就参与决策的领导层成员怠于投出赞成召回的一票与损害结果的个别因果关系作出认定。对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或许也能够加以适用:由于负有作为义务的领导层成员没有作为,因此也就和前述“政治局案”的情形完全一致了。在此便可以像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去假设其他领导层成员会合乎义务地为促成召回决议而付出努力。于是,任何领导层成员都不可能以自己的努力可能因其他成员的反对而作罢为由,为自己怠于付出努力的不作为开脱罪责。采用这样一种不作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方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集体不负责”之不合理结论。不过,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解决缺陷产品不召回案件中的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还能够拓展适用于其他分工合作的场景,消解因自由意志介入而造成的不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
场景一:企业内部成员的义务违反。例如,在“齐二药集团假药案”中,由于采购员因失职被骗和质检部门出具虚假报告,导致冒充丙二醇的有毒二甘醇被作为药品辅料投入亮菌甲素注射液的生产,最终造成使用该注射液的十余名患者的伤亡后果。除了对采购员和质检员等一线员工追究刑事责任外,一审法院还对作为集团总经理的尹家德的管理过失责任予以了认定。尹家德的辩护人提出,其被指控的行为与重大伤亡事故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本案是因为质监部门出具虚假报告造成的,〔99〕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穗中法刑一初字第321 号刑事判决书。这无非是说即便自己履行监管义务也无法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根据本文的结论,应当假设质检部门在被告人尹家德充分履行管理监督职责的前提下能够合乎义务地出具药品辅料的检验报告,由此再来判定尹家德管理过失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场景二:医疗系统成员的义务违反。例如,在“脓肿案”中,作为被告人的住院医生发现了一名刚接受盲肠手术不久的病人身上有红肿的症状,但无法对之给出解释。尽管如此,他却违反义务地怠于请教主治医生。而主治医生在周末探视病人时同样发现了该病人的这一症状,却将全面的化验检查安排到了下周的周一进行。等到周一该病人已经病危了。〔100〕Vgl.BGH,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1986,S.217(218).一审法院以如下理由肯定了住院医生的不作为和病人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主治医生本可以在一周内就安排立即实施诊断措施,而他之所以在周末时没有实施诊断措施,是因为化验室周末只有一个值班人员在岗。但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理由是:如果无法排除,主治医生即便接到了住院医生在周内及时提交的报告也一样无动于衷,那么就不可能认定,被告人因为怠于向负责住院部的主治医生报告病情而引起了病人的死亡结果。〔101〕Vgl.BGH,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1986,S.217(218).但根据本文的结论,主治医生是否会在住院医生合义务地向他报告之后安排诊断和治疗措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决定性的是他负有义务这样去做。如此,我们也就很容易判定住院医生的不作为与病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场景三: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主体的义务违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7 条规定,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补救措施,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如果在实际案件中,因责任主体未能履行及时通知相关职责部门和个人的义务而造成个人信息大量泄露甚至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害后果发生的,该责任主体就无法辩称,即便自己履行了通知义务也无法避免信息泄露和其他损害后果的发生。根据本文的结论,应当假设相关职责部门在接到通知后会合乎义务地采取防止信息泄露等保护措施;个人在接到通知后也有机会做出是否采取保护自身信息的自由决定从而使相关后果归属于自己的负责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