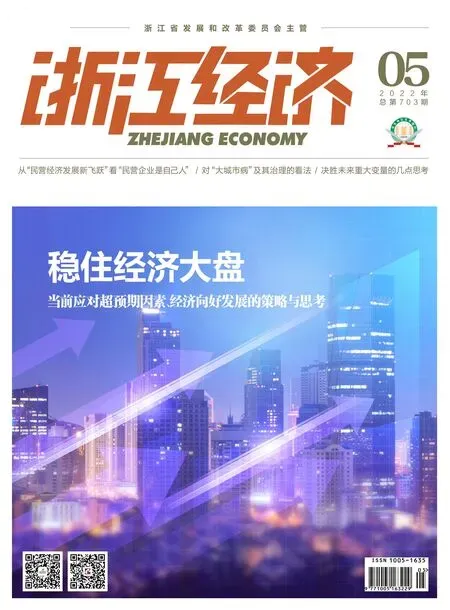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发挥好小城市培育试点的关键纽带作用
2023-01-08方康恒
文/方康恒
小城市培育试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应重点关注并支持小城市培育试点发展,做好“新”“高”“聚”“强”“硬”五篇文章
小城市培育为浙江首创,是破解特大镇“成长的烦恼”、实现特大镇向小城市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得益于块状经济活力和十多年接续不断的试点建设,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但仍然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发展空间不足、公共服务不优等问题。笔者认为,小城市培育试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下一步应重点关注并支持小城市培育试点发展,做好“新”“高”“聚”“强”“硬”五篇文章。
小城市培育试点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至关重要
有利于推进“小平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城乡居民获得感。随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推进,浙江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现有的中心城市及县城节点虽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但并不能够覆盖全域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因而在县城外,选择与县城有一定空间距离的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新型城镇化“小平台”,全面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广大农村区域加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这对提高浙江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
有利于推动“小空间”的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浙江要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努力成为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省域示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需要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小城市培育试点一般产业相对发达,在全面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推动小城市培育试点的乡镇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变,并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为小城市培育试点周边辐射的农业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试点周边“小空间”的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有利于加快“小节点”的就近就地城镇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浙江人多地少,必须走集聚发展的路子,但不可能把所有人都集聚到大中城市。依托并关注小城市试点发展,将小城市试点打造成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小节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小城市试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带动周边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
有利于形成“小区域”的数字化改革和现代化治理范式,促进浙江打造数字社会建设样板省。随着浙江打造数字社会建设样板省和数字政府建设先行省,全省大中城市、小城镇以及农村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数字化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其中小城市培育试点相比中心城市,一方面直面基层,公共服务力量明显不足,有需求通过加快数字化改革进程予以补充,另一方面体量小、体制机制灵活,有条件率先推进数字变革与治理领域的数字赋能。从现实看,浙江已经有一批小城市培育试点分别在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数字化治理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因此,让数字化改革与现代化治理在“小区域”率先深化细化,有利于加速全省的数字化改革与治理领域现代化进程。
新时期小城市培育发展存在问题和障碍
行政体制的制约,职责与权限不匹配。在条块分割的体制背景下,乡镇级政府职能逐渐弱化甚至缺失,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也不例外。这就造成镇一级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阻碍了小城市培育试点新时期高质量建设步伐。
财政体制的制约,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由于财政分成体制制约,造成镇一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未充分匹配,县一级政府承诺的部分扶持政策难以兑现,补助资金难以到位,影响了小城市培育试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这方面在城市道路、文化、体育设施等城市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表现尤为突出。
要素配置的制约,土地资源与产业发展需要不匹配。
要素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刚性制约,已越来越成为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提升城市发展空间的最大障碍,造成每年都有大量的成长型企业从小城市培育试点外迁,进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影响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的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
发展空间的制约,城市开发边界与城镇化建设需求不匹配。由于城市发展边界、行政区域的限制,小城市培育试点中的部分特大镇如柳市镇等在产业分工、要素配置上不能做到科学合理,对实施“退二进三”产业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造成直接影响,也限制了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中心镇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公共配套的制约,公共服务供给与常住人口数量不匹配。当前全省62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人口达755.99万人,但在这些试点人口快速集聚的同时,城市功能配置、建设品质尚未完全跟进。各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政功能配套,尚未能充分满足人口集聚的需求,就医就学、社区服务等供给水平还存在不均衡不优质等问题,与居民期望仍存在差距。
发挥好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城乡关键纽带的重要作用
做好“新”的文章,推进共同富裕县域先行区建设行动。2020年,全省62个小城市培育试点城乡居民收入比1.69,远低于浙江省平均值1.96;地区生产总值达5974.76亿元,高于山区26县地区生产总值5916.1亿元。可以看出,小城市培育试点作为距离农村最近的城镇化节点,能够且应该成为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县域先行区。建议条件合适的试点编制共同富裕县域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谋划一批重大项目与重大改革措施,支撑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可及。
做好“高”的文章,推动试点进一步强镇扩权。进一步规范指导县(市、区)对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放权扩权工作。推动建立县委常委联系小城市培育试点制度,逐步全面实现小城市培育试点党委书记由所在县(市、区)党委常委兼任。针对个别条件合适的,尤其是集聚人口大的小城市培育试点,明确县级管理权限。
做好“聚”的文章,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2020年,62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以占全省7.8%的行政区面积,集聚了11.8%的常住人口、创造了10.2%的总产出。很明显,小城市培育试点已经成为了全省人口、经济等要素的重要集聚地。建议下一步有序稳妥推进条件合适的小城市培育试点进行“强并弱”“大并小”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科学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服务功能。
做好“强”的文章,全面加强小城市要素资源配置。
2020年,柳市镇、横店镇、慈城镇、观海卫镇、塘下镇、杜桥镇和周巷镇进入全国百强镇行列,为深入做大做强,建议进一步压实小城市培育试点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地方主体责任,从省级层面明确县(市、区)对小城市培育试点的要素投入下限,鼓励其根据地方实际加大对小城市培育试点的要素投入,使试点小而强,确保全省小城市培育试点GDP年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以上。
做好“硬”的文章,推进一批“硬核”改革。建议建立“人钱”挂钩的激励性政策,进一步推动省、县两级政府依据吸纳常住人口数量给予小城市培育试点人员编制、领导职数、预算内投资等适当倾斜。推动建立“人地”挂钩的激励性政策,推动常住人口增长规模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保障相匹配,每年新增用地指标对常住人口增量大的地区倾斜。推动教育、医疗等增量资源在市域内与各地常住人口增量相挂钩,确保常住人口依法享有基本权益,逐步建立“人地钱”挂钩的政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