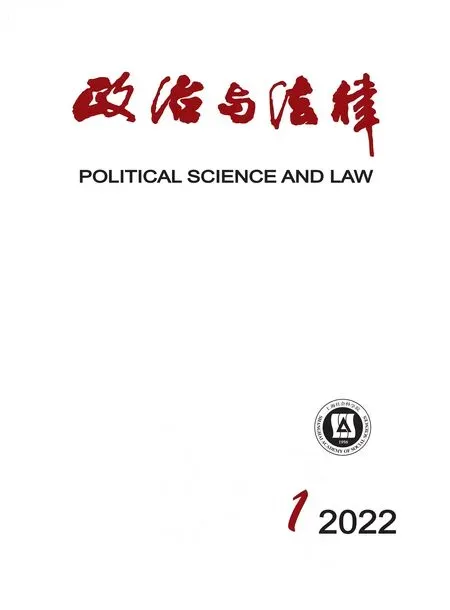情势变更制度下的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之反思
——一个法经济学的视角
2023-01-08吴逸宁
吴逸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一、问题的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533 条首次以法规范形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下的再交涉义务。〔1〕《民法典》第533 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据本条规定,情势变更产生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485 页。再交涉义务于20 世纪80 年代域外学说中首次被提出并于90 年代之后被《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国际性商事立法所采纳,〔2〕关于再交涉义务的形成史,域外学说多有介绍,概括性内容[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89-126 頁参照,此处不再赘述。虽然是否将其明文化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几经波折,〔3〕在《合同法》起草初期,《合同法》征求建议稿第四章第52 条、《合同法》草案第77 条曾尝试将再交涉义务明文化,但因《合同法》未规范情势变更制度而被搁置,其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虽然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但因对再交涉义务的研究尚未成熟也束之高阁。前期立法过程参见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174 页;沈德咏、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3 页。直至近10 年《民法典》编撰的需求,再交涉义务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再交涉义务最终得以规范化的前提还是得益于其相当契合现代合同法理念。从内在的意思自治理念角度上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理应由其自身通过再交涉达成新的合意,实现对当事人的自主性与自律性的尊重。〔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486 页。相同观点,另参见戚枝淬:《论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法律效果》,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年第3 期;王洪、张伟:《论比较法研究域下的情势变更规则及其使用》,载《东南学术》2013 年第3 期。从外在的诚实信用原则角度上看,再交涉义务本身契合诚实信用内涵,双方当事人应为对方利益考虑,体现了相互体谅义务的要求。〔5〕参见张素华、宁园:《论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再交涉权利》,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3 期。相同观点,另参见韩世远:《情事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3 期;杨明:《论民法原则的规则化——以诚信原则与情势变更原则为例》,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5 期;王闯:《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商事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09 年第9 期;张超:《论再交涉义务理论》,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院)》2011 年第7 期。前者正当化进路是对传统意思自治理念的适用维度进行扩充,从传统的契约严守原则(pacta sunt servanda)要求之“合意尊重”延伸到合同缔结后为解决纠纷而要求的“当事人尊重”,该理念契合我国鼓励交易原则,〔6〕王利明:《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 条》,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3 期。也体现了私法国际统一化“合同尊重(favor contractus)”的法思想。〔7〕“合同尊重favor contractus”是指通过限制合同不成立、无效与解除而使合同关系尽可能的成立与存续,尊重当事人自主设定的合同规范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关于“合同尊重favor contractus”理论之介绍,[日]森田修「『契約の尊重(Favor contractus)』について-債権法改正作業の文脈化のために-」遠藤光男元最高裁判所判事喜寿記念文集編集委員会『遠藤光男元最高裁判所判事喜寿記念文集』(ぎょうせい·2007 年)199 頁以下参照;[日]曽野裕夫「Favor contractus のヴァリエ一ション-CISG と債権法改正論議の比較を通じて-」松久三四彦ほか編『民法学における古典と革新―藤岡康宏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成文堂·2011 年)255 頁以下参照;中文文献参见[日]曾野裕夫:《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PACL 的相互作用》,焦淼淼译,小林正弘、韩世远校阅,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3 期。后者正当化的实质则以“关系合同理论”为基础,提倡当事人所负担的再交涉义务是产生于该交易中当事人形成的自身关系,经由诚实信用原则的检视上升为实体性规范以维护合同关系的“继续”与“应变”的要求。〔8〕“关系合同理论”的详细内容,[日]内田貴『契約の時代』(岩波書店·2000 年)43-88 頁、89-129 頁、133-169 頁以下参照。尽管考察角度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强调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自律性,还是倡导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协作性,两种合同价值观并无冲突和优劣之分,而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形成了对再交涉义务正当化的有力保障。
学界对再交涉义务的法理基础基本达成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欲实现再交涉义务的自律性、协作性的价值理念,其法律性质应如何定位。因再交涉义务产生于司法介入效果之前,学界普遍将其作为司法适用的前置程序规范。〔9〕《民法典》权威释义认为该义务具有法定性、强制性,是当事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前的必经程序。参见王利明、朱虎:《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45-346 页;朱广新、谢鸿飞:《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529 页。作为司法适用的一环,规范解释上将其与后续的司法介入效果作联动适用的观点愈发成为主流。一方面,为实现自律性,解释上应让当事人自行掌控合同的利益关系,缓和法院直接适用变更或解除效果的刚性,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过度介入的恣意性,如有观点主张应由当事人提供再交涉方案,而赋予法院依据该方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合理的权限。〔10〕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另一方面,为实现协作性,解释上有必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课以“诚实交涉义务”,通过法院对违反该项义务的当事人课以不利益的效果提升当事人协作解决纠纷的能动性,如有观点认为违反再交涉义务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1〕参见张素华、宁园:《论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再交涉权利》,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3 期;时明涛:《情事变更视域下再协商义务的理论构建》,载《西部法学评论》2020 年第2 期。或丧失后续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权限。〔12〕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王利明:《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 条》,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3 期。因而从理论上看,将再交涉义务定性为司法适用规范的解释不仅可保障其自律性、协作性的价值理念,从体系解释上看,再交涉义务与后续司法介入效果的良性互动也可使得情势变更制度法效果的适用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但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真能呈现如此美好的学理愿景吗。至少从笔者收集的案例来看法院似乎并不遵循这一学理解释。
实务中再交涉过程中一方具有违反协作性的再交涉义务行为,如明确表示拒绝交涉,〔13〕参见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2018)甘1124 民初3574 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7 民初581 号民事判决书。再交涉过程中作出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14〕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4 民初2441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 民终21355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 民初3825 号民事判决书。或者双方虽进行了再交涉,但长期交涉不成,〔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6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53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 民终3911 号民事判决书。一方提出再交涉方案,但仍无法达成合意〔16〕参见黑龙江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11 民终31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8 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等情形并不在少数,观察法院司法介入的判决内容,对当事人的风险损失分配或是平均分担、〔17〕依据各案件当事人请求的内容不同,此处的利益风险损失包括租金、承包费、押金、案件受理费等一系列的损失。前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皆体现了这一判决思路。或是依据相关合同、规范文件分担,〔18〕前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6 号民事判决书体现了该判决思路。或是依据案件事实分担,〔19〕前述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体现了该判决思路。质言之,法院的判断仅依据公平原则关注案件内容本身,而非将再交涉义务置于司法适用考量并对当事人的再交涉行为的样态抑或再交涉内容作出法律评价,学理解释所主张的再交涉义务与司法介入的效果衔接与相互作用似乎被割裂了。〔20〕笔者查阅的案件中,仅有1 件法院对于一方当事人非协作性的再交涉行为给予了否定的法律评价。参见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3 号民终2578 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既有的裁判思路是否存有不足,尤其在《民法典》已将再交涉义务明文化的背景下是否应依照学理解释作出改变,抑或现有的裁判解释路径有其合理性,应延续既有的裁判思路。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观点认为再交涉义务不应联动后续司法介入效果,其法律性质应定性为倡导性的。〔21〕参见尚连杰:《风险分配视角下情事变更法效果的重塑——对〈民法典〉第533 条的解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1 期。该观点与学界关于再交涉义务的主流学说形成对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与既有的裁判解释路径也相契合,但稍显遗憾的是提出这类观点的理由仅是建立在对现有的义务说、不真正义务说、附随义务说、权利说等观点的批判之上,而非从正面系统性论证为何对再交涉义务应作倡导性之限缩解释。当今价值多样化社会中,无论效率原则还是法经济学分析已为现代民法教义学理论的建构与阐释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22〕宏观理论层面的研究,参见熊丙万:《中国民法学的效率意识》,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5 期;贺剑:《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载《中国法学》 2019 年第2 期;微观制度层面的研究,参见贺剑:《担保人内部追偿权之向死而生——一个法律和经济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1 期。本文认为仅从传统法律价值层面去定位与设计再交涉义务过于理想化,下文欲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学理与实践产生落差的缘由及今后《民法典》再交涉义务祛司法适用化的根源所在。
二、再交涉义务的经济功效与适用界限
(一)再交涉义务的经济功效
合同关系要实现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检视政府、司法等公共主体对于私人生活的介入方式,另一方面则需要解明私人主体自主意思决定的运行机制。但问题在于现代合同关系纷繁复杂,合同一方当事人往往拥有对方当事人无法观察到的信息,双方当事人之间也存在各种形态的交易费用。即使双方当事人能把握这些信息与交易费用,但如何向法院证明也不易实现。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制约,当事人往往无法将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项都写入合同当中予以确认,为了诠释当事人意思决定的机理及其对合同立法、司法介入的理想形态,需要借助以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理论为中心的法经济学之分析方法。〔23〕[ 日]内野耕太郎=山本顯治「契約の経済学と契約責任論(上)」NBL942 号(2010 年)11 頁参照。依据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的观点,能够记录将来一切不确定的与合同相关联的事项的合同被定义为“完全契约”,而与之相对的无法在合同上记录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项的合同被称之为“不完全契约”。与“完全契约”相比,“不完全契约”往往无法带来效率性的结果,无法实现最优资源分配。因而如何在“不完全契约”交易形态下实现双方效用总和之最大化成为法经济学重要的课题之一。See Alan Schwartz,Incomplete Contracts,in Peter Newman ed.,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Palgrave Macmillan,1998,p.277-283.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实现合同的帕累托效率最大化,合同当事人首先会尽最大努力达成最佳投资从而实现事前的效率性(Ex Ante Efficiency)。但即使实现事前的效率性也并不意味着合同履行阶段必然带来效率性的结果,尤其在长期性、持续性合同中,纵观整个交易的从始至终,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偶发因素,如情势变更带来的风险变化使得事前的合意并不总能保证当事人所欲实现的利益分配,依合同缔结时的设想,需要将事前的利益分配规则依据事后的风险变化进行修正,从而实现事后的效率性(Ex Post Efficiency)。为达至这一目标,当事人有必要进行再交涉。〔24〕See Alan Schwartz&Robert E.Scott,Contract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Law,113 Yale Law Journal541(2003).具体而言,再交涉有如下经济功效。
对于再交涉本身的经济价值而言,一方面当合同需要调整去实现事后的效率性时,再交涉能为优化合同提供机会,特别对于那些糅合多种利益的合同变更问题,也仅能由正确把握其现实的利益状况的当事人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于事后发现、创造新的价值,因而相较于其他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再交涉更能发挥其效率性解决纠纷之功效。〔25〕Andreas Nelle,Neuverhandlungspfichten:Neuverhandlungen zur Vertragsanpassung und Vertrasergänzung als Gegenstand von Pflichten und Obliegenheiten,1993(Müchen,Diss),S.157.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171 頁。另一方面,学理上也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论证其效率价值,如有观点认为相较于法官主导模式,再交涉能够节约成本,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26〕参见张素华、宁园:《论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再交涉权利》,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3 期。在合同内容复杂的案件中,单纯由法官判断是一种浪费司法资源、效率低下的做法,经由当事人于合理期限内的低成本磋商是一种极具效率的体现。〔27〕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优化当事人地位、实现新的价值创造以及降低成本仅是再交涉本身所内含的价值内容,为使其隐藏的价值创造等经济功效予以现实化,实现当事人真正的利益共享之局面,有必要对当事人课以再交涉义务。〔28〕Horst Eidenmüller,Neuverhandlungspflichten bei Wegfall der Geschäftsgrundlage,ZIP 1995,S.1068.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195 頁。
(二)再交涉义务的适用界限
诚然,理论上再交涉义务能成为保障当事人新的价值创造之制度性担保工具,但这种观察往往建立在单一的、固定的理想化交涉形态之中。换言之,再交涉义务虽能促成当事人去实施再交涉的行为,但现实中当事人呈现的再交涉形态显然更为复杂。依据交涉理论,交涉模型分为原则性交涉(principled negotiation)与立场型交涉(positional negotiation)。前者交涉模型中双方当事人不拘泥于纷争对象本身,相互理解对方背后的利益情况,制造出各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同时也符合市场价格、专家意见、习惯、法律等一系列客观基准,这种交涉无疑能增进帕累托效率。而后者交涉模型恰恰相反,双方当事人对立观点鲜明,交涉往往使当事人关系更加恶化或者隐藏当事人背后之真正的利害关系,因而无助于纷争的解决,经济上也不会产生新的价值。〔29〕[美]ロジャ一·フィッシャ一=ウィリアム·ユ一リ一=ブル一ス·パットン([日]金山宣夫=浅井和子訳)『新版 ハ一バ一ト流交渉術』(TBS ブリタニカ·1998 年)16 頁参照。
由此可得,再交涉发挥经济效用的前提是建立在原则性交涉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但关键是这类以协作性行为导向的再交涉形态往往与当事人的现实行为产生了背离。如前述司法案例中,一方当事人再交涉过程中具有发出解除通知、〔30〕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4 民初2441 号民事判决书。搬离店铺、〔31〕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 民终21355 号民事判决书。撬门换锁〔32〕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 民初3825 号民事判决书。等不予协作性的再交涉行为,或者虽然当事人提出再交涉方案,但相互不肯妥协,导致再交涉长期无法达成合意,最终以解除收场。〔33〕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53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6 号民事判决书。为何再交涉过程会产生此类“立场型再交涉”之情形,问题的本质还是需考察阻碍当事人采取协作式再交涉立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理论成因。
(三)“立场型再交涉”的理论成因
缘何会形成“立场型再交涉”,究其原因在于既有的研究注重对于如何履行该项义务之法律行为的正当性评价,而忽略了最为本质的围绕再交涉构造、再交涉策略等涉及到再交涉行为本身分析的实践性观点。具体而言,其理论成因体现于以下两方面。
1.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
从当事人的交涉心态或战略来看,当事人的交涉行为本身面对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如上文所述,交涉的形态分为协作型的原则性交涉与对立型的立场型交涉。从经济意义上讲,前者的这类交涉形态能实现“扩大资源”之价值创造,而后者的这类交涉形态只能形成“掠夺资源”之价值索取。尽管合作能实现利益共享的原则性交涉无疑是当事人的最佳抉择,但如果依照博弈论分析当事人的交涉行为,答案会有所不同。因为交涉中对方采取协作交涉之立场,而自身采取消极交涉之立场时,自身就可以掠夺对方资源,对方采取消极交涉之立场时,为防卫自身不被对方掠夺资源,自身还是会采取消极交涉之立场,因而即使双方意识到采取协作交涉之立场会实现“扩大资源”之价值创造,采取消极交涉之立场的交涉行为仍会占据上风。〔34〕See David A.Lax&James K.Sebenius,The Manager as Negotiator:Bargaining for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ve Gain,Free Press,1986,p.29-45.当将该交涉中的博弈行为放置于情势变更产生后的再交涉情境中,只可能加剧这种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因为已被机会主义交涉行为利用的当初的“扭曲的合同均衡”面临着被当事人非合作性的机会主义交涉行为再一次分配的风险,其结果只能使优化合同、实现价值创造的目标渐行渐远。〔35〕Andreas Nelle,Neuverhandlungspfichten:Neuverhandlungen zur Vertragsanpassung und Vertrasergänzung als Gegenstand von Pflichten und Obliegenheiten 1993(Müchen,Diss),S.132f.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173 頁。由此观之,当再交涉存在被机会主义利用,即当事人将当初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有利于自身的形式再次分配时,再交涉义务很难起到抑制作用,反而会加剧机会主义行动风险产生的可能性。〔36〕再交涉义务的规范解释上,存在经由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课以“诚实交涉义务”,对违反该义务的当事人课以一定的责任来抑制机会主义行动产生的弊端。但问题在于不仅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法律后果存在理论上的争议性与模糊性,法官对于当事人违反“诚实交涉”之机会主义的认定往往并不容易。关于该点的详细分析见于后文。
2.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
从当事人的交涉构造来看,双方当事人的再交涉地位往往并不处于均势。首先,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信息量本身的差距。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信息和对合同理解能力等不足,通过交涉获取远远超过交易产生的总剩余的收益,导致双方的利益失衡。〔37〕此即所谓“寻租”(rent seeking)的问题。See Avery Wiener Katz,The Economics of Form and Substance in Contract Interpretation,104 Columbia Law Review 496(2004).为矫正此类当事人信息或能力上的不足,制度上可通过对信息优势方课以提供信息义务或对格式条款规制等方式来抑制此类问题的发生。因此情势变更产生后面对当事人再交涉时信息不对等之困境,有观点主张再交涉义务应该包括提供信息义务。〔38〕Andreas Nelle,Neuverhandlungspfichten:Neuverhandlungen zur Vertragsanpassung und Vertrasergänzung als Gegenstand von Pflichten und Obliegenheiten 1993(Müchen,Diss),S.262.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187 頁。我国亦有学者主张当合同调整方向不甚明确时,再交涉义务表现为当事人间的信息提供义务。参见朱朝晖:《潜伏于双务合同中的等价性》,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1 期。但提供信息行为作为再交涉行为的一部分,即再交涉的目标指向资源、收益之价值掠夺时,比如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其本质都有被机会主义行动支配的风险。
其次,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合同缔结后容易产生情势变更的长期合同本身更易加剧当事人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长期合同中,当事人因仅对该合同先行投资〔39〕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该类投资被称之为交易特殊性投资,即该投资仅对和特定对方之间的交易产生价值,对除此之外的交易没有任何意义。[日]細江守紀『法と経済学の基礎と展開―民事法を中心に-』(勁草書房·2020 年)35 頁参照。而享有该合同关系存续利益的不在少数。因而发生情势变更时,通过先行投资而确保了一定利益的当事人不得不进行再交涉,先行投资的存在就会弱化自身再交涉的立场,结果导致不得不让步,带来的代价就是事前期待利益的损失。此时再交涉义务无疑成为一种负担,预测到事后无法避免再交涉情形的当事人会担心再交涉会使先行投资变为徒劳,从而取消投资或放弃交易,影响事前效率性的实现。另一方面,原本不希望调整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反而会欢迎赋予其再交涉的机会,因为与其接受之后法院对其不利的合同调整,还不如利用其再交涉地位的优势形成对另一方的压力,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再交涉义务不仅无法抑制这种再交涉地位的落差,而且还会助长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成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掠夺资源更加“稳健”的手段。〔40〕Michael Martinek,Die Lehre von den Neuverhandlungspflichten:Bestandsaufnahme,Kritik.und Ablehnung,AcP 198(1998),S.374.,378ff.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204 頁参照。
基于上文的分析,当再交涉存在被机会主义行动利用的风险、双方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等固有缺陷时,无助于经济价值创造的立场型再交涉形态无疑会成为现实中的主流,再交涉义务不仅无法治愈该负面因子,反而会成为这类负面效应的助推器。那是否有办法消除这类不利的因素,还原再交涉义务所构想的应有的价值内容呢?理论中似有将其置入后续司法适用过程,通过后续司法介入效果来支援发挥再交涉义务功效之办法。
三、司法介入与信息偏差
(一)司法介入的必要性
根据《民法典》第533 条的规定,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后果包括了再交涉义务与后续的司法介入效果。既有的观点主要从法官过度介入当事人合同的担忧,有必要限制法官介入权限的角度去论证再交涉义务的必要性,从而形成两者司法适用的互动。〔41〕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但从法经济学角度观察,两者关联逻辑恰恰相反,后续的司法介入恰能弥补再交涉义务中隐藏的消极效应,发挥再交涉义务的价值内容,其手法有以下两条。
首先,法官可事后观察当事人的再交涉过程,寻找出双方“再交涉地位不对称”的因子,如当事人信息的获取和理解能力、信息的开示与否等,依照如无该再交涉地位不对称就会达成的再交涉结果之标准对合同内容进行修正。
其次,法官完全站在事后的立场,以对当事人来说该结论可谓公平之标准对合同内容修正。值得注意的是,为矫正再交涉过程产生的机会主义,法院需要观察当事人再交涉的行动过程,依照如当事人“诚实交涉”就会达成的再交涉结果之标准对合同内容进行修正。
由此观之,司法介入对于抑制当事人再交涉中产生的机会主义行动,矫正当事人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具有无法忽视的作用。从该角度考察,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恰能发挥其应有价值功效。
(二)法官信息偏差的困境
尽管理论上存在通过司法介入修正合同之路径弥补再交涉义务固有的缺陷,但该路径是否具有可行性则需要进一步论证。按不完全契约理论,合同不完全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五点。第一,合同用语的暧昧性;第二,当事人的不注意、怠慢;第三,缔结完全合同所需的费用;第四,信息的不对称性;第五,当事人不区分自身的属性订立合同的可能性。其中,对于前三种原因,法官可以通过效率性的条款对合同进行补充,对于第五种原因,法官可以通过促进当事人提供相关信息,实现效率性合同的缔结。〔42〕[美]イアン·エ一ル=ロバ一ト·ガ一トナ一([日]渡辺達德訳)「不完全契約における欠缺補充――デフォルト·ル一ルの経済理論」[美]ロバ一ト·A·ヒルマン=[日]笠井修編『現代アメリカ契約法』(弘文堂·000 年)177-183 頁参照。唯独第四种关于信息不对称之原因,法院尚无有效应对。如果某项信息对于当事人不能观察时,当事人也就无法根据该信息缔结合同,同样当该信息对于法官不能验证时,那依据该信息缔结的合同也无法得到强制履行。无论如何,法官都无法适用以补充当事人所期望的条款之方法来填补合同的不完全性。该结论不仅是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即使从法官应依照公平原则所提示的解决方法之传统进路也无法得到有效的答案。换言之,如果合同不完全的原因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则无法采取有效补充手段的法官,也只能默认合同具有完全性,按照合同文意对合同进行解释。〔43〕See Alan Schwartz,Relational Contracts in the Courts:An Analysis of Incomplete Agreements and Judicial Strategies,21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71(1992).
根据上述理论,当法官面对情势变更后当事人再交涉之局面时,无疑更会面临因信息偏差无法对合同做出有效修正之困境。如前文所述,当事人再交涉失败主要原因是基于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与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称,后者本身涉及到当事人的信息的获取、理解、处理等能力的差异,而前者也会存在当事人故意操作信息的机会主义风险,因而这些信息对于法官来说大多无法观察,也不能检验。例如对于机会主义的判断,仅凭当事人事后“利益状况的显失公平”判定基本不可能,还需要考察当事人再交涉的意图、进行再交涉的背景、动机等信息内容,同样对于再交涉的意思决定是否合理之判定,不仅是对于各种风险因素之考察,对于再交涉背后所涉及的交易主体的短期、长期之投资战略、经营规划等信息要素亦需要权衡考虑。由此观之,再交涉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都无法完整把握的信息内容,需要法院在有限的信息中观察当事人的再交涉过程,判定机会主义的存在,全局把控情势变更后纠纷的全貌更不现实,从而导致法院判断失误可能性大大提升,无法很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之公平分配的目标。
四、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之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得出,再交涉义务虽然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有用性,但受制于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以及再交涉地位的不对等因素,其应有的价值内容无法得到有效地发挥。即使通过事后司法适用试图弥补再交涉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因素,但法官所面临信息偏差之困境使其无法很好地承担这一角色。我国对于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的要件、内容和法律效果的构建都受到德国学者霍恩(Horn)及奈勒(Nelle)的再交涉义务论之影响。〔44〕对域外再交涉义务论详细引荐的代表性文献参见刘善华:《日本和德国法上的再交涉义务及对我国合同法的启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奈勒(Nelle)所构建的再交涉义务的动态体系论,其司法适用的前提也是建立在“具有完全信息的独立观察者的视角”基础之上的。〔45〕Horst Eidenmüller,Neuverhandlungspflichten bei Wegfall der Geschäftsgrundlage,ZIP 1995,S.1070.转引自[日]石川博康『再交渉義務の理論』(有斐閣·2011 年)201 頁。换言之,理论的设想无意识中预设了法院对当事人再交涉背景及再交涉过程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而这一假定无疑对当事人的再交涉行动、策略起着制约作用,如识别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机会主义,在这一前提下,法院实现公平之目标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当法官面对产生情势变更之后当事人多样化利益需要再分配之课题以及再交涉形态的错综复杂情形时,其常能获取充足的信息得到妥适的结果之前提并不现实,前述司法案例中当事人消极交涉或交涉破裂情形下法院避开对当事人再交涉过程作出法律评价也间接佐证了该观点。当然,笔者的这一预设需要结合《民法典》规范作进一步学理论证。
依据交涉理论,当事人的再交涉行动、策略是以再交涉不成时的利益状态为基准的,在预测法院作出何种结论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再交涉。因而考虑到司法后续介入效果适用的可能性,当事人会将该介入效果作为引导其设计再交涉战术的依据。根据《民法典》第533 条的规定,司法介入效果为合同变更与解除,因而有必要以这两种效果为前提对当事人再交涉的行动过程予以分析。此外,既然法官信息偏差会对司法介入效果、当事人再交涉形态产生影响是本文论证的焦点,下文将以此为区分基准作分析。
(一)假定法官无信息偏差
以买卖合同作为典型模型分析产生情势变更后当事人的再交涉行为。假设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了某个产品的买卖合同,该产品买卖合同的固定价格是P,对于买受人来说该产品的价值是V,出卖人制造该产品的成本为C,后因原料价格急剧上涨,出卖人的制造成本也飙升到C'(假定C'>P>C),同时对于买受人来说该产品的价值也飙升到V'(假定V'> C'),且该原料价格的急剧上涨满足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要件。如将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介入效果定位于合同解除,当事人会将合同解除作为再交涉不成时的后果而行动。合同解除时各当事人的利益状态主要由合同解除时发生的费用和替代交易时的期待利益构成。假设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各自解除费用分别为A1、A2,期待利益分别为B1、B2,变更价格为P'。
首先,出卖人、买受人同意合同变更的条件分别为B1-A1 ≤P’-C’、B2-A2 ≤V’-P’(解除后的利益状态≤变更后的利益状态)。因此当满足C'+(B1-A1)≤P'≤V'-(B2-A2)的P'存在,即满足(B1+B2)-(A1+A2)≤V'-C'条件之时,当事人才可能一致达成合同变更的合意,反之当该条件不满足时,合同被解除符合当事人的利益。换言之,合同是否被解除取决于(B1+B2)-(A1+A2)与V'-C'的大小比较,因此当当事人期待利益的总和B1+B2 过大或者当事人解除费用总和A1+A2 过小时,两者之差无法满足小于V'-C'可能性就会变高,合同被解除的倾向就会变大。但问题在于一旦出卖人解除时利益(B1-A1)与买受人解除时利益(B2-A2)间产生落差,如出卖人可确保充分的期待利益B1,而买受人的期待利益B2 过小或解除费用A2 过大时,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利益状态会失衡。因此尽管合同解除效果上直观明了,但无法忽视出卖人基于对替代交易的期待而无视买受人继续履行合同要求的风险,导致其固执于合同解除的机会主义行动的产生。尤其对于买受人来说,当其替代交易十分困难,或者合同解除会给其带来巨大的损失时,对于出卖人的合同解除请求有必要通过制度的设计予以限制。
由上述案例观之,将合同解除作为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效果时,存在着制度上巨大的弱点,尤其是涉及多数人参与的直接或间接合同交易形态,解除合同会导致巨大的解除费用,导致双方当事人间显失公平的结果。因此,以合同变更取代合同解除,赋予法官变更合同的权限,是否更能够抑制机会主义的产生并矫正当事人利益分配的明显不公平之现象?通过前文分析,当法院无信息偏差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具体而言,当将再交涉义务置于司法适用的法律评价时,法院以能获取充分信息为前提观察当事人再交涉的过程,发现当事人再交涉地位不对称及机会主义行动的不利因素,通过后续的合同变更效果矫正再交涉地位的落差以及机会主义行动引发的利益失衡;反之,合同变更效果的作用会间接影响当事人再交涉的策略选择,从而发挥再交涉义务应有的经济功效,比起具有助长机会主义风险的合同解除,合同变更无疑是情势变更制度司法介入法律效果的最佳选择。
(二)假定法官有信息偏差
经由上文分析,假定法官无信息偏差,辅以后续合同变更之介入效果时,再交涉义务无疑能彰显其制度的优越性,但问题在于当司法实践中法院遇有信息偏差时,则未必能得出如此理想化的结论。
将合同变更作为司法介入效果时,与将合同解除作为预设前提不同,当事人再交涉不成时将以此调整自身的再交涉策略并展开再交涉。此情形下,当事人会预测被法官最终认定妥当的合同变更判决,并将其作为再交涉不成时的利益分配内容,相较之法官的认定方案,如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再交涉无法获取比其对双方更为有利的变更内容,即无法实现更优的帕累托利益分配时,再交涉的结果也只能是无限接近被法院认定妥当的合同变更内容。但问题在于,当事人事前预测被法院认定妥当的变更内容无疑非常困难且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要法官从双方当事人那里获取的信息有限,法官的判断未必就能做到公平。由此产生的疑虑是,当事人预料到法官判断的不确定性,反而会有意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进而引导法院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因此,即使是一些合同类型或性质上易于找到再交涉上的妥协点的案件,当事人也会通过操纵自身掌握的信息意图制造出不容易找到妥协点的外观。考虑到再交涉不成时只能依赖于法官的合同变更,当事人势必会在再交涉的现场仅将被法院认为对自身有利的事实与信息置于台面上,无形中受到法官判断结果影响的再交涉,对于合意形成无疑会产生巨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将合同变更和合同解除分别作为司法介入的效果予以分析,如果依照《民法典》第533 条的文义解释,当有赋予法官自主裁量合同变更或合同解除之解释可能,此情形下当事人的再交涉会面临更加复杂的难题。且不论合同变更单独作为司法介入的效果尚有诱发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如法官享有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的选择权,当事人在制定再交涉策略时,自身的再交涉立场会随司法介入效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需考量的因素更加复杂,当其有必要将法官引向合同变更或合同解除的任一方向时,该诱导策略也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如将法官介入效果引向合同变更,如何决定变更的内容也是不得不考量的因素。因此当再交涉掺和了各种机会主义的博弈,其不仅无法消除当事人再交涉地位不对称之障碍,也会导致与实现当事人公平之利益分配的目标渐行渐远的结果。反之,对于法官来说,当面对合同变更这一复杂课题时,原本对当事人课以再交涉义务使其能透过观察当事人再交涉过程,获取更多合同变更所必要的信息,但充斥着信息操纵的策略性的再交涉形态,显然带给法官的不再是当事人自主交涉中提供的信息,而只可能是预见法官终局性介入情况下带有战术意义被操作过的信息。当法官无法获取有效信息时无疑会影响到法官司法介入结果之公正性。
(三)小结
假定法官无信息偏差,通过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能克服其固有的缺陷。但这一假定几乎是理想化的状态,司法实践中当法官遇有信息偏差时,当事人的再交涉必然以法官司法介入的判断作为再交涉不成时的最终利益分配的前提,预料到法官判断的不确定性时,各种机会主义就会不断涌现,当事人通过对信息的操纵引导法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因而将再交涉义务置于司法适用的法律评价时,再交涉的实质终究是着眼于法官最终介入的“影子交涉”,〔46〕“影子交涉”的文献,See Robert H.Mookin&Lewis Kornhauser,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A Testable Model of Strategic Behavior,11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25(1982).而无法促进当事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交涉。从法官的角度来看,在顾及判决结果之公平性的同时,还需要专注于当事人再交涉过程的行为状态与内容,无疑使其判断愈发困难。
五、现有学理解释的反思与出路
如开篇所述,为保障再交涉义务的自律性、协作性之价值理念的实现,学界普遍观点是将再交涉义务作为司法适用的前置程序并与后续司法介入效果形成联动适用的效应。但经由上文论证分析,当着眼于当事人再交涉过程中行为的博弈特征及法官信息偏差的现实困境,将再交涉义务置于司法适用之法律评价的规范解释反而会引发司法介入效果适用的混乱,不利于法官事后对当事人利益分配的公平判断,因而有必要重新反思对于再交涉义务的现有学理解释。
(一)诚实交涉义务之质疑
诚实交涉义务是学界对于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的核心规范内容,其也是受外在诚实信用原则获取正当性的应有之意。〔47〕参见王利明:《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 条》,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3 期。因而无论是义务说、不真正义务说、附随义务说还是权利说等观点皆会通过强调当事人具体的义务内容,如提供充足真实信息的义务、提案义务,主张违反该项义务承担一定的不利益后果,如损害赔偿责任或丧失后续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权限〔48〕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来促成当事人进行实质性的再交涉以抑制机会主义行动的产生。
然而,如前文所论证分析,在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逻辑下,司法实践中再交涉现场是以法官的终局性介入为预设前提掺杂着各种复杂的博弈,当预见再交涉义务内含“诚实交涉”之要求,质言之自身的再交涉姿态影响着法官的判断时,当事人关心的也不会是再交涉本身会不会促成合意的达成,而是尽力展现出一个“诚实”再交涉的姿态去实施各种再交涉的策略,如即使不同意对方的再交涉方案,也会表现出积极参与再交涉之假象,最终导致再交涉长期拖而不决反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从法官的角度来看,“诚实交涉”本身即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基准,其相当于对法院又创设了一个新的任务,假设无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法官仅需专注于合同介入效果之结果上的公平性,但一旦加入再交涉义务这一道前置程序,法官还需负担“诚实交涉义务”之判断,识别当事人在再交涉过程中实施的提供信息等一系列行为是否具有机会主义因素以及观察当事人是否具有协作性的再交涉姿态并对其作出妥适的法律评价,当法官遇有信息偏差时,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二)再交涉方案合理性判断之缺陷
我国有学者也意识到法官判断能力的局限性,主张限制法官自主决定变更合同的内容,而改由仅赋予法官判断当事人的合同变更方案是否合理的权限。〔49〕参见吕双全:《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在理念层面,该观点也能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的意思自治。但问题在于,当法官遇有信息偏差时对于合同变更方案是否合理的判断同样会举步维艰。再者当事人提出甲方案不尽合理,那会继续提示乙、丙、丁等方案,只要当事人提示其所预设的所有可能的方案,法官也需要一一予以回应,无形中又增加了法官相当的负担。此外更易被忽略的是,一旦该规范解释被采用,当事人在再交涉过程中自主达成合意的妥协将更不复存在。以前述买卖合同变更为例,即使买受人不同意出卖人提出的变更方案P1,其也可以提供比变更方案P1 更低的变更方案P2(P2 <C'),采取伪装协作的再交涉态度而实则回避达成再交涉妥协之策略,将最终判断交由法官处理。而对于出卖人来说,同样考虑到再交涉过程自身的让步对于法官的判断会产生影响,因而也不会轻易达成妥协,而是固执于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变更方案P1,这样的再交涉无疑多会以交涉决裂收场,法官也不得不面临着更多合理性判断之难题。
(三)出路所在:再交涉义务祛司法适用化
由以上分析可得,无论是诚实交涉义务还是再交涉方案合理性判断的观点不仅无助于实现再交涉义务所应有的自主性、协作性之价值追求,而且给法官创设了几乎难以完成的新的司法判断之负担,导致适得其反之规范适用效果。在此意义上,再交涉义务司法适用之规范解释逻辑构造上非常完美,但却忽略了当事人再交涉行为的博弈属性及法官信息偏差之现实困境的不利因素,因而有必要在《民法典》视域下重新定位再交涉义务。
其一,再交涉的本质一定是双方自愿行为,不应对一方拒绝再交涉或其他不予协作再交涉的行为作出法律评价。如果强迫没有再交涉意愿的当事人去再交涉,只会形成消极再交涉,不仅双方无法达成自主合意,还会诱发再交涉过程中机会主义行动风险的产生,在法官遇有信息偏差之困境时,其无法进行有效判断。此时再交涉义务虽有“义务”之名而无“义务”之实,即理论上不应将其定位于任何一种形态的义务属性,违反该“义务”也不会产生任何不利益的法律后果。
其二,即使双方都有再交涉意愿并展开了再交涉的行为,无论是出自于何种动机与目的,只要无法达成合意的,应限制法官介入当事人的再交涉过程并对其再交涉的内容作出法律评价,包括对当事人的再交涉方案进行合理性判断。因为一旦解释上法院享有对于再交涉过程及内容的评价权限,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当事人“影子交涉”的倾向,阻碍当事人真正的自主再交涉。且在法官遇有信息偏差之困境时,也无法对再交涉过程及内容作出正确、有效的判断。
基于上文的论证分析可以得出,将再交涉义务是否置于司法适用之法律评价,其对法院的判断要求与司法效果会产生巨大差别,而情势变更制度之目的的本质在于法院对于当事人客观上导致的利益失衡之状态进行矫正,而并非对再交涉本身的样态与内容作出评价,因而对于再交涉义务的定位只可能是祛其司法适用化,将其纯化为一项倡导性规范,只有如此其反射性效果才能避免机会主义再交涉行为的产生,实现当事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再交涉,同时缓解法院后续介入之司法负担,最大程度保障对当事人利益分配的司法判断之公平性。
六、结 论
纵观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立法过程,为发挥再交涉义务理念上解决纠纷之自律性、协作性的价值基础,学理解释上普遍将其作为司法适用的前置程序规范,主张其与后续司法介入效果形成体系化互动,实现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效果适用的逻辑一贯性。但司法实践的运用未给予学理期待之积极回应,需要对学理与实践产生的落差及《民法典》成立后再交涉义务的定位作出解答。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再交涉义务能作为实现优化当事人地位、创造新的价值以及降低成本等诸多经济功效的制度性担保工具,但受制于再交涉行为特有的博弈属性以及再交涉结构固有的不均衡因子,再交涉的主流形态只可能是对立而非合作,再交涉义务无法抑制再交涉中机会主义行动风险的产生以及矫正再交涉地位的落差。虽然原理上通过借助后续司法适用的法律评价,联动司法介入法律效果可克服适用再交涉义务所产生的弊端,但司法实践中考虑到法官信息偏差之现实困境,面对当事人以法官终局性介入为前提而开展的“影子交涉”,法官无法对再交涉过程中的行为样态及再交涉内容作出准确、有效的判断。而诚实交涉义务抑或再交涉方案合理性判断之构想无形中又阻碍了当事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交涉及给法官创设了介入再交涉过程和作出妥适的法律评价之新的司法负担,反而背离了通过再交涉义务的司法适用实现当事人利益公平再分配之目标。《民法典》视域下唯有对再交涉义务作祛司法适用化之限缩解释,将其纯化为倡导性的规范,切断其与后续司法介入效果的适用关联,限制法官介入再交涉过程之法律评价,始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法官有效完成当事人利益之公平分配的司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