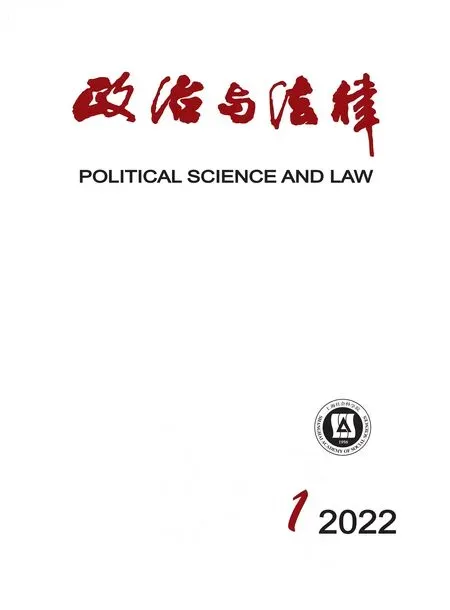美国轻罪治理体系的现状、困境及反思*
2023-01-08冀莹
冀 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根据美国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NCSC)的统计,在美国,轻罪的数量占到所有犯罪数量的3/4,〔1〕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80%的案件都属于轻罪,参见Alexandra Natapoff,Criminal Misdemeanor Theory and Practice,in Markus Dubber &Tatjana Hörnle eds.,2016.Oxford Handbook Online,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52.001.0001/oxfordhb-9780199935352-e-9,2021 年7 月20 日访问。每年大概有一千三百多万个轻罪案件。美国的轻罪制度实现了犯罪处遇的“两极化”,强化了刑法对公民行为的规训和指引,修正了传统的犯罪处理机制,缓解了美国大规模监禁造成的监狱压力,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但是,轻罪制度适用中酿生的正当性危机,也诱发对这一犯罪治理机制的深入思考。我国正在经历立法观的代际更新,积极主义立法观导向下的中国刑法立法,〔2〕参见魏昌东:《新刑法工具主义批判与矫正》,载《法学》2016 年第2 期。不断扩大以规制风险为目的的轻罪范围,《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新增高空抛物、冒名顶替、袭警、妨害安全驾驶以及催收非法债务等属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轻罪被认为是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是刑法向“严而不厉”结构化调整的标志,是行政处罚权司法化改造的方法。〔3〕参见苏冠宇:《我国轻罪制度构建的困境及对策》,载《中州大学学报》2019 年第2 期;王振华:《新时代轻罪治理的观念转变与路径选择》,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但是,轻罪的增扩也被指责加大了象征性刑法的范围,有违刑法谦抑的原则,偏离了刑事立法的法益保护基准。〔4〕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载《法商研究》2017 年第6 期;魏昌东:《刑法立法“反向运动”中的象征主义倾向及其规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6 期。轻罪的学术争议折射出刑法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地位的迷思,本文以美国轻罪制度为例,探究美国轻罪治理体系建设的经验,为我国轻罪立法模式与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美国轻罪的规范性定位
美国的轻罪制度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依托制定法规范发展起来,是一个以立法为先导的自然建构的过程。轻罪罪责轻微且罪名范围广泛,尤其在20 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轻罪案件数量激增,造成与有限的犯罪治理资源之间的冲突。通过减损部分程序性权利和广泛适用非监禁刑,轻罪制度实现了案件分流,构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轻轻”一极。
美国的轻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普通法关于轻罪的规定。〔5〕John M.Scheb &John M.Scheb II,Criminal Law,Wadsworth Publishing,2011,p.10.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在普通法中存在已久,轻罪一词最早为demeanor,原意为对他人实施的恶行,属于侵权行为,〔6〕“Misdemeanor”:Not Always a Crime,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words-at-play/misdemeanor-word-history-not-always-acrime,2021 年8 月18 日访问。16 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犯罪类型的一种。〔7〕Dennis J.,Owens,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The Definitions of an Impeachable Offense,Journal of Legislation,1975,vol.1:Iss,article 8.英国自从14 世纪就开始使用“犯罪与轻罪”(crimes and misdemeanors)一词,并作为固定搭配沿用至美国独立战争。法官依据刑罚的轻重程度将犯罪分为叛国罪、重罪和轻罪,〔8〕叛国罪后被纳入重罪的范畴之中,重罪与轻罪的分类标准得以继续保留。划分目的在于对不同犯罪的处置程序进行分别处理。轻罪作为危害结果和恶意都较重罪更为轻微的行为,〔9〕Commonwealth v.Flaherty,25 Pa.Super.490,493(1904).开始与重罪遵循不同的处理模式,如轻罪案件无大陪审团参与起诉,无预审程序,一般在较低层级的法院审理,非陪审团审判,审理流程也较为简单。如果被定罪,轻罪人被关押在看守所而非监狱里。〔10〕Martha A.Myers,Common Law in Action:The Prosecution of Felonies and Misdemeanors,Sociological Inquiry,vol.52(1),p.1-5.1982.在轻罪诉讼制度中,国家机器的介入相对有限,正当程序的价值也并不凸显。普通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区分在决定法院的审理层级、处理程序、刑罚种类以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等问题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为美国的轻罪制度奠定了基础。
普通法是美国刑法的重要渊源,美国判例法延续了重罪与轻罪的分类方法。美国大多数州在独立之前的殖民时期就存在普通法罪。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继受了普通法中的轻罪教义,〔11〕Stanislaw Pomorski,American Common Law and the Principle Nullum Crimen Sine Lege,De Gruyler:Mouton,1975,p.164.只是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受到大陆刑法法典化运动的影响,美国的制定法主义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诸多州纷纷出台刑法典废除普通法,普通法罪在联邦和州层面被逐步废除,普通法上的重罪和轻罪也被成文法化。美国法典以及各州法典对普通法中的轻罪进行了整合和分级,仍然以刑罚的轻重作为重罪与轻罪的主要划分标准。美国制定法对普通法中轻罪的调整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制定法一方面对轻罪和重罪的边界进行了现代化的调整,如伪造罪、绑架罪等在部分州的普通法中曾经是相对严重的轻罪,在制定法中被纳入重罪范畴,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于罪行轻重的认知。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社会管理日益复杂化的现实需要,制定法在延续普通法规定的前提下不断引入新罪罪名,对普通法中轻罪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导致规范化后的轻罪在种类上急剧增加。普通法中只有几十种轻罪,目前轻罪的种类却增加到数百乃至上千种。〔12〕Issa Kohler-Hausmann,Managerial Justice and Mass Misdemeanors,Stanford Law Review,vol.66,p.630.2014;Jenny Roberts,Why Misdemeanors Matter:Defining Effective Advocacy in the Lower Criminal Courts,UC Davis Law Review,vol.45,p.294.2011.随着交通领域中轻罪的加入,轻罪的适用主体从社会贫困人群覆盖到中产阶级,〔13〕Lawrence M.Friedman,American Law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83.轻罪随之发展为整体性的行为规训与风险控制机制。
至今在美国,轻罪与重罪仍然是犯罪最为重要的分类标准,多以“一年以下的刑期”作为决定刑罚轻重、诉讼程序和附随性结果的依据。美国刑法大多先在具体罪名中规定个罪对应的轻重等级,再另行规定不同等级犯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在具体适用中,司法机关需通过个罪与量刑规则的对接完成对具体刑期的判断。以刑罚轻重为标准,通过轻罪轻判、重罪重判,尽量避免因量刑不规范而违背宪法修正案中比例性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联邦层面,《美国法典》第18 篇“犯罪与刑罚”设有关于重罪、轻罪与违警罪的条款,第18 篇第227 章第3559 条对重罪、轻罪进行了详细分级,触犯轻罪可被判处五天至一年的监禁,超过一年刑期的刑罚均被归为重罪。在各州层面,许多州的刑法典也对轻罪进行规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是多数州的做法,如《纽约州刑法典》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分为三大类,其中,轻罪会被判处一年以下十五日以上的监禁或罚金,包括不同等级但均相对轻微的骚扰、盗窃和诈骗等行为。违警罪对应十五日以内的监禁,如五级教唆(第100 条)、二级欺凌(第120.17 条)以及扰乱秩序等行为(第240.20 条)等,属最轻微的犯罪类型。再如《佛罗里达州法典》第775 章也对轻罪、重罪及违警行为进行了区分,其中第775.08 条规定,轻罪的监禁不超过一年,与重罪合称为犯罪行为。只是在佛罗里达州,违警行为不属于犯罪,处罚也仅限于罚款、没收犯罪工具或者其他处罚方式等。〔14〕The 2020 Florida Statutes.
轻罪涵盖了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的诸多个罪,其中,危险驾驶行为、轻微的骚扰行为、未达到规定数额要求的盗窃行为和持有大麻等四种行为属于最为常见的轻罪类型。在纽约州,此四类犯罪占据了所有轻罪案件的50%-60%左右。〔15〕Sandra G.Mayson &Megan T.Stevenson,Misdemeanor by the Numbers,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61(3),p.980.999.2020.其他罪名包括公共场合醉酒、非法入侵、卖淫、抗拒逮捕、故意向警察提供不实信息、持有犯罪工具、威胁他人和违反动物保护法等。除数量庞大的个罪外,不完整犯罪以及共同犯罪等修正的犯罪构成也是轻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纽约州刑法典》第100-115 条规定了教唆、共谋、未遂和帮助型犯罪,〔16〕NY Penal Law § 110-115.根据目标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犯罪人的主观目的性以及参与对象的个体性特征,如被告或受害人是否包括未成年人等因素,这些修正的犯罪构成也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刑罚。
不过,就轻罪的范围界分、罪名以及分级标准等问题,美国不同州会有相异的规定,“一年以下监禁”并非轻罪与重罪之间唯一的区分标准,部分州刑法规定的轻罪并不受一年监禁等刑期的限制。各州对轻罪的分级也并非完全一致,〔17〕如内华达和田纳西州刑法典中轻罪的法定刑均低于一年,科罗拉多州的轻罪最高会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在艾奥瓦州和佛蒙特州,轻罪最高刑为两年,而在宾夕法尼亚州,轻罪的监禁刑甚至长达五年。并且虽然大多数州(除了五个州)对轻罪内部进行了分级,但也存在一到七种不同的等级。密歇根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等对轻罪并未进行细致的分级,如密歇根州仅就轻罪规定了不超过一年的刑期和不超过1000 美元的罚款。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马里兰州的刑法典却和我国一样,既没有轻罪、重罪的区分,也没有罪名的分级,仅就具体个罪设定了不同的刑期。同样的行为在不同州的刑法典里可能被分别划分为重罪、轻罪或违警行为。〔18〕See Ariz.Rev.Stat.Ann.§13-3405(2019);Ky.Rev.Stat.Ann§218A.1422(West 2019);Md.Code Ann.,Crim.Law§5-601.1(West 2019);Tex.Code Crim Proc.Ann.§14.06(West 2019)。以上案例显示,美国不同州对持有大麻行为规定了差异化的处罚方式,分别包括六级重罪、B 级轻罪、不作为犯罪处理等。轻罪在不同辖区内的规范表现和司法适用差异,由美国的立法体制使然,是各州刑法结构上的不同。对此,国外学者也曾指出,轻罪具有不同的州际特征,可以在本州内实现不同的功能,满足自身的社会治理需要。〔19〕See Alexandra Natapoff,Misdemeanors,The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11,p.267.2015.只是虽然各州的轻罪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与重罪相比,轻罪基本为各州最为轻微的犯罪行为,且案件数量巨大,在处理程序和轻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共性特征。就行为人而言,轻罪的核心逻辑在于行为规训、矫正和复归;就国家而言,轻罪的关键功能在于节省诉讼资源,并进行风险防控,轻罪在美国刑事司法中与重罪具有完全不同的体系性位置和角色分工。
二、美国轻罪的制度性分工
在美国历史中,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诉讼理念,轻罪案件一直采取与重罪不同的处理模式,在诉讼程序设置与当事人权利保障上均存在差异。从普通法时代开始,轻罪被告人就基本被剥夺了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只有重罪才可能获得更为全面的诉讼权利,并得到其他诉讼主体的足够重视。随着美国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破窗理论”的应用、“零容忍”的刑事政策的出台以及拦截盘查(“stop and frisk”)的广泛推行导致轻罪案件数量急剧攀升,更是进一步激发了轻罪制度的繁简分流机能。与重罪制度不同,诉讼程序的简化与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社会化是轻罪制度的主要特征,轻罪制度修正了传统的对抗性刑事司法程序,在罪责承担上吸收了刑事实证学派的思想,以行为规训和节省司法资源为主要特征,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的风险预防和社会的犯罪控制功能。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国整体犯罪率提升的背景下,轻罪的动态增长趋势也较为明显。据统计,1972 年美国全国轻罪数量为五百万件,到了2006 年则增加为一千万件以上。〔20〕Robert C.Boruchowitz,Malia N.Brink &Maureen Dimino,Minor Crimes,Massive Waste:The Terrible Toll of America’s Broken Misdemeanor Court,https://www.nacdl.org/getattachment/20b7a219-b631-48b7-b34a-2d1cb758bdb4/minor-crimes-massive-waste-theterrible-toll-of-america-s-broken-misdemeanor-courts.pdf,2021 年8 月18 日访问。尤其在进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以“破窗理论”作为理论依据的“零容忍”政策主张打击轻罪有助于实现对暴力犯罪的预防,在此政策影响下,轻罪案件数量激增。如1993 年在纽约市推行的“提高生活质量政策”以打击公共场合醉酒、游荡、乞讨等秩序违反行为为主要目标,直接引发了九十年代纽约市轻罪犯罪率的攀升,从1993 年至2000 年,轻罪数量增长了75%,其中包括毒品相关行为以及街头犯罪行为等。在重罪案件和暴力犯罪的数量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的同时,轻罪庞大的案件数量给司法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促使轻罪制度更为注重追求诉讼效率,缩减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减少对司法资源的占用,与重罪在制度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愈加明显。
简化的协商性诉讼程序与限缩的程序性权利是轻罪诉讼程序的核心特征。随着辩诉交易在20世纪七十年代被合法化,据统计,目前在美国,95%的轻罪案件均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在治安法官组织的第一次听证会中解决。〔21〕See Alexandra Natapoff,Misdemeanors,The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11,p.259.2015.如果被告决定认罪,就意味着放弃了庭审权和沉默权,会被处以监禁、罚款或者法庭规定的其他处罚性项目,案件就此宣告结束。辩诉交易是协商性程序正义理念的直接体现,〔22〕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1 期。与轻罪更具契合性。无论对司法系统还是对被裁判者而言,诉讼效率都是重要的价值追求。如果被告拒绝进行辩诉交易,案件将在后续进入庭审阶段,轻罪的庭审流程通常也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由法官最终决定被告的罪名和刑罚。不过即使选择正式的庭审程序,审理过程也非常迅速,甚至几分钟即可解决。并且,与轻罪的处罚速度和方式对应,轻罪被告人较重罪让渡了更多程序性权利,除了超过六个月的刑期才有权获得陪审团的审判,美国还通过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方式,进一步限缩轻罪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认为,在仅会被判处罚款而非自由刑的轻罪案件中,若无律师辩护并不违宪。只有在被判处自由刑或缓刑的情况下,律师的辩护权才是必需的。〔23〕Scott v.Illinois,440 U.S.367(1979);Alabama v.Shelton,535 U.S.654(2002).另外,按照法官的自由裁量,轻罪案件在得到被告同意的情况下还可以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重罪中的缺席审判则被禁止。“作为刑事诉讼两大基本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发展史,诸多制度的设计都涉及两大价值之间的平衡。”〔24〕杨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法考察——以适用范围与权利保障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7 期。在轻罪制度中,对程序性参与权的保护明显让位于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
除了程序的简化,轻罪也通过行刑社会化缓解了美国大规模监禁所造成的监狱资源紧张。轻罪的刑罚一般包括不超过一年的监禁、缓刑及非监禁刑如罚金或社区服务等,非监禁刑是轻罪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真正执行监禁刑的犯罪人其实非常少见,〔25〕See Alexandra Natapoff,Misdemeanors,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85,p.101-162.2012.处罚多通过罚金、戒毒治疗、社区服务、家庭参与、针对性咨询、工作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在美国,矫正模式自20 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兴起,到七十年代左右在刑事处罚体系中占据了垄断地位,直到七十年代末,在“矫正无效论”的影响下,矫正模式才慢慢趋于衰落。〔26〕See David Garland,The Culture of Control: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st edition,2002.195.矫正模式倡导复原型的国家干预,而非报应性的刑事惩罚;主张国家应为犯罪人提供个体化的矫正措施,而非统一化的监禁。矫正模式以刑事实证学派的主张为理论基础,同时受到美国20 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认为专业治疗、社会变革和公共福利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核心。
但是,矫正模式与重罪的不兼容问题逐渐凸显。20 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为了解决犯罪控制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对重罪采取了以威慑和隔离为主导的刑事政策,重建“法律与秩序”;对轻罪则继续采取缓刑、假释等转处措施和非刑罚处罚方法,形成了分类分级的“两极化”犯罪处理模式。对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施行重刑化的治理措施,重新强化监禁刑的地位以进行威慑和隔离。对于轻罪,则多延续使用监禁刑的替代处罚方式,通过罚款、缓刑、社区矫正和技能培训等方式缓解监狱系统压力,消减重罪所导致的大规模监禁的负面影响。“轻罪是对人群的分类(sorting)、检查(testing)和管理(regulating),而不是长期的隔离和绝对的控制。”〔27〕Issa Kohler-Hausmann,Misdemeanor Justice:Control without Convi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9(2),p.357.2015.只是与刑罚福利主义时代不同,在巨大的案件压力下,此时的轻罪刑罚虽也践行了“非监禁化、刑罚社会化”这一刑罚改革理念,但重心已不在于为罪犯提供福利之上,〔28〕葛磊:《当代美国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及其借鉴》,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1 期。而在于通过刑事司法系统与社区的关联对风险进行辨别与控制,对可矫正性较强的犯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社会复归,实现行为规训。一旦发现难以通过包容性的轻缓化措施有效防止其再犯风险,则会考虑采取其他排斥性的、重罪化的犯罪策略。
因此,美国的轻罪制度发源于普通法中的轻罪,普通法对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为当前的双轨运行模式奠定了基础。当前美国轻罪制度的建构以秩序违反行为为规制对象,以提高诉讼效率为价值导向,以协商性的简化程序为路径,通过社会化的多元处遇实现对犯罪人的规训。重罪制度则继续坚持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的传统路径,重罪广泛适用监禁刑,通过惩罚、监禁和前科制度对重罪人群进行更为严密的控制,这不仅是报应主义的要求,也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刑罚民粹主义的回应。轻罪与重罪双轨运行模式构成了犯罪控制的不同路径,形成了美国刑事法体系的当代图景。
不过在美国,轻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重罪发展和演变的影响,甚至成为重罪政策的附属。轻罪制度虽具有自身的制度特征和品格,如相比重罪犯人,刑罚对轻罪人的行为规训作用更为显著,适当程度的惩罚就可以对轻罪犯罪人起到震慑作用,导致轻罪不以威慑和隔离作为主要的功能性目的,但近年来轻罪范围的扩大化和程序的不断简化多是出于预防重罪发生和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功利性需要,如轻罪近年来在数量上的增加就是重罪预防政策所带来的附加产物。重罪一直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关注的核心,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战争是政府维系基本的“法律与秩序”并赢得选票的关键,英美学界的关注也集中于大规模监禁、反恐战争以及种族歧视等重罪政策所引发的负面影响,致使轻罪长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与此同时,轻罪制度已经产生了犯罪门槛过低、法律适用随意性较强、以及罪刑不均衡等各种问题,影响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导致轻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自由剥夺与限制并不低于重罪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美国轻罪制度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国轻罪制度是对强调诉讼参与、平等对抗和以监禁刑为主导的传统诉讼程序的修正,辩诉交易成功分流大量轻罪案件,非监禁、社会化的处罚方式也极大缓解了监狱压力,但是近年来,美国轻罪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正逐步显现,轻罪制度对传统程序的修正增加了其背离古典主义刑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在正当性上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预防性立法招致危害性原则的崩溃,精简的诉讼程序由于控辩力量失衡而动摇了程序正义的根基,附随性后果的无差别适用在实质上出现了对罪刑均衡原则的悖反。
(一)危害性原则的崩溃
危害性原则是普通法系国家为刑法立法提供正当化根据的原则,是划定犯罪圈的关键标准。危害性原则起源于密尔的《论自由》:“阻止社会成员伤害他人是国家合法使用暴力的唯一目的。”〔29〕参见密尔:《论自由》,陈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165 页。密尔认为危害是对他人利益的侵犯,行为危害他人,不仅是国家强制干预个人自由的唯一缘由,也是个人享有自由的道德底线。〔30〕参见姜敏:《“危害原则”的法哲学意义及对中国刑法犯罪化趋势的警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1 期。基于保护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化,需要防止牺牲个人的实质利益,如自主权、人格自由和尊严。“危害性原则是犯罪论的前提与基础,它一直被用来诠释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作为批判法律道德主义的工具存在。”〔31〕See Bernard E.Harcourt,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vol.90,p.119. 1999.但是,美国对“无序社会”的“零容忍”政策以及“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构成模式引发了轻罪的泛化,加剧了危害性原则在现实中的崩溃。
20 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在刑罚民粹主义的影响下,降低犯罪率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目标,犯罪学理论也在主张降低犯罪门槛会对社会治安状况产生积极影响,倡导对乞讨、游荡、公共醉酒等失序性行为进行犯罪化,导致刑法中危害性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诸多欠缺危害性的行为被纳入犯罪,于公共场合饮酒、乞讨、无证驾驶、网络暴力、持有赃物等道德违反行为或行政违法行为均可能被作为轻罪处理。“对于几乎所有的道德性过错行为,人们都已先默认危害存在,且并非微不足道。”〔32〕See Bernard E.Harcourt,Illusion of Order:The False Promise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14.危害性原则的批判机能逐渐弱化,表现为古典自由主义危害定义的维度逐渐丧失。〔33〕参见王耀忠:《现代风险社会中危害性原则的角色定位》,载《现代法学》2012 年第3 期。近年来,为了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所谓的危险犯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轻罪的数量进一步膨胀,“危害的抽象化与普适化,使得危害性原则在持续性扩张中消解并摧毁了它自身。”〔34〕王钧、冀莹:《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与安全刑法的兴起——兼评伯纳德·哈考特与劳东燕的“崩溃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年第9 期。部分轻罪如“缺乏不法目的的游荡行为”在客观上并无法益侵害,同样会触发刑罚以及其他刑罚附加的不良影响,对法益的客观威胁是相当有限且遥远的,所谓的公共安宁等集体法益的判断标准主观又模糊,与危害性原则的设立初衷相悖。
国外也有学者将轻罪定义为“半刑罚”、“管理型犯罪”,甚至是“无犯罪行为的处罚”。〔35〕Alexandra Natapoff,Criminal Misdemeanor Theory and Practice,in Markus Dubber &Tatjana Hörnle eds.,Oxford Handbook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但美国的轻罪与我国语境下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性质并不相同,轻罪在客观行为上与重罪的认定标准一致,罪责上也以罪过作为必备要件,不法与罪责均并未突破犯罪的基本框架。并且,美国模范刑法典以及部分州的刑法典明确将犯罪区分为重罪与轻罪,还在轻罪之下规定了违警罪(violation)作为犯罪之外的一般违法行为,这显然与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类似,采取了违警罪与刑法单立的立法模式,将违警罪纳入警察行政处罚的范畴。〔36〕卢建平:《法国违警罪制度对我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3 期。而轻罪则仍属于“罪分二类”中的一类,被视为刑事犯罪,仍受到危害性原则的制约。
除此之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中“司法定量”在限缩案件数量上的不力也是轻罪门槛过低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采取了“宽进严出”的“漏斗型”出罪机制,只需满足特定的行为类型就成立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无需考虑定量要素的入罪功能问题,轻罪的出罪主要诉诸于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依赖程序化的司法出罪路径来划定犯罪圈。一般说来,警方将轻罪案件移送之后,检察官不仅要对案件证据是否满足“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要求进行评估,也需结合司法资源是否足够、以及起诉是否符合公共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37〕Ronald Wright &Marc Miller,The Screening/Bargaining Trade off,Stanford Law Review,vol.55,p.29.2002.只是当面对数量巨大的轻罪案件时,检察官的决定很容易过分依赖于警察的逮捕行为,导致轻罪被驳回起诉的比例远低于重罪案件。〔38〕Issa Kohler-Hausmann,Misdemeanor Justice:Control without Convi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9(2),p.358.2015.检察官所起的出罪作用有限,无法起到有效的过滤功能,导致轻罪案件数量过于庞大。
面对轻罪门槛过低所导致的正当性危机以及案件数量过大的问题,美国目前的改革策略仍然是沿用“立法定性”对重罪与轻罪的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对轻罪的范围进行限缩,对危害性原则中的危害内涵进行明确化。第一,降低不同等级轻罪的刑期,或直接对部分轻罪如非法持有大麻等行为做无罪化处理。如马塞诸萨州已将轻微的扰乱治安行为、无证驾驶、未购买车辆保险驾驶的首次犯罪行为非犯罪化。〔39〕Joel M.Schumm,National Indigent Defense Reform:The Solution Is Multifaceted,American Bar Association,2012,p.9.通过在立法中直接提高入罪门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轻罪数量过多的问题,减轻轻罪给公众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通过在制定法中增加不法目的等主观要素的方法,仅保留对利益真正具有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将纯粹的秩序违反行为逐出犯罪圈。如援引古典意义的危害性原则对罪名进行检验,仅将“为实施不法行为而进行的闲逛”或“为实施恐怖活动而进行的持有”等行为纳入轻罪范围,对公共或他人利益并无实质性危险的行为则不构成犯罪。以上做法均是重新恢复危害性原则的批判性功能,通过限定“危害性概念”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扩张,尝试“走出危害性原则崩溃后的困境”〔40〕劳东燕:《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载《中外法学》2008 年第3 期。。除此之外,在历史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多次通过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原则,以法律本身欠缺明确性且容易导致司法肆意为由,推翻明显欠缺危害性的轻罪立法,防止因过分追求集体法益威胁到公民的自由空间。如1972 年Papachristou v.City of Jacksonville 案、1974 年Smith v.Goguen 案以及1999 年Chicago v.Morales 案等,〔41〕Papachristou v.City of Jacksonville,405 U.S.156(1972);Smith v.Goguen,415 U.S.566(1974);Chicago v.Morales,527 U.S.41(1999).联邦最高法院均通过宪法审查的方式宣布相关的轻罪法无效,捍卫危害性原则的精神内核。
(二)轻罪程序的异化
协商性程序正义的目的在于追求司法的效率性和灵活性,其正当化基础在于保障程序的自愿性、可协商性、可获益性,但现实中轻罪程序存在忽视真相的制度性弊端,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明知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辩诉交易极易助长检察官的职责懈怠与权力滥用,甚至引发检察官的报复性起诉,侵害被告合法权益。”〔42〕郭华、高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风险及程序控制》,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1 期。“很多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在受到胁迫、信息不对称、缺乏正确评估交易中风险的能力和判断力的情况下作出的。”〔43〕郭华、高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风险及程序控制》,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1 期。再加上证据标准也无限降低,增加了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导致出现了正当化危机。
在检察官决定起诉后,真正进入庭审程序的轻罪案件数量非常少,案件主要通过辩诉交易方式快速解决。可是在轻罪中,辩诉交易存在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通常只有在重罪案件、联邦最高法院管辖的案件、以及代理律师较为审慎负责的情况下,刑事程序的进行和证据的采纳才较为规范。轻罪罪责轻微且案件数量更为巨大,无法像重罪一样获得司法程序的足够关注和权利保障,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容易造成对正当程序的反噬,在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有些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在受到胁迫、信息不对称、缺乏正确评估交易中风险的能力和判断力的情况下作出的”,甚至促成冤假错案。〔44〕[美]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无罪之罚:美国司法的不公正》,郭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 页。
并且,轻罪人一般很难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对案件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在存在律师协助的情况下,律师通常也没有足够时间为轻罪案件做充分的准备,导致有些案件从始至终缺乏律师的有效参与。〔45〕Shima Baughman,The History of Misdemeanor Bail,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8,p.841.2018.当诉讼效率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辩诉交易更是几乎消灭了检察机关和法院详细审核现有证据的可能性。法官在庭审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在辩诉交易中,法官较少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细致审核,仅对量刑建议进行简单审查和确认。“即使是刑法专家也不能对潜在的犯罪人命运作出精确的预测,这些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法律手上,真正的刑法,是由警察和检察官掌握的”。〔46〕Dougas Husak,Overcriminalization: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检察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异化为审判权,违反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立法原理。即使轻罪被告人不选择辩诉交易而是选择庭审方式,轻罪案件的庭审通常非常迅速,也容易演变成形式化的走过场,被告的知情权、参与权都受到减损,程序的正义性受到严重挑战。
轻罪早在普通法中就被区别对待,轻罪诉讼制度尤其体现出对于诉讼效率的特殊偏好。尤其是在美国辩诉交易盛行的背景下,诉讼程序以诉讼主体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根基,〔47〕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1 期。当事人通过有限度、自主性的放弃部分诉讼权利来换取诉讼程序的简化和量刑上的宽待。而轻罪长期作为重罪制度的附属存在,罪量众多却易被忽视,逐渐演变为压制性的效率化诉讼机制,凸显出协商式诉讼程序的深层争议。美国轻罪程序在诉讼权利保障上存在严重不足,导致被告人处分权的实质性缺失是轻罪制度出现异化的根本原因。对诉讼权利的部分放弃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丧失,欧洲人权法院在2007 年审理O’Halloran and Francis v.The United Kingdom 案时,持反对意见的帕夫洛夫斯基(Pavlovschi)法官曾明确主张,“如果某类案件的数量实在太多,以致于国家几乎不可能在所有同类案件中都完全贯彻基本的程序保障,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此类行为非罪化。”〔48〕See O’Halloran and Francis v.The United Kingdom,[GC],Appl Nos 15809/02 and 25624/02(ECtHR,29 June 2007).美国学者也是在近些年才开始重视并呼吁轻罪中的程序正义问题,〔49〕See Eisha Jain,Proportionality and Other Misdemeanor Myth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8,p.953-954.2018.如有学者主张提高起诉阶段和辩诉交易阶段轻罪的证据审核标准,增加律师数量以保障被告的被帮助权,〔50〕Alexandra Natapoff,Misdemeanors,The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2015,vol.11,p.259.以此来减轻轻罪问题给美国刑事司法体系造成的负面效应。但目前尚未出台新措施去抑制检察机关在轻罪中的自由裁量权,或保障被告的被帮助权。虽然检察官办公室设立了监督部门,相关的“洗冤计划”却很少会考虑轻罪,而是放任轻罪作为社会控制和风险预防的手段,检察机关在轻罪处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未受到明显抑制。
(三)比例原则的悖反
“美国刑法早在德国法上比例原则概念于全球流行之前,就有本土的‘刑罚合比例性’的讨论。”〔51〕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比例原则在美国具有宪法位阶,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不应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应强科过分之罚款,不应滥施残酷和不寻常之刑罚。”其中,“残酷的”指刑罚具有残酷性,应避免不必要的痛苦;〔52〕[美]富兰克林·齐姆林:《美国死刑悖论》,高维检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17 页。“不寻常的”则强调相当性,要求罪当其罚,比例严重失衡会导致违宪的法律后果。判例法中,比例原则被用来判断死刑和累犯等极端案件的合宪性,从未适用于轻罪案件之中。在轻罪中,非监禁刑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非监禁刑天然具有自主性、个案性和反规范性,较难像重罪一样进行对比分析,但是在轻罪的罪刑适用中同样存在明显的比例失衡现象。
首先,虽然轻罪制度已经在试图减轻刑罚的惩罚性,可由于再犯危险性难以评估,犯罪人人格不确定,加上矫正机构资质不一,矫正人承担的现实负担反而会比监禁刑更重。美国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导致矫正模式趋于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矫正机构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多元化刑罚所带来的刑罚不确定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促成了“正当程序”原则的回归和量刑委员会的设立。至今,轻罪多元化处理结果在形式上的轻微性和实质上的严重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仍被学者诟病。这在本质上源于矫正模式存在的固有内生性问题:个性化的刑罚难以保证确定、统一的处理措施。与相对确定的监禁刑相比,非监禁性的惩罚性项目如戒酒措施、精神治疗、社区参与和工作技能培训等可能会给犯罪人带来更多且不确定的痛苦和负担,实际上间接扩大了国家惩罚机制(penal apparatus)的范围。〔53〕Eric Miller,Embracing Addiction:Drug Courts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ism,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65(6),p.1574.2004.多元化的处遇方式对犯罪人生活的侵入可能会更为严重,国家机器对公民权利的影响范围也会进一步拓展。
其次,与重罪相同,轻罪也会产生一系列附随性后果,影响犯罪人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职业选择,如被吊销执照或许可证、被剥夺(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公共住房、丧失退休金等福利资格、丧失工作机会或被驱逐出境等。〔54〕Eisha Jain,Arrests as Regulation,Stanford Law Review,vol.67,p.826-44.2015;Jenny Roberts,Ignorance Is Effectively Bliss:Collateral Consequences,Silence,and Misinformation in the Guilty-Plea Process,Iowa Law Review,vol.95,p.182-83.2009.在美国,犯罪的附随性后果被零散规定在《美国法典》及各州法典中,据2021 年1 月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联邦和州层面规定的附随性后果总数多达四万多种,其中有的和个罪关系紧密,如针对性犯罪人的注册制度,但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附随性后果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和犯罪性质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55〕Chidi Umez &Joshua Gaines,After the Sentence,More Consequences:A National Report of Barriers to Work,New York: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Justice Center,https://csgjusticecenter.org/publications/after-the-sentence-more-consequences/national-report/,2021年8 月3 日访问。附随性后果不属于正式刑罚的一部分,检察官和法官在辩诉交易阶段不会专门考虑,但对犯罪人的影响却广泛又深远,尤其是其“社会排斥”功能将如影随形,〔56〕参见姚建龙:《社会变迁中的刑法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09 页。轻罪也不会自动排除附随性后果的适用,容易出现罪行较轻但实际惩罚过重的结果。
轻罪中的“刑”并不局限于刑罚本身,轻罪的失衡是系统性、实质性的,是在制度参与者的长期忽视下,行为轻微却仍需承受程序、刑罚和附随性后果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失衡,是由轻罪门槛过低与附随性结果影响过大等因素共同导致的。在危害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均遭受冲击的背景下,轻罪行为单纯的失序性并不能和由此所产生的实体与程序性法律后果完全对应,在现实中构成对比例原则的悖反。美国现有的规范性框架也无法为轻罪失衡提供有效约束,虽然宪法第八修正案在理论上适用于联邦和州的所有罪行,可“残酷的且不寻常”标准多用来判断死刑和累犯等极端案件的合宪性,从刑罚的严厉性来看,轻罪的监禁刑通常为一年以下,宪法审查很少适用于轻罪。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法发展出来的检测方法也只是对刑罚本身的审查,轻罪中非监禁刑是刑事责任主要的实现方式,较难像重罪一样对刑罚轻重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
不过,虽然对于社会化的刑罚方式难以进行该当性的评价与制约,美国司法机关已经开始重视附随性后果给轻罪犯罪人带来的负面作用。2012 年以来,根据《2007 年法庭安全完善法案》(Court Securi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7)的规定,美国律师协会专门建立了犯罪附随性后果目录数据库,用以协助司法机关明确评估对个罪施加的所有惩罚性后果。〔57〕National Inventory of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onviction,About NICCC,https://niccc.nationalreentryresourcecenter.org/node/127,2021 年8 月3 日访问。这是合法性原则的要求,也是实现比例原则的前提条件。2018 年《美国量刑指南》第八章第C2.8 条也规定,如果犯罪人将被判处一定的附随性后果,则应在量刑指南规定的幅度内降低罚金数额。〔58〕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Guidelines Manual 2018,Chapter 8,C2.8.在辩诉交易中,部分检察官在决定正式刑罚时,开始考量轻罪附随性后果的影响,会因为附随性后果较重而选择较轻的刑罚,甚至降低罪名指控的等级,充分体现出司法的实用主义特征。
另外,为了削弱前科制度对轻罪人就业的过度影响,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删除和封存制度之外,美国部分辖区对轻罪如交通类犯罪和大麻类犯罪的犯罪记录也予以封存或删除。如2009-2014年间,至少有三十一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在扩大删除和封存记录的适用范围,甚至开始实施“既往不咎法”(Clean Slate Law)以淡化犯罪标签、消除犯罪记录对轻罪的影响。〔59〕Kenny.Lo,Expunging and Sealing Criminal Records,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criminal-justice/reports/2020/04/15/483264/expunging-clearing-criminal-records/,2021 年11 月21 日访问。只是在美国,犯罪人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监控、犯罪控制需要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冲突,相比欧洲,美国对罪犯的前科消灭制度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尤其是对重罪犯罪如针对儿童的性犯罪的犯罪记录,美国还采取了强制公开制度以更好的保护公共利益,公众可以对犯罪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查询。这一保守态度也减少了轻罪犯罪记录“被遗忘”的可能。不过,即便如此,如密歇根州等州的既往不咎法也已经生效,对轻罪和部分重罪设置了自动犯罪记录删除期限,方便犯罪人更快复归社会。
四、结 语
普通法系国家素有轻罪制度的肇始国之称,〔60〕Sandra G.Mayson &Megan T.Stevenson,Misdemeanor by the Numbers,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61(3),p.979.2020.经历了20 世纪末的政策转型,美国形成了“轻罪-重罪”双轨运行机制,以满足现代社会愈加复杂的治理需要。作为犯罪行为的重要分类标准之一,轻罪具有特定的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轻罪制度以秩序违反行为作为主要对象,以提高诉讼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追求,通过协商性的快速审理机制和多元化的社会化惩罚方式实现对公众的行为规训与社会的风险预防。轻罪在坚持刑罚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节省了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却也忽视了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多重正当性挑战。刑法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仍应建立在维系古典主义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虽然政府出台相关改革措施,效果仍然不够显著。美国的司法体制与刑法结构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其制度设置和缺陷仍然可给我国以启示。
中国的犯罪治理需要,决定着刑法的发展方向。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轻罪化的刑事立法和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司法已然成为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重要面向。随着预防逐渐成为与惩罚并存的犯罪化事由,危险犯的数量与范围不断扩张,轻罪成为社会防卫的手段,轻罪的数量也将随着刑事立法能动主义而大幅增加,截至2020 年10 月,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已从54.4%上升至83.2%。〔61〕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0/ca9ab36773f 24f64917f75933b49296b.shtml,2021 年7 月29 日访问。判处非监禁刑(含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比例从20%增至30%,与之相反,重罪被告人的数量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62〕段陆平:《健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实践背景与理论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2 期。轻罪与重罪具有不同的立法保护目的,二者之间存在功能分野。轻罪行为相对较轻的可谴责性、行为人的易预防性、罪责的轻微性以及案件数量的巨大性决定了轻罪制度以行为规训和诉讼效率为首要价值追求,轻罪是对公民规范信赖与规范意识的强调,而非强化刑罚的威慑与隔离功能,因此迫切需要改变传统以重罪为主的刑事制裁体系,对重罪、轻罪乃至微罪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区别对待,这也与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一脉相承,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在我国,轻罪的扩张是刑法积极参加社会治理的体现,为解决实务难题、消减司法困惑,防止重罪被滥用,轻罪的增设具有一定合理性。〔63〕参见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6 期。面对新型社会问题,我国刑法仍需适度扩张。当前,美国以及英国就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犯、帮助犯等也在进行积极的犯罪化,各国刑法都体现出功能主义的发展趋势,密切回应刑事政策的安全性要求。只是美国轻罪泛化的弊端显示,犯罪门槛的过分降低会给轻微犯罪行为带来过度负担,从而引发正当化危机。美国对“无序社会”的“零容忍”政策是引发轻罪泛化的重要原因,导致宪法也难以为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轻微犯罪行为提供有效保障。在我国,轻罪的入罪仍应坚持法益的批判功能,避免法益保护原则过分抽象化、精神化、普世化。法益保护原则与普通法系的危害性原则类似,本意是对刑法立法起到限缩作用,只是近些年来分别受到我国集体法益扩张和普通法系国家危害性原则崩溃的影响,在轻罪的立法批判功能上愈发有限,犯罪的危害越来越难以凭经验、感觉加以认知,目前新增的轻罪多是为了保护集体法益创设的危险犯。与侧重保护管理秩序的行政法不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质”上不应被泛化为各种抽象的秩序,而应与个人法益保持相对明确的关系。如果违法行为仅仅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并未对个人的自由发展造成实质威胁和危害,则不应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因此,在轻罪立法中可增加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要求危险犯的成立需对法益造成实质的紧迫且现实的危险,或增加“情节严重”等条款,提高轻罪的入罪门槛,适当容忍“无序”状态,避免轻罪范围泛化。在司法中,也应鼓励法官在法律解释时进行目的性限缩,通过法教义学的解释方法、结合法规范保护目的对欠缺目的性或实质危险性的轻罪行为作出罪化处理。
在坚持法益的批判功能、对轻罪进行必要的有限度扩张的同时,还应加快全面的配套制度跟进,防止出现与美国轻罪体系相类似的困境。首先,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处分权,增强控辩合意。美国刑事程序存在忽视真相的结构性弊端,在辩诉交易制度内在强迫性的压力之下,传统刑事程序的权利保障和查明真相能力大幅减损,轻罪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明知性无法保障,构成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悖反。在我国已经全面铺开认罪认罚制度的背景下,虽然诉讼效率是认罪认罚程序重要的价值追求,追求程序的效率性仍需以保障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判决结果的正当性为底线,应通过坚持认罪与不认罪案件标准的统一化,以及落实值班律师制度等方式,防止过分减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避免造成美国式的程序异化。其次,在轻罪罪刑均衡的本土性制度构建上,是否存在犯罪记录是引发附随性后果的前提,而附随性后果会对犯罪人及其后代进行从业禁止和其他资格限制。附随性后果承载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在维护公共安全、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贯彻审判公开原则上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轻罪的附随性后果与重罪并无不同,不仅与轻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并不相当,给轻罪犯罪人带来的生活、工作上的负担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报应刑的框架。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刑法修正案八》也增设了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条款,但是在适用范围上仅限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目前可能的改革路径之一是以特殊预防的需要为限,构建类别化的前科消灭制度,如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且之前并无犯罪记录的轻罪犯罪人,在经过一定考验期后确立全面的前科消灭模式,全面消除附随性后果的不当影响。或者对我国所有的附随性后果进行细化、规范和整合,由检察官在量刑建议中、以及法官在审判阶段一起综合考量,结合案情和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对附随性后果进行公开的选择性适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惩罚性后果的公开性、透明性,更能促进实质意义上罪刑均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