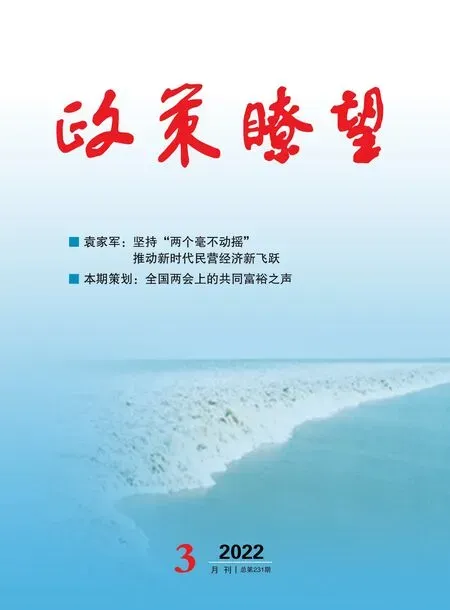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2023-01-08王祖强
王祖强
共同富裕美好社会是社会结构更优化、体制机制更完善的社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统计标准,中等收入为成年人年均收入3650美元至365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4万元至24.45万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内部测算标准,中等收入群体为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2020年我国达到该收入的家庭数量为1.4亿万户,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口,占总人口30%。《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近年来,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社会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民生发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日益凸显。
一、浙江具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良好基础
浙江正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率先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序列,这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持续扩大,“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步形成。2021年浙江人均GDP达到11.3万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3.8%,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75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21年新标准,人均GDP在1.2695万美元之上属于高收入国家,由此判断,浙江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序列。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社会橄榄型结构正在形成。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1年和第37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2021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万元,其中城镇居民6.85万元、农村居民3.52万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浙江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高于中等收入的最低临界值。按照七普人口资料,我省家庭户均人口数为2.35,户均可支配收入约13.5万元,也超过了家庭收入10万元的最低临界值。
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趋向高级化、多元化、数字化。2021年全省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666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2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19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5415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9倍和1.60倍。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0.278。2021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53.3辆;计算机62.5台,其中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58.3台;移动电话253.6部,其中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电话222.0部;彩色电视机175.0台、电冰箱111.7台、洗衣机97.8台、空调217.9台、热水器106.7台。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结构呈现高级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可穿戴智能设备、照相器材、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92.4%、41.9%、27.2%、22.6%和19.5%。线上消费持续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5.9%。
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城乡发展趋势从二元结构转向一元融合。2021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4,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得益于社会保障事业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速增效。2001年,浙江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浙江率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率先实现基本养老金制度全覆盖和人员全覆盖;2018年,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实现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2021年末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42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5655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1793.5万人、2741.6万人和1811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180元/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月人均提高105元。
二、浙江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难点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现代化企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等。我省高质量就业岗位不足、收入渠道来源单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仍较突出,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等风险挑战依然存在。
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占比偏高,就业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水平不高限制我省中等收入群体扩大。2020年,浙江省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这三大产业,分别达到就业总人口的35%、15%和11%。这三类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都属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动报酬相对较低。2020年,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的平均收入水平仅为61990元、59803元、58135元,低于全省所有行业71523元的平均水平,远低于金融业147964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48439元、卫生和社会工作139630元的水平,而这三类高收入行业的就业人数不足总人口的5%。
收入来源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收入分配中个人所占比重偏低。2014—2020年,我省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都在57%以上,财产性收入占比处于较低位置,仅为10%左右。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占比有下降趋势,而财产性收入占比上升了将近1个百分点,间接说明了我省居民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态势,收入来源渠道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按照2020年数据测算,浙江居民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7.5%,虽然高于全国44.5%的平均水平,但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65%的水平,收入分配格局需要继续优化。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尤其是财产性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浙江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户籍人口约占3/4,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约占1/4,城市居民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在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远远低于城镇居民。202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为1951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55.2%;财产性收入为949元,仅为城镇居民的10.85%,其中差距最大的为出租房屋净收入,城镇居民为2591元,而农村居民仅为421元。我省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充分关注农村居民这个群体,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拓宽收入来源,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
三、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举措
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目标之一,是要培育一个庞大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力争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群体比例提高到80%以上,20万元至60万元群体比例提高到45%以上,基本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因此,要深入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深入研究推动“扩中”“提低”问题。“扩中”群体包括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与小微创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提低”群体包括低收入农户、困难群体等。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企业成长、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举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例如,新加坡大力发展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挪威将家庭收入分为14个等级,对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精准设计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宜采取以下举措:
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技术工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技术工人队伍。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强化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大力培育和超前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速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推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产业链龙头企业核心环节能级,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化、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软件与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服务业竞争力。
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形成合理有序收入格局,建立相对公平分配制度。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改善营商环境,减轻税费负担,提供更多市场化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稳定经营、持续增收。以科创板、创业板为契机,培育上市企业,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空间与渠道。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与获得感。进一步破除市场中的壁垒,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并予以相应政策优惠;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益就业岗位、社区就业岗位。探索加快税收结构变革,深化分项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办法,探索建立根据家庭负担情况相应豁免费用的制度,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
深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集成改革,有效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渠道。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安心进城,稳定就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最大潜力在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努力增加财产性收入是提升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比重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行“人地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广绍兴农村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交易)系统、宁波象山乡村产业信息对接平台等改革经验,厘清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之间的关系,探索完善宅基地分配、流转、抵押、退出、使用、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的方法路径,重点结合发展乡村旅游、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等,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各项社会保障项目的保障标准,加快推进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统筹,适当增加公共支出规模,缓解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重视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内的积极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和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教育、技工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育训兼融,优化教育资源布局配置和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