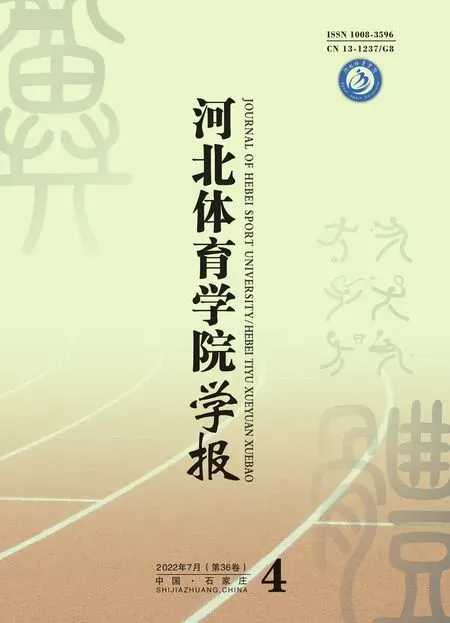当代武术“头人”的生产机制与运行逻辑
——一个民间武术门派掌门人现象的考察
2023-01-06侯胜川
侯胜川
(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郑州 450044)
2005年5月18日,在福州市地方拳种香店拳第五代宗师房利贵去世24年后,在其家乡登云上山村召开了规模空前的100名弟子大会[1],商讨门派的未来发展事宜,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选举出本门派的掌门人。基于民间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香店拳的师兄弟们明白必须推选出门派意义上的“头人”,形成新的权威,以继承师父的技艺和凝聚集体意识。武术社会中如何确立下代掌门人,新任掌门人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进而保障门派秩序的正常运行?作为省级非遗拳种,香店拳掌门人选举事件和常见的武术社会中的“头人”传承存在哪些区别,其现实意义又是什么?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武术发展事件,折射的是当代我国民间武术发展的文化自觉,掌门人选举不失为一种突破的路径。
1 武术社会中常见的掌门人传承机制
在武术社会中,作为民间武术门派权威,“掌门人”一词颇具玩味。一方面,人们迫切需要构建一种专用术语来描述现实中的武林,并且极力建构出传统宗法结构中的家族社会来管理门户[2]、门派等类似共同体的日常运作;另一方面,武术门派又需要特定的“头人”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中介,来促进各自之间的联系。从武术历史脉络来看,门派的“头人”权威构建问题基本经历了三种模式:儿子的血缘继承、弟子的德才继承、综合因素考量。
1.1 血缘传承
以杨式太极拳为例,第一代宗师杨露禅传艺凌山、全佑、万春及自己的儿子(长子早亡,次子班侯,三子建侯),从技艺上看,凌山、全佑、万春三人在武林中分别有得其“筋、骨、皮”之美誉,但是,为了确保第二代掌门人的“儿子中心”[3]地位,“杨露禅不仅让三人拜其子班侯为师,而且还在临终前当着众弟子面上演了向其子秘授心法以确认其子掌门人地位的仪式。”[3]杨露禅以血统确立了其子班侯的正统。哈布瓦赫指出,“在贵族当中,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续了一个世代绵延的传统和记忆。”[4]这也是为什么民间武术门派的权威、掌门人的传承中,多数沿用上代权威、掌门人直系后裔继任的原因。
1.2 弟子传承
在孙氏太极拳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中,我国古代的王权禅让制度再次出现。在第二代传人孙剑云先生看来,“孙家拳掌门,惟有德者居之。”[5]“近来,孙老师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决心在自己健在的情况下确立第三代掌门人。她打破封建的家族传承旧习,推荐了一位经过一定时期考察且得到同门弟子赞同的品学兼优的非孙氏家族的入门弟子、47岁的孙永田为蒲阳孙门第三代掌门人。”[6]中国武术协会前主席张耀庭认为,“这一举动不仅一反过去武术界封建保守的传承方式,而且体现了择优选拔人才的先进性,是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值得武术界效法。孙老师在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主动交班的气魄与行动更是值得提倡和宣传的。”[6]然而,弟子中心的传承毕竟要直面血统的问题。戴国斌认为这种“弟子中心”的德技传承,一方面有利于门户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升门户在武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因破坏西周形成的嫡长子继承制传统,而带来门户社会秩序的动荡。”[3]
1.3 权力技术综合考量
在血缘正统和门派发展之间,如何保持二者之间合理的张力,既能传位于血缘的合法继承者又利于本门派的发展壮大,一直以来是个难题。戴国斌[3]认为武术门派掌门的世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因其具备了英雄基因,从而在天赋上更能接近祖传;另一方面,其后天的生活习惯更能在“武术理解与成就”上受到上代英雄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商周以降的朝代更替中,哪家、哪国的家族血缘传承经历了千秋万代?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武术门派的掌门人传承中。在上代掌门人后裔无才无德或放弃承担门派发展的重担后,其他弟子必然站出来担起发展的责任。或者,在上代权威、掌门人因故去世却未指定下代传人的前提下,众弟子各执己见,掌门人后裔又不愿参与其中,如何推出令各方满意的掌门人尤为困难。在现代社会中,掌门人的选举是多方角力、综合考量的结果。当选的掌门人如何团结有异议的门人弟子继而成为真正的门派权威是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2 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发展的现实需要
香店拳为福州市地方拳种,属南少林拳系,相传为清乾隆年间传入福州。目前,香店拳主要由第五代宗师房利贵门户弟子在福州传播。房利贵去世后,为了更好地传播和发展香店拳,其弟子大胆革新,进行了系列“传统的发明”,选举掌门人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失去了传统宗法社会权威的当代社会,掌门人的头衔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某一拳种、门派、门户存世的、被构想出来的象征,这一象征如何才能具备真正的权威是关键[7]。在上代宗师故去已久,人们在新时期亟需重建昔日的精神家园,对掌门人的选举与确立,是地方武术门派在现代社会中再造权威、重拾祖先荣耀的必要路径。
2.1 式微的传统亟需“头人”的象征
米歇尔·沃尔泽指出,“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8]如对总统的选举,人们选择是“国家的首席象征制造者”[9]。同样,掌门人的产生是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在传统式微背景下的自我救赎。
2.1.1 现代社会传统的式微
人口流动加剧、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了部分乡村的消失,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0]当师父房利贵的家乡上山村整体迁往山下市郊的城市社区“登云新村”后,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也解体了。林婷认为:“宗族秩序和社会秩序、宗族权威和公共权威在历史发展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社会秩序与公共权威以强势长驱直入的时候,宗族秩序及权威就弱化,甚至被消解,反之,就有所恢复和抬头。”[11]在房利贵1981年去世直至2005年的24年间,香店拳师兄弟们四散他处,没有形成新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权威故去后,在“乡土社会”解体的背景下,新的公共权威和社会秩序并没有形成。根据香店拳第六代弟子吴孔谈的口述,原本在宗师房利贵去世后,大师兄徐心波的威望最高,应该继承师父的衣钵,但可惜其英年早逝。
徐心波为何具有仅次于师父房利贵的权威?其一,少部分人因为亲眼目睹了祖先的各种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沟通先人和后人的中介。哈布瓦赫认为,“他们在他们所监护和养育的这一代人中间,享有着不可比拟的威望。”[12]在访谈中,吴孔谈说“徐心波他是正宗的很小跟着师父,师父教徒弟,都是他在协助师父。”甚至替代师父教师弟散手,大师兄承担了乃师乃兄的角色。其二,大师兄的第二重身份是香店拳第四代掌门人林庆桐的外甥,林庆桐在去世前将徐心波托付给自己的徒弟房利贵,这种颇有托孤意味的代际传承暗含了第四代对第六代的赞许与内定,换言之,徐心波的权威有宗法结构的隔代认证与加持。即使如此,大师兄徐心波的权威也无法避免其差序格局的传统式微结果,从其丧葬仪式亦可感受到。吴孔谈说:“师父的葬礼大家都去了,他的徒弟基本上都来了。”而大师兄的葬礼则相对简单,师兄弟去的较少。大师兄去世后,其余师兄弟更加无法承续师父和大师兄的权威。
2.1.2 武术门派发展的现实需要
香店拳权威相继故去,新的核心集体没有形成,香店拳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青城派掌门人刘绥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现在差不多有50来个(门派)因为‘掌门人’故去,手下徒弟不再习练,而逐渐销声匿迹了。”[13]所以,选举新的“头人”,再造现实权威,重新凝聚集体意识,成为香店拳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福州市香店拳委员会秘书长吴孔谈认为,“社会上,政府不承认我们掌门人,在我们本派中大家承认就好了。”掌门人一词的实际意义在于民间武术门派将上代掌门人、师父的前世传统权威象征化以应对现世社会现实权威的衰落,这既是自我救赎也是文化自觉[14]。但是,“中国的民间权威,不只是一种‘自然圣者’,而是离不开官僚体制的,他们或为官后被承认为民间权威,或成为民间权威后被官方接受。”[15]在香店拳内部,王华南、吴孔谈均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将科层权威转换为传统权威。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殷琼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权威凭借人们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支配和整合力量,礼治的主体——传统的宗族道德权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心。”[16]香店拳的武术精英正是以掌门人选举的权威再造手段,完成了师父去世后组织成员的团结凝聚和发展转型。
2.2 权威再造的困境
在阿伦特看来,“权威者的最明显特征是他们没有权力。”[17]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民间武术门派掌门人称谓的“诡异”之处在于,它塑造出民间非正式组织意义的“首席象征制造者”,甚至是一种权威,但却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孙氏太极拳掌门人孙永田才会发出“我这个掌门人又能掌谁的门”“他们承认我是掌门我就是,不承认就不是”的无奈。在没有权力的背景下,“权威的内涵或本质就是一种合法性的自我确证。”[18]掌门人成为这一权威的合法称呼,他没有权力,只有付出,却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也印证了阿伦特“任何社会在缺乏一个权威主义架构的情况下都无法存在”[17]的观点。孙永田的无奈在于他在失去传统权威支持后,难以引领新的集体前行,换言之,新的集体没有形成新的权威和新的集体意识。
3 民间武术门派“头人”的生产机制
不同于杨氏太极拳“头人”的血族传承,房利贵的儿子房贞义没能成为第六代香店拳核心,除了个人性格、意愿等原因,也有其现实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城镇化造成的乡村社会解体导致 “我们都处在一个不知权威真正为何的处境下。”[17]在哈布瓦赫看来,一个贵族家庭不在了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传统的烟消云散,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也会消逝。因为这部分历史“不可能像一个官僚被另一个官僚顶替那样,为另外的历史所取代。”[4]最终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为王华南,从新“头人”的生产背后可以窥见其如何转嫁宗师传统权威,以及如何平衡兼顾科层权威和宗师后裔传统权威之间的关系等,而这些对香店拳的现代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3.1 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产生的合法性
郑杭生、帕森斯等国内外学者认为,虽然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意识趋于衰微,却并没有瓦解和消失,而是发生了演化,“这并不意味现代社会没有集体意识,只是集体意识的内容变得与传统社会不同而已。”[19]没有新集体意识就没有香店拳的再生,而新的集体意识必然要由新的权威——掌门人来凝聚。香店拳的精英通过确立掌门人的合法地位,进而塑造新的权威和集体意识,完成了香店拳的权威再造。其一,宗师嫡宗的让渡。师父儿子房贞义的提名推荐,为王华南转嫁了部分血族传承的传统权威。房贞义的坚定拥护代表了房氏血脉的正统承认。其二,选举的仪式性。“大家举手表决,大家全体通过”的现代选举方式使王华南的掌门人具备了民间组织“头人”的合法性。选举过程使每个人参与其中,具有举手表决权,既照顾了个人意识又完成了集体团结,“仪式和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他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20]尽管在香店拳掌门人选举的过程中,部分师兄弟存有异议,但还是会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和选举结果。
3.2 民间武术门派“头人”当选的综合考量
景军认为在宗法结构的组织中要取得较高位置需要4个标准:“道德权威、政治影响、仪式专长、个人魅力”[21]。是否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一定的财力背景,能否公正处理门派公共事务,性格、技术能否独当一面,能否操办组织内的重大仪式,能否处理组织外部事宜,这些均是对香店拳侯选掌门人考量的因素。显而易见,香店拳的掌门人传承既不是儿子中心,也不是弟子中心,而是综合技术考量的结果。
其一,王华南退休前曾在多个政府行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这有利于香店拳和政府间的沟通。其二,王华南极具亲和力,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受香店拳师兄弟的拥戴,具备一定的传统权威基础。其三,王华南在师父房利贵的5位义子中排行第二(大师兄徐心波为第一),这使宗法形式的类血缘关系更加牢固,从而比一般意义上的徒弟更深入香店拳权威核心。在后续的访谈中,吴孔谈认为:“徐心波过世后他(王华南)也算大师兄了,理所当然就要他出来撑场面了。”其四,“功夫不错”是王华南的硬实力。吴孔谈说:“练武之人都是三教九流,一要靠人缘关系,一个要靠功夫镇得住,不然不行的。”“他(王华南)是我师兄,论功夫也可以了,我都跟别人说我的功夫有的还是王华南教的。”房贞义也指出“他群众基础好,技术也比较好。”从而,软硬实力不俗的王华南以现代秩序的选举方式当选为新一代香店拳掌门人。
3.3 民间武术门派“头人”科层权威向传统权威的转化
2006年6月,王华南顺利成为掌门人,之后在其带领下香店拳于2007年顺利获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上具有了一定名气。从香店拳“申遗”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的民间权威离不开官僚体制的支撑,即福柯眼中的“权力关系植根于整个社会之网。”[22]从吴孔谈“他功不可没”和房贞义“他贡献最大”的评价来看,王华南成功实现了科层权威向传统权威的转化,提升了香店拳弟子的集体意识和凝聚力,以此奠定了其香店拳掌门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形成新的集体意识创造了条件。
4 现代民间武术门派发展中的社会分工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详细论述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用以解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维系,和亚当·斯密等学者不同的是,涂尔干确认现代社会中分工的真正意义不是经济作用,而是实现社会的整合。“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23]对掌门人的选举与确认,本身就是香店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分工机制。
4.1 机械团结的衰落
从第五代掌门人房利贵到第六代掌门人王华南,香店拳的运行有着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秩序的差别。房利贵在其60余名弟子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作为现实和精神的偶像,他将一众弟子凝聚在一起,形成集体意识,使弟子们在信仰、情感、目标上具备相似性,实现了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在房利贵去世后,香店拳弟子们怀有的共同情感和信仰日渐衰弱,房利贵所构筑的机械团结微弱地延续下来,作为一种低级分工方式为香店拳在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基础。
4.2 有机团结的形成
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与机械团结相对,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某种特定的或专门化的职能,社会分工不仅使得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存在,而且还成为与其他人相互依赖的基础与条件,由此形成社会有机统一体。香店拳需要在城市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建构新型的分工形式来适应新的发展,因为“起初机械团结还能够,或几乎能够独当一面,后来则逐渐失势了,有机团结渐渐跃升到了显著的位置。”[12]传统社会以集体意识为维系的主要方式,而现代社会中分工是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来看,香店拳的掌门人选举机制意味着民间武术门派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家长制管理模式,开始迈进现代意义的民间组织管理。
在接下来的香店拳发展运作中,各成员均利用其资源为集体做贡献,如在拳谱《香店拳》编纂、出版过程中,大家各司其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完成了香店拳门派从未有过的壮举。香店拳现代分工的初具规模印证了涂尔干所指出的“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基础上被重新构建出来的。”至此,作为门派的香店拳初步具备了有机团结的分工机制。涂尔干认为分工成就了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得以可能的前提,他进一步指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在于“这些功能的紧密结合”[12]。分工使香店拳获得新生,形成了“比师父当初更大的局面”。
4.3 社会分工中现代门派的意义构建
香店拳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2005年香店拳弟子开展了“家底普查” ,2006年完成了掌门人选举,2007年成功申报了省级非遗,2010年成立了香店拳俱乐部,2015年出版了拳谱以及举行了年度“厨会”[1],等等。在社会分工意义上,掌门人选举具有将香店拳集体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换的中介作用,促使众弟子形成了有别于师父在世时的集体意识。换言之,香店拳门派以房利贵创造的机械团结为基础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掌门人的产生就意味着一般意义的民间社会团体成立,确立了武术社会中新的香店拳门派集体。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民间武术门派,香店拳在日常生活实践[24]和宗师祭祀仪式中构建了自己的现代社会出场。
5 传统与现代交织中民间武术门派“头人”传承
现代社会的民间武术门派,要想获得更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就必须沟通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如郭于华所指出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态与民众观念之间的联系,沟通和活动过程才是认识社会构成与文化特质及其变迁的最重要角度。”[25]通过现代选举制度产生的掌门人的权威确认,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法血缘权威的彻底崩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秩序的运行不得不考虑传统的宗法制度。所以,面对礼俗性的宗族秩序,即使合法的现代社会秩序也不得不做出适度妥协,它反映在香店拳第六代掌门人王华南身上,则是如何处理好对师父的个人感情以及现实中师父后裔的关系问题。
尽管香店拳在2006年已经选举产生了第六代掌门人,但在法律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团体。截至2010年,香店拳弟子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家”——独立法人的民间社会组织,也是因此,香店拳在2006年申报省级非遗时,不得不依托福州市群艺馆作为上级保护单位进行申报。为了今后避免此种尴尬,在香店拳精英的积极推动下,福建省庆香林香店拳俱乐部于2010年7月由民政局批准成立,第一任会长是王华南,房利贵之孙为秘书长。上任之初,王华南就提出最终要把“俱乐部”“还给”房氏家族,2010年下半年,王华南辞去会长职务,房利贵之孙接任会长。“多套牌子,一套人马”在我国官方和民间交叉的各类机构中极为常见,作为香店拳门派的分支机构,俱乐部的领导由掌门人担任未尝不可,为何王华南主动提出“禅让”会长?
尽管涂尔干认为“在分工制度得以确立以后,种姓制度就逐渐趋于衰落了”[12],但在香店拳掌门人选举中,韦伯提出的法理型权威和传统权威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两者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但宗法结构的严格规定,让其成为一种稳定系统,这是普通公共权威秩序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完全无视传统宗法秩序的存在和影响,在任何时候,宗法秩序都能够起到追本溯源、凝聚共同体的作用。王华南对会长的“禅让”,既是对儿子中心血统的妥协,也是稳定门派权威的技术。通过选举产生的现代法理型权威和通过血族传承的传统权威共存于当代民间武术门派中,构成了民间武术门派运行逻辑中的文化奇观。
6 结论
考察民间武术门派掌门人的权威再造活动,我们能够管窥中国武术社会中常见的武术门派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如郭于华所指出的:“所谓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其实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与权威、民众生活动力等各种因素互动与共谋的复杂的历史过程。”[24]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产活动,民间武术“头人”的出现揭示了民间武术门派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自觉和自我救赎,其发展既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分工特点,也要观照传统社会的宗法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武术门派完成了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社会中的有机团结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