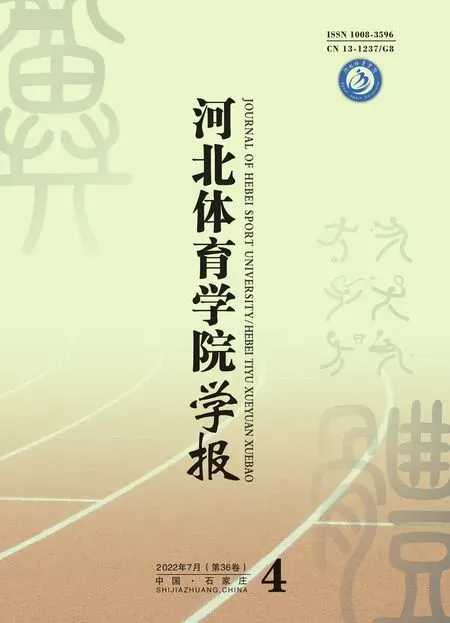武术善良向度的时代价值
2023-01-06马敏卿高会军
陈 青,马敏卿,田 杰,高会军
(1.河北体育学院 武术系,石家庄 050041;2.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信息传媒系,江苏 苏州 215100;3.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1 问题提出
从武术具象的搏击技术结构功能中,人们抽象出技击性,并视之为武术的本质。技击性是人类暴力的表现,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中恶的流露。即使是发展至虚拟技击阶段,武术依然难掩所谓合理宣泄的攻击性。武术的暴力存在似乎是毋容置疑的唯一存在形式。
随着文明的进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督促下,与恶有关的暴力事件逐渐减少。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思考,武术有没有其他存在形式?富有善良向度的武术是否更具时代价值?对此,本文将通过身体暴力—身体力量、人性从善—自我约束、善良意志—良民追求等维度,对武术存在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哪类武术向度更具时代价值,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2 武术叙事中的恶与善
习武人的身体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搏杀武技是作战工具,这使武术与军事战争如影随形。有统计表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12 800余次战争,其中大规模战争3 791次。最残酷的当属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人口锐减2/3,这个人口数量相当于当时全球人口的1/6[1]232。频繁的战争促进了暴力类武术的成长。而战争之外的私斗中,武术也始终是有效的搏杀工具。暴力是在冲突性紧张/恐惧中人们所实施的对他人和自身产生伤害或影响的行为[2]。武术在其中扮演着暴力执行者角色,虽有掩饰、改变,但依然难祛或具象或抽象的暴力成分,冷兵器时代的武术可谓是暴力综合体。
如德勒兹所言,习武人将自己的身体练就成身体武器,以防身自卫、保卫家园。这种方式并非中国人独创,而是人类的共同行为。洛伦兹强调人的暴力活动主要是受攻击性本能驱使,弗洛伊德也认为人的行为是自私的“本我”不自觉地外溢。可见搏杀技术没有族群之别,是人运用身体进行暴力厮杀的通用技术。
张震发现,习武人的身体武器曾经是贵族的特权和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贵族们以精熟的身体武器垄断而身居庙堂。但是随着社会演进,习武人在秦代之后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后虽有武举制的特殊通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无法再登庙堂[3]。习武人的个体身体暴力逐步被军事、政权等国家垄断形式取代,掌握身体武器的习武人回归其应属的社会序列。现实中,集大成的习武人,多与社会底层相连,俞大猷家境贫寒,戚继光戎马一生,程冲斗以武护镖,吴殳寄人篱下。为逃避禁武之忌,集大成者巧妙地将杀人术罩上养生术、娱人术外衣。民间有大量的习武高手,如早先的游侠,常常会做一些大悖于人伦常情的异事[4]。在董仲舒看来,该群体属于斗筲,当被奴役、被压迫。但有压迫必有反抗,反抗将本性中隐藏的攻击性放大,所以这类人创造的搏击术自然包含着暴力成分。
暴力绝非武术的全部属性,善存恶除是社会运行主流,是必然中的自然。在儒家文化教化下,武术的套路化让人性之善自然流露。在流传至今的129个拳种中,极少直白表现暴力的拳种,暴力多被善良遮蔽,其技击性需通过拆招、说招的解读才能被人理解。同时,套路化的拳种日趋表现出强大的健身、娱乐、竞技等文明价值,成为民众广泛接纳的身体行为,善良向度成为武术区别于始终富含暴力色彩的军事和异域武技的重要特征之一。
3 善良人之本:善良拥有生物和社会基础
人性之初,始存善恶。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却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疾恶、好声色、耳目之欲,如果顺从人性,必生争夺趋于暴乱。由此看来,人之性恶[5]。告子则坚信人之初性无善无恶。至董仲舒则通过“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分析认为“善质非善”。在等级化的人群中,只有圣人本善而斗筲性恶,对于大多数的“中民”来讲,须通过“事在性外”的教化善才能显现,进而得出“人性三品”[6]。朱熹也认为“天命之性是理”“理则无有不善”,气质之性“一本万殊”,须伦理教化以袪恶从善。西方文化中,苏格拉底认为人性本善,善就是知识、理性。柏拉图则说人性是自私的,间接说明人是恶的。亚里士多德毫不客气地说人更接近野兽,而远离神灵,人性就是恶。倾向于人性恶的基督教义则引导着西方文化,性恶观促使契约、法律等成为西方人抑制恶的重要手段。科学家们也加入讨论,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众多的斯坦福大学生很快变成了冷酷、以施虐为乐的“狱卒”。似乎,人性为恶。
然而,如何解释人类暴力事件逐渐减少、良行善举广为流行、文明进程不断加速、套路化的武术成为主流等不争事实。对此,阿比盖尔·马什给出了答案:常人看到他人恐惧时,大脑中的杏仁体活动异常活跃,在基于抚养和保护后代的后叶催产素作用下,人会表现出强烈的避免、缓解他人痛苦的善良欲望和动机。此刻,后叶催产素瞬间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引发强烈的“共情反应”,二是抑制逃避和躲闪的冲动,并使人对处于恐惧中的对象产生亲近和关爱,驱动利他的善良行为[7]265-277,可见,人性本善拥有牢固的生物学基础。习武人较常人会更多接触面露恐惧的对手、弱者,激发这种生理反应的几率也高于常人。这样看来,孟子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人性之易,需要后天教化与规训。正如墨子认为“人性如丝,必择所染”、荀子判定“涂之人可成禹”一样,踢打摔拿本无善恶之别,其善与恶完全在于习武人的持武向度和习武行为。在福柯的规训、埃利亚斯的公共垄断下,恶得以抑制。在早已步入“良民宗教”公共垄断性规训的中国,习武人被辖域,踢打摔拿等搏击技法被虚拟,套路化更胜埃利亚斯的体育化,助力习武人锁定善良向度,走向文明。
在主客合一的身体之中,有机体中的生理机制与教化、规训等文化规范相榫卯,向善的叠加力量使得从善的社会性逐步取代趋暴的生物性,不断完善的理性充分发挥对人性的“染化”,凸显善良。当然,教化、规训人之生物性难如移山,需通过“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善恶进行辨识和践行。人欲祛恶“必志于仁,而后无恶。”船山先生认为“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养之,则耄期而受命。”人能改变自己[8],习武人亦能。
在本土“主体性阐释”的性善和教化主导下,习武人主动进行从善的身体化,将身体暴力转化为身体力量,以套路化进行着武术文化的再生产。武术生成了明显异于重伐人、尚暴力的军事和异域武技,具备益于人身心健康的身体和技术结构,表现出强劲的善良向度和文明属性。
4 从善人之归:习武人的从善身体化
善良是人性的归属,决定文化走向文明。成型后的武术大都为“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子,主导着武术发展,这是习武人良知追求、良民形塑等系列从善身体化,使身体暴力的搏杀演变为身体力量的套路演练,驱动武术文明化的结果。
4.1 习武人的良知追求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成圣成王的核心,欲获德性首要修“正”——从形正到心正,步步递进,不断养成。《大学》道:“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为帮助民众理解,君主们提出“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将这个目标榜样化,使民众明白如何格物致知,教导民众理解“三纲八目”、内外兼顾、由圣而王、实现良知的逻辑关系。这种润物式教化更能促使民众效仿,实现自我控制。
对习武人来说,内圣外王也是他们致良知的必经之路,其中也备受润物式教化滋养。其一,孟子认为欲达内圣外王,须充分发挥性善作用,以仁心通仁政,将“不忍人之心”扩展为不忍人之政、之行。孟子更将“内圣”理想人格内涵,纳入生命关注之中,为进行生命活动的习武人提供了具体可及的目标。其二,源于搏杀的武术备受各方指责和限制。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要“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决不能“兵强天下”。《左传》则通过“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对武术加以束之、化之。其三,统治集团通过政权和军队逐渐垄断了暴力,控制着个体暴力的随意使用。伦理道德叠加国家暴力垄断,促使习武人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其四,习武人通过对道德礼仪、传统哲理的身体阅读和体验,切身理解了使用暴力获利亦会受害的道理,进而尽量避免武力冲突,以“格拳致知”[9]进行人格修炼,彰显具象的口德、手德、身德;改一招制敌的搏杀技术为点到即止的娴熟技能,变利己私斗之径为报效国家之途,智慧地创造出练以为战、练以为健的套路,成为人类独特的蕴含搏杀因素的善良身体文化。
暴力肆虐,文明受阻。西方的中世纪,充满着暴力,“15世纪的城市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家族之间以及集团之间的争斗。”[10]中国民风总体良善,但也有像唐朝后期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延绵40余载的平藩、长达10年的黄巢起义等举国战事的暴虐插曲,辉煌盛唐衰于战乱,毁于暴力,文明不再。可以想象当时民风趋暴,习武人甚至认为以暴制暴为治世之道。暴力武术泛化,善良难以容身,武术文明化进程步履维艰。
善良普世,文明彰显。当国家对暴力垄断能力加强时,习武群体的身体暴力被抑制,并适时转向身体力量的应用。身体力量是一种运用身体进行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活动能力。春秋时期“以武犯禁”的武侠销声匿迹后,逐渐出现了利用身体力量营生的“尚武重义”的豪侠、“重气任侠”的游侠、“持武重利”的镖师等习武群体。通过身体力量,习武人拓展了致良知之路。首先,米尔格拉姆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具有天生的恻隐心[7]48-50。习武人面对无招架之功的恐惧眼神时,怜悯同情油然而生。其次,武术为血缘家族式传承,习武群体多为家族或拟家族成员,相互间少有残暴现象。最后,文明帮助人类趋于善良,在文明大环境影响下,暴力武术难觅立锥之地,趋善的套路化大行其道,太极拳入选人类非遗即为明证,更是武术文明化的曙光。
4.2 习武人的良民形塑
在辜鸿铭看来,中华民族以“良民”著称,良民是善良与合规相融的公民。辜鸿铭分析“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着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11]良民之“良”源于心灵。对此,马什也强调:“驱动行为的是欲望,而不是理性。”[7]313自然,内生与外控缺一不可,“爱之以礼”的情欲与“做一个识礼的好人”的“良民宗教”共同作用方能育化良民。良民的社会氛围,迫使习武人运用特有的递进式身体化手段改良武术,变伐人为塑人,用拳种套路之笔,书写恢弘的民族文化。
第一,技术演绎。冷兵器的身体武器攻击力始终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习武人在探索中不断进行技术完善,为能够有效实战而惯勤肢体。吴殳的“一十八扎,十二倒手,攻防兼备”的峨眉枪技,以“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之灵敏和“回龙扎”“带打扎”等“狠手”,实现了务实的技击效果,欲求达到这种效果必须通过套路,以身心训练为先,“手足运用,莫不由心。心火不炽,四大自静。”[12]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和延伸身体武器。苌乃周完善拳技的形气合一,同样格外强调将阴阳入扶之气贯穿于“头如蜻蜓点水,拳似山羊抵头,腰如鸡鸣卷尾,脚似紫燕穿林”的技法中,充实了苌家拳。残酷的现实真切地告诉习武人,身体武器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锋利,习武人则通过演绎实现了对身体武器尤其是其局限性更全面、准确的认识,进而领悟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自觉转向探索自保而后全胜的方式和方法,此身体体验、认知和身体创造奠定了武术套路化的基础。
第二,虚拟对抗。习武人的对抗对象经历了从对手到同门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身体对武术搏击技术的体验,产生不同的认知与创造。从与对手较量的一招制敌,变成与同门三五回合不见分晓的比试,武术从实战走向了虚战。何良臣训练枪法就用了模拟法,“以二十步内立木靶一面,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一寸木球在内。每人持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正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13]256相互的对抗也多以棍头裹白灰包互击,以双方身上白点判胜负。模拟实战使习武人体悟遮蔽暴力的重要性,非功利性的套路凸显价值、大行其道。《东京梦华录》载:“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13]197这种趋势引发了“贵柔”“守雌”类拳种的萌发与勃兴,遮蔽暴力的责任身体化成为武术的主旋律。
第三,说招拆招。说招拆招意在明确技击含义,实现移情体验。招法的拆分练习,可达岳飞“授兵指画,约束明简,使人易从”的效果[13]223。当某种招法在模拟条件下说明讲透,习武人通过模仿练习,能充分体验自身可能遇到的威胁,同时领悟对方的伤害,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嵌入习武人的意识,唤醒同情心,渐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理,练就表现自我身体力量的点到即止的娴熟技法。“人的生命‘选择’,指在一定环境下,人对自己行为的决策和挑选,是自觉的能动的改造外界和改造自我的行为实践。”[14]这种行为实践中派生的移情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将心比心,树立了习武人尊重生命的人际交往原则,强化着以德报怨的意识。在内在的技术移情与武戒、武礼等外源性规训的叠加作用下,习武人创造出了“尚德不尚力”的独特武德。
第四,拍打功夫。通过拍打练习,提高疼痛感觉阈值,唤醒应激反应,从而提高打击和抗击打能力。拍打功夫可增强相应功力,唐朝硬气功名将汪节曾在御前表演“俯身负石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15]197“羊侃也有掌指功夫,……侃因以手扶殿柱,没指。”[15]112这种功夫不仅发挥着威慑作用,并且可以触发杏仁体和后叶催产素等生理机制运行,引发共情、移情效应,以助减少或放弃暴力性对抗。习武人通过耗能的拍打练习,难以获得身体武器攻伐收益,因而转向于惜命、重生的功法、套路。唯有将人性之善和自我从善、生命冲动与生命塑造“致中和”,习武人方能塑就温良尔雅的“良知”、成己兼善的“良能”、浩然正气的“良民”之内圣,渐入“经邦济世”的外王境界,赢得社会认可。
第五,套路演化。《南齐书·恒康传》记载:“宜兴拳捷,善舞刀楯。回尝使十余人以水浇洒,不能著。”[15]166虽夸张,然套路演练的敏捷技法、身械融一跃然纸上。薛巅“在一次有许多武林人士的集会上,突然表演了一手功夫,……将所有人都惊住了,因为他的身体展示出了野兽般的协调敏锐和异常旺盛的精气神,当时就有人议论薛巅的武功达到了神变的程度。”[16]薛巅精彩的套路表演,展示出其强大的技击潜能,更表现出其卧薪尝胆的自我控制能力,使他挽回了先前在搏击场失利的颜面,赢得了尊严。正如埃利亚斯所认为的自我控制是人性完善、社会文明的重要环节,在武术套路演练中技与法、形与意等复杂的身体控制更是自我控制形式之一,是记录拳种的有效载体[17]。身体控制下的矫捷身法、精湛技艺可助习武人沉浸于“美善同意”之境。
通过递进式的身体力量转化,套路演练助力习武人从善,从善的套路化改变了武术的技术结构,从而生成、巩固了善良武术。
5 善良武术的时代价值
5.1 道德共振的时代价值
良民形塑是习武人通过武术特有的“以搏塑人”“支配技术”实施塑人的“技术支配”,在善良与道德共振中将良民意识内化,表现为道德自律,完成习武人的善良身体化。共振将行为与意识有机结合,催生符合时代需求和体现时代价值的现实、具象的身体共鸣教化体系。
善良是在责任的道德定言命令下,以理性的善良意志自律地依照法则去改变人的世界。在康德眼中,责任是善良意志的实践表现,定言命令要求人人遵循普遍规律,理性独立于偏见选择实践中必然的善,自律为善良意志立法,并且主动地自觉守法,只有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善良,呈现出永恒的文明价值。
第一,强国的“匹夫之责”。康德认为“出于约束性的行为客观必然性,称为责任。”[18]46这种强大约束力的责任使人尊重生存规律和人性演进规律,从中强化具有道德价值、内含责任的善良意志。习武人在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生命对人、对国的价值,自觉地以塑造生命为己任,成就了武术的善良意志。康德说:“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并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18]7,46这种自在的善成就了人,塑造了人,使文化表现出善良特质。善通过责任来完成文化任务,并对文化进行不断完善,使之成为普遍有益于人类的文明。“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而只能出于责任。”[18]10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化仁爱、爱国、强国为己任,是长期艰难的履责过程。责任驱动着伐人武术走向娱人和完人武术[19],引导着习武人从忽视生命,转向呵护生命、为国健身、为国强身的义务演进。
第二,“扬善抑恶”的定言命令。人类的文化是人为地人化过程,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成果,其中,人为地为人是其本质和规律。如何人为地为人,善良至关重要,没有善良的人为,必将破坏为人的过程和目标。以善制恶、以德报怨的善良武术能激发无限的博爱与合作,有效解决争端和冲突,此乃武术文化持久发展的规律。“扬善抑恶”需要以不争的定言命令去执行。即以善良消除暴力,是无条件的,是对人有益的普遍存在。人性的善良意志使“以搏塑人”准则作为武术演进的普遍规律和习武群体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通过执行武术“以搏塑人”,具身地对照“以搏伐人”,可深刻体验现代社会中善良的时代价值,有效培养人的文明意识。
第三,理性的“仁爱”。无欲望的纯粹责任难觅,凝练规律的理性常在,理性帮助选择向善、行善,接近纯粹责任,理性与纯粹责任共同辅佐道德,使道德显示出普遍意义。儒家凝练出超越个人经验、爱好、普适的“仁爱”理性,以仁义礼智信的责任体系,有效地维系着中华文化,教化着民众,使民温良。“仁爱”理性帮助习武人充分关注人的身体建设,不断完善“以搏塑人”武术的虚拟技术结构,创造出文明属性的健身类拳种,拓展了武术的生存空间,彰显了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心之所可”的自律。康德强调自律至上,但并未完全否认他律。智慧的中国人从务实的身心修炼出发,以天人合一为标准,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他律践行道德,化他律为自律。“以搏塑人”武术的技术结构和目标追求完美地再现着“身心如一”“一体三相”的儒家生命观、身体观,以“心之所可”之“可”,依托自律力量,实现身体建设。习武人以尊重生命为普遍准则,以德技双馨为文明标杆,使善良武术成为发展方向。
5.2 资本榫卯的时代价值
在埃利亚斯看来,“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通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自我约束以及羞耻、厌恶和信任等情感的生成,逐渐形成控制攻击性情感与暴力行为的习性。”[20]但是,埃利亚斯忽视了由人性驱力和经济张力构成的合力。当代人通过资本榫卯、追求资本效益,生成了遏暴趋善的主导力量。
在文明化中,人性之善促使武术迎合文明之需,易伐人为塑人,善良向度越发明晰。为生命塑造的武术套路遮蔽搏击技法,较仅戴上厚实手套的拳击等规则化,其文明改造更加彻底。套路化彰显着武术的善良成分,使善良武术在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养成健身习惯、形成文明生活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强化身体资本、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展现出多维度的价值。
第一,“贵生”经济张力的连锁价值。经济张力借助人的行为向度杠杆撬动社会运行,满足人的利益诉求。经济利益让人们主动放弃暴力,以实现互惠互利。骑士对抢劫或筹款、损失与收益的算计中发现,“还不如诚实地辛苦一把。”[1]98的确,商业将人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如重商的宋朝统治319年间,虽深受边患威胁,却仅爆发83场战役,相比唐朝286年里130多次边域战争,其军事活动大为减少,但经济成就位列世界前茅。又如,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秉持和平发展理念,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即便充满针锋相对的“囚徒博弈”,在重复博弈后,合作依然成为最终抉择。在惨烈的一战期间,英、德士兵对峙中定时定点炮击、射灭对方蜡烛而不伤敌军等现象体现着人类虽由自私基因掌舵,但好人终有好报意向却占据主导[21]。和平时期,人与人在利益共享中互动,更以和谐与友善为主。经济与社会、文化相辅相成,欲达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文化最优化,须与人的善意和合相榫卯。庄子说“道之真以治身”,强调身体的重要性,“贵生”文化深入人心。“贵生”的经济张力促使武术向身体建设产业延伸,展现武术尊生、养生的经济价值,善良武术提升了经济为人服务的程度,展示着经济的文化价值,拓展了习武人的生存空间和经济的生命空间。武术所显现的从武校、拳馆、赛事向武术演艺、健身干预、康养服务等产业的拓展之势,恰是这种连锁的必然结果。
第二,身体资本链的复合价值。以生命塑造为向度的善良武术,相对于生命冲动的搏击武术更具身体建设价值。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到布迪厄完善人力资本理论,清晰地显示了人力资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其中,身体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的基础。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及各国经济增长率均有积极促进作用。”“拳起于易,理成于医”的善良武术提供了丰富有效的健身手段,可使人的健康身体资本增值。健康身体资本与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相榫卯,共同构成完整的人力资本链条,铺设以人为本的文明轨道,帮助习武人“锻炼行道”,“从主体‘人性与天性’两个层面,促进主体的自我实现”,显示着“练以成人”[22]的复合价值。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以身体工具为榫,纳身体消费入身体资本之卯,将身体武器之锋芒,收敛于求真向善之鞘室,为武术提供了施展“以搏塑人”的机遇,使武术熔为“合金”身体文化,满足人类健康消费、身体建设的需求,进而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3]。此外,在激烈逐利的现代,习武人保持“以静水比德的价值观”[24],充分尊重生命,以“利为不争”的文明习性,发挥善良武术的健身、修心、益群、崇德的时代塑人价值,引领人体文化之文明走向。
6 结语
埃利亚斯看到体育化加速人类文明进程,我们发现武术通过善良化—身体化—套路化拓展了人类文明范畴。善良化使习武人通过善良意志、习武行为自控与道德共鸣,使“合金”的武术超越私欲,合乎规律,接近法则,达到利他益己的完全责任,诠释人性本善、人性可塑。身体化通过武术特有的技术手段,将身体暴力转化为身体力量,丰富人化能量,使人的从善意识和行为贯穿于人体文化,凸显中华文明的教化智慧、和合价值。套路化以修身至上的套路为支柱,用睿智的中国话语表述文明进程,借“以搏塑人”的身体建设方式强化人力资本,服务人类健康共同体,彰显中国的文化担当。经久不衰的善良化—身体化—套路化的善良武术已然证明其存在价值,随着其套路化—身体化—文明化,必将进一步引领不断充实与完善人体文化的文明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