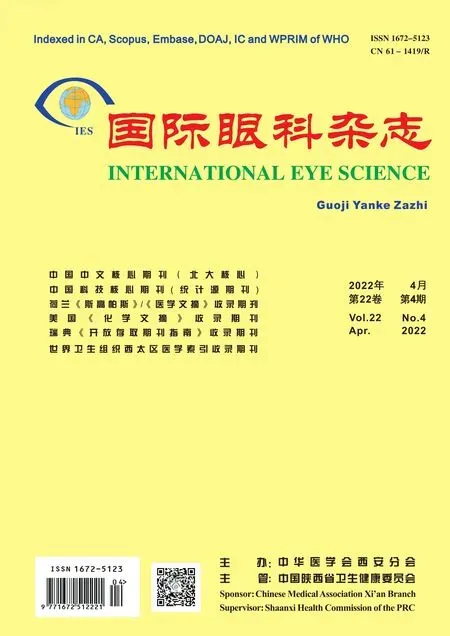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研究现状
2023-01-04王亚文任胜卫赵东卿
王亚文,任胜卫,赵东卿
0引言
圆锥角膜(keratoconus,KC)是一种以角膜扩张、中央区角膜基质变薄、呈圆锥状突起为特征的角膜病变,常导致近视、不规则散光、轻度或重度视力下降[1-2]。一项包括来自15个国家5 000多万人的Meta分析显示,圆锥角膜的全球患病率为138/100 000[3]。该病通常于青春期发病,病变呈进行性发展,通常于患者30~40岁时停止进展[1]。由于发病年龄偏小以及视力较差,圆锥角膜患者经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及经济负担,生活质量较差[4]。
圆锥角膜的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的研究表明,圆锥角膜的发生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圆锥角膜与其他遗传性疾病相伴随(如唐氏综合征、马凡综合征等)和双胞胎在圆锥角膜临床表现方面的遗传一致性均表明圆锥角膜具有遗传基础[5-6]。Kriszt等[7]通过家系共分离分析表明圆锥角膜是一种复杂的非孟德尔遗传病。此外,Hashemi等[8]通过对403个家庭的研究发现圆锥角膜家族聚集性较高。多个研究发现圆锥角膜一级亲属患病率较高。上述研究均表明圆锥角膜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但是遗传因素在该疾病发生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患者的一级亲属包括患者父母、同胞和子女。一级亲属对于遗传性疾病的家族聚集性分析和多基因遗传病的遗传分析至关重要。患者一级亲属的研究可帮助解答有关遗传疾病的病因、遗传方式、诊疗、预后及预防等问题,预估患者亲属特别是子女中该病的再发风险,并对咨询者的婚姻、生育及遗传监护等予以指导。本文就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临床研究和遗传学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深入了解圆锥角膜的一级亲属人群临床表现和遗传特点,为研究圆锥角膜发生中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1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临床研究现状
1.1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中圆锥角膜的患病率圆锥角膜的发生有家族聚集现象,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中圆锥角膜的患病率。研究发现,中东地区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中圆锥角膜的患病率较高。Shneor等[9-10]、Karimian等[11]、Besharati等[12]、Awwad等[13]和Kaya等[14]研究了以色列、伊朗、黎巴嫩及土耳其等中东地区的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发现该地区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为3.6%~27.9%。Kriszt等[7]发现匈牙利地区圆锥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为7.6%。Lapeyre等[15]报道了法国地区圆锥角膜患者父母、同胞及子女中圆锥角膜的患病率分别为14%、10%、3%。Jordan等[16]和Steele等[17]报道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分别为12.4%和14.67%。Wang等[18]、Zadnik等[19]和Szczotka-Flynn等[20]报道美国地区圆锥角膜一级亲属患病率分别为3.34%、13.5%和17.8%。国内Li等[21]评估了26例患者的48位父母的角膜地形图发现父母中圆锥角膜的患病率为2.08%。以上研究表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人群患病率为2.08%~27.9%[7,9-15,17-18,21],远高于普通人群中0.138%的患病率,提示圆锥角膜一级亲属是罹患圆锥角膜的高危人群,圆锥角膜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
1.2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病理生理学目前圆锥角膜的发病机制及病理生理学特点尚不明确,研究表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也存在与圆锥角膜患者类似的病理生理学改变。Ionescu等[22]研究发现圆锥角膜一级亲属泪液中IL-1β、IL-4、IL-6、IL-10、IFN-γ和TNF-α的表达较对照组升高,这些炎症因子的过度表达提示患者一级亲属可能存在局部炎症改变,泪液生物标记物的升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Kemp等[23]]对一个圆锥角膜家系的12位家庭成员进行了总血清免疫球蛋白E(总IgE)和特异性血清免疫球蛋白E(特异性IgE)水平的测定,发现圆锥角膜患者的3个同胞总IgE和特异性IgE水平较高,表明总IgE和特异性IgE可能是指示圆锥角膜的一项免疫学指标。Regueiro等[24]通过流式细胞术对27例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角膜和结膜上皮细胞中TLR2、TLR4表达进行了检测,发现圆锥角膜亲属组角膜上皮细胞中TLR2的平均表达量以及结膜上皮细胞中TLR2、TLR4的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该研究认为角膜和结膜上皮细胞中TLR2和TLR4过表达可以监测地形图正常的一级亲属的早期眼部变化。Ozgurhan等[25]采用角膜共聚焦显微镜观察了53名地形图正常的圆锥角膜亲属的角膜显微结构,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地形图正常的亲属组前后表面角膜细胞密度较低、基质神经直径较高。该研究表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在典型或细微的地形特征出现之前即有圆锥角膜早期显微结构的变化。
1.3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临床表现
1.3.1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形态学改变角膜形态学变化是圆锥角膜患者的重要临床特征,研究发现一级亲属的角膜形态学也发生了相应改变。Salabert等[26]、Morrow等[27]、Gonzalez等[28]评估了圆锥角膜一级亲属地形图中的上下角膜曲率差值(inferior-superior dioptric asymmetry value, IS),角膜中央曲率(central keratometry, CK)和双眼角膜中央曲率的差值。Salabert等[26]研究发现,除了CK外,圆锥角膜亲属组的IS值和双眼角膜中央曲率的差值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orrow等[27]和Gonzalez等[28]的研究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亲属的地形图上述量化指标表现异常。Wang等[18]、Li等[29]分析了美国地区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的角膜地形图,发现没有圆锥角膜临床体征的圆锥角膜亲属组CK、IS、KISA%均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发生圆锥角膜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存在异常角膜地形图的亲属可能是亚临床期圆锥角膜。Besharati等[12]评估了150例圆锥患者同胞的地形图后发现,12.3%被诊断为圆锥角膜的患者同胞CK及IS相对较高。Kaya等[14]通过OrbscanⅡ对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的角膜地形图进行了研究,发现角膜中央厚度(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 CCT)、最薄点厚度(thinnest corneal thickness, TCT)、后表面高度值(posterior elevation, PE)在亲属组与对照组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Steele等[17]采用OrbscanⅡ对90例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进行了角膜地形图的筛查,结果发现45例一级亲属存在平均角膜曲率(mean keratometry, Km)、IS值或TCT中一个或多个参数的异常。Levy等[30]对圆锥角膜患者的89位一级亲属的角膜地形图进行了分析,发现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3mm区域内IS、角膜不规则散光差轴向较小角(the skewed radial axis index, SRAX)明显偏高。
Kymionis等[31]发现IS、表面非对称性指数(surface asymmetry index, SAI)、相对扇形区指数(opposite sector index, OSI)、圆锥角膜预测指数(keratoconus prediction index, KPI)、圆锥角膜概率指数(keratoconus probability index, KProb)、前表面高度(anterior elevation, AE)、PE等参数在亲属组和对照组间有显著差异。Awwad等[13]对圆锥角膜患者的183例儿童一级亲属进行了角膜地形图评估,结果发现13.7%儿童一级亲属至少有1眼KPI超过30%,21.9%儿童一级亲属至少有1眼KPI超过18.5%。Kriszt等[32]对圆锥角膜患者亲属进行了裂隙灯及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发现30.8%的圆锥角膜患者亲属有Fleischer环,14.5%的圆锥角膜患者亲属有突出的角膜神经。圆锥角膜亲属地形图参数与临床体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CCT与Fleischer环呈显著负相关,其他地形图参数与Fleischer环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些相关性结果提示圆锥角膜患者亲属角膜较薄且不对称。目前国内关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的研究并不多,Li等[21]对48例圆锥角膜患者父母的角膜地形图进行评估后发现,角膜最薄点厚度、角膜后表面高度、总偏差值(overall deviation of nor mality,Do)、最大厚度进展指数(maximum pachymetry progression indices, PPImax)和Ambrósio平均相关厚度指数(Ambrósio’s average relational thickness indices, ARTave)在圆锥角膜父母组与正常对照父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认为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表明圆锥角膜亲代拥有亚临床期圆锥角膜的特征。
Levy等[30]发现在临床上未受影响的圆锥角膜患者亲属中,J形(不对称领结形)和Jinv形(J形的镜像)比例过高。Kymionis等[31]分析了圆锥角膜家系中患者及正常亲属的角膜地形图,发现在没有圆锥角膜临床体征的亲属中,53%的人至少有一眼存在不对称领结伴无径向倾斜轴的下方陡峭或下方陡峭这两种异常模式的过度表达。这些发现补充了Levy等[30]的研究结果,支持圆锥角膜患者亲属中两种异常模式的表达。Shneor等[9]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亲属与正常对照相比,对称性领结形状合并有径向倾斜轴、非对称领结形状合并径向倾斜轴、非对称领结形状合并角膜下方曲率陡峭、非对称领结形状合并不规则散光等模式的比例显著增高。Karimian等[11]对45例圆锥角膜患者的150名一级亲属的地形图进行了分析,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亲属中最常见的角膜地形图大多数为对称型。这一发现与一般人群的报告相似。因为没有对照组,该研究并没有对这种角膜地形图模式的重要性做出进一步的阐述。以上研究表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人群中存在与圆锥角膜患者类似的角膜地形图参数及地形图模式的改变,这些改变提示圆锥角膜一级亲属可能是潜在的圆锥角膜患者。
1.3.2一级亲属生物力学改变研究表明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人群的生物力学特点与正常人群存在差异。Kara等[33]使用眼反应分析仪(ocular response analyzer, ORA)评估30例角膜地形图正常的圆锥患者亲属的生物力学特点,得出圆锥角膜亲属的角膜迟滞性(corneal hysteresis, CH)、角膜阻力因子(corneal resistance factor, CRF)明显比对照组低。Ionescu等[34]采用ORA评估了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的生物力学特点,发现圆锥角膜亲属组中CH、CRF的平均值低于对照组,但高于圆锥角膜患者组。这说明了圆锥角膜患者一级亲属的角膜生物力学存在异常,提示圆锥角膜患者亲属存在圆锥角膜早期改变。但是来自法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圆锥角膜的一级亲属与正常人群的CH、CRF,并未发现两组的生物力学特点有任何差异[15]。因此,圆锥角膜一级亲属中是否存在生物力学改变以及圆锥角膜的生物力学特点是否受遗传因素影响并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论证。
2圆锥角膜一级亲属分子遗传学研究
目前圆锥角膜的遗传方式尚不明确,有研究发现圆锥角膜的遗传方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是伴有外显率降低及可变表现度[17,26-28,35-38]。另有其他研究认为圆锥角膜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18]。而Kriszt等[7]对散发性圆锥角膜家系进行的复杂分离分析表明,圆锥角膜是一种复杂的非孟德尔疾病。随着人们对圆锥角膜认识的加深以及疾病研究策略的转变,圆锥角膜一级亲属相关分子遗传学研究为了解圆锥角膜发生的遗传机制提供了帮助。
2.1双胞胎研究Hao等[39]通过对圆锥角膜双胞胎家系的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TUBA3D基因c.31 C>T突变是该家系的致病突变位点,进一步通过功能预测和体外细胞实验发现TUBA3D突变蛋白不稳定,并可引起人角膜基质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增高、氧化应激水平增强。随后通过多组学分析发现WNT16、CD248、COL6A2、COL4A3和ADAMTS3等基因变异可能通过影响胶原蛋白及细胞外基质蛋白的表达从而导致圆锥角膜的发生[40]。Mishra等[41]对857对双胞胎进行研究后发现PDGFRA基因附近的rs2114039位点与角膜曲率有显著相关性。
2.2以家庭为基础的研究患者一级亲属的亲缘系数是1/2,研究该人群可以帮助确定圆锥角膜致病基因并进一步了解遗传因素在圆锥角膜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Bisceglia等[42]对来自意大利南部的25个圆锥角膜家庭133名个体进行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发现在染色体区域5q32-q33、5q21.2、14q11.2、15q2.32表现出最强的连锁证据。Tyynismaa等[43]对20个芬兰圆锥角膜家系进行连锁分析,结果表明圆锥角膜的致病基因位于16q22.3-q23.1染色体区域内。Li等[44]对67个圆锥角膜同胞对家庭进行了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在4、5、9、12和14号染色体上均发现与圆锥角膜连锁的区域,进一步通过一个白人四代家系把该病致病基因定位于5q14-21,这一区域与LOX基因所在的5q23.2比较接近,提示LOX基因可能与圆锥角膜的发生有关。Bykhovskaya等[45]通过对圆锥角膜家庭进行GWAS进一步证实,LOX基因第四内含子区的rs10519694及rs2956540位点与圆锥角膜的发生有较强的相关性。但这些位点与圆锥角膜发生的相关性并未在后续的研究中得以验证,因此需要更进一步探究。Tang等[46]通过全基因组连锁分析把1个圆锥角膜家系的致病基因位点定位于5q14.3-q21.1区域,Li等[47]通过对40个白人圆锥角膜家庭进行连锁分析发现定位于该区域的钙蛋白酶抑制蛋白基因(calpastatin,CAST)rs4434401位点与圆锥角膜的发生有关。
Tang等[48]在75个圆锥角膜家庭中未发现VSX1基因R166W突变,2个个体发现H244R杂合性突变;2个个体发现L159M杂合性突变。Saee-Rad等[49]通过26个伊朗圆锥角膜家系的测序研究发现VSX1上R166W和H244R两个错义突变在有圆锥角膜体征的家庭成员中共分离,但在没有圆锥角膜体征的家庭成员中不存在此种情况,该研究结果表明R166W和H244R可能对圆锥角膜有致病影响。Chen等[38]通过对88个圆锥角膜家庭的测序研究发现了VSX1上的移码突变c.758-765delTCAACTCC(p.L253Rfs*18)。一些研究认为VSX1中其他的突变如c.715 G>C(G239R)、L268H、Q175H、D144E可能是外显率不完全或低表达的致病突变,在圆锥角膜中存在致病作用[50-53]。但也有一些研究持不同的观点。Aldave等[54]的研究在单个病例中发现了VSX1基因的错义变异p.(D144E),随后Liskova等[55]对该变异进行了Meta分析后认为VSX1基因的错义变异p.(D144E)与圆锥角膜的发生无关。另一项Meta分析也没有发现VSX1基因与圆锥角膜相关的证据[56]。以上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突变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布不同所造成的,需要进一步探讨。Li等[57]在41个白人圆锥角膜家庭中也证实了COL5A1基因rs1536482、rs7044529位点可能通过影响圆锥角膜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而参与该病的发生过程。Lin等[58]在一个南印度三代圆锥角膜家系的10个受影响的个体中发现COL5A1基因上IVS50-4 C>G剪接位点突变,提示该位点可能通过影响外显子的剪接从而导致该病的发生。
Vincent等[59]在11个圆锥角膜家系中发现ZNF469杂合子频率和致病性变化的频率增加,提示ZNF469参与圆锥角膜的发生过程。然而,随后的两项在欧洲人群中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该基因与圆锥角膜的发生无关[60-61]。另外,Davidson等[62]在11个圆锥角膜家系中也发现ZNF469基因上的罕见错义变异与这些家系圆锥角膜的发生无关。Gajecka等[63]通过对18个厄瓜多尔圆锥角膜家系多位点的连锁分析及单倍型分析将圆锥角膜发生的致病基因位点定位于13q32,深入研究发现定位于该区域DOCK9(dedicator of cytokinesis 9)基因的c.2262 A>C突变可能是其中一家系圆锥角膜发生的突变基因位点[64]。然而Karolak等[65]的研究发现DOCK9基因c.2262 A>C突变引起的DOCK9蛋白生物学特性改变可能与圆锥角膜的发生过程无关。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实DOCK9基因c.2262 A>C突变在圆锥角膜发生过程中作用。Udar等[66]在圆锥角膜家系156名未受影响的受试者中发现了SOD1基因第二内含子区7bp的缺失,进一步探究发现该缺失可降低患者体内SOD1的表达水平及活性,使得抵御氧化应激的能力减弱,从而导致圆锥角膜的发生。但在其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SOD1与圆锥角膜的相关的证据[49-50,63]。Li等[67]在70个家庭的307名受试者研究中证实了rs4954218与圆锥角膜的相关性,表明位于RAB3GAP1基因附近的SNPrs4954218是圆锥角膜潜在的易感位点。但是Rong等[56]的Meta分析发现该位点与圆锥角膜的相关性较弱。因此,RAB3GAP1基因附近的SNPrs4954218与圆锥角膜发生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Nowak等[68]在一个圆锥角膜家系的家庭成员中频繁地观察到中IL1RN基因c.214+242 C>T序列变异和SLC4A11基因c.2558+149_2558+203del54变异,表明这两个基因可能与圆锥角膜家系的病因有关。Khaled等[69]在两个圆锥角膜家系中发现了位于PPIP5K2基因磷酸酶结构域的两个新变异,以及PCSK1基因中一个潜在的功能性变异,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发现PPIP5K2在正常角膜功能和圆锥角膜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
3小结
综上所述,圆锥角膜具有重要的遗传学基础,一级亲属是罹患圆锥角膜的高危人群。研究该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地形图异常改变及分子遗传学改变可为探讨该病发病机制的中遗传作用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