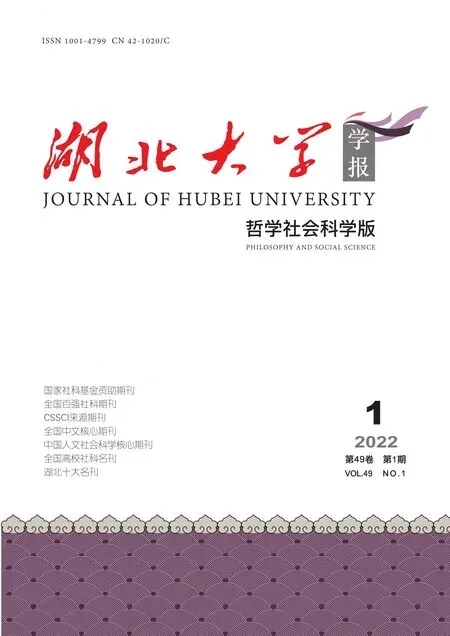《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国家观及其人民性思想
2023-01-03王代月
王代月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国家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然而关于马克思的国家观的研究处于相对边缘状态。究其根源是长期以来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的国家仅仅被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最终要走向消亡。这种从依附、从属与暂时性上理解国家的批判和否定观点似乎与我国当前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相悖。但对马克思国家观的上述传统解读有简化马克思复杂的国家思想之嫌。马克思在早期曾提出国家具有共同体的属性,能够实现人的社会存在性(Gemeinwesen)(1)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2,Berlin:Dietz Verlag,1982,S.150.马克思这种思想并没有因为后来提出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思想而消失,这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文本对国家相对独立性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在《莱茵报》时期,他在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自私与偏狭,背离了国家所应该具有的普遍性时,提出好的国家制度应该具有人民性,并从制度的制定、落实与监督三个层面分析了如何实现制度人民性的问题。这不仅确立了马克思国家观的基本价值属性,构成了马克思后来国家观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能为我国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资源和价值引导。梳理这些思想,有利于彰显马克思国家观所具有的建设性维度与时代价值。
一、国家的存在根据:从精神到人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作为编辑和主编初次走出书斋,与现实政治生活近距离接触,国家问题成为了他关注的主要对象。主导马克思这一时期国家观的是被青年黑格尔派改造过的黑格尔主义理性国家观。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集中论述了他的国家观。国家是自由意志经历抽象法、道德到伦理的发展产物,融合了古典政治对国家首要地位的强调和现代社会对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体特殊性和国家普遍性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构成了“具体自由的现实”(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0页。。对于个体特殊性而言,唯有进入到理性国家中,以普遍性为自己的实体性根据,个体才能获得存在的根据。“特殊性的原则,正是随着它自为地发展为整体而推移到普遍性,并且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达到它的真理以及它的肯定现实性所应有的权利”(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1页。。而对于国家普遍性本身而言,也需要借助个体特殊性才能在思维中获得定在,得以实现。“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3页。。唯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都得到了发展和实现,国家才能成为一个肢体健全、真正组织良好的有机体国家。
黑格尔的国家观试图沟通特殊性与普遍性这样两个不同的原则,但在他的论述中常常存在着普遍性是主,特殊性为辅的现象,特殊性似乎主要表现为一种主观的爱国情绪,对于普遍性只在于接受、自觉地希求,并将其规定为自己的伦理性根据,因此是被动的。特别是在世界历史部分,黑格尔将理性的国家置于自然状态之中,国家与国家为了各自的私利和荣誉而战。为了在国家中实现自己的伦理普遍性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个体特殊性应该将牺牲生命视为至上的荣耀。这与黑格尔多次对个体特殊性权利的肯定相矛盾。世界历史的背后是精神,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精神的自我异化和复归。“由于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而在精神中理性的自为存在是知识,所以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这种发展就是普遍精神的解释和实现”(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2页。。个体特殊性在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仅仅是工具和手段。
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但他们更加强调个体特殊性在国家中的地位,从人的角度对国家进行了新的解读。在他们看来,与特殊性相对立,并以特殊性为工具和手段的世界历史,是神在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他们将黑格尔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由精神置换为人。对于费尔巴哈,人是作为类存在的人,而对于鲍威尔,人则是自我意识。由此,国家理性的背后不再是脱离人的精神,而是人本身。例如,在《改造哲学的必要性》(1842)中,费尔巴哈提出“[真正的]国家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真实的、完全的、神化的人”(6)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8页。。鲍威尔1841年在《基督教国家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明确地宣称,国家“只有当被把握为自由的自我意识之普遍性的客观存在时,方能被理解”(7)丹尼尔·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陈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6页。。卢格在1842年的《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的时代》中通过重新解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7节的内容,强调“自我意识是国家的实存,国家的本质不仅是目的,也是自我意识活动的产物”(8)Arnold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Erster Artikel”,Die Hegelsche Linke,Leipzig: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1985,S.448.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潮流的引导者,他后来在《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中大胆地提出了民主主义的口号,“德意志世界,为了葬送当前,保障未来,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意识,在所有领域都将自由人作为原则,并将人民提升为目标,一句话,就是把自由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Arnold Ruge,“Vorwort.Eine Selbstkritik des Liberalismus.Der vorige Jahrgang”,Die Hegelsche Linke,S.573)。。国家作为自我意识的产物,是对黑格尔将国家规定为精神实体产物的颠倒。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理性精神的现实化,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肢体与身体的关系,每一个公民都是和国家“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国家也应该平等对待他的每一个成员,这样国家才能成为“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7页。,普遍性构成了国家的本质规定性。但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马克思同样将黑格尔的精神置换为人,提出要以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强调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出发来阐明国家”(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6页。,认为以人的眼光来看待国家是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页。。虽然马克思此时并没有赋予人科学的生产关系内涵,但根据马克思《莱茵报》政论文章中所关注的群体,此处的人并非停留于个体特殊性,只知道追求私人利益的特权者,而是以贫民为主体具有普遍性的人民。
二、国家制度的价值旨归是人民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制度是“国家的机体”,构成了国家的基础(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6页。。国家治理需要借助国家制度来实现,国家治理的效能又反映了国家制度的优劣。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从新闻出版自由的讨论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观察到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和冲突,以及特殊利益不惜牺牲人、绑架国家的现实。他在对特殊利益的胆大妄为和毫无顾忌进行描述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国家制度的价值旨归是人民的思想。
首先,国家制度需要妥善处理好与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根据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论述,近代政治哲学实现了由义务向权利的转变。自然权利构成了近代契约论思想家的理论出发点,在他们看来,人天生就具有一系列自然权利,国家制度构建的合理性根据是人们对自然权利的让渡。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存构成了人最首要的自然权利,但在自然状态中,人性的恶劣、人与人相互为敌的状态并不能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因此在理性指导下,人们将除了生命权之外的其他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由国家来维护和实现人的各种权利。洛克认为人们之所以组成政府,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德国古典哲学颠倒了近代社会契约论对国家与私人利益关系的论证。康德将法哲学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对人的外在规范,区别于道德对人的内在规范(14)参见吴晓明、刘日明:《近代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纯粹实践理性源于作为理性存在物的自我立法,它超越于一切感性之上,表现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命令。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法哲学,承认了人作为目的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作为社会成员自我选择的自由、作为臣民与他人在法律前的平等和作为共同体成员自己给自己立法的独立。国家是“由所有生活在一个法律联合体中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15)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6页。共同体,自由、平等和独立构成了国家建立的先验论基础。康德实现了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转向,即国家制度和法的根据不在因果必然性的现象界,而在理性的自我立法,在对人格的尊重。黑格尔虽然提出伦理区别于康德的道德,认为人的自由在伦理世界才能实现,然而他同样延续了康德对私人利益与法哲学关系的处理,认为制度的根源在于精神。精神在自身中组织起来,在自身中设定差别,通过差别完成它的圆圈运动。国家制度作为精神的客观性环节,不应该成为维护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否则就取消了国家制度内在的理性根据以及个人进入国家的客观必要性。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国家制度的基本规定,认为国家制度和法代表着事物的理性本身,是自由的定在,具有普遍性。而特殊利益自私自利,“渺小、卑鄙和肮脏”,“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261页。。马克思从国家制度与特殊利益的本质差异出发,对现实中所存在的特殊利益绑架国家制度和立法的做法进行了批判(17)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由于还停留于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国家观之中,缺乏对国家的物质根源与阶级属性的理性认识。但从他对贵族和贫民两种习惯权利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要批判的不是一般的物质利益,而是特权者的私人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将国家降为特权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7页)。。
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莱茵省议会在特权者的左右下,试图修改林木管理条例,制定林木盗窃法,将拾捡枯枝、采摘野果这些中世纪贫民的习惯权利规定为违法。马克思指出,就法本身的适用对象而言,拾捡枯枝被定性为盗窃,混淆了拾捡枯枝和盗窃林木这两种不同的行为。第一是两者的意图不同。黑格尔将不法区分为三个层次:“无犯意的不法”、“欺诈”、“强制和犯罪”。在马克思看来,贫民拾捡枯枝是无犯意的,他们承认法,只是出于生存压力被迫为之。盗窃则是明知是他人的财产,却强行将其变为自己的,这已经是有意地侵犯法。第二是结果也不同。由于林木所有者所拥有的对象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林木,而不是枯枝,因此拾捡枯枝并不构成对他人所有权的侵犯。将这样两个本质不同的行为混淆起来,实质是见物不见人,胜利的是木头,牺牲的却是人。马克思将那种试图绑架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特殊利益称为“下流的唯物主义”(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页。,指出国家制度应该维护自己的普遍性,要善于与特殊利益区分开,旗帜鲜明地指出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马克思还利用《波恩笔记》中的拜物教知识,提倡就像古巴野人将他们崇拜的兔子扔入大海一样,国家制度也要克服拜物教的影响,体现出对人的尊重。
其次,国家制度需要妥善处理与人的关系,当国家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马克思认为应该维护人而不是制度。对于当时特权者制定的制度,马克思将它称为事物(die Sache),与人格(die Personen)(19)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Berlin:Dietz Verlag,1975,S.98.马克思此处用的是人格的复数形式(die Personen),体现了他对人格平等性与关系属性的强调。在德语中存在三个重要概念,在中文翻译中常常混在一起,即Mensch(人)、Person(人格)和Persönlichkeit(人格性)。其中Mensch强调人的自然性和个别性一面,人生来就是Mensch,但人生来并不就是Person,例如,在古罗马时期,奴隶就不具有人格。根据康德的区分,人格一方面是具有经验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指具有意志自由,前者以后者为根据才能实现人格的高贵。Persönlichkeit(人格性)是人格的能力,即意志自由的能力。黑格尔在延续康德区分的基础上,强调Persönlichkeit(人格性)作为抽象的自由意志,需要不断在经验世界现实化自己,要通过Person(人格)来作为概念的自由和在经验世界中的实现。相对立。在康德看来,事物是无理性的存在者,它们不是依据我们的意志,而是依据自然的意志而存在,因而它们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而人格(Personen)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具有绝对的价值,他们的本性凸显为“目的本身”(Zwecke an sich selbst)。当国家制度仅仅维护特权者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维护人民的自由和对真理的追求时,这样的国家制度就不是自由的制度,而是沦落为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普鲁士政府为了掩饰他们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反动性,故意美化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认为现实之所以不存在出版自由,并不是因为书报检查令的存在,而是因为书报检查官没有恪尽职责,保持一贯的忠诚。由此将国家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归咎于个人,以此来维持不合理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露了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Personen)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die Sache)本身,即制度。”(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9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S.98.表面上,普鲁士政府牺牲的是少数书报检查官,但实际上,它通过维护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牺牲的是人民的出版自由和对真理的追求自由。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再次批判了这种维护制度而牺牲人的做法。当现实存在的酒农贫困问题无法被否认时,官僚们不是从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找根源,而是将酒农贫困问题归结为自然原因或是酒农的个人不当行为。这些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国家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才是造成酒农贫困的根源,酒农的贫困体现了治理的贫困。因此他提倡不能因为国家制度而牺牲人,而是应该跳出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去发现酒农贫困的真实原因,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
最后,国家制度要平等地对待国家的每一位公民,特别是要保护贫民的基本生存权利。黑格尔认为人格本身就包含着权利能力,构成法的概念的基础,因此法的命令就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6页。。人格规定了所有人法权意义上的形式平等。人首先是直接的定在,他需要在有机的身体中活着,因此维持生命就成为人的权利。黑格尔所提出的紧急避难权就是对人生命权利,特别是贫民的基本生存权的承认(22)在没有出版的《法哲学原理》讲稿第127节中,黑格尔详尽地谈到了贫民的生命权。“紧急避难权(Notrecht)并不意味着侵犯另一个人的诸如此类的权利:关切只是指向一小片面包,他并没有把另一个人当作没有权利的人来对待”(Hegel,Vorlesung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Vierter Band,Von Karl-Heiz Ilting,Stuttgart-Bad 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 Verlag,1974,S.341)。。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的习惯权利,表述了与黑格尔同样的思想。贫民不管多么贫穷,他们都是国家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应该尊重他们作为国家成员的权利,平等对待他们。贫民源自中世纪的习惯权利是一种符合自然的道义权利,不应该被剥夺。贵族的习惯权利却是“动物的权利”。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基于血缘关系对作为有机体的国家进行机械的划分,它将人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贵族们处于社会的上层,凭借习惯权利,像寄生虫一样依附贫民为生;贫民则仅仅拥有劳动的双手,为贵族们辛勤劳作,供他们挥霍享受,而自己却只靠尘土为生,被沉重的劳动和食不果腹的生活最终折磨死。马克思指出这不是人类世界,而是精神的动物王国。
特权者代表着私人利益,仅仅具有特殊性规定,与国家制度的普遍性精神相悖。因此,马克思强调国家制度应该具有人民性,维护人民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谓的人民主要不在于有产者,而是贫民。这体现了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弱势人群的价值立场。
三、以人民代表制取代等级代表制
要使国家制度作为自由的客观实现,就需要将人民引入到国家制度之中。国家制度所体现的理性本身,是人民的理性。“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9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甚至以人民的参与作为制度真实性的衡量标准。。人民参与国家制度制定,不仅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实现国家治理普遍性的根本保障。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经验的观察和材料的分析,已经揭示出普鲁士所存在的国家制度是事物,这种制度见物不见人,甚至为了物而牺牲人。由于他当时没有从事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找到这种见物不见人现象的物质根源。但他通过对围绕林木盗窃法和书报检查制度所展开讨论的分析,指出特权者不论立场如何,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他们等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要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只能诉诸没有特殊利益要维护,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群体,即人民。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马克思提出要以人民代议制取代等级代议制。
等级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黑格尔根据分享普遍财富的方式和方法,将不同的人群划分为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级、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以及普遍的等级。等级之所以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是因为借助于等级,私人的利己心“同普遍物即国家结合起来”(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2页。,即通过等级这个中介,市民等级进入到国家生活中去,而国家的普遍性也借助于等级进入到市民社会。马克思发现贫民并不被包括在等级的范畴内,现实所存在的等级与黑格尔的逻辑区分并不一致。1842年的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由诸侯和上层贵族代表、骑士或下层贵族代表、城市的代表、农民和小农业主代表四个等级组成。根据参加等级委员会的条件,除了品行端正的名声、30岁的年龄资格、隶属于某个基督教会的条件外,连续十年占有土地是主要条件。这就意味着当时占人口很大比重,但不占有土地或是没有连续十年占有土地的贫民被排除在等级的范畴之外。
由贫民为主体所构成的人民,与黑格尔对等级的规定完全不同。黑格尔认为个人只有归属于某种等级,才能摆脱他的个体特殊性,通过他本身的活动、勤劳和技能,获得正直和等级荣誉,具有实体性。“不属于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6页。。与此相反,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等级,不管私有财产的多寡,都是一个标志着有产者的范畴,通过省等级会议来维护他们等级的特殊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有等级的存在,没有省的存在。由这些停留于特殊性的等级所组建的等级委员会,不具有国家理性,不仅不能使自己等级的特殊利益服从于国家的普遍利益,甚至还以等级的特殊利益对抗省和国家的利益。对于这种特殊利益对抗国家普遍利益,在政治上独立化的现象,马克思将其诊断为国家机体内部已经生病,长出了肿瘤。
而人民不同,他们是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人民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多样的概念。马克思此处吸收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资源,强调人民所具有的普遍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同情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等同于美德,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的身上,认为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就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苏联学者格列茨基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与罗伯斯庇尔具有相似性,“他们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但这种接近还不仅是在政治纲领上,而且也在其理论的、哲学的依据上”(26)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罗伯斯庇尔所谓的人民主要是贫民,是对抗资产者的希望。在《未发表的文件》一文中,他写道:“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者;为了战胜资产者,必须团结人民。必须……使人们向长裤汉付款,使长裤汉留在城市里。必须充分供应他们武器,激励并教育他们。”(27)《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Vierte Abteilung,Band 2,Berlin:Dietz Verlag,1981,S.169.
在对人民内涵的规定上,马克思同样采取了人民与资产者对立的视角,强调人民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贫民,“我们也必须让城市等级尽情发表他们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看法。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市民反对派(Bourgeois),而不是公民反对派(Citoyen)”(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5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S.157.。Bourgeois具有“有产者,资产者”的含义,Citoyen在此处被马克思用来特指贫民这个只具有公民称号的群体。19世纪初的普鲁士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除了大量传统的贫民外,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贫民。在18世纪后期,贫民构成了普鲁士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的数量急剧增长。到1846年,这个人群在普鲁士中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二(29)Wolfram Fisch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2,S.244.。他们由无主无地的农民、无主的赤贫手工徒、无主的失业仆人组成,不属于市民社会任何等级,也不受领主的保护。马克思对贫民存在状况进行了描述:“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这种一无所有的存在,使他们能够破除物的非凡魅力,保持自己的人类本能,具有对人的类本质的普遍性意识。虽然贫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但马克思依然将他们称为所有者(Eigentümer)。“‘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是一项公认的原则,而这种法理感和公平感同维护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正相对立;这些人的财产只是生命(Lebenseigenthümer)、自由(Freiheitseigenthümer)、人性(Menschheitseigenthümer)以及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des Eigenthümers von Nichts)的公民的称号”(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S.230.。贫民拥有的不是特殊的物质利益,而是使人得以成为人的规定性。Heinz Lubasz认为“在马克思的眼中,贫民几乎是人类的精华”(32)Heinz Lubasz,“Marx’s Initial Problematic:The Problem of Poverty”,Political Studies,Vol.XXIV,No.1,1976.。
通过贫民,马克思刻画了人民的形象,即没有被物所奴役和支配的人,他们的存在就具有普遍性。这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普遍性的规定相似。“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由于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是在传统社会的解体中产生的,因此Luabsz 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雏形(34)对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来源,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来自黑格尔,如对黑格尔普遍官僚等级或是贱民概念的改造;也有观点认为来自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马克思《莱茵报》中对贫民存在状况以及普遍性的规定,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规定非常相似,这表明马克思《莱茵报》中的贫民思想构成了他提出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一环。。
基于等级与人民的本质差异,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等级代表制与人民代表制对国家的不同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有机体。等级代表制将人民机械划分为不同的构成元素,割裂了国家作为有机体的存在,使国家失去了内在不同要素相互作用和转化的活力,“把人民机械地划分成几个固定的、抽象的组成部分,并且要求这些无机的、被强制确定的部分进行独立运动(这只能是抽搐运动),同样也不能实现有机运动”(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3页。。人民代表制虽然没有消除现实所存在的差别,然而这些差别不是机械地外在划分的,而是源于国家内部结构所造成和决定的,因此没有中断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活。
马克思区分了功利的理智和自由的人民智力。等级代表制遵循功利的理智,以地产为依据,所代表的是被动的、物质的、无生气的、不独立的、受到危害的东西,地产、工业和物质力量作为粗陋的要素要求实现,同国家讨价还价,限制国家的活动。人民代表制遵循人民智力,是人民自身权利的实现,维护的是人民的普遍利益,实现了国家的理念,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国家,不受到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各种粗陋要素的约束,在国家中进行活动的不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个人,而是自由的人。“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5页。。
由此,马克思认为必须限制等级代表的特殊利益,以人民代表制取代等级代表制,使自由的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只有这样,国家制度才能摆脱特殊利益的支配,体现出应该具有的普遍性和人民性。
四、人民报刊与人民性的实现
国家制度制定后,还需要贯彻和落实。这就存在着如何实现国家制度实施的公开性和普遍性,以国家制度的实施来维护人民权益的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虽然提出了官僚等级是普遍等级,但他并没有忽略官僚等级可能存在的腐化问题。在第295节中,他指出国家和被统治者存在“受主管机关及其官吏滥用职权的危害”(3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13页。,他将防范措施诉诸等级制和责任心,以及自治团体和同业公会的权能。黑格尔实际是诉诸官僚制度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马克思同样关注到危害国家和被统治者的现象,但对于具体的解决措施,他提出与黑格尔不同的见解。
黑格尔的第一个解决措施是诉诸“主管机关及其官吏的等级制和责任心”(3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13页。。但马克思通过经验观察,却发现官僚的等级制和责任心并不能解决官吏滥用职权的问题。官僚们并非如黑格尔所规定的是普遍等级,仅仅关注普遍利益,实际上,他们也存在自己和小团伙的利益。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官僚理性,而不是对被治理对象的责任心。例如,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指出在对待摩泽尔酒农贫困问题上,特里尔地政局局长、税务稽查官冯·楚卡尔马里奥审核《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报道时,援引的材料就是官方的审核意见。官方的审核意见与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答复并不一致。官方认为协会理事会存在夸大亏损的倾向。“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9页。。
马克思对官方意见与协会理事会报告的不一致进行了原因分析。首先,源于调查贫困问题官员的身份。他是政府委派的,委派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认为他是“十分内行的”、“是亲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的”(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1页。。这种带有价值色彩的评价意味着政府对这位官员的信任。而官员也是不负其信任。马克思此处用“不是存心”(41)德文原文是“Dieser Beamte ist nicht abgeneigt”(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S.308),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这句翻译为“这位官员存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1页),实际上马克思此处强调的是这个官员在他的官员理智的作用下,并不需要他有意,他所看到的世界也只是他的官员利益和官员思维所允许他看到的世界,即官僚现实。虽然这个现实可能是虚假的,甚至是颠倒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颠倒的。这个词语来表明这位官员主观上并非故意去发现申诉书与他所持的官方见解以及他以前所从事的官方活动之间的不一致,但客观上这位官员确实发现了申诉书和他所持的官方见解以及他以前所从事的官方活动的不一致。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相悖源于官员所持有的官员理智。一方面,他对官方见解深信不疑,并以官方文件中得到的确定事实为评判标准;另一方面,他必然对请愿者的意图进行怀疑,对他们抱着敌对的态度,对他们所反映的贫困现状与官方意见进行对照,一旦出现不一致,就认为请愿者所说的事实即使是昭然若揭,也只是虚构的。其次,对于酒农的贫困原因,官员通常是在管理机构的范围之外去找。这就体现了官员特有的利益立场。假如这位官员碰巧是请愿者管辖区的,贫困问题关系到他对该地区管辖效果的评价问题,因此他自然会推卸责任,否认问题存在。假如实在无法否认贫困的存在,他就会在管理机构之外的自然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去发现造成贫困的原因。他不会质疑支配他的管理原则和国家制度,因为这意味着他质疑上级的权威和理性判断力。由此,马克思就揭示了黑格尔所谓的等级制能够防止官吏滥用职权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正是因为这种等级制,造成了官官相护,形成了官僚小集团。马克思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官僚集团是国家中的同业公会,他们维护着官僚们的特殊利益,将国家作为工具来使用。
对于自治团体和同业公会在防止官吏滥用职权中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通过对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报告与官方审查意见的对比表明,靠这种自治团体并不能监督官员的行为。相反,它们的意见被官吏斥责为不合事实,官吏认为这份报告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给酒农降税,而不是反映真实的情况。
在客观原因方面,贫穷的葡萄种植者通常受教育水平不够,囿于自身的处境,无法清晰完整地反映他们的处境。作为私人的葡萄酒酿造者同样也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私人利益所蒙蔽,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由于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个体与作为整体的人民之间并不能直接等同,个人对问题的说明总带有私人的诉苦性质,因此不能将个人的呼声等同于人民的呼声。从地域上看,相对于整个省和整个邦而言,摩泽尔河沿岸只是个别的行政单位,仅仅具有私人的地位,它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衡量。
要使官员在执行制度时实现公开,不为了维护管理机制而牺牲人的利益,就需要人民进入到国家之中,使国家真实地了解现实情况。马克思通过对官员和葡萄种植者所持有的理性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囿于自身的利益,都无法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要解决上述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bürgerlich)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8页;Marx/Engels 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1,S.313.。国家治理应该把人民因素引入,由具有公共理性的自由报刊来忠实报道现实,反映民情,使国家治理不被特定人群的私人利益所左右。
自由报刊之所以能够充当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第三个因素,源于自由报刊所具有的人民性。它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表现,也是把个人同国家连接起来的纽带。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描述了自由报刊的特点:“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2页。。自由报刊因为具有人民性,所以它能够大公无私地反映真实现实,“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8页。此处马克思的表述似乎表明他是支持君主制的,但这与他1842年3月5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将君主立宪制称为“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相矛盾,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是反对君主制的。之所以出现这种不一致,可能源自当时普鲁士所存在的书报检查制度。因此研究《莱茵报》政论文章,需要区分马克思的真实意图和与书报检查制度作斗争的策略性的表述。,克服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狭隘性,具有普遍性。借助自由报刊,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的国王就能了解真实的情况,从而采取切实的措施来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由此马克思提倡要废除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满足现实对自由报刊的需要。
五、马克思国家观及其人民性思想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在《莱茵报》政论文章中,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国家制度的人民性思想,并将人民具象化为贫民,这构成了马克思后来国家制度思想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此时期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主义理性国家观的影响,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并非对黑格尔主义理性国家观亦步亦趋。在黑格尔看来,政治制度是精神的自我运动。马克思将国家制度的主体置换为作为贫民的人民,实现了国家制度向人的回归,并将人民的理性和自由规定为国家制度普遍性的保障。其二,受黑格尔主义理性国家观的影响并非全然毫无价值。黑格尔的国家观,既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社会对主体性和法权平等的强调,是自由意志实现的客观形式。马克思从这种国家观出发,建构了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价值规范,以人的自由批判作为事物的制度,以人民理性的普遍性批判特权阶级对特殊利益的放肆追逐,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并以自由为关键词构建了一个“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当时所使用的几对范畴中(45)特殊性与普遍性、事物与人(格)、特权者与人民、资产者与贫民、市民与公民。,事物与人格、资产者与贫民构成了他后来理论探索的关键范畴。事物与人格这一对范畴,被马克思发展为以生产关系为本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46)马克思在批判林木所有者对赔偿的贪得无厌时,使用了“资本”这个概念,虽然其内涵并不准确,但林木所有者所表现出来的追逐最大利益的贪婪性,与马克思后来所描写的资本逐利本性相似。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拜物教来分析这种现象,这为他后来提出三大拜物教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也证实了马克思《莱茵报》政论文章并非因为还深受抽象的理性主义影响,就毫无价值。。资产者与贫民则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马克思当时对国家制度人民性的强调,颠倒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确立了他的国家观的基本立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制度人民性,强调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创立者,国家制度要回归人民本身,成为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环节。此时马克思对国家制度与人民关系的规定还只是一种应然逻辑,而没有从国家制度与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进行分析。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成熟,马克思深入到物质生产实践,揭示出国家制度只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要实现国家制度的人民性,就需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国家政权压迫人的性质。“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科学论证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除了强调国家制度人民性的物质根源外,并没有忽略国家制度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废除旧的国家机器,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上保证了制度人民性的实现。巴黎公社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尝试,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63页。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详尽列举了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普选权,议行合一;建设廉价政府,取消公职人员的特权地位;取消面包工人的夜工,用法律严厉惩罚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等。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处理不同利益的关系。国家制度立于什么人的立场,最终国家就能够实现谁的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观察的国家制度是封建的国家制度,它所实现的必然是特权者的利益。马克思立于贫民的立场,认为国家制度应该要公平地维护人的利益。他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转向共产主义的立场,但他对国家治理的现实分析和应然规定,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与马克思在《莱茵报》政论文章所批判的现实不同,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着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4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3页。。我国的社会性质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实现了人类制度史上的彻底变革。但国家制度价值旨归上的人民性仅仅是一种应然逻辑和价值规定,它还需要在现实中贯彻落实。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着新任务和新要求,这对实现国家制度的人民性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使国家制度的人民性表现为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
其一,制度的制定需要立于人民的立场。制度一旦制定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甚至构成人生活的第二自然。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国家制度的制定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对莱茵省等级委员会通过修改贫民源于中世纪的习惯权利,将拾捡枯枝定性为盗窃实质的分析,指出国家制度为了谁的问题至关重要。我国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全方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制度的制定之中,从源头上确保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但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在现实中的存在并非毫无差异。我国目前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之外,还存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在公有制经济中的就业人数。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关系。资本有利于活跃经济,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调动其积极性,但它具有逐利本性,会为了利益牺牲人,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国家需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立于劳动者的立场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在社会弘扬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就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所指出的,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5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9页。。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健全再分配体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5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只有将人民性贯彻到制度制定的各个环节,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
其二,制度的改革创新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价值旨归。在《莱茵报》政论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它的制度,不惜以人的牺牲为代价。在我国当前,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经历了发展完善,形成了科学的制度体系。然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这就要求将国家制度的人民性通过相应的具体体制机制渗透到这些方面。一方面是创新。为了推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建设,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实践创造出具体的相关体制机制,以满足人民在新时代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全面向往,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是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制度和法规体系不断地完善,但后单位制社会所具有的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加强等,要求对某些与新的现实不相符合的具体制度进行改革,适应人民新的生活方式。通过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有条不紊地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更好地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制度,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提出了官员的理智(Beamtenverstand)这样一个概念,特指处于官僚体系中的官员对官方见解深信不疑,并以官方文件中得到的确定事实为评判标准,不相信甚至怀疑人民,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官员是封建制度下的官员,与我国当前的党员领导干部有本质不同。但马克思对官员在国家制度贯彻落实中所发挥作用的分析,提示我们应该注重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很大,但制度具有统一性,这就要求国家制度在落实的过程中,要兼顾地域差异,从而给予国家制度的实施者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这种发挥究竟是背离了国家制度的基本精神,还是落实了国家制度的基本精神,对国家制度的实施者,即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德与能的基本要求。就德而言,党员领导干部需要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将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就能而言,为了能够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抓住战略机遇期,妥善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折不扣地将制度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
其四,加强网络舆论环境的治理,使人民的利益需求更好地得到表达。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提出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应该有第三个因素的参与,唯有这样,人民的真实存在处境与利益需求才能被治理者了解。在我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通过全过程民主的制度架构,能够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在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发达的时代,人民除了可以利用传统的信访制度等渠道之外,网络构成了人民表达自己利益需求更为直接、便利和快捷的渠道。但在网络空间中,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特别是在当前,存在着资本介入到网络空间,试图引导舆论发展,推动舆论娱乐化、消费主义化等不良倾向。这阻碍了人民对网络渠道的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5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98页。通过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才能使人民通过网络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
综上所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国家制度人民性思想,在承认国家制度相对于社会所具有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强调人民理性与特权等级理智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根本分歧,提出应该将人民性贯彻到国家制度制定和落实的方方面面。这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国家治理观所具有的建设性价值,在国家制度价值旨归的人民至上性以及实现和保障制度人民性的具体对策上,对于我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