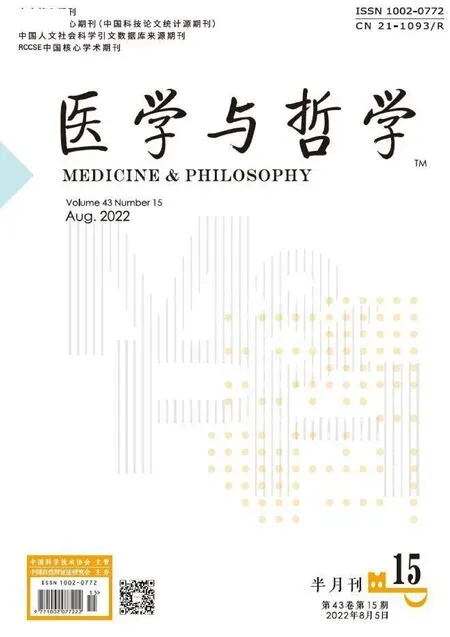控烟干预的伦理框架:共识和争议*
2023-01-02许浦生
萧 鲲 许浦生
吸烟,即烟草依赖,本质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高成瘾性疾病,可引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冠心病、恶性肿瘤等多种烟草依赖相关性疾病,对健康危害巨大。就健康而言,控烟干预可令吸烟者显著获益,但是,由于烟草依赖的发生、发展包含着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控烟干预中的伦理问题不能被忽略;由于新型烟草制品的日益流行、对特殊人群戒烟治疗的日趋细化和控烟研究的日渐深入,控烟干预中的伦理问题出现了争议,控烟干预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控烟专家的关注和思考。
1 控烟干预的伦理共识
1.1 控烟干预的基本伦理框架
烟草依赖对人体健康危害巨大,大量研究证实,烟草使用导致的死亡是世界上最可预防的单一死因,通过控烟干预,可降低烟草依赖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因此,无论是对于临床医学(个体)或是公共卫生(群体),控烟干预均符合生物伦理学四原则[1-2]中的有利原则,亦因此尽管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3]下不同国家/地区的控烟干预策略有所不同,但在“使烟草使用和接触烟草烟雾持续大幅度下降,从而保护当代和后代免受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的一致目标下,有利原则形成了控烟干预伦理共识的基础。
美国学者Fox[4]认为,控烟干预应具备伦理依据,从而保证公众中的吸烟者、非吸烟者或潜在吸烟者都能对控烟干预措施支持和认同,故而在有利、尊重自主、不伤害和公正的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对控烟干预的伦理框架进行了丰富和解释,包括:(1)有利原则,为增进他人利益而行动的义务,是控烟干预伦理原则的共识和基础,优先于其他的伦理原则;(2)不伤害原则,为保护他人利益不被减损的义务,指行动者在涉及他人利益的行动中不得造成他人利益的减损,如增加烟草税和提高烟草价格虽然可能导致烟草消费需求的下降[5],但同时应考虑可能导致极低收入吸烟者放弃生活必需品来满足烟瘾的风险[6-7];(3)公正原则,指根据一个人的义务或应得而给予公平、平等和恰当的对待,即应考虑到控烟干预措施对不同特征人群的影响的差异,并尽可能限制这种差异的程度,如应保障低收入国家的国民、穷人和未成年人能平等、公正地获得充足的烟草依赖危害的信息[8],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4)尊重自主原则,指行动者尊崇他人、视他人为一具有自身目的的利益主体的义务,即尊重他人具有不受控制影响的权利;(5)透明度原则,并非指对吸烟者隐私的公开,而是指控烟干预措施中的利益关系应该透明化,如与戒烟药物生产企业的关系,从而保障独立、公正的立场;(6)真实性原则,既是指控烟干预的措施需建立在客观的、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也是指关于烟草依赖或控烟干预的相关科学证据应全面地、而非选择性地公布,从而保证控烟干预措施的公信力。
当然,上述的伦理框架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例如,未成年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可能由于自主行为能力不足、部分吸烟者可能没有充分地接受到正确的相关信息、部分吸烟者可能存在特殊生理状态、遗传倾向[9-10]或其他物质依赖,而不能完全意识或抵抗烟草依赖所导致的伤害。因此,针对三种特殊人群的控烟干预伦理框架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调整。
1.2 妊娠期吸烟者的控烟干预伦理框架
妊娠期吸烟者的特殊性在于其伦理框架既需要针对吸烟者,亦需要关注尚未出生的婴儿,因此其制定更为细致、具体和全面。在有利原则方面,既需要考虑控烟措施对于妊娠是否有效[11],亦需要考虑控烟措施是否能激励吸烟者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妊娠妇女是否对干预方式感兴趣,如有研究发现[12],不同类型的控烟干预措施对妊娠吸烟者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而与婴儿和怀孕相关的干预措施效果可能最为迎合妊娠吸烟者的喜好。在尊重自主原则方面,需注意对妊娠吸烟者隐私的尊重和保护,而且应以详尽、完整、客观、清晰的方式进行表达,避免吸烟者因为“虚假”的信息进行戒烟而使控烟干预措施的公信力受损的同时,以激发内在动机[13]为目标进行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戒烟行为的持续性和自主性[14]。在不伤害原则方面,需要注意避免“污名化”,否则可能导致戒烟意愿降低,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和自我效能较低的吸烟者[15]。在公正原则方面,需要在增加对妊娠吸烟者关注的同时,注意避免对妊娠非吸烟者的忽略。
1.3 未成年或青少年吸烟者的控烟干预伦理框架
未成年或青少年吸烟者的特殊性在于该群体往往被视为不完全自主行为能力者,而且其心理状态和成年人也有较大区别[16],因此既需要顾及到他们对控烟干预措施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对其进行控烟干预措施前需要得到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同时亦要考虑到戒烟干预措施是否会导致他们受到父母、监护人、师长的惩罚和责备,或令他们为了取悦父母或监护人而被迫参与戒烟干预治疗[17],故而其控烟干预伦理框架强调“确保保密”和“保护异议权”[18]。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父母的价值观可能与未成年吸烟者的价值观并不一致,但法律上父母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主要保护者,因此有观点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权衡“青少年的保密和隐私”与“父母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1.4 医务人员的控烟干预伦理框架
医务人员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通过自身行动来维护、宣扬其健康价值观的伦理责任。在伦理上,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在职能活动方面合乎伦理规范,还需要对人类健康文明具备责任精神。作为健康信息的充分知情者,医务人员对烟草控制“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态度可直接影响人们对烟草控制的信度和力度[19],因此对于医务人员,其伦理框架更为宽广和严格,除了基本的伦理框架之外,还包括自身不吸烟、督促同事戒烟、帮助吸烟患者戒烟、倡导无烟环境、分享戒烟经验和推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obacco Control,FCTC)[20]等,亦即我国王辰院士所提出“戒烟,医者先行”的理念含义。
2 控烟干预的伦理争议
虽然国际上医学界、科学界以及广大公众均广泛支持减少烟害的政策,而且在生命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人们对控烟干预的伦理框架有了基本的共识,但随着新型烟草制品的日益流行、对特殊人群戒烟治疗的日趋细化和控烟研究的日渐深入,控烟干预中的伦理问题出现了争议。
2.1 关于电子烟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争议
电子烟分为“加热型烟草制品”(heated tobacco products,HTPs)和“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ENDS),由于HTPs 未广泛流行,因此本文中电子烟特指后者,为一种模仿传统卷烟外观、以电池为电源、通过加热雾化手段、向呼吸系统传送尼古丁的装置。关于电子烟的伦理争议主要为电子烟是否应该被严格监管。
推广使用电子烟的支持者强调,虽然阻止青少年群体使用电子烟毋庸置疑,但即使要对电子烟进行监管,其强度不应比危害更大的燃烧卷烟更为严格[21],甚至应将“电子烟可用性”(e-cigarette availability,ECA)作为一项烟草减害战略,通过让吸烟者清楚知晓电子烟比卷烟减害,并确保他们能方便地获得电子烟,从而减少烟草依赖危害[22]。其主要根据是控烟干预框架中的真实性原则和尊重自主原则,即基于真实性原则,控烟干预政策告知公众电子烟同样有害的同时,亦应如实告知公众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少于燃烧卷烟,因为如果刻意隐瞒、歪曲电子烟的作用,会让公共卫生机构丧失公信力,使公众质疑甚至无视其发布的其他风险信息,进而造成重大公共卫生危害;而基于尊重自主原则,控烟干预政策应尊重个体根据自身意愿做出知情决策的权利,因为吸烟者个人在健康方面拥有最高自决权,所以戒烟医生在伦理上,有义务为吸烟者提供电子烟减害信息,并在充分地基于现有证据对患者进行风险评估、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尊重吸烟者根据自身价值观和偏好自愿做出是否将电子烟作为一种减少烟害的治疗方式[23],而且由于英国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使用ENDS 的人中,不足1%的人是从不吸烟者,即ENDS 的使用者基本上均是现在吸烟者[24],因此电子烟支持者认为,总的来说,现在吸烟者通过使用电子烟而减少吸烟危害所获得的公共健康收益,可能远高于不吸烟者使用电子烟而造成的公共健康的损害。
以上的观点被激烈反驳和争论,其反对者认为,在尊重吸烟者自主决定权的同时,应该维护医生的特殊干涉权,因为吸烟者的价值观和医生的价值观可能是不同的,医生的立场可能并不为吸烟者所接受,当吸烟者存在烟草依赖的时候,其自主行为已经被影响,不应再被视为具有完全自主行为能力,因此医生行使特殊干涉权并不违反伦理[21]。此外,虽然电子烟对吸烟者个体的危害的确少于燃烧卷烟,但电子烟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戒烟方法[25];而且如果吸烟者要通过电子烟减少吸烟危害,前提是完全改用电子烟,而非燃烧卷烟和电子烟两者兼用[26-27]。更重要的是,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但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关于电子烟的控烟干预伦理框架不应该只考虑对吸烟者的尊重自主原则,亦要考虑对公众健康的不伤害原则,毕竟,即使ENDS 对长期健康风险最后被证实只有燃烧卷烟的10%,但如果相关政策令使用电子烟的人数基数急剧增大,那么ENDS 造成的疾病负担仍将十分巨大[28]。
2.2 关于二手烟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争议
二手烟(second-hand smoke,SHS),是指由卷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及由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所形成的混合烟雾[29],已被证实对人体有害,这是控烟干预措施制定的依据之一。因此,目前关于SHS 的控烟干预措施伦理争议主要并非在于“是否应该因SHS 而在室内禁烟”,而在于“因SHS 而在室外禁烟的标准是否过于严格”。
室外控烟干预措施支持者的主要证据是室外禁烟可减少垃圾和火灾[30],而且有研究证实健康年轻人急性暴露于环境烟草烟雾(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ETS)可导致早期动脉损伤[31],6 小时ETS 暴露即可通过降低人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而增加个体患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32],而反对者则认为针对SHS 而制定过度严格的室外控烟干预措施可能并不符合伦理:首先,过度严格而且缺乏依据的室外控烟政策,不但不会获得公众对控烟政策的支持,反而会深远地影响公共卫生利益[33];其次,虽然一些研究表明即使是短暂的、急性的暴露于SHS 也能引起暴露于它的人可测量的生理变化[31],但在开放的室外环境中短暂接触SHS 的情况与研究中所涉及的密闭室内环境中接触的情况完全不同,而抛开强度、一致性、特异性、时间性、生物梯度、生物合理性、连贯性等来谈ETS 的危害并不合理[34-35],因此上述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与室内ETS 不同,除非吸烟者在靠近室内区域的入口,或拥挤、有遮挡的区域吸烟,否则室外ETS 似乎不会增加SHS 的暴露[36],只有在暴露持续且显著的情况下,如在拥挤的观众体育场,才有理由禁止在户外吸烟[33]。
2.3 关于住院患者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争议
戒烟对吸烟者的健康有好处,对于因疾病住院治疗的吸烟者来说尤为如此,研究证实,即使是暂时的禁烟也可以改善吸烟者的疾病预后和缩短吸烟者的住院时间。与不吸烟者相比,围手术期和术后吸烟与更差的呼吸和全身结果相关[37];但另有调查发现,即使给予吸烟的住院患者规范劝诫、疾病相关健康教育、住院期间及出院后免费使用戒烟药物承诺,仍有近1/3 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而入院的吸烟者拒绝戒烟治疗[38]。因此,目前关于住院患者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争议是“允许或帮助患者到户外吸烟区吸烟”还是“常规引入戒烟治疗而不考虑患者意愿”。
有部分意见认为,在医疗卫生机构有能力对烟草依赖和尼古丁戒断进行药物/非药物治疗的前提下,应该将戒烟治疗作为住院治疗的一个必要部分[38],因为在一个公共资助的医疗体系中,患者需要承担避免不必要的使自身病情恶化和复杂化的伦理义务,而且帮助患者到吸烟区吸烟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短缺,以致忽略其他患者,亦会令医务人员接触到患者吸烟所产生的ETS,对医务人员的健康产生损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伦理上,对患者自主权的尊重应高于强制禁烟或短期戒烟所产生的获益,认为医务人员更重要的作用是利用吸烟者因患病住院这一“特殊时机”,在真实性原则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增加其戒烟意愿,而非忽略对患者的尊重而强行禁止吸烟,在不伤害原则、公平原则的理念下,医疗卫生机构亦有着制定“吸烟患者指导方针”以保障医务人员、非吸烟患者和吸烟患者利益的伦理责任,如倡议患者不要在医疗查房期间离开病房到吸烟区吸烟、禁止医务人员以强制出院的方式威胁患者不得吸烟。
3 结语
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却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其产生和维持有着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参与。关于控烟干预的伦理问题,目前既有已达成的共识,亦存在不少的争议,其中,共识的基本点是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自主原则、透明度原则和真实性原则的伦理框架,而争议的矛盾点是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和公共健康的获益的伦理权衡,前者强调的是个人自主权的不容退让,后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人类群体的责任。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共识的形成,是由于烟草危害的循证证据已被广泛承认,争议的产生,是由于部分控烟干预措施仍缺乏充足的循证医学研究支撑,提示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认识的深入,伦理争议可能会逐渐达成新的共识,但也可能产生新的争议;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处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时,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要求必然亦有所不同,那么,目前的控烟干预措施伦理框架是否适用于我国?在大数据时代和精准治疗的背景下,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要求是否需进一步细化?尚需开展什么研究以探讨我国控烟干预措施的伦理要求?这些可能是我国控烟政策的制定、控烟工作的开展和控烟研究的设计的日后方向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