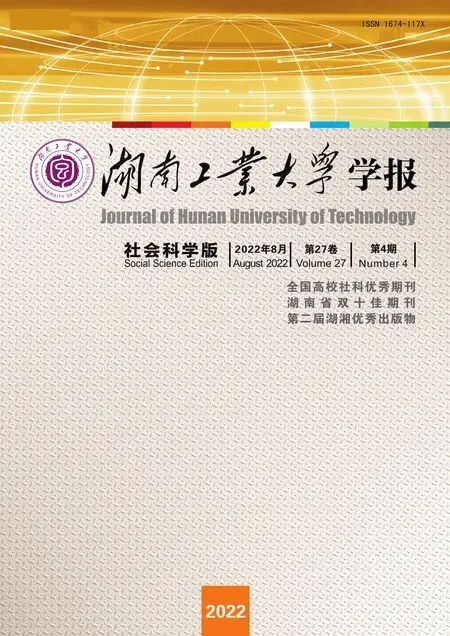《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身体性的二律背反
2022-12-31王如
王 如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残雪的《吕芳诗小姐》在身体性上具有同一性。两部作品都包含丰富的身体书写,并都把身体和精神共同作为生命的表达。在《达洛卫夫人》中,生命处在理想状态时,身体与精神统一、感性与理性兼具。当身心分离或感性与理性失衡时,生命处于困境。伍尔夫通过突出身体中新鲜活泼的感受性,使人的生命脱离抽象观念的桎梏,恢复生命活力。《吕芳诗小姐》的创作机制中就包含身体性,这个机制的内涵就是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图形就是残雪实验小说的哲学图型,它是全部残雪小说的根和底蕴。”[1]14对于残雪来说,人与自然同体,人是自然最高级的器官,灵肉之间的张力不仅形成人性图案,也形成生命与宇宙图案。其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描写、背景、对话、事件都指向这幅图案,它通过表演“肉体性的想象力”,展现灵与肉的抗衡与合一[1]12-17。
与此同时,《达洛卫夫人》和《吕芳诗小姐》中表现的身体性也呈现出差异。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两部作品中身体性诸多要素的性质与关系都是相互矛盾的。《达洛卫夫人》中的身体表现为功能化的身体,身体的性别、感受、结构等要素最终服务于身体的风格化转化,以实现和精神的和谐共生。《吕芳诗小姐》中的身体更接近于尼采意义上的身体——表达生命存在的场所,展开强力意志的场域,“身体和生命没有根本的差异”[2]。在残雪看来,身体的特性在于要展开活动,身体活动意味着生命力量。
可见,《达洛卫夫人》和《吕芳诗小姐》两部作品在身体性上呈现出同一与差异并存的局面。目前学界对伍尔夫与残雪小说的研究,均有从意识流写作、精神研究向身体研究转向的趋势,探索两位作家小说中的身体美学、身体政治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同为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家的伍尔夫和残雪,有关两人创作、思想之间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早已出现,但其多从宏观、整体角度出发,尚未发现有研究者对两位小说家的作品进行微观的比较研究,更没有研究者对《达洛卫夫人》和《吕芳诗小姐》中呈现的身体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身体性是两位小说家思考人性和生命的一个重要维度,与其创作意图和思想本质密切相关。探究二者身体性之间的关系,跨越中西身心思想的疆界看待身体的现代性问题,并从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认知伍尔夫和残雪小说中的生命书写与人性思考。
一、身体性的自然背反:性别与性欲
身体性在自然层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不平衡,是现代身体性的基础问题。身体从生物构造上区分男女,性别就成为了身体的自然事实。与性别不同,性别意识不仅被视为一种自然事实,存在性别的差异;它也被视为以性别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塑造,强调男性、女性的区别,并发展出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在这两种性别意识中,以身体和性别差异为前提的性欲,分别被看作是一种自然本原的存在和一种功能性的存在。针对身体间的不平衡问题,伍尔夫和残雪都从本能的生命力量中寻求解答,两人均试图重建现代性欲;不同的是,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选择保留性别,在《吕芳诗小姐》中残雪尝试取消性别。
《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保留了性别事实,小说中性别与性别意识呈现无法分离的状态,这也成为了伍尔夫解决身体问题的起点。尽管她在小说中立场鲜明地批判了性别意识对女性的抑制,例如女性受传统家庭观的影响,成为生育机器和家庭附属品,等等;但在解决现代性身体问题上,伍尔夫也看到了性别意识和性别事实带来的问题。她在随笔《女性小说家》中曾论及,女性作家用男性的化名,也许不仅仅为了获得公正的评论,还可能是为了要在写作时摆脱女性的自我意识[3]315。这表明,伍尔夫不仅关注女性意识的政治性问题,更承认并关注性别意识与性别事实之间的关系。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尝试取消性别事实,布鲁顿夫人就被设定为一个在生理事实上比较模糊的人。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刚强、威武、营养充足,家世显赫,直率而冲动,感情奔放而缺乏自省的智力”[4]104,但布鲁顿夫人几乎无意识地就把自己的意识归咎于作为女人的天性上。不会写信的事实,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弱女子,因为在她看来,要能擅长写信,就必须拥有感性和丰盈的女性气质。除了天性以外,伍尔夫笔下的人物常常无法为自己之所是找到根源性的解释。更甚之,当布鲁顿夫人在与男宾谈论政治时随口问出的“克拉丽莎好吗”[4]102,都表露着“她承认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4]102,“骨子里对女人怀有更深的情谊”[4]102。也就是说,性别事实自身不仅是无法改变的存在,而且与性别对立和联结同时存在。《达洛卫夫人》以此为身体性问题的基本前提,小说中性别事实决定了男女两种意识的特质,这两种特质并不总是通过突显角色的社会性别而来,而是作为两种相当深刻的天性,与原初的身体性质相关。
《吕芳诗小姐》中,性别事实被取消了,残雪以此表现了一种充满张力的现代身体关系。残雪首先有意隐匿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设定上的性别差异,她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进行生理特征或者外在表征上的细节描写,不像伍尔夫的小说那样关注男女生理特征、着装打扮、行为风格的性别差异。小说中,有且仅有一对幸福生活的夫妻,那就是生活在理性之境的小花父母。残雪明示这种幸福而严肃的爱情,“属于一个旧时代”[5]237。既然她将现代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建立在无性别事实区分之上,那么小说主人公吕芳诗的“大众情人”身份也就顺理成章了。吕芳诗作为妓女,她属于男人,也属于女人。残雪认为,在性别事实上,现代人就处于平等而无序的相对关系中。残雪在表现男女关系时,常常展示他们之间的性欲,而不提及任何浪漫的要素;男女之间只有激情,没有情感。男女交合的场景,往往是“并没有性的冲动,只有一种没来由的激情。两个身体紧紧地缠在一起,汗水交流,痛苦不堪,内心却无比振奋”[5]6。有时这一场景更被描绘成一幅血淋淋的与豹子发生性交的场景。这种由激情与力量驱动的性欲,在剥离情欲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取消情欲的源头——性别区分。残雪小说中对性欲充满激情、力量且粗俗的描写,从身体层面上展现了现代性中涌动的权力与激情。
两部小说中性别事实之所以都值得探讨,在于它们均承认了一种前提,即性别与不同的身体内驱力的形成有关。身体中存在一种内驱力,从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讲就是“力比多 ”(libido)。“力比多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6]也就是说,内驱力作为一种身体本能,是一种为完成其目的而呈现的能量和驱动力。这种内驱力在身体中处于流动的过程,它会以紧张、舒缓、断裂、平稳等变化的形式得到释放。在释放过程中带来的欣快感或力量感,会服务于个体自我感的建立。两部作品对此有不同的表现。
《达洛卫夫人》中的身体内驱力,是一种普遍、精微、多样的无性类性欲,或者说无性愉悦,并具有审美特性,结合了梅洛庞蒂之“普遍愉悦”和康德之“审美愉悦”的主要特征,其促成了男女有差异的风格化呈现。在这里,无性愉悦服务于个体感知,并使得个体自我风格化。小说中,呼吸、端坐、平躺、伸展、漫步、饮食、打扮中微妙的感受都是被关注的对象,它们传递出一种片刻的愉悦放纵。正如小说开篇,克拉丽莎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她感到“多美好!多痛快!就像以前在布尔顿的时候”[4]1。这种鲜活的愉悦感并不会因为普遍而变得平淡,它们一次次唤醒身体意识。“在吃饭、呼吸、感知、移动中,身体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超越了自身。”[7]这样遍在的身体感受,是一种现代的生命力量,其使得身体在周遭世界中逐渐风格化。其小说中诸多人物的主体成长都在这种风格化情境中进行的,并展现出审美愉悦性。在鲜花店里,达洛卫夫人沉醉于玫瑰的芬芳、花丛的斑斓,恍惚于报春花和小飞蛾的灵动,这些感受“使她感到超凡脱俗[4]11,并实现一种升华。小说中,伊丽莎白的自我风格化也伴随着审美特性。在达洛卫夫人宴会上,伊丽莎白穿着浅红色上衣,在父亲见证中完成了由孩子气向漂亮、冷静、可爱气质的转变。要强调的是,克拉丽莎和伊丽莎白的审美风格化又都是女性的天性使然,缺乏这种天性的理查德就对审美毫无建树。相反,他基于男性化的单纯天性和一股韧劲,形成了实干、务实的风格。在伍尔夫看来,身体中的内驱力是现代人愉悦和审美的起点,而作为天性的性别,比之性别意识,其对个体风格化的转化之影响是根本性的。
不同于《达洛卫夫人》,《吕芳诗小姐》中身体内驱力与自我风格化不存在联系,即身体性与审美性之间不存在联系,它只与生命力相关。残雪将身体内驱力表现为单一的、强烈的性欲激情。生命之流就存在于性欲中,性欲是生命流动的源动力。在小说的权力关系中,妓女的身份是居于最上位的,高于商人、知识分子。原因在于,妓女被认为是难得的有活力的女人,这一活力的来源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妓女强大的、不竭的性欲。在这里,性欲的强弱就是生命力的强弱。也正因此,小说中的人们才会视追寻吕芳诗为追求生活的意义;人们回忆与其的性场景时,会令幸福感充满全身;与其“交合”,意味着生命的相互联结。小说中,人物性关系的常态是单个个体与多个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总有一些对象是隐没的、迷踪的。因此,整个小说中的人物以这种方式结为一个若隐若现的整体。每个人都以满足性欲为目的,寻觅着其他人。作为性欲的象征,生命力最强的吕芳诗联结着所有人。从这个角度看,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人际间的疏离、冷漠,都与性欲衰竭有关。在残雪看来,真正能使得性欲成为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不是沦为一种享乐主义的是反思性的身体意识。小说中,在妓院“红楼”工作的人,都在“贫民窟”有房子,嫖客也会无意间来到这个鬼魅般的居所,赤裸裸地接受别人的评判、驱逐和惩罚,此后才良心稍显安定。这便是一种内在反思性意识对自身放纵性欲的谴责,它可以理解为在全身关注于自己的身体体验时形成的身体意识[8]。它的产生,意味着身体在深处寻求一种优化的经验感受,它是冲动的性欲激流下的一股潜流,二者的合力指向生命之流的方向。
伍尔夫认为,性别事实根本上不能取消,因为性别在身体层面上的区分与个体自我风格化的联系是根本性的,而以无性愉悦取代性欲,能更好地实现个体对自己的接纳,促成身体审美化。也因为性驱动力中缺乏人与人的相互吸引,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残雪取消了性别事实的区分。她强调的是一种无情欲、纯粹作为一种驱动力的性欲,并使其成为生命性的表现,为个体的生活提供方向,作为群体关系的深层纽带。在关于身体的驱动力上,两人相互矛盾地取消或重建了性别与性欲。伍尔夫通过保留性别,重建性欲,实现了身体审美化;残雪通过取消性别,保留性欲,实现了身体生命化。如此,在自然意义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身体性有差异地并存。
二、身体性的观念背反:个体性与普遍性
关于身体的观念性问题,本质上是身心问题。在身体的观念层面上,身体意识更直接、显见地对身体施加影响。在现代性语境中,身体的整体处境在于其受到抽象观念的宰制,被迫与具体处境中的感性需求分离。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逐渐形成一种理念化、心灵化的普遍性,然而人始终以身体感知作为生存的基础,不可能失去身体意识上的差异,身体必须保持其个体性。面对这一问题,伍尔夫试图取消身体的抽象普遍性,重建身体的个体性;残雪则试图取消身体个体性,重建一种生命层次的普遍性。
《达洛卫夫人》中的身体书写,将人物可察觉的身体过程和相关的内心体验交织,以人物身体在情境中的具体特征来抵制使身体抽象化、普遍化的规范。伍尔夫对于人物习惯性姿态的刻画,展现了身体内的生命过程与依赖于外部事物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小说展现了布雷德肖夫人的身体习惯在社会秩序之中发生的挣扎与转变。年轻时候的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4]96,思维和行动都表现得十分机敏;成为贵妇人之后,在许多场合“应付裕如,礼数周全”[4]96。一方面,身体习惯展现着身体的自我风格化与审美化;另一方面,身体习惯又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习惯是社会的庞大稳定节动轮,是社会的最可贵的保守势力”[9]。尽管社交规范逐渐主宰了身体意识,但它依旧无法保证稳定的身体秩序,布雷德肖夫人时不时也会“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4]97,表现出呆板与不安、支吾与困惑。在这里,布雷德肖夫人的具身习惯,表述着对普遍性身体规范的无力抵制——抵制普遍性对个体身体感受的不公正扼杀。与之类似,基尔曼小姐还有些更为隐性的习惯,她会无意识地“双手扭曲着,仿佛在搏斗”[4]129。基尔曼小姐矛盾的身体状态,揭示了其深信的宗教、知识对她自身感受的扼杀。抽象观念使她失去真正的自我,其名字基尔曼(Kilman)似乎就是对杀掉人的感觉这一事实的隐喻。由于忽视身体感受,追求抽象精神理念,她本人几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本能般的扭曲与搏斗。相反,彼特的身体怪癖则呈现了一种身体与观念的此消彼长。彼特从青年到中年,都习惯甩弄折刀,尤其是在见到克拉丽莎的时候,他一定会掏出折刀,通过习惯的身体动作,消除见到克拉丽莎时紧张的心理状态,这是彼特多年来一直保留着的感性状态的直观体现。这尽管看起来不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却突显着具身心理对普遍规范的冒犯。
有别于《达洛卫夫人》中的具身书写,《吕芳诗小姐》的书写特征具有“鲜明的肉感”[10]11,残雪试图通过肉身性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浑然状态。小说中最具有肉感的象征就是故事的核心场所——妓院红楼。红楼虽然处在都市京城,实则为原始丛林的隐喻,人物在这个幽暗混沌的地带纵欲,找寻、汲取原始的生命力量。小说还把肉体直接作为人与人共享经验的介质。例如,小说中的大小人物如吕芳诗、林姐、王强以及贫民窟的全部居民,都是从红楼出来的。他们不仅共享许多生活经历,甚至还能通过一个人残留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气味找到他人的下落,彼此之间亦能赤身相待。这种经验的共通性,使得他们不用语言交流就可以与他人实现相互间的理解,在他们身上,经验的交流从语言符号返回至身体感觉本身。此外,小说中的肉体形象还存在明显的人兽拼贴痕迹,正如上文所提及,男女交合被形容为血淋淋的豹子性交。这种身体形象一方面体现了对自然的亲切感,同时又具有超自然的神秘特征。由此可见,其小说中的身体的“肉感”已经超越了人本身,近于梅洛庞蒂意义上的泛肉身性,展现了一种走向他人和世界的特质,残雪实际上强调的就是身体在生命深层的普遍性[11]。 具体而言,“我的身体是用与世界同样的肉身做成的。我的身体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世界反射我的身体的肉身,世界和我的身体的肉身相互僭越”[12]。这与残雪“人和大自然同体,又是自然的最高级的器官”[1]15的母性肉体想象非常一致。从根本上看,残雪的身体重构思路与中国原始先民构建图腾的形象思维同源。它们都出于对自然之物的亲切感、神秘感、敬畏感,将种属迥异、形象悬殊物种的“身体部件”信息进行创造性重组,塑造出超自然、超现实、超人的怪异形象,同时表现出重组世界、重组生命体的强烈愿望[13]。
在《达洛卫夫人》中,具体的身体会作为经验的手段,促成人物主体差异化的认知。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从自身身体出发,依赖其感知与体验,建立起对世界和他人的独特认知。例如面对伦敦这一城市空间,克拉丽莎、彼特、理查德依靠其身体在城市中进行漫步与感知。克拉丽莎在伦敦闹市中体悟到宁静,认为伦敦生活里充满美和希望。彼特望着伦敦一切新鲜的事物,在柔和、丰美的诱人景色中,察觉到城市一派文明的气息。身体经验木讷的理查德,看见流浪的底层人民,同情心被唤起,继而反思伦敦社会制度的诸多过失。三个人顺着各自感觉经验,获得对伦敦各不相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反过来又在多个维度上呈现了伦敦的特征,赋予伦敦以内涵,赋予场所以精神。有学者认为,“在她的小说中,伍尔夫努力给出一个完整的主观性和感知的描述。”[14]伍尔夫极力以个体经验的差异性来说明身体是如何参与知觉行为的,其对生活多样的、现象性方面的呈现,意在表明关于事物的知识总有其身体性的根源。
与之相反,《吕芳诗小姐》中的身体与经验之间没有具体的、差异化的身体活动作为中介,在这里,经验是被世界直接赋予身体的;经验来自大地母亲的生产,经由身体直抵逻各斯之下生命深层的基底,具有深层的普遍特性。小说中的“红楼”是一个诱惑人放纵原始欲望的场所,不管以海市蜃楼般的轮廓出现在天边,还是运营在帝国大厦里,每个人进入这个场所,都会体会到红楼有关身体和生命力的场所精神,只不过不同个人对于生命力量的感受在强度上存在着明显差别。此种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不是认知的中心,身体也不是认知的方式,具身认知与感受并不能表述真正的世界经验。残雪以此反思几千年来思想界发生的一件事情,即人们试图用“说”来取代一种更具有母体性质的语言[1]17,用具身的认知来取代一种逻各斯之下的肉体性、意向性的表达。残雪的小说在叙事层上也展示了她的反思意图,例如小说在塑造“春天”旅馆经理这一人物形象时,让他作为小花的情人、阿利的老板、琼姐的情人同时呈现出来,让这三个人物从不同侧面去感知处在中心眼的经理。在这里,处于叙事视角中心点的事物才是认知的中心,而事物本身的意义是先在的、恒定的。此外,三个人对经理理解则理解,不理解则始终不理解。人要达成对他人和世界的认识,往往需要与一种隐秘的信息相通,方才恍然大悟。也就是说,事物的意义不是由主体自己去认知与把握的,它往往像礼物一样,是被赠予与之自然连结的个体的。而这种连结得益于身体与自然之间永恒的共通共享。残雪以这种方式,呼吁人们由关于身体的认识与观念,返回到由自然所支撑的自身的肉体,将生命体的地位提升到与精神齐平。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身体经验往往是通过感性精神来表达的,充满含混的暗示和寓言,但绝对不乏理性精神,其具有深层的普遍结构性。
《达洛卫夫人》中,身体作为具有差异性的感性存在,在抵制世界对自身的抽象改造中,以无性愉悦作为驱动力,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审美性、本真性。小说中,休的身体传承了一派古风,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这使得他尽管接受公民化改造,拥有公职人员装腔作势、墨守成规的刻板特征,却不失雅致与可爱,拥有独特的个性。家庭教师基尔曼总是感受到痛苦,她意识到“问题在于肉体”[4]125,但她不知道痛苦的根源是抽象知识,“知识产生痛苦”[1]128。只有与美同在时,与年轻貌美的伊丽莎白呆在一起,基尔曼的身体才会愉悦;一旦“伊丽莎白走掉了,美消失了,青春消逝了”[1]128。可以说,伊丽莎白的美好将基尔曼从知识导致的慢性病痛中解救出来。小说中最为抽象观念所宰制的是赛普蒂默斯,他是文明和真理的改造对象,时刻都在质疑文明和宗教福音的意义。他认为这些远大的理念都抵不过“彼得斯太太的帽子”。谈到此,塞普蒂默斯便一反常态,显得称心如意、洋洋自得。帽子既是真实和实在的事物,又是审美之物,它为身体召唤出一种关于美的实感,使身体短暂地打破抽象,呈现人的本真。由此可见,伍尔夫在小说中将身体的地位推至文明、知识、真理的高度。
《吕芳诗小姐》中的身体以激情化性欲作为驱动力,创造泛肉身在生命层的联结,使得身体拥有共通性、经验性、普遍性特性。小说中的身体都被一种力量牵引,聚合并形成稳定的群体。这种牵引力源于身体中性欲的驱使,由此,人们不自觉地出入红楼、贫民窟。激情化性欲使身体联结,这种联结又保证了激情化性欲的流转,从而实现身体与身体、身体与世界的互通。小说中常常以暧昧的气息来暗示人与人“深埋地底的盘根错节的关系”[5]18。例如,一个人的气息总能长久地留在另一个人身上;来自南方墓园的味道飘游在京城中。不管是无处不在的气息,还是深埋地底的关系,都是一种生命之流突破身体与身体,及至身体与泛身体层的隐喻性表达。而这个生命之流还将引导人们前往西北光明之地定居,最终形成最稳定的生活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里,长者的言语就像箴言。长者年岁的增长,意味着身体经验的累积,而非能力的衰微,他们是群体生活经验的传递者。在残雪那里,身体不被视为一种工具,它实质上重组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连结群体,承载经验,唤醒群体经验下的生命意识,具有一种生命深层的普遍性。身体作为生命本身,勾勒出生命的疆域,蕴积着生命的力量。
由上述可见,在身体的现代性困境中,伍尔夫承认身体高度参与了个体认知、经验的形成,并认可身体活动帮助个体抵制着抽象观念对人性的普遍性改造,身体由此与审美化、本真性的个体性密不可分。相反,残雪没有以个性化的身体作为解决现代身心矛盾的进路,而是试图对身体进行超自然重组。她强调肉身与他人、自然的连结,以此重组群体关系和群体经验,致力于展现身体抵达生命底层的力量,身体因此具有生命深层的普遍性。在两种解决现代身体问题的路径中,身体在观念上截然对立,分别具有个体性和普遍性,然而二者又在中西方思想语境下分别合理自洽,都能改善现代人的身心矛盾处境,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生命状态。
三、身体的社会背反:虚拟与实在
在社会意义上探讨身体问题,处理的其实是身体内外的关系问题。身体与外界发生交集和交换时,身体表现出来的结构性质,是一种实在的躯体还是虚拟的身体化空间,这一区分将决定自我与世界的划分、生活世界的内涵以及意义的最终归属问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身体结构的虚实存在明显对立,并导致了二者在生活世界内涵、意义归属问题上的最终差异。
《达洛卫夫人》中的身体没有明显的边界,虚拟与现实身体的界限被抹除,身体类似于身体意义化的空间。对于身体与身体化的空间,借用法国现象身体哲学家伊德的理论表述,可以对应于“身体一”和“身体二”, 前者指一种现象学所理解的定域化、动机化、知觉化和情感化的“在世存在”,它是我们之所是的身体;后者指我们在社会和文化中所经验的“身体”[15]。伍尔夫的身体没有清晰的界限,原因在于她将“身体一”与“身体二”结合在一起。在她看来,除了人的自然躯体本身,依附于身体的装饰、气质、风格等特点,都作为具身的一部分。因此,《达洛卫夫人》中,装饰、风格等等可能并不是用来凸显人物的某一性格特征,而是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在身体与外界交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不在达洛卫夫人宴会邀请名单上的埃利•亨德森,她只能“买几束廉价的淡红花,然后在黑色的旧衣服上披一条围巾”[4]16。衣着所示的身份地位,并不是使她失去参加舞会资格的原因,衣着显露得过于斯文、怯懦的身体状态,才使她被认为不适合周旋于宴会。如果我们将人物的着装作为表现人物性格、阶级的方式,势必倾向于对伍尔夫的着装、时尚、消费书写进行文化解读,而这种解读很难与叙事进程产生联系。与此相反,着装书写作为一种身体叙事,直接服务于身体乃至人性矛盾的主题,着装作为一种扩展的身体空间被纳入到身体意义之中。
相反,《吕芳诗小姐》中,身体即为身体存在本身,表现为具有清晰边界的无器官身体。这种无器官身体的特点,十分类似于德勒兹意义上的“无器官身体”(CsO)。它并不强调身体的生理特征,反对功能化身体,认为身体是一个尚未拓展成有机体和器官组织的充实的卵,是纯粹强度性的,为包含着能量转化的动态趋势以及包含着群体迁移和迁徙的运动所界定,器官在身体里只作为纯粹的强度而出现并发挥功用[16]。《吕芳诗小姐》中的身体书写没有任何具身特征,也从未涉及生育等生理现象。在这里,人物的身体展现总是与活力、生命力有关,例如与人与人交合时扩张的力量感有关。身体之中有一种力量,驱动人物去追求自由、彼此爱恨。在无器官身体中,边界的意义在于,它划定了身体力量积蓄的场所,让性驱动力能够充分蕴积,并为生命力量流向他人时爆发出冲击力。对于残雪来说,这种身体力量的爆发值得兴奋和激动,而对于伍尔夫来说,因为其过于不稳定而应该被克制。
《达洛卫夫人》中,真实与虚拟身体结合,人物身体感知由此变得更加丰富,但这一结合也导致了真实身体的沉默。在伍尔夫看来,虚实身体结合,身体空间范围扩大,人的感知范围也相应变得丰富。小说中,克拉丽莎因为更加注重身体的修饰,拥有更大边界的身体,比理查德的感受更发达。而理查德对自己的鉴赏力没有信心,对写信和表达爱意都不擅长,也与其自身的纯粹、简约的风格导致感知范围窄化有关。然而,在主体开始把依附于身体表面的装饰、使用的工具、甚至从事的职业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时,正如哲学家波兰尼所言,“我们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那样意识到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内化了这些事情并且开始寓居于它们之中”[17]。虚实相生的身体孕育着一种新的危机,即由于虚拟身体的活跃,真实的身体开始沉默,并逐渐物化为虚拟身体的一部分。小说中,休就是过于依赖宫廷身份给他带来的虚拟身体,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头脑。他因为受制于宫廷礼数,对生活的感受逐渐贫乏。这也侧面说明,尽管伍尔夫认为虚拟身体能让人对生活有更丰富的体会,但是生活意义多样性的关键仍然在于真实身体实体。
《吕芳诗小姐》中,清晰的身体边界并没有暗示超越身体的可能,人物在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最终都在身体所给予的范围里。小说开始,大多数人物都处在意义缺失的阶段,他们没有自由、方向,时常陷入黑暗的场景如舞池、山洞、地下室之中,看不到生活的方向。他们通过身体的运动与交合,才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情节发展到后来,心神不定的吕芳诗通过前往西北而点亮心情;曾老六通过抵到西北使自己身心舒畅、获得工作的热情;健忘症患者搭火车去西北得到疗养。人们在此通过参与跳舞之类的活动,最终达到一种有激情而又不狂热的理想状态。小说并没有将生活意义的实现诉诸于情节与事件的发展,事实上,只有身体及其运动才能为意义的达成提供生活的合法性。小说人物最终跟随着身体的力量抵达生活的目标,获得意义与满足,而力量本身就孕育在身体之中。尽管残雪对身体的重构的理想因过分臆想而显得渺茫,但她因此极大地肯定了身体作为生命根本的价值,即她认为行动的身体远比抽象语言和意识更能创造生活意义。
正因为《吕芳诗小姐》中生活的意义存在于身体本身,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意义不消失身体便不会真正消亡,所以,在《吕芳诗小姐》小说世界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死亡。活着的人不一定就是活着,他们生活在摆满骨灰坛的“公墓小区”。死去的人不一定死了,好比离奇生病死去的段小姐,死后还有人收到她的短信。她死时,身体呈现出在母胎时的蜷缩姿态,隐喻着生命的回归。小说中身体的最终归宿,往往是作为某种元素与自然融合。大多数人的生命尽头不是死亡,而是不知去向,比如在沙漠中失踪,然后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存在于世界。死亡意味着生命力的匮乏,而非身体的消亡。《吕芳诗小姐》结尾是红楼重新开业,在帝国大厦中永远屹立。它隐喻着自然与都市的永恒联系。生命力的本源长存于现代社会,并为现代人提供源源不断的身体力量,延续其生命意义。由此可见,人类的本质在于其身体,身体具有永恒性。
相反《达洛卫夫人》中的身体是会消亡的,它自始至终都为人的精神提供一种服务,是实现一种永恒、稳定精神的手段。伍尔夫在小说中强调身体,因为她要树立现代社会中一种理想的身体状态。身体依靠兼具普遍愉悦与审美感受的无性愉悦,拥有超出自身实体的感知范围,始终保持感性的存在,获取关于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然而,身体自始至终都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它无时无刻不需要保持一种节制,来稳定某种不可遏止的身体冲动,因而,必须形成一种稳定的个体自我风格。只有让这种个体风格作为一种精神超越了身体,身体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永恒的力量。克莉斯汀娜(Kristina)认为,伍尔夫作品中,具身自我在发展意识时,也造成了人与人的距离,因为精神是被封闭在具身身体之内的,精神必须超越身体,人与人才能建立亲密关系[18]。事实上,小说中赛普蒂莫斯的死,就意味着精神最终超越了身体,他自杀前的宣言“让你瞧吧!”[4]114,意味着他拼尽全力超越了身体的局限,在精神上永远不屈。因此,尽管身体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得到了重视,但它至始至终只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
由此可见,《达洛卫夫人》和《吕芳诗小姐》在身体的虚实问题上是对立的。伍尔夫将身体视为一种虚拟的身体空间,强调以更丰富的身体感受为主体精神提供服务,并最终使精神超越终将消亡的身体;残雪认为身体是边界清晰的无器官身体,是生命激情蕴积和爆发的场所,只要生命力不匮乏,身体就不会消亡。从根本上来讲,正是因为伍尔夫把身体作为实现精神救赎的手段,而残雪把身体作为生命存在的目的,才导致二者在身体性问题上出现同一与差异并存的局面。
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身体都与精神共同构成人性的矛盾,这是二者身体性的同一基础,而把身体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这对根本的正反命题,决定了身体性在自然层面、观念层面、社会意义中的一系列对立。这种对立和差异不是一种僵局,其将身体从脱离感性存在的事实中解救出来,分别实现了身体的审美化和生命化,体现了更本质、更稳固的身体性。因此,两部作品中体现的身体性,具有包含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二律背反关系,这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