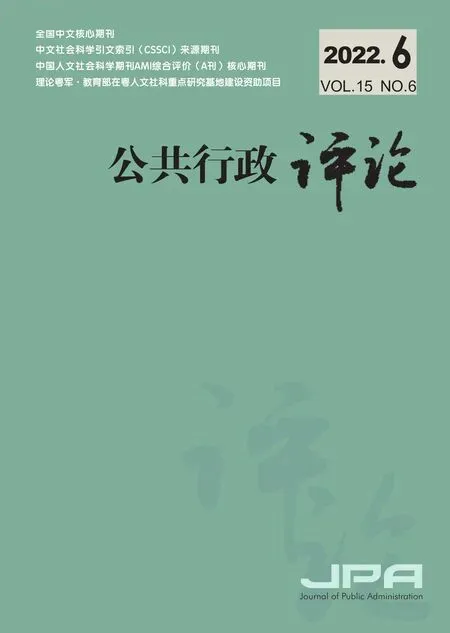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及其驱动机制
——以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为例
2022-12-30李春生韩志明
李春生 韩志明
一、引言
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治理资源和技术,对基层社会的监控和干预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Mann(2008)区分了国家的专制属性和治理属性,将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描述为发展基础权力的过程。按照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生产逻辑,国家直接在基层或边远地区推进行政化,或直接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是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理想形式之一(Soifer & Vom Hau,2008)。但基层社会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空间场所,各种矛盾纠纷和问题摩擦数量很多,有些问题还会反复出现,需要多次处理才有可能解决。如果所有问题都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去处理,治理成本无疑非常大,也是国家难以负担的(欧阳静,2022)。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压力下,培育社区治理主体,激活社区治理活力,重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政社分离,降低政府负担,成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毛丹,2018)。
但社区还存在大量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有责无权或权责关系比较模糊的问题,居委会没有直接干预的权力,却要为问题的处理不当担责(郭巍青等,2019),如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物业公司、服务企业和业主冲突产生的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会演化为更严重的矛盾冲突甚至群体事件,影响基层稳定,动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围绕业委会违规运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最为突出,比如江西某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非法牟利240万元,侵吞维修资金6万元,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闵尊涛等,2021)。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冲突或“合谋”,绕开居委会和基层政府开展行动,违规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的问题很多,经常引发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很多小区的业委会或物业为了避免流程上的麻烦,动辄多年不使用维修资金,也不对房屋问题、社区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备和绿化等进行定期检修,使小区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此外,诸如同一部位反复维修、未做项目直接支付和签订阴阳合同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这些问题上,居委会的态度和行动不仅决定着问题走向,更影响着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城市基层有大量无制度安排或权责属性模糊的问题,居委会是否介入,直接影响问题的处理及结果(魏娜,2003)。那么,居委会什么时候会干预这些问题,有效引导问题的处理直到解决?什么时候又会采取不理会或冷漠态度,任由问题发展恶化?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居委会的态度和行动?
当前基层有大量权责模糊的风险性问题,处理起来的难度和复杂性都很高,是街头官僚个人依靠自由裁量权难以处理的,需要街头官僚组织决定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与街头官僚个人不同的是,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指的是街头官僚组织在无制度安排或权责关系模糊问题中的自由裁量权使用的问题,涉及的是街头官僚组织是否处理、如何处理权责范围之外或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而并非是组织如何遵守规则或执行公共政策(May & Winter,2009)。那么,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是如何被激活的?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其中包含着怎样的驱动机制?本文将通过对H市T小区维修资金使用冲突案例的田野观察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街头官僚研究的组织自主性缺口
自利普斯基率先开展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以来,有关街头官僚的研究日益拓展,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相关学者,都从本学科的视角对街头官僚及其行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叶娟丽、马骏,2003;韩志明,2008、2010、2011;董伟玮,2018;蒋晨光、褚松燕,2019)。相对于街头官僚个人的研究而言,街头官僚组织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对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讨论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集中于对社会组织基于生存逻辑的自主性讨论,对行政性街头官僚组织政策执行和问题应对策略的零散解释,很少有系统性的阐释和分析。具体到以居委会为主体的街头官僚组织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只有个别提及,并没有进行专门研究。
自主性(Autonomy)在语义学上有三种含义,分别是独立性(Independence)、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e)(黄晓春、嵇欣,2014)。在组织行为领域,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运作机制,社会组织自主性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纪莺莺,2013)。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不同政府部门在和社会组织打交道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需要社会组织根据具体情境和合作对象选择合适的行动策略(徐家良、张其伟,2019)。总体而言,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讨论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层面,国家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给社会组织留下的自主行动空间(Lin,2007);二是策略层面,在“强国家”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如何展现“寄居蟹的艺术”(王向民,2018),采用合适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尽量免于受到外部控制(宋程成等,2013)。
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为打开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黑箱”提供了重要的切口和视角。尽管社会组织也是一类典型的街头官僚组织,但对于组织自主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的生存逻辑(Yang,2005),讨论的是组织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很难展现出行政性街头官僚组织在政策执行和问题处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策略性。对组织规则及其遵从的关注是街头官僚研究的起点。有效规则设置能够使组织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运行(Graen & Uhl-Bien,1991),也可以减少组织运行的不确定性(DeHart-Davis,2009),降低组织合作难度(Fleming,2020)。但是,并非所有组织规则都可以被有效执行,组织规则在具体情境中的适应性及其执行,以及管理官僚和街头官僚对于规则理解的差异性,才是街头官僚规则遵从研究的重要内容(Feeney & DeHart-Davis,2009)。
由于大量政策具有模糊性或“一刀切”的特点,需要街头官僚组织结合自身的情况对政策进行重构。在模糊性政策中,不同的组织有不同办法,也有不同策略、技术、工具以及结果,构成了基层政策执行的独特景观(葛天任,2018)。与上级组织相比,街头官僚组织具有更加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也更容易创造自主行动空间(Lavee & Cohen, 2019)。在社区治理中,居委会还具有双重整合能力:一是向上整合行政权威,依托类行政化的组织身份,然后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执行行政性任务(Bing,2012);二是向下整合各类自治主体或资源,比如通过各类服务项目来吸纳社会组织(唐文玉,2010),以管理网格来整合社区精英骨干和积极分子(金桥,2010),从而在政策执行中获得配合或支持。
Brodkin和Majmundar(2010)认为,街头官僚组织的规则和流程设置会影响公众的服务选择偏好,增加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隐性成本。韩志明(2011)从空间维度进一步阐释了这个结论,他通过对街头官僚组织对工作空间设置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不同工作空间隐藏着街头官僚组织对任务处置内容和流程的控制。还有的研究揭示了街头官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分类控制策略,指出街头官僚组织通过信息裁量权的使用,控制接受服务的群体及其数量(Herd et al.,2005)。但是,对于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因素,目前只有零散性的阐释,比如资源约束、规避责任和关键个人在激活街头官僚自主性中的作用(Moynihan & Herd,2010)。
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治理压力下,街头官僚组织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自主性,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三点启示:第一,作为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涉及的是处理或不处理无制度安排或权责的事项,即特定问题能否进入组织处理流程。第二,对于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是否激活,可以从街头官僚组织在特定问题中,是否自主决定对问题的干预及其程度两方面进行判定。第三,对于街头官僚组织是否激活自主性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各个影响因素背后都潜藏着不同的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给街头官僚组织带来了不同的约束、预期和激励,引导着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的方式、内容及其策略(Hirsch & Lounsbury,1997)。但对于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具体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已有研究缺少足够的关注。
本文将通过社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深描,深度阐释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在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居委会没有直接参与管理的权限,业委会常常会直接绕过居委会直接使用维修资金,进而引起矛盾、纠纷和冲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首先,将阐明研究案例的选择标准,以及选择H市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主要依据,说明对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的资料搜集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其次,对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进行深度描绘,展示T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前后的行动过程;最后,将结合已有的对街头官僚组织及其自主性的零散研究,根据T小区维修资金案例,提炼出在T小区维修资金案例中,激活居委会自主性的过程及其驱动机制。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搜集
由于社区具有类属地管理的属性,居委会在社区的多数问题中要承担兜底责任。除了少数有明确管理主体或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事务以外,居委会通常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管理本社区的大小事务和问题。但维修资金主要是由业委会管理和使用的,居委会只有监督职能。在日常运行中,业委会往往也不愿居委会过多地干预相关问题,经常绕开居委会开展行动,比如维修资金的存储、拨付使用和维修项目的合同签订。在社区维修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居委会的权限很小,直接干预也很困难。但是,维修资金是社区最大的公共资产,小区业主对其关注度很高。如果业委会频繁违规使用维修资金,非常容易引起业主的反感,进而引发更严重的矛盾冲突。
H市是中国最早建立社区业委会的城市之一,目前几乎所有小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业委会。早在2014年,H市就将85.6%的维修资金划拨到业委会的专门账户,由业主监督维修资金的使用(盛智明,2017)。也正是基于此,H市每年都会产生大量与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的问题。表1展示了部分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获得的部分资料,可以看出, H市P镇的部分小区每年都会发生业委会或物业违规使用维修资金的问题。金额小至数百元,大至几万元。在H市的其他小区,甚至还发生过业委会违规使用几十万元维修资金的情况(1)资料来源于调研材料。如无特殊注明,本研究所涉及相关材料均为调研资料。,引发了很多矛盾冲突。在对维修资金使用冲突现象的长期调研中,T小区维修资金使用冲突案例进入我们的视野。

表1 H市P镇2020年部分小区部分非正常使用维修资金问题
选择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案例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T小区的维修资金冲突的影响大,包括前期闹到电视台和各大媒体,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舆论反响,后面又包括罢免和重选业委会,更换物业公司,出现的问题在维修资金冲突中比较典型。二是T居委会在维修资金冲突中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主导者的过程,能够比较生动地呈现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激活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在资料的搜集上,首先是对T小区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前后的媒体报道及其他相关处理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其次是进入T小区,对维修资金问题处理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详细搜集;最后是对参与处理维修资金冲突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最终获得了约10万字的文字材料和约15万字的访谈材料。
四、违规使用维修资金问题与T居委会行动过程
H市T小区建成于2000年,是商品房小区,建筑面积180729平方米,有1188户居民,常住人口为3900人,拥有房屋专项维修资金1521万元。相较于周边其他小区,T小区规模不大,维修资金相对较少,社区的各种设施老旧和破坏程度比较严重,需要养护和维修的小区部件很多。但从2005年到2020年,H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上浮近4倍,T小区的物业费却始终保持在1.20元每平米,15年来从未上涨。如果出现上涨的苗头或变相上涨物业费,便会遭到小区居民的抵制,多个物业公司数次尝试上调物业费的努力均告失败。
长期低水平的物业费使T小区的物业公司日常运营举步维艰,成本不堪重负。即便是要对小区部件进行维护,使用维修资金也非常困难。在现实压力下,T小区经常出现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私下签订阴阳合同,用维修资金和公益收入补贴公司日常管理成本的情况。或将社区维护的项目承包给物业公司相关的工程公司,然后按批分拨工程款,配合物业公司转账付款。频繁的违规操作衍生了大量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引起了小区部分居民的怀疑,多次有居民试图审计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长期的低维护管理水平带来了很多问题,诸如墙体剥落、消防设施老化无效和小区绿化环境差等硬性问题比比皆是,不断挑战着小区居民容忍的底线,已经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满。
(一)居委会保持中立与部分业主的“闹大”
2018年4月,为了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T小区第四届业委会在没有与居委会提前沟通的情况下,自行将业委会内部商议通过的《停车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在小区内进行公示。部分业主对《办法》中要求第二辆车加倍收费的调整提出不满,多次向业委会和居委会提出反对意见。居委会认为,调整停车收费是业委会的职责,在小区也已经公示,没对部分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也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在业委会的推动下,新《停车管理办法》经过全体业主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开始正式实施。
随后,原先反对《新停车管理办法》的部分业主转而对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其他日常管理内容提出质疑,重点内容包括对维修资金的保管、使用及其审计情况的质疑。为了扩大事情的影响,部分业主将小区的日常管理和维修资金使用中诸多存疑的问题,先后在H市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H市教育电视台《帮女郎》栏目和《看看新闻》等媒体披露,以弱者的身份诉说T小区管理中的诸多存疑问题,包括维修资金使用流程不规范、维修工程推进不到位、小区基础设施维护不及时和可能存在签订阴阳合同的问题。此事一出,公共舆论一片哗然,业委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二)合法性危机与居委会初步干预维修资金问题
由于居委会在一开始并没有正面回应部分业主反映的问题,开始反对新《停车管理办法》的部分业主联合其他业主,质疑居委会在维修资金使用上监督不力的责任,认为居委会存在不作为的问题,甚至有个别业主直接提出居委会与业委会存在合谋,将维修资金问题的矛头指向居委会。2018年7月,恰逢新一届居委会选举,质疑居委会的维权业主在业主群广泛动员,发动业主积极前往居委会投票,选出了他们推选出来的新居委会主任,原居委会主任落选。尽管如此,新一届居委会班子的多数成员认为,持反对意见的业主提出的问题与居委会无关,如果现在贸然干预,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不满。
选出新居委会主任后,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业主频繁对居委会和业委会提出质疑,小区内的矛盾冲突愈发严重。眼看苗头不对,T小区所在的M镇镇政府在8月份紧急向新居委会派出了临时工作组,指导新一届居委会开展工作,并向居委会选派了新的居委会书记,协助处理解决部分业主提出的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尽管如此,新居委会并没有直接参与维修资金问题,而是借助M镇镇政府的权威,组织房管局代表参与协商,帮助维权业主寻找专业鉴定机构或人员,定期组织各方代表进行会谈交流,参与协调维权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其他主体,以渐进的方式挽回前期流失的合法性。
(三)权威重塑需求与居委会持续参与维修资金问题
原居委会由于对小区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出台过程始终保持沉默,激怒了部分维权业主,在维修资金问题上又受到了维权业主的猛烈攻击,因而在小区相关问题处置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时,居委会迫切需要在小区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发挥作用,展现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塑自己在小区居民心中的权威形象。由于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属于社区内部问题,基层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的权限。第四届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是重点维权对象,也不能发挥作用。维权业主又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没办法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维修资金,只能依靠居委会继续处理维修资金问题,给居委会的进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镇政府、维权业主和小区其他居民组织的共同提议下,刚刚经历换届风波的居委会开始全面参与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的处理。
新居委会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收到解决维修资金问题的任务后,立即开始着手相关问题的处置。2018年12月,对于此前维权业主提出的问题,居委会委托第三方机构A公司对相关维修工程项目进行了勘验(2)为把问题核实清楚,2018年12月,T居委会委托A公司对小区维权业主提出的“三个虚构”(13号1001室、64号1002室和33号11楼楼道)和“三个存疑”(消防栓更换、16号1102室和中心广场大理石沉降)维修工程项目进行勘查验证,A公司于2019年1月4日组建了由H市建筑设计研究所、H市X集团造价师、H市J集团工程监理师、H市B建筑工程部、物业工程水电方面的6名专家对6个工程项目同时进行了现场勘查。。在2019年1月4—9日,A公司组织了6家专业单位的6名专家,对维权业主提出的6个存疑的维修部位进行了现场勘察。1月10日,A公司组织了工程方、业主代表、业委会和居委会进行了现场复验。专业勘验结果显示,部分维权业主提出的6个存疑问题基本属实(见表2)。在居委会的监督下,施工方认可勘察结果,退还了没有施工的项目工程款。居委会要求T业委会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在业主群和小区公示栏公示。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掌控全局、多方协调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获得了居民和镇政府的认可,原先丢失的权威逐渐得以重塑。

表2 T小区6个维修项目费用及实施情况
(四)权力扩大激励与居委会全面接手后续问题处置
在听取结果汇报后,维权业主对业委会的维修资金使用提出了更多的质疑,包括工程存在造假夸大的情况,成员存在贪污腐败行为,维修基金使用不规范,工程预算未进行审价,未公开小区所有公共收益情况,绿化养护工作不善,未对电梯养护费用提高的原因进行说明,车位分配不透明,未对小区收入和支出进行合理规划,小区安全隐患问题(3)监控室(小区16号2楼)、顶楼跃层房屋(17号、37号、40号)、58号地下非机动车车库及小区会所1-2楼部分房间存在住人情况;消防通道(37号、40号)存在乱堆杂物情况。,小区环境问题严重(4)小区楼道门口台阶、大厅、消防通道处存在台阶开裂(建筑物沉降)、墙皮脱落等情况;小区会所未合理规划(卫生间脏乱、2楼部分区域荒废),小区篮场球、儿童乐园、小区网球场年久失修;小区整个区域内名贵树木大量死亡,绿植、草地养护不当。。维权业主要求居委会全面处理这些问题,追回使用不当或损失的维修资金。这代表着维权业主对居委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充分信任,也赋予了居委会全面干预维修资金问题的正当性。对于居委会而言,这不仅是不得不处置的棘手难题,也扩大了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中的干预权限,进而可以更深入、更全面、更直接地参与以往很难插手的问题,无形中对居委会形成了权力扩大的激励。经过调查,除了难以核验的问题,其余问题均或多或少存在。居委会立即与施工单位协调,追回了部分维修资金,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后续其他问题。
在勘察并核验了一系列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后,维权业主对第四届业委会更加不满,部分业主提出要罢免第四届业委会,投票选举新一届业委会。2019年3月,超过20%的业主提出提前召开业主大会,在居委会的组织协调和房管局的监督下投票罢免了业委会(5)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建房〔2009〕274号)第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因其他原因不宜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情况的,由业主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或者持有20%以上投票权数的业主提议,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授权,可以决定是否终止其委员资格。。居委会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的有效处置获得了M镇镇政府的肯定,也获得业主们的认可,他们均普遍主张居委会应该在包括维修资金相关事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M镇镇政府和小区其他主体也更愿意将其他重要的问题交由居委会处置,比如在新业委会选举产生之后,T小区与B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6)T小区与B物业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为期3年,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第五届业委会提出要更换物业公司。理论上,新物业公司的选聘应该由业委会组织进行,但由于新业委会刚成立,工作班子和制度还没有搭建起来,也是基于对居委会的信任,业委会主动提出由居委会代为主持选聘工作(7)新居委会制定了详细的选聘规则和流程,邀请专业第三方公司参与新物业公司的选聘工作,引导第五届业委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这又扩大了居委会在物业选聘相关事务中的权力,使居委会更愿意投入精力解决相关问题。
至此,T小区本次维修资金风波告一段落,在居委会的全面主导和其他主体的通力配合下,几乎所有问题均得到了妥善回应或处置。表3总结了T居委会在不同阶段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从保持中立到初步干预,再到持续参与和全面接手,T居委会在每个阶段都会试图根据相关问题演化的趋势及其特征,选择合适的干预和介入机制。在初始阶段,居委会只是严格遵守规定,保持中立态度,没有干预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出台。到了最后,居委会则是基于问题演化的形势及其解决需求,选择全面主导维修资金相关问题的处置。整体看来,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偶然性,也蕴含了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处理中的策略和智慧,展现了居委会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

表3 居委会在不同阶段激活自主性的表现和结果
五、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机制分析
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及其挑战,街头官僚组织的行动能力和资源很有限。对于本职工作,街头官僚组织即便存在敷衍了事、形式主义等行为,通常也会投入一定的资源和精力(Harrits & Møller,2014)。对于本职工作以外或权责模糊的问题,街头官僚组织是否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则取决于街头官僚组织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从而激活相应的自主性,然后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应对问题或参与问题的解决。为了将居委会的本职工作与非本职或权责关系模糊的工作明显地区分开来,本文以居委会对社区维修资金问题的干预过程为例,展示了居委会自主性激活的过程、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其中的驱动机制。
毋庸置疑,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深受组织制度因素、行动情境和自身行动能力的影响。新居委会在介入维修资金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因素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但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居委会在感受到上级政府和相关问题压力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立刻采取全面行动,而是有策略地按部就班,利用自身在维修资金问题处理中的优势逐步推进,最终全面接手维修资金及其后续问题的处置,不仅恢复了早期流失的合法性,重新建立了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威性,还扩大了居委会在很多其他问题中的影响力。从居委会介入维修资金问题的整个过程来看,综合不同阶段新居委会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及其行动,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机制包括问题性质转换、纵向权威推动、关键信息掌控、行动界面重构和组织绩效激励。
(一)问题性质转换
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治理结构下,居委会需要承担大量行政事项,经常陷入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的困境。对于不符合组织目标或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居委会经常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需要处理的事务数量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在维修资金问题初期,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内容及其出台过程,业委会都严格遵守小区相关制度和规定,并不存在违规问题,也获得了多数业主的支持,居委会没有干预的权限,更没有叫停的理由。居委会如果贸然迎合部分维权业主的诉求,干预新《停车管理办法》的实施,很可能引起业委会和多数业主的不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居委会没有动力处理这些事情,也没有必要着急去干预。
少数维权业主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将矛盾对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维修资金问题,相关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尽管居委会并没有管理和使用维修资金的权限,却要承担监管和出问题后的兜底责任。第四届业委会在维修资金使用上出现了问题,意味着居委会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不能再做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如果说收取额外的停车费是市场行为或自治行为,居委会还可以“作壁上观”,那么对维修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则是居委会的工作失职,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居委会对维修资金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寻找合适的契机介入相关问题的处置。从停车办法的自治问题到维修资金的监管责任,问题性质的转变直接建构了居委会的责任,使得居委会改变了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及其行动策略。
(二)纵向权威推动
当前社区治理主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体制化”趋势,对体制内权威的认同开始从资源依附向理念认同转变(盛智明,2019)。长期与政府打交道不仅可以得到更多行政权威的注意力,还可以获得更充分的政治空间及其相应的合法性支持(张紧跟、庄文嘉,2008)。在镇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居委会已经身陷囹圄,在相关问题中完全处于弱势。一是前期的不干预或少干预策略,使居委会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此时任何行动都有着“师出无名”“亡羊补牢”的色彩。要是再走错几步,会带来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二是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处理中的权力非常有限,并没有直接干预的权力。此时,居委会采取的就是折中策略,保持适度的辅助和协调,帮其他主体处理问题搭建平台,调动资源和多方联动,寻找干预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随着M镇镇政府向T小区派驻临时工作组,并选派了新的居委会书记,这标志着新居委会在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置中,获得了纵向行政权威的强力支持及其相应的行动空间,可以调动多方力量,吸纳多重资源,整合工作机制,直接干预维修资金相关问题。此时,居委会前期在维修资金问题中的弱势逐渐被扭转过来。上级部门的进场给居委会提供了双重激励:一是上级政府对维修资金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本小区的维修资金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注意,居委会不能再坐视不管,需要想尽办法参与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理,推动问题的解决。二是行政权威的“站台”给居委会强力介入之“势”,使居委会干预维修资金问题有了足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事实上,纵向权威的施压意味着对模糊性或不确定性问题的再次定义,对相关问题中的权力和责任进行再次分配,为街头官僚组织决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引导,从而影响街头官僚组织对问题的判断及其选择的应对策略。
(三)关键信息掌控
对相关问题信息的掌控,是组织行动的基础。在街头官僚组织的日常运行中,即便是权责范围之内的问题,也需要经过信息搜集和处理后,才有可能进行准确判断,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于非本职工作或权责模糊的问题,街头官僚组织往往会根据对相关事实信息的掌控程度,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和权衡,然后才会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介入(de Boer et al.,2018)。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事项上,居委会是相关事实信息的“集散中心”,可以实时汇聚并处理相关问题信息,对相关事实信息的控制程度很高,掌握着问题处理的进度和节奏。在维修资金问题上,起初相关信息都是由维权业主、相关媒体或其他主体披露的,居委会甚至还是后知后觉的。此时,任何行动的不确定性都很高,风险性也很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
随着维权业主进一步披露维修资金使用可能存在的多个问题,需要由居委会主导,追回维修资金或处理维修部位问题。这时,关键信息的汇聚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有问题的相关信息要首先汇总到居委会,由居委会处理和扩散,居委会逐渐成为相关问题信息汇聚的中心节点。这其实在两方面推动了居委会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一是居委会对关键维修资金问题信息的掌控能力增强,可以据此进行更精准的研判,采取更多行动,比如邀请专业组织调查维修部位问题;二是将居委会打造为相关问题信息的“集散中心”,给居委会施加信息处理压力,比如需要第一时间发布相关问题处理或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街头官僚组织对关键信息的掌控程度越高,行动的不确定性就会越低,处理相关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会越高。
(四)行动界面重构
街头官僚组织是否主动干预职责范围以外或权责模糊的问题,还取决于组织在相关问题行动界面中的位置(韩志明,2008)。维修资金由业委会管理,居委会只能发挥简单的监督作用,很多时候都无法掌握维修资金保管和使用的确切信息。在T小区维修资金问题的行动界面中,第四届业委会处于中心位置,是维修资金管理和使用的主体。即便是在维修资金问题暴发的初期,业委会饱受质疑,无法继续处理维修资金问题,全体业主也是维修资金问题理论上的处置主体。在以业委会或全体业主为中心的行动界面中,理论上,处理相关问题的一切资源、主体和要素都是围绕着业委会或相关维权业主转的。居委会此时在行动界面中的位置是非中心的和边缘的,只能起到协调和帮忙等辅助作用。
当问题发展到需要维权和资金追回阶段时,业委会、全体业主或维权业主代表在法律上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居委会就逐渐被推向维修资金问题行动网络的中心,成为相应问题行动界面的绝对核心。此时,业主、业委会、镇政府、物业和其他主体,都要依托居委会开展后续工作。而如果居委会不采取有效的行动,维修资金问题会一直悬置,甚至可能会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行动界面的重构不仅赋予了居委会绝对主导的权力,还为居委会拓展了行动空间,使居委会可以采用熟悉的工作制度、规则和方法来处理问题,从而降低了居委会处理问题的难度,也避免了使用临时性制度或出现“特事特办”的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居委会的行动成本,也让居委会更有意愿主动参与相关问题的应对和处置。
(五)组织绩效激励
与街头官僚个人相同,街头官僚组织也只有有限的治理资源,权责范围以内的事务都需要控制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绩效激励,街头官僚组织很少会主动去干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范围模糊的问题(Brodkin,2012)。在T小区维修资金冲突中,起初问题只是第四届业委会的日常工作,原居委会根本无需参与,不回应维权业主诉求是最理性的选择。这个时候,居委会即便投入很多资源进行处置,也有可能“弄巧成拙”“吃力不讨好”。在维修资金问题初期,随着镇政府对相关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维修资金问题性质发生变化,从居委会的额外工作转化为上级关注的重要工作,是上级对居委会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推动组织外部绩效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居委会也更有动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理也是对新居委会的一次“大考”,如果能够处理好,获得广大业主的认可,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业主对新居委会的认同感,还会便于日后在小区开展日常管理工作。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维修资金的日常管理和使用事务中,减少业委会违规或不当使用维修资金的情况,是很多居委会的共同愿望。就此而言,居委会是更愿意参与维修资金问题处置的,具有相应的内部绩效激励。居委会对维修资金问题的全面统筹干预,还可以积累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机制和经验,为居委会接下来继续参与维修资金相关工作预留“口子”,无形中也扩大了居委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影响力,实现了组织内部绩效的扩大再生产。可以看出,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内外部绩效能给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是影响街头官僚组织被动而为或主动作为的关键变量。
面对大量不得不处理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模糊的事务,不断激活自主性,想办法处理相应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街头官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有主动和被动的差异,相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也非常复杂。有大量研究表明,突发性事件(Lavee,2022)、领导注意力(Keulemans & Groeneveld,2020)、街头官僚组织中的关键个人(Petersen,2021)和组织自我学习(甘甜,2019),都对街头官僚组织是否处理职责外的问题有显著影响。在对T小区的后续观察中我们发现,新居委会对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已经产生了一种“本能反应”,会快速介入到维修资金相关问题。关键个人对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则不太明显。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对关键问题的有效处理或创新可以作为个人的加分项,却也意味着责任或背锅风险(倪星、王锐,2018)。在相关问题复杂性和重要性难以识别和判断的情况下,街头官僚组织中的关键个人也不愿承担风险去贸然干预非本职工作或权责关系模糊的问题(Lavee,2022)。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在街头官僚的研究谱系中,组织自主性问题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在实践中,街头官僚组织在控制公共服务供给(Harrits & Møller,2014;蒋晨光、褚松燕,2019)、制定公共政策(Lavee & Cohen,2019;Zhang et al.,2021)和无明确制度安排事务(李春生、韩志明,2021)的处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社会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不断提升,大量复杂问题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精准判定权责主体,需要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采取相应行动。本文通过T居委会从“局外人”到谨慎介入,再到全面接手维修资金问题过程的深描,阐释了街头官僚组织激活自主性的驱动机制。其中,问题性质转换、纵向权威推动、关键信息掌控、行动界面重构和组织绩效激励,构成了激活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的驱动机制。
在基层治理的研究谱系中,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也是重要的议题(8)这三类组织都是街头官僚组织。为了方便比较,突出行政性基层组织自主性的特殊性,笔者在这里将行政性基层组织称为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则不使用街头官僚组织的概念。。表4比较了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尽管都是非常典型的街头官僚组织,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主性在行动主体、基层性质、主要功能、责任类型、知识基础、驱动机制和问题面向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比如,在行动逻辑上,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是政权建设,遵从的是政治逻辑,社会组织遵从的是生存逻辑,街头官僚组织则遵从的是政策执行或解决问题的行政逻辑。在驱动机制上,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是基于维稳压力,社会组织是获得生存空间,街头官僚组织是解决问题或执行政策。不同的街头官僚组织的自主性有不同的特点,激活的动力和方式有很大差别,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表4 街头官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比较(9)表4关于基层政权自主性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观点为笔者根据已有研究整理,相关文献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街头官僚组织自主性及其激活是推动国家基础性权力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在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在基层直接设置行政机构,是将国家权力触角延伸到基层社会,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理想方式。但国家机构和人员的下沉(尤其是基层和边远地区)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投入,治理成本很高,治理负担很重。因而有了乡绅、乡贤与宗族组织和书吏与差役组织“协助”国家处理基层问题,涌现了大量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Reed,2000;黄宗智,2019;欧阳静,2022)。在新时期,街头官僚组织被动和主动激活自主性,对问题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有很大影响,影响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如何将街头官僚组织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推动街头官僚组织更加积极主动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切实减轻国家治理负担,实现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扩大再生产,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