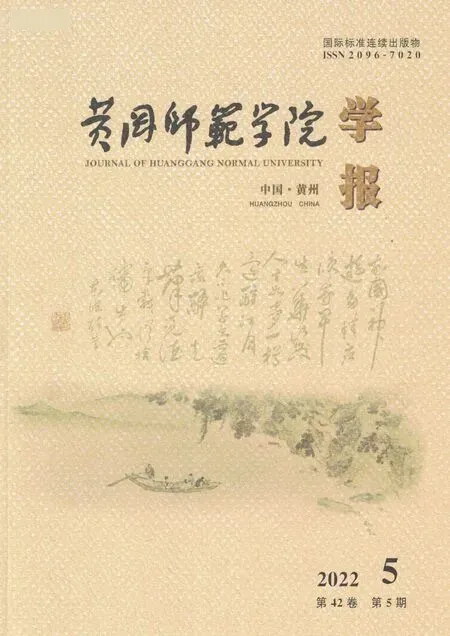国家叙事视角下的中国“两弹一星”题材电影
2022-12-30李芳芳
彭 涛,李芳芳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早在1953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力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进行重重围堵。在极其险恶的国际形势下,为打破少数国家的核垄断、核威胁,党中央果断决策,上马“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就使中国人民站直了。正如邓小平1980年曾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多次拍摄有关“两弹一星”题材,尤其是逢十大庆之年,都有相关题材电影以“献礼片”问世,使此类题材电影有明显的周期性书写特征。1999年,建国50周年之际,电影《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上映;2009年,建国60年之际,电影《邓稼先》(王冀刑导演)上映;2019年,建国70年之际,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总导演)之《相遇》(张一白导演)上映。此外,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诞辰纪念之际,也会推出相关电影:钱学森诞辰百年之际(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拍摄了电影《钱学森》(张建亚导演),并于2012年上映;2019年,郭永怀诞辰110周年之际,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举行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为主题的科技脊梁系列电影短片《郭永怀》首映式,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策划推出了微电影《永怀初心》。中国电影周期性地对“两弹一星”题材进行书写,虽有某种因标榜解密而获利的现实商业动机,但更旨在通过宏大叙事,对内“润物细无声”地引导受众认知,凝聚国人共识,对外则宣示大国形象,展现国家实力。
一、个体“生命写作”——国家宏大叙事的微观表达
“两弹一星”题材电影往往以“个人化”的记忆书写,折射出“两弹一星”重大历史事件。此类电影多为有关个人人生经历的传记电影。《邓稼先》讲述了邓稼先为实现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爆破而无私奉献一生的事迹;《钱学森》讲述了钱学森青年赴美、励志求学、涉险回国、建功立业等一系列曲折人生;电影短片《郭永怀》、微电影《永怀初心》讲述了郭永怀异国求学和赤诚报国的故事。即使是非传记电影,也都有明确的人物原型,并围绕特定人物的生命历程展开叙事。《横空出世》重点讲述了将军冯石和科学家陆光达在完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过程中个人的成长故事。影片中,科学家陆光达的人物原型是邓稼先,将军冯石的原型是张蕴珏。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相遇》里的无名科研工作者原型是无数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的人,讲述了那个年代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的情感故事。电影叙事客体聚焦于个人而非群体,围绕具体的人物生命历程展开叙事,进而将特殊时期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在具体个人的行为与选择、受难和死亡等直接、感性的形式中。
电影将个人生活的重大转折点与国家历史的重要瞬间相重叠,以个人的人生历程的微观视角,来展现国家重大历史性事件,进而完成国家宏大叙事的微观表达。电影将“两弹一星”参与者作为普通人,不回避他们的个体欲望,同时,又不止步于此,而是将其欲望进一步提纯,使个体欲望与国家利益合一。电影无一例外地描绘了这些科学家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坚如磐石的婚姻。《邓稼先》中,邓稼先临行前,妻子追问其去处,邓稼先说:“希希,做好这件事,我的一生就会很有意义,甚至说可以为它死了也是值得的,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妻子许鹿希默默点头,不再追问。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离家28年,归家已是癌症晚期,作为医生的妻子许鹿希却无力拯救生病的丈夫,万分悲痛。电影以许鹿希的视角叙述邓稼先的一生,但她却错过了他一生中重要的28年,默默守候了28年;《钱学森》以年轻的钱学森向蒋英求婚为开端,蒋英在美国营救狱中的钱学森,在国内与钱学森相濡以沫,老年时无怨无悔:“这个国家可以没有像蒋英那样的歌唱家,但是不能缺少像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我愿意为此做出牺牲,这不是遗憾,这叫光荣。”影片以钱学森生前影像表述:“我认为人不但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还要文化、艺术跟音乐。”通过钱学森对音乐的强调,肯定了蒋英的事业价值和为自己做出的事业牺牲。但这些影片要建构的意义,显然不能止步于坚贞不渝的爱情。当爱情婚姻和事业无法协调时,主人公们的选择,才是影片意义的重点。《横空出世》里,陆光达与妻子王茹慧同为麻省理工核物理专业毕业,但在特殊年代,妻子的政治身份受到不合理质疑。陆光达内心虽然坚信妻子的清白,但为了他宏大的事业,他选择刻意疏远妻子。与此同时,妻子对丈夫的行为不仅没有怨怼,反而表示理解,并最终也参与“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中,成为相互保密的“两弹一星”事业夫妻。《我和我的祖国》“相遇”单元,“无名科研人员”高远为“两弹一星”事业“消失”三年,女友方敏三年痴情等待与寻找,坚信高远一定是有苦衷的,电影展现一旦“许国”便只有相遇没有相聚的悲壮,他们的相遇虽是遗憾却无怨无悔;《永怀初心》《郭永怀》中,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尽管不知道丈夫具体在干什么工作,但相信他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无怨无悔地支持、守候他。因此,这些影片中的爱情,不仅是“自指”,更多是“他指”。这里的爱情是建立在“两弹一星”事业价值理念一致的基础上,就爱情本身而言,默默守候、同甘共苦的生活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的爱的体验,而是作为对信念的无悔认同的结果以获得意义,对爱情的忠贞和痴情守候也意味着对“两弹一星”事业的忠贞和痴情守候。
人生随时面临选择,如何选择折射人的境界和情操。“两弹一星”精英们可以选择的机会更多。当钱学森、陆光达们选择放弃西方优渥的物质生活,投身新生祖国的怀抱时,理想与信仰的旗帜早在他们内心飘扬。而当他们面临生死时的抉择,就更显出信念的执着与大无畏的气概。《邓稼先》里,航投实验过程中原子弹未爆炸,邓稼先深知核暴露的危害,拒绝随从,只身赴险,探寻失利原因;《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无名科研人员”高远在领导发布紧急撤离命令后却逆行关闸门。“核辐射”成为个人无法对抗的力量,主人公在面对危及生命的核辐射时表现出超越普通人的精神境界,诠释了“两弹一星”成功的精神密码。《郭永怀》中,同事提醒郭永怀:“永怀,必须坐飞机吗?作为科研人员,总理是不允许我们坐飞机的,何况你还身兼数职”,郭永怀却坚定地说:“我是搞航空的,我不坐飞机,谁还会坐飞机,而且现在时间太紧迫了”,在飞机失事时,与警卫员用身体紧抱机密文件,为自己热爱、坚持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主人公们的个人抉择,虽然导致了个体的牺牲,但却避免了国家的重大损失,推进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进展。在《邓稼先》中,邓稼先受到核辐射,却确认了事故是降落伞的问题,原子弹的设计本身没有问题,为之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排除了障碍;在《我和我的祖国》中,高远逆行徒手关闭实验闸门,凭一己之力拯救了全部科研人员和此次研究成果,在其受到核辐射伤害几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郭永怀》殉国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黑格尔谈到悲剧时曾说,“由于永恒正义的权力的合理性,我们看到有关人物的毁灭时仍然感到安慰”[3],这些为了“两弹一星”正义事业而陨灭的生命,其精神却永生了。
“两弹一星”题材电影通过将个人“命运”置于“两弹一星”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中,个体在迈向未来中国的历史想象中,他们的坚贞爱情、生死抉择都与国家政治主题交织互融。这些个人的“生命写作”与民族国家写作是相互依存的,这些个体的成长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个体使普遍意义具体化,“个人命运沉浮叙事是与国家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的,把个人、个体家庭的锥心之痛与新中国的伤痛缝合为一体,个体让位于整体,家国真正合成了一体”[4]。电影试图“即要揭示历史悲剧的残酷性,又要表明这个历史悲剧不足以动摇那个造成悲剧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5],进而呈现出“一种具有伦理情谊和发挥人生向上的中国民族精神”[6]。
二、道德认同——知识分子的“德性之知”
《大学》提出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就人格的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掌握具体事物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是“见闻之知”;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是“德性之知”,强调“德性之知”的价值高于“见闻之知”。“两弹一星”题材电影中主人公兼具“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电影更强调他们的“德性之知”,借助献身集体事业,牺牲个人“遂利”或“情感私欲”,人物精神上作自我完成,进而形成一套“既存在的表意系统,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具有历史的作用”[7],凸显国家利益下的“德性之知”。
爱国情怀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成长的内在动力。“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成长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时代,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这些科学家救国图存的信念,终身如一。战乱时,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合办的西南联大的校歌《满江红》中有一句词:“千秋耻,中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正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横空出世》里的吕陆光达与妻子王茹慧,《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里的主人公都怀着振兴中华的壮志,远赴大洋彼岸,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两弹一星”研制时,中国一穷二白,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等一代科研工作者,放弃国外优渥的物质生活,克服重重障碍,毅然回国,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大业,以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自强自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影片通过大量的对比手法来肯定这种献身集体事业的自我精神完成行为,引导观众认同其“德性之知”。《横空出世》中陆光达与夏世忠对比,陆光达麻省理工毕业后义无反顾回国参与核研究,好友夏世忠对于美国记者的提问:“你是美国培养的核物理学家,如果大陆留你工作,你会答应吗?”只回答“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能回答你的问题。”电影将夏世忠回国访问下飞机与陆光达回北京汇报工作进行并置,两个多年朋友、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同时下飞机,一个是有众多鲜花和记者迎接,风光无限,一个由于做着保密工作,不为人所知。
《邓稼先》中邓稼先与杨振宁对比,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举世闻名,邓稼先为“两弹”事业隐姓埋名;杨振宁回国受到国家领导人隆重接待,邓稼先却蒙冤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钱学森》中钱学森国外优渥物质生活与国内研究坚苦环境对比,国外对学生的挑剔与国内对学生的耐心教导对比。通过对比,搭建了主人公的个人能见度,使观众在心中自动区分和评判人物,进而把参与“两弹一星”研究的主人公视为道德的“典范”。“这种模式能将一种完美感知(情节化)与一种认知行为(论证)结合起来,以至于从可能看似纯粹描述性或分析性的陈述中,衍生出说明性陈述。”[8]“两弹一星”题材电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连接了叙事概念化的情节结构,另一方面连接了特定历史事件,为合理的“道德性”解释提供了论证形式,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认同“两弹一星”科学家的个人选择,进而认同国家的“两弹一星”事业。
电影强调人物的“德性之知”,即实现“人”的价值是以赢得社会舆论的赞扬为前提的。这些主人公都具有理想主义道德,形成权威性的道德引导。在“牺牲”“奉献”“理性”等表示“善”的词汇中被肯定的生活原则,和在“情”“欲”“利”等被称为“恶”的词汇中被否定的生活行为之间,拥护前者而压抑后者,凸显“人”的家国情怀、道德理性。电影一方面确认科学家与另一半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横空出世》中陆光达与王茹慧为事业伴侣、《邓稼先》中邓稼先与许鹿希28年痴情等待、《钱学森》中钱学森与蒋英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等等,“情中亦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科学家回归“理”,在否定和轻视世俗的感情与肯定或重视世俗的感情之间的紧张之间形成巨大的冲突。主人公的选择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其权威性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信任和信心,同时也在情理选择中引导道德理想,成为笼罩与支配性的普遍原则。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是来自仁心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规则,是处在人/己、公/私、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的道德生活指南,给予人们在满是荆棘的道路中前行的精神动力。影片在不断地寻找和创造一种信仰体系,“一种对于现实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信仰,一种用以支配人们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的‘命令——服从’关系中行动的基本原则”[5],主人公的道德选择也即政治选择,用道德话语展现政治话语,进而引导观众从对科学家的个人认同到对国家“两弹一星”宏大事业的认同。
三、国之大者——“两弹一星”事业的合理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冲突不断发生与调和的历史。任何国家的和平策略必须取决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和平或战争策略[9]192。中国的“两弹一星”战略是独特的,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战略选择。影片对于“两弹一星”建设动机和核力量态势的细节处理,关系到国家对于和平的态度。“国家安全界倾向于(实际上是急于)将某些武器认作是天然防御性或进攻性的,是导致稳定或破坏稳定的,从而显露出它试图集中关注可计算和已确定的管理事物和工程问题,以此规避政治和战略的危险。”[10]影片正是将镜头对准“两弹一星”背后故事,来证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是防御性的,其目的是追求战略稳定和平衡。这种基于国家叙事的影片叙事策略,一方面能从宏观上证明“两弹一星”事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争取理解和同情,同时,对内也能塑造认同,提振民族自信心。《横空出世》片头解说词详细说明了“两弹”事业是正当的防御型事业:“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一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共同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一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接着影片呈现军人冯石观看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内部资料影像,进一步确认我国“两弹”防御战略迫在眉睫。影片一开始就将中国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复杂纷纭状态做了呈现,表明在面临残酷核威胁的冷战时期,中国必须独立研发原子弹以保障国家安全。《钱学森》中,周恩来对钱学森说:“学森,今天我要跟你好好谈一谈,我们现在正在计划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早一天掌握导弹技术,把原子弹和导弹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获得真正的安全。”聂荣臻元帅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啊!目前我们国家还是很穷,朝鲜战争把我们的家底打光了,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要求,你晓不晓得为啥子?因为你在为国家铸造一把锋利的宝剑,这把宝剑在手国家才会有尊严,人民才会有和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所导致的一个重大而令人不安的结果,是这些武器强化了把战争威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手段[11]217。“两弹一星”题材影视剧,向观众清晰地陈述了中国的核安全战略:中国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为了防止核讹诈,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和平,不得不研制原子弹。中国完全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
影视剧也通过科学家内心的挣扎来表明原子弹等核武器研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瑞典化学家诺贝尔有能力发明烈性炸药却无力阻止炸药的滥杀无辜,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奠定了其原子弹理论基础,却无法阻挡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科学家也不希望自己的研究被用来制造战争和灾难。《钱学森》通过钱学森和罗友来的对话来点出科学家内心的挣扎。罗友来:“不,我不会去参加的,我绝对不会去制造这么巨大的毁绝性的武器,学森,现在全世界有良心的科学家都在禁止它,你知道的。”钱学森:“如果有一天,原子弹投到中国人的头上,我会后悔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学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你也说过,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哪怕它的存在带来质疑和争论,但是我认为,这是对抗侵略的准备,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最终以罗友来参与到原子弹研发工作表明科学家的最终抉择。邓稼先在临死前对妻子说过,“我热爱和平,我不赞成核武器。但是为了和平,我们必须拥有核武器”。[12]中国科学家在进行“两弹”研究时,也充满对这种可能毁灭世界文明的武器的担忧。但是,这种担忧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中国人自古就明白,以战止战,方是上策。中国决策者和科学家们坚信“成功威慑的获得是使用实力来平衡实力的结果,而不是任何放弃实力本身的结果”[11]218。正像肯尼思·华尔兹所指出的核革命的作用:“战略核武器威慑战略核武器(尽管其作用不限于此),当每个国家都必须竭力维护自身的安全时,一国所采取的手段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努力相适应”[13]。
影片中的诸多细节反映中国的“两弹一星”策略是为应对国际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型战略,中国的这种战略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的。《钱学森》片头展现了中国在公海领域进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时,为了确保世界各国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提前发布公告,保证本国的国防科学试验不会损害他国利益,误伤他国公民,展示大国情怀,也更宣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是防御型事业。《邓稼先》影片开头,杨振宁在美国收看中国新闻,新闻播放的正是中国宣称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声明。中国向世界表明自己捍卫和平的决心和态度,并为之采取行动。片尾人民纪念碑前的和平鸽也含蓄地表现科学家内心的期待,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期望。
“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不仅是一个出于功利目的需要避免的坏事,而且是一种出于道德理由必须避免的邪恶。”[14]中国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共赢。先进的技术的发展使得战争更加可怕,也会使和平的愿望更强烈[9]202。核武器的使用使战争中不存在任何赢家,投放核武器的一方摧毁了另一方军队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同时也摧毁了战争可掠夺的相应资源。基于理性威慑,核武器的相互制衡威慑作用能保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平衡,维持一个暂时稳定的和平状态,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两弹一星”题材电影中的叙述充分表明本国的研究并无发动战争的企图,并对战争进行道义谴责,避免了在道德上的邪恶,充分证明我国的“两弹一星”研究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自卫考虑、生存需要和民族尊严,巩固了道德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中国热爱和平的大国情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随后,在中美大使第123次会谈中,王国权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的声明草案,展示我国推动世界和平的诚意。有了罗布泊的这一声巨响,人类战争即将放慢脚步。1966年3月,中美大使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议上,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128次谈判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也是中美谈判以来,美方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原子弹研制的成功,有效地增强了中国外交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两弹一星”精神及其时代价值。2020年4月23日,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写道:“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两弹一星”先进群体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将为民族复兴提供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精神支撑。电影将这一伟大精神永远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激励中华儿女为早日实现伟大梦想披荆斩棘、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