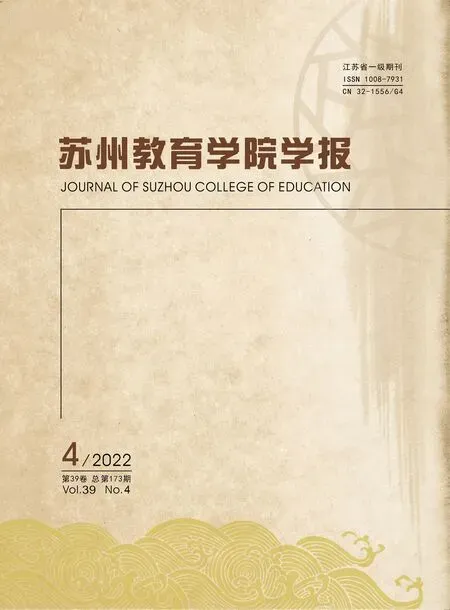论陈映真的现代名教批判—重读《唐倩的喜剧》
2022-12-30易文杰
易文杰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现代名教问题的再出发—从第三世界的视野来看
随着晚清新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西潮涌入,大量的主义、思想、观点、名词被译介到知识界。然而,接受者却常有自树权威的态度,从而出现了许多症候:“名”与实践脱节,成为空幻的符号世界,即“名词拜物教”。[1]倡导者人云亦云,并无主见,或等而下之,其实内心并无信仰,只是以此沽名钓誉而已。2019年,金理出版的《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对这个问题有精彩的研究。①该书修订自金理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还为此书召开了研讨会。主要的讨论参见:姜义华、陈思和、赵京华等:《优秀青年学人第四辑 金理 走出“名教”时代》,《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161—192页;康凌:《破名与破己—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第250—259页;黄平:《本真性个人的情感转向—以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为例》,《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第34—41页;何亦聪:《“破名者的姿态”—评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第4期,第34—37页。金理基于“名教”概念的历史演变,特别是现代人在具体表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揭示了“名教”背离、歪曲现实的现象,以及“名教”所指向的“名词拜物教”,由此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
而在笔者看来,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章太炎到鲁迅再到胡风为脉络进行考察研究,而鲁迅与胡风的现代名教批判,正好是“鲁迅左翼传统”的鲜明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鲁迅左翼传统”中的重要人物陈映真展开思考,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第三世界左翼视角出发展开对殖民性知识生产的思考。正如赵稀方指出的那样:“最为重要的是,陈映真给我们提供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最为匮乏的批判殖民性的视角,这才是陈映真的真正意义所在。”[2]可见,陈映真的重要性在于他独特的批判殖民性的视角。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批判殖民性的视角即是“第三世界”视角,“第三世界”指的是曾经或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势力所殖民压迫的国家。尽管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时期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但是,处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仍然承受着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霸权压迫与不平衡、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以文化与此进行“搏斗”。例如詹姆逊认为,鲁迅的作品中充满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搏斗。[3]陈光兴认为,陈映真的许多作品体现了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4]
从第三世界文学的视角来看,陈映真对殖民性、资产阶级现代性都有着深刻的反思,也可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如徐纪阳提示的那样,陈映真的“第三世界文学”视野与鲁迅早年关于东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观点有相通之处。[5]赵京华也指出:“鲁迅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东亚。”[6]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鲁迅影响下的陈映真基于第三世界语境反思殖民性的现代名教批判也纳入这一左翼谱系之中,以丰富我们对现代名教生成、影响的理解及批判现代名教的路径。譬如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1967),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忧郁诗学,对当时都市知识分子界的“现代名教”展开了尖锐的反讽:国民党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如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现代意识形态—的全盘盲目接受。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台湾社会的症候:冷战期间,台湾成为了美国的“傀儡”政权,成为了冷战前沿的意识形态堡垒,只能紧紧依附于美国的“新殖民”霸权,经受经济殖民与文化殖民的双重宰制。
二、“转向者”—第三世界“现代名教”与知识分子
(一)竹内好的“回心”“转向”之辨
在16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历史中,东亚与西欧存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差异,西欧更是通过暴力的殖民加快了自己的现代化速度,乃至上升到帝国主义式的侵略,并通过意识形态机器源源不断地向东亚等第三世界地区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戴维·哈维指出:“资本主义走到哪里,它的幻觉机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镜子系统就不会在后面太远。”[7]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性被译介到本土,如何把这些知识在地化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乃至国族的一大难题。
因此,在二战后的日本这一语境之下,竹内好从鲁迅处汲取思想资源,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反思,提出了向外依附的“转向”与向内超克的“回心”,展开对东亚现代性的探索。在此镜鉴下,第三世界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需要超克东方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器。竹内好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深刻的反思: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类似于“优等生”的文明,是全盘接受而缺乏思考的“转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则是“回心”型的话语,是对西方知识批判性的继承,“面对自由、平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输入,鲁迅进行了抵抗。他的抵抗,是抵抗把它们作为权威从外部的强行塞入。……总而言之,他并不相信从外部被赋予的救济”。[8]根据两国近代化的差异,竹内好也提出了两种知识分子的类别:回心型知识分子与转向型知识分子。对竹内好提出的“回心”与“转向”,汪晖进行了诠释:“‘回心’与‘转向’都涉及立场或价值的转变,但‘转向’是随波逐流的变化,是由于外部压力或诱惑而引起的改变,而‘回心’则是经历内心的挣扎、抵抗之后的决断。”[9]在竹内好和汪晖的延长线上,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揭示“转向者”之困境。
(二)小说中的“伪士”形象及其“转向”
鲁迅小说中对“伪士”的反讽艺术是较为辛辣的,体现出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比较、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等特点。陈映真的反讽技巧与鲁迅先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批判“伪士”时使用了大量漫画化的笔法,充满喜剧、荒诞色彩的同时,讽喻尤深。《唐倩的喜剧》中的男性形象,就集中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潮涌入中国台湾的情况:对于西潮话语的接受,其转向与改变只停留在了虚空之中。譬如,其对存在主义启蒙话语的接受与转向,是极为肤浅的。
郑鸿生指出,存在主义是当时流行于台湾知识界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观念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础,反对任何先验观念对个体存在的精神束缚,在文学青年中颇受欢迎。[10]然而,在《唐倩的喜剧》中,老莫接受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老莫之所以鄙视基督教学派的存在主义,是因为姨妈反对他和姨表妹的近亲爱情,这使他发现了基督教的“伪善”,转而倡导罗素的性解放理论,并借此与唐倩公开同居,但不久他的真实面目便暴露出来了。陈映真借用了唐倩的评论,“伊不久就发现到老莫也具备了一些男人—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所不能短少的伪善”[11]97,还有叙述人的评价声音,“这些个在逛窑子的时候能免于一种猥琐感的性的解放论者”[11]94,形式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以极其轻蔑的方式嘲笑和讽刺了对象,举重若轻,使小说具有尖锐的批判力量。与此同时,老莫虽主张“人道主义”,但在私人的日常空间里却异化为极端的性的技术主义者,他借用罗素的种种理论为自己的私欲进行辩护,实际上只是不想对唐倩负责,虚伪的嘴脸尽收笔底,“‘我喜欢和你有一个孩子,小倩’,他柔情似水地说,‘可是,小倩,孩子将破坏我们在试婚思想上伟大的榜样……’”[11]100。自然,当唐倩选择放弃孩子的时候,他纵横的涕泪也只是一种造作的、虚伪的体现。如果说当时英美的性解放理论是一种把青年从资产阶级的虚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力量,那么当它“理论旅行”到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却成为不少知识分子借此不负责任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具有批判力量的,然而,在老莫那里,或者说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那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左翼维度被阉割。在老莫的影响下,唐倩所秉持的“存在主义”也只是为了“自我”,而缺乏和社会、和他人有机、饱满、在地的联结。老莫所指导的唐倩的文学创作也只剩“亚流”的现代主义:她对里尔克的接受只停留在一种空无的倦怠的无力感;她创作的小说致力于描写孤寂、无力、去势的男性主体与绝望、凄凉、伤感的环境。“介入”一词仅仅是她口中的时髦字眼,实际上她缺乏和社会之间的真正联结。总的来说,从“竹内鲁迅”的视野来看,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在纷涌的西潮之中,是阉割西方理论、片面接受西方理论,只为了一己私欲的“转向者”。由于外部压力随波逐流,都有着“伪士”的意味。而在他们影响下的唐倩,也并不是“抵抗”“超克”的“回心者”。
三、现代名教困境之一:日常生活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文本性态度”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陷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爱德华·萨义德曾提出过一个“文本性态度”的概念,指的是尽管无数实例证明,“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12]。然而,当知识作为一种话语存在,它本身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在权力生产的过程中带有某种隐秘的立场。在“依附”型的世界格局体系中,这种知识生产更不鲜见。从第三世界语境进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知识分子变成了“伪士”。
我们先从对日常生活的想象进行考察。在《唐倩的喜剧》中,“现代化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了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想象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通过精彩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将奴役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装置。对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日常生活艺术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日常生活,应该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一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艺术作品”[13]。德波则通过批判性地继承列斐伏尔的思想,提出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奴役的本质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关系对微观日常生活细节不可见的殖民。[14]
如第三个和唐倩结合的“伪士”乔治周,他的举止无不体现着作为现代名教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神话:他对唐倩的教诲,无不是以“普遍性价值”的态度吹嘘美国的进步、贬低中国的落后。他总是在中文里夹杂一些英文来表征自己的身份,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围城》中的张吉民。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他的位置又是什么呢?陈映真通过乔治周这个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异化劳动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他被淹没在一家大公司的员工体系中,看似有着理想的生活,实则只是被异化的工具—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就在“技巧”方面有着发明才能,懂得运用“技巧”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是万能的,更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是正确的。当人的“技巧”变成浸泡在利己主义冰水中的工具理性,那就是对人本身的反噬。
陈映真通过乔治周的“去势”,集中体现了技术理性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悖论。乔治周陷在“去势”的罗网之中,在他和唐倩订婚的那夜,他便成了一个极端的性的技术主义者,那种机械的无情的行为,自然使他们的婚姻也成为一个悲剧。回美国后不久,乔治周就被他的新婚妻子唐倩抛弃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5],他的“性无能”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对身体的规训。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清教徒精神标榜劳动是侍奉上帝的“职责”,而身体则被诽谤为万恶之源。[16]由此可见,官僚主义/科层制度使每个人都变成巨大机器的一部分,身体被抽象为巨大生产链中的一个功能,与劳动无关的身体意识需要被禁止。在小说中,都市人成了物质人,都市人的爱欲被物欲所异化。都市人的个体生命完全依附在物上,成为了物的奴隶,成为了商品拜物教的教徒。他们只剩下一个贫乏的平面想象,一个崭新的都市神话—这里的宗教是拜物教,这里的主义是消费主义,这里的人是被物化与异化的都市人,这里的都市洋溢着一种物欲的吊诡的迷思。
马泰·卡林内斯库曾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中区分了两种现代性: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性,两者是分道而驰的,后者可谓是对市侩、庸俗的前者的一种反抗。[17]陈映真的写作正是后者的鲜明体现。
四、现代名教困境之二:殖民性知识生产的世界形象与民族寓言
在“文化冷战”的语境之中,不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想象与美援文艺相差无几,其世界体系想象也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序,极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大多数国家变成附属国,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昭示了世界经济体的极度不平等,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18]《唐倩的喜剧》对知识分子的“文本性态度”的批判,在老莫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战争—越南战争—的认识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老莫看来,“被火焰烧成木乃伊一般的越共的尸体,在西贡的闹区被执刑了的年轻的囚犯,穿着黑色衣衫的战俘”,不过是“卑贱的死亡”,而越南人民的反抗,只不过是“愚昧的暴行”,“胖子老莫坚持:美国所使用的,绝不是什么毒气弹……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使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小怪物们,决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11]98-99
为何老莫会这么想呢?归根结底,是在于他对西方,对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本性态度”。在小说中,他拿着美国《生活杂志》《新闻周刊》《时代周刊》上剪下来的越战的图片,借以向唐倩宣讲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由此可见,他是通过《生活杂志》《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这些文本来认识西方与东方的,故而他会发出如此吊诡的感叹。国内学者也曾引述过萨义德对西方记者“文本性态度”的分析: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一位法国记者从巴黎来到黎巴嫩,感伤地写道,夏多布里昂笔下的东方一去不复返了。[19]对西方记者而言,东方代表了异国情调与罗曼蒂克,而这种对东方的共识来源于15—18世纪的西方行旅、商贾,尤其是文人的经典游记。也就是说,是这些有关东方的文本而不是现实主导了西方人的东方观念。在小说中,老莫的观念同样如此,他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他的言行显然与他所推崇的萨特的言行并不一致—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时,萨特坚决反对,并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场审判美国入侵越南罪行的庭审,法院的名誉主席正是罗素。
这种殖民性知识的宰制也造成了深重的悲剧。如小说中罗大头的故事,罗大头的自杀并不是出自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出于对“去势”的恐惧。“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0]归根结底,这个被迫“虚伪”的伪士悲剧,展现了第三世界内战/冷战结构下知识分子的一个侧影。在“反共”意识形态的阴影笼罩之下,他遁入高深的“逻辑实证论”里面。当然,这种“逻辑实证论”也只是他装点门面的工具,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不是为了求真。这让我们想起《围城》中的褚慎明,他学习“逻辑实证论”的原因竟是罗素曾经请他喝过茶。褚慎明经常翻阅外国哲学杂志,找出世界上伟大哲学家的通信地址,并给他们写信,哲学家们随后回信称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奠基人,他用三四十封这样的信吓坏了无数人。
但罗大头无法真正地逃避,因为在战后中国台湾地区肃杀萧瑟的政治环境中,他也只能被迫献媚,违背知识分子的操守。这种痛苦与不安无法清除、消解,只能抑郁于心,最后转移、爆发在和唐倩的关系里。《唐倩的喜剧》既是陷入“去势”焦虑的知识分子力比多压抑的故事,又是民族寓言,表征着在压抑的“双战结构”之中,遭遇精神危机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灵魂症候。在这篇小说发表的30年后,陈映真发表了《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①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发表于1997年10月19日人间出版社与夏潮联合会在台北主办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参见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858/c0。一文,总结了乡土文学“双战结构”批判的意义。但实际上,从《唐倩的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性风潮影响下,在从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文学季刊》时期”,陈映真便“部分地克服了早期作品的感伤和忧郁风”[21],在《唐倩的喜剧》中犀利地批判了台湾的“双战”思想结构—冷战思维使知识分子依附于反共政权之中,丧失了对第三世界的基本关怀;内战思维更使知识分子加深了这种偏见,并陷入了冷战的神话之中。
五、余论
金理新著着眼于现代名教批判,探讨后发国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困境。而事实上,在第一世界现代性神话的冲击与殖民知识的传播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冷战”阴影笼罩之下的中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着现代名教的殖民性症候,陈映真对此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总的来说,秦制之后,传统的士失去了独立性,变成依附于各种权力话语的附庸,譬如儒家意识形态。到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则依附到了各种西方话语上,以此“混饭”。这就是胡适所批判的“名教”,折射出传统之“士”向“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历史症候。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思想的全盘拒绝。理想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独立地接受、批判地继承古今中西传统,吸收一切有益于本土发展的文明成果。如对陈映真影响颇深的鲁迅先生,以“拿来主义”的眼光勇敢地拿,并且以“回心”的态度批判性地接受,创造性转化为适用于本土民族的知识。鲁迅先生以深沉且具有韧性的战斗精神,进行“阵地战”,成为不断地“反抗绝望”的“有机知识分子”,突出东亚“铁屋”的重围。当中国遭受殖民者的入侵,中华文化面临危机,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还在青年时的他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2],他的一生也正是如此实践的。
陈映真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思想熔铸了解放神学与马列主义,他的文学形成受到了契诃夫、鲁迅、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又具有独特的“忧郁”美学风格。正如陈美霞所言,在陈映真的心中,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一个与穷人、罪人和被侮辱被损害者在一起的人,陈映真从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这是他左翼情感的基础,也是他的作品总是充满感性力量的原因。[23]与此同时,尽管曾因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入狱,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并当“统”“独”论争时,撰写文章,坦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第三世界的立场反驳陈芳明的“分离主义”倾向,高扬反民族分裂的旗帜,发出“中国认同”的真诚声音,“在长期的写作与社会斗争中,陈映真从未试图通过高悬理想以获得同情,相反,他对那些廉价的理想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同时选择将理想和理想主义者投入现实的熔炉予以锻造,以锻炼人的主体意志”[24]。总的来说,鲁迅和陈映真都不是狭隘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而是将多种西方思想熔铸为一体。无论是作品还是人生,鲁迅与陈映真都在践行着批判“伪士”、走出“现代名教”、成为“真人”的理念。笔者以为,这就是《唐倩的喜剧》这一作品能给予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