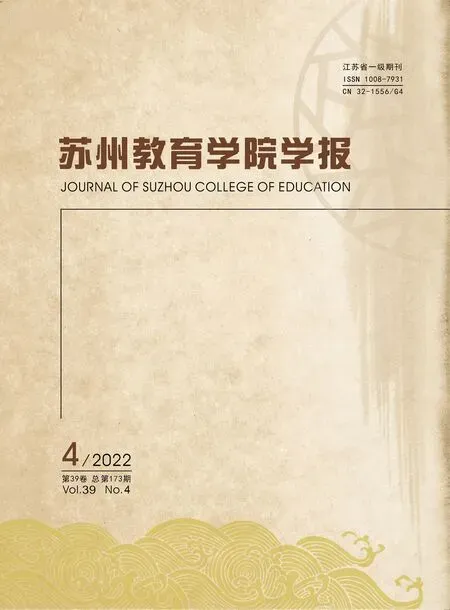古典与近代诗学的二重变奏—论森鸥外汉诗的近代价值
2022-12-30史可欣
史可欣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森鸥外(1862—1922),名高湛,号鸥外渔史,通称林太郎,与夏目漱石齐名,二人并称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两大文豪。其文学造诣几乎涵盖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兼具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诗人等多重身份,被木下杢太郎(1885—1945)喻为底比斯“百门大都”。其创造出的文学世界横跨东西洋文明,亦被我国学者王晓平称作是以调和东西方文化为己任的双足作家与学者。[1]
学界对森鸥外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小说以及翻译、文学评论等方面,于汉诗关注较少,日本学界仅有神田孝夫的《若き鴎外と漢詩文》与藤川正数的《森鴎外と漢詩》①本文所使用的日文文献资料,均为笔者翻译。。中国学界对于森鸥外的汉诗研究,有邢化祥《森鸥外和汉诗》[2]等,但多关注森鸥外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启蒙作用,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和、汉、洋多种不同文学相互融合的特征;仅有陈生保《森鴎外の漢詩》[3]是相对完整成体系的研究。
森鸥外汉诗作品存量不多,长谷川泉指出:“加上《面影》(按:又译《于母影》)所收的长诗,与《诗歌日记》《常磐会咏草》《我的百首》《奈良五十首》等相比就不能不令人惊叹它的贫乏了。”[4]18据栾殿武统计,《鸥外全集》第十九卷共收录汉诗164首,陈生保统计森鸥外汉诗总数为224首,入谷仙介统计为201首,藤川正数统计为219首。[5]我国学者陈福康认为森鸥外汉诗留存220多首[6],从现存资料来看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森鸥外汉诗的被关注度远不及同时代的夏目漱石,有观点认为鸥外汉诗过度流于世俗,且创作水平在明治时代十分普通,不值得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5]值得探讨的是,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启蒙者,应看到古典与近代多元文化对森鸥外汉诗创作的影响,以及汉诗在其文学思想中的特殊定位。
一、保守与革新共存的二重变奏—森鸥外汉诗中的思想观念
文久二年(1862),森鸥外出生于石见国(今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町,其家世代为藩主侍医,是当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家庭。鸥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时人称为神童。据其最小的弟弟森润三郎在著作中回忆,庆应二年(1866)鸥外五岁之时即师从藩儒米原纲善(与森家有亲戚关系),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庆应三年(1867)入藩校养老馆,教授有山口鼓溪、渡边积、村田义实等先生,在之前“四书”素读的基础上熟读原文及章句,又学习“五经”,并《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课程。[7]3森鸥外《庚辰岁旦醉歌》诗云:
忆昔乡校讲六经,羞我负才又恃龄。 一苇航到凤城下,骄梦此时俄然醒。[8]591
虽然明治维新前后时势改变,汉学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迅速衰落,但通过观察其早年的学习内容可以发现,成长于江户末期到明治之初的少年森鸥外,传统汉学依然在其所受到的启蒙教育中占主体地位。鸥外十几岁时,即跟随父亲到东京,入外文学校学习德语,为其日后留学德国之准备。东京帝国大学(包括东京医学院预科)毕业后,他加入日本陆军,后由陆军省委派官费留学德国五年,可谓少年得志。在东京求学期间,森鸥外对汉学依然保持了浓厚的热情,课业之余跟从依田学海(1833—1909)学习汉文。依田氏原为佐仓藩儒臣、藩主侍读,喜好稗史、小说、戏剧,推崇中国的韩非子、苏老泉(苏洵)、魏叔子(魏禧),明治时期担任史局编修、文部省权少书记官,属于正统的官僚文人。[9]可以说,以儒学为根基的汉学是森鸥外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汉诗、汉文也是他记叙生活、抒发个人情感时的自觉选择。其晚年创作的《涩江抽斋》《伊泽兰轩》等史传著作体现了扎实的汉学功底。
明治十七年(1884)年八月二十三日,森鸥外大学毕业,即将赴德国留学前夕有诗云:
一笑名优质却孱,依然古态耸吟肩。观花仅觉真欢事,题塔谁夸最少年。
唯识苏生愧牛后,空教阿逖着鞭先。昂昂未折雄飞志,梦驾长风万里船。[8]575
句中“观花”一语出自白居易诗《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白诗云:“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10]824此诗约作于元和三年至元和六年(808—811),时白居易任翰林学士。“题塔”亦引白居易诗《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10]736唐代进士登科,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提名会。当时明治天皇通常会亲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式现场,以示重视,这让鸥外联想起唐代曲江赐宴的故事。长濑静石于森鸥外的《航西日记》书眉批注曰:“曲江提名,宛然在目。”[11]76“最少年”一词出自张籍《哭孟寂》名句“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12]。暗喜自己是所有毕业生中年纪最小,也是那个年代最年轻的医学学士。
森鸥外《航西日记》自述:“(森鸥外)明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六时汽车发东京。抵横滨,投于林家。此行受命在六月十七日,赴德国修卫生学兼询陆军医事也。七月二十八日诣阙拜天颜,辞别宗庙。八月二十日至陆军省领封传。初余之卒业于大学也,蚤有航西之志,以为今之医学,自泰西来,纵使观其文讽其音,而苟非亲履其境,则郢书燕说耳。”[11]76又曰:“盖(此时)神已飞于易北河畔矣。”[11]76青年时代的鸥外意气风发,欲求新知于万里之遥的雄飞之志跃然纸上。翌日(八月二十四日)登船出发,鸥外有组诗三首,其一:
水栅天明警柝鸣,渭城歌罢又倾觥。烟波浩荡心胸豁,好放扁舟万里行。[8]576
此诗化用了王维著名的离别之作《渭城曲》,使得远渡重洋之时,告别故国和亲人的离别之情更加委婉。《航西日记》八月三十日载:“三十日,过福建,望台湾,有诗。”[11]78鸥外于船上作组诗三首,其一:
青史千秋名姓存,郑家功业岂须论。今朝遥指云山影,何处当年鹿耳门。[8]577
鹿耳门圣母庙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南市,系台湾规模最大的妈祖庙。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痛击荷兰殖民者,据民间传说,船行至鹿耳门港时见妈祖显圣,后立庙纪念。长濑静石注此诗曰:“成功当首肯于地下。”[11]78但需要注意的是,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与中国的“民族英雄”形象有所不同,鸥外的老师依田学海在甲午战争前后写的《国姓爷讨清记》故事,通过打造郑成功反清的形象,企图从文学层面为日本侵略清统治下的中国提供历史依据,也可说为《马关条约》后日本强行占领台湾埋下了文化上的伏笔。
森鸥外是近代日本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但阅读其汉诗可以发现,因旧式教育而产生的封建观念依然占据其头脑。其《辛巳十月十二日作》歌颂明治新政:
昨迎龙凤驾,今拜纶言下。闻说明治廿三年,黔首可得参政权。
政事浑因公论断,天皇度量大如天。却笑聪明舜与禹,当年仅能设旌鼓。[8]577
此诗发表于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按:诗中“廿三年”或当为明治十三年),正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高涨时期。明治七年(1874)一月,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组成日本最早的政党—爱国公党,拉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意在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确立地方自治和修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不可否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改革具有跨时代的进步意义,可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这种烙印也始终伴随着日本近代史的历程。鸥外在诗中赞扬了平民参政、开设议会等进步举措,但将这一切的成绩都归功于“天皇度量大如天”,还反向讽刺中国尧舜禹三代之治徒有其表,这其中透露出的封建思想之局限性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不值得肯定的。
从德国留学归国后,鸥外供职于日本陆军,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随军行动,担任过“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陆军省军医总监等要职。出于守旧意识的局限,森鸥外汉诗中也有少数粉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作品,如《旅顺战后书感次韵》写道:
朝抛鸭绿失边疆,暮弃辽东作战场。磷火照林光惨淡,伏尸掩野血玄黄。
雄军破敌如摧朽,新政施恩似送凉。天子当阳威德遍,何须徒颂古成汤。[8]594
这首诗作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一月十二日,是为中日甲午战争①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终于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期间,日军侵入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地区,在此之前还发生了针对中国平民的“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21日起)惨案。诗中描绘了战争的惨烈,烘托出阴森可怖的战场氛围。思想内容上,却把发动战争的侵略者比作商代圣君成汤,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天子威德”送来的“凉气”,让人难以苟同。同年九月七日,鸥外所作《台湾军中野口宁斋有诗见寄次韵》有“好是天南凉气到,桂香飘处赋平蛮”[8]595句,同样是美化日军侵略战争的表达。
可以发现,森鸥外的汉诗具有封建守旧思想与革新观念的双重属性。这固然与鸥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也可看作是日本近代变革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特殊意识形态。鸥外的汉诗记录了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变革,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个人的,更具有近代历史环境下的复杂性。
二、旧体与新诗过渡的二重变奏—森鸥外汉诗与近代诗体融合
森鸥外精湛的翻译功底为近代学界所公认,其翻译的安徒生小说《即兴诗人》被认为是超越原著的再创作。鸥外留德回国翌年(1889)出版翻译诗集《于母影》(又译作《面影》或《面纱》)引起文坛轰动。译者以典雅的文字、高超的译法将西洋诗歌的精髓植入日本近代诗歌,特别突出“句译的技巧性”,在正确把握诗歌原有意味的基础上,通过不同语言文字的切换重现诗境和韵律美。包括汉诗在内,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诗意流通,为日本近代诗歌指明了方向,也为日本近代诗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地。[13]
《于母影》主要收录明治二十二年(1889)由森鸥外主导的新声社《国民之友》杂志上翻译的诗歌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鸥外和他的朋友们用出版《于母影》所得的50日元稿费创办了日本首部以文学评论为主的杂志《栅草纸》,是为近代文学启蒙活动的先声。翻开《于母影》扉页,赫然并立着两句:
陸奧のまの(真野)のかや(萱)原とほ(遠)けどもおもかげ(面影)にして見ゆとふものを 万叶集
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 东坡诗[8]2
这首短歌取自《万叶集》第3卷396番歌,相传为笠女郎写给大伴家持(718—785)的恋歌,嗔怨不得见其面影。“陆奥”系日本古国名,是日本东北地区的总称,萱原约位于今福岛县相马郡鹿岛町真野川流域。“陆奥”一词有广袤荒凉之陆地深处的意味;“おもかげ”意为昔日的容貌,亦作“面影”;“見ゆ”意为看见,暗含恋人之间的思念之情。整句连接起来,带有悠长、深邃的和歌审美意境。汉诗则出自苏东坡《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七首其一,鸥外单独取东坡一句诗与和歌相对,句意上形成呼应,使汉诗的审美出现语境上的跳脱,注重自我抒发与美学层面的共融。
鸥外译诗并非皆是将西洋诗歌翻译为日语,亦以汉诗翻译西洋诗作,如调译(从原作之意义字句及平仄韵法者)德国诗人Nicolaus Lenan(1802—1850)的《月光》(“Das Mondlicht”):
思汝无已孤出蓬户,沿岸行且吟。安得俱汝江上相聚,闻此流水音。
安得俱汝江上联袂,瞻仰天色开。时自前岸平野之际,明月徐上来。
光彩飞散其色银白,依约凝架虹。虹也千丈中断潮脉,遥达幽树丛。
逢此光彩辉映娱目,波亦心自怡。翻见波起波伏相逐,其逝长若斯。
看到汀树浸影之处,茫忽疑有无。微听其响无见其去,如对千顷湖。
吾所希眼波一摇耳,何日能得偿。思汝无已嗟汝何似,吾夜之月光。
期汝时听跫倒吾屣,深夜空决眸。昏黑生路如大江水,呜咽停不流。
逢汝时又看李花面,明月将失妍。生路流水如箭如电,嗟奈其瞥然。[8]12
作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行者,鸥外对于诗意的理解既充分注意到了遣词造句、平仄韵法等形式特征,更强调诗意与美学之间的相通,认为“詩の想髓は形骸のために變ぜず(诗的精髓不为形骸而改变)”,并说“夫れ詩を譯して情文兼ね至ることを得ば、固よりこれに優ることあるべからず(即使译诗达到情文兼备的状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精髓)”[8]67。译诗之于森鸥外而言,可以看作是一种跨越文化界限的再创作。正如《月光》以精湛的功力,将原属于德语诗的意境转换为东方的汉诗,以共通的诗意打破了语言形式带来的复杂隔阂,这种游刃于异质文化之间来回切换的功力,是让人惊叹的。
除创作汉诗的能力之外,森鸥外对于汉诗与中国古代诗人也有自己的喜好和理解,如《于母影》中意译(从原作之意义者)高启《野梅》为日语:
めづる人なきやま里は うばらからたち生ひあるる
籬(ひもろぎ)のもとに捨てられて 雨にうつろひ風にち(散)り
世をわびげなる梅の花 あひみるにこそ悲しけれ[8]58
句中“……のもとに”表示“在……之下”;“うつろひ”意为衰败,指经历风吹雨打而变得无力;“ちり”可写作汉字词“散り”,有离散、凋谢的意味。整篇对应的是高启《看梅漫成三首》其三①此诗收录于《鸥外全集》,鸥外本人另有和译七言古诗《青邱子歌》。然三浦叶谈及高启《看梅漫成三首》和译版认为:“これは歌人井上通泰の譯と推察されている(这首诗推测为歌人井上通泰的翻译)。”推测其为《于母影》合著者井上通泰(1866—1941)所作,但作为森鸥外认同的翻译作品则没有疑问。参见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出版,第252页。:
野人不省爱梅好,弃在荒篱荆棘边。细雨东风欲零落,我来相见一潸然。[14]
高启喜咏梅,有不少佳作。森鸥外对高启亦钟爱有加,《于母影》译诗中仅有两首诗原作者为中国诗人,皆署名“高青邱”。后人对高启咏梅,多提及七律《梅花九首》。但值得玩味的是,鸥外选择的恰是高启诸多咏梅诗中不甚出名的一首。然译成日语之后,会发现更加吻合日本和歌的趣味,更易突出梅花在野地的空寂、虚幻,似有侘寂之美。也可说明鸥外对汉诗的审美理解,在文化上带有明显的自主选择意识。
近代以来的日本诗坛,随着俳句革命和新体诗运动的兴起,汉诗的典范地位被动摇。以正冈子规(1867—1902)为代表的诗人倡导俳句革命运动,一反传统写法,号召排斥旧派“宗匠”,清除旧派俳句陈腐卑俗的流弊,强调短歌要具备客观性、现实性以适应新时代所需要的文学精神,使得古老的“五七五”短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由留美化学博士外山正一、植物学家矢田部尚今,以及留德哲学家井上巽轩(哲次郎)共同编撰的《新体诗抄》号称“明治新体诗的始祖”,井上哲次郎在《新体诗抄》序中说:“外山仙士(外山正一)与尚今居士(矢田部尚今),陆续作新体诗以示余,余受而读之,其文虽交俗语,而平平坦坦,易读易解。”②外山正一等編:《新体詩抄》,東京丸屋善七明治十五年(1882)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语言文字的改革使和、汉混用的“普通文”取代汉文,逐渐发展成为被日本政府推广的标准文体,更加深了汉诗在日本社会地位的转变。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明治政府和当时的知识阶层都期望通过制造“民族语言”及“民族文化”,进而建立基于本民族美学意识的审美史观,最终完成近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15]探索近代民族语言的诗学范式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不断的创作尝试,包括经典作家的示范,才能最终定型和规范化。例如外山正一等人发起的“新体诗”,虽然有始创之功,开启了日本近代实验文学的序幕,但也难免为后人讥评为“门外汉”之作[16]。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森鸥外无疑是“经典作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相形之下,《于母影》在文学性的完成度上要比《新体诗抄》高得多。不应忽视的是,汉诗或者说汉学元素为森鸥外诗学的思想输送了充足的养分,也是近代日本诗歌改良运动走向雅化的重要思想渊源。
三、新潮与古典的二重变奏—森鸥外汉诗的近代性价值
明治、大正时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步阶段,创作于这一阶段的日本汉诗自然受到近代文学因素的影响,但汉诗依然维持着稳定的型态。入谷仙介《近代文学としての明治漢詩》之第六章《近代性精神和汉诗》提及近代新型读书人与汉诗的关系时,将森鸥外、夏目漱石与河上肇并举,认为“皮肉にも三人とも漢詩壇とも全く無緣の人物であった(讽刺地说,三个人本来都是与汉诗坛完全无缘的人物)”[17]。但事实上,森鸥外汉诗的近代性价值,恰在于通过自身的丰富阅历将多元文化要素与汉诗书写自然融合,最终形成由东方古典文化向近代文化的延伸。
森鸥外的出生地津和野在江户末期虽是小藩,却在藩主的重视下大力发展教育,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现代化培养了众多人才。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即出身于津和野。森鸥外之父森静男也曾奉藩主之命学习兰医,学习过荷兰语,是藩士阶层中较早接触西洋医学的知识分子。[7]4明治维新以后幕府解体,新式大学取代官学和藩校,留学西洋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新的上升通道。
森鸥外大学毕业后不久,受陆军卫生部指派于明治十七年到二十一年(1884—1888)赴德国深造。与夏目漱石在英国期间近乎幽闭的痛苦体验不同,森鸥外较早就接触过兰学、外语等西方知识,因而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社会,并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和自由思想。留德期间写成的《航西日记》《在德记》《队务日记》《还东日记》等皆用汉文。森鸥外的汉诗写作,很多都夹杂于日记中,其个人化的书写带有明显的随笔性质,也时常兼及沿途所感。如明治十七年十月七日作(七首其六):
回首故山云路遥,四旬舟里叹无聊。今宵马赛港头雨,洗尽征人愁绪饶。[8]581
是年也是鸥外抵达欧洲的第一年,漫长的旅途过后,映入眼帘的是满目异国风情。他写下了《咏柏林妇人七绝句》[8]584-585:
其一 《试衣娘子》(“Probiermamselle”)
试衣娘子艳如花,时样妆成岂厌奢。自道妃嫔非有种,平生不上碧灯车。
其二 《卖浆妇》(“Sodaliske”)
一杯笑疗相如渴,粗服轻妆自在身。冷淡之中存妙味,都城有此卖浆人。
其三 《行酒儿》(“Kellnerin”)
红烛揭檐卖绿醅,几多小室暖如煨。怪他娘子殊嗜好,特向书生笑口开。
其四 《歌妓》(“Soubrette”)
娇喉唱出斩新词,插句时看意匠奇。万卷文章属无用,多君只阕解人颐。
其五 《家婢》(“Maedchen fuer alles”)
效颦主妇曳长裳,途遇尖鍪百事忘。谁识庖中割羊肉,先偷片脔馈阿郎。
其六 《私窝儿》(“Die Gefallene”)
二八早看颜色衰,堪惊绛舌巧讥訾。柏林自有殊巴里,唯卖形骸不卖媚。
其七 《露市婆》(“Hoekerin”)
家积余财儿读书,老来休笑立门闾。钟鸣十二竿灯暗,一筥腥风卖鲍鱼。
这组诗收录在鸥外留德期间写成的《独逸日记》卷末附录部分,诗歌生动地烘托出其在柏林市井中所见的女性群像,宛如《舞姬》中场景再现。这种汉诗题材与当时日本诗坛流行香奁体也有一定关系。鸥外的汉诗中,也能读到留洋生活的丰富多彩,如描写舞会盛况的《踏舞歌应嘱》:
雕堂平若镜,电灯粲放光。千姬斗娇艳,浓抹又淡妆。
须臾玲珑天乐起,凌波女伴驾云郎。锦靴移步谐清曲,双双对舞拟鸳鸯。
中有东海万里客,黑袍素襟威貌扬。风流岂让碧瞳子,轻拥彼美试飞翔。
金发掩乱不遑整,汗透罗衣软玉香。曲罢不忍辄相别,携手细语兴味长。
知否佳人寸眸锐,早认日人锦绣肠。君不见诗讥屡舞不讥舞,君子亦登踏舞场。[8]583
此诗写于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十五日,将西洋舞会的场景描摹得栩栩如生。彼时日本国内亦正值鹿鸣馆夜夜笙歌、西化之风盛行之时。在当时的保守派看来,西洋舞会有伤风化,但鸥外在西洋尽情享受着盛装舞会的快乐,流露出传统诗教观中君子应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折中思想。可以说,西洋留学生活给鸥外留下了深刻记忆,而将西洋文化自然地融入汉诗写作当中,则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自觉选择的一种自我文化表达。值得留意的是,明治时代中国清诗盛行,性灵诗风的转向对鸥外汉诗的自我书写具有一定的影响,如《题羽化怀旧谈》:
清门儒学见渊源,舛命从教老筚门。偶向江湖成小著,性灵谁识个中存。[8]606
要之,崇尚“性灵”诗风的作者,多强调个性与真性情,追求诗歌内容的新颖。从鸥外的汉诗创作来看,这种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加之森鸥外汉文用语朴素,所以难免给人留下过于世俗性的感受,但因此而否定其汉诗创作的整体价值并不理性。
汉诗是森鸥外诗学思想的重要一面,而鸥外诗学又是他浪漫主义文学理念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鸥外的美学思想受德国哲学家哈特曼的理论影响,坚持以美作为绝对基准来品评和裁断批评对象。[18]他因此与持自然主义文化论观的坪内逍遥(1859—1935)进行过所谓的“没理想论争”,这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首次就文学理念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论争。森鸥外的诗歌创作与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观开拓者的思想不可分离,除唯美、典雅的译诗名著《于母影》外,诗体融合的观念也是森鸥外诗学思想中十分值得注意的特质。汉诗、俳句、短歌,包括当时还在成长中的“新体诗”,都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经历了打磨。
近代文学史上,森鸥外参与组织的观潮楼歌会对当时的名流影响甚大。参与歌会的与谢野宽、伊藤左千夫、佐佐木信纲等一同计划诸派合流以及歌风革新等活动。根据贺古鹤所、山田弘伦等好友的回忆,鸥外曾以汉诗的形式翻译过《牵牛花日记》《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其随手写作的读书随想和评论小言多是汉文,可知汉文修养依然是森鸥外诗学乃至文学世界的重要底色。试读森鸥外《现代俳画集题诗》:
墨潘重重不可揩,谁投此笔向山斋。山斋此卷为何用,忽有人来曰是俳。[8]607
鸥外在以美为绝对基准的文艺观之下,传统诗学、俳学以及画论之间的界限亦转向融合,都指向对“美”的价值追寻。这种观照亦涉及对世界文学的思考,如《题译本波斯诗》:
宠辱何关讽世诗,此心方许蛰龙知。傥从禹域求同调,除却坡仙更有谁。[8]604
大正四年(1915)十二月二十日,诗注载“作者偶与苏轼同时,故及”。和夏目漱石临终前百日接连创作75首汉诗一样,对汉文学的精神认同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这一点在鸥外接近晚年的时候也表现得越发明显。试读鸥外晚年诗作《丙辰(1916)乞骸骨,同班购书为赠,赋谢》:
解绶非成趣,挂冠拟避贤。媕婀雕朽木,老大免左迁。
圣世无所补,友僚幸不捐。去时叨嘉贶,图书百千篇。
世上争名利,群蝇逐腥膻。惟吾甘守拙,深知鹏鴳悬。
不叹贫厨素,叹无买书钱。一朝插架富,宿恨方才蠲。
有似古东野,喜迎玉川船。不羡邺侯轴,五车任独专。
对此忘寝食,朱丹手磨研。闲房有至乐,足以送暮年。[8]607
此诗刊登于大正六年(1917)四月《大正诗文》第三帙第六卷。据《森鸥外年谱》载:大正五年(55岁)四月依愿豫备役,六年(56岁)十二月任帝室博物馆长兼图书头。[19]411鸥外一生宦海沉浮,也曾因遭受“身为陆军军人,却疏忽职务,过多地从事文学”的讥评,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六月,由原近卫师团军医部长兼军医学校校长调任第十二师团军医部长,[19]410度过了三年被称为“小仓左迁”(驻地在福冈县小仓市)的生涯,直到日俄战争(1904—1905)后才正式复出文坛。
长谷川泉认为,森鸥外教养的根基是儒学,汲取中国文学之精髓。[4]18可以看到的是,正是小仓时期的蛰伏,让鸥外远离政治中心,重新开始省察自己的内心,他开始思慕汉学古籍,关注佛典,并学习法语、俄语和梵文,这段承上启下的经历对他生涯后期的精神结构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可以看到他回归古典的汉学情怀,并将这种修养融会贯通于更高的境界当中。
四、结语
森鸥外的汉诗人身份,一直以来得到的关注较少,大抵因为汉诗与其整体文学成就相比,不如小说、翻译、文学评论等突出。如果仅仅站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维度考察,难免得出森鸥外汉诗流于平实、缺乏文采的结论。然而,明治时代是日本文学由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变革期,江户之前以汉学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结构发生改变。因此,重新理解汉诗在日本近代诗歌当中的地位是有必要的,而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森鸥外汉诗就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首先,森鸥外的汉诗淡化了中国传统诗论观的影响,转向于日本近代的内在自我书写,虽然其思想感情中依然有一定比例的封建意识,但近代思想的影响更加清晰可见。其次,近代日本诗坛和、汉、洋多元文化相互影响也彼此吸收,作为经典作家的森鸥外,其汉诗创作实践融汇东西,始终贯穿着自身独立思考与特有的文学观念。最后,幼年起接受的传统汉学教育和思想,是扎根于森鸥外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也是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家,鸥外所无法剥离的文化底色。
因此,当我们以传统诗学标准审视森鸥外汉诗之时,更应当注意到其文学思想构成的多重性和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的身份。换言之,森鸥外汉诗体现出日本诗学偏离古典范式,向近代文学过渡的离心力,其中古典与近代诗学交融之二重变奏,恰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日本诗学思想向民族化、近代化过渡的经典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