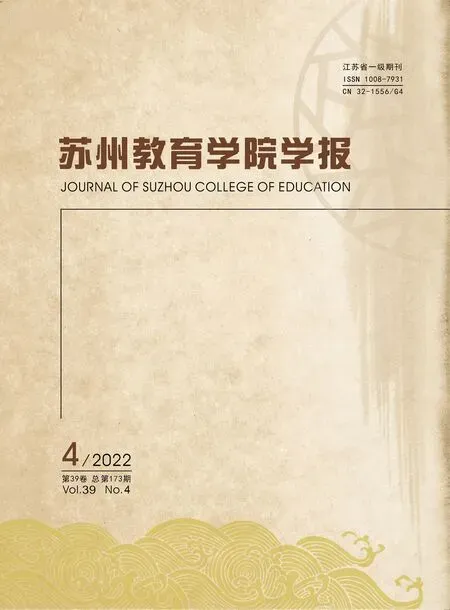朝鲜文人申靖夏的诗学理念
2022-12-30罗春兰王超凡
罗春兰,王超凡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申靖夏(1681—1716),字正甫,号恕庵,又号反观居士,朝鲜肃宗朝文臣、诗人。靖夏少通经史,颇有文才。曾拜金昌协(1651—1708,号农岩)为师,学文章之术,对农岩素所服膺,农岩亦十分赏识靖夏才学。其平生所好,唯山水与文章,又广交士子,交游唱和。挚友后人裒其诗文,编为《恕庵集》十六卷。申靖夏虽曾任职馆阁,勤于政务,亦执教乡里,有教化之志,然素来心向山水,颇显隐世放浪之姿。其诗多写于闲居之时,时人评其诗风“清和遒丽”(尹凤九《屏溪集》卷五十四)[1],“成一家则”(郑来侨《浣岩集》卷四)[2]561。此外,申靖夏浸淫于好论诗文的时风,因以留下卷帙颇丰的品评文字,或可视为其诗学理念之呈现。
朝鲜肃宗年间(1674—1720),诗坛因袭前代之风,明代复古派诗论颇受尊崇,以致模拟之诗风普遍。当此时,白岳诗坛推举“性情”“真诗”之说,以示对当时诗风的不满与抗衡。其诗坛盟主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有言:“夫诗之作,贵在抒写性情,牢笼事物,随所感触,无乎不可。事之精粗,言之雅俗,犹不当拣择,况于古今之别乎?于鳞辈学古,初无神解妙悟,而徒以言语摸拟……若用唐以后事,则疑其语之不似唐,故相与戒禁如此,此岂复有真文章哉?”[3]376昌协明确提出“性情”诗论,用以驳斥模拟蹈袭之辈。而且,在白岳诗家看来,只有发“性情”于肺腑,而非汲汲于言辞章句,才能创作出饱含真情实意的所谓“真诗”。这种诗学理念在当时形成了一定声势。
申靖夏作为白岳诗坛的中坚人物与金昌协的得意门生,其诗学理念与“白岳”诸家有相合之处,却也极具个人特色。一方面,申靖夏受到“性情”说的感染,对“真诗”创作亦行推重。其《恕庵集》卷十曰:“余尝见世所谓能诗者矣,尖新以为巧,组织以为工,时花美女以为丽,牛鬼蛇神以为怪。至急于取悦人目者,如傀儡之登场,而惟恐观者之不笑,如此而岂复有真诗哉?”[4]362批驳当时一些诗人刻意矫揉、好为奇巧的做法,从反面立论以提倡“真诗”,与乃师桴鼓相应。另一方面,申靖夏在前论统摄之下,又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一、推举宋诗,渊源有自
(一)陶潜:开“冲和简淡”之一脉
东晋陶潜作诗力求“平淡”,影响了不少诗人,唐代如韦应物、白居易等。在宋代,梅尧臣则开“平淡”风气之先,他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①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四十六,影印本,上海涵芬楼藏明万历间梅氏祠堂刻本。,刻意追求诗歌的平淡美。这种思想在宋代诗坛弥漫开来,影响深远。朝鲜诗坛不少诗人、诗论家亦接受并内化“平淡”论。
申靖夏对陶潜无比倾慕,甚至在走向人生终点之时,吟诵的也是陶潜的自挽诗。安锡儆《霅桥集》卷五载:“近者申学士靖夏临死,诵渊明自挽诗曰: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5]究其原因,当在于申靖夏“冲和简淡”的诗风追求与平淡自然的陶诗颇为投合。
申靖夏讲论诗风,尤以“冲和简淡”为尊。所谓“冲和简淡”,自有平淡之意。申靖夏本就主张“真诗”创作以反拨强为“尖新组织”之诗,因而对发于性情、不事工巧而力求简淡的诗风颇为推崇。其《恕庵集》卷六云:“粗知诗人风旨,贵在于冲和简淡……长公之纵逸奇变,非颖②应为“颍”。滨之所可仿佛,而独爱其淡甚……(金昌业)以不工自处,而其或发于吟咏者,自然有萧散简淡之趣……盖执事之不工,颖滨之淡也。”[4]284申靖夏对六朝时期关乎“平淡”的诗歌、诗论有所关切,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陶诗的论述,《恕庵集》卷十六云:“渊明之诗,平淡出于自然,其初不倚拟模仿,明矣。而钟嵘以为出于应璩,陋哉嵘也。”[4]475以对钟嵘《诗品》的反拨突出陶诗的平淡自然之风。《恕庵集》卷十六又言:“梁吴均有‘雁足印黄沙’之句,沈约谓‘语太险’,古人为诗之不欲险异如此。此自常语耳,而犹以为险,况其他乎?”[4]475赞同沈约不欲为“险语”的论调。这都可以视为申靖夏对平淡诗风的一种肯定。于宋诗,申靖夏偏爱苏辙诗之“淡”,即冲和简淡的诗歌风格,更青睐陆游诗中写山水风物、隐逸闲居的作品,这部分诗大体都有萧散平淡之风。
对于平淡诗风,申靖夏不仅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也向后辈予以推广。其《恕庵集》卷七言:“来诗得细看,其词意之悲伤不自得……盖吾侄(申昉)胸中,秋冬之凓冽严凝太多,春夏之和荣舒畅不足,此前书所以勉其着工于和平二字也。”[4]303劝导后生为诗少一些冷峭悲飒,而要走“和平”的路子。这与申靖夏对宋诗“平淡”风的受容不可分割。
陶潜向来被认为对宋诗面貌的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申靖夏对宋诗的尊崇,沿波讨源,与其对陶诗平淡诗风的推重一脉相承。
(二)杜甫:得“忠厚”之致
朝鲜一朝,杜诗在文人心中的地位素来极高③关于杜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参见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63—188、209页。。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对当时的宗杜风气就有论述:“子美、青莲各有能事,历代题品亦不一。至于近世,爱杜者多于爱青莲,然要当以杜为今文,而以青莲为古文尔。”[4]476申靖夏认为,肃宗时期朝鲜文人多爱杜诗,其原因在于杜诗偏向“今文”,即近体诗。而众所周知,杜甫长于律诗。就体裁而言,朝鲜时代的汉诗创作本就近体居多,其中律诗则更受青睐。可见至少在肃宗时期,杜甫的近体诗创作,尤其是律诗成为了朝鲜诗家接受杜诗的先导因素。
申靖夏与时人相同,也特别看重杜诗的“忠厚”品格,其《恕庵集》卷十六言曰:“古今诗人,唯子美、务观两人而已,何也?诗本忠厚也。”[4]478以“忠厚”之旨推举杜、陆二家诗,这体现出其诗学理念的鲜明“诗教”色彩,而且与他的儒家立场是相符的。
中国诗家多以“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评判诗歌,朝鲜诗家亦复如是。《东文选》所收无名氏《八家诗选序》对此有过论述,文中以为李、杜、韦、柳、欧、王、苏、黄八家诗虽各具风神,而皆得“风雅”,若能“体之以性情之正,用之以言行之和”则“自得夫温柔敦厚之风矣”①徐居正等:《东文选》,金属活字本,朝鲜肃宗三十九年(1713)刊行。。此为朝鲜诗家对“温柔敦厚之风”的普遍理解,可以视为大多数朝鲜文人论诗的典型性概括。申靖夏将杜甫视作第一流诗家,就是看重杜诗中所具有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教”底色。
“忠厚”的另一层含义是忠诚仁厚,亦属于性情的一种。申靖夏乃文人清流,一生秉持尊周思明、忠于王室之大义,无论是为王世子读书讲经,还是入台谏为官,其立场坚守如一。任职地方之时,他亦勤勉务政,又乐于提点后学,始终保持着奉上忠诚、待事仁厚的儒士清操。正是基于这样的为人处世原则,他十分重视杜诗中充溢着的爱国忠君、仁民厚生之性情。就申靖夏的诗歌创作而言,其存世之诗就有十数首为次杜、拟杜之作,有些诗题则直言为次杜诗,如《元日病眼独坐次老杜腊日韵》《九日共家兄车起夫次老杜九日韵》等。申靖夏对杜诗的推崇可见一斑。
自宋而下,中国诗论多以为杜诗乃唐诗之变,不少朝鲜诗论家对此也予以认同。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有言:“沧浪洪世泰少日为唐,晚乃学杜,其格颇变。”[4]480近世朴汉永(1870—1948)《石林随笔》亦载:“是以朴贞蕤有云:近日所谓学杜者,诗之下品。学唐者,诗之次上。”[6]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学唐”与“学杜”路数不同,杜诗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唐诗。而杜诗于宋诗而言,则有开辟之功。有宋一代,诗人不仅欣赏杜诗胸怀天下、干预现实的精神内涵与纵逸多变、包罗万千的创作风格,而且深入细致地学习了杜诗的艺术手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庭坚对杜诗炼字、造语、谋篇、声韵、格律等手法的借鉴。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宗,黄庭坚的学杜经验对后来的宋代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以后的中国诗论又往往将宗杜的诗人归于宗宋之流,宗杜与宗宋已然合为一脉。于朝鲜诗人而言,宗杜者也多宗宋诗,有类中国。
(三)韩愈:“吾诗”中有“近韩”者
与杜诗相比,韩愈诗歌对朝鲜诗坛的影响相对较弱。不过,不少朝鲜文人往往将韩诗视为李、杜之外的“第三家”,评价不可谓不高。肃宗朝前后,朝鲜文人对韩诗的正面品评尤多,如当时的大儒宋时烈、白岳诗家洪重圣等。总体而言,朝鲜文人对韩诗的接受,多侧重于其中所展现的“诗教”理念及“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②关于韩愈诗歌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影响情况,以及朝鲜文人接受韩愈诗歌的侧重点所在,参见安生:《朝鲜时代韩愈诗学的诗学史意义》,《浙江学刊》2021年第3期,第187—195页。
申靖夏对韩诗亦有推崇,其《恕庵集》卷十六有三处“记吾诗”的夫子自道,其中两处与韩诗相较,其一,“余尝在湖舍有《泛湖》诗曰:‘归来卧虚楼,梦境皆波涛。’……今见退之《游湘西寺》诗云:‘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意思之偶合如此,不觉自喜”[4]480,诗相埒等。①相关深入研究,参见赵睿才:《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图书馆杂志》2010第6期,第72—77页。自此,陆诗经由王室的宣扬而影响渐广。
在唐宋诸位诗家之中,申靖夏最是推崇陆游。这首先表现于他特为拣编的陆诗选本—《放翁律钞》,此书虽无传世之本,但从申靖夏所撰《放翁律钞跋》一文来看,其编书缘由可知。其《恕庵集》卷十二言道:“余尝谓古今诗人,杜子美以后,惟陆务观一人。……余自小酷嗜其诗,至忘寝饭,盖非特为其诗之工而已,爱其言之切于我也。……(务观)诗之得于渔歌菱唱者为多,而余又水居,故其言之种种着题如此。”[4]390申靖夏明确表示对陆游的钟爱主要在于“爱其言之切于我”,即陆游山水诗的创作经历与自己颇为契合,因而对这类陆诗偏爱有加。
申靖夏对陆诗的推崇,还体现在仿效一法。其效法陆诗的七律《书同游乐事》收于《恕庵集》卷二。其《恕庵集》卷十六载:“余尝在湖舍效放翁为诗曰:‘葛巾渌酒乌藤杖,木几蒲团白竹扉。僧因汲水晨犹往,客为看花暮不归。饮弱尚能夸量大,诗荒也道赏音稀。颇知我辈疏狂甚,莫遣傍人惹是非。’诗翁沧浪子以为陆家还魂。”[4]480他将《书同游乐事》一诗完整抄录于诗文评中,又借友人洪世泰之口点出其与陆诗之神似,言语间不无自矜之意。而且这首诗从风格上来看,颇得陆诗记游之作的平易自然或萧散平淡。与此诗相类的近体诗还能在申靖夏的别集中找到不少。无怪许多同申靖夏交游唱和的文人都将其诗风与陆游并举,如李器之(1690—1722)称赞他“其诗剑南”②李器之:《一庵集》卷二,木活字本,朝鲜英祖四十四年(1768)刊行。,郑来侨(1681—1757)评其诗文有“黄陆骨格”[2]561。可见申靖夏与陆诗的渊源十分深厚,而这也成为当时申靖夏交游圈中的共识。
二、兼采众家,宗尚通达
清初的“唐宋诗之争”历来引人瞩目,诗论家围绕唐宋诗争辩不休。朝鲜诗坛也经历了类似论争。上文提到,“白岳”诸家欲写性情、作真诗,以反拨当时一味“宗唐”的风气,其具体做法便是主张向宋诗学习。主盟坛坫的金昌协即大力导入宋风,其《农岩集》卷三十四云:“(宋诗)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途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3]375明确提出向陈与义、陆游等宋代诗人学习。《农岩集》卷三十四又称:“简斋虽气稍诎,而得少陵之音节;放翁虽格稍卑,而极诗人之风致。……无宁取简斋、放翁,以其去诗道犹近尔。”[3]375农岩门生李宜显(1669—1745)亦为之助阵,其《陶谷集》卷二十七云:“宋人虽自出机轴,亦各不失其性情,犹有真意之洋溢者。”[8]429他们都期望朝鲜诗人通过学习宋诗,抒发性情与真意,从而激发诗坛新的活力。
不过,金昌协虽推举“宋风”却也不废唐诗,其《农岩集》卷三十四道出了原因:“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此其可法也。”[3]375在他看来,无论学宋或学唐,关键在于是否能写出真性情;若学唐者强求形似而无真性情,便无足可观。这显示出金昌协兼采唐、宋而超然于唐、宋的诗学观,而且这种观念在肃宗年间很有代表性。③李丽秋在《韩国古代诗坛的唐风与宋风—第二次交替:朝鲜中期至朝鲜后期》(《韩国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53—67页)一文中指出金昌协非是批判唐诗本身,但仍将其归于“批唐主宋”一类,显然有些笼统。金昌协虽有批唐言论,综而观之是肯定唐诗的,只不过由于金昌协主张导入宋风以批判当时诗坛的“主唐”论调,因而往往有学人将之归入“宗宋”一派。事实上,金昌协论诗倾向于唐宋兼取,融二者之长以批驳“专主盛唐”的论调与模拟习气。这同后来诗家评判钱谦益诗论的逻辑是相同的。但金昌协的诗作风格的确更偏向宋诗。肃宗时著名诗人洪世泰(1653—1725)虽好学唐诗,却积极参与金昌协等人主持的白岳诗坛唱和,其诗风亦向宋诗靠近。这都说明当时不少朝鲜文人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出唐入宋之风的影响。
在宗唐与宗宋之论交相融浸的时风之下,申靖夏亦并隶唐宋,主张广泛地向唐宋诗人学习,唐宋诗家皆是其师法对象,并无宗唐或宗宋的门户之见。他在《恕庵集》卷十六中多有阐述:推崇韩愈,却也以为其诗“多让于宗元”[4]476;举白居易《秋池》诗,感叹其“费却许多思虑,写得许多光景”[4]476的苦心经营;他还引欧阳修诗并以之自况,得其中诗家趣味,等等。而在明代诗人之中,他更是直言“最爱唐顺之”[4]479。虽只言片语,亦可见其融通。
总的来看,申靖夏论诗并不强分诗家门户,而是上溯六朝,折衷唐宋,兼及“皇明”,正所谓不拘一家。不过,从他主要宗尚杜甫、韩愈、苏轼以及陆游的诗学法度来看,确乎是偏向推举宋调的。这大体合于“白岳”诸家力主学宋、兼而法唐的理念。
朝鲜文坛的风尚变化与中国文坛密切相关。金万重(1637—1692)《西浦漫笔》评论朝鲜一代诗体变化时说:“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9]其间或学宋诗,推崇苏、黄;或转学唐调,再尚明风,多以中国诗坛风向为标的,但学习、接受、创作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相类之中又有不相类”。创作如此,诗学观亦然。申靖夏与“白岳”诸家的诗学宗尚存有异同,他吸收了当时白岳诗坛所倡举的性情与真诗之论,并据此加以通变,颇具才识与胆力。他主张兼采各家之长,有宗派意识,却无门户之限,所持为通达调和的诗学观。
三、敢破陈见,“我东”特立
早在朝鲜初年,其文人就萌生出建立本朝一代文学的自觉意识。徐居正(1420—1488)所撰《东文选序》云:“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丽朝,极于盛朝,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①徐居正等:《东文选》。徐氏有传道继圣的担当与自立开辟的气概。但那时的朝鲜文坛尚不足以匹敌中国,名家、名作还较少,习汉字的士子们对中国诗文仍是凛凛踵武。不过,经由科举制度的仿效、文学典籍的传播、官方民间的往来等形式,朝鲜文人的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时至肃宗朝,历经宗国更迭与社会文化转型,此时的朝鲜自视为存续中华正统之“小华”,至少在文化心态上有了同中原王朝抗衡的底气,其文化自信已见端倪。申靖夏论诗,也往往表露出基于本国文化自信的强烈思辨意识。
(一)对中国诗论的思考与论辩
申靖夏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诗论,且多有不同于中国诗论家的评判。其《恕庵集》卷十六针对欧阳修《庐山高》批评道:“欧公作《庐山高》,自以为得意,而梅圣俞亦甚许之,以为‘使我更作诗,三十年不能道得其中一句’。以今观之,词格极冗长,无一语可采,不知欧公何以为得意,而圣俞老于诗者,亦何以推服至此也。”[4]477其以锐利之言批驳欧阳修的自矜态度,并对梅尧臣的诗评提出质疑。又言道:“王荆公次《四家诗》,以青莲编于其末,曰‘其诗言酒色者十居八九’,此论非知青莲者。黄山谷云:‘青莲诗语如生长富贵人,宁于醉中作无义语,不作寒乞声。’必如此论,然后乃可。”[4]475-476宋人重杜轻李由来已久,申靖夏以王安石、黄庭坚二人对李白诗的不同评价作为对比,激赏青莲诗歌多“富贵”之语。将前人评语互为比较,更增几分可信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上,申靖夏也有其独特思辨。中国诗论家受传统思潮影响,多将宋诗与唐诗相较,未免任意轩轾。而申靖夏的看法反比中国明清时期的很多论者更为通达,持论平正,能兼及诸家诗派,如他盛赞苏洵诗“雄杰浑深,非二子之比”(《恕庵集》卷十六)[4]477,可谓独具慧眼。
由此可见,朝鲜文人对于中国诗论并非无条件地听随,而是根据自己对于汉文典籍的阅读经验作出独立裁断,甚至时有对中国诗论的颠覆。朝鲜诗家脱离了中国诗学派别的束缚,相对客观地审视诗歌之优劣,秉持通达的批评态度而较少顾忌地表达个人观点。
(二)对中国诗话的利用与新变
申靖夏的诗论明显受到以宋诗话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话的影响,而论及本国诗人、诗歌时又有所创新,呈现出与中国诗话“学而不同”的形态。朝鲜时代,文坛向来有编撰诗话以讲论诗歌的传统。远及徐居正《东人诗话》,为朝鲜时代专著论诗之嚆矢。至朝鲜后期,诗学大盛,文人好论诗歌,因而诗话类作品层出不穷。这些诗话或记载本事,或品评诗句,或自成理论,总之是一派繁荣的景象。申靖夏自然也参与其中,其别集中就专列有“评诗文”的门类,从文集中别裁而出,后世均视其为“诗话”。
考察《恕庵集》中“评诗文”一门,其条目多有出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林广记》等宋代诗话典籍者,或录其文字略加品评,或以为参照独抒己见。例如:
《诗话》云:“子美《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句,人尝过骊山,梦明皇称美云。后人以为子美此诗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之语,则致世之乱者谁耶?明皇岂得不耻而犹诵其语乎?”余以为明皇因重色而致乱,固不可矣,然以护前而失名句,尤不可。[4]476
此条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杜少陵一”条引,并申以自己的见解,认为尽管唐明皇荒淫无道,却不可因其行而“失名句”。《恕庵集》卷十六又记:
李肇谓:“退之游华山,穷极幽险,不能下,至发狂恸哭。”沈颜辨之以“阮籍穷途之哭”为喻。肇固陋矣,而颜亦不知退之者也,唯谢无逸辨之最合理。今以其诗观之,有“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镌铭”之语,谓恸哭者,以此傅会。然其上句有“下袖拂天星”之语,则此诗极言华山之高,而其云“悔狂咋指”者,亦自夸其穷高远之览尔,而世俗不知,反以为真有是事者,甚可笑也。[4]477
此条前半部分李、沈、谢三人对韩愈“游华山”诗的论述出于《诗林广记》卷五“韩退之”条,申靖夏引出自己对三人评语的判断,意在比对各方观点进而凸显自身理念。
从上述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诗话对申靖夏的诗论有着极深的影响。不过,我们对此并不能一概而论。文人论诗,无非记诗人或诗歌本事、摘章句或诗论以批评、辨证考异、理论批评等几种类别。《东人诗话》作为朝鲜诗话中评价本国诗人诗歌的典范,其中记诗人本事者颇多,又“每每以宋人诗话记录中国诗人之事者为引发”[10],后世论东人诗者多有仿效。申靖夏讲论本国诗时也参考这样的做法。其《恕庵集》卷十六云:
欧公守滁,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山谷中,命幕客谢判官杂种花卉,谢以状问名品,公以一绝书纸尾答曰:“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花不开。”古今传以为韵事。仆在湖舍,家兄寄书与诗问归期,仆不作书,只次韵答曰:“日为湖上舟游去,直到林中花尽归。”亦庶几于欧公事耳。[4]477
欧公事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六一居士上”条,借欧阳修答谢判官诗一事自比以诗酬答家兄事,认为颇得欧公之趣。但申靖夏论诗又不全然如此。《恕庵集》卷十六言道:
余有诗友曰金君山,有独绝才。尝曰:“诗之于人,正如貌之不能废眉。”其论如此。尝有“时危百虑听江声”之句,诗老洪世泰闻而方食失箸,其为人所推服亦如此。然其苍老太早,且过于悲伤,而和平者绝少。爱君山才者兼以为忧,今果入鬼录。悲夫![4]480
此条独记友人金君山言行及他人对君山诗的推许,为专论本国诗人的条目。
如上而知,宋代诗话典籍对申靖夏的影响实在举足轻重。他既吸收宋人诗话的论诗经验,又能以之为本国诗评之用。这些条目从专评中国诗到杂记中朝两国诗,再到唯论本国诗,可见申靖夏的诗学思想中依稀蕴涵着“去中国化”的自立自新的精神与理性思辨的意识。
(三)诗论中高扬的民族意识
申靖夏诗论中具有一股强烈的标举“我东”的民族意识,显示出对本国诗人、诗歌的高度自信。一个诗学群体自信与否,常在于是否能毫不愧怍地称颂群体之内的诗家贤哲。于朝鲜诗人而言,中国诗歌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前,难以逾越。与申靖夏同时的李宜显在《陶谷集》卷二十七中言道:“我东虽称右文之国,于文章效法不高,识见甚陋。……(农岩诗)亦苏、黄也。”[8]430对本国诗文评价并不很高,即使其业师金昌协于肃宗朝诗名大盛,也不过以为是步踵苏、黄之诗。可见李宜显并无足够的自信,以为朝鲜汉诗优于中国。
反观申靖夏,他时将本民族的诗人提升到与中国诗学大家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前者更高一筹,实属难能可贵。金昌协《农岩集》卷五有组诗《赋梅》,《赋梅》其六于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得“清”字五言四韵,诗曰:“仲举叹鄙吝,谓不见黄生。况我惭古人,安可少此兄。并立虽不言,饮人以和清。但恐零落去,坐使尘虑婴。”[11]此诗沿用了《山园小梅》一诗的题材与格律,同写隐逸之思而能翻空易奇,无怪乎申靖夏盛赞颈联曰:“此句出而古今咏梅诗尽废。”(《恕庵集》卷十六》)[4]479文学作品当然不会因形式的沿袭而妨害自身的价值体现,相反,如果能超越前人,则更能说明作者文才之出众。申靖夏深谙其中道理,将这句诗推高到他诗“尽废”的地步,虽不免过誉之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多半出于对业师农岩的崇敬及其诗才的推许,亦表露出一种对本国诗歌的自信。
更为明确地展现出这种自信的,在于申靖夏对朝鲜前期著名诗人朴訚的评价。朴訚诗文历来为朝鲜文坛所称道。孝宗年间(1649—1659),当时名士郑斗卿(1597—1673)即称:“(朴訚)诗气格放逸,可与黄太史雁行。”[12]是为比拟其诗于中原诗人之肇始,但用词颇为谨慎。时至肃宗一朝,申靖夏则于《恕庵集》卷十六中放言:“翠轩之诗,出于苏、黄而其高过之,其神仙俊逸,天以与之,非区区学唐者所可企及。”[4]479比之前者,将朴訚之诗又抬高一格,认为已然超苏轶黄。苏、黄之诗向来为朝鲜文人所看重,足见靖夏对朴訚评价之高。
可以看到,申靖夏评点本国优秀诗人、诗歌,常有十分之自信。在他心目中,朝鲜诗坛英杰辈出,汉诗于中国亦不遑多让,甚至时有超越。这种标举“我东”的鲜明论调,正是出于对本国诗学水平的高度自信,也愈发彰显其诗论中自立求新的精神。
由清而上,朝鲜半岛文学素有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惯性,但随着朝鲜文人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与思辨意识的强化,其本土诗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在朝鲜文人眼中,中国诗学固然丰华卓秀,足资取法,却也并非不可指摘。申靖夏的诗学理念就呈现出脱胎于中国诗论而有所变异的状态,他汲取中国诗学的深厚营养,又基于个人的、本民族的立场发为议论,其诗学观自具一种特立的“我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