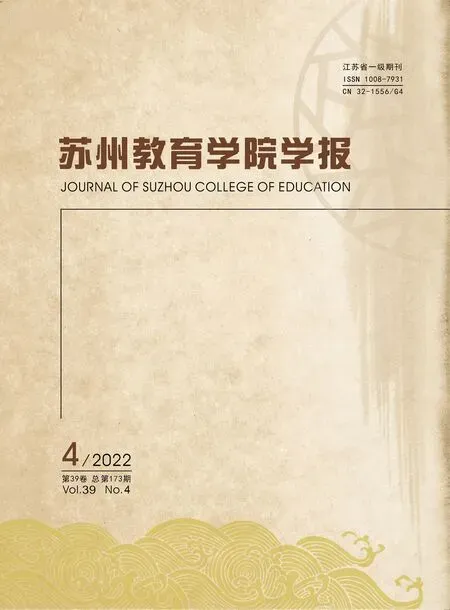江户萱园派的诗风承变—以服部南郭、仲英父子为枢纽
2022-12-30刘丝云
严 明,刘丝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服部南郭(1683—1759),名元乔,字子迁,通称小右卫门,号南郭、芙蕖馆,京都人。服部氏是高冈的名门望族,是上层町人的知识分子代表,南郭父、伯父均有较高的和、汉学素养。在承袭家门、获得出仕机会的期望下,南郭从京都来到江户,十六岁(1689)仕于柳泽吉保(1659—1714)家,并学于荻生徂徕(1666—1728)门下。南郭卓有诗才,徂徕殁后,成为萱园派名高一时的诗人进而主盟江户诗坛。享保十八年(1733),服部仲英(1713—1767)入其门下。仲英本姓中西,名元雄,小字多门,号白贲、蹈海,摄津人,先入汉学家田中桐江(1668—1742)之门。仲英少时以“孝”闻名,其父被构陷,流放而死。他誓证父亲清白,奔赴江户,经多方周旋,终为其父昭雪。后转入南郭之门,又入赘成为南郭“婿养子”,分担芙蕖馆讲堂之事,最终成为芙蕖馆二代目(第二代掌门人)。
服部南郭与服部仲英父子二人,先后执掌芙蕖馆,均以汉诗文擅名。高野兰亭(1704—1757)《寄服子迁》赞赏服部南郭:“典故传三代,文章照五车。自今陈俎豆,终古说诗书。国器人相望,时名谁得如。”(《东瀛诗选》卷五)[1]服部南郭二十四岁入荻生徂徕门学古文辞,并与徂徕、太宰春台等人组萱园诗社,以明七子为师,尊唐复古,创作了大量文辞高华、典雅的汉诗作品。仲英在汉诗文方面亦有盛名,大内熊耳(1697—1776)在其《蹈海集》题尾云:“以此风靡海内操觚之士,而海内操觚之士至今思慕不已。”[2]397-398仲英虽为服部南郭“婿养子”,在学习中承袭南郭古文辞特色外,又呈现出“不守家风”的倾向,最终能够独辟蹊径,其诗作风貌别具一格。大内熊耳评其曰:“余尝遇其房,于几上见有《端明集》,乃亦知其于文不必汉,于诗不必唐,将集众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为,文不必汉,未尝不汉;诗不必唐,未尝不唐。而二者杂诸宋,未尝随宋,则虽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风矣。”(《蹈海集·题尾》)[2]399-400他指出服部仲英学诗不限家数,也不拘于家门诗教,聚众美而自成一家的诗作特点。
一、对古文辞学的承袭
荻生徂徕四十多岁时,深受明朝复古诗派尤其是“后七子”首领李攀龙(1514—1570)、王士贞(1526—1590)的影响,注重从传统经籍等古文中把握圣人之道。荻生徂徕领悟到日本人的汉诗写作须克服和习、和训的弊端,并模仿明人的复古之志,而提出具有日本汉诗文创作特色的古文辞学。作为入门大弟子,服部南郭继承了徂徕的汉学及诗文传统,成为江户徂徕派的掌门人,其诗名亦在江户诗坛盛极一时。
古文辞派的影响力,通过服部南郭传承到服部仲英。父子二人的汉诗创作及诗学观念多有相似,其中高华雄浑、古雅悲壮的诗风,是服部父子对唐诗仿学的共同认知,也是他们身为儒师的诗作自觉,显示出对日本历史的主动关怀。
(一)尊唐复古:“唐后而有诗”
作为古文辞派的倡导者,服部南郭在唐诗认同方面有着坚定的立场,其言道:“明朝之诗,亦非一样,善学得唐诗之诗,宜朝夕讽诵。”(《南郭先生灯下书》)[3]又言“唐后而有诗也”(《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七)[4]491。他推崇汉魏六朝,诗学唐明,其《唐后诗序》曰:“夫诗不必相因,不必不相因也,而后世诗,至唐极矣。极矣,故知者不创物,述之守之,参之风雅。故古诗曰汉魏,律绝曰唐。天工人其代之,造化之蕴,其尽于斯乎……是亦所以知明乎,是亦所以知汉魏与唐乎?”(《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七)[4]489-493南郭曾谈及自己创作汉诗的体会:“夫诗临题命意,就兴得辞,固也。而又以调得辞,从辞而得意者。但不先设意,则体亦难立,往往虽有佳句,主意不贯,前后偏坠,难成一篇,是词人所患……昔有人,自患诗格不觉堕卑者,物子教之依调构思,得辞作篇,先谙熟盛唐诸名家,合作句调,而后习此事尔。不必先立意,一唯求似古人,此一道也。”(《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十《答鹅湖侯》)[4]334-335从模拟盛唐名家中习调,由调得辞,由辞生格,调亮则格高,遵此作诗之法才能于古言中求得古义,通过熟读古文辞而感悟圣人之道。
在汉诗创作实践上,南郭始终秉持“诗自唐诸体,人皆汉大夫”(《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三《九月九日猗兰台集》)[4]366的观念,其诗作中多借用“汉宫”“汉水”等中国名称,融入金玉城阙等富贵意象,惯于描摹想象中的高山大漠等宏大场景。如《又和雨后上金龙山》诗云:“谁谓仙宫难可攀,金龙近指彩云间。河边鸟道通秦畤,树杪人家接汉关。雨歇冰夷鸣鼓出,日摇玉女弄珠还。烟波长映银台上,更似鼇头海外山。”(《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四)[4]386使用“秦畤”“汉关”等古语突出金龙山(东京名胜浅草寺)的气势,再以“仙宫”“玉女弄珠”“银台”等词语渲染浅草寺庙宇建筑的华美朦胧。可见此诗并未实描浅草寺、隅田川的雨后风貌,却通过汉唐诗中常见的典故用语,烘托出浅草寺具有诗人想象中的仙山龙宫般的壮丽气势,这样的诗笔表现出南郭汉诗的盛唐风神。
其子服部仲英在诗文中也表现出对唐诗的倾心认同,其《唐诗选类材题跋》言唐诗“其藏既富矣”,并对唐诗富藏作了形象说明:“处山谷间,豫樟楩楠,良材出焉,不可胜用。其所余者,川流以下,远达于海,波及天下,无所不至。”(《蹈海集》卷七)[2]318在追慕唐诗和推崇明七子诗风的潮流中,仲英写了不少模拟诗作。比如“蓟北春风汉署前,梅花何处报新年。一枝送色西山雪,千里关心南国天。笛里还惊孤月落,陇头空望尺书传。美人不见罗浮晓,客有含香梦寐悬。”(《蹈海集》卷四《拟李于鳞署山中有忆江南梅花者因以为赋》)[2]154-155用李于鳞诗作中梅花、驿使、笛声等常用名词,架构出一段生动深情的汉诗叙事。仲英虽未曾经历江南赏梅场景,此诗却通过渲染想象,写出了颇有中国南北各地风味的赏梅意境。再看其诗作中的城市想象:“皇城五云里,朔雪晚漫漫。已积鹅毛色,高悬凤阙寒。上林迷玉树,大道逐金鞍。此日谢家宴,堪怜柳絮看。”(《蹈海集》卷三《长安雪望》)[2]64想象长安城雪景,以高大的建筑、富丽的装饰、满溢的才情铺展出盛唐大都市的宏伟气象。还如其诗作中表现出的雄浑之气:“朝看仙客向瀛洲,万里沧波不可留。东望布帆天际去,海门秋色使人愁。”(《蹈海集》卷五《海门送别》)[2]188以宏大气象渲染人生的离别悲伤,使诗作韵味深远。
(二)儒者身份:“务修大雅德业”
服部家传承儒业,为大名诸侯讲授汉诗文及经义之学。秉持儒者的身份,服部南郭不仅有对辅国安邦、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思考,更注重以汉诗文立身的儒学修养。
长期修习儒业使得服部南郭产生经世济国的责任感,如其自言:“校书投览御,上策协咨询。名达元无近,德闻必有邻。即今经国业,敷施太平人。”(《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三《徂徕先生奉教授书,书颁行特赐时,服赋此奉赠》)[4]376坚守儒家理想,使其汉诗创作多表现治国安天下的内容。“诗其可知也,何谓吟咏性情也,何谓主文也,言君子之志也”(《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七《唐后诗序》)[4]487,南郭指出,“文章者,行远之道,经国大业成然存矣,亦不可不常讲其用法焉。今诗犹古之诗也,温厚和平,士君子所养,安得谓无益于事乎?”(《南郭先生文集四编》卷五《赠熊本侯序》)[5]154秉持以古文辞表现温厚平和、以温厚平和颐养君子之气、以君子之气赋予诗文政治功能的原则。
服部南郭从元禄十一年(1698)至享保元年(1716)间出仕,之后闲居市井坊间多年,醉心于汉诗文。“犹有诗篇传漫兴,不妨身后自成名”(《南郭先生文集三编》卷三《寄稷卿》)[6]106,以儒学者自居,在诗书中体味人生乐趣,是南郭人生的极致追求。“即亦三坟五典,九流百家,以为居室,朝修夕诵,麋费笔墨……试与流俗巧捷之士,挈其长短……然而自童既习,遂成之性,亦以为自得焉。虽则无用,终乃是以至老死而已矣,亦从吾所好也”(《南郭先生文集三编》卷三《送田大心序》)[6]256,服部南郭性情平和,举止文雅,在汉诗文创作中找到了使身心融洽的生存方式。中国学者高文汉曾经这样评价:“南郭的学识、文赋俱佳。或许是其温文尔雅、不愠不燥的性格所致,诗作缺少清俊奇绝的警联佳句,但常毕全力于一诗一文,注重整体上的协调,其作品仍不失为大家气象。”[7]
南郭倾心明七子的雅正大家风范,服部仲英亦承续此风。“仲英得南郭指授,为儒雅士”(《先哲丛谈》卷六)[8]409,其儒雅风范,主要来自于南郭家传的儒学修养。服部仲英长期修习儒家经典,有君子之志,秉持责任感及仁爱之心。如其与大名的交往诗云:“玉露金茎汉阙头,星河遥送斾旌流。好凭熊轼临藩镇,不比仙槎犯斗牛。十五国风东海道,芙蓉狱色白云秋。封疆民庶争迎拜,到处讴歌拥紫骝。”(《蹈海集》卷四《七月七日鸟羽侯新就国作此奉送》)[2]136-137在美好祝愿中描摹出民众尊拜的理想之治。再如《寒夜闻雁》,表达出对为国守边征士的关切同情:“永夜风霜楚水寒,征鸿声苦向前滩。应怜千里无衣客,似报乡书寄不难。”(《蹈海集》卷五)[2]218在江户汉诗雅集活动中,服部仲英提出尚“雅”的诗评要求,其《诗誓》言:“君子出辞气,温厚和平,斯远鄙倍。……事毋不敬,各慎尔仪,务修大雅德业。”(《蹈海集》卷八)[2]355秉持严肃的汉诗创作态度及对高雅汉诗艺术的追求,成为江户萱园学派汉诗创作的基本原则,其中体现出对自身儒学者身份的深刻认同。
(三)叙说历史:辞体典雅,古今通鉴
江户儒学者逐渐加强了对本国历史的关注,江户诗坛也出现了探寻本土历史叙说的诗作动态。在学习中国诗歌经典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叙说本国历史的诗歌模式,既符合汉诗体裁语句规范,又可以表现出日本文化色彩的深远情韵,这是服部南郭父子汉诗改革实践的重要方面。
服部父子写过不少怀古诗,吟咏日本历史事件及传世人物事迹,往往触景生情,吊古伤今,情韵深厚。父子二人通过叙咏本事进行历史叙说,讲究用“古辞”匹配古体、古典用事,展示出古文辞学派的高超语言功夫。比如南郭《相中览古四首》其三:“鸟合原头黄鸟飞,荒山春老草初肥。穆公一去秦良尽,无限丘坟知者稀。”(《南郭先生文集二编》卷五)[9]162此诗咏古,想象秦穆公去世、秦国良士殉葬情景,比拟日本相中地区盛衰历史和英雄萧瑟。还比如《菅相祠二首》其一云:“皇都大岳自氤氲,神降当年辅圣君。谁辨南庭飞霹雳,仍朝北斗感风云。叡心难发金滕悔,祀典还崇玉册勋。冠带俨然明德远,长令髦士仰斯文。”(《南郭先生文集二编》卷四)[9]146南郭在阅读菅原道真(845—903)诗文时,感受到道真忠君报国的拳拳之心,满心钦佩,感慨万分。诗中借用周成王发现金滕中周公祝辞而感悟到周公德行的典故,将平安朝菅原道真比作中国上古时代的圣人周公,盛赞其忠诚爱国心与出众文采。
传承南郭诗作家风,服部仲英亦有不少咏史组诗表现其深刻的历史感叹。比如仲英《咏史诗三首》叙咏日本史的本事,赞颂史上英雄人物的悲壮雄豪,其二云:
熊袭怀不庭,皇子率六师。生年才二八,神武震西垂。王化时未洽,东辕征虾夷。
莽莾大野间,豺狼伏且窥。如何阏伯氏,炎赫助逆驰。据鞍引神剑,反风在一麾。
行行蹈总海,海若骄为危。我妃变侍侧,报恩从此辞。风波忽已定,燕婉念在兹。
振膂陟彼罔,回望心东悲。远道疲跋涉,山泽一倭迟。不避龙蛇害,濯足瀵水湄。
英魂为白鸟,冲霄何处之。奕奕蓬岛朝,长于日夜辉。
(《蹈海集》卷一)[2]29
日本神话传说小碓尊杀其兄大碓皇子,但最终完成讨伐熊袭、平定虾夷等伟业,而成为日本的武尊(事见《日本书纪》《古事记》《风土记》)。类似的神话英雄有类中国古史传说的火神阏伯。本诗以中国的阏伯类比日本的武尊,突出远古英雄的丰功伟绩,可见服部仲英对中国典故的熟悉,以及对日本古代英雄的崇拜。
服部父子的古体诗擅长叙述日本历史事迹,突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及悲剧命运。比如服部南郭的名篇《小督词》,叙写高仓天皇(1168—1180在位)善良多情,他与宠妃小督局的爱情故事在《平家物语》中有浓笔描写。小督局遭到平清氏中宫的嫉恨被迫出家,命运悲惨,后不知所终。此古体诗共72句,从“宠姬小督逃宫中,死生朝野无消息”到“御前直赴长安西,深夜行行骢马蹄”,描写高仓天皇苦心寻找而不得。诗中夹叙小督的悲情出逃,“昭君远嫁楚妃欢”“私侍深宫人不知”“蝼蚁那惜此身亡”(《南郭先生文集三编》卷一)[6]29-31,援汉典入和史,细致描绘了小督的行为和心理,渲染悲情,使得此诗引发江户诗坛的巨大同情共鸣。
服部仲英继承了南郭取材日本历史而长篇叙事的汉诗写作传统,继续创作了《妓王怨》《小宰相词》等作品。《妓王怨》取材于《平家物语》“祇王”故事。从祇王“共称佳丽白拍子,王侯贵戚争招邀”到“母子此外无所营,胜因朝暮唱佛名。摄取之誓长不朽,愿生西天极乐城”(《蹈海集》卷二)[2]36-40的传奇经历,书写出多才多艺的神女祇王把握自身命运的觉醒过程,展示了平安时代佛教风行中的女才子命运。仲英的《小宰相词》同样取材于《平家物语》“小宰相身投”,叙说战乱中将士家眷“何异当年虞氏悲”(《蹈海集》卷二)[2]42的悲苦人生,叙事笔法变化多端,人物事迹生动感人。
总之,服部父子在江户诗坛能够引导创作风气,规范汉诗体裁,或古体、或律体、或七言歌行,借用中国史典,书写江户汉诗人对本国历史的解读和感慨,以古文辞成章,聚合古今诗法,叙说或悲壮或婉转的日本故事,从而展现出古文辞诗派的复古诗风的创新发展。
二、突破家风的新探
服部南郭是江户前期较早出现的专业性质的汉诗人,他在荻生徂徕门下一心创作汉诗,追求诗作的独立性,进而推进了江户儒者汉诗创作的革新进步。然而身处儒学名门,服部南郭未能淡化儒学者身份,其汉诗创作大致遵守礼乐之本。诗作多展现其身为儒生欲施展抱负的期望以及失落,亦掺杂其追求隐逸放达的心志。“宦迹知何态,诗篇会有真”(《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三《春日偶作十首》其五)[4]357,这是南郭以汉诗作为人生事业的寄托;“薄俗从佗恶,腐儒私自怜”(《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三《秋日书怀七首》其二)[4]361,又表现出身为“学而优”者的不甘;“吏情顾笑为何趣,一醉沧州不可求”(《南郭先生文集初编》卷四《月夜忆子和》)[4]393,其中更有诗意生活的适意放达;“草根求服食,松韵拟观涛。僻性终难化,时纷暂可逃”(《南郭先生文集四编》卷一《酬答营道伯闻余营小庄见赠》)[5]328,自有一番艰难世俗中的隐者乐趣。
身为服部南郭的弟子及婿养子,服部仲英没有恪守养父的汉诗观念及创作,反而有意突破家门诗风,追求诗作的创新。仲英的诗作并不纠缠于学古家数,重视自得的感悟,而较多为就某事某物而感发情思。仲英曾自言“苟有得于我,虽家风所不必守也”,时人大内熊耳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蹈海集》题尾评仲英诗作特点是“别自出机轴,以为一家”(《蹈海集·题尾》)。[2]398-399对比服部父子的汉诗,可以见到仲英在汉诗创作的个性化、日常化、本土化等方面,皆有新进,显现出不同于其父南郭的诗风,以下分别叙述之。
(一)重视对生活细节的描绘感悟
仲英诗作中的咏物诗占比增加,注重摹写生活事物,这有别于南郭汉诗,更是对南郭汉诗的新开拓。如生活中养鱼、养鹤等细节,仲英能在此中有所感悟而化写为诗,将外物“着我之色”,以我观物,传达出心中有物的清韵诗趣。比如:
不待西江激,乾坤尺水浮。一盆回片石,千里自长流。
岂羡吞舟大,堪同纵壑幽。此中真性足,无意避悬钩。
(《蹈海集》卷三《盆池养鱼》)[2]82-83
忆尔曾同云侣班,层霄今日杳难攀。九皋元自传声远,尺水犹看弄影闲。
敛翼黄昏悲独处,离栖珠树望仙山。不知驯养阶庭下,孰与回翔湖海间。
(《蹈海集》卷四《养鹤》)[2]121-122
仲英汉诗创作的奇特处,在于经常表现生活场景事物给诗人带来的瞬间感悟及活现的生机。比如“屏上丹青卧且游,水光山色思悠悠。一丘一壑能知我,莫是当年虎顾头”(《蹈海集遗·书室屏风边廷辉为山水图赋谢》)[10]41,诗人观画与画中丘壑进行对话互动,山水图的活灵活现与自然生机跃然纸上。又如《木落见佗山》:“风霜黄落冷园林,林外山光入牖深。为是不违颜咫尺,坐疑身在岫云阴。”(《蹈海集遗》)[10]38深秋山色沁人心脾,诗人心魂早已浸润于山中风光,颇有顿悟哲理之趣。此外,在咏写人物题材方面的拓展,也展现出仲英擅长以生活入诗的特点,如:
阿夷偏喜此身闲,松路岩扃断往还。梵宇住来抛粉黛,贝经翻罢浣潺湲。
岂应寒谷期鸣律,遮莫春风不驻颜。何物袅从前岫出,无端忆昨绿云鬟。
(《蹈海集》卷四《山中女僧》)[2]172
诗中描写了梵宇僧尼的修行生活细节,是仲英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社会真实。服部家世代修儒学,同时与僧尼多有交往,关系密切,佛缘颇深。服部南郭早年在江户增上寺前的三岛町设帐授业,指导过耆山、义海、云洞、海云、玄海等多位僧人,后来也常去东海寺少林院举行赛诗大会,与诗僧唱酬甚密。在此亦儒亦佛家风的影响下,服部仲英也常常出入僧院,与海云、正定、丫义等诗僧交往。熟悉僧侣的生活经验成为仲英的汉诗题材,其诗集中颇多与僧人的交游唱和,其诗作则拓展出较之其父南郭更多的对佛教人物及环境氛围的详细书写。
(二)注重个性表现和袒露性情
受到江户前期汉诗注重拟古和表现儒士之志的风习影响,服部南郭在诗作中注重表现儒学者心志,而往往缺少真实质朴的个性情感表达。南郭的汉诗数量远超仲英,但在诗人对生活环境的认知、创作心态与诗作语境的和谐方面,服部仲英则超越了父亲,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比如在仲英诗作中,访友是“下榻携棋局,呼童命黍鸡。回看蹈青处,烟暗野桥西”(《蹈海集》卷三《春日郊行值雨过友人庄》)[2]62,而非南郭的“黄垆开酒肆,青草助诗新。坐爱林塘色,未承城市尘”(《南郭先生文集三编》卷一《春日访友郊居》)[6]53。仲英春游观赏之景是“空山行不尽,数里入烟霞。涧壑春光遍,藤萝栈势斜。林传樵斧声,径逐鹿蹄遐。稍觉仙源近,溪流送落花”(《蹈海集》卷三《春日山行》)[2]80,而非南郭的“步出东门春色开,凤城芳甸五云隈。谁家踏草骅骢马,几处看花鹦鹉杯。羽猎南山通御道,仙游上苑绕灵台。相逢借问刍荛者,莫是文王囿里来”(《南郭先生文集二编》卷三《春日郊行》)[9]114。
仲英行旅诗的诸多描写呈现出情景契合的境界,暗写个人情怀,透露出诗意如画、诗情入景的微妙意境。相比之下,服部南郭的行旅诗描写,大多着意呈现儒者身份及道德意识,使其诗作难以摆脱古文辞诗派的守旧模式。譬如南郭《送东伯通归冈崎》写道:“锦绣追陪五骕骦,三河归客有辉光。八公久让淮南术,大药应传海上方。龙跃风云悬旧色,风来山岳映朝阳。兼将笔札惊乡国,不独君卿家世良。”(《南郭先生文集二编》卷四)[9]127-128视角由此地到目的地,笔力雄厚,笔法繁细。比较仲英的《送申少八归美浓》:“故山西望彩云浮,下有清泉日夜流。归到应逢家酿熟,送君遥想美浓州。”(《蹈海集》卷五)[2]202诗中所写只有“山”“云”“泉”的场景连缀,却将眼前的纯粹之景,及至美浓的生活之物,简单真切地呈现出来,在流畅的抒情中展现了仲英真诚朴素的友情。
不同于南郭温文尔雅的性格,仲英为人个性坚韧而又性情放达。仲英曾经嗜酒成性,成为南郭养子后移居江户赤羽,始行戒酒。其自言:“苟知吾生有涯,不肯婚宦,交无所择,博徒卖浆,逢着则欢。欢则饮,饮则醉,醉则歌,歌则舞蹈,何所不至,傍若无人。窃念亦如是而足矣,而性非上顿之量。”(《蹈海集》卷八《复松叔豹书》)[2]364可见仲英的本性自由不羁,正是这种个性中的率意行事,使得服部仲英在其汉诗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及自由性情。
(三)日本汉诗本土化的加深与拓展
服部南郭与仲英父子以日本历史事件及本土著名人物为题材创作汉诗,这在江户汉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本土化价值和开创意义。服部父子两相比较,南郭诗中已有本土化倾向,但仲英汉诗中的本土意识则明显高于其父。
仲英除了擅长用汉诗描写日本历史事件、人物,还用融汇日本古谣曲的方式推进日本汉诗的本土化。比如他创作的《拟古神乐催马乐辞》《右催马乐七曲·橘妃叹》两首汉诗就被当代日本学者德田武称作“树立独自性的尝试”[11]1029。
平安初期,唐朝传入的雅乐逐渐走向日本化,催马乐即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雅乐包含唐乐和高丽乐,之后配以日本的汉文诗歌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声乐体裁。[12]其中,唐乐由四拍子、八拍子逐渐变化为日本的三拍子和五拍子,这是催马乐日本化的显著特征,随之形成的汉诗创作更展现出其独特的风貌。《拟古神乐催马乐辞》序文曰:
称神其朝乐乎,催马盖出自委巷歌谣。甘美酒食,推谭仆远,彼此为异,古今邈矣。以此视此,昩者不鲜,译此拟彼,其可拟乎?而志之所之,嗟叹永歌以成其俗者,彼此为古,风致同符。今于两部中,择辨可拟者若干首,言拟彼古,意拟此古,仿佛乎此古,而有如彼古者。若夫裁制,经纬长短,一从我杼柚,临机为政。本题多以章首语命之……
(《蹈海集》卷一)[2]13-14
“经纬长短,一从我杼柚”,在《拟古神乐催马乐辞》中表现为:“神之木,郁哉芬,庙门下,箫䜵纷,长锡而荣,青葱欣欣。”(《蹈海集》卷一)[2]14三言、四言组合;“朝出阳明门,车中坠冠帻,头上何得固,短发徒狼藉”(《蹈海集》卷一)[2]16,则又五言呈现;“蟋蟀行行何所求,大木根下学鸟啄,欲穿不穿鸣且悲,盘根固结折其角”(《蹈海集》卷一)[2]16,又如一首七言诗。因此德田武总结仲英《拟古神乐催马乐辞》云:“一、题材为日本古代歌谣;二、并不模仿唐代乐府正文;三、根据歌谣的内容使用多种句型。”[11]1032
结合江户汉诗发展历程,可知服部仲英在尝试着将日本古代歌谣体与中国的乐府诗体相结合,由此探索一种日本化的新型乐府诗体。其名作《右催马乐七曲·橘妃叹》,咏叹《日本书纪》中的动人故事情节:危急时刻,弟橘媛投水以平息海神之怒,海浪平缓后武尊得以顺利归航。其诗序写道:“武王东征,总海风恶,王舟将覆。妃投身,祈请海神,六师无恙。王哀而思之,登山望海作。”(《蹈海集》卷一)[2]19序言介绍了本诗作的缘由。其诗曰:“我妃乎,我妃乎,长与我辞,吁我所美……”(《蹈海集》卷一)[2]19亦是三言、四言杂糅成一体。
三、对萱园诗派古文辞的反思
(一)“模拟”潜藏的创作危机
江户萱园诗派在荻生徂徕及服部南郭主导下修学古文辞,以唐诗为宗,秉持温柔敦厚的汉学规范,服部仲英同样长期受此诗风熏陶。但随着江户诗坛的形势变化,他逐渐意识到汉诗创作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性,对中国的古文辞传统也需要在继承中发展。于是他将日本历史事件及人物故事,创造性地改写融入汉诗创作中,又将江户市井生活中的琐碎画面,结构成富有生气的汉诗作品。仲英在《题习之五言古什后》中提出:“转今为古,古不易为。诗之于古,唐人犹病。诸习之非居汉魏之土,非食典午之粟,有䩄面目。吾大东人也,兹什当今之世,能古其言,宛乎生气?自晋以上,口不知习之何为者,肉汉魏之骨乎?”(《蹈海集》卷七)[2]320-321可见其对于江户诗坛一味“习古”风气的质疑。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质疑,使得仲英对服部家门的诗风传统,既有传承的一面,亦有创新的一面;既有秉持温厚平和性情的一面,亦有活泼个性和独立思考的一面。
江户前期诗坛古文辞派盛行一时,其重视模拟的弊端被后来萱园诗派的传人逐渐摒弃。服部仲英的汉诗创作显示出对萱园诗派模拟弊端的批评与克服,这在当时颇有响应者。比如汉诗人大内熊耳也曾明确指出:
自徂徕先生唱古文辞,推李王,海内风靡之士,仰李王为日月矣,而诸家皆掩焉,即大家若韩柳,亦犹蔑如也。则可谓高矣,而从二子,于其所好学之,则步步趋之,唯其似是先,甚则袭取其句语以成篇章谓技,莫以尚于此矣。高则高矣,唯是株守一家,不博涉于诸家则袭。犹虾在斗,终日选之,卒不能出其域,枯而浚已耳。且夫苟唯此是先,无自立辟,恐骈故失之,有如邯郸之玉,蒲伏而穷者也,识过师犹有让于德焉,况于出村为下奴隶者乎。
(《蘘园集前编》之《熊耳余承裕撰并书》)[13]
对明七子汉诗的过度推崇,使得日本汉诗创作受到局限,难以表现出更多的本土内容和生动趣味。而过于强调“无自立辟”,也会束缚汉诗的健康发展,江户汉诗创作的活力就会被抑制。服部仲英的汉诗改革,就是在看到这一时弊后而进行的突破家门诗风的改革,这对江户诗坛而言无疑有着开拓本土新境的突破性价值。
(二)探索自我价值的主体意识
汉诗规范化的创作定型之后,历代东亚各国汉诗人在长期固定的模式中不断消解着自由个性,因此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各国汉诗的发展活力。于是谋求从汉诗规范中解脱,在汉诗人主体身份体悟中发现汉诗创作的意义,就成为东亚各国汉诗创作生命力的持续显现。日本汉诗的发展过程也同样如此,服部仲英及宫濑龙门等人对汉诗人主体价值的彰显,就成为萱园古文辞学派继续更生发展的必由之路。
服部仲英没有辜负南郭对其传承家业的殷切期望。在亲生儿子相继去世后,南郭挑选能够以南郭之女为妻的“冒服氏”(改姓妻家姓)的后继者,担起“专向诸侯讲学”(《服部文库目录·序言》)①早稲田大學図書館:《服部文庫目錄》,《早稲田大學図書館文庫目錄:第8輯》,東京早稲田大學図書館,1984年。的家业重任。养子继承制度在日本历史悠久,养子作为“实家”的养子,其责任是延续家业的发展。“去别人家当养子,或者出家做和尚,曾经是平安时代贵族家庭长子以外男性成员的主要生活手段。江户时代初期,出于抑制大名势力的需要,幕府对养子继承有严格限制,造成不少大名因绝家被改易,很多失去主人的武士成为浪人,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时不得不对养子之制解禁。作为延续家业的必要手段,养子继承多了起来,并向制度化发展。”[14]服部仲英接受了婿养子身份,“令翁讲堂之上勿复顾虑,且家人生业及应对赠答一承之,令翁无所与闻,就间乐余年耳”(《蹈海集遗·白贲先生墓志铭》)[10]75-76。服部仲英作为“婿养子”,不仅承担起照顾南郭家人的责任,更是成为继南郭之后芙蕖馆的掌门人。“其子孙至今世住南郭故宅,不坠家声,是古人所稀见也。”[8]410芙蕖馆服部家族历经五代150余年,直至明治时期仍坚持开塾授课、传承汉学。
但是服部仲英并没有继承南郭对古文辞学的偏爱。南郭主修经义,诗学唐明,著《礼仪抄图》《易捷》《唐诗选国字解》等,校《庄子音议》《庄子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唐诗品汇》《明诗选》。南郭第三子服部惟恭(1724—1740)著有《唐音》;芙蕖馆第三代掌门服部仲山(1741—1808)更著有《春秋经传集解》,有《老子书闻》《列子书闻》《世说·左传·学则书闻》《乐府要解抄》等杂记,留有写本《易图》《礼仪标写》《南华经》《诗范》等,均对中国经书典籍、诗学章法有较深研习。唯有服部仲英,作为芙蕖馆第二代掌门,仅有诗文集,而无经籍汉学论著传世,这在服部历代掌门中显得特立独行。对此仲英在《复宇和岛侯书》中这样解释:
非敢有意以吾技于王侯,私自顾念,庸劣鄙琐,无干事材,碌碌为人世无用物。天之爵我以之,安而受焉……且白面生,书臭袭人,雄窃所厌。孟子游事齐梁,动作养望,务崇其道,愿欲人君由是敬我。战国游说之世,盖有不可已之势,然亦足以窥其技俩矣。至于圣人,温良恭俭让,岂有此气象乎?缝掖之徒,率无其实,妄贪虚誉,小窥圣籍。不知之为知,傲然抗礼王侯,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者,自雄观之,与彼浮屠奉佛,缮饰其教望,愚夫愚妇崇信之者,何异之有……
(《蹈海集》卷八)[2]375-376
在功用化的江户养子制度下,为继承门面、讲学诸侯,仲英必定要修习经义学问,但他并不将经义学问奉为圭臬,而有重视“实”学的倾向。这种求“实”的态度,必然影响其对古文辞派模拟学风诗风的抵制,并将描写现实世界、体现个性真情汇入自己的汉诗创作中。
萱园诗派传人中除服部仲英外,宫濑龙门(1719—1771)以其个性自由、才华横溢而得到服部南郭的赞赏喜爱,但最后却遭同门嫉妒而被迫离开。他直言:“修李王之业,其旨与之同,而驰骋骤步,别占一格,与当时诸家异之趣向。诸家极力锻炼,潜思字句,将造请其精微矣。龙门乃不然,为诗若古文辞,随题命意,遇境遣辞,意在笔先,下笔成文。志之所至,辞必至焉,操舍如意,纵横自若,未始焦神极虑。”(《先哲丛谈后编》卷六)[15]这表现出江户才子诗风的放任个性。作为同一时期的南郭门人,宫濑龙门在汉诗创作上的不拘文辞,意达神通,实与服部仲英有着惺惺相惜的共同之处。
四、结论
江户时代的汉诗创作趋于兴盛,诗社林立,诗风迭变,诗学发达。江户汉诗人中,儒学者汉诗家族尤其是父子汉诗人层出不穷,前后呼应,成为江户汉诗坛引人瞩目的现象,为日本汉诗创作达到高峰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著名的父子辈汉诗人有林罗山(1583—1657)、林鹅峰(1618—1680)、林梅洞(1643—1666)、林凤冈(1644—1732)等传承官学;伊藤仁斋(1627—1705)、伊藤东涯(1670—1736)、伊藤兰嵎(1694—1778)父子以学者汉诗人立身;伊藤坦庵(1623—1708)、伊藤龙州(1683—1755)与其后代伊藤锦里(1710—1772)、江村北海(1713—1788)、清田儋叟(1719—1785)盛名绵延;还有中井甃庵(1693—1758)、中井竹山(1730—1804)、中井履轩(1732—1817)共兴汉学教育;青山延于(1776—1843)、青山延光(1807—1870)、青山延寿(1820—1906)父子世治史学;近世更有赖春水(1746—1816)、赖春风(1753—1825)、赖春草(1756—1834)、赖山阳(1780—1832)、赖鸭厓(1825—1859)等,可谓世代相传,家风赓续。在江户儒学者家业继承制度长期存在过程中,汉诗创作深受其影响,呈现出不同家风的诗作特色,并透露出日益明显的本土因素及价值。萱园学派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江户前中期的汉学发展及汉诗文创作方向,其中服部南郭和服部仲英的传承及变异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显示出古文辞学派的兴盛及本土化转向。
服部南郭之后,如何打破汉诗创作“言必有典”的旧习,直接表现外在真实与内在自我,成为汉诗新变的发展方向。“唯是徂徕夫子序郭翁稿于其诗曰:刻意于鳞,岂弟过之。余于仲英于郭翁亦云:而尚之以隽永有味,则不翅岂弟过之,是为一家也。”(《蹈海集·题尾》)[2]400-401服部仲英作为服部南郭的弟子及婿养子,对讲学以延续家业的重视、受身边文人张扬个性的影响、与僧人频繁的交往,使得他在汉诗创作中少了些儒学者的书袋气,增添了江户市井生活的情趣,使其汉诗创作在继承南郭儒雅风格和唐诗典范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日本历史事件人物的本土化内容,借以表现当下生活及具体感受,体现出汉诗创作与个人生活和本土语境相融的诗学思考。其“聚众美以成大者”的诗学主张,正是萱园诗派拟古规范日趋松弛而清新性灵诗风逐渐兴起的先导,同时也反映出萱园诗派内部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著名学者日野龙夫论及日本近世诗风之变时指出,“切合现实掀起了新的诗风。这种诗风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用日本本土材料承载思想,即和习的正当化,另一个是针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即对现实的关心。”[16]从服部仲英继承和发展南郭诗风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探索汉诗创作中的和习正当化,追求汉诗创作中的描写真实,正是这样的变化方向,使得萱园诗派内部产生了孕育新体汉诗的创作动力。
综上,服部南郭的婿养子服部仲英在延续家业的过程中,呼应同时代汉诗人意识的觉醒,以写“真”和赋“实”给江户汉诗带来了超越拟古的艺术魅力。江户汉诗由萱园儒学古文辞派,到后继者的反思变革,寻找到了汉诗本土化与贴近现实的创作方式。服部南郭及仲英父子在深化汉诗创作中推动了江户汉诗的多元发展,使得汉诗创作在江户诗坛走向全面成熟,形成了日本汉诗的本土特色,这是服部父子汉诗传承变革的特殊价值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