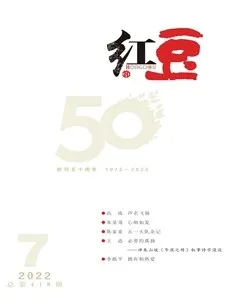必要的孤独
2022-12-29王迅
进入朱山坡的小说世界,你会经历阅读不畅的过程。随着阅读推进,一个又一个疑问会接踵而来。就短篇小说《午夜之椅》(《天涯》二〇二〇年第五期)来看,“我”与芳、琼、莹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之间存在怎样的情感纠葛?那把沙发椅竟然可以使人的情绪突变,如此奇特,如此魔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些疑问,在未读完文本之前,我们在欲说还休的叙述中,确实有些理不清。但随着叙事的铺开,我们会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不能自已,越来越为作者的发现拍案叫绝。这是我读朱山坡小说的审美体验,也是我看好朱山坡小说创作的理由。这种阅读体验根植于短篇小说诗学空间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山坡把小说当作诗来写的艺术探索,发扬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化传统。
从小说结构来看,这篇短篇在“我”与三个女性之间展开,看似讲述寻常的婚变故事,但细究起来,你会发现,它所显示的不止于那种俗套的都市情感故事,而是在情感纠缠中蕴含了关于精神归宿的终极追问,寄托了作者对人生境界或精神层次的思考。朱山坡的先锋气质及其“朝着经典写”的胆魄,决定了这篇容易陷入通俗婚恋叙事的短篇小说的写作难度。短篇小说是朱山坡近年来主要经营的文体。他追求“最纯粹、最干净、最接近诗歌的语言”(朱山坡:《文学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读者的参与》,《文艺报》二〇一五年五月十日),这种小说语言往往使小说的叙述看似平静如水,而在文字深处却潜伏着惊涛骇浪。诗化叙事也是朱山坡同乡林白所孜孜以求的。其实,翻开小说之际,作品标题就使我想起林白的中篇小说《回廊之椅》,这篇一九九三年发表在《钟山》杂志的中篇小说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小说中的标志性作品,曾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姨太太朱凉与七叶主仆二人同床共枕、相亲无间。该小说通过唯美的叙述构筑女性乌托邦,把娇艳、妖媚的女性之美渲染到了极致。林白以回廊之椅的宁静神秘反衬男性世界的暴力动荡,试图去解构那个冷酷、狰狞的父权制“菲勒斯中心主义”。作为短篇小说的《午夜之椅》当然没有这种性别意识形态诉求,但其叙事张力的构设却与《回廊之椅》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朱山坡的叙述语言是节制的,甚至显得有些拙朴。他不愿意像林白那样极尽铺排之能事,因为他知道短篇的任务,就是以极简的话语洞穿现实生活的秘密。
稍稍清理人物的情感踪迹,可以发现,该小说除了讲述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在男主人公情感生活中还隐含着丰富的精神层次和心理层次,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的次序可以简括为:交易→占有→融合。芳将那把沙发椅连同“我”一起卖给琼,以换取智障女儿的治疗费用。爱情对于芳来说,不过是一场交易。而“我”和琼看起来如胶似漆,相见恨晚,其实两颗心却是疏离的,表现为一种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琼不懂画。她只是崇拜书生。或者说,谈不上崇拜,只是她能把一介书生掌握在手里觉得有安全感而已。每次以她为模特,画到最关键的时刻,她总是露出小市侩的浅薄来,让我大为扫兴。”显然,琼并非“我”所追求的理想对象。只有莹,这个具有古典气质的女性,才能与“我”达成精神契合,是“我”画作的真正欣赏者,正如“我”所虚构的那幅奥运题材画作中手执火炬的少女,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所以,“我”画的很多仕女都以莹为模特。更重要的是,莹把“我”从一个流浪汉改造成了爱情饱满、踌躇满志的男人,这个过程是芳和琼所不曾见识的。可是,这样以精神相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爱情为何也陷入了困境呢?你可能以为,原因在于“我”折腾的生意均以失败而告终,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其实并非如此。可以说,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她之所以能成为仕女画的最佳模特,就是因为她对物质的拒绝,抑或说她是古典诗意的化身。这一点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得到印证:“你不能跟烟火味靠得太近。会熏死你的。”尽管莹后来被一家广告公司所骗,离“我”而去,但她对作为画者的男主人公的劝告却无疑是出自内心的,而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对所有艺术家的告诫?
在一篇短评里,我曾把朱山坡的小说归结为一种“诗小说”,而如何赋予小说以诗性的空间,写出诗化小说呢?我以为,象征和暗示当是必不可少的修辞。如果说沈从文、废名是现代诗化小说史的开山者,那么,新时期以来,汪曾祺、何立伟、残雪算是小说诗化艺术追求中的杰出代表了。从史学意义上来讲,朱山坡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的确,象征和暗示是朱山坡短篇叙事的重要策略。就《午夜之椅》而言,那一把神奇的沙发椅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意象,因为这个意象统摄或主导着叙事的精神空间。这是一把神奇的忧伤之椅,之所以神奇,是因为作者赋予它一种特异功能,任何人,只要心中有忧伤,坐上去情绪就会失控。与这把椅子相匹配的主人必然是多愁善感的,而琼显然不属于这类人,所以她要为它寻找新的主人。同样,尽管芳经受着家庭的分裂之苦,属于不幸之人,但也“劝我扔掉它(椅子)”。芳与琼,虽然在身份和处境上有别,但显然,这把椅子对她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同于她们生活中的“异物”。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女性对椅子的态度,也暗示了她们与主人公的精神距离。
同时,小说中沙发椅又是一把心灵之椅。“我”之所以无法离开它,是因为要借助它画出人的忧伤。哪怕是古代仕女,在“我”的画作中也无不带有忧伤之情。关于椅子之于画者的神奇功能,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他们(前来画像的人)兴致勃勃地站在我的面前,一旦坐到椅子上去便慢慢变得深沉,继而露出悲伤的表情,我再三提醒也无法让他们恢复喜悦和甜美。因此所画的画像无一不满脸忧伤或哀怜,仿佛是被画者刚刚丧亲,或已经知晓大难临头、厄运将至。而一离开椅子,他们便恢复常态,恍如刚从另一世界脱逃归来。”这里描述了被画者坐在椅子上或离开之后的情绪变化。椅子魔幻般的神奇功能与“我”的画作风格是一致的。而从椅子与主人公的关系来看,二者在精神气质上也是相通的。所以“我”是这把椅子的真正主人,“我”与它融为一体。小说一再强调,“那张沙发椅的产权必须是我的。这是作为一个画者最后的尊严”。是否可以说,这把椅子充当了画者的精神道具,它与画者的融洽无间,象征着高等艺术的独创性?从隐喻功能来看,画者所画的人物,无论琼也好,一般人也罢,画出她们的忧伤,又何尝不是画者自我境遇的折射,抑或说是自画像呢?
那么,主人公的情感裂变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先弄清主人公的现实境遇,也要把小说中无处不在的隐喻关联起来。“我”从小跟随舅舅学画,而画作是传达理想追求的艺术形式。失去三个女人,意味着主人公艺术追求的流产。一个流浪者的悲哀由此而生。除了莹,没有一个人欣赏“我”的画,不但如此,莹无异于一位艺术女神,是“我”创作的精神支柱,呼唤和催生艺术佳作。而小说开篇第一句却显示:莹跳楼自杀了。这句话为小说奠定了悲伤的基调。不错,朱山坡写了一个悲伤的精神流浪者的故事。对此,作者除了通过椅子的无处安放,隐喻“我”始终被现实所驱逐的命运,还借助三个女性的话语反复暗示男主人公作为现实中的独行者的悲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孤独又是必要的,因为“我”肩负着艺术之神赋予的使命,必须向着更高的精神层次迈进。对此,作者以芳的父亲所说的话加以暗示:“你跟我不一样,你不应该只满足于做一个好人。”而莹的话则更直接,奉劝他远离那些“人间烟火味太浓的地方”。朱山坡通过这样的人性结构图谱,向读者传达了他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主人公的孤独是一种时代焦虑症的表征,更是长期以来艺术家生存的普遍状态:在无尽的精神流浪中摆脱庸俗,走向艺术之圣境。
责任编辑 谢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