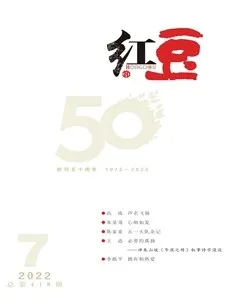高堂在上
2022-12-29唐晓勇
我父母都是乡下人,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之间好像只有亲情,而没有爱情。其实,我父母不懂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就知道踏踏实实过日子,就知道把孩子养大成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父母舍得让孩子读书。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七岁。打我记事起,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有过卿卿我我的亲密,更不用说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缠绵。母亲是急性子的人,稍不如意便大声斥责父亲,父亲并不反驳,总是嘿嘿一笑,默默地把母亲交代的事情做好。
父母亲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结婚的。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碰到不好的年成,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生活,他们把我们兄妹四人交给奶奶照顾后,拉平板车到蚌埠码头去运米挣钱。我家距离蚌埠四十多里路,他们拉着平板车凌晨四五点就要出发,到蚌埠也八九点了。他们的工作是根据客户要求,在集市把大米用麻袋装好,运到船上。父亲控制着车把,母亲在前面用绳子拉,身体用力地前倾,像纤夫一样。平板车一次能运几百斤,每天从集市到码头三四趟,挣得十几元钱,除去早上和中午的生活费,还能剩七八块钱。晚上他们舍不得在外面吃,再步行几个小时,晚上八九点回到家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天要在路上跑十多个小时,他们不停地走,个把月鞋底就被磨破了不说,母亲腿疼得几乎抬不起来。回来的路上父亲就让母亲坐在平板车上,他拉着走。母亲开玩笑说:“这是结婚时也没有的待遇。”母亲怕父亲累着,要下来和父亲一起走,父亲说:“能拉着你走,我走路都有劲。就算你不坐在车上,我也是一步都不能少啊。”
父亲有小学文化。三十多岁时,父亲当上村里的会计,手里掌握着村集体的资金。记得当时有一位卖稿纸的商贩来到我家,给村里带来几十捆信纸,顺便给我家带来一口精美的老式木制挂钟。母亲便在父亲面前唠叨:“公家的便宜咱一点也不要占,湿了毛矣,小了虫矣。”父亲就把木钟放到了村部,作为村里的公有资产。后来父亲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一辈子清正廉洁为群众办事,现在不当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十多年了,但还受到村民的信任。
母亲的身体不好,五十多岁就患上哮喘病,咳嗽得厉害,有时候连着咳,脸色憋得发青,喘不上来气。父亲带着母亲,从怀远的医院到蚌埠的医院断断续续治疗了三年多。每次住院,父亲都从家里拿张竹席,在母亲的病床前一铺,日夜陪伴着。母亲有时咳不出痰来,憋得难受,父亲就用吸管吸。医生说吃乳鸽对母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就跑到几十里外的养鸽场去买乳鸽,亲手炖汤喂母亲。母亲后来患上了肺癌,被病魔折磨,痛苦无处发泄,就无理由地拿父亲出气,经常把父亲端到嘴边的饭碗打翻,热汤洒了父亲一身。父亲并不气恼,一边握紧母亲瘦弱的手,一边抚摸母亲苍白的脸,热泪无声地沾湿了病床上的被单。
母亲离世的前一晚,我们都围在床前。母亲对父亲说:“我平时太好强了,有时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你发脾气,你却从来不生气,受了一辈子的委屈,马上就解脱了。”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大声,我还不习惯呢,还想多听你发脾气。你要好起来,不能先走。”
母亲舍我们而去了,父亲几乎一个月没有合眼,没有说一句话。到“五七”那天,我们兄妹几人为母亲立了墓碑,父亲说:“把我的名字也刻上吧。”
说到母亲,我总想她要是有文化多好,哪怕是初中或小学文化也罢。而事实呢,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有读过书,更不用说识文断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认为她是很有些学问的。尽管母亲去世十几年了,但是她说的很多话常常在我耳边回响。
“眼是孬蛋,手是好汉。”这是和母亲一起干活时,她常说的口头禅。那时候农村还没有收割机,收麦时全靠一家人几把镰刀割麦子。为了抢收,我上小学时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割麦子。刚到麦地,我干劲很大,手脚也麻利,弯腰割一会儿,直起身看看前面还有很多,再弯腰割一会儿,看看前面的麦田依然很长,不禁有些泄气。母亲说:“眼是孬蛋,手是好汉。不要看,闷头干,再长也能割完。”于是我再也不站起来看前面,只顾挥镰割麦。
“孩子,你能行。”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我上初中一年级那年,有一天放学,我和母亲一起下地收山芋。我们收完了一块地的山芋满载而归,我拉着平板车上一座桥。上到半坡时我感觉力不从心,母亲不帮我,却坐在桥头说:“加油!孩子你能行。”我咬咬牙,把绳背在肩头,开始冲刺。就要到桥顶了,腿像灌了铅,肩上的绳仿佛勒到骨里,车子仍停滞不前,甚至还往后退。“危险!”母亲大声说,“孩子,加油!你能行,还有一把劲就上来了。”母亲似乎在看一场毫不关己的比赛。我知道如果车子后退会是怎样的结果,车会翻掉,我也可能摔伤。我感到绝望甚至愤怒,一股冲劲上来,把车子拉到桥顶。我委屈地哭了。母亲帮我擦了擦眼泪,说:“在你危险的时候,我当然会帮你,但是我知道你能拉上来。”每当我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母亲总是说:“孩子,你能行。”就是这句话,激励我迈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坎坷和沼泽。
“力气是浮财,用完还会来。”这句话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说的。要下雨了,邻居家的地里还有很多的庄稼没有收完,母亲总是鼓励我不遗余力地去帮忙,别嫌累。不要吝惜力气,即使筋疲力尽,休息一会儿就又有力量了。在公共劳动时别偷懒,义务植树时忙得满头大汗也是高兴的。力气对于人来说就像美德一样越付出越闪光。
“湿了毛矣,小了虫矣。”我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听到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她好像是说给父亲听的,也似乎是说给我听的。起初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到很拗口。后来母亲解释:“就是小鸟或是虫子身上只要沾了水,羽毛就会变湿,身体也就变小了。”我慢慢琢磨着,母亲是说人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一点好处,否则就会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说话腰杆不硬,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当时是不理解的,心想我们家又没有当官的,为何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呢?父亲原来是村里的会计,后来又当村党支部书记,大概母亲是给父亲敲警钟吧。现在想想,做人的确如此。我现在有时也面临很多诱惑,每每想到母亲的这句话,告诫自己不要把衣服弄湿了。
随着工作调动,我和妻子二〇〇五年在城里买了房。母亲去世后,我几次接父亲到县城居住,他每次都是住不到三天就回去了,说住不惯。他让我把村里的老屋翻修了一下,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便安居乡下。
父亲七十七岁时,身体还好。他养了几只鸡,房前的空地里种了一些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我每个周末开车回老家看他,他都要在后备箱塞一些,说他一个人吃不完,带回去吃,省点钱。
老屋里的摆设和母亲在世时完全一样,只是正面墙上多了一幅放大的母亲照片。父亲只摆弄小块菜园,不再种小麦和水稻等主粮,不过他经常会背着手去地里转转,他说见不到土地和庄稼,心里不踏实,平时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唠唠,傍晚也常去母亲的坟前看看,在旁边坐一会儿。一日三餐,父亲经常做他喜欢吃的面疙瘩,只是常对我说:“怎么就没有你妈做的好吃呢?”
父亲的生活很节俭,我在冰箱的几个抽屉里,严严实实地塞满了鸡鸭鱼肉等荤菜,他却老是吃不完。我说:“冰箱存放食物,时间长了也不好,要抓紧时间吃掉。”他笑笑说:“年龄大了,牙齿也没有劲了,老年人吃素菜好消化。”我知道他是怕我多花钱。后来,我干脆把做好的荤菜带回去给他吃。
女儿去西安上大学那年,我和父亲一起送她到火车站。她就要进站时,父亲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一沓百元钞票,递给她,说:“孙女,在大学没有人照顾你了,别缺着钱。”我惊讶父亲怎么有这么多钱。父亲笑了笑,说:“这都是你平时给我的呀,我每月有四五百元的养老金,你每月还给钱,我一个老头子哪里能花这么多钱?你给的我都存起来了,留给孩子上大学。”
风烛残年的父亲,在乡下守护着他的老房子,守护着他的记忆,守护着他和母亲曾经的时光。转眼又是五六年,父亲就这样一直在乡下守着他的老屋,陪着母亲。
老屋是父亲四十年前亲手盖的,当时村里盖瓦房的还不多。父亲的父亲留下两间土坯房,随着儿女的出生、长大,两间土房显得拥挤不堪。父亲和母亲靠辛勤劳动,从牙缝里抠出一千多元,重新选择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三间明亮的大瓦房。那是我们幸福的暖巢,我们一天天长大,父母一天天变老,那三间曾经令我们自豪的大瓦房,也像父亲一样慢慢衰老、破旧,墙皮开始脱落,屋脊上还长了几棵挺拔的青草。父亲比他的老屋老得还快,父亲是一瞬间突然变老的,一直走路很快的他,忽然有一天对我说:“我腿脚不行了。”我从板凳上扶起他,他却不敢向前迈步,不断地说怕跌跤。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昨天还好好的呀。
CT、脑彩超、磁共振,能查的都查了。一个老专家让父亲自己颤巍巍地走了几步,让父亲抬抬胳膊,又用一根小木棍敲了敲父亲两腿的膝盖,说:“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也就是帕金森病,属于不可逆的,只能延缓症状,有的还伴随面部表情僵硬、走路不稳、手抖等。”我不死心,又连续到上海、北京找专家给父亲治疗。“别再到处乱跑找人治疗了,安心吃药,维持现状,经常锻炼,可以延缓症状的加重。”不同的专家同一个说法。
幸好,父亲并不失忆,过去的事情他几乎都记得,手也不抖,只是腿脚僵直,行动迟缓。我就和他一起回忆过去的事情,卖香油、盖房子、姐姐出嫁、我结婚,还有现在孙女考研了、外孙当兵了,他开心地笑着聊着。我让他手扶轮椅练习走路,累了就自己慢慢坐上去休息。有时我搀扶着父亲,有时故意慢慢丢开手,让他自己走。他很害怕的样子,无助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蹒跚着,像个学步的孩子。摸着他树皮一样干裂的手,凝视他布满皱纹的脸、空洞的眼神,我的眼泪禁不住簌簌而下。父亲,我面前的耄耋之年的父亲,自小他扶着我教我学走路,现在我却要扶着他教他学走路,我是越走越稳、越走越快,他却是越来越不稳、越来越慢了呀。
望着越发苍老的父亲,我任热泪流过面颊,无力擦拭。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