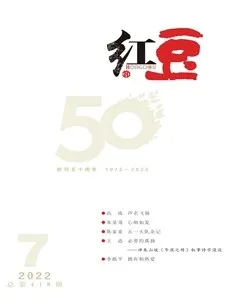五一大队杂记
2022-12-29陈家麦
我年少时,家在五一大队六队胡家里。五一大队在后来恢复了原名,叫后洋村。村北有个小地名叫棺材丘,可见留有土葬年代的烙印,“后洋”意指此地,有着海洋渐变成陆地的遗迹。
池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凡有人居处之地必有池塘,五一大队一口口池塘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太阳光。池塘里的水一来供农民灌溉农田,二来供生活用。胡家里位于村西,是以胡姓人为主的自然村,有两口狭长而相交的池塘。两口池塘边铺了一条石板小路,池塘的前端与入江的支河相连,村民到池塘洗菜、洗衣裳、汲水。那时没有自来水,胡家里的人家从池塘取来水,倒入屋前的大水缸中,放入明矾,沉淀一段时间后,取上部清水作为生活用水。
池塘建有石板拼接的简易埠头。每逢夏天,大人、小孩在池塘里戏水和洗澡,初学游泳的孩子趴在埠头双脚蹬水,抱着一只木桶或木盆练习,一群鸭子在旁边游来游去,不时扎入水中觅小鱼,人与鸭倒也快活自在。碰到大雨天,水漫上埠头,这时下埠头洗涤需格外小心,常有人掉到塘中喊“救命”,被救上来时像只落汤鸡。
胡家里的孩子常在周边广阔的田地里乱跑撒野,以挥发童年过剩的精力。我们那时的食物虽然缺油少荤,但没有那么繁重的作业,书包里只有语文、算术课本。
石板路下面是堆砌的乱石,乱石大多淹没在水下。我玩水时总免不了用手在乱石缝中摸鱼,小手被挤得像压缩馒头,但摸到鲫鱼就忘了痛。有些摸鱼高手,双手像工兵扫雷似的往茭白根部探摸鱼群,那些来不及逃窜的鲫鱼被他们双手紧紧握住,接着被放进鱼篓内。我有时也会拿一根竹竿系上纳鞋底的线,线头捆一枚打弯的绣花针,用这种原始的钓具一天下来也能钓上半桶各种各样的鱼。池塘内的鱼很多,一方面原因是资源丰富,另一方面原因是鱼繁殖很快,更重要的原因是池塘与江河相连,有时台风带来过多的雨水,江河、池塘、稻田里的鱼到处串门,等到洪水退时,不少鱼留在新居住地繁殖下一代。
在闷热的夏天,我选择一口小池塘捞鱼。我不带任何捕捞工具,先游到池塘中间,用四肢把水搅浑,等到塘底的泥浆都浮了上来,那些憋不住的鱼、虾、蟹就跟着泥浆浮上水面张着嘴呼吸,我再用脸盆在水面捞。等到水色有点清了,又再次搅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两个钟头下来,能捞上一桶的鱼虾。全家人一起分享我的胜利果实,脸上洋溢着“一人捞鱼,全家幸福”的喜悦。
水沟
比起江河、海湾,水沟可算是小不点儿。这种水沟有七八米宽,是运河的分支;最窄的可一步跨过。大小水沟分布在农田之间、村前和村后。即便是最窄的水沟,被抽干了水,之后有雨水,沟里也会出现鲫鱼、黄鳝、泥鳅之类的小生命。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小时候的我常常坐在星空下冥思苦想。
我和两个伙伴,三个人赤脚来到齐腰深的水沟,选了一沟段,用泥巴垒起一道高于水面的堤,开始协同作战。我们将堤内的水不断运到堤外的沟段。堤内的水下降的速度很慢,然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和耐性。
堤内的水缓缓地下降,堤外的水在升高,我们不断加固防护堤。因为这种泥巴垒的堤,很容易被堤外的水冲垮。
堤内的水浑浊起来,水浅到脚脖子,沟里的鱼才有动静。再浅下去,那些稍大的鱼拼命地游动起来。水浅到一指深、半指深,鱼儿全都像倾斜的小船,等待我们捕捞。
暮色渐浓,一排排瓦舍飘出炊烟,听到大人在晒谷场呼喊我们的名字。把桶里的鱼分了吧,倒出分作三堆,用“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分出先后,各自拿了鱼,走在归家的田埂上。
渡江
西江就在五一大队的东边,那时的水是“咸淡冲”的,因为潮汐,受月球的牵引,到了关闸后水变清、变淡。
对于准备第一次横渡西江的小孩子来说,需要结伴而游,才会有这份胆量。好在那时西江里游泳的人多,就像一口铁锅里下的饺子。而我打算一人横渡,方显“英雄本色”。
临行前,一个大人跟我说,千万别往远处看,意思是看得远了会感到水路迢迢,失去了勇气。下水时,我挺担心半途脚抽筋,但我反复练习过仰泳和潜泳,万一遇到不测,这两项技艺会救我的命。如此一来,我的胆子大了。我采用蛙泳的姿势,一扑一仰,吸气吐气,用力均匀。看到中心桥洞,我知道已游到江心,心里怦怦狂跳,那是我最害怕的水段。我换成仰泳,头看蓝天白云,身体像块门板似的推进。听到桥上阿爸直喊我的小名,他在桥墩上比画着,我才发现自己偏离了“航道”,呈“之”字形了。我翻身调整成蛙泳的姿势,阿爸在桥上紧跟着为我加油,这是阿爸在给我力量。横渡之举变成小菜一碟,即使遇到腿脚抽筋,我也会自行解决。
雨季来了,西江闸要放水,这是黄岩城内最大的闸。江里洪水汹涌,浪打着浪,向闸口的外江奔去,又遇到平潮时的咸水倒灌,水涩涩的。也就是说,放闸时的横渡西江,好比在海潮中游泳。我采用侧游的方式,以减轻涌浪的冲击。我呛了水,咳了起来,胸腔火辣辣的,我的脸色肯定涨成了猪肝色。过桥的行人停了下来,都在看我热闹,还有人说这小猢狲胆真大。我娘急急寻到了江岸,发现我好好的,连忙把我连拉带扯地带回家。
第二年夏天,全城民兵直渡西江,有几百号人,当中英姿飒爽的女民兵都把枪放在一块插了小红旗的门板上,边游边瞄的样子。直渡的线路从南门的太婆塘口到西门闸,全程约五百米,说是军事行动,非民兵不能参加。这番热闹怎能少了我们?我跟几位小泳伴在后头追。追上了,大胡子连长挥着一只手叫我们滚回去。
夏末,比我大三岁的邻家男孩从桥上跳水,一会儿水面不见了他的身影。我猛扎入水底,双脚踩水把他托上岸。吃过晚饭,他娘领着他上我家,向我一家连声道谢,夸我是救命恩人,还送了两包干桂圆。我轻飘飘地说,不用谢,小事一桩。现在,再没有小孩乱渡西江了。安全第一,千万不要把生命当儿戏。
水井
五一大队处处有池塘,以小队为单元,池塘还兼具浇灌农田和清洗农具以及汲水之功能。但要汲水,还是离家远了些,于是凡有民居处皆有水井。每座大小不一的杂院都有水井,每户人家的洗涤、做饭都离不开井水。那个年代,除了活命的粮食,水井和木柴同等重要。
我们胡家里大杂院有几十户人家,百来号人,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水。水井在台门前,原先有一道院门,后来门被毁了,水井变成巷道口的露天景观。这口井深十来米,井口直径一米多,呈梅花形。水井离阿花姆的房门口不到五步,阿花姆是个寡妇,充当这口水井监护人的角色。对于水井的使用,我们杂院形成了不成文的乡规民约,其中一条是不准把脏物抛到井里,特别是洗马桶时要远离水井。当然,洗菜洗衣服除外,于是水井也成了妇人们述说家长里短的地方。对于井边的遗留物,比如菜叶,阿花姆会主动打扫干净,为此她获得了邻居们的尊敬。
我家位居大杂院西厢房,到水井取水有一百来步。父亲做工回到家往往已到晚饭时间,因此取水的事由母亲承担。她提了小木桶,打上一桶水,一路斜着身走来,桶里的水跟着跳跃,往往溢出不少。等到我少年时,我成了帮手,母亲改用大木桶来和我抬水。抬水时,一根扁担吊了木桶,母亲考虑到我力气小,尽量把绳头往她那边移,这样扁担的重心便集中到母亲的肩膀上。尽管如此,我也吃不消,途中要歇上一脚,换换肩。后来我就要求母亲把绳头逐渐往中间移,表示要分担一半。妹妹长到七岁时,抬水的任务由我俩包了。父母对我俩的这项工作很满意,我俩也得到邻居们的称赞。
孩子们对水井的好感,主要是在夏天。井水温度低,提了一桶水,从头淋到脚,那份痛快是无法形容的。难得吃西瓜,用井水浸泡个半天,咬上一口,透心凉,纯本味的,不像如今用冰箱冰过的西瓜,总有股鱼肉的串味。
水井也是危险之地,特别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在大人没空照管时,会对水井产生好奇。我们常听说别的杂院的小孩子掉下井里,也有大人想不开跳到井里,如不及时被人发现,就会被淹死。所以家长们会拿这些事对自家小孩教育一番。阿花姆真是个大好人,即使在自家灶台上做饭,那眼睛也没一刻闲着,不时瞟向井口,一旦发现有小孩子靠近井边,就大声训斥起来。孩子们很害怕她,一听到她的大嗓门,撒腿便跑。她对我比较宽容。我长到九岁时,对井底下的小生命产生了兴趣,爱趴在井口看,她会过来拽住我的衣领。我会看个半天,井下有青蛙、鲫鱼、鳖、鳗、黄鳝,这些都是从家里溜逃到井里的,从此水井成了它们的栖居地。
每过两三年,水井就要来一次大清淤。有人专做掏井活。掏井前,阿花姆像个小队长,扯了嗓门通知,每户人家往水缸里备足了水。掏完井,把从井里捉住的活物均分了,当然掏井的费用也每户分摊。掏井后,井水甜滋滋的,每户人家提了桶来挑,喜滋滋的。
水缸
在旱季,雨水像金子一般珍贵。胡家里大杂院里的两个女人站在屋檐下寒暄时,往往抬头望着久晴不雨的天空。一个女人说,这老天爷怎么还不落雨哇!另一个女人接上话茬,用带有安慰性的口吻说,快下了吧!
盛夏时,家家屋前大水缸缸沿长出了青苔,缸底的水都快见底了,水中滋生出可用来喂金鱼的小游虫。白天阳光十分猛烈,户外被蒸干了水分;到了夜晚,人们为了乘凉,往天井里泼点水,也很快被蒸发了。井水勉强够大杂院里的居民日常使用,但越来越少的井水水质不好,这样的井水烧成白开水后,会遭人嫌,于是人们渴望能喝上纯净的雨水。
那时候的天气预报不像现在的这么准确,还不能通过卫星云图分析计算出云团飘移的时间和地点。我曾听大人们说,当时的气象站养了些能感知天气的小动物,凭动物的生理反应作天气预测,比如看到蚯蚓从泥地里钻出来,在地上打滚,就判断出不久后要降雨。当然这种土办法,具有一定的经验性,但也会有预报失灵的时候。我家隔壁的宝富婶成了我们大杂院里的义务气象员兼广播员,早上她看到天井里的蚯蚓打滚,就吊起了大嗓门。于是那些妇人把头探出窗外,我们这些小孩子会跑到宝富婶所指的蚯蚓打滚地,捉蚯蚓来钓鱼。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做法,宝富婶通常会制止一下。因为她的天气预报不说整个大杂院里家喻户晓,至少有一部分人知道,而我们的“就地取材”影响了她的口头传播效果。可孩子们动作太快了,蚯蚓很快被我们一抢而空。这时,妇人们迅速行动起来,把水缸底掏干净,用竹刷刷,喊来各自当家的和孩子,全家齐参战,一起用力抬,倒出大水缸的积水。每家空出的大水缸对准屋檐接水口,仿佛都在张开血盆大口,迎接来自天上的雨水,准备大口大口地喝。
果然,日上三竿后,天空飘来黑云团,乌云集合。妇人们都兴奋起来,像迎接一个大节日。我娘嘀咕道,宝富婶不在家。大家都知道她上电影院卖薄荷糖去了。我们村靠近县城,不少农民都有副业。不一会儿,飘起了雨丝。人们期待老天爷进一步施恩时,宝富婶扛着薄荷糖货架回来了,头发有点湿。然而那雨根本不能算雨,大约飘了一个钟头,连地皮都湿不透。屋檐接水口压根出不了水。接着,云开日出。宝富婶只好感叹一番,刚对老天爷骂出半句,连忙收口。我们知道她平日吃素,烧香拜佛。她又扛起薄荷糖货架做生意去了。
真正的雷雨来了,家家的水缸满得溢了出来,灶间所有的大小水缸都满满的。大杂院里的男女老少挤到屋门口,喝起了第一道雨水。有人学了电影中的一个片段,说,又喝到了“家乡水”——天落水。
泡茶店
吃过晚饭,孩子们最怕听到大人们吩咐:去泡茶!这是一件很耗时间又让人等得心头发慌的劳动。黄昏,本属于孩子们的时间,我们被剥夺了这份自由,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干活。
听到我娘这么差遣,我的头立刻大了,要不是阿爸一声紧吼,我还在磨蹭。再不接,阿爸要动真格了,我又要受皮肉之苦了。
我家住在巷尾,我提了三只空水瓶,走了两三百步,才到泡茶店。泡茶店在桥上街中段,是一个巷道的转弯口处。店主姓毛,绰号毛桃,一家七口人,都在店里帮忙,店里店外全是顾客,大多是小孩。毛桃婶手指了指,让我把水瓶放到第三灶。三口灶台上排满了水瓶,大多是竹壳水瓶,也有几只铁壳水瓶,后者一般户主是新婚人家。每口灶台有七八只水瓶,摆放得十分整齐,连转弯的方向都界线分明。户主紧盯着自己的“家人”,用毛笔在水瓶壳上写上自己的大名。我记住了自己“一家三口”的位置。若有户主发现自己的“家人”掉队了,或被加塞了,可立即要求插队。这种情况一般是主人开了小差,回来后得申辩一番,须得到同一灶台的多数户主的允许。有时未获高票通过,泡茶店成为斗嘴之地,很久才能平静。
泡茶的价格分为两大类,按水质分有两档。用明矾滤过的河水江水井水泡的茶,统称为普通茶,每壶茶三分钱;拉水郎从十里外的九峰米筛井拉来的山水泡的茶,称为山水茶,每壶为五分钱。按冷热程度来区分,又分为滚开水、温开水、凉白开,价格从高到低。最便宜的是凉白开,一壶为二分钱,一勺为一分钱,常有口干舌燥的行人咕噜噜地喝了,扔下一分钱了事。也有街坊私下里说,毛桃的凉白开是做了手脚的,因为自己在半夜里往泡茶店的门缝里偷窥,发现毛桃往凉白开缸里掺未烧过的水。这在当时属于弄虚作假,好在人们没将这事闹大,否则毛桃会没好果子吃。但街坊给毛桃背地里“恶搞”——毛桃开水,吃了要死。现在想想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犯红眼病,看到他的店在整条街别无分号,按今天来讲,属于垄断企业;从另一方面来讲,泡几壶茶要等这么久,街坊们怨气太重了。
泡茶排队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两三个小时。有时,一户有四只水瓶,轮到第一灶水开了,给灌了三瓶,余下一只瓶只好等到第二灶水烧开,还得耗半个小时,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一天晚上六点半,有线喇叭播完了新闻,我的“三口子”终于灌上了茶。几百米的街只有三盏路灯,分别在街头、街中、街尾,灯泡功率不到五十瓦。我右手提了两只水瓶,左手拎着一只水瓶,斜着身向灯光渐暗中走去,不时换手。就在这时,我摔了一跤,打碎了一只水瓶,滚烫的茶水洒了一地,我大哭了起来。路人没有问我摔痛了没有,被烫伤了没有,而是问瓶胆摔破了没有。我不敢回家,大约半个钟头后,我娘寻了来。自然她为一只碎了的瓶胆心痛,听说要一元多钱,也为好不容易打来的一壶茶白白地成了“扫街水”而惋惜。好在我娘还是问了一下,有无烫伤脚?
我还是有点不敢回家,怕挨阿爸的门闩杠。我娘拍着胸说,没事的,有我在呐!
掇瓦
五一大队到处是砖瓦结构的两层楼,一排排民房,黑瓦像鱼鳞一样叠加着,自上而下,从屋栋到屋檐,排列得错落有致。黑瓦中有垂直的一指余宽的排水沟,像长发女子梳出来的一条清晰的头路。这么多瓦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如无数黑色的小精灵,与我们朝夕相处。
瓦片的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用来防水、排水,保护木结构的屋架,给楼上的房主晒东西。比如主妇在临窗的瓦片上摊了一张团箕,放上受潮的被子和鞋帽,或是豆子、番薯条等,给它们晒晒太阳。此外,瓦当既起着保护檐头的作用,又增加了房屋的整体美感。
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头,古人称为瓦当,即瓦面上带有花纹的圆形的挡片。瓦当是古代建筑的重要构件。我看过房主曾是大地主的宅院的瓦当图案,有云头纹、几何形纹、动物纹等,繁复又精致。
晴天,胡家里大杂院里的住户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即不可在楼上乱倒水,需要倒水时,最好先瞅准楼下有没有人,或是倒之前先吆喝一声,做个提前预告。可是一些房主为了贪图方便,或是一时忘了,随手将一盆洗澡水顺手泼向瓦顶。这时正好有人从瓦檐下奔向天井,给兜头浇了一盆水,不仅吃了眼前亏,还被认为沾染了晦气;或是站在屋檐下正在唠家常的两位妇人,忽见雨从天降。水已泼到人,除非泼水的人认错态度好,否则会招来恶言恶语,男人甚至拳脚交加,女人则互揪头发,演绎一出邻里“战争风云”,最后由村委会主任来调停。
下毛毛雨时,一顿饭工夫,瓦背上的雨水凝聚起来,形成一股股细细的水流,从屋顶流向瓦头,滴到屋檐下的水缸里,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有如弹琴;中雨一来,瓦檐上的雨水眨眼之间流出,其声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暴雨时,瓦檐上的雨水持续不断,有如洪水猛兽从峡谷中奔出。三九严寒,屋檐下挂起了一根根冰碴子,坚硬透明、晶莹发亮。
日子久了,瓦片也有“生病”的时候,一家屋顶的瓦片阵中有数片瓦,或是被台风掀了,“错”了“骨骼”,排列的次序发生混乱;或是房主晒东西时不小心踩坏了当中的瓦片,瓦顶“缺胳膊少腿”,雨天排水受阻,甚至往屋内渗漏水,害得家人睡觉不安生。一般来说,每家的瓦片通常一两年来一次小修小补。有不少男房主会换瓦或修瓦,会过日子的妇人也会上屋收拾瓦片,我们小城里的人称之为“掇屋瓦”,“掇”是“拾掇”的意思,即收拾。也有技艺不精却自作聪明者亲自“掇屋瓦”,结果到了下雨天,屋里漏水反而更厉害了。于是只得请掇瓦匠了,稍大的工程得有一个师傅带两三个徒弟来做。我感到很惊奇,这些掇瓦匠在屋檐上行走如飞,像武侠片中的黑衣夜行者,他们知道瓦片上的哪个部位可以轻走,哪些地方可以重踩,而瓦片却安然无恙。这种活一般一日半天就成,房主管顿酒饭,给师傅们分别送四五角一包的上等烟即可。当然我们这些久未吃肉的小孩子也趁此开开荤,似乎盼到了一个节日,一家大小都有点喜洋洋的。
土灶
今天用燃气灶做饭的人,很少见过缸灶,镬灶只在乡下偏远地区才能见到。缸灶比镬灶简易,在瓷缸上开个方形的缸门,用来添加柴火,上头放口铁锅,就可以煮饭、做菜了。因为没有烟囱,做饭时,屋内浓烟滚滚。
镬灶就是土灶,或叫老虎灶,镬即锅也,一灶两镬,中间还嵌有一口小铜锅,又叫热水锅,利用炉膛内柴火的余热,变废为宝,在煮饭烧菜的同时,将小铜锅内的水煮沸,用来泡茶。镬灶上的灶台有一丈余宽,用来切菜和搁盆碗盏,冬天时可将炒好的菜放在灶台上保温。灶门边配有一个风箱,拉风箱的活常让放了学的小孩子来做。主妇站在灶台前,无小帮手时,主妇两头兼顾。在那个年代,镬灶是经济条件中等的人家才用的,一般请来会点瓦工的师傅,做一两天的活。请砌灶师傅还得管人家酒、饭、烟、工钱。所以,家境不宽裕的人一般不砌镬灶,除非儿女成家时才考虑砌一个装装门面。
缸灶是最原始简陋的,市场有现成的,日杂公司也有出售,不需要凭票供应,甚至自家买口水缸,让补缸师傅凿出一个缸门即可。
缸灶烧的是木柴,没有风箱,所以一般一家配有一只火滚。“火滚”是台州方言,竹筒形,长一尺多,就像水烟筒。“火滚”一词就是用风吹得烟火滚滚。一顿饭菜未成,屋内早就烟雾弥漫,直到柴火透旺时才散开。
烧缸灶的重头戏是引火起燃,没有金刚钻可不敢揽瓷器活。想想只有一方缸门,上头铁锅压着,如泰山压顶,缸内空气几乎不流通,光凭几根火柴来引,这火如何引得?火柴用两根以上,会招来母亲的问责。母亲能用一根火柴就把木柴引燃。她先找来一张废纸,再将缸门内的四根白萝卜般粗的木柴棍或柴爿,呈十字形叠起来,这样有了足够的空间,然后在十字形柴爿下铺松枝。啪的一响,火柴一亮,点燃废纸,废纸引燃松枝,松枝火开始烘燃木柴棍或柴爿。这时她得拿着火滚不停地吹,我看到母亲的两腮鼓了起来。
父母干活忙得顾不了家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自己动手烧缸灶做饭,丰衣足食。第一次烧缸灶,我浪费了十来根火柴,屡次燃火不成,肚子饿得慌,而又非得把这事做成,否则愧对空肚子。因为母亲言传身教过,又亲见了母亲的烧火过程,多少积累了点理论知识,两三次失败后,我终于把火引燃了。等到饭快熟时,母亲归家,哈哈大笑,原来,她笑我成了小黑人。我往水缸里一照,果然脸都是黑黑的。我也笑了,是胜利之笑。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这种功夫逐渐练得炉火纯青了。我发扬传、帮、带的作用,带会了妹妹,形成谁有空谁来烧缸灶的约定。当然,我们也不忘在烧火的同时,往炉膛的灰堆中埋几个番薯,尝尝煨番薯的味道。
煤油炉
我爸、我娘开了一家裁缝店,到了青黄不接时,他俩就回第六小队当农民、记工分,我爸记八分,我娘记六分。等到了凉秋,他们再做裁缝,属于亦工亦农的角色。
相比那些笨重的缸灶和固定不动的镬灶,煤油炉属于家庭烧饭做菜的一种轻便“武器”,小巧玲珑,易于搬移,像行军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煤油炉风靡一时。
煤油炉体积跟今天的懒汉炉一样,但重量比后者要轻得多,这是因为煤油炉的材质是薄铁皮,有正方形、圆形两种,有大、中、小三种规格。煤油炉由三部分构成:上部像人的头脸,装有支架,一般有四个支架,支架上可以放置中、小铁锅或铝锅;中部像人的心胸,即为炉膛,外装人工调节开关,内呈圆柱形,环绕着十多个棉芯头,点火后棉芯头吸油燃烧;下部像人的腰肚,有大腹便便的储油罐,连着盘根错节的棉芯,棉芯头的油料来自此“大本营”,输送油料时得提起中部串着长棉芯的“腰”。
在我们五一大队,除了土灶,还用煤油炉做中午饭。尤其一些手艺人,忙时一日三餐用这种炉灶在店内解决,闲时只做中午饭。我爸在五一大队街上开裁缝店。有了煤油炉,店铺里无须再砌占空间的镬灶,或屋角堆放乱糟糟的柴草。在五一大队我爸与我娘是手艺人,夫妻搭档。店铺内有只煤油炉,我们兄妹放学回来,我娘在店里生火做饭,一般半个多钟头就成。
烧煤油炉,人们最早用轻柴油做燃料,我记得凭票供应是每斤四角左右。当人们觉得肉痛时,改用重柴油,凭票每斤一角左右。于是在居民的粮票、布票、肉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中,又多了一项——煤油票。
可是重柴油不比轻柴油质量好,前者产生的烟雾多,引燃速度太慢。特别到了隆冬时节,重柴油会被冻住,人们在炉周边泼点热水,或用引火纸来烘烤,让冻油融化。而被冻僵了的十多支棉芯头,主人得擦掉几根甚至十来根火柴才能点燃,于是人们又想到用废报纸来引火。重柴油杂质太多,煤油炉容易积垢,供油棉芯常常堵塞,得隔三岔五地清洗煤油炉。这一系列的工作先是由大人承担,等到孩子们学会了,孩子们就负责清理炉子。
最难的一项活是拔棉芯头和穿棉芯头。棉芯头用久了,由长变短,等到火力弱小时,不是棉芯头缩成跟孔洞一样平了,就是缩进洞孔里不出来了,这时需用眉钳来拔,很费时,而且动作不可过猛,否则连一点“游丝”都找不到,只有用力到位了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碰到回天无力时,只好重穿棉芯了,将老棉芯从底部倒拔出来重新穿上。如果棉芯已被烧短接触不到油料了,得换新棉芯了。这种活,我当年学了一手,如果今天让我重新来做,闭着眼睛都会。
奇怪的是,在我味觉的记忆库里,还保存着重柴油的气味,以及另一种气味——那是我放学回来,老远就闻到煎带鱼的香味。在炉上架上一口小铁锅,我娘手拿锅铲翻着鱼,带鱼滋滋地冒出油花,酱油、蒜、酒、醋的香味跟鱼香混在一起,向四处飘散……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