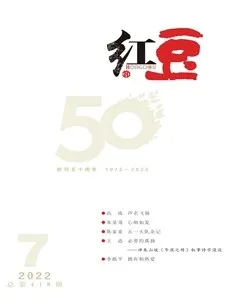从心生呼啸到自由舞蹈
2022-12-29张世勤
1
我跟作家们交流时,曾说过“文学是似是而非的路标,生活是似非而是的抵达”,这句话被大家认为是金句。这说明大家有同感,认可这个说法。这句话我主要是针对小说创作而说的。在我的理念里,生活是没有道理的,如不加深究,一定会呈现出一种热热闹闹的混沌状态。那么文学怎么办?文学能否给出一个清晰的蓝本?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其实,生活再怎么混沌,也一定有它内在的逻辑,只要找到它的规律,你就可能发现一应的生活细节都是严丝合缝的,所有的一切都有来龙去脉,遗憾的只是我们当下具备火眼金睛的作家少之又少。不是不努力,是学识和素养、心胸和境界、能力和眼光、思考和揣摩都还达不到。当然,另一方面,能够给出答案的文学,又不见得是好文学。这也正是文学创作的吊诡之处,或者说,这也正是文学自有规律和尺度的结果。
当下文学落后于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生活日新月异,人们已乘上高铁、飞机,甚至已经搭乘宇宙飞船。尤其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已将空间无限压缩又无限拉大,已将时间任意抻长又任意缩短。许多曾经不好解释的事物或现象,已被科技轻松提溜进了科学认知的范畴。多维空间的叠加和宇宙光谱的渗透与照耀,让原本枯燥的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和活泼。相反我们的文学基本上还是那驾自先秦沿袭下来的老牛破车,好一点的算是马车,能开上高级轿车驶上现代高速公路的并不多。甚至当下一些炙手可热的一线作家,将来被埋进垃圾堆的一定大有人在。
2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就诗歌成就而言,细数也不过那么三五个有代表性意义的时期。从《诗经》和《楚辞》开始,至汉赋,至唐宋诗词,至民国期间,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诗,都可视为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主要成就在小说和散文。在改革开放初期,诗坛以朦胧诗为代表,在与小说创作日月争辉中并未落下风。但自此之后,诗坛虽有众多主义盛行,但都只在声量上形成嘈杂,未能在文本上实现超越。
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虽然是为写小说直奔中文系而去,但诗歌浪潮的冲击,还是让我身不由己地混迹于校园诗人之中。毕业时,由我的老师、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先生作序,我出版了诗集《情到深处》。工作后我也出版了一本诗集《心雨》。去年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旧时光》。但我对这些诗作却少有满意。诗歌比不上我的散文,也比不上我的小说。
当下所谓的文学疲软,首先是小说的疲软,其次就是诗歌的疲软。对其他文体的探讨意义终归不是很大。在文学创作各体裁门类中,诗的门槛貌似最低,仿佛只要把正常的句子折断,搞得参差不齐就行。所以当下最大的创作群体(网络文学除外)就是诗人,文坛中很大的一个坛,是诗坛。其实诗对作者的要求最高,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单单分行肯定是远远不够的。用最节俭的语言,三笔两笔即勾画出场景,制造出情绪,让熟悉的词汇变异,让新鲜的意象飞舞,让认知抵达真相,让情感形成风暴,没有第三只眼,没有第六感,没有第十一维的能量,是很难达到的。
3
病毒都知道变异,难道文学不知道?其实,整个文坛要求“变异”的呼声很高。一方面,大家呼吁创新;另一方面,大家对创新的包容度却又低得可怜。一般的编辑,大多还是认准传统的文学模样,稍有“变异”便觉不适。倒是对功成名就的大家、名家,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不管文本实际如何,总有评论家一哄而上,谄媚叫好,表现出了最大的包容。其实,大家、名家之所以是大家、名家,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实力达到了自己创作的巅峰。有一些能够始终保持着超强的创造力,以良好的创作状态,以高质量的创作文本,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继续着自己的引领;也有一些人,明显已经力有不逮,只能在一定水准上惯性滑行。
面对当下诗歌创作的失向和失质,有人希望能把科学家、工程师、智能技术人员等引进来,以图改变现状。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很悲哀。那些人如有诗情,自会加入到诗人队伍中来,根本不用你去引;如无,各司其职,才是正道。拉郎配,显然不是高招。
去年因疫情困坐在家,我读了若干书,生发了若干思考,并重拾诗歌表达,写下了若干断行文字。这些文字,反复打磨,但一直未往外拿。我把它们分别归类进了《古典诗空》《时光之吻》《故国神游》《庚子诗草》几辑之中。这些文字,与我过去所写已有很大不同。不同并不代表一定就好,它需要编辑、读者和专家去评判和鉴定。
我渴望心生呼啸,更希望能做到天地通透、自由舞蹈。但想是一回事,呈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艺无止境,文无最好,我唯有苦心求索,躬身笃行。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